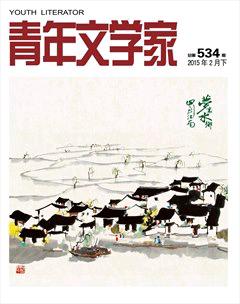司馬遷作《史記》宗旨闡示與其父子的學術路線
摘 要: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談其作《史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三句話除了陳述其著作宗旨外,還明示了司馬父子學術研究的思路與途徑,即發乎子、觀乎史而成于言。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宗旨;學術路線
作者簡介:黃艷燕,女,1978年出生,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古代文學,現為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文化與傳播系文秘教研室主任。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6-0-02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談其作《史記》的宗旨為:“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東漢《史記》成書以來,千百年間,論者的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在對“成一家之言”這一句話的理解上。結合司馬父子的學術行實與成果來綜合考察,這三句話的關系應當理解為司馬父子學術研究的三大步驟設計,概而言之,便是發乎子、觀乎史而成于言。
一、發乎子——究天人之際
司馬談是漢武帝初期的著名學者,其留存而貢獻于世的便是《論六家之要旨》。在司馬談之前,可謂學術盡在諸子,若欲行學術之路,百家雜說首當其沖,難以規避,必于百家雜說之中,或有所選擇而適從,或有所闡發而建樹。司馬談在百家之言中爬羅剔抉,擇其“務為治”的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概括其要旨,研判其短長,終至崇尚黃、老之學,以為“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1]1772司馬遷于《太史公自序》中將其父《論六家之要旨》錄入并加以闡發,恰恰是承繼其父完成的學術歷程的第一個階段為自我學術的開端。
諸子之學于漢初時本為核心學術,其學術最為重大的課題便是天人關系,即天道與人事的終極關系的探討,其起因在于漢之前的兩大王朝,商代崇神鬼,周代重人事。人類于社會進程中的能動性的日趨彰顯,為漢代統治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的確立提供著討論和選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司馬遷便以此核心命題指代思想與理論的探求,以“究天人之際”稱代其父的理論探討與思考、歸屬與建樹。司馬遷之為《太史公書》便是承其父未竟之事業,將其父子學術推向又一階段。司馬談臨終耿耿憂懼于“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其諄諄期待令司馬遷“俯首流涕”承其所望:“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1]1781其父子所言均以“論”言治史之事,足見其為“史”之旨在于思想與理論的闡發,即所謂“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1]1781體現出為史的目的性所在,也是《史記》的本質意義所在。
二、觀乎史——通古今之變
司馬遷之治史是以其父理論探求為前提而進入父子學術的又一階段,即在既定的思想基礎和理論視角之下對歷史的觀照,從而實現思想的歷史驗證和理論的系統闡發。
司馬遷曾引其父之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而能紹明世,正《易經》,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并頗為動情地說:“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1]1777其意所在恰是于五百歲后“繼《春秋》”,他在與壺遂的討論中,明確地闡述了孔子作《春秋》意圖在于“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 [1]1778的理論建樹,孔子的一句“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1778恰是司馬遷“意在斯乎”的真切意義。一如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所說:“遷著書最大目的,乃在發表司馬氏一家之言,與荀況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質正同,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發表耳。”[2]231
綜觀《史記》于史實的記述中時時處處彰顯著思想的結論和理論的意圖,如對漢初七十年與武帝即位后的政治進行了有意識的對比:
“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 非遇小旱之災,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 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充溢露積于外, 至腐敗不可食。”[1]436而 “自是(武帝登基)以后,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興利之臣自此始也。”[1]437這里對漢初推行與民休息政策而取得的顯赫成績給予充分肯定,而對漢武帝即位后, 實行了一系列多事擾民的舉措予以否定。
在吏治主張上司馬遷肯定“奉職循理”的官吏,如稱贊曹參的“與休息無為, 故天下俱稱其美矣。”[1]847并借百姓之口歌之曰:“蕭何為法, 覯若畫一;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凈, 民以寧一。”[1]847稱贊漢武帝時期的名臣汲黯“治官理民,好清靜”、“治務在無為而已!”[1]1625作《循吏列傳》、《酷吏列傳》,對民眾畏而恨之的酷吏給予否定。并于《序言》中推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1]1646的觀點,并有“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1]1620其所循之理,當是《自序》所謂“揣事情,循勢理”。
司馬遷這理民以靜的政治觀,是對漢初幾十年歷史進行深刻的現實的反思,又是對歷代治亂興衰的總結,也正是出于家學淵源,即因襲其父子的“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思想而生成的無為而治、順民而治的政治觀念。甚至連司馬相如之賦也歸結為“《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夸,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為。”[1]1802
三、成于言——“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在歷史記述的過程中完成了其父子學術第二階段——“通古今之變”的同時,也成就了第三階段的內容,進而實現了其父的遺囑和完成了其本人的學術宏愿。司馬遷《自序》中說“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1]1807,而“史記”一名據考證,乃始見立于東漢桓帝元年的東海廟碑。《太史公書》之名,當與《孟子》、《商君書》等一家之言的理論著作于本質上并無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乃借史的形式”而已。從《史記》整體內容看,充斥著理論闡發的內容,貫穿這一條理性思考的線索。
首先是具有綱要性文獻的《太史公自序》,其中除闡明了著述的思想基礎、理論視角和宗旨之外,還概述了各篇的寫作旨趣。這既可作為著作者對著作讀法的提示,更應當視為著作者對讀者在意義領會上的導引,而這指引的意圖恰恰在于司馬氏對史實的論斷。于是,或盛贊功績,如“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五帝本紀》第一)[1]1777;或稱頌賢德,如“嘉莊王之義”(《楚世家》第十)[1]1794;或嘉許俠義,如“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1]1804,如此種種,無不顯示其承自《春秋》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1]1783的理論意圖。恰如韓兆琦所言:“《自序》高古莊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奧衍宏深,一部《史記》精神命脈,俱見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3]1845
其次是“太史公曰”,司馬遷于各傳記文字所附“太史公曰”,對所傳人事加以評斷,如《呂太后本紀》肯定“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并揭示其原由為“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1]234再如《魏世家》辯駁“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提出“天方令秦平海內”[1]722大勢不可逆轉的觀點。又有《陳涉世家》引“褚先生曰”及錄賈誼之《過秦論》以證明“地形險阻”、“兵革刑法”之“未足恃”[1]794,昭揭其仁義為本的政治理念。
其三,若以《自序》為概論,則“太史公曰”便是詳說,以《自序》為總論,則“太史公曰”便是分解。如于項羽,《自序》云:“誅嬰背懷,天下非之”[1]1779,“太史公曰”則云:“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引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1]1793再如于越王勾踐,《自序》云:“嘉句踐夷蠻能脩其德,滅強吳以尊周室”,[1]1779 “太史公曰”則云: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強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1]1794又如于藺相如,《自序》“能信意強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諸侯”,[1]1801 “太史公曰”則云:“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1]1156 一如其論孔子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1]1778之意,只不過《春秋》是微言大義、寄寓褒貶的隱性暗示,而司馬遷之大義乃明言顯語的直接闡發。
如果將《自序》譬若一部之綱,這“太史公曰”無疑就是綱下之目,而綱舉目張,太史公所欲闡發的思想便網羅起三千年的歷史,司馬氏之“一家之言”的理論功業建樹起來,彰昭于世人面前。程金造“《史記》借史事明道理,有如孟軻、荀況、韓非諸人的著作,書中有其自己的思想核心與體系。”[4]63若以《伯夷列傳》視之,司馬遷之理論意圖則更加昭昭然矣!全篇828字,而本傳不過只289字,其余皆為論贊詠嘆之辭,難怪論者多有“名為傳紀,實則傳論”之說。
司馬氏父子的終極學術追求當然是“成一家言”,而這作為最后一個階段的總結性成果的形成必須以第一階段的理論基礎的奠定和第二階段歷事實的觀照為兩大前提而完成。司馬父子前赴后繼,耿耿營營于學術探索,汲汲孳孳于理論建樹,沿著既定的學術思路和途徑,成就了父子學術——治國之術的“一家之言”。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長沙:岳麓書社,2012.
[2]楊燕起.歷代名家評史記[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3]韓兆琦.史記評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4.
[4]程金造.史記管窺[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