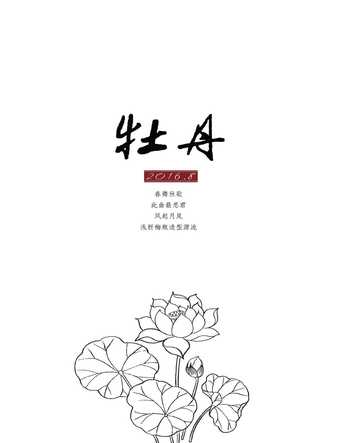形象的物化與態度的流變
李慧君

《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是英國當代著名漢學家雷蒙·道森的代表作品,該書從中西比較文學的研究視角出發,通過選取大量“被注視者”的“文化物象”進行時間軸分析,向讀者生動地展示了“注視者”(歐洲)眼中中國形象的流變。本文著力研究《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的“被注視者”——中國,由于形象本身被“物化”,成為了某個時代的隱喻象征。與此同時,這個形象又被附著在后殖民主義的西方話語里,呈現出雙方漫長歲月的歷史變遷。
跨文化自然會產生諸多問題,誤讀就是其中會出現的現象,英國漢學家雷蒙·道森在《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的前言部分談到:“1958年,我來到了中國,這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我過去讀過的許多東西是不準確的。”為此,他渴望通過自己的表述改變歐洲對中國的錯誤看法,他在“歐洲”與“西方”之間周旋,在其他領域的知識里徘徊,收集了大量的佐證資料,完成了這本書,盡管從某些角度看并非完全正確,但雷蒙·道森嚴謹與求真的態度及竭盡所能的努力必須得到充分的肯定。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都是當代比較文學中研究東方主義的優秀范例,在這樣的光環下,作者及作品達到了社會公認的地位。諸多海外漢學家由于觀察視角與觀察立場的不同,很快便開辟了一條“漢學主義”的研究道路,《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正是“漢學主義”的產物,而賽義德關于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最初探討給“漢學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也正是這種“東方主義”的方法論給海外漢學家帶來了很多的啟示,以《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為例,書中作為“注視者”與“被注視者”的線索被固定客觀地保留,而作為后殖民主義的話語,中國的形象被賦予了一種類似“物化”的形象,如同資本主義的商品一般被有意識地擺弄,只有商品的價值變動才能讓歐洲人的態度得以改變,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根植于西方文明最原始的資本積累欲望之中,并為他們的態度而轉移。
一、話語的力量:“變色龍”是對話語境的中庸表達
雷蒙·道森使用“中國變色龍”作為中國形象的總體概括,簡單而富有深刻的隱喻,一方面,“變色龍”表達了歐洲態度發生轉變;另一方面,暗含著中國的歷史變遷。作者在書中描述的語言是平實而謙虛的,并不使用鄙夷或浮夸的口吻。但無論作者如何努力地做到客觀而公正,都不可能擺脫本土的語境,遠離政治和經濟的文化因素,任何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都將面臨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的文化選擇問題,最重要的是,作者的話語如何能使問題變小或者弱化,“那么,能不能用完全屬于本土的話語來和他種文化進行對話呢?”這顯然是不明智的,在漫長的歷史歲月無意識的熔爐中,要想尋找另一種純粹的與本土無關的話語是不太可能的,而且這種“純粹”在文學作品與現實社會中顯得蒼白和無趣,作者的最佳方案無疑是成為一個“中介”。對照《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這種“中介”其實成為了一種“旁觀者”的話語,在文中,作者不遺余力地在以下幾個部分弱化了可能出現的雙方的文化沖突與歐洲的排外感。
第一,對象的稱謂。在整本書中,作者始終對本體——歐洲的稱謂為“歐洲”,有時也會稱“西方人”;作者把自己與讀者稱為“我們”,表明“旁觀者”的身份;對中國這個客體大多數的稱謂是“中國”;而對文中提到的中西文化交流緊密的商人、傳教士、歷史學家、哲學家等,作者的稱謂是他們的名字。作者十分在意稱謂的表述,盡可能使用全名,旨在避免因稱謂導致“中介”的視角混淆,進而影響態度的無意識先行。作者的在意無疑是正確的,稱謂的表述很重要,應該保持“旁觀者”的態度,因為作者無法安插任何社會集體想象物的情感,所以顯得真實而具有說服力。
第二,被注視者的描述。作者的研究對象是歐洲對中國的態度,而態度本身帶有主觀性的偏見,作者并沒有因為偏見就避而不談、敷衍了事。在第一章里,作者就歐洲對近代中國的印象做出了如下表述:“一個扇子與燈籠、辮子與斜眼、筷子與燕窩湯、亭臺樓閣與寶塔、洋涇浜英語與纏足的國度。”這樣的表述難免帶著一些歐洲對中國的蔑視態度,作者并未刻意遮掩與擅自修改,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作者的初衷,是展現歐洲對中國的“誤讀”,并不是想改變歷史。作者也是“他者”,延伸到作品的另一側面,“被注視者”——中國在歐洲的眼中是一個神秘而傳統甚至有些奇怪的國度,但“注視者”一方卻像“淘金”一樣滿眼放光地隨意涉足這個國度,西方有點瘋狂的好奇也正是因為處于20世紀的殖民幻想里。作者本身無疑也充滿了好奇,但作為研究者,他隱藏他的態度與想象,在描述中避免了“一邊倒”的立場。
第三,“變色龍”的空間感。20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在歐洲人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樣的形象,作者并沒有自己下定論,他通過展示資料、勾勒歷史、回顧事件來告訴讀者答案。同時他利用文獻,利用人物,也利用器物進行長時間的觀察,以小見大地反映中國的空間形象,是多維的、立體的、有色彩的。雷蒙·道森在中國的經歷使他認識到中國的不同,他耳濡目染長期被灌輸的“中國”形象被分解,他站在中間的立場上去解讀這種差異,筆者認為,他將自己作為“中介”這樣的角色去看待兩種文明之間的關系演變,并用“中國變色龍”這樣的整體形象概括,是一種中庸思維的表現,這種中庸視域的形成與漢學家的身份有關,也與他在中國的親身經歷有關。換句話說,作者自身文化認同的轉變的微妙過程,促成了他中庸分析觀的形成。
綜上所述,可以確定雷蒙·道森在《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中相對客觀地表述了歐洲對中國形象的態度轉變,它體現在一些文本細節上,帶來了新的閱讀體驗,而“中國不是龍,是變色龍”的論斷更貼近中國的實際,這也昭示著作者的成果——一種無聲的話語力量。
二、形象的物化:中國作為殖民地的歷史語境
盡管作者盡量做到站在“旁觀者”的位置,但也很難避免“西方中心論”的主體批判,文化影響的雙向性并未涉及,相互之間的影響只是歷史的縮影,而比起這些,筆者更關注另外一個領域,就是作者在本書中所描繪的“被注視者”——中國的形象,以歐洲為主體的“注視者”因為歷史的緣故站在相對較高的位置,因此,中國在曾經一個階段被無意識地排擠出西方文明圈,成為一個既遙遠又陌生、既無知又盲目的形象,筆者用“物化”這個概念來界定這種作為殖民地的語象。“物化”是盧卡奇首先提出來的名詞。而物化本質上是人的“事物化”,物化社會也指人被當作機器一樣被無意識地擺弄,在《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的描述中,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淪為歐洲的殖民地,歐洲對中國的幻想隨之變成嘲笑,而中國變成了一個可以被隨意踐踏、愚昧無知的國度,這時候,無論從哪個角度,中國都已經成為歐洲人眼中“物化”的形象,不再是個生機活力的世界。
雷蒙·道森在書中列舉了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物象”來闡述19世紀中葉以后歐洲對中國態度的轉變,這些“物證”見證也象征著由仰望變成鄙夷的態度轉變的過程(見表1)。
以上所列的“文化物象”,清晰地展現了“中國”形象在歐洲的完整變遷,如工藝品的早期崇拜到大量復制及掠奪,再到重新審視與鑒賞,“中國式風格”的烙印一直存在于西方,但“中國形象”卻始終被“物化”,它體現在:西方人認為中國“缺乏感情”“低于人類”,既“古怪”又“粗俗”,直到如今,他們的教科書及課堂上仍很刻板地介紹19世紀中國的歷史,文明的沖突是導致中國形象走向沒落的直接原因。
反觀之,中國被“物化”的形象從19世紀后一直存在,是中國作為殖民地的歷史語境所決定的,20世紀80年代,后殖民主義的誕生闡明了這個道理,后殖民主義強調文化精神被政治控制的要害,并認為“除了政治上、經濟上受殖民主義宰制,第三世界國家與民族在文化上也被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控制著。”中國作為殖民地,無疑在文化上也屬于“第三世界”,從書中描述的這些“文化物象”,可以看到其任由擺布的局面,同時,作者所列舉的“物象”,也是書中的一種意象,象征著中國作為殖民地的一種無力抵抗與喪失意志的“物品”形態。其次,19世紀末在西方資本主義無盡的“藐視與擺弄”下,此時的歐洲仍對中國“低劣”的形象反感,直到20世紀初“共產主義”的悄然興起,才引起歐洲對其形象認識的一點轉變。作者利用共產黨中國作為見證,敏銳地指出政治因素對歐洲態度轉變的巨大影響,直到作者所處的20世紀末,這種被“物化”的形象,才得以為歐洲做出不情愿的改變。顯然,從“物”到“人”,是要跨越漫長的時間歲月的。
三、態度的流變:“我”對“他者”文化的認可過程
在《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中,“我”與“他者”之間存在著一段曲折的歷史經歷,作者運用大量的文獻資料佐證這些態度流變的過程,文章以歐洲的“認知”為原點,以中國為終點,進行全方位的認知探索。實際上,這個過程就是建構對中國的文化認同,但是,建構認同也意味著建構“他者”,作為一種自身的主觀定位,“認同”是一種對所謂“歸屬”的情感。那么,在書中談到的歐洲對中國,是否也逐漸找到一種“歸屬”的情感,是否也會吸收中國的文化因子,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筆者整理了書中提及的“注視者”與“被注視者”的態度轉變關鍵詞,制作了表2,作為整本書的總括。
從表格中可感知發生這種態度變化的歷史背景,是由鴉片戰爭開始的近代侵略戰爭,而作者并未涉及過多的筆墨在歷史事件的影響之上,這其中的緣由,筆者認為是作者有意地規避文明沖突造成的文化相斥主義,在這樣的規避下,讀者不會太多地感受到因戰爭殺戮帶來的血腥場面,只能在文明的世界中體會到中國的興衰起伏對歐洲文明觀的影響,這必然會招致來自中國學者的質疑:是否這種刻意的規避只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虛偽。但作者卻又在文中有意無意地提到“基督教的優越感”帶來的“誤解”,也認為“歐洲對中國文明和世界上其他非基督教控制地區的文明持一種蔑視態度”,指出了根植于歐洲人心中的高傲是掩蓋擴張歷史的一種托詞。
現在來解決之前提出的問題。在歐洲“文化認同”的道路上,直到現今,歐洲人是否真正改變了對中國文明的看法,在書中的最后一章《黃變紅:20世紀的考慮》中,作者提到:“對現代中國產生曲解的下一個因素就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怖與仇恨。”所以,無論嘴上說的多么令人振奮,始終很難出現“歸屬”的情感,歐洲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到20世紀末,都只能說是一種文化上的“認可”。任何語句都不可能脫離政治和經濟的語境,也就是說,中國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程度,決定歐洲對其態度改變的程度,這也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作者在書中弱化了這種政治的因素,僅僅從文化的角度來探討,顯得不夠透徹。
回顧歐洲對中國文明觀的態度流變過程,可以說是歐洲的知識認知過程,更可以說是對中國的文化認可進程,但拋開本書的觀點,客觀地講,這種認可并不是真心實意的贊賞,而是對后殖民地中國發展迅猛的震驚,轉而對中國的文化開始感興趣,這種政治引致的認可,有可能是打開友好外交的開端,如作者一般的海外漢學家的深入研究成為雙方打開心門的一把鑰匙。不管“東方主義”的何種歧視與偏見,在全球化的視野下,未來雙方的“對話”都將可能如本書所說的“可以毫無偏見地注視”。
四、結語
“他者”并不是一個模糊不清、神秘莫測的形象,在雷蒙·道森的筆下,《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以豐富多樣的資料、圖文并茂的形式展現了中國形象在歐洲心目中的變遷,盡管中國的形象在某個時期內被“物化”、被誤讀,但這就是最接近事實的真相。而歐洲對中國態度的流變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不斷被真正理解的“他者”,文化的排外與語言的障礙,使雙方的“對話”不可能再恢復“平視”的姿態,對于“他者”的認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又全面客觀。無論“中國變色龍”是把什么樣的顏色傳達給歐洲,這種作為時代“想象物”與歷史“遺留物”的現狀已然存在,歷史不會變,“我”與“他者”的地位也不會變。在今天全球化的視野下,隨著科技時代的來臨,信息網絡的高速發展,對“他者”的認知將會更深入更全面,而那些殖民地與后殖民地的文化隔閡,也會慢慢消除,成為見證歷史的記憶。
(暨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