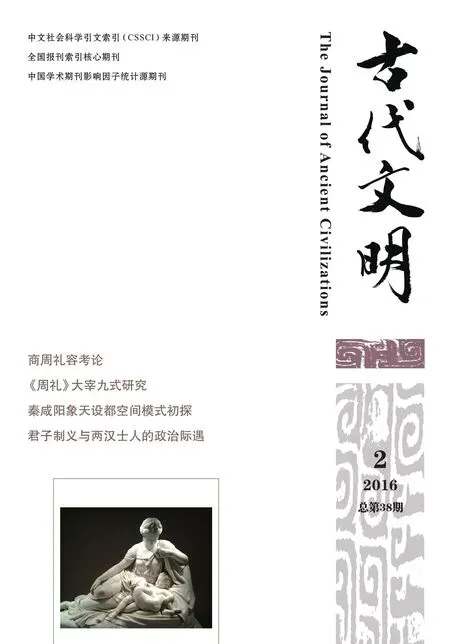西周異族邦伯考
王坤鵬
?
西周異族邦伯考
王坤鵬
提 要:異族邦伯作為一類政治團(tuán)體早在商代已經(jīng)存在。西周時(shí)期的異族邦伯品類復(fù)雜,部分與周關(guān)系密切,臣服較早,在伐商過程中立下功勞,故或進(jìn)入王畿擔(dān)任官職,或被置于邊關(guān)要地,承擔(dān)鎮(zhèn)守之職。這類邦伯作為一個(gè)團(tuán)體,參與周王朝的祭祀大典等政治活動(dòng),王朝則通過聘禮或勞慰等方式加強(qiáng)與邦伯的臣屬關(guān)系。部分邦伯處于邊域,叛服不定,遭受王朝的武力打擊,成為周王的“王臣附庸”,供周王驅(qū)策或賞賜諸侯大臣。西周時(shí)期分封的地方諸侯對(duì)封域內(nèi)的異族邦伯亦有因治之責(zé),至遲到西周晚期,這種因治已形成一種比較成熟的模式。
關(guān)鍵詞:西周;邦伯;族群
* 本文為吉林大學(xué)基本科研業(yè)務(wù)費(fèi)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種子基金(博士啟動(dòng)專項(xiàng))項(xiàng)目“商周時(shí)期‘伯’的性質(zhì)及相關(guān)問題研究”(項(xiàng)目批號(hào):2015BS016)成果。
西周出土資料中常見一類族邦稱伯的情況,既有自稱也有他稱。1自稱者例如沫伯鼎:“。沫伯疑作寶尊彝”(《集成》2344),他稱者例如作冊(cè)夨簋銘:“唯王于伐楚伯”(《集成》4300)。這類邦伯多為夏商舊邦,于西周王室而言,均屬異族,故稱之為異族邦伯。隨著商周易代,大部分異族邦伯或主動(dòng)臣服﹑或遭到征服,逐漸以不同的身份融入西周政治體制之中。由于品類復(fù)雜,其進(jìn)入周王朝政治體制的時(shí)機(jī)與際遇則各有不同。相對(duì)公﹑侯而言,異族邦伯的地位并不顯赫,似乎在西周歷史中并未留下多少特著的事跡,也因此一直未引起學(xué)界的關(guān)注。
近年來,隨著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以及對(duì)舊有材料的重新解讀,越來越多的證據(jù)顯示,這一群體在西周政治結(jié)構(gòu)中同樣承擔(dān)著不可或缺的政治﹑軍事及社會(huì)功能,對(duì)異族邦伯的招徠﹑征服﹑管控與使用一直是周王朝的重要事項(xiàng)之一。目前學(xué)界的相關(guān)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等爵制及諸侯稱謂等問題上,2參見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歷史研究》,1983年第3期;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職官系統(tǒng)》,《待兔軒文存》,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第130—131頁;韓巍:《新出金文與西周諸侯稱謂的再認(rèn)識(shí)——以首陽齋藏器為中心的考察》,芝家哥大學(xué)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xué)中心﹑芝家哥藝術(shù)學(xué)院主辦:“二十年來新見中國青銅器國際學(xué)術(shù)研究會(huì):首陽齋藏器及其他”學(xué)術(shù)會(huì)議論文,2010年;李峰:《論“五等爵”稱的起源》,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3輯,臺(tái)北:史語所,2012年,第166頁;劉源:《“五等爵”制與殷周貴族政治體系》,《歷史研究》,2014年第1期;朱鳳瀚:《關(guān)于西周封國君主稱謂的幾點(diǎn)認(rèn)識(shí)》,載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兩周封國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2—284頁。關(guān)于異族邦伯的專題研究尚未充分展開。本文不揣谫陋,試在前賢的基礎(chǔ)上,就西周時(shí)期異族邦伯的性質(zhì)﹑作用以及其與西周王室乃至地方封國之間的關(guān)系等問題作專題論述,祈請(qǐng)專家指正。
一、性質(zhì)與來源
邦伯作為一類政治團(tuán)體在商代業(yè)已存在。甲骨卜辭有“執(zhí)三邦伯于父丁”(《合集》32287,歷二類),父丁指商王武丁,卜辭意謂利用俘獲的三個(gè)邦伯向商先王武丁獻(xiàn)祭,所執(zhí)者當(dāng)是與商為敵的異族邦伯。卜辭亦有“多伯”,例如“癸亥卜,永貞,克以多伯。二月”(《英藏》199,典賓類)﹑“余其比多田于多伯正(征)盂方伯炎”(《合集》36511,黃類)。多伯即多位邦伯,陳夢(mèng)家比之于《周書》中的“庶伯”,1陳夢(mèng)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28頁。接受商王或王室重臣( )的統(tǒng)率,顯見其已臣服于商。臣服的異族邦伯逐漸成為商王朝政治結(jié)構(gòu)的一個(gè)組成部分,是以文獻(xiàn)中說到商代的政治結(jié)構(gòu)都說到“邦伯”,例如《尚書·盤庚》云:“邦伯﹑師長﹑百執(zhí)事之人”,2孔安國傳,孔穎達(dá)等疏:《尚書正義》卷9,《商書·盤庚》,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72頁。《酒誥》云:“外服:侯﹑甸﹑男﹑衛(wèi)﹑邦伯”,3孔安國傳,孔穎達(dá)等疏:《尚書正義》卷9,《周書·酒誥》,第207頁。《召誥》云:“庶殷:侯﹑甸﹑男﹑邦伯”4孔安國傳,孔穎達(dá)等疏:《尚書正義》卷9,《周書·召誥》,第211頁。等,“邦伯”均代表一類政治團(tuán)體,是王朝外服的組成部分。
周承商緒,臣服的異族邦伯在西周亦曾作為一個(gè)政治團(tuán)體而出現(xiàn)。最近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出土的西周早期器荊子鼎銘文云:“丁巳,王大侑。戊午,荊子蔑歷,賞白牡一。己未,王賞多邦伯,荊子麗。賞鬯卣﹑貝二朋,用作文母乙尊彝。”5參見李學(xué)勤:《斗子鼎與成王岐陽之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1期;黃錦前:《荊子鼎與成王岐陽之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9期。“多邦伯”與商代的“多伯”性質(zhì)類似,相對(duì)周王室而言,均是異族而有封土者。黃錦前先生認(rèn)為鼎銘“荊子”即指楚子,6黃錦前:《荊子鼎與成王岐陽之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9期。劉源先生認(rèn)為荊子位在“多邦伯”之列,7劉源:《“五等爵”制與殷周貴族政治體系》,《歷史研究》,2014年第1期。說法可據(jù),西周早期的周原甲骨以及銅器銘文中均有稱楚為“楚伯”的例子,8周原甲骨H11:14云:“楚伯乞今秋來即于王”(曹瑋:《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第14頁);作冊(cè)夨令簋銘云:“惟王于伐楚伯”(《集成》4300)。似可說明楚國在周初應(yīng)即異族邦伯之一。學(xué)者多將荊子鼎銘與保卣﹑保尊“四方會(huì)王大祀侑于周”(《集成》5415﹑6003)的內(nèi)容聯(lián)系起來,認(rèn)為其反映了周成王時(shí)期所舉行的“岐陽之盟”的史事情況,9李學(xué)勤:《斗子鼎與成王岐陽之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1期;黃錦前:《荊子鼎與成王岐陽之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9期。這是很有道理的。這種由王室舉行的“會(huì)同”實(shí)即一種盟誓活動(dòng),一個(gè)重要目的就是為了穩(wěn)定各級(jí)封建主對(duì)王室的臣服關(guān)系,如學(xué)者所論:“盟誓要對(duì)鬼神起誓,在祭祀神靈之后,面對(duì)神靈盟誓﹑建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約定關(guān)系。”10于薇:《湖北隨州葉家山M2新出子鼎與西周宗盟》,《江漢考古》,2012年第2期。其中保卣銘云:“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誕貺六品”(《集成》5415),所記的是周王殷會(huì)并賞賜“侯”之事,荊子鼎銘所記則是會(huì)見“多邦伯”并加以賞賜。不同銘文記載了不同的參與者,參互可見,說明“侯”與“邦伯”這兩個(gè)政治團(tuán)體均是周王朝所舉行會(huì)盟活動(dòng)的重要參與者。
納入西周政治體內(nèi)的異族邦伯,一般具有久遠(yuǎn)的傳承,部分是早在伐商之前即已臣服于周。例如伯簋銘所云:
部分異族邦伯則來源于周王朝的武力征服。前舉荊子鼎中的“荊子”即“楚伯”,作冊(cè)夨令簋銘記昭王南征之事,其云:“唯王于伐楚伯”(《集成》4300),記載了周王朝早期對(duì)作為異族邦伯的楚的征伐。成王時(shí)期的鼎銘記載了周公東征之事,其云:“唯周公于征伐東夷,伯﹑薄姑咸”(《集成》2739),周王朝征服了包括伯﹑薄姑等在內(nèi)的東夷邦伯。伯,或釋豐伯﹑4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第114頁。或讀為逢伯,5譚戒甫:《西周<鼎銘>研究》,《考古》,1963年第12期。林沄認(rèn)為“”從二亡之訛,并非“豐”字,6林沄:《豊豐辨》,《古文字研究》第1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4頁。是有道理的。寶雞竹園溝西周墓地M7曾出土一件公鼎,其銘作:“公作尊彝”(《集成》2152),學(xué)者早已指出公鼎及同出的一件觶并非墓主所鑄,均屬外來之物。7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14頁。該鼎口沿下飾夔紋與渦紋相間的紋飾帶,該類紋飾常見于商代銅器,下可延及西周早期。8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93頁。另外,鼎的形制及紋飾與竹園溝M13所出“作父辛鼎”(《集成》2253)基本相同。M13所出銅器多銘有“史”﹑“戈”﹑“冉”﹑“覃”﹑“刀”﹑“秉”等不同族徽,均為商末周初大族,另有“子墉鼎”(《集成》1314)亦是商代子族稱謂,這種情況顯示,包括作父辛鼎在內(nèi)的諸器應(yīng)系伐商俘獲所得。公鼎亦應(yīng)為同一途徑所獲。M13墓主活動(dòng)在成﹑康之世,M7墓主當(dāng)康﹑昭之世,從時(shí)代來看,公鼎很可能即是伯家族參與周公東征,征伐伯所獲。公并非公爵,只是自稱,9李學(xué)勤:《論芮姞簋與疏公簋》,上海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編:《兩周封國論衡》,第62—63頁。從周王朝的角度則可以稱之為伯。《逸周書·作雒解》記載周公東征:“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10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8頁。熊﹑盈為所征服的東夷族姓,伯似應(yīng)為其中的一種。
西周對(duì)異族邦伯的征伐時(shí)見于銅器銘文。例如近年公布的山東滕州前掌大西周墓地M18所出的一件青銅盉銘文云:“禽(擒)人(夷)方(澭)伯夗首乇,用作父乙尊”,11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02頁。前掌大墓地為商周時(shí)期的薛國貴族墓地。12何景成:《商代史族研究》,《華夏考古》,2007年第2期。盉與鶴壁龐村西周早期墓所出盉形制近似,學(xué)者將其定為西周早期器是有道理的。13所謂“夷方澭伯”是指隸屬夷方之下的澭伯,1馮時(shí):《殷代史氏考》,陜西師范大學(xué)﹑寶雞青銅器博物館:《黃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jì)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化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頁。其性質(zhì)則與伯相似,均是東夷族的異姓邦伯。銘文中的史氏貴族因?yàn)榍塬@了夷方的澭伯而為“父乙”作器,以作銘記。從以上例子來看,這類遭到征伐的異族邦伯,往往位于王朝的邊域,對(duì)周王朝叛服不定,故銘文中常見周王朝派部加以征服。這部分異族邦伯有的被征服收編,成為隸屬周王的“附庸王臣”,有的臣服后被奠置在地方,或被周王賞賜給封國重臣,逐漸成為地方封國的因治對(duì)象。
概言之,異族邦伯作為一個(gè)政治團(tuán)體自商代即已出現(xiàn),逐漸成為商王朝外服的一個(gè)部分。西周時(shí)期臣服的異族邦伯,其性質(zhì)與商代略似,在政治結(jié)構(gòu)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周王朝所舉行的會(huì)盟典禮中,臣服的異族邦伯與諸侯一樣,均接受周王的冊(cè)命賞賜,可見已經(jīng)融入了王朝的日常政治之中。由相關(guān)銅器銘文來看,部分異族邦伯在商周之際即已臣服于周,接受周的轄制,助周攻伐商朝,是周王朝開國的功臣。因此在西周時(shí)期,這部分異族邦伯有的進(jìn)入周王畿擔(dān)任王朝官職,有的雖仍居原地,卻接受周王征召,常有聘使往還。另有部分異族邦伯,一般處于王朝邊域,叛服不定,則受到王朝征伐,成為“王臣附庸”或地方封國所因治的對(duì)象。
二、管控與利用
異族邦伯品類復(fù)雜,其中的部分邦伯或很早已臣服于周,曾作為周王伐商的前驅(qū),或被封于重要區(qū)域,承擔(dān)武裝防衛(wèi)的職責(zé)。從相關(guān)記載來看,這部分異族邦伯一般與王朝中央的關(guān)系比較密切。周王朝對(duì)它們不時(shí)施以管控或者加以利用,其中主事者包括周王﹑王后以及王朝重臣,各種處置手段充分反映了異族邦伯在王朝政治體內(nèi)所具有的相應(yīng)功能與地位。
臣服的異族邦伯一般遵循周禮,與王室或王朝重臣之間常有聘使往還。這種禮儀活動(dòng)可以強(qiáng)化上下級(jí)之間的關(guān)系,應(yīng)是周王朝對(duì)臣服邦伯加以管控的一種重要手段。近年新發(fā)現(xiàn)了山西翼城大河口霸伯墓地以及橫水倗伯墓地,學(xué)者多認(rèn)為倗﹑霸二伯應(yīng)屬于文獻(xiàn)記載的“懷姓九宗”,2田偉:《試論絳縣橫水﹑翼城大河口墓地的性質(zhì)》,《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5期。韓巍先生進(jìn)一步認(rèn)為二伯近似于外服“邦伯”,也即是本文所說的異族邦伯。這類邦伯見機(jī)較早,早在伐商之前即已臣服于周。3韓巍:《橫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兩周封國論衡》,第403頁。臣服的異族邦伯遵循周禮,接受王室的賞賜蔑歷,霸伯墓地M1071所出霸伯盂銘文充分說明了這一點(diǎn):
唯三月,王使伯考蔑尚歷,饋茅苞、芳鬯,臧(咸)。尚拜稽首。既稽首,延賓、贊,儐用虎皮乘。毀,用璋,奏。翌日,命賓曰:“拜稽首。天子蔑其臣?xì)v,敢敏用璋。”遣賓、贊,用魚皮兩,側(cè)毀,用璋,先馬,右毀,用玉,賓出。以俎,或延,伯或(又)原毀,用玉,先車。賓出。伯遺賓于郊,或余(予)賓馬。霸伯拜稽首,對(duì)揚(yáng)王休,用作寶盂,孫孫子子其萬年永寶。4銘文照片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聯(lián)合考古隊(duì):《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釋文參考李學(xué)勤:《翼城大河口尚盂銘文試釋》,《文物》,2011年第9期;黃錦前:《霸伯盂銘文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5期。
銘文記載周王使人蔑歷霸伯并饋送苞茅﹑鬯酒等,霸伯接受并鑄作禮器,記錄來自王室的褒獎(jiǎng)。銘文詳細(xì)記載了相關(guān)禮儀過程,屬于后世禮書中的聘禮。整個(gè)過程包括五個(gè)環(huán)節(jié):開始是蔑歷之禮,使臣代表周王勉勵(lì)霸伯;其后是儐禮,霸伯以虎皮四張慰勞使臣;接著第二天行賄禮,霸伯還致禮物給周王,報(bào)答來聘之盛意;之后是饗禮,霸伯餞別使臣;最后是郊贈(zèng)之禮,使臣舍止于郊,霸伯以馬匹贈(zèng)予使臣。與《儀禮》所記的“聘禮”相比較,銘文所記雖然在細(xì)節(jié)上仍有一些疏漏,但大體已經(jīng)齊備。1張亮:《考霸伯盂銘文釋西周賓禮》,《求索》,2013年第2期。周王室與異族邦伯之間聘禮往還,一方面其目的在于所謂的“時(shí)聘以結(jié)諸侯之好”,2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37,《秋官司寇·大行人》,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90頁。更深一層來看,是為了達(dá)到“官職相序,君臣相正”,3鄭玄注,孔穎達(dá)疏:《禮記正義》卷22,《禮運(yùn)》,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本,第1427頁。在融洽關(guān)系的同時(shí)強(qiáng)化上下尊卑,正如王國維所論周禮“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tuán)體”。4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54頁。
此外,周王或王朝大臣不時(shí)派出使臣對(duì)某些處于畿外的異族邦伯加以勞慰,這在銅器銘文中有不少記載,一般稱為“安”﹑“寧”或“伐”。例如盂爵銘云:“惟王初禱于成周,王令盂寧鄧伯,賓貝,用作父寶尊彝。”(《集成》9104)唐蘭認(rèn)為盂爵屬康王時(shí)器。5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2頁。《左傳》昭公九年云:“巴﹑濮﹑楚﹑鄧,吾南土也”,6杜預(yù)注,孔穎達(dá)等疏:《春秋左傳正義》卷45,昭公九年,第2056頁。“鄧”即銘文中的鄧伯。鄧為曼姓,為夏商舊邦,亦是本文所稱的異族邦伯之一。《春秋》經(jīng)傳或稱之為“侯”,當(dāng)與楚稱“子”相似,或?yàn)槌挤苁液笏鶅?cè)封,也或與文獻(xiàn)中關(guān)于五等爵制的記載受到理想化的整理有關(guān)。鄧伯地處今天的南陽盆地,是漢水流域與淮水流域的連接地帶,地理位置關(guān)乎中原腹地的安危,是周代經(jīng)略南方的重要立足點(diǎn)之一。7于薇:《淮漢政治區(qū)域的形成與淮河作為南北政治分界線的起源》,《古代文明》,2010年第1期。“惟王初禱于成周”,當(dāng)指周王繼位之后首次來到成周舉行祭祀大典。周王于繼位之初即派遣使臣南下勞慰鄧伯,加以籠絡(luò),一方面是出于周禮的要求,新王繼位需要通過重新冊(cè)命等禮儀形式,來穩(wěn)定并強(qiáng)化與異族邦伯之間的臣屬關(guān)系,另一方面也凸顯了這類邦伯處于關(guān)鍵位置,在西周政治結(jié)構(gòu)中擁有一定地位,是以受到王朝的重視。
相似的銘文已發(fā)現(xiàn)不少,足見王朝與異族邦伯之間此類交往之頻繁。例如:
惟十又九年,王在 ,王姜令作冊(cè)睘安夷伯,夷伯賓睘貝、布。揚(yáng)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寶尊器。(《集成》5407,作冊(cè)睘卣)
惟十又一月初吉壬午,叔氏使 安 伯,賓馬轡乘,公貿(mào)用揚(yáng)休魯,用作寶彝。(《集成》2719,公貿(mào)鼎)
惟十又一月初吉辛亥,公令緐伐于 伯,伯蔑緐歷,賓緐柀廿、貝十朋。緐對(duì)揚(yáng)公休,用作祖癸寶尊彝。(《集成》4146,緐簋)
唯十又一月,井叔來拜,廼蔑霸伯歷,使伐,用幬百、丹二糧、虎皮一。霸伯拜稽首,對(duì)揚(yáng)井叔休,用作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8王保成:《翼城大河口霸伯簋試解》,《中原文物》,2013年第2期。(霸伯簋)
“安”﹑“寧”﹑“伐”三詞意思相近,9《爾雅·釋詁》:“寧,安也”。伐,意為夸獎(jiǎng)。《論語·雍也》:“孟之反不伐”。銘文中均指周王朝對(duì)地處畿外的異族邦伯加以慰勞籠絡(luò)。其中“夷伯”為姜姓,《左傳》桓公十六年有“夷姜”。“ 伯”亦是姜姓古國,商代曾稱侯,西周時(shí)國于山東東南。10王獻(xiàn)唐:《山東古國考》,濟(jì)南:齊魯書社,1983年,第61頁。作冊(cè)睘卣的“王姜”,唐蘭認(rèn)為是昭王之后,11唐蘭:《論周昭王時(shí)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5頁。“公”﹑“叔氏”或“井叔”等則為王朝執(zhí)政大臣。主事者均是王室近戚或重臣,代表王朝勞慰散處邊域的異族邦伯,反映了異族邦伯在西周政治體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這種不定期的勞慰籠絡(luò)當(dāng)是周王朝管控邊域臣服邦伯的一種重要手段。
除了接受王朝中央的聘使及勞慰之外,部分異族邦伯還參與了王朝的重要事務(wù)。從甘肅靈臺(tái)白草坡西周涇伯墓(M1)﹑12,簡報(bào)釋作“潶”,李學(xué)勤釋作“涇”,劉釗亦有論證,我們同意這一意見。西周晚期克鐘(《集成》204)“涇”字作,比較可知只是增加了五點(diǎn)代表水滴的點(diǎn)劃,兩者應(yīng)為一字。參見李學(xué)勤:《西周時(shí)期的諸侯國青銅器》,《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研究院學(xué)報(bào)》,1985年第6期;劉釗:《涇伯器正名》,《文物研究》第5輯,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第219頁。伯墓(M2)的材料看,1下文關(guān)于兩墓的考古數(shù)據(jù),參見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duì):《甘肅靈臺(tái)白草坡西周墓》,《考古》,1977年第2期。異族邦伯被西周王朝奠置于軍事要地,承擔(dān)防衛(wèi)之責(zé)。兩墓均屬西周早期,其中涇伯墓略早。涇﹑ 二伯不見于文獻(xiàn)記載,從墓葬形式來看,兩墓坑底均設(shè)腰坑,坑里埋有狗骨,與近年新發(fā)現(xiàn)的山西翼城大河口霸伯墓(M1)有諸多相似之處,學(xué)者認(rèn)為相關(guān)葬俗具有較顯著的殷遺民色彩。2張懋镕:《高家堡出土青銅器研究》,《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4期;韓巍:《橫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兩周封國論衡》,第398頁。但從隨葬品來看,二伯并非普通殷遺,而是早已臣服的異族邦伯,其中時(shí)代略早的涇伯還參與了伐商戰(zhàn)爭。兩墓中均無發(fā)現(xiàn)隨葬生活用品如陶器等,卻隨葬大量兵器,計(jì)涇伯墓171件﹑ 伯墓127件,其中包括大量的攻擊性武器戈﹑弓箭等以及防守性武器甲胄﹑盾牌等,足見二伯的軍事功能異常突出。而且墓中隨葬的啄戈等武器具有純正的北方文化因素,很顯然是與北方族群之間通過戰(zhàn)爭交流所獲得。3韓金秋:《夏商西周時(shí)期中原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研究》,吉林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9年。涇伯墓中出土了8件帶有不同族氏銘文的器物(上圖),來源復(fù)雜。這種情況多見于商末周初貴族墓葬中,由于商人多使用族徽,一般認(rèn)為這些器物應(yīng)是墓主參與伐商所分得的戰(zhàn)利品,故隨葬以示戰(zhàn)功。4《史記·周本紀(jì)》記載武王伐商后:“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從西周早期的軍事地理看,涇伯﹑ 伯應(yīng)是王朝派駐宗周西北方的守衛(wèi)力量。張懋镕先生認(rèn)為白草坡墓主作為鎮(zhèn)撫一方的邦族首領(lǐng),捍衛(wèi)周王朝的西北邊陲。5張懋镕:《高家堡出土青銅器研究》,《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4期。這一看法很有道理。古代由西北進(jìn)入渭河谷地最便捷﹑主要的通道即沿固原﹑平?jīng)雯p涇州﹑長武一線向東南到達(dá)西安,由于這種地勢(shì)的原因,今天這一帶所修的公路大致仍沿該線鋪開。戰(zhàn)國時(shí)期的秦國在今天固原境內(nèi)設(shè)有蕭關(guān)以扼守此道,史稱“蕭關(guān)道”,“川道平坦,水草不缺,便于騎兵的活動(dòng)。雖然距離關(guān)中較為遠(yuǎn)些,但北方游牧民族很早就由此向南進(jìn)攻。”6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1年,第110頁。《史記·匈奴列傳》云:“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7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83頁。可以說隴東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華夷分界線。學(xué)者曾提出“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指由橫斷山脈﹑祁連山脈﹑賀蘭山脈﹑陰山山脈直到東北的大興安嶺,所構(gòu)成的一個(gè)弧狀的邊地文化帶。8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考古與文物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頁。隴東地區(qū)正處于這條文化帶上,因此,西周早期在這里設(shè)置涇伯﹑伯以布防,抗擊西北方的戎狄族群。前述白草坡墓地隨葬品中出現(xiàn)了不少純正北方風(fēng)格的武器,也恰能說明這一問題。
據(jù)以上考證,部分異族邦伯臣服于周,仍被周王朝奠置于畿外,接受王朝中央的管控。它們熟習(xí)周禮,不時(shí)與王室或王朝大臣聘使往還,通過周禮不斷強(qiáng)化上下之間的隸屬關(guān)系。同時(shí)王朝在新王繼位或者其他重要時(shí)節(jié),亦常會(huì)派出使臣對(duì)位處重要地域的異族邦伯加以勞慰籠絡(luò)。這些均說明這些異族邦伯在西周政治體內(nèi)所具有的地位,對(duì)異族邦伯的管控已成為王朝日常行政的一項(xiàng)重要事務(wù)。此外,西周王朝還在一些關(guān)鍵地區(qū),布置異族邦伯以作軍事屏障,這部分異族邦伯已然成了王朝的心腹爪牙,充分反映了其間的密切關(guān)系以及融合程度。
三、征服與因治
除了部分異族邦伯臣服較早而與周王朝關(guān)系密切之外,多數(shù)邦伯處于邊域,時(shí)叛時(shí)服,屢受征伐而改編為周王的“王臣仆庸”,1這種由俘獲異族邦伯而來的“王臣”近似于隸仆,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君臣之“臣”截然不同,下文的“王臣”均具有這種特殊內(nèi)涵。成為周王的私屬力量,供驅(qū)策或賞賜之用。這一情況自商代即已存在,例如商代卜辭有“沚伯”(《東大》B.0945),又有“呼比臣沚,有冊(cè)三十邑”(《合集》707正),有“衰伯”(《合集》3439),2“”字省刻較多,例如(《合集》768正)﹑(《合集》777正)﹑(《合集》783)﹑(《合集》787)等。唐蘭曾釋為《說文》“衰”字,姑從之。參見唐蘭:《殷墟文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2頁。亦有“呼取衰臣”(《合集》938正)。3“”字或釋為“舞”。參見曹錦炎﹑沈建華:《甲骨文校釋總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57頁。沚伯與衰伯原是商王朝之外的異族邦伯,經(jīng)常與商發(fā)生爭戰(zhàn),后遭征服而成為“王臣”,4此問題筆者另有專文《商代沚方考》(《考古與文物》待刊)加以探討。卜辭中的“臣沚”與“衰臣”都是由受征服的邦伯轉(zhuǎn)化而來。5林沄先生曾指出卜辭中的“多臣”與西周“虎臣”﹑“夷仆”性質(zhì)相似。參見林沄:《商代兵制管窺》,《吉林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報(bào)》,1990年第5期。
進(jìn)入西周時(shí)期,這種情況依然普遍存在。宜侯夨簋及大盂鼎銘顯示,征服為“王臣”的異族邦伯,仍以“伯”為單位:
王令虞侯夨曰:遷侯于宜……錫在宜王人□又七里,錫奠七伯,厥盧□又五十夫,錫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簋,《集成》4320)
王曰:盂……錫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大盂鼎,《集成》2837)
上引銘文中的“伯”,學(xué)者常作官長或管理人員來理解,6諸家說法參見郭寶宏:《西周青銅重器銘文集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9—191頁。銘文語境中應(yīng)專指遭到征服的異族邦伯,而且“伯”與“里”相對(duì)應(yīng),也是一種人群的單位,當(dāng)包括伯長所在的整個(gè)族群,并非專指首領(lǐng)。“奠”自商代就是處置臣服邦伯的一種方式,也成為安置這些臣服者的區(qū)域名稱。7裘錫圭:《說殷墟卜辭的“奠”——試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裘錫圭學(xué)術(shù)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169頁。“奠七伯”指遭征服而置于奠中的七個(gè)邦伯,包括其所在的整個(gè)邦族,韓巍先生認(rèn)為它們屬于周初遭征服而被置于關(guān)中的異族,8韓巍:《橫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兩周封國論衡》,第405頁。是有道理的。盂鼎中的“王臣”指隸屬于周王的臣附者,亦是來源于臣服的異族邦伯,故大盂鼎中的“王臣”也是以“伯”為單位,同樣包括伯長所在的整個(gè)族群。
至于“邦司”與“夷司”的不同,可能與邦伯的來源及所受管轄的不同有關(guān)。“司”意為司掌﹑管理,此可見不管是“邦司”還是“夷司”,這些不同來源的異族邦伯都要接受周王朝的管理。西周晚期的詢簋記載周王命詢管理夷族:“先虎臣后庸:西門夷﹑秦夷﹑京夷﹑ 夷﹑師笭﹑側(cè)新﹑□華夷﹑弁狐夷﹑夷﹑成周走亞﹑戍秦人﹑降人﹑服夷”(《集成》4321),詢所管理的這些“虎臣”或“庸”,就是銘文中的若干夷族,實(shí)際也是臣服的異族邦伯。
作為周王的私屬,這些遭到征服的異族邦伯往往會(huì)被賞賜給諸侯或大臣。宜侯夨簋中周王命虞侯遷侯于宜,賞賜了七個(gè)邦伯,大盂鼎中周王賞賜盂十七個(gè)邦伯。這種賞賜在西周前期應(yīng)是比較普遍的,此時(shí)西周王室仍保有大量遭到征服的異族邦伯。例如大約康王時(shí)期的榮作周公簋銘云:“王令榮眔內(nèi)史曰:害(介)井(邢)侯服,賜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集成》4241),周王賞賜給邢侯的“臣”,包括州﹑重﹑庸三個(gè)族群,這三個(gè)族群實(shí)即是我們所說的遭征服而成為“王臣”的異族邦伯。這些成為隸仆的異族邦伯,往往保有舊有的宗族組織,整族整族地被周王室賞賜給屬下,朱鳳瀚先生認(rèn)為它們舊有的親族組織依舊,只是等級(jí)身份下降為供周人役使的附庸,1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第247頁。是有道理的。
遭到征服的異族邦伯作為“王臣仆庸”,往往具有比較突出武裝性質(zhì),學(xué)者指出由異族邦伯改編成的這類臣仆經(jīng)常組織起來,主要被派用于戰(zhàn)斗﹑守衛(wèi)等任務(wù)上。2裘錫圭:《說“仆庸”》,《裘錫圭學(xué)術(shù)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第109頁。穆王時(shí)期的班簋銘文記載周王朝征伐東方戎夷之事,其中講到周王命重臣毛公“秉繁﹑蜀﹑巢命……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徒馭﹑人伐東國 戎”(《集成》4341)。“秉命”指毛公可以命令繁﹑蜀﹑巢諸異族邦伯,這些邦伯就是后文中跟隨毛公征伐的“邦冢君”,沈長云先生認(rèn)為“邦冢君”相當(dāng)于大盂鼎中的“邦司四伯”。3沈長云:《釋<大盂鼎銘>“人鬲自馭至于庶人》,《河北師院學(xué)報(bào)》,1988年第3期。可見被征服的異族邦伯在周王朝征伐東夷的過程中成了前驅(qū)武裝。
西周王朝中央的武力以及文化上的吸引力終究有限,因此除了王室的管控之外,地方封國亦對(duì)其封域內(nèi)的異族邦伯加以因治,這應(yīng)是周王朝封建諸侯的重要目的之一。這種因治即文獻(xiàn)中所講的“因以其伯”。《詩經(jīng)·大雅·韓奕》記載了西周晚期周宣王冊(cè)封韓侯于北方之事,其中說到:“以先祖受命,因是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shí)墉實(shí)壑,實(shí)畝實(shí)藉。獻(xiàn)其貔皮,赤豹黃羆。”4毛享傳,鄭玄箋,孔穎達(dá)疏:《毛詩正義》卷18—4,《大雅·韓奕》,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72頁。據(jù)《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記:“邘﹑晉﹑應(yīng)﹑韓,武之穆也”,5杜預(yù)注,孔穎達(dá)等疏:《春秋左傳正義》卷15,僖公二十四年,第1817頁。韓首封者為周武王之子,宣王時(shí)重新冊(cè)封為侯,統(tǒng)領(lǐng)百蠻之國,即毛傳所云:“長是蠻服之百國也”。6毛享傳,鄭玄箋,孔穎達(dá)疏:《毛詩正義》卷18—4,《大雅·韓奕》,第572頁。其中“因以其伯”句,鄭玄箋云:“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7毛享傳,鄭玄箋,孔穎達(dá)疏:《毛詩正義》卷18—4,《大雅·韓奕》,第572頁。解“因”為虛辭﹑“伯”為侯伯,實(shí)是一種誤解。這里的“因”與前述“因是百蠻”意思相同,都是統(tǒng)領(lǐng)﹑因治之意。文獻(xiàn)中說到對(duì)民眾的統(tǒng)領(lǐng)往往用“因”字,例如《國語·鄭語》云:“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8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69頁。《左傳》定公四年記封魯事云:“因商奄之民”,諸“因”字內(nèi)涵相同,均是統(tǒng)治之意。9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第247頁。“因以其伯”即統(tǒng)率﹑管理北國域內(nèi)的追﹑貊等異族邦伯。此可見周王封建韓侯的一個(gè)重要目的即在于控制封域內(nèi)的異族邦伯。
對(duì)異族邦伯的因治并非僅具形式,還包括一些具體的措施。《韓奕》中的“墉”指筑治城衛(wèi),“壑”指濬修溝池,均是修整邦伯所在地的城郭防守。“畝”指整理劃治田畝,“藉”則是指據(jù)田畝數(shù)征發(fā)賦役。可見西周時(shí)期的地方封國,需對(duì)受因治的異族邦伯提供武力保護(hù),同時(shí)也會(huì)征發(fā)各邦伯民眾參加藉田勞作。除了提供力役,邦伯還需要貢獻(xiàn)某些地方土產(chǎn),諸如狐﹑豹﹑熊之類的毛皮都在其列。從《詩經(jīng)》內(nèi)容來看,諸侯封國對(duì)異族邦伯的因治可概括為若干環(huán)節(jié):包括周王授權(quán)﹑整頓防衛(wèi)﹑劃定田畝﹑貢獻(xiàn)土產(chǎn)等。可見到了西周晚期,周王朝包括地方封國對(duì)異族邦伯的因治已經(jīng)約定成俗,甚或形成了一種成熟的制度。
當(dāng)然,因治實(shí)亦包括對(duì)異族邦伯的征伐。《左傳》僖公四年記載周王室初封齊大公時(shí),曾授予其命書:“五侯九伯,女實(shí)征之,以夾輔周室”,10杜預(yù)注,孔穎達(dá)等疏:《春秋左傳正義》卷12,昭公四年,第1792頁。關(guān)于“五侯九伯”的內(nèi)涵,舊釋異說紛紜,一般認(rèn)為泛指諸侯。1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89頁。齊國初封時(shí),東方很多地域并不在周的控制之內(nèi),封齊的目的即是對(duì)封域內(nèi)的異族邦伯加以節(jié)制。因此我們認(rèn)為這里所說的“五侯九伯”,應(yīng)非周室所封,實(shí)指舊有的土著邦伯。禽簋銘中成王所征伐的“蓋侯”(《集成》4041),以及上文所引到的 鼎銘中周公所征伐的“伯”即所謂的“五侯九伯”,均是殷商舊國,只有管制它們才稱得上是“夾輔周室”。
綜合以上所作考論,異族邦伯的由來十分久遠(yuǎn),在商代文獻(xiàn)及甲骨材料中,這一團(tuán)體即已成為王朝的一股政治勢(shì)力。西周時(shí)期除了公﹑侯等較大的政治團(tuán)體外,尚有大量的異族邦伯散處王畿內(nèi)外,因此周代文獻(xiàn)中“多邦伯”亦與“侯”并列,成為政治結(jié)構(gòu)中的一個(gè)組成部分。異族邦伯品類復(fù)雜,傳承久遠(yuǎn),具有自己的屬地與宗族,往往具有一定的武裝力量。總的來看,其一,部分邦伯與周有較深的淵源關(guān)系,有的在克商之前即已臣服于周,助周征伐,在周伐商的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是以在周王朝建立之后,或進(jìn)入王朝擔(dān)任重要官職,或被奠置于邊關(guān)要地,鎮(zhèn)守一方邊陲。在周王會(huì)盟典禮上,這類邦伯雖位不及公侯,但亦是參與其中的重要角色之一。這類異族邦伯與王室或王朝重臣之間常有聘使往還,從現(xiàn)有的材料看,這種交往一般嚴(yán)格遵循周禮的儀程。同時(shí),周王或其代表亦經(jīng)常派出使臣對(duì)地處關(guān)鍵位置的異族邦伯加以勞慰。這種禮聘往來一方面鞏固了周王與異族邦伯之間的臣屬關(guān)系,一方面也顯示了異族邦伯團(tuán)體在西周政治中擁有一定的力量及地位。其二,仍有部分異族邦伯位處邊域,叛服不定,遭到周王朝的打擊與征服,征服之后往往會(huì)整族地轉(zhuǎn)變?yōu)橹芡醯摹巴醭几接埂薄K鼈円环矫婵梢宰鳛橥醭M(jìn)一步攻伐其他方國的武裝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由周王賞賜給諸侯或大臣以作獎(jiǎng)賞。其三,西周實(shí)行分封制,所封建諸侯的一個(gè)重要功能即是鎮(zhèn)撫﹑管控當(dāng)?shù)氐漠愖灏畈N髦芡砥诘奈墨I(xiàn)中說的“因以其伯”即是說諸侯對(duì)屬地內(nèi)的異族邦伯加以因治,其統(tǒng)治內(nèi)容包括負(fù)責(zé)邦伯的防衛(wèi),劃定田畝,征收賦役等具體事項(xiàng)。這說明到了西周晚期,地方封國對(duì)封域內(nèi)異族邦伯的因治已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制度與模式。
[作者王坤鵬(1984年—),吉林大學(xué)文學(xué)院歷史系講師,吉林,長春,130012]
(責(zé)任編輯:謝乃和)
【中國先秦史】
[收稿日期:2015年10月30日]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