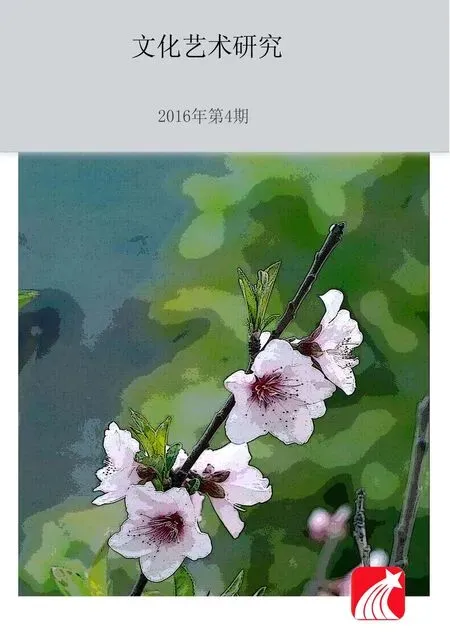《冰河追兇》:暴力呈現下的“烏托邦”幻象
葉 凱
(北京師范大學 藝術與傳媒學院,北京 100875)
《冰河追兇》:暴力呈現下的“烏托邦”幻象
葉 凱
(北京師范大學 藝術與傳媒學院,北京 100875)
以類型雜糅的方式嘗試完成商業電影表層范式的構建,圍繞“暴力”元素的呈現,切入道德倫理價值的現實指涉,在此之上形成關于不同文明價值觀念博弈與興替的反思,影片《冰河追兇》企圖用道德訓誡的方式完成對失范秩序的救贖,但終因價值觀表述的語焉不詳與想象性解決的無力,只能復制一種寄托于“烏托邦”之上的心靈雞湯與陳詞濫調。
暴力呈現;類型雜糅;現實指涉;文明反思;“烏托邦”幻象
“動作性”是審美感知藝術傳達之物的必要方式,普遍存在于展現生命韻律之美的過程中,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論述藝術本質及其規律的專著《詩學》中曾指出:“悲劇是對于一樁嚴肅、完整,有相當廣度的事件的模擬……它的方式是用動作來表達,而不是用敘述”[1],而有中國學者亦認為“動作性也是電影影像敘事性的最本質特性——本性”[2]。以符合康德所論述的“審美的本質特征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3]的觀點,對動作不進行先驗式的判斷而自然地呈現達到美的目的,便是合法性的存在。然而,基于美的標準是否包含道德性的因素,而比如暴力的動作呈現,在遵循藝術形式的自律性之美準則時,何以回應美與道德關系的疑慮,又可以成為被詰問的悖謬。
就電影創作而言,藝術審美規律和現實主義傳統在形式和內容雙重層面的訴求,使暴力呈現成為無法規避的事實;但除了作為藝術的概念界定,電影亦是具有文化價值傳遞、意識形態表達、大眾娛樂消費等復雜功能的公共場域,暴力及其在電影中的呈現不可能只作為藝術審美自律價值存在,而需要受到社會道德觀念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規訓,成為一種被限定和修飾的話語。
國家電影管理制度對暴力元素極其敏感,《電影管理條例》在“宣揚淫穢、賭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4]方面設置了禁止性的規定,因而在中國電影長期以來的創作實踐中,暴力美學的視覺呈現和可能牽涉暴力內容較多的類型片種,便成為了稀缺甚至是不可見的存在。但作為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的驅動力量,更加豐富的內容產品是保持電影市場急速擴張條件下持續進步的前提,許多之前被遮蔽的審美需求被重新呼喚。有基于此,電影的管理方和制作方便在必然的共同訴求中,以彈性的方式達成默契妥協,暴力內容的銀幕呈現在主流價值觀念的規制和主導下,成為某種折中化的存在。影片《冰河追兇》就是在如此背景下誕生的典型案例。
類型雜糅:視覺慣例與敘事營構的僭越張力
“類型”概念來源于文藝研究的方法與視角,當把它運用到電影領域后,除了形成藝術本體實踐的理論化歸納之外,亦有文化產業消費品的目標市場選擇及大眾傳播媒介的受眾心理接受等復雜元素混合其中,它會依據社會歷史條件的變遷呈現出不斷發展的動態化特征。電影類型固然是“一整套無形的套路、主題領域、形式趣味組合……抽象的、不成文的系統”[5],但就文本范式的規定性描述延伸到作品實踐的成型性樣貌而言,“類型是非常具有伸縮性的、有彈性的,是隨著不同時期的文化需求而不斷演變的”[6],而電影藝術發展到今天,“一個單純穩固、不斷復制成規的類型已經很難滿足觀眾的觀影需求了,因此,不同類型雜糅的特點在幾乎所有影片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體現,并且逐漸成為一種大趨勢”[7]。而有些類型的影片,由于敘事模式、題材選擇、影像風格本身交叉以及前后相承的關系,呈現出更加密不可分的關聯。
在影片《冰河追兇》中,關乎警匪片、偵探片、驚險片、黑色電影的類型元素雜糅交織,因涉及犯罪案件偵破產生的懸疑及解密動機而形成影片的敘事張力,但其視覺審美習慣的核心要素呈現,將影片導向動作片的類型歸屬。如果以二元對立的模式劃分人物角色的位置,周鵬、汪豪為代表的“執法者”與李永勝、翁杰為代表的“犯罪者”之間基于社會規則的必然沖突,凝聚在設計縝密的“連環兇殺”惡性案件的敘事載體之中,合乎邏輯地引發了雙方“智力”和“暴力”雙重層面的斗爭。如果說在“智力”層面的斗爭于推動敘事方面中規中矩地因循傳統類型常態而呈現出“中性化”特質,無論應用于“警”“匪”雙方都未嘗不可,反而增強了藝術審美的“自律”化表達;那么“暴力”動作的呈現,不管它多么有效地提供具有感官沖擊力的美學刺激,都無法不小心翼翼地控制力度,力圖避免對法制維護的社會正常秩序和主流倫理道德觀的冒犯,溢出藝術本體而遷延到社會現實層面的“他律”規范顯現無疑。尋求“暴力”元素之于“藝術審美”與“法制倫理”之間的臨界點,便是影片在敘事與視覺上需要把握的關鍵之維。在影片《冰河追兇》的開頭片段中,暴力兇殺的過程就被作為視覺動作的展現開啟了敘事懸念的設置,烏黑冰冷的鐵鉤、發出刺耳噪聲的電鋸、白雪覆蓋的冰湖,某種具備“互文”價值的視覺慣例元素引發了觀眾曾經在觀賞美國暴力驚悚類型影片《電鋸驚魂》《冰血暴》《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中獲取的恐怖體驗,使其產生了對暴力血腥場面的完型想象,而在影片本身的敘事呈現中卻成為了不可見的缺席。鐵鉤和電鋸用于殺戮道具的慣常使用被規避,僅僅成為切割冰面和拖行受害者的工具,冰下瀕死者的掙扎也只以魚群咬破尸體的腳面做出象征性的輕描淡寫,而非無節制地以殘暴的細節描述挑戰觀眾的心理承受底線,但卻在兇手緩慢而冷靜的行動中渲染出緊張的氛圍,構建出敘事的懸念。藝術作品對暴力犯罪過程的展示,因為題材內容及審美訴求的不可完全避免而對社會倫理道德規范有所僭越,這是由暴力本身的性質及其必然存在于社會現實中而不能為藝術忽視的事實所決定的,但這種僭越必須限定在合理的范圍內,需用藝術構思巧妙地完成審美表達與敘事推進。與對犯罪場面的描述相比,執法者的暴力動作呈現在影片中被更加嚴格地加以限定,因為代表秩序正義的身份本身對暴力行為的實施是持否定性立場的,而執法者暴力運用的“合法性”僅在于阻止犯罪的危害,如果藝術作品對其過度表述,就會在藝術和現實的雙重層面上違背主流價值的正確立場。因此在描述年輕警察汪豪于上海偵破綁架案的敘述中,僅僅以其跳橋追車、與罪犯打斗等可被視為“執法者”行動必要的暴力動作作為動作片的類型視覺元素加以呈現,而將打斗結束后暴力過度使用的表現予以回避,并在之后補充了公安領導對汪豪失度的暴力行為施以批評與懲戒的情節,在藝術文本內外完成了主流價值觀念對于暴力動作的嚴厲規訓。
現實指涉:倫理失范與貪欲泛濫的末路迷途
承認暴力存在的客觀性,能夠主動思考并將之作為命題提出,呈現在合乎情理的藝術表達中,這其實是中國電影創作觀念中現實主義傳統原則潛在的慣性指引,因為“在中國電影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現實主義曾擁有大一統的美學地位”[8]。而這種認知放置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場域中立本溯源,可以看到其深受儒家“文以載道”思想的影響,這一術語出自北宋理學代表人物周敦頤所著的《通書·文辭》中“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的表述,“是儒家論及文道關系的基本主張,意即文如車,道如物,正如車之用是為了載物,文之用是為了載道”[9],而文藝的價值,則被理解為“傳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觀念偏于教化目的”*“文以載道”參見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327.htm,2016-5-29/ 2016-9-17。。儒家傳統堅持的“入世”哲學,形成了以思想與學說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映、評判和影響的理念,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里潛移默化地銘刻在中國文化表述的無意識傳承中,關于涉及人與人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倫理規范在文藝創作實踐的具象展示中滲透著某種價值判斷。
影片《冰河追兇》除在類型片種混合運用中圍繞“暴力”兇殺案進行敘事營造和視覺呈現造就藝術審美的“奇絕”景觀之外,亦在案件本身涉及的事件中凸顯出對一定時期社會現象的反映,并隱含著具有傾向性的價值批判。皚皚白雪覆蓋的靜謐而冷厲的北方鄉村環境中上演的神秘兇殺案,在因緣際會的因果鏈條層層推進中,揭示出作為受害者被謀殺的幾個“金源提煉廠”合伙人,正是因為十年前所犯下的隱秘不為人知的罪行,而遭遇小村青年李永勝殘酷復仇的敘事線。如世外桃源般美麗鄉村的空間景致中,靜默地流淌著隱匿于時間長河深處的罪行,因急切獲取經濟利益的欲望膨脹,提煉廠的老板們不惜使用陽奉陰違的手段,將含有劇毒物質的工業廢水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到與村民生活用水息息相關的河流中,造成了村中出生嬰兒大量的先天殘疾。對金錢無休止的追逐動機以及于道德倫理的不屑與踐踏,是他們罪惡行為實施的基本誘因,秉承某種錯位的價值觀念,其行為早已逾越了中國傳統道德認知的底線。對于貪婪欲望的不加克制,在內心中丟棄的恰恰是儒家傳統倡導的“克己復禮為仁”的做人理念,“人們通過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最終使人與人之間擁有理性的仁愛、使社會走向有序的和諧”[10]的目標效果由此走向了反面。以欺騙手段遮掩罪行而罔顧內心良知,失卻了傳統儒家倫理規范中極為重視的“誠信之德”,也就失卻了“道德上立本……本體上立根……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11],人就變得不為人,而形同禽獸。良善倫理的失范造成正常秩序的崩塌,貪欲無德的惡因必然走向惡果,當金源提煉廠的老板們將良知拋卻之時,他們也將自身淪陷于惡的命運輪回中,于是被李永勝的父親發現不能示人的罪行,就為他人提供了敲詐勒索的機會,而使自己陷入危機的困境中。但李的父親也在自身貪欲引發的不當行為中走向末路,為解決危機的合伙人們使用了暴力謀殺的手段,用故意的縱火殺人滅口,斷送了李永勝一家的性命。惡因的線性推進造成了惡行的再度升級,參與謀殺的翁杰也遭遇合伙人疑似的陷害設計,在一場有意制造的車禍中失去了所有的親人,而作惡的老板們也未能逃離“惡理”的循環,被矢志復仇的李永勝用儀式化的手法,溺亡在曾經被他們肆意污染的河流中,而最終以暴制惡的李永勝也在無垠的冰河中了解了這段恩怨,就此結束了自身年輕的生命。在這條惡因推動的敘事情節線中,隱含了創作者對貪欲引發惡行而僭越傳統倫理道德規范造成人性迷失,使得社會失去了正常秩序良俗,讓互相加害的人們走向毀滅的必然結局的批判性表達。一種隱晦的現實主義指涉,可能與文藝觀念的表達習慣有關,呈現了“文以載道”傳統理念即使在強調娛樂功用的當下中國電影創作實踐中,依然在不動聲色地進行著有力的道德倫理的價值詢喚。
文明反思:人性呼喚與道德訓誡的雙重補償
以無節制的物欲釋放為起點,邪惡智慧指導的暴力相爭為路徑,“惡因”“惡行”“惡果”“三位一體”順序推進的因果鏈條造成人物命運的循環往復,影片《冰河追兇》以某種敘事演進的否定性價值展現,凸顯出自我批判現實的藝術態度和倫理立場。然則,文藝作品除用或明或暗的手法指涉評判現實之外,是否還應具備脫離具象之物外的抽象思考?在具體的表象事件的呈現分析之上,能否可從中概括出思想層面更有深度的開掘力與普遍性價值?
“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維坦》一書中關于‘叢林法則’和自然法的思想”[12]可以為深度理解《冰河追兇》所呈示的“惡行”循環提供某種邏輯認知的起點,“叢林法則”主張“弱肉強食”并把謀求個人生存與利益作為至上律令,因此將自我欲望實現凌駕于社會倫理規范之上,“利他”性便被視為無用累贅的存在,于是就“在不能得到和平時,他可以尋求利用戰爭的一切有利條件和功力”[13]去行事。以此看影片中講述的“惡行”,所謂“和平”的“惡”,不過是利用欺騙和敲詐的遮掩,而其無法進行下去時,直接轉變為等同“戰爭”手段的暴力實施的兇殺予以解決。回顧引發事件原點的“金源提煉廠”污染事件,影片在個體現象描述背后遷延的是某段時期為求經濟發展而罔顧生態環境的失當認知,其中或許凝聚著創作者對人類在工業文明發展初期的某種短視和狂妄的反思,那是人們迎來科技發展的飛越而首次取得對自然的比較優勢時,對于自我力量變強的沾沾自喜,因而對資源的開發和索取變得肆無忌憚,自以為是地認為能夠掌控一切。然而這一虛妄的認知,造成的后果何其嚴重,在影片中可以看到,由于提煉廠不加處理而直接將污水排入河中,而使飲用污水的村民誕下了無數先天畸形身患殘疾的后代。連續剪輯的空境運動鏡頭中呈現美到極致的北方冰原意象景觀,似乎在訴說著大自然無聲而靜謐的磅礴之力,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影片鏡語中承載的對自然的敬畏感與敘事推進的縫隙中暗含“生態保護”的觀念表述,契合的恰是老子“道法自然”命題論述中“以‘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自然地對待自然”[15]的思想,而直指“弱肉強食”的叢林生存法則,其中指涉的提煉廠污染事件,恰是對以暴虐的手段對待自然萬物,違背生命倫理之道的“現代工業文明天人對立關系”[16]的否定與控訴。
影片《冰河追兇》用敘事的暗線表述了一種對于文明興替沖突的反思,情節推進最終定位于“人性”與“道德”雙重層面相互牽絆的關系,指向籠罩在命運蒼穹下的迷路羔羊的最后歸途。之于“道德”,是以破敗的金源提煉廠為景觀呈現的后工業廢墟以及利用邪惡資本起家的幾個合伙老板難逃“因果報應”,盡皆溺亡于那條曾經承載著他們“貪欲”與“原罪”的幽靜冰河中的命定結局,以負向性的命運走向實現了“道德訓誡”;之于“人性”,是將人性看作“神性與獸性的合一”[17]的復雜構成,通過對尊崇“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獸性”“惡念”不加控制所帶來的破壞與毀滅的展現,相應地提出了以“神性”“善念”覺醒進行“贖罪”的方式完成對崩塌文明秩序的恢復與重建,《冰河追兇》中“翁杰/韓明”這個人物的行動軌跡就是符合這一“二元”設置的存在,“翁杰”是合謀殺害李永勝一家的兇手,“韓明”則是暗自資助李永勝完成學業以及幫助村中殘疾兒童的“善人”,兩者通過“容貌/姓名”的更替,完成了從“工業文明”“獸性”之惡向“自然文明”“神性”之善皈依回歸的象征隱喻。
結語:價值觀焦慮的語焉不詳與想象性解決
以雜糅并置的方式嘗試滿足商業電影感官審美與傳播接受訴求的表層范式構建,在敘事營造和視覺慣例的常態化設置中圍繞“暴力”元素的呈現,于情節的縫隙中切入道德倫理價值的現實指涉,是遵從中國電影長期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及儒家文化中“文以載道”文藝觀念的慣性表達,在此之上形成關于“工業文明”與“自然文明”、“叢林法則”與“靈魂法則”、“獸性”與“神性”博弈與興替的反思,影片《冰河追兇》企圖用道德訓誡的方式尋找涉及倫理現實與文明思索問題的正確答案,嘗試用呼喚人物內心至善的途徑完成對失范秩序的救贖。在作品結局之處,創作者通過設置李永勝跳入冰河解救與自己“恩怨”糾結的“翁杰/韓明”的方式,給出了一個過于理想的想象性解決方案。然而吊詭的是,一部涉及警匪類型并以兇殺案件為敘事核心要素的作品,其中警察的在場到底在事件的推進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而法律為何在左右敘事的傾向中成為了缺席的存在,就以年輕警察汪豪向刑警隊長周鵬的女兒——周欣怡講述自己做警察的父親如何因挽救失足墜樓的罪犯而被其反手殺害的故事為例,影片似乎提出了關涉“規則……正取代美德而成為道德訓誡的主要方式,現代道德的中心問題正發生轉移,以善為核心的美德被邊緣化”[18]的問題,意圖表現道德與法制之間在現實實踐中存在的矛盾,但其嘗試建立的“至善”信念道德訓誡卻因此表述而在不自覺間走向消解,可律法標準在調節社會關系方面的價值與功能呈現始終未能出場,因而基于批判現實需要而試圖表達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諸種裂變引發的價值觀焦慮及其言說立場,也就顯得模糊不清而又語焉不詳。在影片《冰河追兇》的結尾之處,創作者有意用慢鏡頭的畫面截取周鵬、汪豪、永勝、韓明與村中孩子們一起在潔白廣闊的雪地上快樂地踢著足球的和諧生活瞬間,試圖建立一種返璞歸真地回歸孩童時代的美麗夢想,但其也不過是中國文藝表現傳統中“始終無法擺脫的……一種向后看的特征,建構的是以桃花源為摹本的鄉土烏托邦”[19],這種將希望寄托于不存在時空中的“烏有之鄉”的描繪,也只能是某種心靈雞湯式的陳詞濫調。影片的價值觀表述呈現出保守主義的傾向,也許能以更加穩健的方式謀求商業電影的大眾接受訴求,但始終未能在更深層次上進行開拓性的人文思考與價值觀的現代化建構,不得不說是藝術表達和文化反思上的一大遺憾。
[1] 亞里士多德.詩學[M].楊周翰,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18.
[2] 藍凡. 動作性:戲劇性與電影性的追問[J]. 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09,11(1):93-100.
[3] 劉同亮,杜鵬. “審美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讀康德《判斷力批判》之“美的分析”有感[J]. 美與時代,2009,(10):32-33.
[4] 詹慶生. 審查還是分級?——中國電影的管理困境與轉型難題[J]. 電影藝術,2012,(2):72-79.
[5] 郝建. 類型電影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7.
[6] 羅伯特·考克爾.電影的形式與文化[M].郭青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22.
[7] 劉文寧. 告別輝煌年代——新世紀以來的美國警匪片創作風格[J]. 當代電影,2012,(3):119-122.
[8] 胡譜忠. 中國電影現實主義理論資源的流變[J]. 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03,17(2):43-47.
[9] 馮淑英. 儒家“文以載道”文學觀對古代小說總體構思的影響[J]. 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7,(5): 1-2.
[10] 張自慧. “克己復禮為仁”的因果必然性及其現代意義[J]. 孔子研究,2011,(5):4-10.
[11] 陳根法. 儒家誠信之德及其現代意義[J]. 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2,18(1):77-79.
[12] 鄭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叢林法則”與道德訓誡——探尋霍氏自然法思想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完善作用[J]. 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33(8):50-52.
[13] 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98.
[14] 老子. 道德經[M].高文方,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58.
[15] 帥瑞芳,張應杭. 論老子“道法自然”命題中的和諧智慧[J]. 自然辯證法通訊,2008,30(4):14-18.
[16] 陳夫龍. 歷史沉思和人性呼喚構筑的生命樂章——再論沈從文的小說《邊城》[J]. 畢節學院學報,2012,30(5):77-80.
[17] 夏世勇. 焦慮意識下的人性呼喚——王松中篇小說略論[J].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10,(3):81-84.
[18] 謝惠媛. 美德與規則——從道德訓誡方式的轉變看現代道德中心問題的轉換[J]. 甘肅社會科學,2012,(6):33-35.
[19] 吳曉東. 中國文學中的鄉土烏托邦及其幻滅[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3(1):74-81.
LostinWhite: A “Utopian” Vision in Presentation of Violence
YE Kai
In an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surface pattern of commercial films through a mix of genre, the filmLostinWhitecenters on the presentation of “violent” elements and inserts a realistic reference of morality and ethics, based on which different values of civilization are compared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m is reflected upon. The film intends to accomplish the redemption of confused order in the way of moral admonition; however, because of a vague expression of values and inability of imaginative solutions, it can only replicate “utopian” 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and cliché.
presentation of violence; mix of genre; realistic reference; reflection upon civilization; “utopian” vision
2016-11-25
葉凱(1978— ),男,山東泰安人,博士研究生,編輯,主要從事影視理論、創作與批評研究。
1674-3180(2016)04-0131-06
J9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