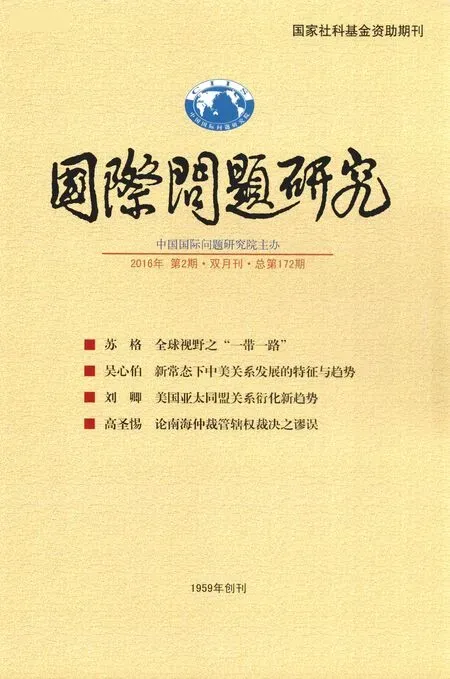美國亞太同盟關系衍化新趨勢
劉 卿
?
美國亞太同盟關系衍化新趨勢
劉卿
〔提要〕自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在深化與亞太盟國關系方面顯現新思路,包括采用更具靈活性的方式拓展與盟國的合作渠道、整合盟國與伙伴國的戰略資源等。美國亞太同盟呈現出向“軟同盟”拓展、向“影子同盟”衍生和向“分權”趨勢發展等特點。美國強化同盟關系的新做法,加大了地區國家間戰略消耗,但能否達到其預期目標還受東盟平衡政策等因素制約。面對新形勢,中國需繼續保持戰略定力,以“兩手對兩手”,妥善應對美國亞太同盟關系變化帶來的新挑戰。
〔關 鍵 詞〕美國亞太政策、亞太同盟、東亞安全
亞太同盟是美國維持亞太主導權不可或缺的依托。近年來,美國深化亞太同盟最為重要的因素是為了應對中國崛起。強化盟國合作是美國“重返亞太”和實施“亞太再平衡”的核心要素。
一、美國深化亞太同盟關系的趨勢性特點
美國亞太同盟是冷戰留下的重要戰略資產。冷戰結束后,美國歷屆政府均謀求保持、強化這一同盟關系,使其適應國際戰略變遷新趨勢和地區變化新形勢,服務于美國的亞太及全球戰略。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遭到合法性危機。由于蘇聯威脅的消失,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受到包括盟國在內的區內國家質疑,加之菲律賓、日本等國民族主義興起,導致美軍被趕出菲律賓軍事基地,美日同盟一度停滯不前,美國在亞太施展領導力的平臺出現動搖。然而,朝鮮核問題和臺海危機為美國延續同盟關系提供了契機。克林頓政府更新同盟條約,包括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簽訂《澳美21世紀戰略伙伴關系協議》等。進入21世紀后,美國及其盟國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怖主義威脅,在共同反恐的名義下,小布什政府賦予亞太同盟關系新任務,美日、美韓、美澳同盟關系超越亞太區域安全責任限制,涉足中東、中亞地區。因反恐戰線拉得過長,美國對亞太地區關注和投入相對不足。而在同期,亞太地區經歷了歷史上少有的快速發展期,區域一體化進展和地區力量的結構性變化使美國對該地區主導力顯現出局限性。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加快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開始將主要戰略精力轉向亞太,提出“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口號,尋求重塑亞太同盟關系。近兩年來,隨著從中東、阿富汗撤軍任務的完成,美國加快調整亞太同盟政策步伐,亞太同盟從合作內容、結構模式到權力運行方式均發生深刻變化,主要呈現以下趨勢:

日美同意加快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一是從“硬同盟”向“軟同盟”拓展,同盟合作空間擴大。在小布什政府重新調整亞太軍事基地布局的基礎上,奧巴馬政府繼續強化傳統軍事同盟“硬核”,夯實與盟友傳統安全合作內容,筑牢“美國治下”亞太秩序的骨架。近年來,美日、美韓、美澳和美菲同盟關系均得到不同程度深化,包括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延遲交韓戰時軍事指揮權、取得在澳達爾文駐軍權及重返菲軍事基地等。[1]Bob Work,“The Third U.S.Offset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artners and Allies,”January 28,2015,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06641/the-third-usoffset-strategy-and-its-implications-for-partners-and-allies.(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同盟政策不再局限于狹義的傳統軍事合作,還向新的“軟”領域拓展,通過“軟同盟”(soft alliance)撐開同盟合作彈性空間。在網絡安全領域,美國提出“加強與國際伙伴關系”倡議,推動盟國就共享網絡情報、開展網絡培訓等達成共識,先后與澳大利亞、日本等達成網絡協議,打造亞太網絡同盟雙引擎,構建虛擬世界的地區秩序。[2]The White House,“Cyberspace Policy Review,”2009,https://www.whitehouse.gov/assets/documents/Cyberspace_Policy_Review_final.pdf.(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在貿易領域,美國與韓國簽署自貿協定,加快推進美日自貿談判,同時推動完成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通過設立“高標準”和“21世紀貿易規則”,建立包括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國在內的貿易集團,并施壓韓國、泰國等盟國向其靠攏。此外,美國還與日本、澳大利亞等加緊打造“民主”、“自由”價值鏈條,向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進行民主滲透。“軟”領域合作的拓寬,為美國與盟國進一步深化軍事安全合作提供新的動能。
二是從“顯性同盟”向“影子同盟”衍生,同盟結構重新組合。奧巴馬政府重新組合盟國關系,在現有雙邊同盟基礎上拓展同盟關系新邊界,建立“影子同盟”(shadow alliance),以此重新定義亞太秩序。[3]Purnendra Jain and John Bruni,Japan,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ttle NATO or Shadow Alli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4.“影子同盟”以雙邊同盟關系為基本骨架,通過一系列雙邊或三邊非條約式的制度安排,將同盟國整合到一個分工協作的機制中,并有選擇地吸納地區伙伴國。在這一制度框架下,美國與盟國和伙伴國之間、盟國之間、盟國與伙伴國之間,尋求通過政治協商、外交協調、情報交換、軍事演習、能力建設等路徑,實現彼此間的橫向聯合,發展緊密的政治、外交和安全合作。盟國間合作并非源于正式同盟條約,而是通過非條約的制度安排。在美國大力推動下,日澳、澳韓均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安全合作“2+2”機制,尤其在軍事人員交流、裝備建設等方面實行對接。美國還謀求建立以其為中心的三邊關系架構:敦促日韓解決慰安婦問題,拆除日美韓三邊安全合作的政治藩籬;游說澳日潛艇技術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提高日美澳三邊裝備互操作性。這些三邊架構組合,部分彌補了過去單純雙邊關系的缺陷。[1]Bob Work ,“The Third U.S.Offset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artners and Allies”.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及盟國在當前雙邊及三邊防務合作安排基礎上,謀求與伙伴國建立一個公開、貌似非排他性的組合體,通過“自主選擇”將松散的參與方納入其中,促進建立一批可重疊的影子同盟關系。美國推動盟國拓展區內安全合作,將伙伴網絡化。這種安排沒有正式條約,看似不包括中國抑或美國在內,但事實上背后均有美國的影子。比如,日本與印尼建立外交與防務部長級“2+2”會議機制,日本、澳大利亞與印度提出組成新三邊組織倡議。[2]Harsh V Pant,“Trilateral Approach Comes to the Fore in Asia,”The Japan Times,August 20,2015.美國還直接上陣,推動建立美印日三邊對話機制,通過“對話”形式繞過印度不結盟政策,擴大與印度防務合作,通過追加多重雙邊或小多邊,強化與盟友、伙伴之間安全合作機制,實現戰略“再確保”(reassurance)。[3]Van Jackson,“The Rise and Persistence of Strategic Hedging across Asia: A System-Level Analysis,”in Ashley J.Tellis,Abraham M.Denmark and Greg Chaffin,Strategic Asia 2014–15:U.S.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t the Center of Global Power,December 2014,http://www.nbr.org/publications/issue.aspx?id=307.(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
三是從“集權”向“分權”過渡,同盟權力重新配置。奧巴馬政府調整亞太同盟體系內部權力結構分布,向同盟國讓渡或與其分享權力,降低同盟等級關系,謀求打造一個相對扁平化的同盟體系。[4]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休?懷特教授等認為,“分權”(sharing power)不僅存在于中美之間也存在于美國與盟國之間。有關“分權理論”參見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鼓勵亞太盟友承擔更多責任,在地區安全、外交等事務上發揮更大能動性。盟友在地區合作安排中被置于優先考慮地位,擁有相對自由選擇合作體的權力。近年來,日本、澳大利亞等在地區合作中的活動空間拓寬,在戰略對話、情報交換、軍備建設、論壇議程設定等問題上自由裁量權增大、自主性上升,美國向盟友轉移權力的過程亦是盟友為美國承擔更多責任的過程。比如,在美國敦促下,韓美同盟更具戰略性視野,兩國商討在韓國部署反導系統。美日修訂防衛合作指針,使日本在美國對外武裝干預行動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1]Gregory Elich,“The US-ROK Military Alliance: South Korea Caught in NATO’s Web,”Global Research,February 16,2015.美國增加日澳“雙錨”在同盟體系內部權重,使其成為亞太同盟“定海神針”。盟友之間也進行了權力再配置,日澳“雙錨”從過去的“北重南輕”向“南北并重”轉變,澳在同盟體系中分量大為提升。對盟友權力配置的調整,彌補了亞太同盟體系內部凝聚力不足的缺陷。此外,美國還向印度等伙伴國分權,在核合作問題上為印度網開一面,支持其從“向東看”(Look East)轉為“向東干”(Act East)。[2]Jayanth Jacob,“‘Look East’ Policy is Now ‘Act East’,”Hindustan Times,October 5,2014;Rahul Mishra ,“‘From Look East to Act East: Transitions in India’s Eastward Engagement,”December 1,2014,http://www.theasanforum.org/from-look-east-to-act-east-transitions-in-indiaseastward-engagement.(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
二、深化同盟關系新思路的戰略考量
美國深化亞太同盟關系的新思維,反映其在地區戰略力量發生結構性變化、盟國利益多元化和區域主義興起的大背景下,精心謀求“借力”、“聚能”、“蓄勢”,以在亞太長久維持霸權的良苦用心。
首先,調動盟國的戰略資源。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兩場地區戰爭和一場金融危機,戰略資源空前透支,權勢和威信受到沖擊,尤其是對亞太區域秩序把控能力下降。與此相對應的是,亞太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美國對霸權喪失的焦慮感空前。奧巴馬在上任后首次國情咨文中稱,美國要永遠維持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絕不當老二,但同時也切實感受到超級大國地位受到挑戰,面臨權威危機。[3]The White House,“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ddress to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February 24,2009,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address-joint-session-congress.(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美國領導地位源于自身實力,但這并不意味美國能夠或應試圖掌控全世界正在演變事件的軌跡;盡管美國非常強大并將保持這種強大,但美國的資源和影響力并非無限。當前世界形勢更加復雜,美國面臨的諸多安全問題難以快速、輕易地解決。”[1]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Feburay 2015,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美國意識到無力再繼續承擔維持霸權的高昂成本,其對外政策的能力與其維護至關重要國家利益目標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即便是維護同盟體系內部運轉,美國亦感到負擔沉重。部分國家善于坐享美國提供的保護,甚至為一己之私“綁架”美國。鑒于此,無論是主政的民主黨還是控制國會的共和黨,對深化同盟合作、撬動盟國杠桿維持霸權表現出高度一致性。為節省在亞太維持霸權的成本,美國力圖通過調結構、換方式加強對同盟的管理,盤活同盟資源存量,通過激活同盟與伙伴合作關系,提高同盟資源增量。修改同盟條約和建立新制度齊頭并進,既能將彼此力量和利益聚合在一起并加以利用,又能卸掉部分擔子,降低戰略風險。讓權是為了避免“搭便車”,更好地動員盟友及伙伴敢于擔當。但讓權并非撒手不管,而是根據對維持同盟貢獻能力的大小進行讓渡,且讓權方式靈活,美國始終保持對同盟控制的彈性。
其次,增強集團主義認識。奧巴馬政府任期之初,美國與盟國離心傾向隱現,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全球化縱深發展大背景下,美國盟國的國家利益多元化,美國對盟國的發展方向和在國際各領域的交往愈來愈不放心。盟國在地區利益、金融治理等問題認識上,表現出與美國不同程度的疏離感。即便是日澳這兩個擔負南北壓軸重任的盟國,也難以保證其國家利益與美國完全一致。日本民主黨政府以構筑“東亞共同體”為目標,強化對亞洲的外交,奉行疏美近華路線,引領亞洲國家改變由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模式。[2]Hiroyuki Hoshiro,“Building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in Vain: Japan’s Power Shift and Regionalism in the New Millennium,”IS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F-172,http://www.iss.u-tokyo.ac.jp/publishments/dpf/pdf/f-172.pdf.(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澳大利亞國家身份定位從西方白人國家向亞洲國家轉變,動搖了美澳關系是澳穩定與繁榮根基的傳統思維。[3]“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October 2012,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australia_in_the_asian_century_white_paper.pdf.(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同盟認同感降低令美國越來越擔憂其亞太地位可能面臨突發性危機,促使其反思和深化同盟關系。二是隨著共同威脅模糊化,美與盟友對這一粘合劑的感受越發不同。盟國不斷發出“不和諧聲調”,讓美國不能不心生憂慮。比如,韓國和菲律賓在對朝核問題上的認識存在天壤之別。日本與韓國、澳大利亞和泰國在認識中國問題上也有較大差距,日本認為中國是直接威脅,但后者認為中國是最重要的貿易伙伴而非直接威脅。在沒有十分明確的共同敵人和現實安全威脅的情況下,美國對盟國的軍事控制十分有限,已不能收到預想的成效,危機感上升,[1]Jaechun Kim,“Alliance Adjustmen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onvergence of Strategic Perceptions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ROK–US Alliance,”Pacific Focus,Vol.30,Issue 1,April 2015,pp.33–58.美國強化集團認同迫在眉睫。為防止盟友分道揚鑣,美國加快更新同盟政策,通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將更多的事務和國家納入體系之中,使之受制于同盟規則。在這種戰略及政治思維指導下,美國巧借區內國家政治博弈,制造和利用地區危機,塑造共同威脅的共識,凝聚人心。
最后,遲滯東亞區域主義進程。近年來,東亞成為許多倡議和提案的焦點,這些提議旨在實現特定的地區愿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倡議并不都以“東亞”為中心,而是超越傳統的地理概念,輻射更為廣泛的地理范疇。隨著地區倡議的落實和推進,各層次地區合作機制蓬勃發展,推動亞洲觀的興起及亞洲內生秩序的加快形成。東亞區域主義的崛起,將日本、韓國等盟國深深卷入這一進程之中,并波及澳大利亞等處于亞洲邊緣的盟國,沖擊了美國亞太同盟體系。[2]Malcolm Cook,“Japan’s East Asia Community,”The Interpreter,September 25,2009;Motoshige Itoh,“Thinking about an East Asian Community,”November,2010,http://www.nira.or.jp/1001english_summary.pdf.(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盟國不得不在區域進程和與美合作中做出平衡,甚至舍棄某些同盟利益而顧及地區整體利益。[3]Toru Oga,Mike Mochizuki,and James Przystup,“The U.S.- Japan Role in Building an East Asian Community,”Feburary 28,2013,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2/28/u-s-japanrole-in-building-east-asian-community/fg6v.(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針對此種趨勢,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積極加入部分地區合作機制,并在議程設置、方向選擇等問題上攪局,還通過深化同盟合作將日本、韓國等從東亞區域合作進程中拉回。一是通過給盟國賦權,擴大同盟合作彈性空間,進一步定格東亞安全格局。利用東亞地緣政治弱點,謀求打牢朝韓、中日、中菲、中越關系死結。借助強化軍事訓練等措施深植同盟文化,使澳大利亞、韓國等在中美之間搖擺的國家向同盟關系傾斜。二是通過利益置換,重新整合地緣經濟資源,使盟國及地區伙伴被裹挾于美國主導的規則之中。奧巴馬在TPP協議達成后發表聲明稱,美國不能讓中國等國家來書寫經濟規則,而應由自己制定這些規則。[1]Jackie Calmes,“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is Reached,but Faces Scrutiny in Congress,”New York Times,October 5,2015.目前,TPP已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4個東盟國家,泰國、印尼、菲律賓、柬埔寨等東盟國家和韓國表示有意參加。TPP談判完成和越來越多的東亞國家參與這一協定,勢必稀釋和沖淡東亞區域主義。
三、深化亞太同盟關系面臨的制約因素
亞太同盟是美國在亞太戰略上的既得利益,維系亞太同盟是美國亞太戰略不可或缺的一環,將伴隨美國在亞太維持霸權全過程。未來無論哪個黨派上臺,都將會檢討奧巴馬政府亞太同盟政策得失,并謀求進一步加快更新同盟政策。但美國能否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還取決于一些限制性因素。
(一)東盟對美國亞太同盟政策的掣肘
其一,東盟平衡政策對沖美國同盟政策。東盟國家長期奉行大國平衡政策,以便獲得更多回旋空間。東盟一方面希望美國保持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以應對中國崛起,并在與其他戰略力量對話中增加籌碼,另一方面擔心美國熱衷于做地區國家軍事合作的經紀人,將導致地區軍事因素增加,尤其是造成中美關系緊張升級。東盟國家希望在經濟上繼續發展與中國的關系,需要一個穩定的地區環境。如果美中競爭特別是軍事競爭加劇,這些國家將面臨選邊站隊的難題,其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也將受到沖擊。東盟國家希望中美相互開放、良性互動,在積累合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碼的信任關系,不希望冷戰集團思維在該地區復活。[2]Kishore Mahbubani,“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the West,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Public Affairs,March 4,2014,p.145.東盟主張以合作安全作為地區安全治理的功能模式,同時堅持對區外大國實行對沖戰略,既追求與美國的安全合作,又保持與美距離,兩種趨勢并行發展。美國如何應對這種發展趨勢,需選擇適中的同盟政策思路和原則,尤其是在對待菲律賓這樣的東盟盟國問題上,否則可能因偏激的同盟政策損害與整個東盟的關系。
其二,東盟中心地位比肩美國中心地位。東盟追求并著力打造自身在東亞合作進程中的“議題倡導者”、“進程設計者”和“規范供給者”角色,強調自身在地區一體化中的“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但美國深化同盟關系政策使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中心地位面臨挑戰。[1]Vikram Nehru,Donald Weatherbee,“The Myth of ASEAN Centrality,”February 20,2014,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2/20/myth-of-asean-centrality/h07b.(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東盟共同體宣布成立,標志東盟一體化已站在新的起跑線上,成員國在經濟、政治、安全等領域越來越走向一體。美國在雙邊同盟與伙伴關系基礎之上打造“混合型”亞太同盟體系,旨在進一步強化美國中心作用,將弱化非同盟和非伙伴國家在地區事務中的作用。東盟中心和美國中心對陣,并呈現兩極化傾向。美國深化同盟合作,尤其是與菲律賓等東盟成員國進行戰略捆綁,為東盟安全共同體建設設置障礙。菲律賓等作為美國重點扶持的對象,容易從美國中心和同盟戰略出發挾持東盟,使其服從于美國亞太戰略。美國利用菲律賓等“特洛伊木馬”,在某些敏感問題上強人所難,牽制東盟處理地區事務的獨立性,引發東盟對美同盟政策的反彈。在美國首次舉行的美國—東盟非正式峰會上,東盟抵制美國壓力,拒絕隨美國指揮棒起舞,未同意將南海問題寫進共同聲明。[2]Prashanth Parameswaran,“A US-ASEAN South China Sea Failure at Sunnylands? ”The Diplomat,February 19,2016.東盟在與美國地位競爭中被矮化,增強了重構中心地位的迫切性,對美國的分外之想進行牽制。
其三,東盟開放主義對沖美國集團主義。東盟成功的經驗在于秉持包容、合作的開放精神。東盟“10+1”、“10+3”、“10+6”機制的形成,最大程度包含了地區大國和世界大國。開放性是東盟的生命力和動力源,東盟在“10+X”基礎上積極致力于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和亞太自貿區(FTAAP),就是這種開放精神的延續。但美國強化同盟自貿協定和軍事安全協作,事實上形成了閉合小集團,不利于東盟開放主義進程。美國強推TPP,以所謂的“高標準”拉攏一派、排擠一派,已造成東盟國家內部合作分歧。[1]美國有選擇地吸納部分東盟國家,使東盟在與美國對話中處于不平等地位。再者,美國深化同盟關系,從安全、意識形態再到貿易合作等領域將亞太國家進行區分,增加地區國家互疑,阻礙東盟與區內國家互動關系,或將引起東盟反彈。
(二)美國國內對同盟政策爭議
長期以來,美國國內就存在對同盟作用利弊的爭議。同盟重點論認為,同盟合作應列為美國亞太政策之首,亞太政策應以同盟政策為根基。同盟是美國在亞太前沿部署的重要依托和安全屏障。反過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關系幫助該地區保持穩定,為該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主轉型提供了重要保證。[2]但持懷疑論者認為,不應高估同盟價值,正是同盟政策使美國在亞太陷入困境。[3]盟國與美國存在利益分歧,甚至存在“綁架”美國的風險。例如,美日是盟友,但日本所為并不一定符合美國利益,而如果不對其表示支持,美國信譽就會下降和受損。從同盟條約來說,盟友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敵人,但實際上并非如此。中日因歷史和釣魚島等問題彌漫敵對情緒,但美中并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沖突。所以,問題不在于中美之間,而在于中國與美國盟友之間。部分人還對盟友的忠誠度表示擔憂。冷戰設計師喬治?凱南曾把美日同盟稱為“反常的親密關系”,建議這種“建立在沖突與痛苦基礎上”的關系不宜走得太遠、太快,需保持對日警惕。[4]安倍政府在歷史和戰爭問題上的模糊認識,暴露了日本經久不去的、復雜的“美國觀”,印證了凱南的政治遠見。日本遠非單維度的親美立場,安倍的動機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深化美日同盟關系恢復日本榮耀,重獲日本在安全事務上的話語權。[1]Peter Ennis,“Obama and Abe: US Taken for A Ride?”Dispatch Japan,May 6,2014.總之,同盟既是美國增強權力、運用權力的工具,但同時也是美國的負擔。
[1] Shohib Masykur,“How TPP can Disrupt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Jakarta Post,January 6,2016;Jingyang Chen,“TPP and RCEP: Boon or Bane for ASEAN?”September 9,2015,http://asiafoundation.org/in-asia/2015/09/09/tpp-and-rcep-boon-or-bane-for-asean.(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
[2] Michael J.Green,Kathleen H.Hicks,Mark F.Cancian,John Schaus,Zack Cooper,“Asia-Pacific Rebalance 2025,”http://csis.org/publications/browse/all/all/all?page=8.(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
[3] Ted Galen Carpenter,“The Japan Dilemma: Asia’s Next Geopolitical Nightmare?”The National Interest,April 26,2015.
[4] Kenneth B.Pyle,“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21st Century,”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ovember 13,2012,http://www.nbr.org/research/activity.aspx?id=296#footnote1.(上網時間:2016年2月20日)
世界上沒有“仁慈霸權”,當美國與盟國建立起令人望而生畏的強大力量且專注于一國時,很難讓潛在的對手不做出反應。
美國亞太同盟政策存在先天缺陷,使美國不得不在中美關系中尋找平衡。以基辛格為代表的戰略家認為,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美國在亞太的相關政策應由此展開。中國從外交戰略上宣誓不做地區霸權、不挑戰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認為太平洋足夠大,能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中國主動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意在向美國傳遞善意,不想與美國搞對抗。中國不是原蘇聯,中美關系不是“零和關系”,美國對華政策大框架應是“兩面下注”,既接觸、又防范。但如果美國試圖籠絡盟國遏制中國崛起,那么先前那些可怕的預言就可能成真。[2]Jeffrey A.Bader,“Changing China Policy: Are We in Search of Enemies?”Brookings China Strategy Paper,No.1,June 2015;Marvin Kalb,“China is Not the Soviet Union,”January 10,2012,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2/01/10-china-kalb.(上網時間:2016年2 月20日)中國不是一個必須加以遏制的貪婪擴張主義者,其戰略意圖至多是不透明的。雖然近年來中國采取了更堅定自信的外交政策,但其本質依然是防御性的。[3]Johan Glaser,“Avoiding War With China: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December 31,2015.遏制中國的戰略不僅成本高且風險大,對于維護美國重大國家利益并不具必要性。因此,美國在遏制中國問題上須保持謹慎。深化與盟友合作是為了打消盟友及伙伴的疑慮,表明美國對軍事同盟的承諾負責,但美國要避免被中國誤判為是破壞其在該地區利益的遏制戰略。部分人士擔心,以對抗中國為目標的同盟戰略將給美國帶來經濟上的風險,還可能使美國更難以得到中國在朝核等關鍵問題上的合作。諸多跡象顯示,中國對美國深化亞太同盟網絡的認知已發生了重要變化,美國應避免顧此失彼的戰略錯誤。
美國亞太同盟網絡不可能永遠以目前的形態存續下去,維護美國亞太利益不僅要以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做補充,還需建立一個包括美國在內、反映本地區其他國家利益的地區框架。未來的亞太秩序將部分地保持舊的秩序,如美國保持與盟友密切關系,還應增加包括中美合作共處等新的內涵。雖然地區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但如果美國及其盟國能夠意識到這種變化的復雜性,就可以找到一種和平發展的共存方式。中美兩國沒有哪一國會崩潰,也沒有哪一國會退出亞洲。美國應接受一個在亞洲擁有更多權利、更大聲望并擔負更多責任的崛起的中國,而中國也應承認美國在東亞的深層戰略利益,包括美國與亞洲盟國的安全關系。現在關鍵的挑戰是,構建一種可以有效緩解安全困境、有效管控各種危機同時規范各種競爭的地區機制。[1]約翰?艾肯伯里:“未來將是一種討價還價式的中美關系”,《國際先驅導報》2010年12月21日。鑒于此,美國需要在盟國和中國之間尋求一種妥協的制度安排。
(三)盟國對美國同盟政策的“再平衡”
美國力圖將同盟利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但現實上很難做到,盟國自身的利益偏好使美國亞太同盟政策打折扣。
一是盟國對華利益與同盟利益存在偏差。韓國、澳大利亞、泰國等盟國與中國經濟關系密切,在貿易、投資和人員往來等方面對中國市場的需求已超過美國。這些國家與中國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視中國為機遇而非直接威脅。即便在某些問題上與中國出現外交摩擦也屬正常,雙邊關系總體健康、穩定并在逐年加深。中國始終以積極、建設性的姿態發展與這些國家的關系,使其對中國的信任增加,雙方安全合作和軍事交流逐漸擴大。這些國家理解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對其施壓,但也試圖向美國解釋其自身利益與同盟利益的不一致性,在某些問題上甚至不顧美國反對而堅定自己的立場。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過程中,盟國與美國利益出現偏差,與美國關系一度緊張。韓國、澳大利亞等認為,亞投行將為亞洲創造共同投資和增長機遇,應在其成立階段加入。而美國則反復對盟國施壓,聲稱不應遷就中國,認為這不是同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1]Jamie Smyth,“Australia to Join China-led Bank Despite US Opposition,”Financial Times,March 28,2015.部分西方媒體對此感慨稱,盟國追求自身利益而“棄美投中”。[2]Mike Bird,“China’s New Development Bank is becoming a Massive Embarrassment for Obama,”Business Insider,March 31,2015.在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行動中,即便美國財長雅各布?盧等高官頻頻對盟國發出警告,稱不能讓中國增強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地位的計劃得逞,澳大利亞、韓國等關鍵盟友還是出來為中國站臺。
二是盟國與美國在地區利益問題上不一致。亞太是韓國、澳大利亞等盟國安身立命之所,其地緣政治利益和地緣經濟利益與美國不盡一致。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方向選擇問題上,澳大利亞等樂見美國主導的TPP在推動亞太經濟合作中發揮接力作用,但美國則過度強調以TPP劃線的地緣政治價值。澳大利亞等認為,TPP最終應與RCEP匯合,共同推動建立更大的亞太區域貿易體系,主張將中國納入TPP進程之中。澳大利亞、韓國均有“中等強國”抱負,力爭在地區事務中擺脫對美國的依附,制定獨立的外交政策,發揮獨立作用。[3]Tanguy Struye de Swielande,Bruno Hellendorff and Alexia Honoré,“Australia: A New Strategy for a Medium-Size Power,”Politique étrangère,2015/1 (Spring);Carl Ungerer,Simon Smith,“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 Middle Power Cooperation and Asian Security,”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Strategic Insights,October 29,2010.這些國家在處理地區摩擦問題上與美保持一定距離,并非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在地區利益上挾持盟國而謀一己之私,將引發盟國的不滿。[4]Malcolm Fraser,“America: Australia’s Dangerous Ally,”The National Interest,December 16,2014.盟國地區利益觀的形成和走向成熟,將引發這些國家對美認識上的新變化,進而將轉化為“去美國化”的政策動力。
四、結語
美國同盟思維根深蒂固,是美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近年來全球戰略重心加速東移,亞太同盟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上升,深化同盟合作有了新動力。
奧巴馬政府深化亞太同盟關系的基本思路不同于其前任:擴充了同盟合作內容,尤其是增加了軟領域合作,剛柔并濟,擴大了同盟合作彈性空間;強化同盟體系緊密度,將盟友之間橫向合作置于優先考慮,同時拓展同盟體系邊界,通過自身和盟國的雙多邊安排的配合,將伙伴國納入其中,形成隱性同盟關系;通過對盟國讓權,打造相對扁平化的同盟體系,讓盟國更加深入地介入地區事務,降低同盟運轉的成本。奧巴馬政府同盟新思維,反映了美國外交哲學中折中主義成分上升,多邊主義和單邊主義褪色。[1]Van Jackson,“The Rise and Persistence of Strategic Hedging across Asia: A System-Level Analysis”.美國博采眾長,凝聚盟友和伙伴的力量,動員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對盟友取予結合,為其所用。
但是,美國深化亞太同盟關系的政策目標受諸多因素限制而難以輕易實現,包括國內政治對以同盟為中心的亞太政策分歧、盟國及地區國家利益日益多元化、東盟平衡者角色的掣肘等。美國亞太同盟政策固有的缺陷,包括在處理某些敏感問題上被盟國綁架的風險,勢必導致美國在處理與其他國家關系問題上顧此失彼。
美國深化亞太同盟關系建立在高度意識形態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上,包含冷戰因子。它以陣營劃線,不具開放性,有形無形中制造地區國家的隔離和疏遠,讓地區國家彼此進行戰略消耗。面對美國抱殘守缺的同盟戰略,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以“兩手對兩手”,化解美國深化同盟關系帶來的挑戰;繼續堅持不懈地做好增強中美互信工作,促其相向而行,共同建設新型大國關系;妥善管理同盟因素對中美關系的沖擊,堅決反對美國利用亞太同盟壓制中國合理合法的國家利益和安全空間;繼續深化與周邊國家睦鄰合作,尤其是繼續著力強化與東盟關系,共同促使美國參與建設更具開放性、包容性和建設性的地區安全機制和經濟一體化架構。
【完稿日期:2016-2-25】
【責任編輯:李靜】
〔文章編號〕0452 8832(2016)2期0040-14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D871.2
〔作者簡介〕劉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代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