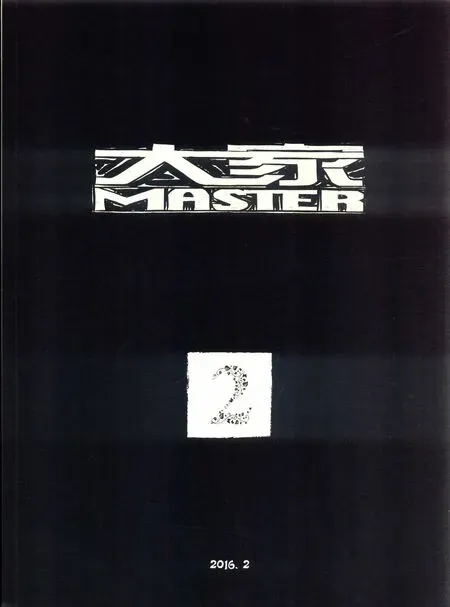小說與負面經驗(主持人語)
∥耿占春
?
小說與負面經驗(主持人語)
∥耿占春

耿占春,文學批評家。80年代以來主要從事詩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主要著作有《隱喻》《觀察者的幻象》《敘事虛構》《失去象征的世界》《沙上的卜辭》等。另有思想隨筆和詩歌寫作。現為大理大學教授、河南大學特聘教授。
看來《大家》雜志的“先鋒新浪潮”并不必然意味著倡導一種純粹的形式試驗,也是為著鼓勵人們尋找一種新的聲音、一種新的敘述口吻,或一種與眾不同的可能有點極端的話語,來傳達特殊的體驗。就本期的兩篇作品而言,這種體驗的特殊性并沒有讓它們失去與社會的直接關聯。事實上,在學群、震海兩位作家的小說中,人物的內心世界遠沒有他們的社會寓意更令人感興趣。
學群沿襲了他去年發表在《大家》雜志上的小說篇名,就像學群上一篇“壞家伙”的敘事一樣,《壞東西》繼續以一種“壞人”的敘述話語、以一種社會地位低處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就像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或阿來的《塵埃落定》從智障者或弱智者的視角講述故事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一樣,他們都能夠看待一個偽裝得較少的世界。“壞家伙”因為從不偽裝自己,也就看到或感受到一個更真實的世界。與“好人”不同的是,“壞家伙”就是讓他自己的生活邏輯與世界的邏輯相一致,而且就像人物自身所說的,這樣他生活起來也就“更容易一些”。
震海的小說與學群小說的風格迥異,或許因為他同時是一位詩人,小說的敘述采用的是詩歌式的并置而非線性敘述,沒有連續性的敘述,甚至沒有清晰的主題,僅僅是城市生活場景的一個瞬間,或對幾個瞬間場景拼貼性的組合。在震海的這個短篇里,酒吧間的每個人物都是他人生活與情感的“闖入者”,每個人都是意外的、偶然的、陌生的存在,而或許正是出于這種偶然性與陌生感,生存的某個瞬間顯得極其神秘或隱約的恐懼。在某種意義上,“闖入者”是對一種特別當代性的城市生活或大眾生活場景的諷喻。《壞東西》和《闖入者》表征著兩個不同的人群頗具當下性的生存狀態,但二者的一個相似之處是對當代社會生活中的負面體驗有相當極端的描述,并力圖在生活的低處尋找生活的意義。
責任編輯:陳鵬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