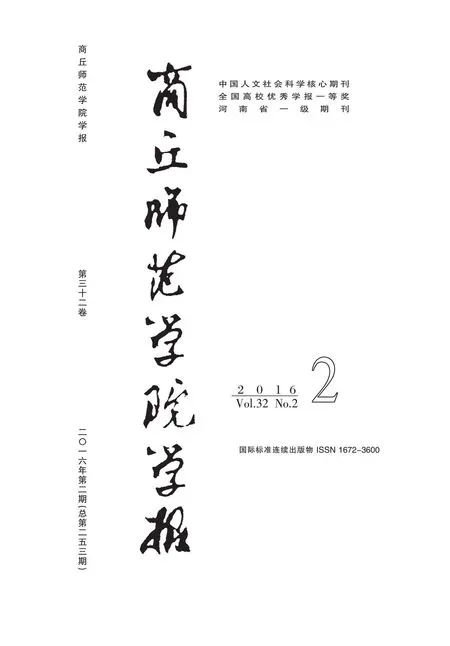論《莊子》中的“圣知”與“齊一”
?
論《莊子》中的“圣知”與“齊一”
[美]艾斯克·簡·莫卡德
(美國羅德島大學)
《莊子》一書有多種維度,可從多個角度闡釋,以下本文將主要闡述其哲學深度。但這一討論一開始就陷入了僵局。眾所周知,哲學是希臘文明的產物,因此就本質特性而言,其與《莊子》是異質的,但據此就否定《莊子》蘊含的哲學深度似又有悖常理,因為正是這一僵局成了學界綿綿不休辯論之源泉。本文提出的淺薄觀點希冀能對這一討論的延展有所幫助。如果恰如吉爾斯·德里烏茲和菲里克斯·瓜塔里所言,“絕圣”乃哲學誕生之必要前提(德里烏茲&瓜塔里,1994:3),那么可以說《莊子》開創了中國哲學研究之先河。如我們以下將討論的一樣,在《莊子》中“圣知”是被擯棄的觀念,但憑借友人相助及民眾共有的知性,就可實現對齊一(平等)和自由的追求。
《莊子·胠篋》中關于“圣知”的批判
根據《莊子·胠篋》,國之君主乃大盜,換句話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為鞏固自身地位,君主自然需要有一定合法性,因而作為提供這種合法性意識形態的“圣知”就被利用來保護竊國的大盜們。圣知和竊國大盜是同一事物的兩面,二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儒家學者會提出反駁,認為應區分儒家“圣知”和腐敗的國家權力。盡管在皇權時期儒家學說是腐敗和專制政權的意識形態支柱,但在歷史上也出現了眾多不受權力腐蝕挺身為人性和正義而戰的儒學之士。毋庸置疑,這是事實。但這一駁斥忽略了道家對“圣知”批判的核心問題,即恰恰是由于深信在腐敗朝廷中存在著正義的核心群體,百姓才甘心順服于客觀存在的朝廷政權,就好比草總是隨風而倒。
《莊子·胠篋》指出,國君是大盜,他們不僅僅是扒開你的衣袋,竊取你的錢夾和搶奪你的房屋及田地。那些倡導圣知的人是更為強大的盜賊。圣知掠去的是人們的自然知性(natural intelligence)。圣知如何掠去人們的自然知性呢?通過將“德”具體化,或如《莊子·胠篋》所言,“外立其德”(《莊子》10/25/19,數字依次為章節、頁碼和行數,下同)。換言之,在社會秩序中“德”被具體化為“君子”和“禮”。統治者教導普通民眾:“德”不是民眾自身所具備的品質,而是一種他們必須服從的外在標準。為了達到這一外在標準,民眾必須遵從那些知曉“禮”的深奧含義的人的指引以及效仿“君子”的言行舉止。原因很簡單,普通民眾無法理解這些道理(《論語》8.9;《孟子》7A5)。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普通民眾逐漸喪失了他們的自然知性。
被掠去自然知性的民眾從此變得愚昧,進而無法進行自我管理。民眾就像孩童或羔羊,只能由精明的統治者及其儒學官員所教導。不過,關于民眾的此類觀點并非為儒家學者所特有,哪怕是在現代社會,這類思想也是普遍存在的。對于啟蒙改革家而言,民眾是沒有原則的,如一盤散沙,難以建立新的社會。對于民族主義者而言,普通民眾缺乏道德資質,所以難以成為具有斗士般獻身精神的公民并參與國家的創建。對于共產主義者而言,普通民眾意識不到他們的階級利益,因此必須接受政黨教育改造并且需要依靠政黨的推動才會采取行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民眾被視為自私的消費者,只能由深諳經濟的技術專家控制和管理。道家對圣知的批判或許有其特定目標,即儒家學說,但同樣有著普適意義。
引進了圣知思想的世界被一分為二:那些具備圣知的和不具備圣知的。引用毛澤東(1893-1976)的話,儒學屬于“一分為二”的激進人本主義。在儒學中,道分為二,即仁和不仁(《孟子》4A2)。德也分兩種:君子之德似風,小人之德似順服于風的小草(《論語》12.19)。知同樣分兩類:先知和被先知所喚醒的后知(《孟子》5B1)。一如人道與非人道的區分掠奪了整個族群,即那些沒能遵從恰當禮儀的野蠻人的人性,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德掠奪了普通民眾的德性,具備圣知與不具備圣知的區分掠去了普通民眾的自然知性。
當圣知思想興盛之后,社會世界就建立在具備圣知和不具備圣知的劃分以及德的具體化之上。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世界,人們失去與生俱來的視覺、聽覺和理解的能力,在具體化的“德”的場景中他們感到眼花繚亂、壓力重重和迷惘不已(《莊子》10/25/18)。更為糟糕的是,這一外部世界全然無序的狀態被當做最高秩序(即“圣法”)呈現在民眾面前。為了讓民眾恢復感知和重獲理性,有必要拋棄這一圣法。《莊子·胠篋》認為,人們一旦摒棄了圣法,“民始可與論議”(《莊子》10/25/14)。一旦圣知被棄絕,普通民眾就能作出理性思考,并能以平等地位進行邏輯思辨。誠然,這在兩千年前是一個好消息,而在今天仍然是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消息。不過,這一觀點與儒家政治意識形態完全相反,因為孔子教導人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16.2)。很顯然,假如民眾無法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自然就無法和其他人一起共同進行理性思考。
正如一旦圣知被棄絕,自然知性就會出現一樣,一旦“德”的外在具體化被摒棄,“德”就自然顯現。《莊子·胠篋》鼓勵人們把人性和正義丟到一邊,因為那樣“天下之德始玄同矣”(《莊子》10/25/17)。這就是說,當人們拋棄了外在世界具體化的德行(virtue),即將人們劃分為君子和小人的“德”,人們就回到了真正意義的“德”即“完整”(integrity)。(道家在相反的兩個意義上使用“德”,我將他們分別理解為“德行”和“完整”。)在“完整”的層面,民眾是平等的,即“同”;莊子稱之為“同德”(《莊子》9/23/24),因為“完整”不會將人們區分為君子和小人,而是從最初就屬于所有人。這種“同德”隱秘且玄妙,但它的奧妙并非因其異乎尋常;相反,它異常普通,如此普通以致很難被人們觀察到。
圣知與自然知性
《莊子·外物》篇講述了有關一只神龜不幸遭遇的怪誕故事。某君王夜里夢見有人披頭散發說,他來自深淵,作為清江的使者出使河伯的居所,現今被漁夫捕捉。君王醒來后派人占卜,回答說:“這是一個被漁夫捕捉的神龜。”君王于是命令漁夫來朝獻上神龜。白色的神龜送到后,侍從們建議君王將白龜剖開挖空,在其殼上鉆孔,用火燒,然后研讀殼上的龜裂以占卜吉兇。于是他們殺了神龜,在殼上鉆了七十二個孔,所做的占卜沒有一點失誤(《莊子》26/78/11-18)。
這則寓言的寓意是“知”能使人陷入危險之中,即便是“至知”(ultimate knowledge)也無法確保安全。神龜有超凡能力占卜吉兇,但卻未能逃脫被殺的悲慘境遇。這則寓言最后告訴了人們三層哲學意義:首先,人們被告知要“去小知而大知明” (《莊子》26/78/19)。這就是說,大知并非需要通過努力才能獲得,當擯棄小知時,大知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這里的“大知”就是人們的“自然知性”。在寓言中,“小知”指的是“圣知”,也即那只可憐神龜逢占必準的非凡能力。此外,該寓言還暗示小知(即圣知)是為政權服務的,而擁有圣知的人深陷政權之網,因此注定是處于厄運的危險之中。
第二層意義與第一層緊密相關。人們被告知要“去善而自善矣”。正如《莊子·胠篋》篇所討論的,在《莊子》中有兩種德,即在外部社會秩序中具體化的德行和人們自然內心的“完整”。“完整”意味著一個完善健全的自我,而不是被外部強加的德行所影響或肢解。具體化的德行將導致自我本性的支離破碎,因為正如老子所言,“善”之所以為“善”,是因為有“惡”的存在(《老子》2章)。在《莊子》中,“完整”是一種內心精神狀態,這種狀態不會將世界分為“善”與“惡”。人們應摒棄的“善”是在外部世界被具體化的德行。當這一外在的“善”被丟棄,那么人們就自然獲得“自善”(to be good of oneself),即不會界定“善”與“惡”的“善”。“自善”即完好保持自我原有的自然秉性,這種“善”有別于根據外在社會標準而成就的“善”。
在一個家喻戶曉的寓言中,孔子對出身門第高貴的盜跖說,他有諸多的德行還四處游蕩搶掠,實在令人感到羞恥。如果能聽從孔子的些許教導,他一定能成為賢明的君主。盜跖回答說:即使你不當面吹捧我,我自己難道不知道嗎?(《莊子》29/87/17)這里有必要強調“自知”這一概念并將之與上文中的“自善”相比較。“自知”與通過贊譽(德行具體化方式之一)后形成的自我認識不同。如果孔子贊譽你的德行,或許你不會像盜跖那樣有勇氣和膽量依據自己的認知站穩立場,你可能會被孔子的優越知識所左右。如果那樣的話,孔子就掠去了你的自然知性,但盜跖正義凜然地對孔子說:“天下沒有比你更大的強盜了,真不明白為何全天下不叫你作盜丘,反竟稱我為盜跖?”(《莊子》29/87/30)諸如孔子這樣的大盜橫行天下時去堅守自己內心的善,也即自然的善,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孔子和其他大師們強加的“然”(即德行的標準)掩蓋了“善”和 “知”的自然本性。
因此,《莊子》敦促人們棄絕強加的“善”,使自善自然顯現;擯棄強加的“知”,尤其是“圣知”,使強大的自然知性自我再現。這種自然知性就是“明”,莊子提議以“明”取代哲學派系強加給人們的“是”與“非”(《莊子》2/4/13-14)。盜跖的故事是道家思想的經典例子,表明一種善于使用自身的“知”而不是依賴社會秩序中具體化的“知”的勇氣。在康德的術語中,這就是自知的勇氣,也就是使用自我的“知”以擺脫外在影響,從而獲得自主能力。
誠然,《莊子》中的道德自主性與康德的道德律令不同。在《莊子·田子方》篇中,老子告訴孔子如何讓人的思想回到原初之混沌虛無之境,即達到至美和至樂。孔子對此印象深刻,認為這種完美的德行一定是修養心性所致。不,老子回答說,這與任何修養無關,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夫水之于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莊子》21/58/9-11) 天、地、日月的德行是因為它們自然如此。同樣,自我也不是靠修養而成的。《莊子》中的其他論述也斷然否定了自我修行是達到至圣的必由之路。例如,在《莊子·刻意》篇中,人們被告誡要摒棄的不僅是儒家的行為規范,而且也要棄絕所謂的“道教”修煉,只需要在與天之德性相合的自然虛靜和澄明中息心即可(《莊子》15/41/1-25)。
《莊子》有關大全(great perfection)和大知(great knowledge)的闡述可能會使人們聯想到禪宗某方面的“頓悟”,但在《莊子》里大知不是什么神秘或者玄奧的知識。在《莊子·外物》篇中有關神龜故事的結尾,我們知道所謂的大知就是人們最本原的知性,是并不需要等待教導后才能激活的認知能力。這就是神龜故事的第三個也即最后一個哲學啟示:“嬰兒出生后沒有高明的教師教導,他們也能學會說話,因為他們與會說話的人自然相處。”(《莊子》26/78/19-20)嬰兒并不是聽從了教師的教導,而是在生活環境中鍛煉他們的認知潛能從而學會說話。這種原本的知性即稱為大知,它既不是老師的知識,也不是圣人的知識。稱之為“大”,其實它非常普通平常,而這種人人具有的認知能力(即人們的自然知性)被異常的圣知所遮蔽了。
最后有必要區分《莊子》中的“大知”和孟子所稱的“良知”。在孟子那里,“良知”是指人們不需要學習就與生俱來的實踐生活中的知識,比如:懂得愛父母,即“仁”;懂得尊敬長輩,即“義”(《孟子》7A15)。莊子在剖析具體化社會德行時揭露了其中隱藏的欺騙性邏輯,并將“德”的闡釋回歸于人的本性:這就好比聲稱“今天到越國去而昨天就已經到達了”(《莊子》2/4/10)。也就是說,自我修養的結果(具體化的德行)被當成了出發點(即自然本原)。對于莊子而言,孟子對儒家德行的內在化較之簡單順從于孔子倡導的禮更為不及,因為他的學說完全遮蔽了人的本性自然“完整”的源頭。不過,這里要強調的是,莊子的自然的“知”不是關于某物的知識(如人性、禮教、正義等),而是一種認知潛能。而這種人人都具有的認知能力,也即知性,對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平等齊一的。
《莊子》內篇的“齊一”思想
在內篇中,“齊一”和“自由”是兩大主題。《莊子》的第二篇就是關于“齊物”的長篇論述。但莊子不僅僅為“齊一”辯護,他的論述本身就彰顯了他所辯護的齊一思想。莊子的論述并沒有圣知與非圣知的區分:那些自認為具備圣知的人從來不確定他們真的知道,而那些說話的人從未真正明白他們說了什么。這事實上就是人類最常見的狀況。在閱讀莊子的論著時,我們沒有看到圣知,而只有人類生而就有的認知能力。莊子把這種認知稱之為“明”。這種認知能力普遍存在于所有的人。在莊子的認識里,“齊一”和“自由”總是結伴而行。
孟子在一篇著名的論述中,與許行的門徒討論后者從一位來自楚國南部研究神農學的老師那里學到的平等主義教義。孟子解釋說社會世界必定是不平等的,它是通過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君子和小人、腦力勞動者和手工勞動者的區分來構成的。社會需要在田地中勞作的農夫,也需要那些忙于“憂民”的圣人們。社會既存在對一定人際關系的劃分,也有對漢人和未開化人的劃分(孟子很明確地指出楚國的教義是未開化的)。最后,孟子總結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3A4)。莊子在論述萬物齊一觀點時所解構的正是儒家這種不平等的本體論哲學觀。
在內篇中有數個寓言故事清晰地談論了“齊一”的概念。在《德充符》篇,一位遭受斷足之刑的犯人和一位地位頗高的官員同拜一人為師。一天,當他們學習結束準備離開時,大官對這名形體殘缺的罪犯說:瞧,我是執掌大權的官,我不能被人看見和你一同離開講堂。一個身體殘缺的犯人是不能等同于一個大官的,你應該走開一點。那位身體殘缺的犯人回答:“當我跟隨老師學習時,我從不感到我是個斷了腳的人。在學習時,我們是平等的,在內心以德相交,但現在你卻把我拽到了社會倫理不平等的外部世界。”(《莊子》5/13/23-14) 《莊子》里的內在齊一世界是與外在不平等的社會世界相對的。在這個寓言故事中,這一對立是在講堂內和講堂外兩者之間,前者由內在齊一性管轄,而后者則是社會不平等世界。
《大宗師》篇記敘了更為正式的有關內在齊一性的哲學思辨。子桑戶、孟子反和子琴張互問:“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問題沒有答案,只有虛靜平等的內心體驗。“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莊子》6/18/9-11)但這種平等的內心體驗并非不可言喻。它可在一條準則中表述出來:“相為于無相為”。這一準則可稱為“齊一性”法則,其與儒家兩條家喻戶曉的道德準則截然不同。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15.24)而孟子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7A17)儒家準則預設了善的知識。這個預設是:人天生知曉何為正確的欲,何為錯誤的欲。這類知識的全部就構成了圣知,也即社會倫理秩序的律法。不平等的社會倫理秩序主要建立在具備圣知和不具備圣知的人的區分之上,并依據“報”的原理運作。孔子認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14.34)儒家道德準則指的是外在世界中具體化的德行。這種外在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交換之上,因此具體化于外部世界的德行成了可交換的物品。
莊子關于“齊一”性的法則并不預設任何有關善的知識,也不預設任何關于“己所欲”及“己所不欲”的知識。這些和圣知一起都是應該被棄絕的。莊子的道德法則不關注外部世界秩序,只關注于內心世界,因為只有在內心世界才可能“莫逆于心”。其道德法則同樣也沒有體現在“報”的外在社會秩序中。因此,莊子說,真正的“德”是“與而不求其報”(《莊子》20/53/26)。莊子的道德法則僅僅適用于朋友之間,也就是說,適用于平等身份的人之間,因為朋友是不會彼此期待回報的。
在精神層面,莊子的道德法則很接近康德的道德律令。康德說過,“要這樣做,永遠使得你的意志的準則能夠同時成為普遍制定法律的原則”(康德,1981:30)。一如莊子的道德法則,康德的范疇律令不預設任何善的知識。道德意志不會由關于什么是正確的欲望和錯誤的欲望預先裁定。和莊子一樣,康德也不關注基于回報的社會倫理秩序。根據康德的觀點,基于回報的倫理制度只在一種假定法則上運作,因此并不合乎道德。更為重要的是,一如莊子一般,康德拒絕圣知,并且斷言人類具有普遍共同理性能力。康德的道德律令不會告訴人們該做什么,它只是簡單地告訴人們依據道德律法而行為。這看起來好像是空談,但實際上它把理性的能力還給了民眾,而這種能力早已被那些告訴民眾要依據外部道德標準行事的人掠去。
莊子的道德法則和康德道德律令的另一個重要相似之處是:二者都談論內心世界,并且都沒有清晰指明人們如何能將內心世界的準則運用于外部世界(即社會秩序)。在康德的術語中,這些準則被稱為道德律令,而在莊子的術語中,指“齊一”和“自由”的內心體驗。眾所周知,黑格爾試圖在外部社會秩序中實現康德的道德法則,即內心世界的自由和理性。在其有關主人和奴隸的論述中,兩個擁有自我意識的主體之間為爭奪自我確定性的斗爭推動人性進入了社會世界。贏得這場斗爭的成為主人,而失敗方則成為奴隸,并在主奴關系基礎上進一步確立了文化和社會秩序,這種秩序經過一定的時期就成了理性。在黑格爾看來,在社會接納了一定的理性形式之后,這種不平等性就被巧妙地通過邏輯論證抹除了。
《莊子》明確否定此類有關自我確定的邏輯論證可以在社會世界中實現平等。《莊子》經常描述一種存在于文化和國家出現之前的原始時期人類處于完全平等的狀態。這類描述自然不能被視作史實,它只是一種虛構的理想,但這種理想告訴我們:必須從平等角度出發討論,因為平等不是人類自行建構的或需要努力追求的,而只是人類存在于世界的基礎。不平等的社會秩序是建構的,當人們將德外在化,就產生了不平等。一旦那樣,世界就分裂為那些具備圣知的和不具備圣知的,擁有高尚道德的和只擁有基本道德的,或者用黑格爾的術語,主人和奴隸。當今人類社會和文化是建立在對自我意識確定的斗爭之上。《莊子》指出,在浮華文飾和廣博俗學的社會中,“心與心識知”。但也正是這時出現了大盜,因為那些被確定為具備圣知的人將“以知窮天下”。這就是說,通過被確立為具備圣知的群體,他們掠奪了普通民眾與生俱有的自然知性。因此,在對自我確定的邏輯論證過程中,人類與生俱有的原本的“德”就消失了。《莊子》說:“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莊子》16/43/8)由于自我的確定否定了平等和自我完整性,因此,對自我確定的邏輯論證是無法在社會世界中實現平等的。人類注定要生活在不平等和腐敗的社會嗎?為了更好地闡明這個問題,也為了表明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以下本文將簡介一位也似莊子般陷入僵局并倡導激進平等主義哲學家的思想,然后再概述莊子對這一問題的解答。
能所不能
法國哲學家雅克·朗西埃是路易·阿爾都塞的學生,兩人關系親密。路易·阿爾都塞是20世紀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領軍人物之一。1968年5月法國爆發學生工人運動之后,朗西埃認識到他的老師阿爾都塞并不理解在運動中被付諸行動的激進平等主義思想,于是決定與老師分道揚鑣。根據阿爾都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觀點,平等是由政黨及其知識分子領導大眾的未來世界的目標。但朗西埃認為,這樣的觀點只會維持不平等的狀態,因為它使那些具有知識的人和不具有知識的人的區分有了合法地位。
朗西埃在談論一位法國教師約瑟夫·雅克托特(Joseph Jacotot,1770-1840)的書中逐步奠定了激進平等主義理論的雛形。雅克托特在王政復辟后逃離法國。1818年他在比利時一所大學得到一份教授法國文學的工作。不過,他自己不通佛蘭德語,而他的學生則不懂法語,因此他無法采用傳統的教學方法教授學生相關的科目。于是,他給學生們一本雙語版法語小說,讓學生們運用自己的智力去理解所學科目。學生們背誦書開頭的段落,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重復這些詞語。令雅克托特感到驚訝的是,最后學生們不僅能自己閱讀法語,而且還能將閱讀心得用法語寫成頗有文采的論文。
基于這樣的經歷,雅克托特發展了一種新的教學理論。在此僅概述一下朗西埃從雅克托特的經歷中學到的主要經驗。朗西埃寫道:“存在一種將世界一分為二的方法論神話,更確切地說,這種神話將智力分成兩類,即高等智力和低等智力。”(朗西埃,1991:7)低等智力是只懂得感覺和實證驗證,這就是普通民眾的智性能力;高等智力通過推理和方法理解事物,這就是教師們的理性。由于只有他們懂得理性和掌握恰當方法,因此教師們必須向低等智力者解釋世界。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這種過程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根據朗西埃的觀點,高等和低等智力的區別會使人們變得遲鈍,它將導致“強加的遲鈍”(朗西埃,1991:7)。此處法語詞“abrutir”被譯成“遲鈍”,它蘊含著“使人愚鈍,當作笨蛋一樣對待” 之意(朗西埃,1991:7,譯者注)。朗西埃指出,“遲鈍”“將會使理性運動中止” (朗西埃,1991:9)。為了重獲理性能力,必須回到出發點,那就是回到客觀事實,即所有人生來就具有平等的知性潛能(朗西埃,1991:18)。
朗西埃關于平等的觀點與《莊子》中的“齊一”性論述極為相似。二者都認為對圣知和非圣知的區分掠奪了普通民眾的知性,因此必須摒棄這種區別,要從一開始就肯定所有的人具有平等的知性。在考察朗西埃對蘇格拉底的評論時,朗西埃和莊子的相似之處就更為明顯。在朗西埃看來,蘇格拉底是通過使用自己的理性和方法將他人(在某種情形下顯然是奴隸)引向知識世界。毫無疑問,蘇格拉底承認他自己是無知的,但這種無知成了邏輯論證(對話的)過程,正是通過這樣的過程,他將對話者引向知的世界。因此,據朗西埃的觀點,蘇氏教法是“遲鈍化的完美形式”(朗西埃,1991:29)。正如蘇格拉底一樣,莊子也是從無知出發,但莊子并沒有借助對話或者邏輯論證克服無知。在莊子眼里,無知不是將未知引向已知的方法。無知是對圣知和非圣知區分的否定,同時證實人類的普遍知性:人類都平等地“無知”,因而具有平等的“知性”。莊子沒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發展出一套基于對話和邏輯論證的科學方法,這恰好有助于他避開了朗西埃強烈抨擊的“使理性遲鈍化”的問題。
朗西埃和莊子都展示了一種激進平等主義哲學愿景,也都面臨同樣的困境:激進平等主義是人類相遇時最根本的體驗,但它無法被運用于社會世界。朗西埃認為,社會世界不會也不能體現平等。社會世界并不基于理性,它是非理性的,甚至是瘋狂的。如果人們有幸生活在一個和諧社會,那么他們可能避免無序狀態。但是,即使是和諧社會也不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分人之上的。這就是社會秩序最根本的非理性。不過,在朗西埃看來,即便是身處這樣非理性社會,也仍然有可能體驗到“理性時刻運動的奇跡”(朗西埃,1991:96),而這種理性時刻給了人們足夠的理由去相信平等是有可能在社會秩序中實現的。朗西埃寫道:“這正是人類社會得以產生的關鍵所在。”(朗西埃,1991:73)朗西埃采取的是介于基督教和康德傳統的中間立場,認為兩個世界的劃分,即平等世界和不平等世界、正義世界與非正義世界、理性世界和非理性世界,都只能通過信任和希望得以消除。
對于如何在社會世界實現激進平等主義,莊子提供了另一種解決方案。莊子沒有像朗西埃一樣寄希望于奇跡的出現,他叫人們“能所不能”(《莊子》22/63/24)。要理解莊子的這句話,需要先知曉他所說的“內”的所指和“無為”的含義。對于莊子而言,“內”并非某種深藏于人的內心和頭腦的東西,而是事物在外化為“物”之前的本質或性情。“內”就是最初的本性。因此,“內”其實早已存在于“外”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內”是比“外”更為“外在”的東西,因為事物一旦外化為外部世界的有形物體,它就否定了它自身的最初存在,否定了它自身原初的本性,而不再真正地以本性面貌再現,因此也就無從清晰地看出它的本性了。
在莊子看來,“無為”即是讓萬物本性自然而然顯現,而不是把它定義為某一類“物”。簡而言之,“無為”就是使事物自然呈現原初的本性。莊子的道德法則“相為于無相為”就是關于“無為”的典型例子。這一法則指的是人們幫助朋友但卻不會約束他或改變他。這里舉一個例子。有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美國人是美國人,中國人是中國人。在這個意義上,二者都有他自己的“性”(nature)和“命”(destiny)。如果愿意,也可以稱之為“情”(essence)。但是,這種“情”是永恒不變地存在的。那個美國人可能是位女士,來自密西西比,愛吃宮保雞丁,擁有漂亮的眼睛,脾氣暴躁,左臂上刻有紋身,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每周日都去教堂做禮拜,喜歡看韓劇等,但她身上的美國“情”始終存在。那位中國人可能是一位小伙子。他來自昆明,喜歡吃匹薩,開著一輛福特車,愛寫點詩歌,有著燦爛的笑容,有點兒健忘,穿四十二碼鞋,正打算結婚,喜歡看韓劇等,同樣,他的中國“情”也始終存在。但是,如果他們各自的“情”被外化為文化——心理建構概念,如“中國性”(Chineseness)和“美國性”(Americanness),那么他們的“情”就不再顯現了。他們成為眾多事物中的一類,于是確定自我身份和爭奪優勢地位的戰斗就開始了。這就是莊子想要避開的問題。
要避開這樣的斗爭就需要讓“情”自然而然顯現,而不是成為某一類事物。但這是我們無法做到的,因為只要我們有所“為”,事物就會被定義為某一類“物”。如果我們對待他人就好像我們希冀他人以同等的方式對待我們,那我們就已經預設了“善”的概念和一種我們必須遵守的客觀標準,那么我們事實上就已經陷入了“物”的外部世界。因此,道家的道德法則說:“相為于無相為”。這是讓人們去做不能做的事情,它教導人們通過“無為”而有所“為”。通過“相無為”,對方的“情”和“性”就會不斷地自然顯現,而不至于陷入有關“物”的界定之中。友誼和平等就是一種可以讓自己和對方的“情”自然而然顯現的契約。要意識到,平等(齊一)其實存在于外部世界,人們只是需要通過“無為”來讓它自然展現。按照莊子的觀點,只要這樣做,平等(齊一)就完全可以在社會世界實現。
結語
《莊子》中關于圣知和齊一(平等)的討論具有多重意義。首先,大多數中國哲學家都將“圣知”視為理所當然,這也就是為何中國的哲學主要是關于哲人自己的論述而不是類似朋友間的智慧對話。通過棄圣絕知,莊子的思想更接近希臘的哲學概念。其次,《莊子》表明圣知尤其是儒家的“圣知”是意識形態的,因為在一定意義上它有助于使一個特定的社會秩序合理合法化。最后,圣知是一種具有權力的“知”。因此,《莊子》對圣知的批判具有普遍意義,可以被視為對所有維護特定社會秩序的各類知識的批判。但是,是否存在一種不與權力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等捆綁在一起的“知”呢?《莊子》指出,如果人們絕圣棄知,則他們的自然知性就會顯現,并成為構建平等社會秩序的基石。問題是如何能將這種平等的體驗運用到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之上的外部社會秩序呢?《莊子》或許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哲學很少能給出確切答案——但它拒絕放棄對平等(齊一)可能性的探求。在這個意義上,《莊子》站在了真正的哲學立場上。
參考文獻:
[1]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1994, What Is Philosophy? [M]. Translated by H. Tomlinson and G. Bur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Kant, Immanuel. 1981. Grounding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M]. Translated by J.W. Ellington, Indianapolis: Hackett.
[1]Rancière, Jacques. 1991. 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Five Lessons in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s [M]. Translated by K. Ro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Zhuangzi 莊子2000. Zhuangzi zhuzi suoyin (莊子逐字索引)(A Concordance to the Zhuangzi) [M].The ICS Ancient Chinese Texts Concordance Series,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譯者:梁燕華,廣西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英國赫爾大學博士)
【責任編輯:高建立】
中圖分類號:B2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600(2016)02-0017-06
作者簡介:艾斯克·簡·莫卡德,羅德島大學哲學系教授,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和文明博士,主講東亞和當代歐洲哲學課程。出版有專著《道家思想引論:〈莊子〉中的行為、語言和倫理學》。
收稿日期:2015-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