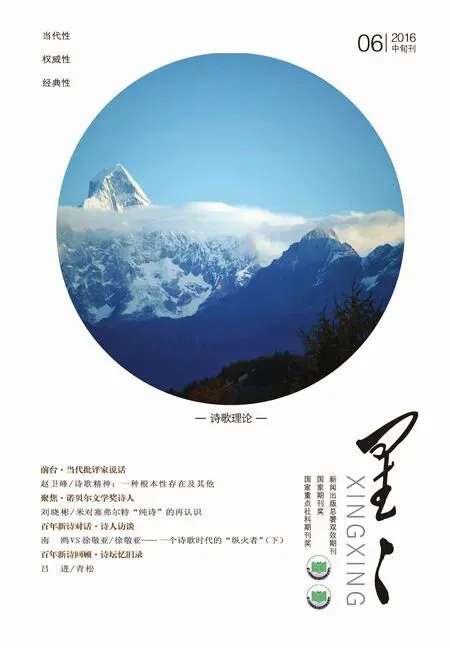智性與感性的結合
——論袁可嘉詩歌的藝術特色
肖 柳
智性與感性的結合
——論袁可嘉詩歌的藝術特色
肖 柳
在九葉詩人中,袁可嘉是個特殊的存在,他以一系列理論文章為九葉詩派建構起系統的詩學主張。他的詩論集結為《論新詩現代化》一書,針對40年代詩界中泛濫的說教和感傷傾向,聲稱“詩不再是激情,而是表現人生經驗”[1],并提出著名的詩學原則——現代詩歌是“現實、象征、玄學”的綜合:在著眼于當前世界人生的同時,用一種暗示含蓄的表現手法進行詩歌創作,從而表現出情感、意志的強烈結合以及機智的不時流露。這樣一種詩學主張關注的是“人生經驗的推廣加深”和“最大可能量意識活動的獲取”[2],“人生經驗”含有更多的理性成分,而“意識活動”則是由感性主宰,他試圖協調理性和感性這對立的兩極,使二者相交,智性與感性達到統一,從而實現人生經驗詩情化和詩情哲理化。
除了豐富的理論著作,袁可嘉也以其創作實踐踐行著自己的理論主張,唐湜也因此稱其為“以詩論詩的思想者”[3]。他的詩歌智性成分很重,但這并不是抽象的哲理,而是來源于他自身的生活感受和人生經驗,但他不滿足于這些感受的獲得;同時,他更不愿意在詩中貌似坦白地直接說明,“抽象觀念必須經過強烈感覺才能得著應有的的詩的表現,否則只是粗糙材料”[4],于是他采取一種暗示、含蓄、象征的手法,將這些感受加以提煉,通過奇妙的想象邏輯將其升華為理性,這種間接性的表現手法和想象性的邏輯結構使他為數不多的詩歌作品閃爍著智性與感性的雙重光芒。
一、以外界事物代替直接說明的間接性表現手法
“人的情緒是詩篇的經驗材料,藝術情緒則是作品完成后所呈現的情緒模式”[5],許多人因為分不清二者的區別而迷信詩就是情緒的完全表達,而過于直接的情感宣泄往往會導致說教或者感傷的惡劣傾向。袁可嘉認為“詩是行動”,是將人的情緒轉化為藝術情緒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文字,文字作為一種符號,具有象征意義,它給人們提供想象和聯想的可能,若充分利用文字的象征作用,以一種間接性的表述來呈現詩情,詩的張力就可以由此體現。在袁可嘉的詩中,他通常是盡量避免直截了當的正面說明,而以外界事物來寄托其意志和情感,例如《旅店》和《難民》二詩中幾乎找不到詩人有關自己內心情緒的正面描述,既沒有出現“悲哀”這樣的字眼,也沒有出現“無奈”這類詞,既沒有激烈的控訴,也沒有嚴厲的咒罵,但這些情緒都真實地存在于詩行之間。
《旅店》擬人化了“旅店”這一形象,通過它的視角來觀照亂世浮沉。前兩節描寫了“旅店”自身,它對現實早已無所期待,所以“眼睛永遠注視著遠方”,這里已經預示了當時所處環境的壓抑;當風雨到來時,“旅店”還是伸出援手去“搶救”來人,旅店本來就是供行人居住的地方,但現在人們卻需要被“搶救”,可以窺見人們所受的威脅,而“遠方的慌亂,黑夜的彷徨”更是人們內心的寫照,他們從遠方而來、趁著黑夜,慌亂和彷徨充斥內心,前兩句的預示在這里成為人們的真實感受——環境已經給人們帶來了不安;但在這樣的環境下,“旅店”是無私的、有人情味的,它“一手”接待過的人不計其數,甚至足夠湊成一幅地圖,環境不斷變化,但它仍然保持不變,用它“深夜一星燈光”照亮“投奔而來的同一種痛苦”,人們流離失所的痛苦都由“旅店”收容,一間小小的旅店尚如此有人情味,這對于無情的現實來說則是強烈的諷刺。到了詩的第三節,詩人正面寫到人群的心態,人們對“旅店”的幫助無以為報,并感到“慚愧”,通過人們與“旅店”的情感交換,投射出的不是人群的無情,而是他們迫于無奈的現實,現實的狀況已經由人們的感受變為親口說出:“無情的現實迫我們匆匆來去”,帶來的只是“一串又一串噩夢”[6],詩到這里結束,詩人始終沒有大喊大叫甚至大聲控訴,他只是從旁觀的角度客觀地描寫“旅店”和人群。
詩中的描寫都是基于真實,抒發了詩人對于現實的不滿,但他并沒有激烈地將內心的情感一瀉而出,而是以“旅店”的角度映射出現實的黑暗和人們處境的艱難,看起來十分冷靜,但冷眼背后卻有著強烈的諷刺與痛苦,詩人的情感在這種間接的描述中呈現出智性化,感受升華為理性。此外,這首詩以相當多的外界事物代替了情感的直接說明。但是這種寫法并沒有給讀者的接受造成障礙,反而在詩行中標明了一個又一個情緒的遞進點,在看似錯綜復雜的情感流動中給讀者提供了明確的指引。
與《旅店》類似,《難民》一詩也是通過旁觀顛沛流離的人群,表達出詩人對現實的不滿以及對人的生存狀況的無奈。但前者是通過“旅店”和人群兩個維度來反射現實,實際是三者并存于詩中;后者則是直接讓人群(難民)與現實相對峙,以難民的被利用、“被人作弄”直刺當局者和實際政治的貪婪、狡黠,所以感情流露比較直接、明顯,但從對“難民”的描述來看,有關個體生命的思考也表現出詩人深沉的智慧。
二、意象的特殊構造
意象在現代詩歌創作中有重要作用,在不滿浪漫派詩歌的意象空洞含糊之余,袁可嘉主張知情合一的意象藝術,認為“只有發現表面極不相關而實質有類似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準確地,忠實地,且有效地表現自己”[7],這類意象是“意志與靈魂的凝合”、“理性與感性的復合”,[8]自覺選擇這類意象與詩人的思想情感相結合后能引起豐富的聯想,擴大詩的意義。
《進城》和《冬夜》二詩中可以枚舉的例子不少,《進城》中有“走進城就走進了沙漠,空虛比喧嘩更響”和“踏上街如踏上氫氣球,電線柱也帶著花花公子的輕浮”[9]這樣的比喻性意象。前一句以城市和沙漠兩種截然不同的空間意象進行對照,但城市卻如同沙漠一般“空虛”,不同的是城市的空虛隱匿在“喧嘩”聲的背后,虛偽的繁華景象展現出來;“街”和“氫氣球”也是一組不同的意象,是實心與空心的不同,“踏上街”本應該是腳踏實地的踏實感,這里卻感覺是漂浮的懸空,連立于地面的“電線柱”也“輕浮”起來,在虛偽的繁華景象中,人的活動也顯得不真實。兩組相反的意象的使用,使得每句詩中都包含一對反義,看似完全不同的表面下存在的卻是互相聯系的實質,產生的諷刺效果則有著驚人的準確。這種意象的選擇,明顯需要詩人的認真思索并挖掘其相關內在,在意象中不僅蘊含諷刺的情緒,又含有詩人的思考,使這類意象成為詩人情感與智慧合一的載體。
在《冬夜》一詩中,更有“街道伸展如爪牙勉力捺定城門”,“炮聲砰砰,急劇跳動如犯罪的良心”,“謠言從四面八方趕來,像鄉下大姑娘進城趕廟會”,“想多了,人就若癡若呆地張望,活像開在三層樓上的玻璃窗”,“東西兩座圓城門伏地如括弧”……如果單獨看這些比喻,只會覺得沒有頭緒,不能體會其中含義,只有在全詩的情緒變化中才顯出它們的準確合適。詩的第一節寫冬夜中的城市,視點由內而外,城市作為一個整體,街道為其四肢,但城市“空虛得失去重心”,街道也就只能“勉力捺定城門”,城門遲早會被推開,而由城內向外的發炮聽起來像“犯罪的良心”,這種抵抗是不安的,遲早會失敗;第二節則從外向內,城門雖然關著,但謠言還是“從四面八方趕來”,“像鄉下大姑娘進城趕廟會”,謠言與鄉下大姑娘看似毫無聯系,其實謠言的傳播和鄉下姑娘進城的過程都是外表極具吸引力而且充滿新奇感覺,城市內部的空虛和謠言四起都昭示著城市的氣數將盡。描述完城市的大環境,詩人將重點落在城市中的人身上,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憂傷”、“沮喪”、“若癡若呆”,“活像開在三層樓上的玻璃窗”,將人比作玻璃窗是個絕妙的比喻,空洞無聊,散盡了人的靈氣;人人都像“臨危者抓空氣”,“卻越抓越稀”,無可奈何;城門如“括弧”,“括盡無恥,荒唐與欺騙”,城內的整個環境都是虛假的,人的生活也失去了生機,行人“像每一戶人家墻上的時辰鐘”,過著機械的生活,沒有思考也沒有突破;測字者算不準自己的命運,商店伙計驅趕讀書人的手勢將人與人之間拉開“一海距離”;寫完城中可見的人,詩人還寫了不可見的“無線電”背后的人,他們的謊言通過無線電傳播,讓整個城市的空氣里都彌漫著虛假,但是“撒謊者”也一如街道上的人們,有自己的哀傷。詩中的每個比喻都是詩人自身所感,并且隨著全詩的情感流動而發生變化,全詩像一架攝影機由遠及近的進行航拍,從城市整體輪廓推進、聚焦到街道上的每個具體的人,使底下的事物在突然縮小中清晰地呈現,空虛的城市中散布著行尸走肉般的人,他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機械、庸俗地生活著,但詩人并沒有辛辣的嘲諷,也沒有憤怒的批判,這些奇特的意象和特殊的比喻中間蘊含的復雜意義早已超越了強烈的思想感情,以其思想力量顯示詩人有關于人生的智慧思考。
三、想象邏輯構筑詩篇結構
一般而言,詩人創作時都會重視全詩的結構安排,如何讓全詩讀起來連貫自如、首尾一致往往成為詩人們組織詩句的原則,但這樣的結構方式是散文化的,不是詩的。袁可嘉認為“現代人的結構意識的重點則在想象邏輯”,“只有詩情經過連續意向所得的演變的邏輯才是批評詩篇結構的標準”[10],他摒棄了原來常識性的直線型起承轉合的結構方法,替之以曲線型的想象邏輯,使表面上不同但實際上可以互相聯系產生合力的各種意象集結在一起,從而找到了詩情的張力。詩人早期的《沉鐘》和《空》兩首詩可以稱為是其年輕時的自畫像,尼采式的詩篇顯示出了這種流動的、作曲線行進的想象結構。
《沉鐘》一詩是詩人的自白,詩人以“沉鐘”自比,自身一如沉鐘的“沉默”、“沉寂”,忘卻了時間和空間,孑然獨立于世。沉鐘像一個年老的高僧,歷經三千年的世事滄桑,任憑風來雨往,對外界不聞不問,如藍色的天空一樣凝重,在死寂中忘了生命的苦痛,寬容地收容從四面八方來的野風,什么也不在乎。年輕的詩人雖將自己形容為年老的“洪鐘”,但他并不是要表現長者參透紅塵的無所謂的態度,而是希望自己以沉默、內斂的姿態接受生命苦痛的考驗,不盲目追求大海的波瀾和蒼穹的無垠,只如凝練的天空般做真正的自己。這是詩人對自己內心的探索,將其思想感覺的波動借助于對“沉鐘”的精神的認識而得到表現,詩情的延展就是“沉鐘”精神(詩人想象)的變化,初看詩里說的只是“沉鐘”的精神世界,實際上卻表現了最完整的詩人的靈魂,“沉鐘”的心理變化就是詩人自己精神上的感染。從這首詩里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古寺中的洪鐘,它古老、深沉、靜止,我們不用與它交談,就能感受到一個純凈、寬容、崇高的心靈,同時這也是詩人的內省體驗,他在向自己的內心審視時也探索出“生命脫蒂于苦痛,苦痛任死寂煎烘”[11]的哲理。經過曲線結構流轉的詩情被淡化,顯現于詩行間的人生智慧相融于無形。
《空》則更像是詩人玄學或哲學的告白,他已經不再是具體的“沉鐘”般的物,而是抽象的一片無形的“空”。“我”被水柔和地包著,由外到里渾身濕透,被下垂的枝條吻著,被風來摟著,雖然身處這樣優越的環境中,但“我”還是想著“我底船”、“旗”和“我底手”,周遭的環境再美再溫柔,詩人也不想陷入其中默默地被動接受,而是渴望用自己的手舉旗撐船而去;于是此時詩人開始問自己,“我底手能掌握多少潮涌”,才能如小貝殼磨得玲瓏,其實“手”在這里即是詩人的心靈,他問的是自己的心靈要經過多長時間的磨礪才能像貝殼般光滑、剔透,經歷了晨潮晚汐的打磨,直到擁有一犀靈空,就可以收容海嘯山崩,在詩的這一節,詩人已經由美夢中醒來,開始關注自己心靈的歷練;波紋形的小貝殼也能把空靈鑄為透明,詩人也相信自己會像小貝殼一樣,經過歷練,使心靈變得空靈、透明,而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在自身“無色的深沉”中,突然發現了自己的力量,“驚于塵世自己底足音”[12]。不去思考這些抽象的意象,我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詩人想象的流動:詩的三節分別可以看做是詩人在混沌中的覺醒,到覺醒后關于磨煉心靈的思考,再到心靈經過磨練后的最終結果的展望,這也是詩人心靈變化的三個過程。雖然初次讀這首詩會有種莫名其妙的感覺,但是如果把詩情發展的曲線在心中重描一遍,便會豁然開朗,并為這絕妙的想象邏輯所動容,詩人用這些與自己的情感密切聯系的外在事物將詩情的線索藏在字句之下,并讓意象隨著自己的情緒、想象而變化,不僅擴大了這些意象的含義,也加深了情緒的起伏震蕩。詩人自己的心靈體驗被詩情化,同時詩情也以哲理化的句子呈現出來,“我乃自溺在無色的深沉,夜驚于塵世自己底足音”,感性中有思辨,抽象中有具體,詩歌整體上呈現出智性和感性的雙重魅力。
注 釋
1.袁可嘉:《詩與民主》,《論新詩現代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47頁。
2.袁可嘉:《新詩現代化——新傳統的尋求》,《論新詩現代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頁。
3.唐湜:《以詩論詩的思想者——袁可嘉》,《九葉詩人:“中國新詩”的中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頁。
4.袁可嘉:《詩與主題》,《論新詩現代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76頁。
5.袁可嘉:《對于詩的迷信》,《論新詩現代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61頁。
6.袁可嘉:《旅店》,《九葉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頁。
7.袁可嘉:《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技術諸平面的透視》,《論新詩現代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8頁。
8.王澤龍:《中國現代主義詩潮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頁。
9.袁可嘉:《進城》,《九葉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頁。
10.袁可嘉:《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技術諸平面的透視》,《論新詩現代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9頁。
11.袁可嘉:《沉鐘》,《九葉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頁。
12.袁可嘉:《空》,《九葉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