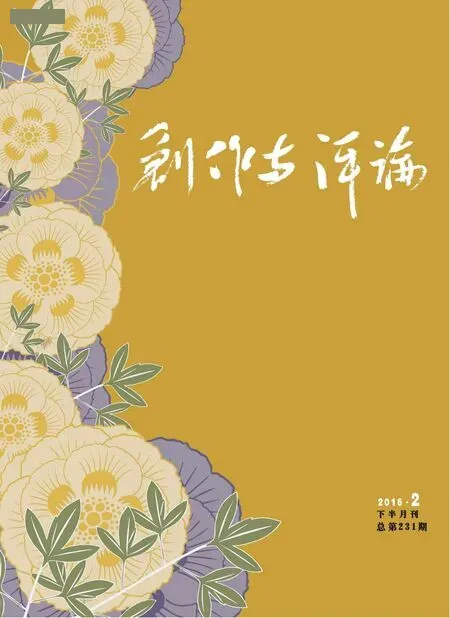冰明玉潤天然色,冷暖鏡像人間事
○郭 艷 黃詠梅
?
冰明玉潤天然色,冷暖鏡像人間事
○郭艷黃詠梅
主持人語:
這是一篇奇妙的對話。對話雙方關系復雜。郭艷是魯院老師,著名學者;黃詠梅曾是魯院學生,著名作家。她們又是朋友,故熟悉彼此的理路和作品。郭艷是評論家,但亦創作小說;黃詠梅是作家,但深具學者氣息。二人之間相摩相蕩,既是評論家和作家間的交流,也是同行之間的互相切磋,有問有答,有難有辯,問、難者真,答、辯者切。由之,或可部分地見出二人立場、思路和風格。

黃詠梅生于20世紀70年代,文學碩士,2002年開始小說創作。在《人民文學》《花城》《鐘山》《收獲》《十月》等雜志發表小說近百萬字。多篇被《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小說選刊》等轉載,出版小說《一本正經》《把夢想喂肥》《隱身登錄》《少爺威威》,曾獲“《十月》文學獎”“《人民文學》新人獎”等。
郭艷:近二十年中國青年寫作賦予當代寫作清晰的個體存在感,這種個人主體性日漸在一個審美現代性的維度上開始了對于中國當下生存的文學性敘事。在《負一層》《單雙》《把夢想喂肥》等小說中有著對于他者小人物的精彩摹寫,在《父親的后視鏡》《小姨》中呈現出自我鏡像中的主體性敘事,請談談你創作中個體存在感的敘述轉換。
黃詠梅:在你面前談主體性這個問題,我覺得很心虛,因為我讀過你的長篇小說《小霓裳》,早幾年前吧,那時我們還沒見過。但是我就認定,那里邊的女博士,就是你,雖然不完全是你,但起碼大部分是你。小說的個人主體性很明確、堅定。幾年后我們相識于魯院,更加堅定了我的判斷。可以說,在小說里無論是個體的價值觀、世界觀、美學觀都跟現實中的你很貼近,你獨立、堅守、知性,就像小說中的女博士。實際上,我認為這樣的文學形象在當下小說中實在太少,而現實生活中卻有不少,我很奇怪為什么沒有人去闡釋這類形象呢?或者真的是男權社會所一貫秉持的方式——躲避?
我的小說,如你所說的,早期的作品主要寫他者,在我身上找不到對應的地方,即使連人物的存在感都不明確。拿陳曉明老師對我的評價就是——“去主體性的小說”。我喜歡把“我”隱藏起來,以使得我與人物可以共存在同一境遇中,存在著人物的存在。我認為這樣隱藏的好處,就是我可以變身,變身為他者,這樣看起來我的敘述轉換會顯得自然。到了后期,我有了些改變,我的自我在小說里藏不住了,因為我對小說不再滿足于呈現,我迫切地希望自我附著在人物身上,以貼切地表達我的想法和判斷。這種改變,我理解為從一種不自覺的感性寫作轉換成一種自覺的理性寫作。我讀過帕慕克談寫作的那本《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天真和感傷的劃分,席勒早就作過闡釋,前者的創作傾向于自然性、感性,他們將自我與自然融合并呈現,毫無分裂感,而后者的創作則是理性的,他們時刻感到自我與周遭的分裂。帕慕克屬于后者。兩者不存在誰好誰壞,只是由個體的想法所左右。當我與自我常常感到分裂的時候,小說自然變得感傷。那么你呢,你在寫《小霓裳》時,有沒有覺得在那里邊,實現了自我?
郭艷:實際上《小霓裳》的寫作是為了和自己的一部分過去告別。我這半年就是在不斷地告別自己的過去,父母是擱在你和死亡之間的一道簾子,把你擋了一下,老父親大歸讓我直面生死,世界至此對于我有著大不同。這半年生活對于我來說是顛覆性,能夠聽到來自不同時間的聲音,在一種無法和過去厘清又糾結于一切記憶的狀態中,唯有深夜抄錄《心經》才能獲得片刻安寧。我明白,對于我而言,《小霓裳》時代真正結束了。然而,書齋生活及其偏狹趣味依然對于我有著某種原初意義。作為受過現代教育的女性在堅硬的現實面前何以確證自己的心性和面目?在日常性中的穿越,在物質主義中的徜徉,在城市人群中的游蕩……內在性的分裂造成了自我主體性的碎片和漂浮,在對于他者的碎片化的感知中,小說和文字日漸沉淪在鈍感的敘事中,日漸告別純粹的快樂,卻依然期待有著飽滿充沛的情感與經驗,而我依然希望能夠重塑一種自我經驗世界的部分完整性。在你的小說中,“冷”的去主體性中,實際上暗含著對于他者主體性的艱難尋找,即便負一層中的女孩,也在地下室中為著自己幻想中的主體性付出了最為駭人的熱情。
在日漸告別饑餓和戰爭的日常中現代人既無法體驗苦難又無法獲得更多的幸福感,現代病由此產生,而現代人的精神病癥和現代物質生存方式密切相關。請談談《暖死亡》的寫作。
黃詠梅:這個小說寫于2007年。也是我第一次給《十月》雜志投稿,當時的責編是我喜歡的作家周曉楓老師,我記得她讀完給我打電話要我對小說里的一些細節進行修改,有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刻:“你這個小說里探尋的死亡問題,比現在大量小說里那些轟轟烈烈的死亡要有意義得多。”除了感激之外,我還很慶幸,慶幸這個作品落在了像曉楓老師這樣的編輯手上。說實在的,我覺得這個小說不會有很多人喜歡,因為它太溫吞了,就像小說里那個胖子,總是在一點點慢慢地咀嚼、吞食食物。它所探尋的死亡問題,看起來一點沒有震撼性,也就是說一點都不“轟轟烈烈”。正如你說的,我們日漸告別饑餓和戰爭,我們日漸滿足、和平,直至平庸,轟轟烈烈只出現在藝術品上。正是這些平庸讓我們失去了感受力,就像渡邊淳一說的“鈍感力”。失去感受力,使得現代人呈現了同樣表情的面目。小說里的林求安除了他的體重超人之外,絕對不是生活中的異數。對于一個寫作的人來說,失去感受力無異于終結。我時刻都在提醒自己,或者說強迫自己。這又很像患上強迫癥的林求安。總之,失去感受力或者強迫自己去感受,歸其咎都是因為精神慵懶,這種慵懶會一點點地導致精神在舒舒服服中死去。寫這個小說的時候,我應該是很焦慮的。現代人一直都很矛盾的,既求安,又怕安,既需要俗世,又想要掙脫俗世,我也不例外。其實,只要想明白,一旦精神或者說思想擺脫了慵懶,人就不會恐懼肉身的安了,但做到很難。
郭艷:你自己對《暖死亡》的闡釋遠比批評家要精準,從這一點來說,很多出色的作家都是出色的批評家。《暖死亡》敘述是溫吞的,而其隱喻和象征是尖銳的。對于當下中國城市經驗的摹寫,“暖死亡”無疑具有世紀寓言的性質,這個短篇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如果我寫近20年文學現象,一定會讓短篇《暖死亡》進入文學史。我們進入一個物質日漸豐裕卻前途未卜的時代,70后寫作最突出的價值和意義在于重建現代世俗生活精神合法性。近二十年中國社會世俗生活日漸繁榮。在經歷了近現代無數次殖民、戰亂、政治運動之后,終于以常態現代人的心態去考慮自己的日常生活,對于現代生存的溫和態度成為一種價值共識。2014年以《少爺威威》為小說集名,對于這個短篇小說是否有著不一樣的偏愛?
黃詠梅:嗯,倒也不是對這個小說有多偏愛,它的確是很日常,很世俗的一篇小說。70后作家一貫偏愛寫日常生活,甚至還旗幟鮮明地認為現代世俗生活也有它的精神性和審美性,可以說我們對宏大命題做出了近乎集體性的挑戰。我不認為這是我們的默契,而是,時代選擇了我們這一代,就像時代選擇了1949年以后十七年時期的那批作家成為政治的傳聲筒一樣。時勢造就了我們的書寫。我們真誠地表達著這個時代的現實生活。我很喜歡你在《城市文學寫作與當下中國經驗表達》這篇文章里的闡述:“70后正是以這種對于日常經驗的固守才完成了先鋒文學沒有完成的任務——從文學題材和精神氣質上真正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告別,開始一種現代性的寫作,尋找作為現代個人主體性的中國人。”的確如此。如果說60后作家的主體性表達還呈現曖昧或者期期艾艾,那么70后則顯得更為決絕。
具體說到《少爺威威》這個小說。題目是上世紀80年代香港流行的一首歌的名字,它幾乎是我少時對香港的一種想象,花花綠綠,銀子多多,生活自由、瀟灑,就如這首歌里唱的那樣。我生活在廣西梧州,方言是粵語,后來在廣州工作,也是講粵語。我是聽“香港年度十大金曲”長大的一代,我們見證了香港娛樂從黃金時代到沒落的全過程,這過程,就像小說《少爺威威》里的那個東山少爺所展現的一樣。這篇小說里有大量的粵語方言。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都被認為是嶺南小說作家。主要因為我寫廣州,運用粵語腔調。寫完這個小說不久,我就離開廣州,調到杭州生活了,我告別嶺南生活而投入另一種江南生活。我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移決定了精神氣息、文化土壤的變更。現在,我很少寫廣州,幾乎不用粵語腔調。實際上,我是很依依不舍的。大概因為這種不舍的情緒,我把《少爺威威》作為小說集的標題。倒并沒有從這個小說的日常化的標志性方面考慮,因為,在我這里,寫日常不需要“宣誓”,哈哈。
說到這里,我有個困惑想請教你,我這樣舍棄粵語腔調寫作,是否好?粵語因為一向偏離北方官話系統,遠離文化中心,不像其他如東北方言、陜北方言等北方語系,說起來都能通,都是一根血管分出來的支脈,而粵語無論從音調還是語序上,都像是另外一支血脈,都會讓你們這些北方語系的讀者難以產生呼應。在我起步寫小說的時候,就有一位北京的著名評論家勸說我不應該只做嶺南作家,要擺脫粵語這種“鳥語”的寫作,因為他覺得它們阻礙了我的表達效果。我很想聽聽你的看法。
郭艷:小說家的直覺體現在對于語辭的選擇上,《少爺威威》作為一部短篇小說集的名字,的確耐人尋味。我所感興趣的是少爺威威身上那種天然的城市生活經驗描述,當香港的迪斯尼在中國孩子眼中也不過如此而已的時候,少爺威威的生活成了一種過去時態的緬懷,由此日常性經驗通過倒轉的鏡頭發現了時代底色上凡人俗世的光影痕跡。所謂的普通話寫作是不斷丟失方言及其文化魅性的過程,我自己出生于皖西南,對于南方方言無疑很有親切感。很喜歡經過作家轉化之后進入文本的方言,像現代經典作家吳組緗的皖南味道、李劼人的巴蜀風格都很讓人癡迷。語言即風格依然適用于當下小說,遺憾的是,我們往往在言辭的表達中更深地迷失了自我。
黃詠梅:是的。從某個角度來看,語言是一個作家的精神家園,或者說“根”,因為我們自從有認知開始,語言就是思維的一種形式,語言對于寫作的人,就是故鄉。方言在逐漸消失,這不僅僅是作家才面臨的問題。現代人的遷徙,一代比一代普遍。你曾談到我們這一代是“無根的一代”——生長在故鄉,大學開始離開故鄉,大學畢業后到一個他鄉生存,直到他鄉變成故鄉,故鄉變成遠方。“無根”最直接、具體的表現,就在于方言從自己的日常話語里剝落,最終導致精神上的漂泊。我并不認為精神漂泊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尤其對于寫作的人來說,但是,語言失去故鄉,意味著作家割斷了一段重要的經驗——童年記憶。對作家而言,這是進行創作的主要源泉之一,很多偉大的作家都談到了童年記憶對自身寫作的重要性,這是我們不該拋棄的。
另外,比失去語言故鄉更為可怕的是,一種“西方中文小說”的腔調。近年來,我讀了不少西方小說。而它們對我寫作的影響,最為直接的就是敘述上語感的變化。記得以前上學的時候練習英語聽力,老師說,要反復多聽,即使你聽不懂也要把隨身聽放在枕頭邊,聽多了,你的語感就會養成,辨識就會容易起來。西方小說翻譯成中文,變成了“西方中文小說”,這意味著一種新的敘述語言的生成,而這種語言不自覺地“干擾”著我的寫作語言。舉個簡單的例子,我發現我對于破折號的使用頻繁了起來。在一句話里,需要解釋、轉折、加強的時候,我會來一個破折號,這種“破文”的使用,往往使句子加長延伸,讀起來綿長拖拉。破折號的使用在大量的“西方中文小說”里很常見。最近,我重新讀《世說新語》,重新咀嚼魯迅先生對其的評價:“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我覺得,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學,不需要插入任何的工具符號,而是以意來作為工具,寥寥幾筆,就可以完成起承轉合,言簡意深,實在是偉大。那種充斥著破折號的段落,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像一個搭建了高架橋的城市,它可能會緩解繁冗的交通,可它卻在破壞著城市的美觀,這是現代化的利與弊。同樣,過多的破折號也有可能會破壞我們傳統寫作的“文脈”。這是另一種你所說的“在言辭的表達中迷失了自我”。
郭艷:中國作家無法用游戲筆墨與及時行樂精神來解構被物化的人和人群,寫作依然在堅硬的現實情境中游走,你的寫作在觸及庸常小人物的時候是“冷”的,同時又帶著一種堅韌的精神性想象,比如《負一層》地下室飛翔的遙想,《瓜子》中女孩“我”在中途下了車,努力在縱橫交錯的軌道中尋找廣州的方向。正是因為“我”對于現代都市文明的想象,小說才呈現出了現代少年個體自省和自覺的意蘊。請問這個人物對于你寫作的意義。
黃詠梅:我記得在魯院學習的時候,你給我們上課,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你講道:“古代城市中的人和廣大鄉土社會中的人同屬一個穩定的鄉土文化心理結構,有著同構的政治、道德、倫理、情感和審美取向。古代的城市更類似于一個人生的驛站,古人主要有幾個理想——功名利祿、衣錦還鄉。這樣的人生主題,對于大多數進入城市的人而言,最終的結局就是告老還鄉,告老還鄉是一種安穩的人生結局和生命方式。而現在我們進入城市之后,是沒有退路可言的。”《瓜子》里的“我”正是那一大群沒有退路的人。城市容不下她,但她在成長過程中,已經強行使自己跟鄉村進行了割斷,她不再愿意講一句方言、她接受城市的教育、她的娛樂也是城市式的,盡管她明白自己依舊處于城市的邊緣,無法進入真正的城市,命運依舊無法自己掌控,但是,正如你在課堂上說的,這些人“城市理性催生下的心智與情感生長如野草般蕪雜,又如小獸般蠻橫”,所以,她斷然在被送回家鄉的火車途中,偷溜下了車,往回走。實際上,她的前方不是她的故鄉,往回走也不是她的城市,但是這種“蠻橫”和“執拗”主宰了她的人生。說實在的,我覺得她們這些人真的很可憐,身份的不確定使得她們自我不完整,她們是現代都市文明想象孕育出來的畸形兒。
郭艷:“我”沿河鐵軌的行走也可以延伸出更為深入的寓意——現代人沿著時間的線性路徑狼奔豕突,上演著黑色幽默基調上的悲喜劇。現代和古典被傳統所銜接,在斷裂的當下,我們更需要回溯的鄉愁來銜接古與今的裂縫。現代城市孕育出了更多的精神病人,現代人是沒有故鄉的無根者,他們在現代社會的漂游浪蕩既是過程,也是目的,一如卡夫卡的《城堡》的經典摹寫。
《小姨》是一篇具有相當闡釋空間的出色短篇小說,小說獨特的視點和進入歷史的路徑讓你的寫作開始直面整體性社會經驗和現時代精神氣質。小姨是文本層面的主人公,“我”作為敘事者,實質上是真正潛伏在常態生存中的偷窺者、閑逛者和發現者,“我”對于歷史與當下的觀察體現出了70后一代人獨特的寬容與同情之理解的心態。請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黃詠梅:《小姨》是我2013年寫的短篇。正如你說的,“我”的確是常態生存中的一個旁觀者。有時候我會想,在當下這個和平年代,那些貌似常態的狀態下,涌動著多少想掙脫常態而又頹然失敗的理想呢?小說里的“師哥”就是如今的常態,而“小姨”就是那些異數的失敗者。如果一條河流可以回溯,我們可以看得見過去,實在難以想象,這兩個人的結局會是如此迥異。而造成這種迥異的原因是,“小姨”還駐足在過去的河岸上,而“師哥”已經隨波逐流了。我覺得他們都是歷史的受傷者。我記得大學的時候,我那位87級的師哥在整理鋪蓋準備離校的時候,對我說過一句話:“你們是留下來打掃戰場的人。”這話當時我聽得不知所以然,直到若干年后的某一天,忽然就明白了。我們這一代人,生于和平年代,成長一帆風順,但是我們卻隱約知道自己實際上是站在了某個歷史的轉折點,就像《小姨》里的那個“我”,她既是一個敘事角度,同時也是那個留下來“打掃歷史戰場”的人,從殘存下來的一張畫像、半封書信、撕碎的日記本……這些東西里,試圖整理并且保存下來。在我看來,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所需要打掃的“戰場”,我們也不例外。至于你說的寬容和理解的心態,我認為這是我最終所要追求的目標——與整段歷史的和解。說起來,你也是70年代出生的,你怎么看我們這一代人對歷史與寫作的關系處理?
郭艷:因為你的《小姨》,最近去法國盧浮宮,特地在小姨鐘愛的畫像前留影。這是一代人對另一代人的觀察與揣度,小說中的師哥和小姨是投射在“我”這一代人心中最為直觀的歷史印痕。在所謂多媒體、歷史終結與現代社會體制全球性板結的時空節點上,“我”穿透師哥與小姨的肉身與靈魂,看到的是歷史與個體之間的謬誤與荒誕。小姨用貌似怪誕的行為來挽救自身的頹敗,而師哥則徹底投身于頹敗的欲望社會,以新世紀成功“師哥”吸引著長發的小師妹們。即便是相差幾十歲的年齡,只要有著欲望都市和商品社會的虛假繁榮,“師哥”們依然會是永遠的師哥們,他們以世俗的成功為自己和自己一代人的歷史畫上滑稽的句號。所以,我認為70后一代人切入歷史的方式更具備現代個體的主體性和反思性。
如果將自己的寫作與傳統勾連起來,你如何理解傳統?《何似在人間》對于鄉土人物和風俗的敘事,在以后的寫作中還會大量涉及嗎?你如何在寫作中重置“死亡”等終極性問題,并使之獲得超出庸常的意義?
黃詠梅:傳統在我的寫作中,意義更多指向于內部的精神氣息,而不是技巧,更不是寫作的內容。在《何似在人間》之前,我還寫過《檔案》,里邊也涉及到鄉土風物和風俗。這些內容不是我所擅長,因為我從小在城市長大,對于鄉村經驗,僅僅是跟隨父母、丈夫回鄉村短暫停留所獲取。但是,我對鄉村經驗、鄉土倫理遭遇城市文明、城市倫理所產生的錯位很感興趣,對于那些根深蒂固的東西如何被消解的過程感到既無奈又痛心,大概這些東西很符合我的審美趣味,就像張檸老師說我的小說總是呈現一種“挽歌”情緒。我正在寫一個中篇《滴水觀音》,也涉及到這類素材,對我來說,把握起來有點困難,但我真的想寫。
“死亡”這個文學母題,在我的寫作中,也是有階段性的。過去寫小說,為了體現“慘烈”和“沖突”,動不動就把人寫死。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太草率了,即使小說的邏輯沒問題,但用你的話來說,這些死亡都是很“庸常”的。隨意地用“死亡”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對于作家來說是很不負責任的,就像《涂自強的個人悲傷》里的涂自強。所以,我現在很謹慎。死亡是上帝交給每個人的答案,而向死而生才是我們文學需要面對的問題。就像人們常常引用愛米莉·狄金森給她的老師托·溫·希金遜先生的一封信中說的話:“從九月份起,我感到有一種恐懼卻又無法向別人訴說,于是我就歌唱,就像一個男孩走過墳場時所做的那樣,因為我害怕。”我也很喜歡這段話,并將它視為寫作的內心動源。死亡只有通過寫作中才有可能超出庸常,因為作家歌唱著越過了它,即使看不見人了,但那歌聲仍在。文學就是面對死亡、面對終極唱出的歌。
郭艷:你的小說敘事既有輕盈、靈動的才華,又有冷酷、倔強的心性。你是如何看待“寫什么”與“怎么寫”的?請談談以后的寫作路向。
黃詠梅:這個問題我更想聽聽評論家的看法,呵呵。二者的側重點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前者能產生文本的意義,后者能產生文本的意味。有意義的小說和有意味的小說共同構成了豐富的小說世界。就目前我的寫作體會來說,我會花更多的心思在“怎么寫”上,更在意如何能寫出讓人回味的小說。因為自身的局限性,我似乎不太能建構復雜的故事,所以,我對于“內容”的意義的豐富性不是特別苦心,但對題材的敏感度還是有的。再說,我前邊說過,我喜歡也擅長寫日常,實際上寫日常生活的小說更應該在“怎么寫”上下功夫,因為天下并無新鮮事。因為對這個問題,我以前沒想太多,也許我理解得不對。
郭艷:影響的焦慮無處不在,對你影響最大的作家是誰?如果有,請談談他對你的具體影響。
黃詠梅:讀了不少古今中外作家的優秀作品,我想,在里邊總是能汲取到很多看不到的營養吧。我喜歡的作家是有階段性的。比方說,我大學時代,喜歡廢名和張愛玲,還喜歡馮至和里爾克的詩歌。后來,我開始寫小說,就不怎么讀他們了,讀余華、蘇童、三島由紀夫、奈保爾、菲利·普羅斯。如果非要提到對我影響最深的,目前來看是奈保爾和門羅。我想說他們的小說都很對我的路子,或者說我有意識去學習他們。奈保爾是我在以前很喜歡的,他的《米格爾大街》幾乎被我翻爛,我特別被他那些既尖酸刻薄又感傷無奈的筆調所吸引,一段時間以來,我將他的尖酸刻薄視為真誠。很奇怪的,40歲以后,我越發懷疑這些真誠。我在門羅的小說里找到了這些懷疑的證據。如果說,奈保爾那些敢于挑剔、敢于撕裂、敢于反思是作家勇敢的真誠的話,那么門羅小說里那些樂于傾聽、樂于理解、樂于接納的善意就是一種更寬闊的真誠。勇敢的真誠是作家在寫作時的一種姿態,這姿態隨著作家抓起筆的那一刻就必須端起來,而更為寬闊的真誠,是作家的一種常態,它既是生活的也是寫作的,它與作家的價值觀水乳交融。進入中年之后,我慢慢戒掉了那種被我稱為“文藝青年腔”的真誠姿態,試圖向一種淡然無聲的常態靠近,試圖打開世界、打開他人、打開自己的方式變得多聲部些。
郭艷:面對新媒體,你如何處理獨立寫作和市場傳播之間的關系?
黃詠梅:這個問題很容易使人說一些“大話”。誰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廣泛傳播,從而贏取利益,所謂“名利雙收”。我并沒有高尚到說自己不在乎,但是,我實在做不到。我既做不到寫出自己想寫的作品又擁有市場,也做不到為了市場而寫出自己不想寫的作品。按照李敬澤先生說的“理想的讀者”,雖然有點自我安慰的意思,我還是得說,我暗自期待我的作品有幸能被我“理想的讀者”所看到,并喜歡。這是我對自己作為一個“理想的作者”的信念。
責任編輯馬新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