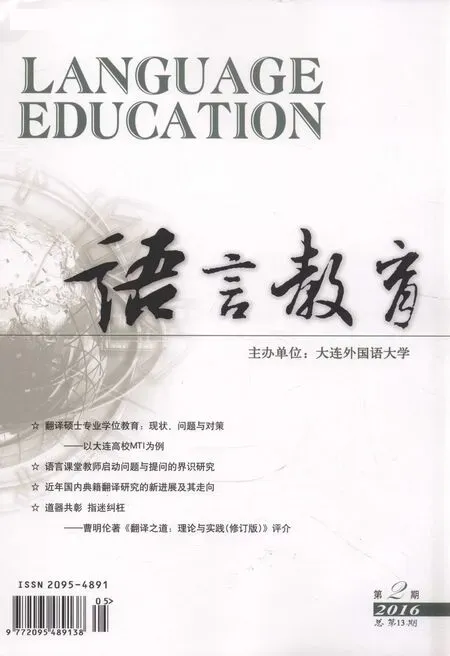英漢語言中“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研究
張淑芳 賈衛(wèi)章(浙江越秀外國語學(xué)院,浙江紹興)
?
英漢語言中“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研究
張淑芳 賈衛(wèi)章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xué)院,浙江紹興)
摘 要:“音響形象”這個說法是索緒爾最早提出的,是指語言的聲音。后來他用“能指”這個表達代替了“音響形象”說法。他認為“能指”和“所指”之間沒有邏輯的必然聯(lián)系,完全是任意性的。任意性被看作是語言的根本屬性。但隨著人們對語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尤其是隨著認知語言學(xué)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在語言的多個層面上,象似性與理據(jù)性也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上,語言學(xué)家、社會學(xué)家、心理學(xué)家等對語音象征(或聯(lián)覺通感、音義學(xué))的研究由來已久。英漢兩種語言即使從“音響形象”的音素層面與單音節(jié)(或詞根)層面上看,語言的理據(jù)性也是有理可證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兩種語言的理據(jù)性是互通的。語言的任意性應(yīng)該指語言的約定俗成性。承認語言的任意性,為研究語言的結(jié)構(gòu)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也就為我們進一步研究語言提供了一個缺省值。但探究人類語音的理據(jù)性無論對人類語言理論的研究完善還是對實際的語言教學(xué)都有很大的應(yīng)用價值。
關(guān)鍵詞:音響形象;語音象征;理據(jù)性;任意性;約定俗成性
1. 引言
語言學(xué)中的“音響形象”是由現(xiàn)代語言學(xué)之父,瑞士語言學(xué)家費迪南·索緒爾(Saussure)提出的。索緒爾(1999: 101-102)認為語音符號連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之后他用“能指”和“所指”分別表示音響形象和概念。他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聯(lián)系是任意的”,即符號(發(fā)音)與它的所指(意義)沒有任何邏輯的必然聯(lián)系。這一理論的提出對結(jié)構(gòu)語言學(xué)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因此任意性原則被奉為語言研究中的根本屬性。
能指與所指之間到底有無聯(lián)系呢?語音與語義之間是否存在著一定的邏輯關(guān)系?很久以來,哲學(xué)家、思想家、社會學(xué)家及語言學(xué)家一直對這些問題感興趣。早在古希臘時代,蘇格拉底就認為音義的關(guān)聯(lián)在于對事物實質(zhì)的模擬(吳漢,2011: 187)。其后柏拉圖也涉入此領(lǐng)域的研究,認為聲音和它們所表示的意義之間有某種聯(lián)系,語音符號并不是一種約定,而是自然的、名稱本身就有的(張立昌 蔡基剛,2013)。
19世紀初,威廉·馮·洪堡特則極力主張理據(jù)說,他在《論人類語言結(jié)構(gòu)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的影響》中說:“一種語言在語音系統(tǒng)方面的長處除了語言器官和耳朵的精巧,除了賦予聲音以更大的豐富程度和最完美的構(gòu)造的傾向之外,還特別建立在語音和意義的關(guān)系上。”(洪堡特,2006: 85)
與索緒爾同時代的葉斯柏森(Jespersen, 1924: 40)指出:“語言學(xué)家必須重視語言的形式和意義,語音和語義、語言形式和語言功能是不能相互脫離的。語言研究不能重視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語音和語義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20世紀50年代起,隨著認知語言學(xué)的深入發(fā)展,尤其是體驗哲學(xué)觀從人身體經(jīng)驗和認知出發(fā),認為語言表達需要經(jīng)常臨摹現(xiàn)實的事態(tài),語言表達會受到人們的感知體驗、概念圖式和認知方式等因素的制約,因此語言會表現(xiàn)出象似性和理據(jù)性。本文從英漢兩種語言的對比研究中探討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
2. 語音象征(或聯(lián)覺通感、音義學(xué))的研究
語音象征又稱語音象似性或音義學(xué),主要研究語音形式與意義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洪堡特(2006: 85)認為語音與意義的關(guān)系有三種表示方式:①直接模仿;②非直接模仿;③按照需要表示的概念親緣關(guān)系用近似的語音來表示。葉斯柏森(Jespersen, 1922: 16)指出語音象似性不僅是最初語言創(chuàng)造時的力量,而且會連續(xù)不斷地發(fā)揮應(yīng)有作用,這樣語音符號與語言意義會相關(guān)性更大。他指出擬聲就是對聲音的直接模仿,但這種模仿由于人類發(fā)音器官的局限性,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模仿,因此在語音選擇上會出現(xiàn)偶然性或意外性,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聲音組合來表示同一單詞,主要是由于不同民族的習(xí)慣化。雅柯布森被認為是音義學(xué)的主要支持者,他旗幟鮮明地反對索緒爾的任意說。他(雅柯布森,2012: 85)指出:“索緒爾武斷地把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guān)系說成是任意的關(guān)系,而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同語言社團中各自的習(xí)慣性的、后天學(xué)到的相鄰性關(guān)系。對于一個語言社團的所有成員而言,這種相鄰性關(guān)系具有強制性。伴隨相鄰性的還有相似性的原則表現(xiàn)出來。”
Hinton等(1994: 1-5)則將語音象征進一步分為:物質(zhì)性語音象征(corporeal)、模擬性語音象征(imitative)、通感性語音象征(synesthetic)和慣例性語音象征(conventional)。物質(zhì)性語音象征是指用來表達說話者情感或身體內(nèi)在狀態(tài)的非書面詞或語調(diào),往往是無意識而發(fā)出來的,如咳嗽、打嗝,或感嘆時發(fā)出的嘆息等。模擬性語音象征主要指擬聲詞。通感性語音象征是指用元音、輔音或超音段來表示物體的大小、形狀,這種語音象征也成聯(lián)覺通感。慣例性語音象征是指某些音素或音素群可聯(lián)想成某些意義,這種聯(lián)想是因語言而異的,具有慣例性。本文中涉及到的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研究主要指后兩種語音象征,即通感性語音和慣例性語音的理據(jù)研究。
3. 音素層面上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
探討語言中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應(yīng)該首先從組成語音的最小成分音素開始。語言學(xué)中,結(jié)構(gòu)主義將音素定義為構(gòu)成音節(jié)的最小單位或最小的語音片段,是從音質(zhì)的角度劃分出來的最小的線性語音單位。音素一般分為元音和輔音兩大類。人類可以發(fā)出各種各樣的聲音,但只有其中一少部分聲音成為語音。而這一小部分的語音在世界大多數(shù)的語言中是基本共通的。漢語中有聲母21個、單韻母及復(fù)韻母35個。英語中有輔音28個,單元音及雙元音20個。雖然在總體數(shù)量上有些差別,但在基本音上兩種語言的音素是基本相同的。
3.1語音與人類自身的生理結(jié)構(gòu)及所處環(huán)境
人類語言在演化的過程中,關(guān)鍵的一步是語音取代了原始的手勢。王士元(2013: 59-60)認為,更為關(guān)鍵的一步,是從一個基本的韻律系統(tǒng)向一個完整的音段系統(tǒng)過渡,即:元音和輔音的出現(xiàn)。韻律特征表現(xiàn)為不同的語調(diào)模式和各種超音段系統(tǒng),它不同程度地保留在所有語言中。但人類語言最大的表現(xiàn)力,來自元音和輔音的交替串聯(lián)。元音除了具有各種音質(zhì)以外,還負載有效的聲學(xué)強度,而輔音負載的強度較小。另一方面,輔音因為有不同的發(fā)音方法,而大大豐富了語音符號單位的數(shù)量。這樣就有可能在保持聲學(xué)區(qū)別性的情況下,建立起越來越龐大的詞匯表。因此,這兩種語音以一種重要的方式互相支持:在需要大聲呼喊的時候,元音提供聲學(xué)動力;輔音則提供大量的區(qū)別特性,以獲取更大的信息量。
為什么世界上不同的語言,其語音的基本形式音素及其數(shù)量會大致相同呢?從生理性質(zhì)來看,一個發(fā)音動作形成一個音素。人類的呼吸是生命的需要,即身體呼吸系統(tǒng)的循環(huán)功能。由于發(fā)輔音時要把嘴巴閉上,而發(fā)元音要把嘴巴張開,這種一開一合的循環(huán),使得說話人在說話過程中,可以進行一種鐘擺式的運動。同時,一呼一吸的節(jié)奏也構(gòu)成了發(fā)音的生理基礎(chǔ)。人類利用語音進行交流時大都是利用肺內(nèi)發(fā)出的氣流,經(jīng)過不同的腔室,通過不同的開閉、摩擦等方式產(chǎn)生氣流的振動實現(xiàn)的。同樣的生理結(jié)構(gòu)及最初先民相似的社會群體生活方式?jīng)Q定了某些易于發(fā)出、經(jīng)濟有效、易于感知的音素成為了人類語言中的核心語音。清代陳澧在《東塾讀書記》中說:“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gòu)之者也,聲音象乎意而宣之者也。”此論述表明,至少在漢語中,中國學(xué)者早就注意到了語言符號的音義之間具有可以論證的理據(jù)性關(guān)系。即,人通過其發(fā)音器官肌肉模擬自然界事物狀態(tài)或形態(tài)的活動,將音與義聯(lián)系起來(見張彥群,2007: 70)。
3.2語音的象征意義
吳漢(2011: 187)指出,在英漢兩種語言中,人們早就注意到很多語音與特定意義間存在某種關(guān)聯(lián),這種關(guān)聯(lián)絕不是個別現(xiàn)象,是無法完全用語言任意性解釋通順的。例如,發(fā)前元音/i:/或/i/時,開口度最小,幾乎是閉合,所以無論是在漢語中還是在英語中/i:/或/i/往往表示細小。而如:漢語中,樹的細梢稱為“樹杪”,谷穗上的細芒古稱“秒”,時間的一個短小單位也叫“秒”,“杪”和“秒”都表示細小微末。藐視的“藐”和渺小的“渺”又都有小的意思。這些字都帶有前元音/i/。英語的teeny(極小的),weeny(極小的),wee(微小的),bit(點滴),mini(微型的)等都帶有/i:/或/i/音。語言學(xué)家薩丕爾(Sapir, 1929: 225-239)通過實驗的方法,用諸如mil-mal這樣的生造最小對立詞匯驗證了語音象征的存在:多數(shù)受試者傾向于用mil類的“細音”來表征小的事物,用mal類“洪音”來表征大的事物。Ultan(1978)研究了136種語言的元音,指出元音與大小規(guī)格的關(guān)聯(lián)的確普遍存在于多數(shù)語言中,且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前高元音表“小”,后低元音表“大”。
對輔音人們通常是用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式來描述。發(fā)音方式和發(fā)音部位的不同,也會造成人們在聽力上對這些語音的感知不同。Leech (1969:98)研究發(fā)現(xiàn):流音/l, r/、鼻音/m, n, n/、擦音和送氣音/f, s, v/等比較柔軟;而塞音/b, d, k, g, p/和塞擦音/t, d/則顯得剛硬。和元音類似,發(fā)音部位靠前的輔音常被感知為“弱小,愉悅”。擦音/s, f, z/常用于描述類似摩擦的聲音和動作,如嘶,hiss等。塞音(如/p, t, k/)多描述短促突然的聲響和動作,如bop擊打,pop爆聲,tap踢踏,tick滴答聲。清濁對立特征也有語義表征功能:清輔音常表征更小、更輕、更加鋒利;擦音比塞音更易表征較小、較輕和較快的概念。/m/是濁音,響音,唇音,在漢語中表黑暗、遮蓋和盲等意義,如幕、墓、暮、昧、霾、霧、滅、幔、茂、密、茫、冥、夢、蒙、盲、眇。英語的murky陰暗的,melancholy悲哀,moody易怒的,mournful悲傷的,gloom憂郁,doom噩運等詞也與表黑暗,憂愁等義有關(guān),其中有些例詞中的后元音/u/更強化了厚重和陰暗程度(見吳漢,2011:187)。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在音素層面上,人類語音的理據(jù)性與人類的發(fā)音器官及相似的生活體驗有關(guān)的。Halliday(1999: 29-30)指出:“從人際內(nèi)容和語篇內(nèi)容來看,語法與語音之間的關(guān)系通常是自然的:因而人際內(nèi)容通常通過音高的上下起伏從韻律上得到體現(xiàn),語篇內(nèi)容則通常通過語音的變化(如語音曲線中主要的音高變化)或序列的變化(如由不同成分與小句首位之間的距離產(chǎn)生的突出梯度)得到體現(xiàn)。”
音素層面是語音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層面,是人類語言的基石,事關(guān)人類語言的形成。但由于經(jīng)歷的歷史久遠,變遷很大,很多音素的理據(jù)性已無法追溯。甚至有些音素與其理據(jù)性完全相反,例如,在英語中常見的表示“大”的big中有/i/,而表示“小”的small中有/:/。所以探討該層面的理據(jù)性頗為艱難,但不能追溯其理據(jù)性并不能說明其沒有理據(jù)性。索緒爾關(guān)于語言的任意性實際上是在此無奈的基礎(chǔ)上解釋語言特征的不二選擇。假定語言音響形象的任意性,實際上是為我們進一步研究人類語言的結(jié)構(gòu)提供一個缺省值。
4. 單音節(jié)字(根)層面上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
4.1單個漢字及聲調(diào)的理據(jù)性
不同的音素結(jié)合構(gòu)成更大層次的結(jié)構(gòu)。由于漢語是單音節(jié)語言,以字為單位,所以漢語中的單字構(gòu)成了大于音素的基本單位。漢字的數(shù)量雖然很多,但眾多的漢字由數(shù)量很少的音素結(jié)合體構(gòu)成。據(jù)2012年第11版新華字典中的漢語拼音音節(jié)索引,共有416個音節(jié)。除了音節(jié)外,漢語中的聲調(diào)也是一種區(qū)分意義的音響形象。
張立昌(2014: 159)指出:“從表面上看,聲調(diào)是一種別義手段,但根據(jù)漢語普通話單音詞語意義的分類表明,聲調(diào)的調(diào)長、音高與強度與詞語所表達的形狀、大小、質(zhì)地、程度等特征都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聲調(diào)在本質(zhì)上,并不是任意性的意義區(qū)分標記,而是分別與特定意義相關(guān)聯(lián),具有理據(jù)性;其理據(jù)在于聲調(diào)在發(fā)音過程中通過其自身的特征和對發(fā)音器官的運動、狀態(tài)的影響,以便使說話者更為準確逼真地模擬事物的特征。”托馬塞洛(2012: 164-165)指出:“人類一開始時會運用某些聲音,并通過自然且有意義的方法,靠著手腳比劃動作或物品。隨著其他人經(jīng)由社交學(xué)會這樣發(fā)聲后,這些聲音就變成慣例而約定俗成,于是就沒有必要用手腳比劃了。”
如果不考慮聲調(diào),這些數(shù)量有限的音節(jié)就是漢語中全部單個漢字的音響形象。即使考慮音調(diào),416個音節(jié)的4倍數(shù)量也是有限的。這些數(shù)量有限的音義結(jié)合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靠慣例而約定俗成的。因為靠慣例約定俗成,這些數(shù)量有限的音義結(jié)合體會因民族或社會群體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漢語中的rou(肉)與英語中的meat(肉)雖然為同一意義,但音響形象不一樣。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任意性并不是隨意的,它是一個民族或社會團體內(nèi)約定俗成的。荀子在《正名》中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從音義結(jié)合的角度理解這句話,則荀子在強調(diào)某音和某義的結(jié)合必須得到社會認可。音義結(jié)合的社會認可過程即“約定俗成”過程,這種“約定”和認可正是音義結(jié)合理據(jù)性的體現(xiàn)。許國璋先生(1991: 37)認為,“任意性”與“約定俗成”不是同義詞,它們屬于兩個層次。“約定俗成”的“約”意味著一個群體的存在,意味著說話人和受話人的存在;所謂“約”是指“社會制約”的“約”。受社會制約的東西,是社會共議的結(jié)果,決不是任意的創(chuàng)造。Langacker(1987: 58)對此也持相同觀點:“象征單位是音位單位與語義單位直接相連的結(jié)合體,象征指一定的形式約定俗成地代表一定意義。”
4.2漢語中同音異義的理據(jù)性
漢語中約定俗成的音義結(jié)合體數(shù)量很少。要賦予眾多的聲音意義就必然導(dǎo)致漢語中大量的同音異義字的出現(xiàn)。同音異義字是研究漢語字面層次上理據(jù)性的突破口。王寧(1996: 146)認為,漢語詞匯的積累大約經(jīng)歷了原生階段、派生階段與合成階段。原生階段,“約定俗成”的規(guī)律在漢語詞匯音義結(jié)合中起重要作用;派生階段,漢語詞匯“音近義通”的現(xiàn)象大量發(fā)生;合成階段,隨著派生造詞方式的淡化,“音近義通”現(xiàn)象逐漸退出漢語詞匯發(fā)展的歷史舞臺。因此,漢語中大量同音異義字的出現(xiàn)可以用“音近義通”來解釋其理據(jù)性。
音近義通是指,當(dāng)語言的聲音與語言意義在運用中被人們約定俗成后,會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成為交際的工具。但隨著社會生活以及人們交際等各方面的不斷變化,需要不斷地產(chǎn)生新的表達方式以滿足社會交際的需要。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表達方式呢?人類認識新的事物往往借助于事物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以及新事物與舊事物之間的某些共同之處。因此,人們在規(guī)定了某種音響形象為某種事物的名稱之后,往往借助于語言的類推作用,用相同或相似的音響形象來表示新的概念。于是,音近義通便成為一種常見的語言創(chuàng)造現(xiàn)象了。因此黎千駒(2009: 83)認為,“聲音與意義之間的聯(lián)系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造新詞時的音近義通,即一組同源詞中源詞與派生詞之間在意義上具有內(nèi)在的淵源流別關(guān)系,構(gòu)成一組音義相關(guān)的詞。第二,記錄詞時的音近義通,即語言中的某個詞(聯(lián)綿詞) 有時用幾個形體不同但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記錄。第三,使用詞時的音近義通,即用借字來代替本字。上述三種音近義通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構(gòu)成了音義之間相互聯(lián)系的三個層面,即同源詞之間的音近義通、聯(lián)綿詞不同書寫形式之間的音近義通、借字與本字之間的音近義通。”
4.3英語語根的理據(jù)性
英語與漢語不同。從其起源來看,英語屬于印歐語系,而漢語則屬于漢藏語系。英語是典型的多音節(jié)語言,而漢語是典型的以單音節(jié)(即單個漢字)為主的語言。研究英語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需從單音節(jié)單詞(或詞根)開始。英語詞根包括自由詞根和粘著詞根兩種。所以馬秉義(2001: 34)認為,英語詞根大體與漢語字的音節(jié)相似。英語單音節(jié)詞的第一個輔音,大體與漢語的聲母相同,后邊的元音和其它輔音相當(dāng)于漢語的韻母。因此,英語中詞根的音響形象與意義的結(jié)合與漢語中單個漢字的音義結(jié)合有著同樣的關(guān)系。雖然英語單詞眾多,但構(gòu)成單詞的詞根的數(shù)量卻有限。英語中常用詞根250多個,加上常用詞綴大約300個,共計不到600個。英語中自由詞根多來自本族語的基本單詞,粘附詞根多來自古典語的基本單詞的詞干部分。由于基本單詞反映的是全民族共同活動的基本概念與情境,所以詞根的語義也帶上了基本單詞固有的特點:常用性、穩(wěn)定性、單一性和能產(chǎn)性。例如:自由詞根work(工作)、man(人),粘附詞根act(做)、anthrop(人),它們的基本語義都是常用、穩(wěn)定、單一的,它們都能產(chǎn)生數(shù)以百計的同根派生詞。這是詞根語義最基本的特征。
4.4英漢語中的音義同源
研究音義的結(jié)合,不能只在一種語言中找例證,最好能在兩種語言或多種語言中找到相似的例子,從而可進一步表明至少在某些音上,音義結(jié)合是同源的。英漢語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關(guān)于“母親、媽媽”的發(fā)音。在漢語中,表示母親的稱呼有“媽、娘、母”等方式;英語中則有:“Mum、Mother、Mummy”等。兩種語言中對同一稱呼的第一個音都使用了鼻輔音/m/或/n/。發(fā)/m/音的要領(lǐng)是:雙唇緊閉,舌頭放平,氣流從鼻腔送出;發(fā)/n/音的要領(lǐng)是:雙唇稍微張開,舌尖緊貼上齒齦,氣流從鼻腔送出。無論是/m/音還是/n/音,氣流都要從鼻腔送出,而口腔要形成封閉狀態(tài)。所以雅柯布森臆測,世界語言里,通常在“媽”等字中所出現(xiàn)的語音,也許是從兒童吸奶時嘴里肌肉活動練來的。
馬秉義(2006)認為英漢語中都有很多表示“看”的詞匯,用于表示各種方式的“看”,各種目的的“看”等等。從語源學(xué)的角度分析,這些詞匯的音義雖有不同卻互有關(guān)聯(lián),看起來好象沒有關(guān)系,卻是同源詞。從語根學(xué)的角度分析,即從人類語言發(fā)生學(xué)的角度來分析,英漢語中表示“看”的詞匯,它們的根很可能原本是同一個。
通過研究《果裸轉(zhuǎn)語記》,馬秉義(2001)探討了漢語和英語中的一些同源詞。為我們研究音義結(jié)合提供了大量的理據(jù)性。《果裸轉(zhuǎn)語記》的作者是清代人程瑤田。《果裸轉(zhuǎn)語記》的大意是,我們的祖先居樹上,稱為有巢氏,吃果子,對果子認識頗為深刻。果是圓的,圓的會轉(zhuǎn),轉(zhuǎn)的聲音是“骨碌”,果子落地就會發(fā)出骨碌之聲,所以凡聽到骨碌之聲,就知道是“果子,有了果子,吃果子”等等的意思。
下面簡單轉(zhuǎn)述馬秉義(2006: 23-24)文中對英漢語中“看”的同源分析。
“骨碌”之音就是gulu,省去后音即為gu,漢字就是“顧”。gu音變?yōu)閗u,即首輔音為k,如kui,漢字為“窺、睽”;kan,漢字為“看、瞰”。gulu省去前音即為lu,lu也可以表示“走”義,由“走”引申為“看”。最常見一個字是“溜”,通常有兩義,一是“走”,如“溜了”,此義的“溜”也可寫成“遛”;二是“看”,如“溜一眼”。另一個字是“瀏”,這個“瀏”與“溜”同音,表示“看”義。“溜”的另一個近音字“瞜”,唐山、北京等地說“瞜瞜loulou”,也是表示“看”的意思。首輔音是l音的還有:“瞭(遠看)、睞(斜眼看)、覽”等。英語中有關(guān)“看”的詞匯也很多,最常見最常用的有下列各組:① glance看,glimpse一瞥,glare光滑的表面,耀眼的光,怒目而視,glint閃光,gleam轉(zhuǎn)瞬即失的光,glisten閃光。② gaze睜大眼睛看,凝視,注視,garage車庫,本義看,保護,保護的地方,garnish裝飾,目的是為了看,garret閣樓,本義崗樓,即望樓,garrison衛(wèi)戍部隊,guide向?qū)В琯uard本義“照看”,引申為“守衛(wèi)”。
馬秉義(2004)提出了20個原始語根,用“因由天地,義由音省,音隨意轉(zhuǎn),音近義通,反義同根”幾項原理,把散沙般的詞匯有機地串聯(lián)起來,建立了英語詞匯系統(tǒng),對英語詞匯地理據(jù)性進行了深層次的挖掘。因此,在單音節(jié)字(根)層面上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較音素層面上的理據(jù)性更為明顯。
5. 語言理據(jù)性與任意性的辯證關(guān)系
在音素和單音節(jié)字詞的基礎(chǔ)上,語言單位進一步按邏輯關(guān)系擴大。因此,在多音節(jié)字詞層面上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是普遍存在的,本文不再贅述。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人類語言音響形象的理據(jù)性是存在的,并非是完全任意性的。那么承認這種觀點是否可以完全推翻索緒爾的任意性結(jié)論呢?答案當(dāng)然是否定的。許國璋(1991: 33-34)指出:“從形而上學(xué)的角度去解釋語言的最始態(tài),即從亞當(dāng)模式的角度看,語言符號是任意的;從后于經(jīng)驗的角度看,語言符號不再是任意的。而承認‘任意性’,即是把詞義從象似性中解放出來,即是掙脫象形和擬形,象聲和擬聲的束縛,看起來毫不講理,其實是為抽象地和自由地造字提供理論根據(jù)。”這段論述至少可以表明,語言音響形象的任意性為人類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如果沒有一些數(shù)量有限的、固定的音響形象,語言系統(tǒng)將失去存在的基礎(chǔ)。
而這些數(shù)量有限的、固定的音響形象是否具有理據(jù)性呢?對該問題的探討實際上等于在探討語言的起源問題。本文事實上也在致力于探討這個問題。通過以上從兩個層面的探討,我們至少可以發(fā)現(xiàn),人類溝通自語音形式出現(xiàn)后,約定俗成的慣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時間一久,慣例慢慢“趨于任意”。如果將語言的約定俗成看成是語言的任意性的話,這些“任意性”的音響形象在數(shù)量上是非常有限的,即,僅局限于音素層面上的語音,以及類似漢語的同音單字或英語詞根。
而在很多情況下,語言音響形象的任意性是指語言的規(guī)約性或約定俗成性。對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與理據(jù)性的關(guān)系,王德春(2001: 76)認為,“任何語言單位及其組織規(guī)則一旦為社會公認,就可約定俗成。但是,語言的意義與人的認識過程緊密聯(lián)系,它與語音形式的聯(lián)系雖然是任意的,但在一種語言內(nèi)部往往具有理據(jù)性”。
目前,語言理據(jù)研究之所以不能取得突破性成就主要是因為理據(jù)的喪失。作為語言符號的主要方面,音響形象自語言產(chǎn)生以來經(jīng)歷了漫長的時間,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語音發(fā)生變遷是很有可能的。由于文字的發(fā)明遠遠晚于人類的語音,所以這種變遷在文字出現(xiàn)之前是無法記錄保存的,只能憑著一代代人的口述留存下來。而這種耳熟能詳?shù)牧舸娣绞绞茏匀粭l件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很大。環(huán)境變化、社會變遷會導(dǎo)致語音的區(qū)域差異,因此即使同一種語言也存在多種方言,而多樣的方言又進一步說明語言符號的約定俗成性。
6. 結(jié)語
雖然索緒爾對語言進行描述時,任意性是主要的特征,但語言的任意性并不說明語言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不存在理據(jù)性。承認語言的任意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人們在此問題上的裹足不前,并為語言的研究打下基礎(chǔ)。但世界萬物中,只有人在不斷地追憶自己的過去、探索遙遠的未來,人的探索與追求是人區(qū)別于動物的本質(zhì)特征。在語言教學(xué)中,探究語言現(xiàn)象的理據(jù)性不僅可以加深語言使用者的印象,而且還可以對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有更深刻的領(lǐng)會。而在外語教學(xué)中,通過掌握原始語根擴展詞匯量是一種全新、高效、充滿趣味的方式,能達到聽音辨義、見詞明理的境界。因此,語言理據(jù)性的研究無論在理論探索還是在教學(xué)實踐中,其意義不可低估。
參考文獻:
[1] Halliday, M. & C. Matthiessen.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M]. London: Cassell.
[2] Hinton, L., J. Nichols & J. Ohala. 1994. Sound Symbol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Jespersen, O.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New York: Holt.
[4] Jespersen, O. 1924.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M]. London: Allen & Unwin.
[5]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 Leech, G. 1969. A Linguistic Guide to Poetry [M]. London: Longman Press.
[7] Sapir, E. 1929. A Study in Phonetic Symbolism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2): 225-239.
[8] Ultan, R. 1978. Size-Sound Symbolism [A]. In J.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4) [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9] 洪堡特.2006.錢敏汝譯.論人類語言結(jié)構(gòu)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的影響[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10] 黎千駒.2009.“音近義通”原理論[J].保定學(xué)院學(xué)報,(5): 82-86.
[11] 馬秉義.2001.果裸轉(zhuǎn)語與R詞族比較[J].解放軍外國語學(xué)院學(xué)報,(6):33-36.
[12] 馬秉義.2004.英語詞匯系統(tǒng)概論[M].北京:氣象出版社.
[13] 馬秉義.2006.“看”的音義聯(lián)想及其漢英比較研究[J].外語研究,(4):23-24.
[14] 索緒爾.1999.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xué)教程[M].北京: 商務(wù)印書館.
[15] 托馬塞洛.2012.蔡雅菁譯.人類溝通的起源[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16] 王德春.2001.論語言單位的任意性和理據(jù)性--兼評王寅《論語言符號象似性》[J].外國語,(1):74-77.
[17] 王寧.1996.訓(xùn)詁學(xué)原理[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8] 王士元.2013.演化語言學(xué)論集[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19] 吳漢.2011.論語音象征[J].甘肅科技,(1):187-189.
[20] 許國璋.1991.許國璋論語言[M].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
[21] 雅柯布森.2012.錢軍譯.雅柯布森文集[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22] 張立昌 蔡基剛.2013.20世紀以來的語音象征研究:成就、問題與前景[J].解放軍外國語學(xué)院學(xué)報,(6):8-13.
[23] 張立昌.2014.聲調(diào)意義的疆域—漢語普通話單音名詞聲調(diào)理據(jù)研究[J].齊魯學(xué)刊,(1):155-160.
[24] 張彥群.2007.語音的象征性與詩歌表達藝術(shù)[J].許昌學(xué)院學(xué)報,(1):70-73.
The Motivated Research of Sound-imag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ound-image was first proposed by Saussure, which was used to refer to the language sound, and later he replaced it with signifier. He though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was not logical and meaning-related. So the arbitrariness of language has been thought of a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for language research. However,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 in especial, more and more evidence has been put forward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and iconicity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on different levels of language. In fact, the research of sound symbolism (or synesthesia, phonosemantics) has been made by linguists, sociologists, psychologists etc. for a long time. The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human languages has show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languages and the object world is not merely arbitrary. Even from the level of phone and monosyllable (or root of sound-image), the motivatedness of language can be verified. In some degree, the arbitrariness of language refers to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language. The arbitrariness of language is useful for language research, as it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of language. That means it gives us a default value to make a further study of language. But the motivated research on human languag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oth to improve the theory itself and to put it into use in ou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Key Words:sound-image; sound symbolism; motivatedness; arbitrariness; conventionalization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891(2016)02-0053-06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4年紹興市高等教育教學(xué)改革科研項目”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張淑芳,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語言學(xué)、應(yīng)用語言學(xué)研究。賈衛(wèi)章,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語言學(xué)、認知語言學(xué)、文體學(xué)研究
通訊地址:312000 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qū)群賢中路2801號 浙江越秀外國語學(xué)院越秀鏡湖校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