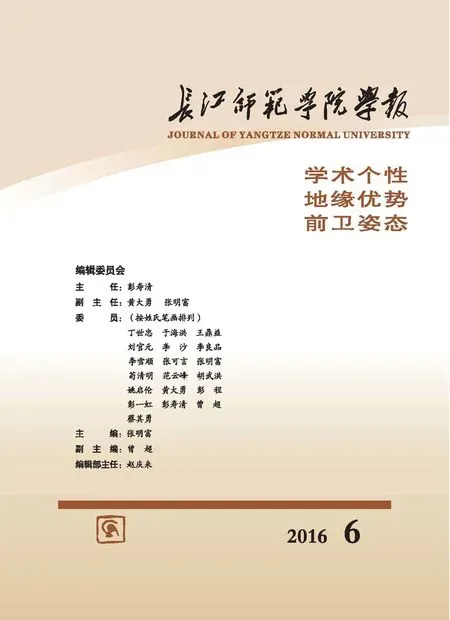教育史學與教育史研究:基于拉格曼的視角
羅曉文
(北京師范大學 教育歷史與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教育史學與教育史研究:基于拉格曼的視角
羅曉文
(北京師范大學 教育歷史與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875)
埃倫·康德利夫·拉格曼的 《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困擾不斷的教育研究的歷史》一書主要體現了作者嘗試從學科史的角度使教育研究走向科學的努力。在實用主義史學觀和進步主義史觀的影響下,作者圍繞教育中的性別問題、教育研究的科學化、教育研究職業化、課程改革以及教育研究的 “內憂外患”等主題并運用敘述史和問題史相融合的史學寫作方式,創造性地開辟了一個教育史研究的方向。
拉格曼;學科史;教育科學化
一、簡介
埃倫·康德利夫·拉格曼(EllenCondliffeLagemann,1945-),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史學家,現任巴德學院里維研究院和巴德監獄機構(BardPrisonInstitute)的教授。在此之前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和歷史學院的教授、紐約大學教育史教授、哈佛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斯賓塞基金會主席等職。她曾出版過AGenerationofWomen:EducationinLivesofProgressiveReformers(1979),這本書中關于進步主義教育中女性的角色也反映在她在2002年出版的 《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困擾不斷的教育研究的歷史》(以下簡稱為 《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一書中,如在導言中她就講到了教育的女性化問題。這本書是在2002年哈佛大學的讀書活動中被全校師生挑選出來公認的4本 “好書”之一,索爾·科恩 (SolCohen)對此書評論道:“書中從一個新的角度折射了美國的教育學校改革運動中的困境,它將會在20世紀的教育史發展中占據重要的角色。”[1]705該書于2006年經由花海燕等譯成中文版。
作為一名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史學家卻覺得教育研究是一門 “捉摸不定的科學”,這里反映出了教育首先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教育是一門科學嗎?如果按照波普爾在 《歷史主義的貧困》中提出的科學是需要證偽的,而且因為 “社會的一致性大大不同于自然科學的一致性。它們從一個歷史時期到另一個在不斷變化著,而人的活動就成為改變它們的力量。因為社會的一致性并不是自然的規律,而是人為的。”[2]9因為很多教育命題不能被證偽,是 “人為”的,所以在波普爾看來教育如果追求像自然科學那樣的規律是難以實現的,而拉格曼要做的就是要沖破這種關于 “科學”的學科界定,試圖撥開教育研究中的迷霧,通過探究教育研究本身去發現教育研究究竟在那個環節上出現了問題,以此努力建立一門 “科學”的教育。《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的歷史敘述方式并不是線性的,而是由8章各自成體系的主題構成,類似問題史的寫法,文章各個主題的寫作時間在1890-1990年之間,是近代美國教育研究突進的重要時間段。在此書中拉格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我將著重探討人們如何定義 ‘科學’,并如何把 ‘科學’與教育的實踐和發掘教育的文化社會意義的努力相聯系。性別差異、教育職業化、組織機構間的沖突和競爭,以及對20世紀行為科學包括對教育產生巨大影響的定量分析方法所持的羅曼蒂克的態度。”[3]7因此,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是從教育研究的角度去探討教育史應該做什么,并以此使教育史的使命更加明確。如果我們能夠從教育史的角度去探討教育的核心問題,并且能夠提取出相關的理論來指導實踐,那么 “科學”的教育史研究也反過來會推動教育變成一門 “科學”,突破教育研究的 “捉摸不定”的不安,以提高教育學的地位,而不是將教育視為 “投錯母胎的嬰兒”[3]17,處于科學研究邊緣的尷尬地位。
二、拉格曼關于教育史研究和教育史學研究的前提假設
這里先從歷史的假設出發去研究拉格曼的教育史學方法和教育史研究相關的內容,是因為歷史本身是歷史研究者對史料的研究。俞吾金說:“歷史是指已經發生過的事實的總和……任何一個史學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面對歷史事實。由于他與歷史事實之間存在著時間間距,因而根本不可能親身去經歷這些早已湮沒的歷史事實,而只能通過歷史資料的媒介,從觀念上去重組歷史事實。”[4]4英國著名的史學家E· H·卡爾在 《歷史是什么》中指出:“只有當歷史學家要事實說話的時候,事實才會說話:由哪些事實說話,按照什么秩序說話或者什么樣的背景下說話,這一切都是由歷史學家決定的。”[5]83卡爾還說:“當我們嘗試回答 ‘歷史是什么’這類問題的時候。我們的回答在有意無意之間就反映了我們自己在時代中所處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廣闊問題的一部分答案,即我們以什么樣的觀點來看待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5]89因此,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歷史學家都有自己的假設和前提。拉格曼在該書中寫道:“因為所有的歷史都是一種想象式的重構,建立在對過去的不可避免的完整性和解釋性的紀錄的基礎上。“[3]245“事實上,任何一部真正的歷史著作或多或少總會涉及思辨歷史哲學中的一系列命題,總會在歷史的敘述和解釋中蘊含著它對一系列命題、歷史意義的看法,但歷史學家并不把這些命題專門抽出來進行討論。”[6]21那么既然拉格曼認為歷史是 “一種想象式的重構”,那么她是從哪里開始走向 “想象”的呢?她關于美國教育史研究和教育學研究的假設是什么呢?
首先,20世紀上半葉美國進步主義學派逐漸壯大,“進步學派的共同點就是分析歷史進程中的矛盾和斗爭”[7]270。拉格曼在 《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中第7章中 “提供基礎與放棄支持:聯邦政府對教育研究的作用”中通過描述教育機構與政府機構之間在經費之間的博弈,這種沖突觀念與進步主義的史學觀相似,同時拉格曼在序言中寫道:“描寫美國教育政策運作的權利下放所帶來的馬戲表演似的混亂不清也是本書的中心內容”[3]7。但是拉格曼不同于20世紀上半葉 “沖突”的進步史觀,而是經過發展而成的 “沖突—和諧”史觀。這是教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范式,歷史上如古希臘時期曾有 “循環歷史觀”“退化史觀”以及近現代的 “進步史觀”,對于歷史的發展路徑是如何的探討影響著歷史學家解釋歷史的角度,影響著人們對于歷史的價值取向。在 《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中,拉格曼明顯地是持有進步史觀。她指出:“教育學術發展的多樣性與不平衡性本身使得教育學術的歷史變得十分復雜。這段歷史并不是一個走向衰退或者喪失機會的簡單過程。”[3]11從拉格曼對美國教育歷史發展的樂觀態度可以看出其深受進步史觀影響。拉格曼在書中贊成恩師克雷明的教育思想,認為克雷明的 《學校的轉變過程》是進步教育研究的范例。拉格曼在2013年與格雷厄姆(PatriciaAlbjergGraham)合著的《勞倫斯·克雷明(1925年10月31日—1990年9月4日)的傳記回憶錄》中,贊賞了克雷明作為一名教育史家對于教育改革所表現出來的熱衷。
其次,美國傳統史學的實用主義傾向。拉格曼在書中寫道:“事實上,我對教育的重要性充滿著樂觀和信心。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也是希望這本書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發展教育學術,進一步提高我們對教育的理解,進一步發展我們進行合理的,具有廣泛甚至普遍意義的決策和實踐能力。”[3]9拉格曼的實用主義思想還體現在她對杜威思想的推崇。拉格曼希望像杜威在 《民主主義與教育》中表達的,將學校改革看成是社會改革的中心。在 《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第2章 “專業化與孤立化:教育研究成為一種職業”中就大篇幅地介紹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而且拉格曼曾經在《教育研究的復雜世界》(ThePluralWorldsof EducationalResearch,1989)中用了很長的篇幅探討了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強調教育研究要服務于教育改革。
再次,學科史的前提假設。拉格曼此書的創新之處在于她開辟了教育史研究中的一個新領域,即關注教育學史。她說:“盡管教育早已是大學的教學與研究中規模最大的專業領域之一,但是近來一些談到大學及其研究的文章著作中,教育學術研究一直受到極大的忽略。教育歷史學家一直關注教育政策史、學校管理史、近來的教師和教學史,而對社會思想史感興趣的歷史學家主要研究社會學、心理學和其他一些專業,特別是醫學,但是沒有人研究過教育研究的歷史。所以我的一個希望就是能夠開始填補歷史學研究中的一個空白,增進對教育、教育研究和大學的了解。”[3]11拉格曼在郵件中與筆者談到其寫作的目的主要是想 “彌補教育史研究的洞”(給筆者本人的郵件),因諸如 “化學、物理等學科都有自己的歷史”,所以拉格曼希望能夠從教育學科研究方面的歷史來研究教育史,使教育學本身成為一門能夠寫自己歷史的學科,而不是像是 “投錯胎的嬰兒”一樣在學科體系中游離。
最后,在教育史學方法的運用上,拉格曼運用了敘述和問題史相結合的方式。如在書中的第2章中,拉格曼圍繞 “教育研究成為一種職業”這一問題,分別從杜威、桑代克、查爾斯·賈德等人在推動教育研究方面的作用去談,同時在單個主題之內運用線性的敘述方式去描述歷史的發展過程。同時,在教育史學方法運用上拉格曼不僅注重史料的收集,而且重要的是注重對史料的解釋。她說:“在本書寫作中,我一直有意識地注重分析解釋而不是面面俱到。盡管我收集了大量的史料,這對研究這個極為龐大的學術領域的歷史十分重要,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史料并沒有羅列在本書中。”[3]6正如卡爾所說:“歷史就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持續不斷的、互相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5]15拉格曼面對紛繁復雜的史料選擇的是與部分的史料進行對話,并且對歷史抱有著 “(我)完全承認,人們對大部分的教育研究的歷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3]7的開放態度,表明了歷史其實是一個開放的領域,而不是一個僵硬體系。
從拉格曼在 《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書中背后隱藏的教育史研究和教育史學的前提和假設,可以看出教育史和教育史學的一個區別就在于分別趨近的學科不同。教育史更多的是與教育學相關的內容打交道,如教育學與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在相互對抗融合過程中的發展,拉格曼在 《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中也是從教育內部研究其發展歷程。而教育史學主要是與歷史學,特別是史觀方面打交道。拉格曼指出,教育史學研究主要還是從史學的角度去研究而不是從教育學研究方法的角度去研究。在拉格曼看來,教育史研究中現在重要的是建立教育學史,以 “增進對教育、教育研究和大學的了解。”[3]11
三、《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中拉格曼教育研究的觀點
拉格曼在書中挑選出了教育研究中應該注重的主題,以此想 “改變在歷史上曾經阻礙教育研究發展的各種狀況”[3]11,并以此推進教育史的發展。針對教育發展中性別的問題,特別是女性對于教育的作用,拉格曼在書中寫到:“隨著教育專業在19世紀末的大學建立之后,對教育研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的推動力開始出現,在這些推動中,沒有一個比教育的女性化更為重要的了。”因為在過去的歷史學著作中,婦女的作用和兒童的發展經常會被宏大的歷史敘述所隱藏,而拉格曼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興起的各種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和民權運動的環境中長大,并且這些運動極大地沖擊著保守的歷史學思想,給史學的發展打開了另外一扇門。拉格曼則注意到了在歷史發展中女性的重要作用,她指出:“教育研究歷史的核心問題就是帶著濃重的性別與專業地位色彩的各種教育競爭以及影響這些競爭的各種更為直接的社會環境因素。”[3]17但無論是在克伯萊的 《美國公共教育》中,或是在克雷明的 《美國教育》中,女性的作用都只是被描述成歷史的 “冰山一角”,在某些教育發展過程中作者還 “欲說還休”。
關于 “教育是不是一門科學”的學科性質探討方面的問題。在早期教育研究嘗試科學化的過程中,一開始是嘗試與心理學、計量學、社會學等結合,并運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式嘗試建立科學的教育學,但是這個過程是 “勉強的”。拉格曼一一分析了所謂的 “教育心理學家”——霍爾、克拉克、詹姆斯等人其實對教育研究的 “勉強”態度,表現了教育研究在 “科學”道路上的曲折。在拉格曼描述的從1890-1990年間美國民眾對教育的復雜態度來看,最重要的問題是關于教育的定義的歧義引起的。克伯萊與克雷明描述的教育史學迥異的軌跡最重要的區別就在于對教育概念的不同理解,“克伯萊與克雷明是美國史學史兩種不同的流派的代表,他們在美國教育史學的前提假設上存在諸多本質上的差異。首先是對于 ‘教育’的理解不同,進而導致了美國教育史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方法以及史料方面的一系列的差異……克伯萊,不難看出他是將 ‘教育’等同于 ‘學校教育’,而克雷明則認為教育是為傳遞、引起或獲得知識、態度、價值標準、技能或情感而作的審慎、系統和持續的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任何成果”[6]22在之后美國另一位著名的教育史家貝林看來,教育則為 “文化隔代相傳的過程”,因此3者在教育史研究中呈現不同的范式不僅僅是因為運用的史學方法不同,同時也因其各自持有自己對教育的理解。這種相對較大影響的教育史著作在某種程度上也混亂了教育學者和非教育學者對于教育的理解,也造成了教育研究自身的混亂。因此在推進教育學成為一門科學的過程中,教育的定義很重要,同時在教育史的研究過程中,各種教育應該盡力在研究的范圍內找出真正的教育研究對象是什么,這樣對于建立一門科學的教育有著巨大的裨益。
拉格曼在研究教育職業化的進程中主要是選擇了杜威、桑代克、賈德3人對教育研究的專注使得教育研究成為一門職業的作用。但是在3人轉向教育研究這種職業都有著曲折的過程,如杜威是從 “哲學”的視角轉向教育研究,桑代克是從心理學的角度轉向教育研究,這個職業化的過程也充滿著斗爭,而關鍵的問題還在于教育研究一直沒有建立良好的學術共同體,沒有形成所謂的學術范式,各個教育研究者在各自的領域內各自耕耘。所以在教育研究內部有各種各樣的研究,但是卻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教育研究也難以成為一門真正 “獨立”的學科。而教育史也因此成為了不知所從的的流浪兒,流浪在無邊無際的教育海洋中。因此拉格曼在 “教育研究的重構”關于提高教育研究的地位低下與孤立、狹隘化的問題以及管理與權力的分解的后果時指出:“可以干預中的一個場所就是大學……大學的變革可能會對整體的社會態度施加影響,有希望可以減少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反教育主義……此外仍然需要持續不斷地努力建立強大的教育專業團體。”[3]243
教育研究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競爭,體現著教育發展內部的張力問題。教育研究在走向科學化的道路上,不僅面臨著自身內部學科的定義和性質定位的問題,還面臨著非教育學科對教育研究的 “責難”。“當教育研究走向專業化的時候,教育研究被非教育研究工作者所輕視;當教育研究走向科學化的時候,教育研究被尋求教育實踐靈丹妙藥的學生所回避……在這兩種相反的力量之間來回折騰是教育學者長期面臨的兩難困境。”[3]178除此之外,教育史與史學之間的矛盾也是教育研究的一個尷尬的地位。“盡管 (在1950年到1960年間許多教育史學家試圖建立教育史的研究體系)如此,一般來說,教育并沒有一直成為歷史學家研究興趣的中心……在 ‘迎合顧客’的沉重壓力下,教育史學家們必須經常把他們的史學研究掛靠到其他更為穩定的教學和研究,尤其是教育政策的研究工作。”[3]178從拉格曼對教育研究發展的 “舉步維艱”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教育史研究在某些領域的 “缺陷”,因為不得不 “迎合”時代的發展,以體現自身的存在價值,所以教育史只好更注重教育政策方面的歷史研究,而對教育內部的課程問題甚少關注。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變成了教育史研究的發展 “阻礙”之一。
美國的教育研究在1890-1990年間確實有了很大的促進,這是拉格曼對教育研究充滿樂觀自信的來源,雖然在 《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中,拉格曼并沒有從正面指出教育史研究和教育史學研究的關系、教育研究對教育的影響等問題,并且在書中反映的主題中,拉格曼還缺少了諸如種族、家庭等社會因子對美國教育影響的主題,但是從拉格曼嘗試從一個學科史的角度來建立科學化的教育的努力以及在研究的過程中將敘述史和問題史結合的角度去挖掘關系,為教育這一門學科的成長與發展另開了一個新的角度,可讓我們對教育、教育史、教育史學的諸多問題進行思考。
[1]SolCohen.AnElusiveScience:TheTroublingHistoryofEducationResearchbyEllenCondliffeLagemann: BookView[J].TheJournalofAmericanHistory,2001(5).
[2][英]卡爾·雷蒙德·波普爾.歷史主義的貧困[M].何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3][美]埃倫·康德利夫·拉格曼.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困擾不斷的教育研究的歷史[M].花海燕,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
[4]俞吾金.歷史事實和客觀規律[J].歷史研究,2008(1).
[5][英]E·H·卡爾.歷史是什么[M].陳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6]周采.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設及其意義[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
[7]張廣智.西方史學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責任編輯:慶 來]
G40-03
A
1674-3652(2016)06-0114-04
2016-10-19
羅曉文,女,廣東佛山人。主要從事外國教育史、教育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