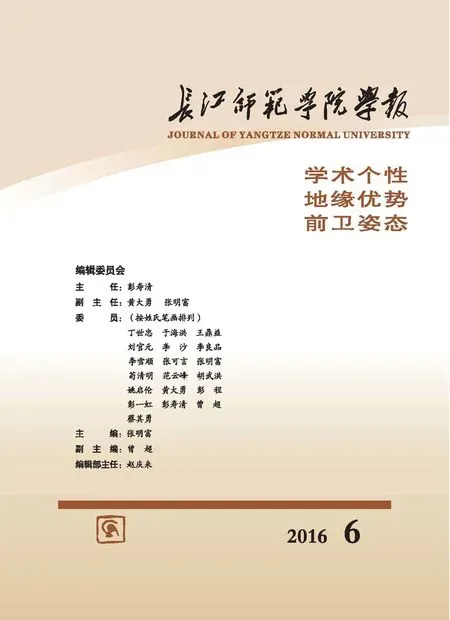論公車府職能演變及唐代詣闕上書的類型
劉林鳳
(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3-9世紀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2)
論公車府職能演變及唐代詣闕上書的類型
劉林鳳
(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3-9世紀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2)
漢代到唐建立前,公車府基本上一直存在,其職能也沒有明顯的變化。到唐代,公車府被廢除,但其職能卻并沒有退出政治舞臺,而是轉移到唐代的外朝行政機構中,繼續發揮著 “詣闕上書”的作用,是連接皇帝與生民的重要紐帶。同時,詣闕上書也是吏民實現其某種意愿、訴求的重要方式。
公車府;職能轉移;詣闕上書;吏民訴求
公車府曾經在漢魏六朝時期發揮著溝通皇帝與民眾關系的重要作用。公車府在空間位置上靠近宮城闕門,主要負責處理詣闕所上之書。公車府與闕門關系的研究并沒有脫離古代城市、宮城建筑研究等范疇。目前,研究古代城市、宮城建筑的著作很多①著作有中村圭爾、辛德勇編《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畫》,[日本]講談社,2001年;妹尾達彥主編《都市と環境の歷史學》第2集,中央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2009年。楊鴻年著《隋唐兩京考》,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辛德勇著《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王靜著《中古都城建城傳說與政治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論文集有傅熹年著《傅熹年建筑史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論文有傅熹年《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原狀的探討》,《文物》,1973年7期;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號,1996年;《唐代長安の盛り場(中)》,《史流》30,1989年;杜文玉關于大明宮功能的研究十分全面,如《唐大明宮含元殿與外朝朝會制度》《唐史論叢》(第十五輯),2012年;《唐大明宮內的幾處建筑物的方位與職能》《唐史論叢》(第十九輯),2014年等。。在唐代的典籍中已不見公車府或者公車司馬令的蹤跡,但是公車府承擔的職能卻在唐朝分散轉移到承天門以及含元殿外的外朝機構中②參見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宮闕與園林——三—六世紀中國皇帝權力的空間構成》,《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中華書局,2008年。。職是之故,這里僅對漢至唐公車司馬令的所屬及其職能演變以及唐代詣闕上書的類型作一簡單的探討。
一、漢至唐公車司馬令的所屬及其職能演變
《說文解字》云:“闕,門觀也。”[1]關于闕門出現的最早時間,據史籍推測約在西周時期。《宮室考》引 《竹書紀年》所載:“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康王二十一年,魯筑茅闕門。昭王元年,復設象魏。任啟運注:按此則魯之有兩觀,因周廢象魏而作,后周復,而魯仍之不革耳。春秋定公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冬,新作雉門及兩觀。哀公三年夏,司鐸火,季桓子至,命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任啟運注:據此則知,府庫與象魏相接,舊章在象魏之室,命徙他處而藏之。”[2]闕門即象魏,按此,至少在西周時期,闕門就已存在。闕門的作用不僅是 “觀”,在實際中往往以 “動態的制度執行”體現出來。
漢代詣闕上書主要包括鳴冤重審和民眾上書請求表彰地方官德政兩部分內容,控訴地方官的情況則比較少見③《宮闕與園林》一文亦持此看法。參見注釋②。。民眾上書場所——闕門,是政治意味極強的場所,受理上書彰顯闕門這種職能的行政機構就是公車府。要把握唐代 “詣闕上書”的走向,需要厘清漢以來公車司馬令的所屬和職能演變,故作如下的梳理。《漢書》記載,公車司馬,屬衛尉。文曰:“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3]東漢時,公車司馬令仍是衛尉屬官,但是在史書記載條式上發生了細小的變化。
《后漢書》記載:“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丞一人,比千石。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征詣公車者。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4]
這時,公車司馬令的職掌更加明確,即 “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征詣公車者。”到西晉之際,除稱謂上的簡略外,公車令與衛尉的關系也基本沒變。《晉書》載:“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冶掾。及渡江,省衛尉。”[5]但 “及渡江,省衛尉”的字眼,又說明東晉時衛尉與公車令的關系發生了變化,衛尉一度被廢置。那么衛尉被廢之后,其下屬官,如公車令有無轉移到別的部門之下,抑或自成一個機構,其演變情況又如何?
首先,衛尉被 “省”后公車令的歸宿問題。“及渡江,省衛尉。”此處的 “省”,當是 “略去”的意思。結合 “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冶掾。及渡江,省衛尉”一句來看,即是直接設武庫、公車等令。這說明東晉時公車令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而不再受衛尉統轄。此外,《宋書》中所載 “晉江左以來,直云公車令”[6]即是明證。
其次,東晉之后衛尉及公車令歸屬何在,二者是否合二為一?爬梳史籍可知,《宋書》卷39載:“衛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 (454年)復置。舊一丞,世祖增置一丞。”[7]同書卷40又云:“晉江左以來,直云公車令。”[8]兩種分開記錄的方式,恰說明東晉后,劉宋政權雖然復置衛尉,但是此時的衛尉與公車令已然互不統屬,公車令正式獨立出來。又 《南齊書》卷16記載了二者的職掌,但是二者在史書撰寫上仍然存在差異,二者之間相隔4頁。文云:“衛尉,府置丞一人,掌宮城管籥。張衡 《西京賦》曰:‘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宮城諸卻敵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改以鐵磬云[9]。公車令一人……屬起部,亦屬領軍。”[10]
據此,在 《南齊書》中衛尉和公車令分開記述再次證明了公車令已然不再隸屬于衛尉的事實。然這樣的情況維持不久,梁朝就回歸到東晉前的那套 “正統”制度。史籍記曰:“初猶依宋、齊,皆無卿名。天監七年 (508年),以太常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衛尉為衛尉卿……衛尉卿,位視侍中,掌宮門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統武庫令、公車司馬令。”[11]這就是說,梁武帝蕭衍初期,官制多依宋、齊,直至天監七年 (508年),始進行了一些制度調整,設置了諸卿,如衛尉卿,隸屬秋卿,并且衛尉卿再次統公車司馬令。
除此之外,衛尉與公車令的關系在北朝制度中也可窺見。《隋書》載:“(北齊)衛尉寺,掌禁衛甲兵。統城門寺,置校尉二人,以司其職。(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籥等事。)又領公車 (掌尚書所不理,有枉屈,經判奏聞)、武庫 (掌甲兵及吉兇儀仗)。衛士 (掌京城及諸門士兵。)等署令。”[12]
北齊時,衛尉為 “九寺”之一,即衛尉寺,仍領公車。公車掌管尚書所不涉及的事務,如有枉屈,經公車判斷奏聞。又因隋襲北周制度,故依隋制可大略推知北周的情形。《隋書》記載:“衛尉寺統公車、武庫、守宮等署。各置令 (公車一人,武庫、守宮各二人)、丞 (公車一人,武庫二人)。”[13]可見,北周同隋差異不大,衛尉仍為 “九寺”之一,統公車署。
綜上,漢魏、南北朝時期,衛尉與公車令基本上一直存在所屬關系。但是遍查唐代制度典籍,只見衛尉的相關記載,且與前朝記載無異,卻再不見公車令的記載。如 《唐六典》載:“衛尉寺:卿一人,從三品……衛尉卿之職,掌邦國器械、文物之政令,總武庫、武器、守宮三署之官屬;少卿為之貳……凡大祭祀、大朝會,則供其羽儀、節鉞、金鼓、帷弈、茵席之屬。”[14]
由此可知,唐代已廢止公車令。但是唐之前各朝的公車令承擔了重要的職能,這些職能可以確定不會消失,應是發生了轉移。那么,唐朝詣闕上書是否會因為公車府的廢除而有所變化?答案是肯定的,唐時詣闕場所已不同于漢魏六朝集中在內朝,而是轉移到了外朝。這可以通過對比漢魏時期闕門的附近裝置以及闕門的職能就可得出結論。史籍記載有 “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自注:蓋古之外朝也。”[15]此其一也。其二,對于具有闕門功能的承天門和大明宮含元殿的佐證還可以根據一套裝置來判斷。在唐之前,金雞、登聞鼓、肺石、謗木等裝置就設在闕門兩旁。《唐六典》載:“北齊赦日,皆武庫令,設金雞及鼓于闕門右,撾鼓千聲,宣赦,釋囚徒。隋因之。”[16]
《梁書》記載:“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可于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17]
《唐六典》也載:“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南面五門:正南曰丹鳳門,東曰望仙門,次曰延政門;西曰建福門,次曰興安門。丹鳳門內正殿曰含元殿。夾殿兩閣,左曰翔鸞閣,右曰棲鳳閣。本注:閣下即朝堂,肺石、登聞鼓,如承天之制。”[18]故承天門以及含元殿外東西朝堂與漢魏六朝時期的闕門功能類似①傅熹年《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原狀的探討》中認為含元殿與太極宮外的承天門類似,屬于外朝的性質,而含元殿兩邊的棲鳳閣和翔鸞閣近似于前代各朝的闕。。至于東都洛陽的情形與長安基本相同,暫不作詳論。
綜上,漢魏六朝時期具有詣闕上書功能的闕門位置在唐朝發生了轉移,且轉移到了唐代宮城的外朝機構中。吏民詣闕上書在唐朝初期多數在承天門外的朝堂進行,然隨著形勢的變化,詣闕上書的場所也發生了變化,或朝堂,或匭院,或閤門,但是這幾處場所是共存的,并不存在相互取代的情況,故唐后期詣闕場所更加多樣化。
二、詣闕上書的類型
詣闕上書有時也稱為直訴②“直訴”一詞作為法律用語在宋代的典籍中多見。但是直訴包含的內容至少在西周就已存在,如路鼓、肺石。可參見《周禮·夏官》《周禮·秋官》。《唐律疏議箋解》“越訴”條劉俊文箋釋說,按唐制,對于案情重大及冤抑莫伸者,皆得直接向皇帝投訴,稱為直訴。直訴的方式有3種:其一為邀駕;其二為撾鼓;其三為上表。日本學者松本保宣《從朝堂至宮門——唐代直訴方式之變遷》中認為“直訴制度“應當還包含密告、諫言、上書自薦、獻策、投匭制度等。”(參見鄧小南、曹家齊、平田茂樹主編《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但這里仍以詣闕上書討論。唐代的詣闕上書大致可分為群臣詣闕上表③群臣詣闕上表本質是一種禮儀性的行為,關于群臣詣闕上表的詳細描述,參見《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第3347-3348頁。、以個人名義的官員上書和普通百姓上書3類。前兩者的上書由于身份、條件的特殊,其上書較之于普通百姓而言,顯得尤為便捷。詣闕上書就具體內容而言,又分為詣闕鳴冤、詣闕陳事兩大類。這兩類 “上書”,前者往往走典制中規定的法定程序;“詣闕陳事”則另有不同。為更好地說明問題,這里將唐代詣闕上書根據內容和性質的不同而分作5類。
(一)群臣詣闕上表
《通典》“群臣詣闕上表”條詳細地描述了上表禮儀及流程,這里不嫌冗繁具列如茲:“前一日,守宮設文武群官次于朝堂如常儀。其日,量時刻,文武群官集,俱就位,各服朝服。奉禮設群官位于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中書令位于群官之北,南向。設奉禮位于群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帥贊者先就位。謁者引群官各就位。禮部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表案立于奉禮之北,西面。立定,典謁引中書令出就南面位。禮部郎中引表案詣中書令前,郎中取表以授,中書令受表,郎中、舉案退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乘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中書令以表入奏,出復位,南面稱 ‘有詔’,群官再拜。宣詔訖,又再拜。謁者引為首一人進,北面受表,退復位。舍人引中書令入,謁者引群官還次。”[19]
群臣詣闕上表所在場所是東朝堂,雖不知所上之表為何人所作,但上表發出機構是禮部,且由禮部郎中引表至中書令前受表,再由通事舍人引中書令遞表入奏。
(二)詣闕鳴冤
詣闕鳴冤是詣闕上書的一類,它適用于任何身份的吏民。唐宣宗時有一著名案例。據史籍記載,“九月,前永寧縣尉吳汝納詣闕稱冤,言:‘弟湘會昌四年 (844年)任揚州江都縣尉,被節度使李紳誣奏湘贓罪,宰相李德裕曲情附紳,斷臣弟湘致死。’詔下御史臺鞫按。”[20]簡短的記述并不能看清詣闕鳴冤的過程,只知道吳汝納身份是前永寧縣尉。但在同書 《李紳傳》中則稍有詳述:“及德裕罷相,群怨方構,湘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寃,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21]從中看出,坐贓而死的吳 (汝)湘兄吳汝納詣闕時的身份是進士,至于前者為何說是前永寧縣尉,許是二者存在被削官的過程也為未可知。
不明詣闕過程情況的類似例子還有很多,如 《舊唐書·孟簡傳》記載:“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七千余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22]除詣闕過程不明外,吳湘案與孟簡案的共同點最終都是御史臺按驗處理。
雖然,史書紀傳未錄具體的詣闕鳴冤過程,但唐代律令卻有明文的規定。鳴冤需要按照規定的法定程序進行,層層遞進,在法律原則上不容許越級訴訟。《唐六典》規定:“凡有冤滯不申欲訴理者,先由本司、本貫;或路遠而躓礙者,隨近官司斷決之。既不伏,當請給不理狀,至尚書省,左、右丞為申詳之。又不伏,復給不理狀,經三司陳訴。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達,聽撾登聞鼓。若惸、獨、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本注:若身在禁系者,親、識代立焉。立于石者,左監門衛奏聞。撾于鼓者,右監門衛奏聞。)”[23]
由上可知,詣闕鳴冤即 “上表”這一程序。按前面兩案。吳 (汝)湘兄與陸翰子弟詣闕鳴冤不論是否歷經前面幾項程序,但詣闕鳴冤實質上等同于上表。但遇特殊情況時也有例外,如穆贊案,“時陜州觀察使盧岳妻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于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佋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佋善,參、佋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撾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為郴州刺史。”[24]
穆贊被誣下獄,其弟穆賞在情況緊急之際,奔走詣闕。但不同的是穆賞并沒有采用上表訴冤的形式,而是通過撾登聞鼓鳴冤。按照常規這應屬于越級,但是從史書記載看,并沒有看到后續的因為越訴被懲罰之事。法律上的僭越行為似乎有時也會考慮人情因素。
關于 “三司陳訴”中的 “三司”,其一是 “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25]其二是 “自永徽 (650-655年)以后,武氏已得志,而刑濫矣。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26]事實上,三司有 “三司受事”和 “三司推事”的分別。“三司受事”即御史臺侍御史在朝堂與門下省給事中、中書省中書舍人共同接受免訟案件,稱為三司受事①三司是一個上訴機構。參見劉后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第121頁。。如屬重大案件,則皇帝詔令尚書省之刑部與御史臺、大理寺共同審理,則稱為 “三司推事”。前面 《唐六典》中提到的 “三司陳訴”指的就是 “三司受事”。儀鳳二年 (677年)十一月十三日申理冤屈制文稱:“見在京訴訟人,宜令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崔謐、朝散大夫守給事中劉景先、朝請郎守中書舍人裴敬彝等于南衙門下外省,共理冤屈。所有訴訟,隨狀為其勘當。有理者速即奏聞,無理者示語發遣。”[27]
再有 《唐律疏議箋解》“越訴”條載:“問曰:有人于殿庭訴事,或實或虛,合科何罪?答曰:依令:‘尚書省訴不得理者,聽上表。’受表恒有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三司監受。若不于此三司上表,而因公事得入殿庭而訴,是名 ‘越訴’。”[28]
對 “三司陳訴”后,仍不伏的,則可以上表給天子;如若不達天子則可通過敲擊登聞鼓或者立于肺石下而作最后的努力。天子收到上表后,往往會交給相關的機構處理,這就是 “三司推事”階段。如上文吳湘案最后 “詔下御史臺鞫按”處理。
隨著GPS、北斗等衛星定位技術精度的不斷提升和移動智能終端的大范圍推廣,大眾對于高精度位置服務的需求呈現了爆發式的增長趨勢[1-3]。配電網絡主要特點就是點多面廣、結構比較復雜,配網密如蜘蛛網,設備絕對數量多,基礎資料缺乏,站、線、變、戶關系復雜,管理難度大,運行中的協調配合要求高,新加入的員工對于電網的線路走向、設備位置不熟悉等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日益凸顯。如何將高精度的位置定位技術應用于電力設施巡檢工作,滿足電力設施的高精度定位、快速查看需求,為精細化管控巡檢過程提供可能性,是目前配電信息化建設的重要工作。
(三)詣闕獻策、諫諍
面對國家存在的一些問題,不乏有識之士積極建言獻策。《文苑英華》卷464申冤制條中說:“其官人百姓等有冤滯未申,或獄訟失職,或賢才不舉,或獻納謀猷,如此之流任其投匭”[29],即體現了統治者的訴求。《舊唐書》記載有一則獻策史料,即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泝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矣。’……以磻石為鹽鐵巡官……于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30]
陳磻石這一建議為當時政府既節省了財政開支,又解決了當時的漕運問題,受到了統治者的重用。其提出的辦法對于后世的漕運也影響極大。另也不乏有才之人,因對統治者的行為或者決策有不同的看法而諫言批評。《舊唐書》卷25《禮儀志》中記載有河南府人孫平子詣闕上言:“中宗孝和皇帝既承大統,不合遷于別廟……玄宗令宰相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太常博士蘇獻等固執前議……時雖貶平子,議者深以其言為是。”[31]
《舊唐書》卷187上 《忠義列傳》中亦有類似的記載。“俞文俊者,荊州江陵人。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并,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至矣!’則天大怒,流于嶺外。后為六道使所殺。”[32]
《舊唐書》卷190中 《文苑中》記載:“陳子昂,梓州射洪人……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33]
這些敢于批評時政的有識之士,雖然或被貶而身死異鄉,或入仕成為棟梁,但是正因如此,他們最終得以名留史冊,光照千古。
(四)密告、揭發
這則史料再現了案發后于頔試圖挽回局面的努力。已是罪身的于頔意圖從建福門進入,遭到建福門司拒絕后,不得已 “退至街南,負墻而立”,其落魄之狀足可想象;不甘心的于頔等隨之又遣人進表,不料又遭到閤門使以 “無引不受”為理由的拒絕,只好 “日沒方歸,明日又待罪于建福門。”在古代奴仆、家僮告發主人是很嚴重的事,要承擔風險,也正因如此,這種告發性質才會顯得尤為嚴重。而于敏家奴王再榮是通過詣銀臺門告發主人的。與之不同的是揭露行為,如 《舊唐書》卷13《德宗本紀下》則記載有崔善真揭發官吏腐敗行為的事,文曰:“浙西人崔善真詣闕上書,論浙西觀察使李锜罪狀。上覽奏不悅,令械善真送于李锜……由是锜恣橫叛。”[36]
誠如上言,崔善真列舉了浙西觀察使李锜罪行,其目的是使皇帝引起重視以便制裁李锜。然這個案例更像是一種監督行為下的揭發。兩相比較明顯密告更為特殊。此外,另一個不同是崔善真是采取 “詣闕上書”的做法,而王再榮作為奴仆,也不可能上書、上表,只能是用行動去告發。
(五)詣闕自舉
詣闕自舉即通過詣闕的途徑達成 “自薦”目的,但是這種 “自舉”是否旨在獲官則很難裁定。《舊唐書》載:“儀鳳 (676-679年)中,(裴懷古)詣闕上書,授下邽主簿。”[37]《新唐書》卷197《循吏傳》載:“寶應 (762-763年)初,(羅珦)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太祝。”[38]從上列 “詣闕上書”的情形可推測,詣闕上書似已成為一種入仕作官的途徑。《舊唐書》卷8《玄宗本紀上》記載:“十五年春正月戊寅,制草澤有文武高才,令詣闕自舉。”[39]對于裴懷古和羅珦 “詣闕上書”的動機是否旨在獲官,不得而知。但是有才能的知識分子針對某件事向天子提出自己的建議,從而獲得賞識,獲得一定的官位,毋庸置疑。再者,從玄宗的制文看,“詣闕上書”已然成為一條未有成文規定的入仕途徑。
(六)其他
史籍中還記載有百姓為對有善政的良吏進行褒揚,乃通過 “詣闕上書”的請求為之立德政碑。如哀帝年間,福建百姓、僧道通過詣闕,請求為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40];宣宗時汝州郡人為令狐緒請立德政碑[41]等。其實,詣闕上書在漢時主要的內容就是民眾上書表彰有善政的地方官,而很少涉及揭露地方官罪行的上書①我們認為至晚在唐代,“民眾上書表彰善政的地方官員”由最初的屬于“詣闕上書”的主要內容之一漸變為“詣闕上書”的末枝,由上書表彰善政變為揭露地方官罪行,這種變化一方面反映了統治者統治力的增強或者說是民眾對從皇帝到中央再到地方的一種嚴密統治力的監督,這似乎也反映了唐代統治者們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統治法則的踐行。。
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垂拱二年 (686年)武則天置 “四色匭”②《唐六典》卷9“匭使院”條下注為垂拱元年(685年)置,中華書局,1992年,第282頁。,直到唐末投匭制度都一直沿用,但是詣闕上書的各種途徑并沒有被取而代之,而是各取所需的并存。
三、結語
詣闕上書作為一種制度,歷經漢唐近千年的發展而逐漸完備。從統治者出于權力的彰顯和證明王權正統性角度講,天子與百姓的溝通是天人合一的治國理念的體現,是天子與百姓關聯的重要紐帶。天子不斷加強與百姓的溝通,如四色匭的設置與不斷完善,既是為鞏固其地位作出努力,也反映了天子的焦慮心理,這種心理或是對前朝經驗教訓的吸取,或是當時統治形勢的不穩所導致的。但反過來講,詣闕上書也是吏民實現自己某種意愿、訴求的重要方式。
[1][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88.
[2][清]任啟運.宮室考[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東漢]班固.百官公卿表[M]//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728.
[4][南朝·宋]范曄.百官二[M]//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3579.
[5][唐]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736.
[6][7][8][南朝·梁]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7:1243、1230、1243.
[9][10][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317、322.
[11][12][13][唐]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724-725、756、776.
[14][15][16][18][22][唐]李林甫,等;陳仲夫,點校.唐六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2:459、217、464、218、192.
[17][唐]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37.
[19][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3347-3348.
[20][21][22][24][30][31][32][33][35][36][37][39][40][41][后晉]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618、4500、4258、4116、652-653、952-953、4883、5018-5021、4131、394-395、4807、1908、808、639.
[25][26][38][宋]宋祁.歐陽修,等.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1235、1414、5625.
[27][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47.
[28][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93:1675.
[29][宋]李昉,等.文苑英華[M].北京:中華書局,1966:2371.
[34][宋]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6418.
[責任編輯:丹 涪]
K242
A
1674-3652(2016)06-0045-06
2016-08-23
劉林鳳,女,山西朔州人。主要從事隋唐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