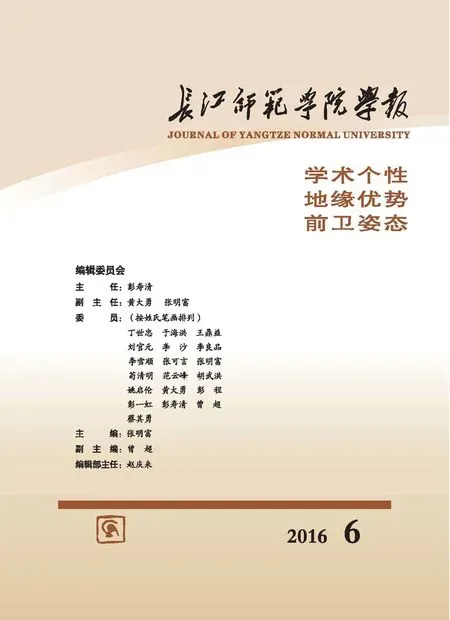論 “古苗疆走廊”中的族群語言構成特點
吳正彪,郭 俊
(三峽大學 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心/民族學院,湖北 宜昌 443002)
論 “古苗疆走廊”中的族群語言構成特點
吳正彪,郭 俊
(三峽大學 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心/民族學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古苗疆走廊”是一個形成于元明清時期由當時的湖廣、四川、云南、廣西 “包裹”下為打通古驛道而在內陸地區建立貴州行政區域的多族群地區。這條古驛道自古以來就生活著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瑤族、毛南族等10多個世居少數民族。這些民族語言的構成由于族際互動的影響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這里僅就這條古驛道中的多民族語言分布及變化特點從歷史語言學的視角進行相應的分析和探討。
“古苗疆走廊”;語用 “文化圈”;族群語言構成特點
“古苗疆走廊”這個概念是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界楊志強、趙旭東和曹端波等著名學者近年提出來的學術術語。“所謂的 ‘古苗疆走廊’,指的是元明時期以后新開辟的、連接西南邊陲云南與湖廣之間交往的一條驛道及其周邊呈帶狀相連的地域。”[1]這個 “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與當今學術界在談論的 “南嶺走廊”“藏彝走廊”“武陵民族走廊”“河西走廊”等,既有許多的共性,同時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性。用龍曄生的話講,這是 “從一開始就是國家先軍事后政治再文化等外力介入下,以驛道為中心,將平原、丘陵、山地、高原、臺地等不同的地貌相勾連,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樣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線保留了大量的歷史積淀的呈帶狀相連的區域。”[2]楊志強等學者強調:“在國家權力和漢族大舉進入貴州省前,這片分屬湖廣、四川、云南、廣西四省包夾下 ‘腹地邊疆’分布著眾多的藏緬語族、苗瑤語族、壯侗語族的民族及族群。族群之間在文化上既保持著自身多樣性特點的同時,又在相互交流互動過程中形成了諸多的 ‘跨族群’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 ‘共性’。”[3]在此,我們以此區域性的 “文化走廊”為線索,結合實地田野調查資料,就“古苗疆走廊”中族群語言的構成特點談談我們的認識和理解。
一、族群語言:“古苗疆走廊”的語用 “文化圈”概述
“古苗疆走廊”是一個以漢藏語系中的漢語語族、壯侗語族、彝緬語族、苗瑤語族4大語族語言族群為主體構成的內陸語用 “文化圈”。語言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識別中探尋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礎。為此,在中國的民族政策中對于 “民族”這一概念的界定,通常采用的是斯大林于1913年提出來的科學定義,即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4]然而在這里我們談 “古苗疆走廊”語言的時候卻用的是族群語言而為何不用民族語言呢?這還得從元明時期以來形成的這條古驛道中由于族際互動后一個民族往往會因為各種歷史原因或區域語言分隔日久導致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語的出現,盡管這些民族方言、土語本身就存在著明顯的親屬語關系,我們在這里只能用 “族群”這樣的概念才能說明 “古苗疆走廊”中長期積淀起來的這種文化現象。
“族群”作為 “在較大的文化和社會體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質以及體質特征的一種群體,其中最顯著的特質就是這一群體的宗教、語言、其成員所具有的對共同起源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群體身份感;它的自然基礎在于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所具有的社會生物屬性”[5],族群的這些文化特質本身就具有 “親族性”“邊界性”“多層次性”“原發情感性和工具性”等特點。因此,一個民族內部可能會由若干個族群所組成,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可能有一個族群就是一個民族的現象。近年來,學術界對 “民族”與 “族群”的概念已經有了明確的界定。
從各個民族的語言使用現狀看,在現代國家界定的這些民族身份中,其語用 “文化圈”具有較復雜的多層次性,在 “古苗疆走廊”區域內,無論是當地的漢族移民還是各個世居的少數民族群體,在語言的使用上都呈現出一種類似于 “族群”結構的文化特點。
(一)漢語族群的語用 “文化圈”
從中國民族學與人類學學者們提出的 “古苗疆走廊”范圍看,主要是以湖南辰州、沅陵到貴州的武陵山、云霧山、烏蒙山等云貴高原臺地一帶以及貫通貴州東部、中部、西部和北部的沅水、清水江、烏江、金沙江屬于長江水系的江水流域。無論是從湖南進入的東線,還是從都柳江和紅水河屬珠江水系經都勻到貴州腹地的南線以及由遵義入川的北線,幾條分干線在貴州中部以貴陽、安順為中心匯合后形成一條由東南與西北為主干線建立起來的長條形衛所 “群”,連接云南的曲靖,直通昆明。這些衛所的設立,不僅開通了湖廣進入云南途經貴州的主要交通線,而且也為明代貴州行省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經濟供給基礎。在這條線上的漢語 “文化圈”主要由這樣的 “語言板塊”所組成:其一 “瓦鄉話”語用族群區;其二 “吉首—銅仁”的黔東北漢語族群區;其三、湘黔邊的 “酸湯話”漢語族群區;其四、黔東南漢語方言群語用 “文化區”;其五、貴州都勻漢語地方話語用文化族群區;其六、屯堡漢語文化族群區;其七、黔中北漢語地方化族群區。
(二)壯侗語族語用 “文化圈”
壯侗語族在語言學上也稱為 “侗臺語族”,從語言使用的 “文化圈”看,它包括 “說壯侗語族的有壯族、布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黎族及仡佬族等9個民族,另有說臨高話、村話、拉珈語、佯獚話、莫話等其他幾個民族群體語言,人口約2500萬人 (1990),主要分布在華南、西南地區的廣西、廣東、海南、湖南、貴州、云南、四川七個省市自治區。”[6]在 “古苗疆走廊”范圍內,主要涉及到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仡佬族和仫佬族。因此,壯侗語族在 “古苗疆走廊”的語用 “文化圈”可劃分成這樣的民族語言使用 “板塊”:其一、布依族語言有3個 “語言板塊”,也就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過對布依語的調查后所劃定的3個土語區,即 “望謨、冊亨、羅甸、獨山、荔波、都勻、平塘、貞豐、安龍、興仁、興義等縣及惠水的一部分屬第一土語區;貴陽、龍里、貴定、清鎮、平壩、開陽、安順等縣及惠水的大部分屬第二土語區;鎮寧、關嶺、紫云、晴隆、普安、六枝、盤縣、水城、畢節、威寧等縣屬于第三土語區。”[7]其二、侗族語言有兩個 “語言板塊”,即以詞匯的異同和語法共性特征為參考的南部方言 “文化圈”與北部方言 “文化圈”,其中南部方言內有4個土語區:榕江 (章魯)、黎平 (洪州)和錦屏這一范圍內所使用的侗族語言為第一土語區;黎平 (水口)、從江 (貫洞)、榕江 (平江)等范圍內所使用的語言為第二土語區;鎮遠(報京)等地屬于第三土語區;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的聘洞所在地為第四土語區。北部方言有3個土語區:以天柱 (石洞)、三穗 (款場)、劍河 (小廣)為范圍所組成的第一土語區;以天柱 (注溪)為代表的第二土語區;以錦屏 (大同)為代表的第三土語區[8]。各個土語區之間主要存在語音上的細微差別,在以語言為標志的 “文化圈”上主要還是在兩個方言中顯示出各自的特點。其三、水族語言有3個 “語言板塊”,就是語言學上所界定的3個講水語的土語區。第一個 “語言版塊”即是以貴州都勻市陽和水族鄉潘洞村為中心的“睢米”[sui3mi6]語言 “文化圈”,在民族語言學中稱為水語的 “潘洞土語區”,其語言使用范圍包括都勻市的奉合水族鄉、基場水族鄉以及獨山縣的翁臺水族鄉和甲定水族鄉;第二個 “語言版塊”是以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三洞鄉為中心的 “睢柳”[sui3liu3]語言 “文化圈”,在民族語言學中稱為水語的 “三洞土語區”,其語言使用范圍包括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境內的三洞、水龍、廷牌、塘州、中和、壩街、九阡等鄉鎮中說水族語言的村寨,獨山縣的塘立、羊場、水巖等水族村寨,荔波縣永康水族鄉、水瑤水族鄉和水利水族鄉等地水族村寨,榕江縣新華水族鄉和從江縣的部分水族村寨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南丹縣六寨鎮龍馬莊等水族村寨;第三個 “語言版塊”是以貴州三都水族自治縣廷牌鎮陽安村和陽樂等村寨為中心的 “睢干”[sui3kam1]語言“文化圈”,其語言使用范圍除廷牌鎮陽安村和陽樂等村寨外,還有鄰近的獨山縣溫泉、懂渺一帶說水語的文化群體[9]。其四、仡佬族在 “古苗疆走廊”中的分布范圍比較廣,在仡佬語的方言劃分中就有黔中方言、黔中北方言、黔西南方言、黔西方言4個大方言,每個方言內部又有若干種土語。如黔中方言有平壩縣大狗場土語、普定新寨土語、織金縣熊寨土語3個土語;黔中北方言有以貴州仁懷縣茅壩鎮亞塘、關嶺自治縣的麻凹和晴隆縣的涼水以及廣西隆林自治縣的三沖等地的仡佬語屬于第一土語區,貴州仁懷縣茅壩鎮板栗彎和遵義市平正鄉的一些仡佬族村寨所使用的母語為第二土語區;黔西南方言有六枝牛坡土語、隆林摩基土語、麻栗坡縣老寨土語、水城打鐵寨土語和遵義尖山土語等5個土語;黔西方言有大方縣普底土語和鎮寧縣比貢土語兩個土語[10]。也就是說,仡佬族語言由于分布面廣、語音差別大,因而每個土語都會自成體系地構成為相應的語用 “文化圈”。其五、毛南族語言在 “古苗疆走廊”的語用 “文化圈”使用范圍僅僅只是貴州省平塘縣的卡蒲毛南族鄉、者密鎮和大塘鎮的羊方村及其鄰近的獨山縣羊鳳鄉壩浪寨和惠水縣高鎮鎮的姚新、交椅、滿告等村,這個自稱為 “哎嬈”[ai11ra:u11]的民族文化共同體,與廣西毛南族無論在語言還是文化傳統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并有其獨特的文化體系。其六、貴州的仫佬族與廣西的仫佬族不同,廣西的仫佬族在語言劃定上屬于壯侗語族的民族,而在貴州則屬于苗瑤語族中使用苗語支語言的民族。仫佬族在貴州的古代歷史文獻典籍中稱為 “木佬”,這支自稱為 “嘎沃”[qa24γo53]且保留有自己母語的文化群體主要分布在凱里、麻江、黃平、都勻、甕安、福泉等縣市。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過貴州有關部門的民族識別調查和 “名從主人”的自愿申報原則,將貴州的木佬人認定為仫佬族,雖然民族名稱與廣西的仫佬族名稱相同,但在語言上卻有著很大的差別,“表現在語音上,廣西仫佬語有p、t、k三個塞音韻尾,而貴州仫佬族則沒有,廣西仫佬語的韻母有90多個,貴州仫佬語只有22個。廣西仫佬語聲調有彎曲調,貴州仫佬語沒有這種現象。從詞匯上看,同源詞、相同相近的詞比較少,不同的詞比較多。”結合貴州仫佬族語言在聲母、韻母和聲調中的使用特點,貴州仫佬族使用的語言 “屬于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分為凱里、麻江兩個方言。”其中仫佬語凱里方言 “以凱里市重擺寨仫佬話的語音為代表點”,仫佬語麻江方言則 “以麻江縣龍里寨仫佬族的語言為代表”[11]。實際上,這兩個方言的語言點就是一個相互獨立的語用 “文化圈”。
(三)苗瑤語族語用 “文化圈”
在漢藏語系語言中,苗瑤語族主要是指苗族、瑤族和畬族。作為 “古苗疆走廊”中的語言文化族群,其語用 “文化圈”的使用范圍主要有這樣一些 “語言板塊”。其一、苗族語言中的方言、次方言及土語使用的文化 “板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語言學專家李云兵在實地調查和分析后將苗語劃分成湘西方言、黔東方言和川黔滇方言3大方言,并在川黔滇方言中劃分出川黔滇次方言、滇東北次方言、貴陽次方言、惠水次方言、麻山次方言、羅泊河次方言、重安江次方言、平塘次方言8個次方言,3大方言及其8個次方言中共有28個土語和3個沒有土語的次方言。事實上,李云兵的這些劃分僅僅只是較為準確地對川黔滇方言內部8個次方言及其土語進行了科學的界定[12]。在 “古苗疆走廊”的區域范圍內,湘西方言的土語數量遠遠超過了李云兵所劃分的 “東部土語”和 “西部土語”的劃分,對此楊再彪對湘西方言苗語調查研究的結論是該方言應當劃分為兩個次方言及其所屬的6個土語,其中以湖南花垣縣吉衛苗話為代表的第一土語區、以湖南吉首市陽孟鄉為代表的第二土語區和以湖南保靖縣為中心的第三土語區應當歸入西部次方言;以湖南瀘溪縣小章苗話為代表的第四土語區、以湖南吉首市丹青苗話為代表的第五土語區和以湖南龍山縣蹬上苗話為代表的第六土語區應當歸入東部次方言[13]。此外,對黔東方言苗語的土語劃分,我們認為至少有7個以上的土語劃分,即以貴州錦屏縣偶里鄉苗話為代表的東部土語、以凱里市三棵樹鎮養蒿寨苗話為代表的北部土語、以劍河縣觀么鄉高雍寨苗話為代表的東北部土語、以都勻市洛邦鎮河口村苗話為代表的西部土語、以三都縣普安鎮甲攬村苗話為代表的南部土語、以荔波縣佳榮鎮大土村苗話為代表的東南第一土語、以從江縣丙妹鎮岜沙村苗話為代表的東南第二土語[14]。此外,在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桿洞鄉內部,有一部分村寨的苗族使用的是東南第二土語,其余的則還可以劃分成一種新的土語。在苗語方言、次方言和土語所構成的 “語言板塊”及其語用 “文化圈”中,每一種服飾類型實際上就是一個具有共同語言特點的語用 “文化圈”。其二、瑤族語言在“古苗疆走廊”中的使用情況。楊志強等人在提出 “古苗疆走廊”這個概念時,認為這個古驛道主要是從湖南沿清水江途經貴州腹地通往云南的一段重要交通線。因此,盡管瑤族在語言使用上比較復雜,但在此 “走廊”古道上的分布依然只有屬于苗瑤語族苗語支中的布努語和瑤語支中的勉語,其中勉語支主要在湖南的江華、藍山、江永、零陵、道縣以及貴州的從江、榕江、三都等縣市,這支瑤族所使用的語言屬于勉—金方言中的優勉土語;屬于苗語支的布努語有布努方言、包瑙方言和努茂方言3個方言,布努方言雖然有3個土語,但主要分布在南嶺走廊一帶,而 “古苗疆走廊”上的瑤族主要是居住在貴州荔波縣境內的包瑙方言和努茂方言,包瑙方言沒有土語,努茂方言內還有努茂土語和冬孟土語的不同劃分[15]。這些方言和土語中的瑤族,分別形成了不同 “語言板塊”內的語用 “文化圈”。
(三)藏緬語族語用 “文化圈”
藏緬語族在漢藏語系中是民族種類較多的語族,從我國現已界定的民族成份中就包括有藏族、彝族、羌族、土家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白族、阿昌族、普米族、納西族等10多個少數民族,這些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四川、西藏等省區,這一語族在 “古苗疆走廊”的語言使用對象中主要是彝族和土家族。其一、彝族語言的使用情況。彝語有6個方言:東部方言、南部方言、東南部方言、西部方言、北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在貴州的彝語主要是屬于東部方言中的黔西北次方言和盤縣次方言。在貴州的這兩個彝語次方言內部還有土語的劃分,其中黔西北次方言有水西土語、烏撒土語和芒部土語3個土語;盤縣次方言有盤南土語和盤北土語兩個土語[16]。也就是說,這些次方言和土語分別形成了彝族在 “古苗疆走廊”語言使用上的 “文化圈”。其二、土家族語言的使用情況。土家語有兩大方言,即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據楊再彪介紹,“北部方言的通行范圍是湖南省龍山縣、永順縣、古丈縣和湖北省來鳳縣還在使用的土家語。南部方言通行的范圍是今湖南省瀘溪縣潭溪鎮還在使用的土家語。現北部方言使用人口約6.1萬余人,南部方言使用人口約0.35萬余人。”[17]兩個方言在 “古苗疆走廊”中形成了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語用 “文化圈”。
二、族際互動與語言接觸:古驛道上的 “跨族性”語言共享
“族際互動”作為民族學的一個基本概念,自然是對兩個民族或者族群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而言的,是“一種建立在相關文化調適基礎之上的作用與反饋交叉出現的連續耦合運作過程。”[18]既然是 “互動”,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必然會出現相互接觸而導致兼用、借用、轉用等現象。在 “古苗疆走廊”這條重要驛道上,這種 “跨族性”語言共享現象隨處可見。如貴州天柱縣遠口、白市與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及會同縣一帶的苗族、侗族、漢族共同使用的漢語方言 “酸湯話”;在湖南懷化市所轄的沅陵、辰溪、淑浦3縣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轄的滬溪、古丈2縣等地一帶被稱作為 “果熊甕”的 “瓦鄉話”漢語方言文化群體,其語言在當地的苗族、漢族、土家族、侗族等民族中同樣是一種 “跨族性”的語言共享。
由于族際互動而導致語言接觸,進而導致在 “跨族性”語言共享中出現了語言轉用、語言借用、語言混用、語言聯盟或雙語兼用等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內的各種語言學教材和研究成果中,有關 “語言接觸”的定義有10多種,既有相同之說,亦有各說其是的學術主張。張興權在 《接觸語言學》一書中說:“語言接觸指使用兩種或多種不同語言或變體的個人或群體,在直接或間接接觸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語言使用現象及其結果所產生的各種變化情況。”[19]如居住在湖南、貴州交界一代 “說侗語、唱漢語歌”的苗族(周邊的民族將這一支系的苗族稱為 “草苗”);19世紀中后期由現三都水族自治縣遷居今丹寨縣后改用苗語進行交流的水族,等等,都是這種族際之間語言接觸與交流所導致的結果。
三、“古苗疆走廊”多族群互動對民間口傳母語歌謠文化的影響
母語歌謠是少數民族口傳歌謠中用本民族母語表述其民間詩律的語言藝術。在 “古苗疆走廊”的許多少數民族中,由于受漢語歌謠韻律的影響,民間歌謠的母語詩歌除繼續保留有本民族的押韻或押調形式外,一些地方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等,也開始出現有用漢語韻律形式和母語唱詞相結合的狀況,體現出多族群互動中不同民族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特點。如在貴州三都、都勻一帶有這樣一首漢語、苗語、水語夾雜的民歌:太陽出來紅彤彤,(漢語)/你不懂我的話我不懂你的語言,/你不聽來我不知 (苗族語言)/我約你出來想見上一面,/我叫你來你沒來 (水族語言)/哄我坡頭曬涼風。(漢語)
顯然,這是一首借用漢語民間歌謠韻律的結構形式編唱的多語情歌。類似的民歌如借用漢語歌謠韻律結構,但歌詞則用苗語、布依族或侗族語言來進行表述的現象在民間隨處可見。又如在湘西地區清代方志中所保存的大量苗族 《竹枝詞》里面,同樣也是以漢語韻律結構的 “漢夾苗”詩詞,如:“大郎 (落雨)沛然遍地儒 (好),農人共話備蓑 (蓑衣)孤 (斗笠)。板邏 (赤腳)嘔切 (兩只)牛三兩,總向陌頭輸 (犁)臘烏。”[20]
在“古苗疆走廊”的許多民族中,民間歌謠韻律通常會呈現出既保留其原語韻律結構,同時也兼用漢語韻律結構的現象,這種民族民間歌謠的表述方式,也正說明了多族群互動對民間口傳母語歌謠文化的影響過程。
四、語言與文化認同:從 “古苗疆”到當下貴州的多民族身份認定
20世紀50年代以來,民族身份的認定一直作為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予以實施。對于民族身份的認定,一般都是按照兩個依據來進行的。其一是根據斯大林關于 “民族”的定義來進行民族識別。不過,這一識別依據在后來的民族學研究中引起了一定的爭議。其二是根據民族認同或心理認同的自我身份選擇實行 “名從主人”的原則以開展民族身份認定。這些民族身份認定的結果,導致了在語言與族屬關系中有著這樣3種關系。第一種是 “一對一”的對應關系,即一族一語的對應;第二種是 “一對多”的對應關系,即一族多語的對應;第三種是 “多對一”的對應關系,即多族一語的對應。處于 “一族多語”對應和“多族一語”對應的民族占中國民族總數的30%[21]。這些民族識別的結果,在 “古苗疆走廊”中也出現了使用同一種民族語言卻屬于不同民族身份的認定。如使用苗語黔東方言西部土語的 “繞家人”被認定為瑤族;使用苗語西部方言惠水次方言北部土語的 “東家人”被認定為畬族;使用侗水語支語言的 “佯獚人”被認定為毛南族等。還有一些民族的身份認定與其所使用的語言歸屬也處于 “多族一語”的狀況。
[1][3]楊志強.文化建構、認同與“古苗疆走廊”[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103、104.
[2]龍曄生.“古苗疆走廊”研究及其現實啟示[J].民族論壇,2012(5):14-15.
[4]《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民族[M]//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303.
[5]菅志翔.“族群”:社會群體研究的基礎性概念工具[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5):139.
[6]戴慶廈.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60年[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234-235.
[7]伍文義,辛維,梁永樞.中國布依語對比研究[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4.
[8]龍耀宏.侗語研究[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181-182.
[9]潘朝霖,韋宗林.中國水族文化研究[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389-391.
[10]張繼民.仡佬語研究[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295-314.
[11]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貴州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辭典[M].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11:52.
[12]李云兵.苗語方言劃分遺留問題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237.
[13]楊再彪.苗語東部方言土語比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74.
[14]吳正彪.黔東方言苗語土語劃分問題的再探討[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120.
[15]蒙朝吉.瑤族布努語方言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4-15.
[16]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貴州省志·民族志[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2:439.
[17]楊再彪.湖南西部四種瀕危語言調查(土家語、小章苗語、關峽平話、麻塘話)[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3.
[18]羅康隆.族際關系論[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8:300.
[19]張興權.接觸語言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5-6.
[20]伍新福.苗族文化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93.
[21]王希恩.中國民族識別的依據[J].民族研究,2010(5):9.
[責任編輯:丹 涪]
H172.3
A
1674-3652(2016)06-0014-05
2016-09-11
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史詩《亞魯王》的搜集整理研究”(13BZW172);三峽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培優基金項目“苗語疊音詞研究”(2015PY093)。
吳正彪,男(苗族),貴州三都人。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南方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與人類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