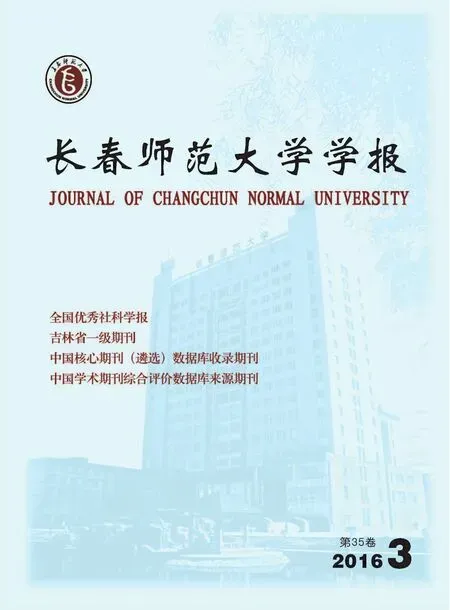英國文學公共領域、咖啡館與約翰·德萊頓的文學公共活動
霍盛亞
(1.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100089;2.中央財經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100081)
?
英國文學公共領域、咖啡館與約翰·德萊頓的文學公共活動
霍盛亞1,2
(1.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100089;2.中央財經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100081)
[摘要]哈貝馬斯在研究資本階級公共領域時提出了“文學公共領域”的概念,并指出這一領域的出現始于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英國。英國文學家通過在咖啡館中進行的文學公共活動介入他們所關注的公共問題,德萊頓是其中最為活躍的一位。以他為首的一批英國作家通過在維爾咖啡館中對文學話題的討論和辯論,訓練了資產階級使用文學實施的“辯論機制”“理性交往”以及“公共輿論”,從而間接促進英國文學公共領域迅速走向頂峰并繼而向資產階級政治公共領域轉型。
[關鍵詞]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維爾咖啡館;約翰·德萊頓
“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ische ffenlichkeit)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旗手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研究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結構轉型時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哈貝馬斯認為,“政治公共領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中產生出來的;它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求加以調節”[1]35。但是歐洲諸國的文學公共領域誕生自不同的文化機構(cultural institutions)中: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發軔于1680—1780年間的咖啡館中,法國和德國的文學公共領域則出現在文學沙龍中。但不管在歐洲的哪個國家,這些文化機構都具有一個共性,即“它們都首先是文學批評中心”[1]37。在17—18世紀英國的數千所咖啡館中,維爾咖啡館(Will’s Coffeehouse)因為以德萊頓(John Dryden)為首的一眾文學家在其中的文學公共活動而享譽歐洲,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的成熟和發展。
一、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的興起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哈貝馬斯將文學公共領域描述為:“是公開批判的練習場所,這種公開批判基本還集中在自己內部——這是一個私人對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經驗的自我啟蒙過程”[1]34。基于哈氏的描述,陶東風教授曾將文學公共領域定義為“一定數量的文學公眾參與的、集體性的文學—文化活動領域,參與者本著理性平等、自主獨立之精神,就文學以及其他相關的政治文化問題進行積極的商談、對話和溝通”[2]。這一概念抓住了文學公共領域的復雜性,也起到了規范這一術語的作用,因為目前國內外學者對這個術語的翻譯和理解還存在爭議。有的學者認為“文學公共領域”一詞在思想層面上應被譯為“文學公共性”(literary publicity或literary publicness);在社會層面把握“文學公共領域”時,這一術語則應被理解為“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而呈現文學公共性的具體物理空間應被稱為“文學公共空間”(literary public space)。
“文學公共領域”一詞由哈貝馬斯最早提出。哈氏從漢娜·阿倫特的“公共領域”論那里獲得靈感,首先研究了古典公私領域關系。他認為基于古希臘高度發達的城邦體系,自由民之間“公共領域”(koine)和“私人領域(idia)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界限,生老病死都存在于“私人領域”中,而“公共領域是自由王國和永恒世界,因而和必然王國、瞬間世界形成鮮明對比”[1]3。到了歐洲的中世紀,由于封建制度的特殊性,公私界限消失,因此“從社會學來看,也就是說,作為制度范疇,公共領域作為一個和私人領域相分離的特殊領域,在中世紀中期的封建社會中是不存在的”[1]6。哈貝馬斯將這一時期的公共領域命名為“代表型公共領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中世紀后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民族和主權國家的形成、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市民階層的日益壯大,傳統的貴族政治衰落了,代表型公共領域開始土崩瓦解。
伴隨著商品和信息交換的發展,國家和社會最終在18世紀的歐洲各國分離,公共權力領域和私人領域也旋即分離。前者以宮廷為代表,后者則由游離于統治階層的第三等級組成,且后者中的個人與個人集合形成了一個與國家權力領域謀求“對話”的領域。這種對話的溝通模式是從宮廷中游離出來的邊緣貴族將宮廷中的社交方式帶到新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間的。“在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相遇過程中,那種充滿人文色彩的貴族社交遺產通過很快就會發展成為公開批判的愉快交談而成為沒落的宮廷公共領域向新興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過渡的橋梁”[1]34。這種對話方式訓練了資產階級的辯論技巧,奠定了公共交往的模式和公共輿論的技巧。而這些對話方式首先是在文學領域得以演練,哈貝馬斯因此將其稱之為“文學公共領域”——一個“不僅是‘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中間地帶,也是‘政治公共領域’的前身,更是‘代表型公共領域’向‘市民公共領域’過渡的一個中介”[3]。文學公共領域的誕生伴隨著一系列新的文化機構的產生,比如咖啡館和沙龍等。通過在這些場所中不斷演練文學批評的技能,“一個介于貴族社會和市民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教養的中間階層開始形成了”[1]37。
在這個中間階層中,實施文學批評的主體是開始走向職業化的文學家。這些文學家逐漸擺脫封建的“文學資助人”,在開始職業化的書商的幫助下,借助咖啡館、沙龍、戲院等機構,討論文學相關話題。在這些文化機構中,不論是文學家還是讀者都接受了批判技巧的訓練。這樣一個具有批判性和自律性的讀者群的形成對于歐洲資產階級政治公共領域的形成具有深遠影響。哈貝馬斯曾說:“通過閱讀小說,也培養了公眾;而公眾在早期咖啡館、沙龍、宴會等機制中已經出現了很長時間,報紙雜志及其職業批評等中介機制使公眾緊緊地團結在一起。他們組成了以文學討論為主的公共領域,通過文學討論,源自私人領域的主體性對自身有了清楚的認識”[1]55。對文學作品的批評與討論,培養了更多具備資產階級公共交往能力和公開批判技巧的社會公眾,同時也幫助他們形成了更強的批判意識和參與公共討論的意識。
按照哈貝馬斯的研究,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發軔于17世紀后半葉的英國,直到“長期反對派”發表三部諷刺作品以及1726年柏林布魯克的《匠人》(Craftsman)雜志的出版開始向政治公共領域過渡。在這一過程中,印刷技術的提高、1710年英國首部《版權法》的頒布、文學贊助人的式微、職業出版商的崛起等都為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的興起和成熟提供了必要條件;咖啡館在英國的流行則為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具體的場域,它們成為英國文學家與國家權力領域進行“對話”的具體場所。具備了“公共性”的文學家通過在咖啡館中對文學話題的討論和批判為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立法”,這為后來英國政治公共領域的發展樹立了范本。可以說沒有英國咖啡館就沒有英國文學公共領域,也就沒有英國民主政治的出現。
二、“便士大學”與英國諷刺文學作品的發展
1665年,署名為“眼見耳聽者”(by an Eye and Ear Witness)的詩人寫過這樣幾行詩:
咖啡與共和
起首皆相同,
共同促革新,
賦民釋與寧[4]68。
雖寥寥數句,卻寫出了英國咖啡館對英國政治、歷史及文化的巨大影響。咖啡如同中國的茶葉一樣,承載著濃厚的文化內涵,它與茶葉和可樂并稱世界三大飲料。咖啡的出現改變了歐洲人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生活方式,改變了英國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英國人不再清晨起床便開始飲酒,而改喝咖啡,由整日酩酊大醉過渡到了更文明的、基于理性對話的、新型的交往方式。這種交往方式對歐洲的影響非常深遠,一位法國哲學家不無夸張地說:“咖啡的出現,帶給了歐洲人自使用火以來最偉大的文明”[5]。
咖啡最早出現在埃塞俄比亞,1615年到伊斯坦布爾尋求東方特色商品的威尼斯商人將之帶回歐洲。1650年,一名叫雅克布的猶太人在英國劍橋經營了“英國甚至是在整個基督教國家的第一家咖啡屋”[6]xiv。劍橋的這家咖啡館既滿足了學者和才子們對東方的獵奇心理,又提供不至于像鴉片那樣容易成癮的咖啡。咖啡館很快開始向英國主要城市進軍,兩年后倫敦出現了第一家咖啡館。根據1663年的一個統計,當時倫敦僅有82家咖啡館,而到了18世紀初倫敦的咖啡館就已多達551家之多。大量咖啡館的出現,不僅改變了英國人的文化生活,還改變了英國人的文學創作習慣和政治生活,因此有學者認為咖啡館是英國“公共輿論”“市民社會”和“民主文化”的策源地[4]。英國日記作家佩皮斯從1660年1月到1669年5月31日的日記中,記錄了他99次訪問咖啡館時的見聞,足見咖啡館對當時知識分子的重要性。
1950年,德裔美國社會學家施拜耳(Hans Speier)在其《公共輿論的發展史》一文中指出,18世紀是現代“公共輿論”理念形成的關鍵歷史時期。他認為在英國和法國,閱讀群體的增加與新型社會機構(new social institutions)如英國咖啡館與法國沙龍的涌現對于歐洲公共輿論意識的形成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英國中產階級(在咖啡館中)接受了教育”[7]376,因為在咖啡館中“新聞匯集、散播,政治辯論和文學批評大受歡迎”[7]376。同為德國人的哈貝馬斯于1962年與施拜耳遙相呼應,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進一步指出,文學和藝術催生了批判性辯論(critical debate),也催生了文學公共領域,其中英國咖啡館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哈貝馬斯曾總結文學公共領域形成的要素和它的運作機制:第一,一個閱讀公眾的形成,即“一般的閱讀公眾主要由學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階層構成,他們的閱讀范圍已超出了為數不多的經典著作,他們的閱讀興趣主要集中在當時的最新出版物上”[1]3;第二,一旦足夠多的閱讀公眾產生,“一個相對密切的公共交往網絡從私人領域內部形成了”[1]3;第三,有了閱讀的公眾和交往的空間,就需要一定的規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以文學家為代表)從游離貴族那里習得的平等交往原則、自由討論方式和依照多數決策等原則得以貫徹實施,而這些要素的形成都發生在一個物理空間——咖啡館中。
在咖啡館這個文化機制中,一套隱形的“規章”通過不斷的文學辯論和討論形成:第一,一種并非建立在“級差”基礎上的社會交往模式的形成,也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這種社會交往的前提不是社會地位平等,或者說,它根本就不考慮社會地位問題”[1]41,但咖啡館并非公眾討論產生的充要條件,因為“雖說不是有了咖啡館、沙龍和社交聚會,公眾觀念就一定會產生;但有了它們,公眾觀念才能稱其為觀念,進而成為客觀要求,雖然尚未真正出現,但已在醞釀之中”[1]41;第二,公眾在文學公共領域中討論的議題不受限制,因為“(哲學作品和文學作品)不再繼續是教會或宮廷公共領域代表功能的組成部分;這就是說它們失去了其神圣性,它們曾經擁有的神圣特征變得世俗化了。私人把作品當作商品來理解,這樣就使作品世俗化了”[1]41;第三,這個文學公共領域具有普遍開放性,也就是說,“公眾根本不會處于封閉狀態”[1]42,“因為,他們一直清楚地知道他們是處于一個由所有私人組成的更大的群體之中”[1],而且在這個空間中討論的話題可以使“所有人必須都能加入到討論行列”[1]42中來。
咖啡館中英國文學家的公共活動直接促進了復辟以降散文與詩歌中“粗俗諷刺作品”(vulgar satire)的發展,這一文類主要包括拙劣模仿作品(low travesties)、滑稽諷刺作品小冊子(chapbook burlesques)、歷史笑話集(jest-book histories)以及抨擊性民謠(broadside ballads)等,它們大多是對控訴書(complaint)、請愿書(petition)、游記(travel journal)、新聞報道( news report)等嚴肅文體的粗俗戲仿。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創造性和藝術性很強的諷刺作品的出現,比如修地布拉斯體(Hudibrastic)就是從17世紀英國作家塞謬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為嘲諷清教徒而創的一首題為《修地布拉斯》的諷刺詩而來。還有一些嘲諷式控訴書(mock-complaint)在當時的咖啡館中很受讀者追捧。這些控訴書通常借輕浮的女仆、啤酒屋女老板或女商販之口,用粗鄙的言辭向法官陳情。此類作品多為文人所作,代替普通大眾控訴時弊,在咖啡館中非常流行,讀者也都是咖啡館中的普通大眾。
英國咖啡館還復興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文類——人物或性格特寫(The Character)。這種文類由古希臘哲學家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所創,常用來刻畫一類具有典型特征的人。這些文章篇幅短小,卻詼諧辛辣,因此常被用作犀利的武器來攻擊持不同意見者。由于篇幅短小、易于出版,這些文章也因此在咖啡館中廣為流傳。第一篇對咖啡館的特寫創作于1661年,題為《咖啡和咖啡屋特寫》(A Character of Coffee and Coffee-Houses),生動地記錄了早期咖啡館中的公共活動。此文至今僅剩三個善本,留存在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圖書館(the Worcester College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th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和蘇黎世約翰納雅科布斯博物館(the Johann Jacobs Museum, Zurich)中,十分珍貴。
英國咖啡館文化史研究專家伊利斯(Ellis)說咖啡館“把來自社會各界的人首次團結在了一個民主的集會中,使得人們暫時擱置我們這個民族所特有的陋習。通過這樣的集會,人們可以感知到共同的危機”[6]xv,不僅如此,咖啡館還是市民階層交流政治觀點、討論文學、科學等議題的重要場所,它在英國人信息傳播和知識習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英國人戲稱咖啡館為“便士大學”(Penny University),因為在這里不管是誰,只需要花費幾個便士就能獲得一杯咖啡,更重要的是他們還獲得了與眾人交流和學習的機會。可以說,在17-18世紀,“英國皇家學會”的誕生、英國散文的發展、現代意義報紙的出現,乃至“英國民族禮節、風度和禮儀的核心價值觀念”[6]316的形成都與咖啡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英國復辟到安妮女王治下期間,眾多的咖啡館中,維爾咖啡館(Will’s Coffehouse)因為德萊頓等文學“才子”的公共活動而備受當時英國人的矚目。
三、維爾咖啡館中的文學公共活動
英國羅素大街上星羅棋布的咖啡館對英國文學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彌爾頓(Milton)、馬維爾(Marvell)、佩皮斯(Pepys)和哈林頓(Harrington)在洛塔(Rota)咖啡俱樂館經常聚會,啟發了哈林頓《大洋國》的創作;艾迪生(Addison)和斯蒂爾(Steele)在布頓(Button)咖啡館開始了他們的報紙寫作與發行,推動了英國報刊業的飛速發展;以約翰·德萊頓為首的文學“才子們”(wits)則喜歡在這條大街上最早開張也最富盛名的維爾咖啡館中聚會。這家咖啡館在復辟時開門迎客,此后的30多年中一直備受當時文學家們的青睞,也成為很多年輕詩人和作家成名的搖籃。德萊頓在維爾咖啡館中對文學相關話題的討論為日后文學鑒賞和批評設立了標準,18世紀的很多作家都效仿他到咖啡館中尋找創作靈感和喜歡自己作品的讀者。
德萊頓是維爾咖啡館的上賓,他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出現在這家咖啡館中,這里設有他的專座。“德萊頓習慣坐在一樓,他冬天的專座設在壁爐旁,而在天氣好的時候他更喜歡坐在陽臺的角落里,在那里他可以遠眺街景,他把這兩個座位叫做‘冬座’和‘夏座’”[4]xi。他的到來使得“當時人們以能親耳聆聽他談論詩文為殊榮”[6]67。德萊頓在咖啡館的文學討論和爭辯中充當法官和陪審團的角色,年輕作家都希望進入維爾咖啡館的文學圈子中,而獲準加入該圈子的標志就是德萊頓從自己煙盒中拿出一支鼻煙讓新人品嘗。康格里夫(Congreve)、威徹利(Wycherley)以及艾迪生(Addison)等一大批作家都曾在這里受到過德萊頓的提點,并因此走向成功。
德萊頓喜歡在維爾咖啡館中寫作,也喜歡加入這里的文學討論。維爾咖啡館里到處都是已刊登或等待刊登作品的手稿,從詩歌到諷刺文章應有盡有。詩人羅伯特·于連(Robert Julian)專門負責從中挑選供他們討論的素材,斯威夫特在其《談話的訣竅》(Hints to an Essay on Conversation)中戲謔而生動地描述了這種文學辯論的情形:
我有生以來聽到的最糟糕的對話正是在維爾咖啡館里,在那里“才子們”(就像人們所說的)正式聚會,他們五六個人聚在一起,在如此嚴肅的氛圍里,拿他們之前寫的幾處劇本,序言或者一些什么也不是的東西彼此娛樂,好像他們所做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崇高的事業,或者他們是“王國宿命”決策者[6]65。
當時的英國咖啡館中有一種非常流行的現象:詩人們通常會在公共場所大聲朗誦他們創作的作品或者大聲議論發表在報紙上的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咖啡館中的文學討論并非如哈貝馬斯理想化的那樣自由與開放,當時主要的幾家咖啡店通常由一個中心人物來主導,他們對各種爭論進行“仲裁”,這便招致另外一些文學家的不滿。斯威夫特就曾在一首詩中嘲諷德萊頓:
他給出決斷性的判斷,
對四下圍坐著的“才子們”,
遞上來的“神諭”。
他為城市發展指明方向,
指點江山[8]。
從這首詩歌不難看出,英國咖啡館中文學公共領域所依托的平等對話的機制被類似德萊頓這樣的“主持人”左右,使得文學公共領域的平等對話原則很難得以真正實現。
另外,英國重要報紙《閑談者》(Tatlar)第一期的頭版中曾這樣寫道:“如果想看勇敢的、快活的、娛樂的報道,就請去懷特巧克力屋,如果要讀詩歌,請去維爾咖啡館,如果要學習,請到‘希臘’咖啡館,如果是要獲取國內外新聞,就請去圣詹姆斯咖啡館”。通過這段記錄,我們不難發現英國咖啡館已經開始按照不同群體的需要劃分了類別,也就是說英國文學公共領域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某種“排異機制”,這種機制將無產者和女性排除在外,為資產階級政治公共領域埋下了自我解構的因子。哈貝馬斯在其“文學公共領域理論”建構中無視這一問題,從而為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等學者所詬病。這種排異機制在文學公共討論的實踐過程中有時會表現得非常激烈,甚至會出現言語乃至身體上的傷害。艾利斯研究稱:
他們用這種文體(諷刺文章)取笑對方,他們尤其喜歡取笑初來乍到的人(尤其是來自鄉下的人,因為他們通常不那么老于世故)[6]66。
1687年,德萊頓曾發表過一首名為《馬鹿與黑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的詩,為自己改信天主教辯解。這首詩馬上就招致普萊爾(Prior)和蒙塔古(Montagu)的辛辣諷刺,他們改寫了德萊頓的詩歌,并把題目改為《馬鹿與黑豹,變身為鄉下老鼠與城市老鼠的故事》(The Hind and the Panther transcended, to the Story of the Country Mouse and the City Mouse),將德萊頓詩中象征基督的鹿和代表教會的黑豹改寫成了一只鄉下老鼠和一只城里老鼠。鄉下老鼠天真無邪、涉世未深,想要參觀有著“才子咖啡館”美譽的維爾咖啡館:
我久仰才子咖啡館,
‘斑點’獸說你定要去瞧瞧,在那里
牧師們呷著咖啡、閃爍著智慧的火花、品著詩人的仙茶;
這里窮人得自由,富人著華服;
這一切讓大官喪氣,讓測試難熬[6]66。
然而,當他們看到維爾咖啡館的時候,卻發現德萊頓高高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他是神圣才子詩壇的判官,
他端坐在自己榮耀的陰影之中。
仿佛月亮女神接收到光芒,
她將周遭照亮;
也照亮了他,在遠處閃閃發光,
他向這顆星借了光芒
高乃依和拉賓所制定的條條框框
被身后的涂鴉者奉為金科玉律。
他把這些借來的真理再次分發,
你將因陰謀分裂受到懲罰
若你膽敢質疑他,或只信自己的判斷[6]66。
城市老鼠諷刺德萊頓充當本市詩歌創作的評判者,認為德萊頓的新古典主義美學原理僅僅是被動地臣服于以高乃依和拉賓為代表的法國詩歌的主張。詩歌作者將這個例子同德萊頓宣誓效忠天主教和獨裁政治的行為聯系在一起,從而達到嘲諷德萊頓的目的。德萊頓確實因為這首詩歌而受到了傷害,他曾在咖啡館中和才子們聚會時說自己的諷刺詩歌在發表的時候總是署名的,而攻擊他的人不敢這樣做。
1679年,德萊頓更因為一首題為《諷刺》的詩招致了身體上的傷害,坊間到處流傳說這首詩是德萊頓為譏諷國王和他情婦之間的丑聞而作。一天晚上,當德萊頓從維爾咖啡館出來回家的路上,這位作家被三個男人截住痛揍一頓,暴徒的指使者很有可能是國王情婦之一的樸茨茅斯公爵夫人路易斯。一首詩歌不僅引發了語言暴力的出現,甚至引發了對文學家本身的身體暴力,而暴力的出現正是文學公共領域的大敵,這是哈貝馬斯在建構理想化“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時所未察的情況。
德萊頓死后十年,維爾咖啡館依然是才子們進行文學創作和討論的中心,直到1712年它的地位受到新開張的巴頓咖啡館的挑戰。此時咖啡館中的文學討論越來越多地摻雜了政治話題,文學公共領域開始逐步向政治公共領域過渡。但從17世紀末開始,英國知識分子在咖啡館里建立起的社交模式已經深入人心,在咖啡館里辯論和社交、讀報紙、看雜志、關心公共事務的習慣都被保留了下來。咖啡館吸引了眾多作家、詩人和藝術家的到來,他們在這里可以自由地分享創作經驗和閱讀的快樂體驗,從而直接參與建構了英國文學公共領域。但從對維爾咖啡館的研究不難看出,英國文學公共領域并非如哈貝馬斯所建構的那樣理想,它通過一系列“排異機制”將女性和平民隔絕在外。另外,語言和暴力的存在也威脅了文學公共領域的發展,這都是哈貝馬斯“文學公共領域”中所忽略的。
[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2]陶東風.阿倫特式的公共領域及其對文學研究的啟示[J].四川大學學報,2010(1):31.
[3]曹衛東.交往理性與詩學話語[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118-9.
[4]Ellis, M. Eighteenth-Century Coffee-House Culture[M].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5]鄭萬春.咖啡的歷史[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7:4.
[6]Ellis, A. The Penny Universities: 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s[M].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56.
[7]Speier, H.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0: 55(4): 376,376.
[8] Pat Rogers ed.Complete Poems[M].London:Penguin,1983:539.
British Literary Public Sphere, Coffeehouses and the Literary Public Activities of John Dryden
HUO Sheng-ya1,2
(1.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2.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Haberm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n his study of bourgeoisie public sphere,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end of 17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18th century Britain. British writers got involved in the public issues in the coffeehouses through their literary public activities, among whom John Dryden was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Headed by him, writers in Will’s Coffeehouse discussed and debated literary topics so that the “debating mechamism”, “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were practiced and reinforced by uprising bourgeois,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terary public sphere to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Key words:British Literary Public Sphere; Will’s Coffeehouse; John Dryden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602(2016)03-0138-06
[作者簡介]霍盛亞(1981- ),男,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后,中央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從事英美文學、西方文論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青年基金項目“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研究(1640—1726)”(14CWW012);中財121人才工程青年博士發展基金項目“英國文學公共領域研究(1640—1726)”(QBJ1425);中央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基礎學科科研扶持計劃支持項目(021650315005)。
[收稿日期]2015-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