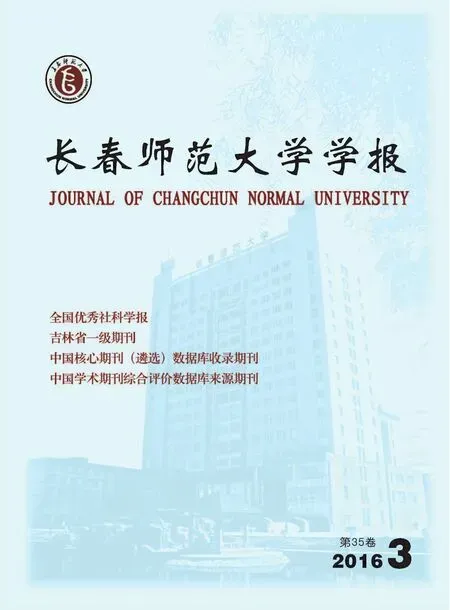“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二元迷思及破解之道
樊小賢,夏玉漢
(長安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4)
?
“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二元迷思及破解之道
樊小賢,夏玉漢
(長安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4)
[摘要]本頓指出馬克思的生態觀的“失誤”在于“支配自然”的技術樂觀主義的幻想,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應以“適應自然”為主題進行生態學重建。而格倫德曼則賦予支配自然以積極意義,認為有效地支配自然才是解決生態問題的良方。本頓和格倫德曼對馬克思生態哲學特別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陷入了二元論的思維模式,走出二元迷思的正確路徑是回到馬克思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辯證思維和實踐智慧的理解上來。
[關鍵詞]支配自然;適應自然;二元迷思;破解之道
20世紀80年代英國興起了以泰德·本頓和格倫德曼為代表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潮,這一思潮把環境運動的理論基礎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泰德·本頓和格倫德曼是英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佼佼者,雖然他們都受益于馬克思主義,但其理論導向卻截然不同。在英國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內部,泰德·本頓和格倫德曼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形成了“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既然都是在繼承生態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形成的理論,為什么對待自然、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與方法截然不同?它們各自的理解有何偏頗之處?他們所提出的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法是否對當今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有所啟示?本文試圖闡釋本頓和格倫德曼在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上的爭論焦點和理論困境,基于人與自然辯證和諧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破除“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之爭的二元迷思。
一、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之爭的理論依據:馬克思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經典論述
本頓和格倫德曼是英國著名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理論家,他們都從馬克思那里得到啟發,并從不同的角度把馬克思的生態觀拓展開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關注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帶來嚴重的生態問題,并且基于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批判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思想觀點、理論與方法。馬克思站在人的勞動本質與人的勞動異化的角度上認為,勞動本身的異化放大了人類的欲望,使人在私欲的滿足中獲得自由、幸福和快樂,為了滿足自己這種動物式的欲望,人類賦予機器以“力量”,展開了對自然的殘酷盤剝和瘋狂掠奪,而這就帶來了自然資源浪費與枯竭、土地荒蕪、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日趨嚴重等一系列環境問題,最終,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奪走了他的無機的身體即自然界”。[1]由此觀之,馬克思在青年時期就認識到了自然異化的嚴重后果,并且把這種環境問題的原因歸于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和生產方式下的異化勞動。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人與自然是基于實踐的辯證關系,他說“人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2]這表明人類在否定自然的過程中使自身蘊藏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這種活動受到他自己意識的控制。然而,馬克思本人并沒有提出系統的生態哲學理論。本頓和格倫德曼在理解馬克思生態學觀點的邏輯徑路和理論分向上有很大的差異。本頓認為,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了許多生態學的觀點,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態困境,但由于理念和實踐的原因,歷史唯物主義本身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生態理論。因此,本頓主張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維度的重建,這種重建意味著歷史唯物主義生態理論的建構與回歸。而格倫德曼則反其道而行之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自身就包含了解決當今生態問題的良方,因此他主張回到和拓展馬克思主義,并且運用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觀點與方法處理當前的生態危機和生態問題。這兩種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致思路徑使得他們在對待人與自然關系上的態度與方法相去甚遠,因此引起了所謂的“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之爭。
二、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之爭:本頓和格倫德曼的不同解讀
(一)本頓與適應自然
本頓站在生態中心主義的立場上,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性的解讀。本頓把歷史唯物主義界定成一種“生產主義”、“普羅米修斯式的”歷史觀,進而把馬克思的生態觀解讀為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和工具主義的自然觀。[3]42本頓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態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本身在生態學上存在問題。他從三個方面剖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問題:第一,把人類解放與自然極限對立;第二,過分相信物質進步和技術進步;第三,只有生產理性而無生態理性。[3]42-46由此,他斷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觀是一種“生產主義的”和“普魯米修斯式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主張通過解放生產力來發展人類社會。他指責馬克思總是以持有普羅米修斯一樣的沖動的態度對待自然界,懷著以人類征服自然為榮的自大而無知的心態,只相信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反生態的工業主義,而對生態環境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卻置若罔聞。[3]49也就是說,本頓把現代生態環境的破壞直接歸因于歷史唯物主義中“支配自然”和“控制自然”觀念的泛濫。因此,他站在生態中心主義角度拒斥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用“適應自然”代替“支配自然”來改造歷史唯物主義,以新的觀念和思想指導人類的生態實踐活動。
本頓基于自然生態價值的轉換,重新建構了以“適應自然”為中心的歷史唯物主義生態觀,以期能夠使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化。首先,本頓對自然概念進行了重新界定。他認為,自然不僅僅是人類實踐所面對的自然環境的場所,還包括自然所提供的各種資源。因此,自然與人類社會是共生的,自然天然(從邏輯上講,而不是從時間上講)包含人類社會,人類社會處于自然界之中。同時,生產必然以自然資源為原料,而自然資源本身源自于自然并且是有限的。其次,本頓對勞動概念進行了重新解讀。本頓把勞動分為生產改造型勞動過程和生態制約型勞動過程。生產改造的勞動過程主要特征是人在勞動過程中作為中介的要素,這一要素功能的發揮依賴于人的適應自然本性。而生態制約型的勞動過程主要特征是“極大地依賴勞動對象所處的自然條件和勞動兌現的各種性質”。[4]因此,本頓弱化了人在勞動過程中帶有征服意味的傲慢的偏見,加強了自然物質在勞動過程中本有的地位與作用。因而,他認為馬克思過分強調勞動的生產改造的性質,忽略了生產過程中的人的適應能力和生態制約性要素的作用,以至于陷入“生產主義”和“支配自然”帶來的生態困境。而要走出這種困境,就要拋棄以支配自然為中心的生產理性,建立以適應自然為中心的生態理性,從而把勞動過程看成是受自然制約的生態調節過程。最后,本頓站在勞動過程即生態調節過程的新的思維方式上,反思了技術革新的生態價值。由于自然的不可控性,技術革新不可能操縱自然,只能以審慎的態度去適應自然。技術革新本質上是基于適應自然的技術漸變過程,而不是掠奪式的突變過程。總之,人類勞動不是為了改變而改變,而是為了適應與生態而改變。
(二)格倫德曼與支配自然
格倫德曼對本頓的唯物主義的生態學批判和建構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格倫德曼首先承認馬克思有關于“支配自然”思想的主張,同時他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上為馬克思的“支配自然”的思想作了有力的論證。其次,他認為那些綠色社會主義理論缺少了馬克思“支配自然”的理論指導,使得生態問題日益嚴重。格倫德曼之前,萊斯追溯了哲學史,認為馬克思的“支配自然”的思想有其理論淵源。在古希臘羅馬神話中,人們通過創造工具來支配自然,但人們的工具理性思維尚處在幼年階,他們對控制自然的態度是非常謹慎的。在中世紀人類充當自然的管理者,認為控制和管理自然是上帝旨意。近代自然科學迅速發展,在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號召和笛卡爾等哲學家主體性思維的覺醒的導向下,人類支配和控制自然的欲望進一步擴張。馬克思就是繼承這種理性支配自然的傳統,形成了以人類為中心的生態觀,進而以這種生態觀導引人們利用、支配和改造自然來滿足人類自身的需求。
格倫德曼賦予“支配自然”以特殊的積極意義,認為“支配自然”才是真正解決生態問題的良方。首先,馬克思是在生存論的意義上談論人對自然的支配。人類只有支配自然和控制自然、與自然抗爭才能從自然界中獲取物質和能量,這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必然要和自然界進行物質與能量的交換,而這首先是一種以獲取物質生產資料為目的的勞動生產過程。其次,馬克思所謂的控制自然是在掌握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有意識地控制和支配自然,而不僅僅是盲目地對自然進行征服與掠奪。格倫德曼認為,對自然的支配絕不意味著用野蠻的暴力方式對待自然。[5]在人與自然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的過程中,人類行為總是有目的、有意識、有計劃的,而這種規劃又總是建立在人類在實踐過程中所掌握的規律的基礎上。這種勞動實踐探索與自然界自身的規律發展的辯證統一指向了人與自然和諧的可能。最后,支配自然是與支配主體利益相關的,是解放人類自身的積極力量,而不是破壞和濫用自然的消極力量。也就是說,格倫德曼在賦予“支配自然”的積極意義的時候不是基于自然而是自然對人的價值、不是基于人類的欲望而是人類的理性。這種理性是建立在人的認知理性和自然規律上的,不是價值理性上的獨斷,更不是感性思維上的臆斷。這種意義上的支配自然正是一種擴張和拓展了的人類中心主義,而不是極端的獨斷的人類中心主義。
三、走出“二元論”的迷思: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辯證
本頓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批判和格倫德曼的積極回應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仍然沒有走出二元論的思維僵局。首先,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都有其使用的范圍和界限,不能簡單地將二者對立起來。支配自然站在人類生存必然要從自然中獲取物質和能量的基礎上,適應自然則站在自然的極限和自然的規律之上。支配自然不是毀滅性的支配,適應自然不是主奴關系式的適應。如果簡單地把二者對立起來,只會陷入無限的爭吵而無益于生態問題的真正解決。其次,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是在人的理性的指導下的活動,不能脫離人的認識能力和價值判斷能力來談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支配自然和適應之然是從自然中關照自身,不是對自然的盲目征服與統治,而是人類理性的尋求和自然價值的滿足的統一。自然界是人類的一部分,無論是支配與適應都應把自然的承受能力與人類的需求、人類的認知與實踐能力與自然界的規律統一起來,讓人類更好地融于自然,也讓自然更好地服務于人類。最后,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是以承認科學技術的作用為條件的,拋開科學技術來談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生產過程中的技術理性不可或缺,生態理性和價值理性同樣不可缺少。技術既是手段,也是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目的。也就是說,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既要考慮生產效率和效益,也要考慮生態效益。可見,單向度的“支配自然”和單向度的“適應自然”的主張都難以實現自然物質的本身的價值與人類所需的自然物的價值兩者的統一。
盡管馬克思雖然沒有給出系統的生態學理論,但唯物辯證法確實為解決生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要走出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二元迷思就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上來,從人類實踐活動出發辯證地理解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
第一,辯證唯物主義是理解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合理性的哲學基礎。馬克思從世界觀的高度界定了世界的物質本性,人的活動無非是物質場域中的實踐活動。因此,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在低級階段和探索未知領域時,必然要依賴和適應自然,通過實踐活動把自然界的物質轉化為人類所需要的形式。盡管這一過程是不可或缺的,但馬克思認為物質絕不只是僵死的、機械的物質。人類的實踐活動特別是生產實踐活動既是對自然界的否定,也是對自然界的肯定。人類用生產工具開發自然,把自然烙上人類的痕跡,否定了自然界的自在存在形式。同時,人類不斷在實踐活動中探尋,使得自身更加成熟地掌握和運用自然規律,肯定了自然規律的客觀性。人類實踐的雙重指向使人類在這一辯證過程中既要適當地適應自然,也要適度地支配自然。也就是說,人類對自然的態度不能以支配或適應這些單向度的簡單形式來概括,這種形式本身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而要把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理解建立在自在自然與人化自然和人類實踐活動的辯證過程的理解基礎上。
第二,勞動實踐是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最本質的形式。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以自身的行為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代謝過程”。[6]也就是說,馬克思的生產勞動概念是建立在人與自然的辯證發展過程基礎上的,它要求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要做到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辯證統一。首先,支配自然離不開對自然規律和自然極限的認識,也就是說支配自然實際上是適應自然的延伸與拓展。如果沒有認識到自然的價值和規律而盲目地支配自然,那么就會適得其反,必然遭到自然的報復。其次,適應自然是有意識的人對自然對象進行有目的的調節性的適應。這一過程是人從自然中獲得解放的過程,因此人類必然會運用自身的力量特別是認知和理性的能力和力量來進行支配性的調節。最后,支配自然和適應自然是建立在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辯證關系的基礎之上的。人類的實踐活動是在人化自然而不是自在自然中進行的,人對自然的改造也是適應性的探索和自然規律的運用相統一的過程。也就是說,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既不能單純地支配自然,也不能單純地適應自然。同時,這一過程也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生產理性和生態理性、人的能動性和客觀物質基礎辯證統一的過程。因此,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辯證統一才是人類繁榮和自然繁榮統一的有效途徑。
第三,人與自然和諧是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價值旨歸。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共同的價值旨歸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馬克思曾指出:社會的最初形態是“人的依賴關系”,社會的第二種形態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在此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人與自然和人與人全面的關系,以社會為根本的“人”的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7]人類社會是離不開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的社會群體,必須兼顧人類的需求與能力和自然界的規律。余培源教授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對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作了深刻的解讀,他認為人類對待自然界的態度經歷了古代的“崇拜”“敬畏”、近代的“征服”“統治”,作為否定之否定的“和諧”形態又是對前兩個階段的積極揚棄。[8]也就是說,從總體上看人類歷史也經歷了適應自然和支配自然的辯證否定,最終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目標與訴求。同時,人與自然的和諧的本質是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辯證,是自然價值和人類本質需求的平衡。站在絕對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上的支配自然和站在極端生態中心主義立場上的適應自然都難以處理好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人類總是在人化自然的基礎上進行生產、實驗等實踐活動以滿足自身的需要,然而也就是在這一過程中人類不斷探索,加深了人類適應自然的能力和適應自然的廣度和深度。因此,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實踐活動推動著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展開,從而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共同繁榮。在這一過程中,人與自然和諧的價值也教育和感化人類更好地支配和適應自然。總之,人與自然和諧的價值皈依始終在發揮著價值內化與價值外化的雙重作用,使得生態倫理理論和生態實踐共同升華。
四、結語
當今社會,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破壞加劇,保護環境和維護生態平衡成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議題和每個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本頓和格倫德曼的爭論為我們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支配自然與適應自然的辯證關系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適應自然”和“支配自然”之爭實質上是依據馬克思的生態學觀點從生態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同角度的解讀與建構。這種解讀與建構在本質上陷入了二元論的迷思,要走出這種迷思,就要站在實踐的基礎上重新認識“適應自然”和“支配自然”的辯證關系,才能夠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和共同繁榮。在新常態的大環境下,我們決不能誤入絕對支配自然的唯經濟主義的歧途,也不能只為環境而犧牲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要把經濟發展與環境友好的雙重尺度結合起來,讓“金山銀山”和“青山綠水”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服務。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6.
[3]倪瑞華.英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2011.
[4]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J].New Left Review,1989(178):67.
[5]Reiner Grundamann.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J].New Left Review,1991(187):109.
[6]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2.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4.
[8]余源培.對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社會的哲學思考[J].湖南社會科學,2005(4):1-5.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602(2016)03-0010-04
[作者簡介]樊小賢(1964- ),女,教授,從事生態倫理學研究;夏玉漢(1990- ),男,碩士研究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倫理問題研究”(13XKS014)。
[收稿日期]2016-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