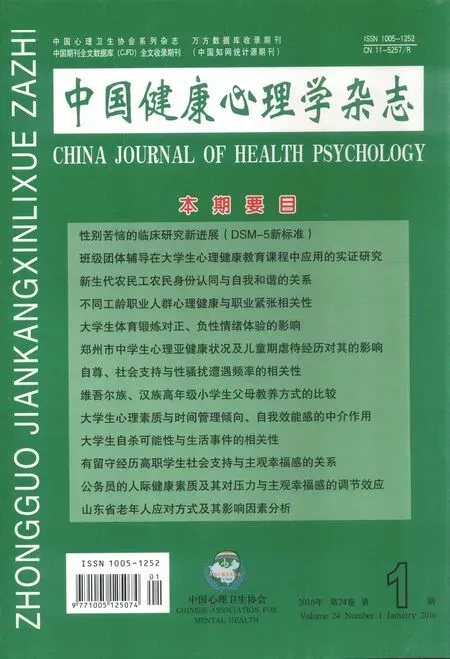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與自我和諧的關系*
高亞東 曹成剛 劉 瑞 岳彩鎮
中國.重慶文理學院認知與心理健康重點實驗室(重慶)402160△通訊作者 E-mail: yczpsychology@ 163.com
?
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與自我和諧的關系*
高亞東曹成剛劉瑞岳彩鎮△
中國.重慶文理學院認知與心理健康重點實驗室(重慶)402160△通訊作者E-mail: yczpsychology@ 163.com
【摘要】目的:探討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與自我和諧的現狀及兩者的關系。方法:采用“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問卷”和“自我和諧量表”對219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測試。結果:①新生代農民工的農民身份認同在性別、收入水平、工作城市(t=-3.681,-12.657,-12.073;P<0.001)和受教育程度(F=30.121,P<0.001)上差異顯著;②新生代農民工自我和諧在性別、收入水平、工作城市(t=-2.972,-13.799,-14.039;P<0.01或0.001)、受教育程度(F=14. 756,P<0.001)上差異顯著;③自我歸類和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自我的靈活性、自我的刻板性呈顯著負相關(r=-0. 19,-0.35,-0.21;P<0.001或0.01);身份重要性和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自我的靈活性、自我的刻板性呈顯著負相關(r=0.37,0.56,0.45;P<0.001);行為投入和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自我的靈活性、自我的刻板性呈顯著負相關(r=0. 31,0.60,0.42;P<0.001)。結論:新生代農民工的農民身份認同越高,自我和諧的程度也越高。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自我和諧;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問卷
"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指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由農村進入城市務工的農村青年[1]。新生代農民工相對于“一代農民工”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他們受教育程度高,對城市期望值高,要求高物質生活享受和精神享受,具有較高的職業追求[2]。長期的城市生活以及城鄉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使他們漸漸地不再適應農村生活。長此以往,他們成為了既融不進城市,又不愿回鄉的“邊緣人”[3]。2010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特別要求大力解決好新生代農民工的各種問題促進其市民化的轉變,該文件的提出充分表現了國家對該群體的重視,同時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存在城市適應及身份認同等方面的問題[4]。
學者們大多從社會學、人口學的角度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問題。趙雪梅,杜棟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進行界定,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是指其在城市融入過程中不斷地與城市居民互動,在認識自身是農民的基礎上,對自身與城市生活的不融入而產生的自身身份的認知、感情歸屬[5]。李東坡認為,農民工身份認同包括兩方面,一是農民工群體對自身內在身份的認知和判斷,二是指農民工群體對自身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的認識[6]。而李虹,倪士光等人給出了明確的農民工身份類型,即城里人、農村人、外來人、農民工,農民工身份認同即對自己是城里人、農村人、外來人、農民工的認識[7]。
在心理學領域,身份認同(Identity)是指個體認識到他(她)屬于某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該群體成員帶給他(她)的情感和價值意義[8]。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表明,身份認同對于個體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它對個體的自尊[9-10]、自我同一性[11]以及心理健康[12]等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工作,面臨著適應環境變化、應對孤獨感、社會歧視等多重壓力[13]。對他們而言,其農民身份認同也有重要的意義。羅杰斯指出,如果各種自我知覺之間出現沖突或者個體體驗到自我與經驗之間存在著差距,個體就會感到內心緊張和紛擾,呈現不和諧的狀態[14]。
自我和諧是羅杰斯人格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是指自我內部的協調一致以及自我與經驗之間的協調,是一個人的自我觀念中沒有沖突的心理現象。羅杰斯認為,個體有著維持各種自我知覺之間的一致性,以及協調自我與經驗之間關系的功能,如果意識中的自我概念與實際上的經驗產生分歧時,個體就會經歷或體驗到人格不協調或不一致的狀態[15]。楊憲華的研究表明,在大學特困生群體,其心理健康與自我經驗的不和諧、自我刻板性存在顯著的正相關[16]。張雯雯通過對高中學生自我和諧與壓力的研究表明,壓力源對高中生自我和諧程度有較好的預測作用[17]。
基于上述兩個概念的內涵以及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壓力,本研究擬從心理學角度探討新生代農民工的農民身份認同與其自我和諧之間的相關關系。
1 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此次調查研究隨機選取227名農民工被試發放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19份(96.48%)。其中男性129人,女性90人;月收入在3000及以下140人,月收入在3000以上79人;在一線城市(東部城市)工作的有131人,在二線城市(西部城市)工作的有88人;受教育程度方面,初級教育36人,高中教育75人,高等教育108人。所有被試均出生于1980年以后。
1.2方法
1.2.1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問卷[18]由蔡貞、汪玉蘭、畢重增編制,共有16道題,分為“自我歸類”、“身份重要性”和“行為投入”3個維度,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8367,且具有較高的同質信度和預測效度。問卷采用5級計分方法,將各個維度的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農民身份認同度就越高。
1.2.2自我和諧量表[15]由王登峰編制,量表共有35道題,分3個分量表:“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量表、“自我的靈活性”量表、“自我的刻板性”量表。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8152,且具有較高的同質信度和預測效度,可用于研究。本量表采用5級計分方法,其中將“自我的靈活性”分量表下的所有題項反向計分后,與剩余兩個分量表的得分相加,得分越低,則自我和諧程度越高。
1.3統計處理
采用SPSS 11.5進行數據的處理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在人口統計學上的差異
本研究對不同性別、月收入水平、工作城市、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總分及各個維度上的得分進行差異性檢驗,見表1。
表1 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及其各維度上的比較(±s)

表1 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及其各維度上的比較(±s)
性別月收入 工作城市 教育程度項 目 男 女 3000元以下 3000元以上 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初級教育 高中教育 高等教育身份認同 56.27±8.49 52.06±8.11 50.25±6.03 62.14±7.01 49.93±5.55 61.40±7.66 63.50±8.32 53.31±6.20 52.41±8.24自我歸類 16.98±3.21 15.91±3.27 15.69±2.75 18.06±3.56 15.47±2.61 18.14±3.51 19.61±3.69 16.64±2.31 15.45±3.04身份重要性 25.29±4.25 23.37±3.56 22.48±2.94 28.09±3.29 22.46±2.96 27.55±3.59 27.89±3.74 23.52±3.43 24.06±4.06行為投入 13.99±2.75 12.78±2.75 12.09±2.19 15.99±1.90 12.00±2.12 15.72±2.17 16.00±2.38 13.15±2.23 12.90±2.87
結果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的性別差異顯著(t=3.681,P<0.001);月收入水平差異顯著(t=-12.657,P<0.001);工作城市差異顯著(t=-12.073,P<0. 001);受教育程度差異顯著(F=30.121,P<0.001)。具體表現為:男性農民工的身份認同高于女性農民工;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農民工身份認同高于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農民工;在二線城市工作的農民工身份認同高于在一線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接受初級教育農民工的農民身份認同最高,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最低。
2.2新生代農民工自我和諧在人口統計學上的差異
本研究對不同性別、月收入水平、工作城市、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自我和諧總分及各維度上的得分進行差異性檢驗,見表2。
表2 新生代農民工在自我和諧及其各維度上的比較(±s)

表2 新生代農民工在自我和諧及其各維度上的比較(±s)
項 目 男 女 3000元以下3000元以上 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初級教育 高中教育 高等教育自我和諧總分 98.17±13.50 103.26±11.68 107.30±7.45 87.78±11.26 108.04±5.97 88.68±11.97 90.50±13.09 100.59±12.81 103.29±11.54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 48.48±6.58 50.77±6.35 52.24±4.99 44.42±6.04 52.22±4.98 45.25±6.46 45.72±6.84 49.69±6.38 50.46±6.22自我的靈活性 28.89±5.61 30.18±5.53 31.69±4.44 25.41±5.18 32.27±3.87 25.17±5.06 25.89±5.77 29.41±5.23 30.60±5.33自我的刻板性 20.80±4.04 22.31±3.86 23.37±2.98 17.96±3.26 23.54±2.73 18.26±3.55 18.89±3.73 21.48±4.04 22.22±3.80
結果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自我和諧的性別差異顯著(t=-2.972,P<0.01);月收入水平差異顯著(t=-13.799,P<0.001);工作城市差異顯著(t=-14.039,P <0.001);受教育程度差異顯著(F=14.756,P<0. 001)。具體表現為:男性農民工的自我和諧度高于女性農民工;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農民工的自我和諧度高于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農民工;在二線城市工作的農民工自我和諧度高于在一線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接受初級教育的農民工自我和諧度最高,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工自我和諧度最低。
2.3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與自我和諧的相關
本研究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農民身份認同各維度的得分與自我和諧及其各分量表的得分進行積差相關分析,見表3。

表3 農民身份認同與自我和諧的相關(r)
結果發現,從表3顯示,自我歸類和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自我的靈活性、自我的刻板性呈顯著負相關;身份重要性和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自我的靈活性、自我的刻板性呈顯著負相關;行為投入和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自我的靈活性、自我的刻板性呈顯著負相關。但是,在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問卷中,得分越高,其農民身份度越高;而在自我和諧量表中,得分越低,其自我和諧度越高。因此,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與其自我和諧呈顯著的正相關。
2.4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與自我和諧的回歸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歸分析,以農民身份認同總分及各因子得分為變量預測自我和諧,見表4。

表4 農民身份認同與自我和諧的回歸分析
結果發現,農民身份認同及各因子與自我和諧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對其自我和諧有顯著預測作用。
3 討論
3.1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的狀況
本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存在性別差異,男性農民工在農民身份認同上顯著高于女性農民工。這一研究結果與徐傳新的研究結果一致[3]。我們認為其原因可能在于他們工作性質的差異。男性農民工在城市中多從事體力勞動,如建筑工人等,這與農業生產活動更加類似;而女性農民工更多從事服務類行業,與城市生活聯系更加緊密。因此男性農民工對于其農民身份更加認同。劉連龍等人的研究也發現,男性農民工的心理問題發生率高于女性農民工,這也說明了女性農民工比男性農民工在城市工作過程中適應性更好[19]。
研究還發現,在不同城市工作的新生代農民工的農民身份認同存在差異,在二線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更加認同其農民身份。我們認為原因在于,一線城市生活節奏快,經濟更發達,在這種環境中生活,個體更容易迷失自我。因而,在一線城市工作的農民工對自己的農民身份認同更加模糊。同時,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低的農民工更加認同其農民身份,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農民工群體獲得文字上對城市的認識少,而且他們進城只是為了生活,又因為城市居民的歧視,使得該農民工群體將自己封閉在一個隔離的空間,比起受教育程度高的農民工群體更容易接受農民身份。而受教育程度高的的農民工群體不愿回鄉,希望留在城市發展,因此更加不認同其農民身份[6]。
3.2新生代農民工自我和諧的狀況
本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和諧度存在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收入水平在3000元以上的農民工自我和諧度顯著高于收入水平在3000元以下的農民工,這和王曉一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20]。在二線城市工作的農民工自我和諧度顯著高于在一線城市的農民工。基于以上結論,我們認為原因可能在于兩個方面:①從個人角度來看,農民工外出務工主要是為了養家糊口,改善家庭生活條件,而收入較低會導致他們的經濟壓力、工作壓力變大,由此導致心理調節不適、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②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一線城市生活節奏變快,生活壓力大,與農村生活明顯不同,從而導致了個體的不和諧。
同時本研究還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自我和諧度越低,原因可能在于:企業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與新生代農民工已有的教育存在著差距,而企業和政府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又極其有限。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滿足,從而導致他們的自我不和諧[16]。這樣的不和諧不僅會有害新生代農民工的身心健康,而且有可能引發“民工荒”和危及社會和諧。
3.3新生代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與自我和諧的關系
研究發現,身份認同及其各因子與自我和諧總量表及各分量表得分上呈顯著的正相關。即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的農民身份越認同,他的自我和諧度越高。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農民身份認同及各因子與自我和諧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但農民身份認同及其各因子對自我和諧的解釋量不夠。自我和諧的影響因素有很多,但身份認同及其各因子對自我和諧的影響力度不夠,也就是不能很好地預測自我和諧。基于以上結論,本研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的農民身份認同與其自我和諧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為了進一步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和諧度,我們建議:①政府應予以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政策、法律的保護,使其獲得社會支持。加快城市化建設,進行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融合,促進“農村人”向“城市人”的轉化;②從企業角度看,新生代農民工在企業中往往掌握著基層的技術,因缺乏系統的學習,而不能最大化地發揮作用。因此,企業可以提供深造的機會,為本公司開發人才,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機會。
參考文獻
[1]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J].社會學研究,2001,16(3):63-76
[2]何磊.農民工政策為何難落地?[J].三農中國,2005(7):28-28
[3]許傳新.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及影響因素分析[J].學術探索,2007,15(3):58-62
[4]岳中志,彭程,徐磊.我國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J].西北人口,2011,32(6):96-100
[5]趙雪梅,杜棟.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調查數據[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5(6):38-43
[6]李東坡.農民工身份認同問題研究[J].理論與改革,2013,26(4): 99-101
[7]李虹,倪士光,黃琳妍.流動人口自我身份認同的現狀與政策建議[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71(4):68-74
[8]張瑩瑞,佐斌.社會認同理論及其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06,24(3):475-480
[9]Phinney J S.Ethnic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A review and integration [J].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1991,13(2):193-208
[10]趙志裕,溫靜,譚儉邦.社會認同的基本心理歷程-香港回歸中國的研究范例[J].社會學研究,2005,20(5):202-246
[11]Mark Storm C,Berman R,Brush G.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Jewish adolescents according to context[J]. Journal of Adolesecent,1998,13:202-222
[12]Uma Ia-Taylor A J,Fine M A.Ethnic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among Latino adolescents: Making distinctions among the Latino populations[J].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2002,17:303-327
[13]劉楊,陳舒潔,袁曉嬌,等.父母身份認同促進行為、家庭環境與流動兒童身份認同的關系[J].中國特殊教育,2013,20(7): 64-70
[14]劉俊英.大學生心理和諧研究[J].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綜合版),2010,8(2):36-39
[15]王登峰.自我和諧量表的編制[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994,2 (1):19-22
[16]楊憲華.特困生心理健康及其與自我和諧的關系[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3,21(5):763-764
[17]張雯雯.高中學生自我和諧與壓力源[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4,22(3):434-436
[18]蔡貞,汪玉蘭,畢重增.農民工農民身份認同的結構與測量[J].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6(4):78-81
[19]劉連龍,李瓊,夏蕓,等.西安市農民工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及其影響因素[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2,20(1):61-63
[20]王曉一,李薇,王蕊,等.通信施工人員自我和諧狀況分析[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3,21(2):237-238
·論著·(職業心理)
Identity and Self-harmon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Gao Yadong,Cao Chenggang,Liu Rui,et al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Chongqing 40216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identity and self-harmon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Methods: A total of 219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onducted the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nd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Scale.Results: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sex(t=3.681,P<0.001),the level of income(t=-12.657,P<0.001),the city they work(t=-12.073,P<0. 001)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F=30.121,P<0.001);Self harmon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sex(t=-2.972,P<0.01),income level(t=-13.799,P<0.001),the city they work(t=-14.039,P <0.001)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F=14.756,P<0.001);Self classification and self experience inconsistency and self flexibility,self stereotyp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r=0.19,0.35,0.21;P<0.01);The identity of the importance and the disharmony of self and experience,self flexibility,self stereotyp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r=0.37,0.56,0.45;P<0.001);Behavior of investment and the disharmony of self and experience,self flexibility,self stereotyp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r =0.31,0.60.0.42;P<0.001).Conclusion: The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 harmony.
【Key words】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Identity;Self-harmony;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Questionnaire
收稿時間:(2015-07-02)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危機干預與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研究”(編號: 11XRK003);重慶文理學院資助項目(編號: R2012JY24)
doi:10.13342/j.cnki.cjhp.2016.01.008
中圖分類號:C912.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1252(2016)01-00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