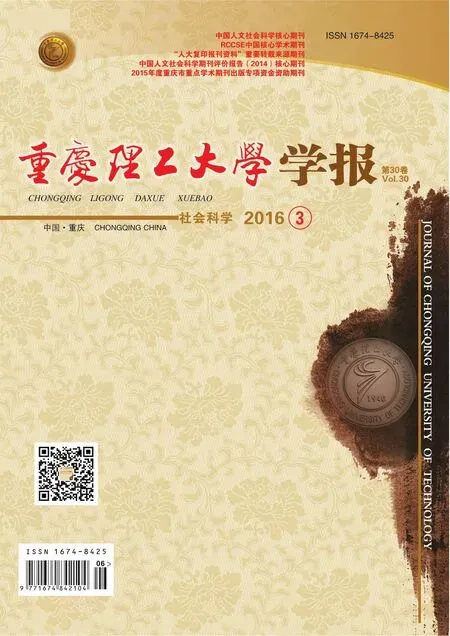論定罪與量刑之關系——以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為視角
譚金生
(1.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2.重慶市人民檢察院,重慶 401147)
?
論定罪與量刑之關系
——以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為視角
譚金生1,2
(1.西南政法大學,重慶401120; 2.重慶市人民檢察院,重慶401147)
摘要:我國量刑問題經歷了從以實體法為主到以程序法為主的發展過程。美國量刑指南建立在定罪與量刑之關系十分清晰的基礎上。不廓清定罪與量刑之關系,強推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效果必然不理想。從刑罰具有的懲罰和教育的功能角度,可以劃清定罪與量刑之關系,懲罰功能通過定罪決定報應刑量來實現,教育功能通過量刑決定宣告刑量來實現。各罪報應刑量應由最高司法機關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適時發布司法解釋來確定。
關鍵詞:定罪;量刑;關系;程序;獨立化
當前,我國解決量刑問題的路徑是以量刑程序獨立化來規范自由裁量權。但是,刑事審判程序主要是圍繞定罪設計的,對量刑程序沒有專門規定。司法實務中,量刑由法官通過辦公室作業方式完成,其他各方被排除在程序之外。這種模式不僅給自由裁量權留下了足夠的濫用空間,而且給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留下了質疑的空間,加之媒體曝光了“同罪不同罰”等現象的佐證,量刑問題逐漸凸顯。最高法院在第二和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中先后提出“健全和完善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規范自由裁量權,將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全面展開。就目前而言,改革已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在解決量刑失衡問題上還任重而道遠。受美國量刑指南啟發設計的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忽略了一個重要前提——定罪與量刑關系十分清晰,而我國主流觀點認為定罪與量刑存在交叉重合關系。有學者從程序法角度論述了定罪與量刑之關系,提出構建專門量刑聽證程序[1]。但是,如果不能廓清定罪與量刑之實體關系,構建“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將會變得較為困難。基于此,本文從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角度,通過分析量刑問題的由來,力圖理清并重構定罪與量刑之間的關系。
一、量刑問題的由來
量刑問題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底至20世紀末,主要針對法定刑過重,以實體法為主;第二階段自21世紀初至今,主要針對宣告刑失衡,以程序法為主。
(一)第一階段:以實體法為主
1979年底,中央決定開展城市治安整頓和打擊刑事犯罪活動。隨后,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從勞動改造、勞動教養場所逃跑或者期滿釋放后繼續犯罪,屢教不改”問題,通過了《關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針對“當前走私、套匯、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盜竊公共財物、盜賣珍貴文物和索賄受賄等經濟犯罪活動猖獗”問題,通過了《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但是整頓活動并未有效遏制犯罪高發態勢。1980年、1981年全國刑事立案數分別同比上升19%和17.6%。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突出,1981年同比猛增57%。1982年,全國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犯罪案件74萬余起,其中大案6.4萬起[2]。1983年8月25日,中央出臺《關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進一步強化了打擊嚴重經濟犯罪和危害社會治安犯罪力度;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將殺人、強奸、搶劫、爆炸、流氓、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拐賣人口、傳授犯罪方法等犯罪確定為打擊重點,并將一些經濟犯罪最高法定刑提高到死刑,新中國第一次“嚴打”*一般認為,“嚴打”是指中國大陸地區的一連串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運動的簡稱。正式啟動。1996年、2001年又先后啟動兩輪“嚴打”。2004年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逐步取代“嚴打”提法。
“嚴打”的顯著特征是“重典嚴刑”,體現為大幅提高常見犯罪最高法定刑,死刑和無期徒刑適用范圍顯著擴大。如根據1979年《刑法》第185條規定,受賄罪最高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將該罪最高法定刑提高到死刑;盜竊罪最高法定刑由無期徒刑提高到死刑。司法實務中發生了不少“偷一元錢判死刑”“流氓罪判死刑”等極端案件。1983年9月17日,朱德之孫朱國華因犯流氓罪,被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公開宣判死刑,并當場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嚴打”雖然暫時穩定了社會秩序,但是不利于國家長治久安,尤其與廢除死刑、以自由刑為中心的刑罰改革、非犯罪化的世界各國刑法發展趨勢不符。一些學者高度關注該問題,并主張改革重刑主義刑罰結構,實現刑罰制度現代化。20世紀80年代,儲槐植認為1979年頒布的《刑法》總體結構“厲而不嚴”[3],即刑罰苛厲而法網不嚴密,1997年修改后也未改變這種結構[4]。 從實務層面看,“嚴打”不僅體現實體法上“從重”,還體現程序法上“從快”。但是學界主要關注的還是實體法問題,核心是解決“重典”——法定刑過重問題。
(二)第二階段:以程序法為主
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經過20余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利益格局顯著變化,長期累積的收入分配、社會管理、官員腐敗等矛盾日趨尖銳,并以信訪形式集中表現出來。全國信訪總量從1992年起,經歷11年持續攀升后,在2003年形成信訪洪峰。2003年全國黨政機關信訪量高達1 272.3萬人(件),同比上升4.1%;中央黨政機關信訪量同比上升46%。集體信訪現象突出,全國黨政機關接待集體信訪31.5萬批次、712萬人次,分別同比上升41%和44.8%,50人以上集體信訪批次和人次分別同比上升33.3%和39%,單批次集體信訪人數高達800余人,創單批次進京信訪人數最高記錄[5]。此外,全國多地爆發嚴重群體性事件,如貴州甕安、廣東烏坎等。進入21世紀,信訪發生顯著變化:隨著沖擊司法公信力案件的曝光,涉法涉訴*涉法涉訴信訪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國家最高司法機關也沒有形成統一標準,一般指司法訴訟類信訪案件。案件進入公眾視野。盡管最高司法機關對涉法涉訴沒有統一口徑,但通過對比其歷年工作報告中有關數據,可以看出問題之嚴重。2005年,全國法院辦結案件794萬余件,辦理信訪404萬余件(人)次;2003—2007年,全國法院審理案件3 180萬余件,辦理信訪1 947萬余件。2003年,全國檢察機關偵辦職務犯罪、逮捕嫌疑人、提起公訴162萬余人,受理信訪52萬余件;2003—2007年,全國檢察機關偵辦職務犯罪、逮捕嫌疑人、提起公訴913萬余人,受理信訪150萬余件*全國法院及檢察機關各年度辦案及信訪數據均來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年度工作報告。。能否妥善處理涉法涉訴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繞不開的坎。
隨著“同罪不同罰”等問題案件的曝光,作為涉法涉訴重要組成部分的量刑問題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當然,要提供有說服力的數據很困難:一方面司法機關對涉法涉訴認識不統一,統計口徑不一致;另一方面司法機關一般不對涉法涉訴作進一步分類,即便分類也不宜公開。但是,從媒體曝光的案件及社會反應*目前,社會公眾對量刑失衡現象的直觀反應是司法腐敗。看,基本可以看出量刑問題的嚴重性。譬如廣東“許霆案”*2006年4月21日,許霆到天河區黃埔大道某銀行ATM取款機取出1 000元后,發現其銀行賬戶只被扣了1元,于是連續取款5.4萬元。隨后,又會同郭安山以同樣手段再次取款。經查實,許霆共取款17.5萬元,郭安山取款1.8萬元。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并全額退還贓款1.8萬元。經審理,天河區法院認定郭安山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1 000元。許霆潛逃一年后被抓獲,17.5萬元贓款揮霍一空,廣州市中院認定許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構成盜竊罪,判處無期徒刑。此案經媒體曝光,引起社會各界嘩然,輿論一邊倒地認為量刑過重。2008年3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回重審,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改判有期徒刑5年。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在輿論壓力下改判5年有期徒刑,量刑反差巨大引發各界熱議。再如同為交通肇事逃逸罪,北京“張建案”*2005年11月10日22時許,張建駕駛紅色寶馬牌轎車,由西向東行駛至北京朝陽區朝陽北路黃渠村人行橫道處,將騎摩托車由南向北橫過馬路的孫某撞倒后駕車逃離現場。孫某因顱腦損傷,搶救無效于次日死亡。張建為逃避抓捕,將紅色寶馬車車身顏色改成白色。2006年1月17日,張建被抓獲歸案。經警方認定,張建負全部責任。朝陽區法院認為,張建構成交通肇事罪。鑒于張建當庭自愿認罪,有一定的悔罪表現,其家屬積極幫助賠償被害人家屬的經濟損失,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致一人死亡,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海南“盛進案”*2006年1月1日,海南國信控股集團總經理盛進駕駛假冒軍牌小轎車,在海口市濱海大道撞飛一輛摩托車,摩托車后載有趙月金、張成蓮及他們8歲的兒子,造成兩死兩傷。事故發生后,盛進駕車逃逸。迫于警方晝夜巡查壓力,盛進于次日向海口市交巡警支隊投案。經警方認定,盛進負事故全部責任。海口市龍華區法院認為,盛進構成交通肇事罪,鑒于其能主動投案并如實交代犯罪事實,且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致二死二傷,反而輕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又如職務犯罪量刑偏輕、緩刑率過高等現象也引發了人們對司法腐敗的懷疑。2003—2005年,職務犯罪年均緩刑率51.5%,遠高于普通犯罪19.4%[6]。人們關注的量刑問題已不再是法定刑的輕重而是量刑的公正與否,而量刑公正與否關鍵在于程序是否透明。因此,一些地方率先開展量刑規范化試驗,最高人民法院加以總結后在全國推廣。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提出:“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制定故意殺人、搶劫、故意傷害、毒品等犯罪適用死刑的指導意見,確保死刑正確適用。研究制定關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并健全和完善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一些地方進一步細化規范量刑的具體措施,例如浙江桐鄉市出臺《刑事審判量刑指導意見》,山東淄博市淄川區推出電腦量刑軟件。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提出“規范自由裁量權,將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研究制定《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導意見》”。2010年,兩高三部發布《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進一步落實量刑程序獨立化構想;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發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從量刑的指導原則、基本方法、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和常見犯罪的量刑等方面作了專門規定。
學界也高度關注量刑問題,研究重點從刑罰結構轉移到量刑程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刑罰結構是立法問題,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兼矛盾多發期,且“刑法權(刑罰權)膨脹是我國刑法傳統的最基本特征”[4],根本改變立法重刑主義、實現刑法“萎縮”在短期內難以實現;二是社會公眾主要關注量刑不均衡問題,特別是對濫用自由裁量權的防范,以及司法權對腐敗“偏袒”的可能;三是確實存在因法律規定不明確而導致程序不透明所造成的量刑失衡問題,該類問題亟待清理解決。受西方新實證主義法學影響,有學者對罪刑均衡問題進行了實證考察。白建軍以“罪刑關系具有均衡性”為理論假設,對422個犯罪及1 107個搶劫案例的罪刑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引發學界對罪刑關系及量刑問題的廣泛關注[7]。此外,有學者提出從程序法角度來研究量刑問題。譬如陳衛東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對量刑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于刑事實體法領域,沒有將其納入到訴訟程序的軌道中思考。事實上,作為刑事訴訟程序重要構成內容的量刑問題并不僅限于實體上的問題,我們還應當關注量刑程序的公正問題。通過公正的程序來保障量刑的合理性可以說是深化刑事審判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8]。又如陳瑞華提出了量刑程序獨立化,基本上與兩高三部發布的《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該意見第1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應當保障量刑活動的相對獨立性。”保持一致立場。對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量刑程序獨立化,學界還有不同意見。陳瑞華贊同最高司法機關主張——“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內容有二:一是確保量刑程序獨立,將其從定罪程序中分離;二是量刑程序相對獨立,與定罪程序處于交錯狀態,不走向完全獨立[9]。
二、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成效
(一)改革成效不顯著
考察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成效可以從司法實務和學界研究兩個角度進行。
從司法實務看,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自2009年起,連續6年簡單提及量刑。2009—2014年分別表述為“推行案例指導制度,開展量刑規范試點,統一裁判標準”;“嚴格規范法官裁量權,推進量刑制度改革,促進量刑公平公正”;“全面推行量刑規范化改革,制定量刑程序規則,確立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量刑方法,規范法官裁量權,促進量刑公平公正”;“全面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規范量刑程序,完善量刑方法,促進量刑公正”;“推進刑事司法改革,完善刑事證據制度,實現量刑規范化”;“推進量刑規范化工作,制定關于常見犯罪量刑指導意見,促進量刑公開透明、公平公正”。上述表述雖略有差異,但仍能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對量刑規范化改革的持續性要求。值得一提的是,除表明主要工作包括量刑規范化外,工作報告中卻未提及改革成效。原因大概有二:一是量刑規范化的核心是“規范法官裁量權”,但如何判斷“法官裁量權”是否得到“規范”沒有可操作性標準;二是量刑規范化改革的直接動因是涉法涉訴,理應以涉法涉訴形勢是否好轉作為判斷標準,但涉法涉訴相關數據一般不適合公開。與最高人民法院相反,地方法院則大力宣傳了改革成績。譬如《云南日報》報道,云南省法院2011年一季度刑事二審收案率同比下降4.95%,刑事再審收案率同比下降58.62%[10]。
從學界研究情況看,大家對量刑規范化改革成效有不同看法,而且與地方司法機關的宣傳存在不小的反差。左衛民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對抗化取向的量刑程序改革不盡如人意”:一是控辯雙方提出的量刑情節和量刑證據沒有明顯增加;二是改革前后量刑效果差異不大,上訴率和抗訴率沒有明顯下降,反而單純量刑方面的上訴率上升;三是量刑成本增加,審判效率下降,法官、檢察官工作量明顯增加,庭審平均時間延長近1/3[11]。針對左衛民的觀點,熊秋紅表達了一些缺乏證據支撐的“直觀認識”[12],既有如量刑程序改革有助于審判的實質化以及加強審與判之間的邏輯聯系、量刑調查和辯論的作用較為明顯、量刑說理有助于加強裁判的可接受性等積極方面的,也有如庭審中控辯雙方爭議焦點不突出、被告人因無力自我辯護使訴訟參與流于形式、在被告人不認罪案件中律師從無罪辯護到量刑辯護的轉化存在明顯尷尬、起訴書包含被告人的前科信息有可能使法官形成有罪預斷、定罪事實與量刑事實難以分離造成重復評價、法官量刑事實和證據難以查明和評判等消極方面的。最后,她建議“量刑規范化改革是我國刑事法律制度改革和完善的過程中出現的新生事物,其實際效果尚待通過廣泛和深入的實證研究予以準確評估”。比較而言,左衛民的結論似乎更有說服力。對改革成效到底如何存在爭議,也說明成效確實不顯著,沒有達到預期。
(二)原因分析
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成效為何不顯著?左衛民認為不該把量刑程序不公當作量刑不均衡的主要問題,雖然“某些情況中,量刑不均衡可能由量刑程序不公所致,但總體上,量刑不均衡和量刑僵化反映的主要不是程序法問題,而是實體法問題”,因此“當前量刑模式存在的問題主要不是程序法問題而是實體法問題的情況下用程序法的改革手段去解決實體法問題,顯然不對路”,并主張“以實體法改革為主,程序性改革為輔”[11]。改革之前,量刑由法官通過“辦公室作業”方式完成,顯然不合常理,當事人難服判。把量刑納入庭審程序,讓裁量權在陽光下運作合情合理。至于量刑問題到底是程序法還是實體法問題,主要取決于考察問題的角度:如果認為量刑不均衡由法定刑幅度過大造成,那么就是實體法問題;如果認為量刑不均衡由程序不公造成,那么就是程序法問題。事實上,造成量刑不均衡的原因既包括因法定刑幅度過寬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又包括刑事訴訟法缺少量刑程序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權運作不透明,這些問題都難以讓當事人和公眾相信量刑結果公正。量刑問題既是程序法問題也是實體法問題,很難分清誰是主要原因。另外,實體法和程序法盡管邏輯關系清楚,但是在實務中容易變得模糊不清。改革成效不顯著的原因不在于量刑問題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問題,而在于忽略了美國量刑程序的前提:定罪與量刑關系非常清晰,反觀我國對兩者關系除哲學和邏輯上的解析外,還沒有從內容角度劃分各自范圍,兩者仍然處于相互交織狀態。其實,有學者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認為“定罪事實與量刑事實有時難以分離,容易形成重復評價”[12],卻被當作構建“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的理由。事實上,即便建立“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也無法回避這個問題。
從《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看,定罪與量刑的界限明顯地存在模糊:首先,從“量刑的指導原則”看,第1項規定中的“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全部屬定罪范圍;第2項規定中的“罪行的輕重”也屬定罪范圍,而“懲罰和預防犯罪的目的”是刑罰的功能;第3、4項分別規定了要求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實現“同案同判”問題,這才是量刑原則。其次,從“量刑的基本方法”看,主要內容是如何確定基準刑,即根據“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實”確定,這也屬定罪范圍。第三,從“常見犯罪的量刑”看,全部是對法定刑幅度的進一步“限縮”,是對刑法分則規定的修正。如交通肇事罪,按照《刑法》第133條規定的3個法定刑幅度,分別進一步縮小了確定量刑起點的范圍,從“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分別限縮到“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和“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這既無法解決量刑起點問題,還可能涉嫌違法違憲。第三部分“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才基本屬量刑范圍。定罪與量刑之關系如此“親密”,怎能實現量刑程序獨立化,怎能不影響辦案效率?
三、定罪與量刑之關系重構
(一)定罪與量刑之關系通說
對定罪與量刑之關系,通說認為:一是“定罪是量刑的前提與基礎,量刑則往往是決定具體犯罪的法律后果”;二是“定罪正確并不等于量刑適當”,因為定罪和量刑遵循的原則和標準不同[13]。這表明定罪與量刑在程序上具有先后性,符合形式邏輯。在定罪與量刑程序合一模式中基本看不出有什么矛盾,但是在定罪與量刑程序分離模式中矛盾必然凸現,因為程序分離模式要求廓清定罪與量刑之界限,而通說僅從程序上進行邏輯構建,對實體關系則未有效廓清。事實上,正因為最高人民法院沒有廓清定罪與量刑之關系,貿然推行定罪與量刑程序分離模式,導致審判效率下降。另外,我國判決書說理性歷來薄弱,量刑部分說理更是闕如,當事人意見得不到有效回應,上訴率、申訴率必然高。前些年,涉法涉訴形勢日趨嚴峻,最高司法機關推行加強法律文書說理活動,以期實現“案結事了”,結果有些說理存在邏輯或用語問題,反而導致更多信訪。有學者受“許霆案”等量刑失衡案例啟發,提出“以刑制罪”觀點,企圖打破“定罪決定量刑、量刑不可能影響罪名”的“刑法公理”[14]。其實所謂“以刑制罪”就是倒果為因,邏輯上很難說得通,不符合司法規律。判斷量刑是否畸輕畸重,是在定罪基礎上劃定相應法定刑之后。量刑程序改革前,已有學者注意到定罪與量刑之關系問題。李潔指出定罪情節與量刑情節“在功能上具有交叉重合的關系,即一個情節在某種情況下既是定罪情節又是量刑情節”[15]。趙廷光認為兩者涇渭分明,但并未跳出交叉重合關系的圈子[16]。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構建“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原因在此,學界因為無法劃清定罪與量刑的界限不得不予以附和。問題在于,如果不廓清定罪與量刑之關系,就算構建“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也很困難。
(二)定罪與量刑之關系重構
在量刑程序獨立化語境下,如何劃清定罪與量刑之界限?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應先弄清定罪與量刑交叉重合關系是什么。李潔認為“交叉”體現為:一是行為事實既決定定罪又決定量刑,二是在一定情況下量刑情節通過可罰性可以對定罪起作用;“重合”體現在“某種事實既是定罪情節,又是量刑情節的情況”,如未遂既屬定罪情節又屬量刑情節[15]。交叉重合關系就是“一情節可以一身二任”。以“李昌奎案”為例,李昌奎強奸王家飛并殺害其姐弟倆的事實,是認定構成強奸罪和故意殺人罪的根據,而據此認定其“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等則是裁量死刑的具體情節。在此,同一事實既為定罪情節又為量刑情節。為解開交叉重合關系,趙廷光主張把“定罪剩余的犯罪構成事實轉化為量刑情節”[17],如某地規定盜竊罪“數額較大”的標準是1 000元至1萬元之間,首先拿出1 000元作為定罪情節,余額轉化為確定具體刑量的情節,這個辦法并未擺脫兩者實務操作上的交叉重合關系。
其實,從刑罰的功能角度可以劃清定罪與量刑之關系。刑罰的功能“是指國家制定、裁量和執行刑罰對人們可能產生的積極作用”[18]。對犯罪人而言,刑罰的功能體現在懲罰和教育兩方面。懲罰功能源于報應主義,表現為剝奪犯罪人的財產、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等基本權利,使受刑者感受到痛苦。教育功能則源于功利主義,表現為把犯罪人當作病人一樣進行教育改造,使其成為無害于社會的人。懲罰是報應實在之惡,教育是預防未來之惡。從刑罰功能角度,可以把刑罰分成兩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是基于報應目的的法定刑;二是基于教育目的的宣告刑。法定刑由定罪直接決定,即一旦確定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犯罪構成,其相應法定刑也就確定了,法官只能接受而不能拒絕;宣告刑由法官根據個案具體情節,在定罪確定的法定刑基礎上,為實現教育目的而進行加減之后所得結果。法定刑是由刑法直接規定,法官只能接受而不能自由裁量,從概念體系明確性出發,應排除在量刑范圍之外。這個辦法的最大困擾是刑法規定的法定刑是“幅”而不是“點”,剝奪法官根據個案在法定刑幅度內確定具體刑罰“點”的行為,看似違背了符合同一犯罪構成的不同個案在社會危害性程度上有差別的常識。從司法實務看,確實存在符合同一犯罪構成的不同個案在社會危害性程度上看似有差別的現象,國家工作人員甲和乙分別貪污100萬元和200萬元,乙的社會危害性好像大于甲,但是,從《刑法》立法設計看,這種社會危害性差別可以忽略不計。
首先,從《刑法》第13條看,犯罪包含罪質和罪量兩個因素[19],符合同一犯罪構成的犯罪,其罪量應該大致相當,或者說沒有再進一步區分的必要,當然也就無需再進一步裁量具體報應刑量。上述案例中甲和乙在其他犯罪情節相同的情況下分別貪污100萬元和200萬元,都符合《刑法》第383條第一款規定,均應在“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這個幅度內確定相同的報應刑量,要么均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要么均判無期徒刑,因為他們的罪量相當。其次,根據犯罪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同,《刑法》對多數犯罪規定了幾個犯罪構成,并配置相應法定刑,進一步說明立法者已考慮到罪量與刑量對應關系,無需裁量其報應刑量。反之,如果允許法官根據社會危害性程度裁量個案報應刑量,那么《刑法》根本無須設置多個犯罪構成。如《刑法》第264條根據“數額較大”“數額巨大”和“數額特別巨大”為盜竊罪設置了3個犯罪構成及法定刑。如果盜竊數額等犯罪情形符合相同的犯罪構成,那么就應認定其罪量相當,在法定刑幅度內任何一點都是其報應刑量。另外,大量案例證明,由法官根據社會危害性程度來裁量個案報應刑量既不可能又易導致“同罪不同罰”等量刑失衡問題。為何不可能?因為符合同一犯罪構成的具體犯罪情況千差萬別,且絕大多數情況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如怎么區分《刑法》第264條規定的“數額較大”與“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誰的社會危害性更大?即便是數額犯,也難以精確區分社會危害性程度。上述案例甲和乙分別貪污100萬元和200萬元,均符合《刑法》第383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能分清甲和乙誰的社會危害性更大嗎?更重要的是由法官根據社會危害性程度來裁量個案報應刑量容易導致“同罪不同罰”等量刑失衡問題,損害司法公信力,“中國當下更需要的可能是一種克制主義司法哲學,一種司法克制性而不是能動性”[20]。昆明鐵路局原局長聞清良收受賄賂2千余萬元,一審被判處死緩。上訴后,聞清良當庭質問法官“受賄3千多萬元的才判無期,為什么判我死刑?”就案情看,聞清良收受賄賂2千余萬元,如果不存在“情節特別嚴重”,那么判處死緩就違法。
既然法定刑是立法者規定各犯罪的報應刑量,那為何又要以“幅”而不是“點”的形式規定?確實,《刑法》除了對極個別犯罪規定了絕對法定刑外,對其他犯罪均規定了相對確定的法定刑,而相對確定的法定刑是以“幅”的形式存在,一旦剝奪法官根據具體個案在法定刑幅度內確定刑罰“點”的權力,將出現個案無法確定報應刑量的困局。立法以“幅”的形式規定法定刑是基于兩個客觀需要:一是基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需要。社會治安形勢總是呈現“治亂”交替狀態,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兼矛盾多發期,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恰當運用刑罰維護社會治安是必要的,立法者以“幅”的形式規定法定刑使刑法保持適度彈性,就是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留下發揮作用的空間,同時又保持了刑法的相對穩定性。具體說,可以由最高司法機關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規定適時司法解釋,在《刑法》分則規定的法定刑幅度之內確定各罪的報應刑量,其好處在于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同罪不同罰”問題,有利于增強社會公眾的預測可能性,化解其對司法公正的懷疑。二是基于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的需要。罪刑法定原則是在反對罪刑擅斷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法院裁量刑罰必須遵循這一原則。《刑法》以“幅”的形式規定法定刑,就是為了防止法官在刑罰裁量上的擅斷,這也是《刑法》明確規定量刑情節適用規則的原因。具體說,就是為法官適用各種量刑情節劃定權力邊界。當然,法官在邊界范圍內仍有廣泛的自由空間,需要立法進一步明確量刑規則,目前《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事實上已在發揮著這個功能。
如上分析,從刑罰的懲罰和教育功能角度,基本能夠廓清定罪與量刑間的交叉重疊關系,從而為量刑程序獨立化掃清障礙。基于此,定罪指法院依法判斷某具體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是否一致的刑事司法活動,其內容包括一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4方面特征:一是定罪主體是法院,其他任何機關均無定罪權;二是定罪內容是判斷某具體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是否一致,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既包括基本犯罪構成,又包括修正犯罪構成,因為犯罪是罪質和罪量的統一體;三是定罪目的是實現刑罰報應功能;四是定罪的性質是一種刑事司法活動。量刑指法院在確認某具體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之后,在確定的報應刑量基礎之上根據法定從輕、從重等情節進行加減并確定宣告刑的刑事司法活動。具有4方面的特征:一是量刑主體是法院,其他任何機關均無裁量刑罰之權;二是量刑內容是在定罪確定的報應刑量基礎之上根據從輕、從重等情節進行加減并確定宣告刑,與犯罪構成有關的一切“事實”或“情節”均屬定罪范圍,而量刑所依據的“事實”或“情節”僅與刑罰教育功能相關;三是量刑目的是實現刑法教育功能;四是量刑的性質是一種刑事司法活動。通過定罪與量刑之間的功能差別,基本可以解決“一情節可以一身二任”的問題,而且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好“同罪不同罰”問題。當然,要從刑罰功能角度劃清定罪與量刑之間的界限,還必須由最高司法機關通過司法解釋在法定刑幅度內確定各犯罪的具體報應刑量。
參考文獻:
[1]陳瑞華.定罪與量刑的程序分離——中國刑事審判制度改革的另一種思路[J].法學,2008(6):40-50.
[2]陶盈.1983年“嚴打”: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J].文史參考,2010(20):30-31.
[3]儲槐植.嚴而不厲:為刑法修訂設計政策思想[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6):99-107.
[4]儲槐植.議論刑法現代化[J].中外法學,2000(5):584-595.
[5]于建嶸.中國信訪制度的困境和出路[J].戰略與管理,2009(1/2):29-45.
[6]王軍.三項對策遏制職務犯罪量刑偏輕[N].檢察日報,2007-08-19.
[7]白建軍.罪刑均衡實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64.
[8]陳衛東.定罪與量刑程序分離之辯[N].法制日報,2008-07-27.
[9]陳瑞華.論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中國量刑程序的理論解讀[J].中國刑事雜志,2011(2):3-14.
[10]張雪飛.我省試行量刑規范化——讓陽光照遍量刑全過程[N].云南日報,2011-09-08(9).
[11]左衛民.中國量刑程序改革:誤區與正道——基于比較與實證研究的反思[J].法學研究,2010(4):150-152.
[12]熊秋紅.中國量刑改革:理論、規范與經驗[J].法學家,2011(5):37-53.
[13]趙秉志.刑法學總論研究述評(1978—2008)[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523.
[14]高艷東.量刑與定罪互動論:為了量刑公正可變換罪名[J].現代法學,2009(5):164-174.
[15]李潔.定罪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研究[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1):16-21.
[16]趙廷光.定罪與量刑:兩種情節涇渭分明[N].檢察日報,2004-11-03.
[17]趙廷光.論定罪剩余的犯罪構成事實轉化為量刑情節[J].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05(1):5-10.
[18]馬克昌.刑罰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18.
[19]陳興良.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國刑法的探討[J].環球法律評論,2003(12):275-280.
[20]李可.也許正在發生?——對司法能動性已在中國發生的質疑[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3(7):55-58.
(責任編輯何培育)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with Independent Sentencing Procedure Reform Perspective
TAN Jin-sheng1,2
(1.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1147, China)
Abstract:Chinese sentencing problems have been experienced a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substantive law priority to procedure law priority. America sentencing guidelines is estabished on the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Without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and that the state supreme judicial organs promote the reform of independent sentencing procedure,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effect of sentencing procedure reform is not unsatisfying. We can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victions and sentencing clearly from the view that penalty has two functions of punishment and education, among which the punishment function of penalt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conviction to decide the amount of retribution punishment, and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penalty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sentencing decision to decide the amount of declaration punishment. The amount of retribution punishment of every crime shall be made by the state supreme judicial organ according to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Key words:conviction; sentencing; relationship; procedure; independence
中圖分類號:D9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8425(2016)03-0090-08
作者簡介:譚金生(1975—),男,湖南安仁人,檢察員,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國家賠償制度。
收稿日期:2015-07-20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6.03.015
引用格式:譚金生.論定罪與量刑之關系——以量刑程序獨立化改革為視角[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6(3):90-97.
Citation format:TAN Jin-sheng.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with Independent Sentencing Procedure Reform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9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