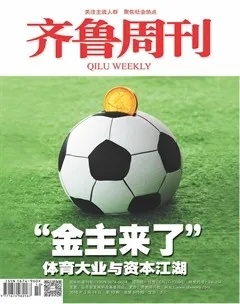“口香糖”一樣的鄉愁
人們在反復販賣故鄉的過程里,不斷的咀嚼“鄉愁”,最終像是失掉了味道的“口香糖”,吐出來也非常難堪。
小鎮青年是上了釉的“毛坯”
在賈樟柯的電影《小武》里,小武駐足小鎮,迎風吹來一臉的黃土,讓他原本亂糟糟的頭發更像荒野里的雜草,一身并不合身的西裝被四散的吹開紐扣,大幅的黑框眼鏡不沾黃土也顯得灰蒙。那是一九八幾年,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正鉆過古城樓,顛顛簸簸的進入小鎮,嘈雜的人聲中,只有小武在街頭落寞。
最近復又翻看這部老電影,小武的小鎮青年形象雖不合時宜卻也熨帖人心。與其說與小武同處電影里的人們難以理解小武,不如說他們根本顧不上去盤問小武,所有的人都在時代的列車里往前跑,發財、娶媳婦,尋思自己的事。
這讓我憶起一年回一次故鄉的春節故事。我們家的姊妹都讀書到了城市,之后在城市居停。每年的聚會上,總是寒暄,沒有人敢去碰觸,你在你的城市活得怎樣?
帶回故鄉的是某一部分的自己,而“城市里的自己”被留在了城市。我的三姐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年在廣州見到了同村的張芳,她穿高跟鞋、化妝、開車來接我,在外企上班的她儼然已經不是村子里穿棉襖的小芳,我與小芳的見面既客氣又局促,互相寒暄著到了住所,等到小芳用家鄉話開聊,我才把客氣的心放回去,親切的攀談起來。但始終也沒有說到心里的問題。”
“你想問什么問題?”我問三姐,她想了想,“也沒什么,大概就是在廣州想老家嗎?覺得廣州好不好之類的。”
我知道三姐也很難形容那個問題,如同我每年不愿意參加小學聚會一樣,大家團坐在一起,聊了孩子聊工作,聊見識聊八卦,卻從來沒有談到內心。
或許只有在深夜里,自己輾轉反側時才會吐露真實。“不合時宜”的存在是賈樟柯通過電影《小武》傳達出來的“小鎮青年”的生存意向,而今天,所有的人奔赴了城市,不知在城市里,是否有過不合時宜的片刻?或者一直以不合時宜活著?
這一切,像極了電影《世界》里,女人打電話告訴男人她在埃菲爾鐵塔前,而其實那座埃菲爾鐵塔不在巴黎,而在游樂園的某個角落。
?
你的城市非你的城市,你的故鄉也非你的故鄉
前年五一節,我一個人去爬村子西面的山。從家出門往西,經過一片麥田,五月里,麥苗正油綠,風吹過來,想起了小時候在田野里撒歡的日子。從父輩弓腰耕種開始,我們被一遍遍告誡要好好讀書,離開“勞苦”日子,到城市里,住樓房、開汽車,過“體面”的生活。
鄉村經過了記憶中的翻炒,如今看到的是新秩序。老人和婦女在家種田,男人在外打工,更多的青年人成了一年一歸的“候鳥”,變成了遷徙到城市里的“新居民”。從故鄉出走后,失去的往往不是根一般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秩序”,“我們被教導讀好書去城市里出人頭地的同時,也被教導著忘記故鄉。”
反過來思考,我們的故鄉還是我們的故鄉嗎?
那年爬山經過麥田后走到“石鼓鑼”,想起了爺爺講的故事,“傳說泰山老奶奶曾經在此留宿,你看石頭槽是用來拴馬的,而旁邊的石枕頭是泰山老奶奶用來睡覺的。一個個三角狀的凹陷,便是泰山老奶奶的小腳印。”兒時我常同小伙伴在石鼓鑼一起玩耍,在爺爺的傳說中,那些石頭因為敲上去像鼓鑼一樣發聲,故得名“石鼓鑼”。不過10歲那年,來了一群地質科考隊,對著大石頭一陣狂轟亂炸,發現其內里是花崗巖結構,也沒什么特別的寶貝,一群人留下一堆石頭灘,一走了之。
故鄉的傳說像是故鄉的一本老“祖譜”,記錄的是這個村子里曾經與天與自然共存中的一些故事,然而在我們背井離鄉后,這樣的“族系”被連根拔起,后來我們開始忙著成為一個新的城市人,從內到外進行了革新。 “在失去與故鄉的某一種約定俗成后,漸漸失去了打開故鄉的鑰匙,傳說算是其中一把。”
“他們不屬于城市,因為他們在城市里找不到位置;也不再屬于農村,因為經過了城市文明的熏陶,他們已經不習慣傳統的農耕生活;而是在城市和農村中間一個特殊的漂移的群體,在心理上缺少歸屬感、穩定感和安全感。”美國《新聞周刊》對背井離鄉的中國“小鎮青年”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作過這樣的描述。
春節過后,更多的媒體在追問春節回鄉雜想,追問何為故鄉?或許應該從物化的記憶中尋找故鄉:
離開祖輩的墳墓
離開父輩耕種的土地
離開母親的溫柔懷抱
離開家里的老樹
離開奶奶的皺紋
離開爺爺的茶
離開左鄰右舍的歡聲笑語
離開院子,離開板凳,離開小河,離開山……
故鄉成了荒誕的存在,精神的“圍城”
在我的老家,很多的哥哥姐姐們都舉家搬到了城市,在那里租屋陪伴孩子讀城市里的學校,“為了給孩子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教育資源。”他們大都這樣認為。在當今年代里,農村與城市的鴻溝正在漸漸消失,新進城主義倡導的是為下一代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農村正在城鎮化。
這正在制造一群“不合時宜”的城鎮人。我表姐在19歲時跟著鄰村的一個男青年跑到了海邊的一個城市,被家里人五花大綁捆回老家后,嫁給了另一個農村青年,婚后倆人又到了那個海邊城市打工。表姐夫在那里蹬人力三輪車,表姐在工廠上工。幾年后,他們又回到了農村,表姐在家生孩子、種地,表姐夫繼續出外打工。
去年回鄉看到已近40歲的表姐,她還是很惦念曾經打工的城市,只是嘆息道:“我們農村人,最終還是得回來,在大城市連房子都沒有。”
曾經寫出《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的作家梁鴻,在年初出版了第三本書寫農村故事的《神圣家族》。“對于那些從外面又回到鄉村的人來說,城鎮卻是最好的選擇。”梁鴻認為這不是他們自愿選擇的,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現在所有的資源都傾向于城市,誰不愿留在城里呢?”
而為什么還屢屢有人說起鄉愁?梁鴻說,“當我們在談鄉愁的時候,都把它作為一個感性的概念,一種情緒的表達,好像之前有個桃花源在等著我們,而我們把它破壞掉了。其實鄉愁是一個最普通的概念,每個離開家的人都有這種感覺。這個詞被敘述了很多遍,已經沒有價值可言。”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故鄉”成了荒誕的意向,在精神上捆綁著人們。梁鴻在其中一篇《到第二條去游泳》中,對城鎮化的農村的荒誕做了這樣的表達:“我當時寫的時候,就是回到家鄉看到那兩條河,從高空俯瞰,像一個巨大的十字架一樣,不過我沒寫出來這種感覺,真是很有象征意味的。豎的是那條水泥河,是整齊威嚴的,橫著那條河讓人感到是萎縮的、凌亂的、被遺棄的,像一個被遺棄的老婦一樣。”
賈樟柯在自述里也說:“我必須回我老家那個山。縣城生活非常有誘惑力,讓人有充沛的時間去感受生活的樂趣。比如說整條街的小商販都是你的朋友。修鑰匙的,釘鞋的,裁縫,你都認識。人處在熱烈的人際關系里面,特別舒服。但是如果每天都不離開這片土地,還是相當枯燥。早上起來躺在床上,縫隙之間會有一種厭倦感。”
(張翠翠,《齊魯周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