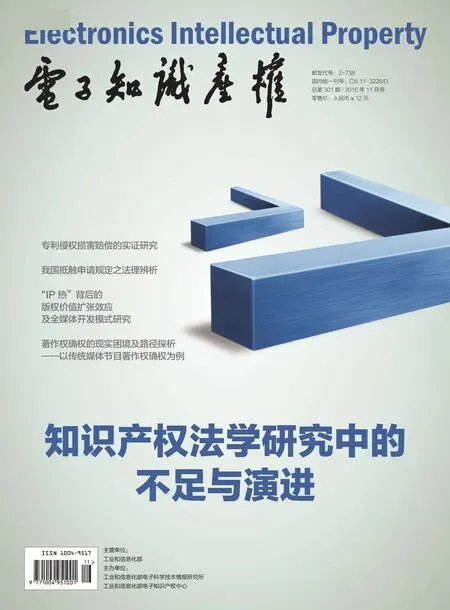知識產權法學研究中的不足與演進(上)
文/劉麗娟
知識產權法學研究中的不足與演進(上)
文/劉麗娟
知識產權疑難案件頻出,卻罕見法學家們提出有價值的解決方案,這意味著知識產權的法學研究存在某種問題。問題主要表現在:法學研究方法粗淺,以及對方法論缺乏認識。幾種現象導致本領域的研究呈現出獨特性。但這些獨特性并不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學研究可以“自外于”大法學,本領域需要理解并關注法學方法論以及其他相關部門法的研究。由于知識產權法學的獨特性,其可能在我國法治建設逐步推進中發揮某種先行者的作用,但作為前提,知識產權法學研究必須正視并克服自己的不足。
知識產權;方法論自覺;法解釋學;紅罐案;iPad案
近年,知識產權大案頻出。其中相當一部分案件,獲得廣泛關注的原因,在于其觀感違反了公眾的公平正義之心,如曠日持久的“榮華”月餅商標糾紛1“榮華”月餅商標糾紛簡介:香港著名的“榮華月餅”在改革開放后進入大陸,但由于香港商標制度實行使用制而未及時在大陸注冊,此商標后被山東一家食品廠偶然注冊。當香港榮華試圖注冊該商標時,由于存在在先近似注冊商標而無法獲得注冊,而廣東順德的一家食品廠卻以從山東該食品廠受讓“榮華”注冊商標的方式,成為了注冊商標權人,順德公司也使用“榮華”生產和銷售月餅。此系列案自1990年代末開始,迄今尚未平息爭端。,以及“iPad”商標爭議2“iPad”案簡介:蘋果公司啟用“iPad”商標前,曾做過全球商標調查,發現唯冠公司已注冊了幾乎相同的商標。臺灣唯冠、深圳唯冠都是總部位于香港的香港唯冠公司開設的子公司。在將iPad正式推向市場之前,蘋果公司需要確保獨占“iPad”商標,由于擔心被“唯冠”這個經營不善的公司訛詐,蘋果另外注冊了一個小公司,以該小公司名義和唯冠協商以35000英鎊轉讓其注冊商標。但在轉讓協議上,簽署協議的是臺灣唯冠,而大陸地區的“iPad”注冊商標的注冊人是深圳唯冠,這使得蘋果公司能否通過該合同擁有中國大陸地區的“iPad”商標存疑。蘋果公司訴至法院,要求確認“iPad”注冊商標屬于蘋果。據絕大多數知識產權業界人士看來,雖然蘋果公司確實冤,但根據我國現行商標法,注冊商標才是王道,深圳唯冠注冊了該商標,注冊時又無惡意,該合同的轉讓方并非深圳唯冠,蘋果只能為自己選擇了一個“弱商標”以及商標轉讓過程中的失誤付出代價。一審因此拒絕認定“iPad”屬于蘋果。但禁止蘋果公司使用“iPad”商標,不但于心不忍,還會帶來惡劣的國際影響,更坐實了“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的國際指責,因此二審法院選擇以調解結案,最終以蘋果向深圳唯冠支付6000萬美元和解,深圳唯冠將大陸地區“iPad”商標轉讓給蘋果。最高院將該案作為2012年知識產權十大案件之首,并認為該案的創舉是以調解方式解決疑難復雜案件之表率。見:(2010)深中法民三初字第208號、233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2)粵高法民三終字第8、9號。。兩案對法院來說,都頗為棘手。其困難,未必在于法律條文的模糊,因為模糊的法律中,法官尚有靈活解釋的空間。真正的困難在于嚴格依照法條會得出不公平的個案結論。兩案的實際處理結果并不相同,iPad案調解結案,這種以調解解決“重大疑難”案件(本案更像是“為難”案件)的方式,獲得最高院知識產權庭的高度認可,被舉為2012年“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
案件”之首。3參見奚曉明主編、孔祥俊副主編:《中國知識產權指導案例評注》第五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而“榮華”月餅案,法院堅持順德榮華擁有注冊商標,因此擁有中國大陸地區的商標專用權,但由于香港榮華在民間的廣泛商譽,順德榮華的月餅在民間實際上廣泛被當做香港榮華的月餅而購買,即公眾誤認的問題,迄今得不到有效解決。
放眼我國整個知識產權領域,尤其是商標領域,此類案件并不少見,一些不符合公平理念、甚至支持了搭便車者、惡意注冊者的判決在嚴格的法條主義教條下頻出。究其原因,首先當然是法律本身的不完善,存在缺陷法條。但缺陷法條的存在實乃成文法之必然,這已是學界共識,也是我國法學界的關注重心逐漸從“立法論”轉向“解釋論”的原因之一。4參見黃卉:《一切意外都源自各就各位——從立法主義到法律適用主義》,載《讀書》2008年第11期,第35-42頁。缺陷法條并非本文關注重點,本文的興趣在于,在缺陷法條難以完全消除的情況下,知識產權法學界未能為一線司法者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持,幫助他們有效應對僵硬甚至有缺陷的成文法條,得出公平合理的個案判決。這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學研究領域存在某種不足,這些不足有些是目前我國所有部門法都存在的問題,有些則屬于知識產權獨有的問題。在筆者看來,我國知識產權法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有必要進行某種方向性反思,為本領域的未來發展辨識方向、增添助力的時候。
一、知識產權法學研究中的不足
面對疑難案件時,法條主義解釋有時無法達致個案的公平解決,是各個部門法都面臨的難題。近年,發生在刑法領域的對于某些法條或案件的爭論,正是此類討論,5參見周光權:《法條競合的特別關系研究——兼與張明楷教授商榷》,載《中國法學》2010年第3期;張明楷:《法條競合中特別關系的確定和處理》,載《法學家》2011年第1期。而在民法領域,此類問題早已不是新鮮的話題。6臺灣地區民法學者對此類問題早有論述,參見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我國大陸民法學者也很早就關注此類問題,并進行方法性思考。如梁慧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版,該書現在已出第4版。學者開始關注此類問題,并由此反思成文法在整個實在法中的地位和價值,反思規則的生成機制,反思法院在整個立法、司法、執法框架中的中心地位,7參見高鴻鈞:《美國法全球化:典型例證與法理反思》,載《中國法學》2011年第1期,第5-45頁。文中,作者提及美國學者對現代法治文明的理論預設中有一條:“立法機構負責立法,執法機構負責執法,法院負責司法,法院是整個法律秩序的中心”,以及現代國家“以司法為核心的法治共識”,第7頁。反思判例制度在我國的必要性和價值8對判例制度的介紹以及在我國實行判例制度的意義,參見何然:《司法判例制度論要》,載《中外法學》2014年第1期,第234-258頁。等等,雖然也是需要深刻研究的問題,但并非本文關注。本文的重點在于,知識產權法領域對此類問題的認識和研究,相比于國外的同類研究,相比于國內其他基礎性部門法的研究,存在明顯不足。
(一)法學研究方法粗淺
人的認識在初級階段可能只涉及認識對象本身,但只有意識并找到合適的研究方法,才能將認識推向高級階段。知識產權法學研究的問題,主要在于對于研究方法的無意識和不重視。
知識產權法學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比較研究、法解釋學研究和極為有限的社科法學研究,各種研究方法都停留在該種方法的基礎階段。
1.比較研究方法
作為相當晚近的舶來品(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制度始自20世紀70年代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后),知識產權制度在我國從一開始就缺乏相應的社會基礎,其對國民的主要說服力在于他國尤其是先進國家的示范。
比較研究雖然也是其他部門法的重要研究方法,但其在知識產權領域卻成為最被倚重的方法,重要性甚至超過基礎性的“法解釋學”方法。這應該是因為其徹底的“舶來”性質:不但制度是外來的,連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都不存在本土傳統中,對制度進行思辨和推理的常情常理往往也難以依據我國本土文化,而必須依據某種最“先進”的符合全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價值理念。而在其他部門法領域,雖然某項制度可以參考外國,但問題的思考和解決終究要回到本土,本土文化中對公平、正義、情理的各種傳統共識,都對制度的理解和解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比較研究需要面對的障礙在于各國迥異的本土環境。一是法系環境不同。雖然法系的不同并不構成比較借鑒的絕對障礙,但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之間的制度借鑒,確實需要進行更深入的論證。法系的障礙對于大量吸收美國制度的知識產權法領域尤其需要重視,比如,我國商標保護采取了注冊制,而美國采取了使用制,商標保護基礎有所不同,導致兩國在何種商標應受保護上不能簡單類比,不能以某種已經使用但未注冊的商標在美國會受到保護,簡單得出我國商標制度對該種使用也應予以保護的結論。9雖然本文作者也認可總體上我國存在對商標的實際使用者保護不力的觀點,但并不認為我國給予使用者的保護強度應該完全等同于美國。參見劉麗娟:《論自然使用的商標的利益安排》,載《知識產權》2013年第3期。另外,商標使用者保護不力問題在2013年新《商標法》頒布后,由于建立了“在先善意使用者的抗辯權”,已有緩解。二是本國制度環境有異。在本國已有既定制度環境的前提下,借鑒何種制度、借鑒的方法等等,都必須考慮與本國其他制度甚至理念的契合。我國知識產權法領域在這方面存在明顯的不足,比如,本領域于2001年入世前后逐漸引入了“即發侵權”和“臨時措施”理論和制度,并認為是來自國際公約的全新的制度,但實際上,這兩種制度基本可以對應于物權請求權制度,只要建立一個類似的知識產權請求權制度(臺灣地區叫做“不作為請求權”),就可以既符合公約的要求,又能與我國現有概念體系相契合。不顧及本國固有的概念體系,而將公約規定作為一種新的制度照搬,固然有與公約銜接更加緊密的優點,卻給國內的司法、執法、法學帶來更大的麻煩,目前的即發侵權和臨時措施的制度,以及相應的知識產權侵權責任的無過錯歸責原則,實際導致了知識產權領域內侵權理論、侵權要素認定的邏輯矛盾,以及與一般民事侵權理論的疏離。10參見董躍:《即發侵權論探析與存疑》,載《中國專利與商標》2003年第3期,第10-13頁。比較研究第三個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各國發展階段甚至政策方向并不相同,這在知識產權領域頗為關鍵。知識產權事關產業發展,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對某些制度的態度差別很大,比如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美國強烈反對,歐洲不太支持但不強烈反對,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卻將之視為需要大力倚重的制度武器。我國需要借鑒哪一種,不但要考慮制度本身的正當性,還必須考慮制度在本土的落地是否真正有利于本國發展,甚至還需要加上國家利益的政策性考量。11關于我國應采取何種強制許可制度,參見劉麗娟:《專利強制許可辯》,載《電子知識產權》第3期,第60-67頁。
為了解決外來制度如何融入本土環境的問題,王澤鑒先生提出“功能性的比較方法”,頗為可信:“功能性是比較法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每個社會的法律實質上均面臨相同或類似的問題,不同的法律制度以不同的方法解決處理相同的問題。因此,從事比較研究時,必須從功能的角度,作為提出問題的出發點。”“功能性可以告知尋找臺灣問題的解決方法,如何進入外國法相對應的領域,有助于增加法律體系的想象力。縱使在例外情形,找不到解決相關問題的法律,亦值得從事比較的思考,即為何不存在相對應的法律規范?”。12王澤鑒:《人格權法——法釋義學、比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頁。傅郁林教授在評
述民事訴訟法的比較研究方法時,也對“簡單法條羅列式的偽比較研究”提出批評,并提出“以問題為出發點,以法律功能為對象的功能主義比較研究方法”才是法律比較研究的真正意義所在。13傅郁林:《追求價值、功能與技術邏輯自洽的比較民事訴訟法學》,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5期,第37-40頁。
比較研究,作為知識產權領域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占據了知識產權論文的絕大多數篇幅。然而,從方法論的角度審視,精細而服人之作甚少。首先,對他國制度理解和介紹的準確性,常常可疑。普遍存在的美國如何、歐盟如何、德國如何、日本如何、俄羅斯如何,對每個國家寥寥數語的比較范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對象國的準確描述,不免使人起疑。其次,他國制度于我國的適應性,少有深刻分析。比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研究在我國非常尷尬,從部門法歸屬上看,其介于經濟法和知識產權法之間,經濟法學者將之作為“競爭法”的一支、一種與反壟斷法關系密切的制度,對知識產權的“兜底性”保護不過是其中并不顯著的內容;而知識產權學者將反不正當競爭法作為知識產權法的一部分,甚至是商標制度的一部分,這種做法顯然受到美國的影響:在美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在聯邦層面只是存在于商標法中的一個條款,美國學者的相關著作是將商標與反不正當競爭放在一起研究的,并不認為反不正當競爭與反壟斷有何密切關系。在立法上,我國主要是繼受了大陸法系的德國一脈,建立了體系完整的反不正當競爭專門法;而在司法層面,不正當競爭案件被放入知識產權庭受理,客觀上使得知識產權學者和法官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認知和研究成為主流。無論是否承認,在知識產權領域,美國制度和理論在全世界都具有壓倒性影響,進而使得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在司法和法學研究領域都走向美國,雖然其立法是歐陸式的。如何將一種美式制度和理論,納入歐陸式的法條中,成了本領域的常態性問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比較研究因此變得非常復雜。借鑒美、德、日等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都會面臨一個既存制度適應性問題,研究者必須對此類問題有所認識,才有可能在借鑒他國制度時,能真正引進一個適合我國國情的能夠發揮良好效果的制度。這種復雜的情形,無疑對比較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2.法解釋學方法
法條必然抽象,需要解釋才能適用,理解和解釋法條是所有部門法學者的基本任務,釋法的方法是部門法學者最基礎的法學研究方法,其稱謂可以是“法解釋學”“法教義學”亦或“規范法學”等。14雖然學者對法解釋學、法教義學、規范法學是不是一回事有爭論,但并非本文關注重點。本文采用了民法領域常用的“法解釋學”稱謂。關于上述爭論,參見:張明楷:《也論刑法教義學的立場》,載《中外法學》2005年第1期,第357-375頁。其中張明楷教授認為刑法教義學就是刑法解釋學,并無新意;蘇力、陳興良、陳瑞華、白建軍:《法學研究與論文寫作》,載《中外法學》2005年第1期,第5-42頁。其中陳瑞華教授認為,所謂法教義學,其實與法解釋學、規范法學是一回事,陳教授自己采用了“規范法學”的提法。民法領域,一般稱之為“法解釋學”,如《民法解釋學》,梁慧星書,同注釋6。
解釋法律,并非易事!依據文義?邏輯?目的?利益?習慣?還是歷史?亦或對未來的預計和期許?伴隨認識的深入,人們對如何解釋法律呈現出一種漸進的趨勢,從法、德民法典時期的嚴格三段論推理的“概念法學”解釋,漸承認法條的不完善,而認可司法者在解釋法律中的靈活性,以應對含義模糊的法條,彌補法律的漏洞。
近年,我國民刑法學者對于能否超越法條文義解釋法律,產生激烈的爭論。大多數學者認為,雖然法律解釋有很大靈活性,解釋者難免將國家政策取向、自己的價值認知、情感傾向、未來判斷等各種因素納入解釋,但無論如何靈活,都不能超出法條的文義,15如民法領域的梁慧星先生,在其寫作的諸多關于法解釋的著作中,始終強調法條文義是解釋的外部邊界。見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否則,法缺
乏基本的權威性、安定性和可預見性。但刑法學者張明楷先生認為,雖然一般情況下,對法的解釋適用應在法條文義范圍內進行,但如果出現了文義解釋無法解決的問題,即“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對現行……法條進行合目的的解釋時”,就“只能批判該法條”16同注釋14,張明楷文,第357-375頁。這種觀點與臺灣地區著名法官楊仁壽先生的觀點一致:“茍法律之惡之程度,已惡于‘無法’,非運用法律闡釋方法所能濟事,不過徒具‘法律’之形貌而已,應認‘惡法非法’,此際,法官不但應拒絕適用,且一般執法人員亦應拒絕執行。”17同注釋6,楊仁壽書,第13頁。這些學者并非不關注法的安定性,他們都強調將“惡法非法”的認定限定在極為有限的范圍:“法律茍非‘惡’至令人無法忍受之程度,法官仍應運用法律之闡釋方法,對此‘惡法’加以闡釋,使之適合社會之要求,俾能貫徹法律目的或社會目的。”18同注釋6,楊仁壽書,第13頁。無論這些學者如何謹慎,他們的觀點都是石破天驚的。這種法官在個案判決中可以批判并拒絕適用成文法條的觀點受到的最致命批評,是如此法官就成為了立法者,司法代行了立法的職權,不但不能說服大多數法學家們,而且由于存在巨大的政治風險,法官并不敢真正采用。然而,在筆者看來,這種貌似激進的觀點,不過是對法律現實的正視,立法不僅可能存在“漏洞”和“模糊”,也完全可能存在“錯誤”,對于一個明顯錯誤而且無法在短時間內修改的法條,法官為了個案公平正義,必然要有所應對,上述方法,不過是指出一條明白直接的道路。而依照傳統觀點,法官不能明確批評某個法條,面對“錯誤法條”時,法官應做的,是運用各種解釋技巧,在法條文義內輾轉達致個案公平。這種方法往往以異常曲折的方式解釋法條,容易產生諸多問題,比如,法條文義被曲解到完全無法反映真實運行的規則,這種“潛規則”模式19本文“潛規則”的說法,借用了何然先生的觀點,但何然先生是針對判例制度的,他認為其實兩大法系都存在判例制度,只不過英美法的判例法是明規則,而大陸法系的判例法淵是潛規則。同注釋8,何然文,第234-258頁。,實際上使人們難以了解真正的規則究竟是什么,并不真正有利于法律的透明公開,不能達到其宣稱者所主張的法的安定性和可預計性的價值,而且無助于錯誤法條的改正,無助于問題的展開和解決。必須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法治環境下,要求法官以法律目的或價值判斷做出不符合實在法邏輯結論但更符合正義的判決,是過高的不近人情的奢望,因為這種靈活性極強的判決的前提是法官有足夠的權威和獨立,20參見蘇力:《法條主義、民意與難辦案件》,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1期。該文中,蘇力先生提到使得法官在個案判決時能夠將民意、政治、價值等因素考慮進去,做出有悖于法條文義解釋需要一個法制的大前提,其中之一就是法官有充分的獨立性、權威性。而這一點,我國目前尚不具備。
概言之,對于如何解釋法律,無論是法理學還是其他基礎性部門法學,都有大量而深刻的討論,且呈現出逐漸進化的趨勢。反觀知識產權法學領域,對法條的解釋方法,主流仍是狹隘的概念法學意義上的,即嚴格地將對規則的理解局限于法條的文義,通過法條本身的用語及其邏輯關系理解法條。
以“iPad”案為例,按照我國商標法規定,“唯冠”擁有注冊商標,只要仍然有效,就能對抗世界聞名的實際使用者——蘋果公司,這是符合我國現行《商標法》的邏輯的,是合法的。該案突出反映了我國商標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僵化(也同時反映了我國合同法、公司法中的一些問題),同一個案子在香港,卻得出支持蘋果,認定唯冠存在合同欺詐的結論。21In the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ction No.739 of 2010.該案給司法者提出嚴峻挑戰:如果嚴格依據我國商標法規定,
不免要禁止“蘋果”公司繼續使用“iPad”,僅僅是為了一個當初在商標轉讓協議中“留了一手”、甚至不能證明自己使用了該商標的、瀕臨破產的唯冠公司!但本文的重點不在于苛責法官,本文的重點在于,iPad案引起的廣泛的社會爭論中,幾乎所有的業內專家都認為蘋果必敗,理由是此乃現有法律的必然推論,知識產權法學家們并未充分展現其作為研究者的價值,未能給法官提供一些先進的理念,幫助法官在法條不完善的前提下達致個案公平。而在發生類似問題的“許霆案”刑事案件的討論中,刑法學家們的大量爭論是在方法論層面的。22關于許霆案的討論,參見《中外法學》2009年第1期的各篇文章。iPad案,法院最終采取調解結案的方式,算是一種解決缺陷法條的無奈方法,至少達到息訴的效果,但法條的缺陷不能得到徹底解決,蘋果出了一大筆和解金,敲詐者仍然得逞,法律正義并未真正實現。此種局面,固然有我國整體法制環境的局限性,也充分暴露了知識產權法學研究的不足。
3.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法學研究有“在法律之外研究法律”和“在法律之中研究法律”之分,前者指法哲學、法社會學、法經濟學等研究,是將法律當做一種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后者則以現存法律為前提,在此基礎上進行法律邏輯推理,為法律適用提供理論上的依據。23陳興良:《定罪的方法(犯罪構成的方法)》,載北京市朝陽區律師協會編:《律師之師——律師素質與思維十講》,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4頁。“在法律之外研究法律”是必要的,由于法學非科學,不能完全依靠形式理性的概念邏輯推理,“規范法學(即上文的法解釋學,筆者加)僅僅站在法律內看法律,走不出自說自話、循環論證的‘邏輯怪圈’”,法學應引入其他視角或判斷,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國,以政治學方法研究法律、以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法律、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法律等等都已是法學當然的一部分,陳瑞華先生統稱之為“社會科學法學”。24陳瑞華:《法學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是幾位學者文章匯集而成的文章《筆談:法學研究與論文寫作》的一部分,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1期,第23頁。
以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法學,在我國仍然主要發生在法理學領域。法理學學者雖然也研究具體的制度、現象,但不過將其作為切入口,落腳點仍是某個一般性理念,而這個理念的價值仍主要是法理意義上的。
知識產權領域中,筆者僅見過極少量以經濟學方法分析知識產權制度的文章,至于以社會學方法研究知識產權制度,更是罕見。然而,社會科學法學一直停留在法理學領域,而未成為部門法學者們自覺采用的方法,倒不是知識產權的獨有現象,各大部門法,甚至與社科法學最為接近的民法和刑法,也少有源自部門法學者的以社科方法進行的制度討論。原因可能在于此種方法的前提是對該社會科學的深刻理解準確把握,部門法學者一般并不具備此種知識背景。部門法學者偶爾對社會科學方法的需要,不過是對主流“法解釋學”的補充,提供價值判斷的依據,這種需求是有限的。就知識產權領域而言,少量的以經濟學方法、社會學方法對知識產權制度的分析,所發揮的實際影響力并不顯著,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業內學者對此類知識的陌生,另一方面更是因為這種文章,倘來自知識產權學者,其對經濟學、社會學這些分析工具一知半解,難以建立令人信服的論證;如源自法理學者的此類文章,社科知識儲備可能足夠深厚,缺陷在于對具體知識產權制度缺乏準確理解,其論證的前提和結論,由于疏離于現有的知識產權制度框架和研究范式,往往難以得到知識產權業界的理解和認同。
應該說,社科法學研究方法的式微,并非知識產權領域的獨有問題。社科研究方法如何真正影響部門法,是所有部門法面對的共同問題,也是法理學者需要思考的問題,非本文重點。
綜上,知識產權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在于無論是作為基礎方法的法解釋學方法,亦或對本領域極為重要的比較研究方法,都處于相當初級的狀態。而這種法學方法上的不成熟,其根源在于本領域迄今尚未出現某種“方法論自覺”。
(二)缺乏“方法論自覺”25參見林來梵:《法學的祛魅》,載《中國法律評論》,2014年第4期。凌斌:《什么是法教義學:一個法哲學追問》,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1期。該文提到,刑法領域近年發生的若干爭論,體現了在刑法領域的可喜的“方法論自覺”。
方法論嚴格說來屬于法學基礎理論領域,應屬法理學者的研究對象,部門法學者從法理學者的研究成果中獲得方法性支持,進行本部門法領域的研究。然而,縱觀法學方法論的各種研究,往往并非出自法理學學者,而大多出自某個部門法學者,尤其出自基礎性部門法學,如民刑法。臺灣地區民法學者撰寫的大量法學方法專著早已為人熟知,近些年,大陸的學者也逐漸從早期的制度研究轉向法學方法研究。法理學者未成為法學方法論的主流,可能是因為此處所謂方法論,主要指解釋法律、適用法律的方法,是一種直接基于司法實踐需要用以指導法官適用法律的方法研究,法理學者由于對部門法缺乏深入研究,不能準確理解部門法的具體制度,也難以發現部門法所遭遇的實際問題。
法學方法論在中國大陸的覺醒,應該始自民法學者對臺灣地區和德國民法學者法學方法論著作的引入,比如楊仁壽、黃茂榮、王澤鑒等26如楊仁壽:《法學方法論》;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王澤鑒:《民法思維》等,這些書在大陸都多次再版。先生的著作;德國法學家關于法學方法的著作,最早引進且成為法學院必讀書的是卡爾·拉倫茨的《法學方法論》,近年有齊佩利烏斯的《法學方法論》等。大陸學者自己開始撰寫關于方法論的著作,較早的應屬梁慧星先生的《民法解釋學》,梁先生后來在給法官培訓時,將民法解釋學的方法簡化講授,匯成《裁判的方法》一書。近年大陸民法學者對釋法的方法興趣更加濃厚,王利明先生于2011年寫就了厚厚的《法學方法論》,并在各種講座中介紹如何利用方法找法、釋法。27如北京市朝陽區律師協會編:《律師之師》,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書中邀請10位著名法學家講授重要法律命題,包括王利明、陳興良、王亞新、張新寶在內的法學家講述的都是方法論問題。在刑事法律領域,隨著對法律認識的深入,相關討論也逐漸從“實然”層面,轉向對“應然”、以及如何以“實然”的法條達致“應然”之公平的爭論。近年刑法領域出現的關于“法教義學”的論述和爭論,其實與民法學界長期進行的“法解釋學”研究是一個路數。28同注釋25,凌斌文。該文提到,刑法領域近年發生的若干爭論,體現了在刑法領域的可喜的“方法論自覺”。陳瑞華先生2009年出版《論法學研究方法》,集中體現出刑事訴訟法律領域越來越強的方法論自覺。
從具體制度轉向方法論研究,標志著部門法學的逐漸成熟。縱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的歷史,法學的研究實際上呈現出某種進化的軌跡。這種進化既體現在看待法的視角的變化,比如蘇力先生認為中國大陸法學體現出一種早期的“政法法學”,繼而“詮釋法學”(即本文所稱法解釋學,筆者加)占據主流,隨后“社科法學”的軌跡;29參見蘇力:《中國法學研究格局中的社科法學》,載《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也體現在對成文法認識的轉變,由早期為了法的安定性而對概念法學的追求,逐漸轉向對概念法學的超越,近來則提出要承認在極端不公平的情況下批判法條,要求承認法官的個人價值判斷對于法律解釋和適用的重要性。
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方法論自覺”在知
識產權法領域迄今尚未引起關注。其原因可能是,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幾乎是外界施壓的結果,知識產權學者的精力主要都用在理解國際公約對我國的要求和影響上,專注于與不斷更新的國際制度接軌上,尚無暇顧及方法論問題。但在制度大規模引進已經基本完成、知識產權制度框架基本齊備的今天,知識產權法學也到了從理解吸收外來制度,轉向這些制度如何更好地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如何幫助法官以現行法獲得公正判決的時候,方法論必須適時進入學者和法官視野。
(三)大法學中的“特立獨行者”
1.對傳統民法的相對獨立
知識產權是私權,因此屬于民法。知識產權法,仍需適用民法對民事關系的一般規定。比如,知識產權各種合同需要適用《合同法》,因為知識產權專門法對知識產權合同沒有詳細規定;再如,知識產權作為民事權利,其繼承需適用《繼承法》。
但知識產權對民法的適用是通過比較松散的特別法和一般法的方式實現的:首先適用知識產權專門法的特別規定,缺乏特別規定時,適用《民法通則》《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等一般性規定,并不進行傳統民法典中總論、物權、債權(合同之債、侵權之債)的“潘得克吞”式的體系化邏輯推理。而且,民法中許多基礎性概念在知識產權領域并不存在,比如,民法總論中作為民法基礎“法律行為”理論和思考方式完全不存在于知識產權領域,知識產權學者一般也對所謂“請求權基礎”的思維方式不甚了了。知識產權的相對獨立性在學術研究領域表現更加突出,由于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基本是為了履行公約義務,大量條款是國際公約的翻譯,知識產權的法學研究已經逐漸形成一套獨立的話語和邏輯體系,迥異于我國傳統民法領域的“潘得克吞”體系化思維方式,并進而導致民法和知識產權法學者互不涉足對方領域,偶有的“跨界”研究,往往以“雞同鴨講”式的爭論收場。302015年初,薛軍教授發表了《質疑非公益必要不干擾原則》,載《電子知識產權》2015年Z1期,第66-70頁。薛教授的“質疑”,引起知識產權學者和法官的強烈反彈,參見《電子知識產權》2015年第3期的相關文章。這些爭論,本質都是民法學者以傳統民法的體系化思維適用于知識產權時,無法得到知識產權主流學術界的認可。
但這種相對于民法的獨立性,是否如同某些學者所言,是知識產權領域需要糾正的問題呢?筆者對此并不認同。原因在于,知識產權對民法的相對獨立,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后文詳論),是一個自然選擇的結果,并非某幾個法學家所能夠扭轉。盲目地以民法的基礎理論統攝知識產權制度,固然可能帶來體系化的好處,但同時可能導致更多的問題。
2.自外于大法學
但知識產權法學研究的獨立,甚至是相對于整個大法學的。
雖然專業之間的隔閡是分工的必然產物,各個部門法之間普遍存在專業的隔閡。但在整個大法學圈中,所有部門法始終共享一些知識,相互有一些基礎性了解。這來自于共同的法學基礎教育,也由于實踐中的問題常常相互交叉重疊。而知識產權領域,大量的從業者和研究者,往往并不具備法學的基本知識積累,其他部門法和法學基礎理論的知識基本空白。這種現象的形成,固然有其歷史原因,客觀上也確實造成了本領域的研究難以與整個大法學溝通,研究者很少有一種大法學的全局觀,而這種全局觀在民法、刑法等部門法學者身上卻很明顯。
毫無疑問,這種現象不利于知識產權法學研究的長遠發展。無論多么特殊,知識產權法仍是一種法現象,是一種規范,應受到關于規范現象的各種理論的統攝和指引。不論是作為財產制度,還是一種裁判規范,知識產權的研究都不可能完全自給自足,與其他部門法的交
叉不可避免,研究者必須對交叉領域的問題有所理解。“iPad”案,就是典型的若干法律相互交錯的糾紛,雙方目的是確認商標的歸屬,但這個問題的解決要依靠之前簽訂的商標轉讓合同的效力的確定,而該合同在中國大陸的效力判定進一步依賴對跨國母子公司關系的理解。31參見該案一審判決書,(2010)深中法民三初字第208、233號。一種視野狹隘的研究,不但無法對大法學的共同研究主題有所貢獻,甚至無法對本領域的疑難問題給出有意義的回應。
(未完待續)
Insufficiency and Evolu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IP System
In China,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IP cases appeared although researchers in this area seldom present valuable solutions.That is due to that there are some insufficiencies in our IP academic researches.The main issue is the ignorance of academic and legal methodology, which leaves the ways to study IP issues oversimplified and low-leveled.IP system is certainly a quite peculiar area from other parts of law, which, however, doesn’t mean that IP research should be an“outsider” of the whole legal research community.It’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knowledge of legal academic methodology aiming at making this area’s research develop further.Owning to some specific features of IP area, the advanced IP researches might act as a pione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untry ruled of law.Before that, IP researchers have to confront and overcome own shortcomings.
Intellectual Property;Methodology;Legal Interpretation;Red can case; iPad trademark
劉麗娟,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法專業副教授。
項目信息:本文受北京外國語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