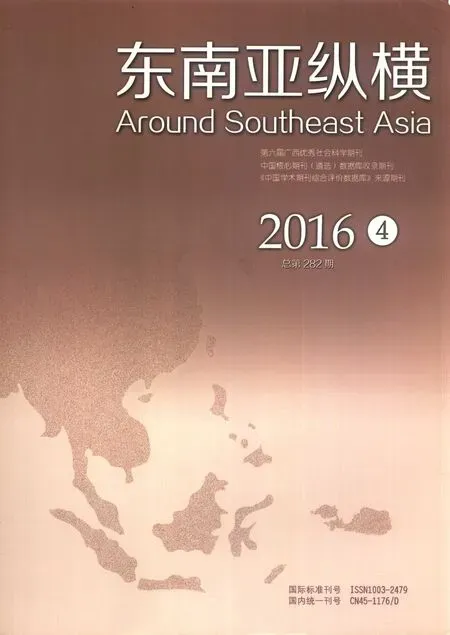中國科舉制度的南植和在地化
——《越南科舉制度研究》書評
韓周敬
[中圖分類號]H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479(2016)04-0089-04
中國科舉制度的南植和在地化
——《越南科舉制度研究》書評
韓周敬※
[中圖分類號]H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479(2016)04-0089-04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文化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隋唐時期以來,科舉制度對于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隨著古代東亞世界交流的加強,作為中國藩屬國的朝鮮、越南和琉球也先后引進了科舉制度,“作貢諸蕃別,登科幾國同”,以至于形成了一個“科舉文化圈”①劉海峰:《中國對日、韓、越三國科舉的影響》,《學術(shù)月刊》2006年第12期。。相比于實踐科舉最久的韓國(共963年),越南對中國科舉制度某些方面的汲取和模仿更為到位。越南正式施行科舉始于1075年,至1919年廢止之時,科舉制度在越南行用達884年之久。越南對中國科舉的移植并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在引進科舉主干制度的前提下進行了改造,這就是科舉制度在越南的“在地化”。“在地化”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與越南本土的文化風俗融合,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在地化”的過程也是科舉制度得以豐富的過程。應(yīng)該說,“在地化”是越南一貫秉持的務(wù)實政策的結(jié)果,這種務(wù)實政策是一體兩面的,既表現(xiàn)在越南極力撇清與中國實質(zhì)上的政治聯(lián)系,又表現(xiàn)在對其自身藩屬地位的維持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渴求與依賴上。
由于科舉制度對越南國家意識的塑造、官僚社會的建構(gòu)和上下階層的流通均有重要作用,因而學界向來對其矚目有加。多年以來,中國國內(nèi)和國際學界篳路藍縷,取得了一些成果,這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總體看來,這些既有探索有以下3點不足:第一,研究成果體量不大,以至于后來學者缺乏足夠的參考座標;第二,研究視野有限,尤其缺乏比較視角下的細化考究;第三,研究層面較淺,多局限于史事概述、數(shù)據(jù)統(tǒng)計以及制度本身,對科舉制度與政治、社會和文化的關(guān)聯(lián)性挖掘不夠,從而也就難以對其他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研究產(chǎn)生足夠的啟發(fā)。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亞歷山大·伍德賽德(Alexander Woodside)為代表的一些學者開始嘗試突破既往的定勢,跳脫“為科舉而科舉”的畛域,對越南科舉制度進行了較有關(guān)聯(lián)性和深層次的研究,陳文《越南科舉制度研究》,(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4月版)一書就是該潮流影響下首部全面、系統(tǒng)、深入地闡述越南科舉制度的專著。
一
《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一書分為緒論、正文和結(jié)論三大部分。緒論較為詳細地梳理了學界對越南科舉制度的研究成果和進展,這種回望既為作者自身的研究建立了參照體系,也為讀者了解該領(lǐng)域的學術(shù)進展提供了路徑。正文分為10章,從正文所體現(xiàn)的內(nèi)容來看,這10章又可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李陳朝時期,包括第一章;第二部分為后黎朝時期,包括第二至六章;第三部分為阮朝時期,包括第七至八章;第四部分是對越南歷代進士地域分布以及漢文化在越南傳播發(fā)展的專題研究,包括第九至十章。尤需注意的是,作者采用的“黎朝時期”這個概念不是僅指后黎一朝,而是用以指代后黎朝所屬時期之內(nèi)的所有政治實體,其中就包括莫朝(1527~1683年)這一非黎政權(quán)。結(jié)論中,作者對《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一書所涉及的內(nèi)容做了扼要的概括,將全豹集于一斑,對全書的內(nèi)容也做了呼應(yīng)。
若對作者以往的學術(shù)經(jīng)歷進行梳理,可知《越南科舉制度研究》是建立在作者自2003年以來產(chǎn)生的一系列專題研究成果之上的,其中作者于2006年答辯的博士學位論文《科舉在越南的移植和本土化——以越南后黎朝為中心》①陳文:《科舉在越南的移植和本土化——以越南后黎朝為中心》,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構(gòu)成了《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一書的主干內(nèi)容。在隨后的8年間,作者一方面繼續(xù)對后黎朝時期的科舉進行補充研究,并將一部分成果在《世界歷史》等刊物上發(fā)表;另一方面又圍繞阮朝、法屬時期以及科舉對儒學傳播的影響等主題進行了后續(xù)研究。正是作者多年來的持續(xù)探索,才逐漸充實了自身的越南古代科舉研究體系,為《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一書的出現(xiàn)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二
通過對《越南科舉制度研究》的分析和解讀,筆者認為該書至少具備以下4個特色:
(一)體例完備
《越南科舉制度研究》將越南科舉置于中越對比的場域之下,對越南北屬時期,以及自主時期所有施行科舉的朝代進行研究,其中尤以黎朝(1428~1789年)和阮朝(1802~1945年)為重點。通觀《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一書,可以總結(jié)出作者的寫作模式,即將越南科舉的研究內(nèi)容劃分為三大部分:科舉考試制度、科舉人員、科舉考試內(nèi)容。而后,在每一部分的考述中,先介紹中國科舉的相關(guān)情況,再詳細考究越南科舉相應(yīng)的內(nèi)容,并將其與中國科舉制度對比,來揭示越南對中國科舉制度的移植和改造。這種寫作方式既是一種宏觀學術(shù)視野的體現(xiàn),也是觀察越南科舉制度歷時性傳承與流變的必由之路。具體而言:
首先,從學術(shù)視野方面來說,中越兩國科舉制度之間的關(guān)系類似于母體與子體的關(guān)系,越南對中國科舉移植和改造的表現(xiàn),可以總結(jié)為3種:第一,主干制度的移植未變,如鄉(xiāng)試—會試—殿試三級制、文武科試等;第二,有些方面被改造后又得到復原,如明命十三年(1832年)將鄉(xiāng)會試由4場改為3場,但嗣德四年(1851年)又由3場改回4場;第三,有些方面被改造后沉淀下來,成為越南科舉的特色,如京寨進士、久虛首名制,這一部分也是《越南科舉制度研究》論述的精華所在。這3種表現(xiàn)如果不借助于宏觀視野下的對比研究是難以曉示的。
其次,從觀察越南科舉制度歷時性傳承與流變來說,作者所論述的時段實際上跨越了越南歷史的中古和近世時期,這兩個時期的丕變在文化上表現(xiàn)為由重佛變?yōu)橹厝濉⒂芍匚渥優(yōu)橹匚摹R舱窃谶@種世風轉(zhuǎn)化的背景下,黎圣宗才改革舊有制度,對科舉制度大力倡行,越南文化中原有的東南亞底色遂趨于黯淡,而浸潤于中國文化中的東亞特色逐漸凸顯,其后的莫朝、鄭主以及阮朝莫不如此。至阮朝后期,隨著法國的入侵,與自主時代相比,越南科舉制度的內(nèi)容又發(fā)生了適時的改變。正是因為《越南科舉制度研究》從歷時性的角度對越南歷代科舉制度的傳承與流變做了梳理,才使得我們窺見了越南歷史的背景色。
(二)理論運用的多樣化,史料求新和求全性
雖然作者在緒論中言明其“主要運用了傳統(tǒng)歷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但我們從第二章中對明朝在安南文教政策的考論中,看到作者還利用了制度經(jīng)濟學的理論;從第六章對黎朝科舉的銓除和影響的考察中又可看出社會學的影響;從第九章對越南進士地域分布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計量史學研究方法的痕跡。
如果說對這些理論的自如運用體現(xiàn)了作者篤實的學術(shù)功底,那么全書豐富的史料則體現(xiàn)了作者專注的治學精神。作者對史料的運用具有兩個鮮明特點:第一,求全性。作者引用的史料體量龐大,以目前搜羅越南漢喃書目最全的《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來作為查檢依據(jù),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其中多數(shù)相關(guān)文獻都有涉及,這些文獻既包括官方編撰的典例書如《黎朝會典》《國朝鄉(xiāng)科錄》,也有私人撰述的文集如《阮廌全集》《吳時任集》。此外,作者還對歷代正史、政書、地理志、碑刻、筆記小說中的相關(guān)資料做了大面積的挖掘;第二,求新性。從作者引用的史料看,其中很多都是此前學者著作中見所未見的,如作者所參考的越南漢喃研究院手抄本文獻,絕大多數(shù)時至今日仍未出版,只有身至河內(nèi)才可以閱覽,這一部分新史料在作者所引用的總體史料中又比例頗大。如此大規(guī)模地使用新史料在此前國內(nèi)學者撰寫的越南史學專著中是很少見的。
(三)研究的精細化
任何研究如果不能具體而微,也就不能使人解其深密,亦不可藉其旁逸。《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一書對于研究對象的分別和細化達到了前人未及的程度,在考述很多問題時都達到了年的尺度,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考證也使得以前的模糊說法清晰化。如第96~98頁對于“三年一大比”起始時間的考證,第163頁對于士望、宏詞二科關(guān)系的考證都可謂精到。這種精細化考證的層層累積使得本書的論證過程扎實而有力度,結(jié)論的成立也是水到渠成。
(四)注重對象間的互相觀照
中越共處于科舉文化圈內(nèi),其互相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但長期以來,我們只強調(diào)中國對越南單向的影響,而對這種影響的回流矚目不多,這實際上是對其文化底色多樣性的無視。20世紀 80年代以來,以基斯·泰勒(Keith W.Tylor)①Keith W.Tylor,A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和維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②Victor Lieberman,Strange Parallels: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c.800~183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vol.1),2009(vol.2).等為代表的東南亞史學者開始對此有所反思,不再強調(diào)單方面文化的影響,而是將研究置于中越文化對比的語境之下,注重挖掘越南文化中深層的固有色彩。作者在撰寫本書時也遵循了類似的理路,比如第十章在論述科舉取士與漢文化在越南的傳播與發(fā)展時也強調(diào)了越南士人對中國的觀察、感知和評價。這種來自“異域之眼”的觀照對于人們從一個更大的范圍內(nèi)客觀認識同屬于漢字天下的“我者”(中國)與“他者”(越南)的分野與交集有著一定的啟示作用。
三
以上所列舉的4點特色是《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一書學術(shù)品質(zhì)的體現(xiàn),但是,我們也應(yīng)看到《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可以繼續(xù)探討之處。
(一)某些章節(jié)尚待補充
筆者看到,《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一書在分期時存在一個饒有趣味的現(xiàn)象,即將黎朝時期和阮朝時期之間的西山朝漏掉了。為何如此安排不得而知,但據(jù)目前的史料來看,西山朝確曾施行過科舉考試。西山朝雖然重視武功,但對于立學興科也是有所注重的。《越南科舉制度研究》第85頁就記載了立于光中五年(1792年)年的《學田碑記》,其中有言:“學貴有師,而受教者不能不供養(yǎng)教師。”但作者并未就此深入探討下去。實際上,既然已經(jīng)興設(shè)學堂,那么下一步就是開科取士,吳時任草擬的《立學詔》:“期以今年開鄉(xiāng)試科,取鄉(xiāng)秀才優(yōu)等升充國學,次等送補府學。”③〔越南〕吳時任:《翰閣英華》,《吳時任全集》第二卷,河內(nèi)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620頁。黎文仍《茶縷社志》載:“本社人潘登第光中時中解元。”④〔越南〕黎文仍:《茶縷社志》,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書號VHv.2454,轉(zhuǎn)引自《西山遺文》注釋,河內(nèi):河內(nèi)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頁。。潘登第所參加的鄉(xiāng)試當是在《立學詔》下達之后不久舉辦的。此外,《野史日記》還記載了景盛三年(1795年)的一次鄉(xiāng)試:“七月,西山試乂安士人,中格者為俊士,得十八名。”⑤佚名:《野史日記》,收入黃春翰《羅山夫子》,河內(nèi):河內(nèi)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24頁。。《西山述略》則記有寶興元年(1801年)“冬,試課生”⑥佚名:《西山述略》,越南國務(wù)卿特責文化處,1971年版,第6頁。。可見西山時期至少曾經(jīng)3次開科。陳重金認為,西山科考時,“常命考官出字喃試題,并命令考生以字喃作文答題”⑦〔越南〕陳重金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2年版,第281頁。。
(二)某些論述尚須補苴
科舉用書是科舉制度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作者對這方面所涉頗多,但由于著力于探索書籍的內(nèi)容、流傳所帶來的正面影響,而對它們帶來的負面效應(yīng)沒有涉及。譬如,《越南科舉制度研究》第132頁、第265頁和第464頁都寫到裴輝璧編寫儒家經(jīng)典《節(jié)要》作為舉業(yè)書,但并未深入分析這些書籍的流行對于科舉士人才學和正常科舉秩序的擾亂。
裴輝璧編四書五經(jīng)及通鑒節(jié)要本是因為朝廷科舉出題所依據(jù)的《五經(jīng)四書大全》《歷代通鑒輯覽》等書“字紙繁重,抬載艱難,紙貴價昂”⑧〔越南〕阮通:《請頒給書籍疏》,見于《淇川公牘初編》,嗣德壬申年新鐫,寓齋藏板,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書號VHc.1719。,為民間稀見,故而編撰這些提要,給舉子提供便利,但這些書籍刊刻以后,“學者奉為科途捷徑,正學不明”⑨〔越南〕阮通:《請頒給書籍疏》,見于《淇川公牘初編》,嗣德壬申年新鐫,寓齋藏板,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書號VHc.1719。。此外,由于裴氏所編之書“所取諸家議論,間多龐駁踳蹋,甚有抄取帖括套語竄入其中,豫為士子剽竊之地,而正史本文實事,轉(zhuǎn)多掛漏”⑩〔越南〕阮通:《請頒給書籍疏》,見于《淇川公牘初編》,嗣德壬申年新鐫,寓齋藏板,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書號VHc.1719。,使得當時的學問風氣趨于虛浮。而坊間書商為了刺激利潤,又刊行了《補正少微通鑒節(jié)要》。針對此種情況,嗣德九年(1856年)議定專經(jīng)條例,反正經(jīng)學,但《新刊通鑒節(jié)要》一書仍然私行于世。嗣德二十三年(1870年)又規(guī)定“以后皆以乾隆御批《歷代通鑒輯覽》為準出題”,“外間贗書俗本(如新刊《補正少微通鑒節(jié)要》諸家議論龐雜之類),不得濫引設(shè)問,以滋他途之惑”①〔越南〕阮通:《請頒給書籍疏》,見于《淇川公牘初編》,嗣德壬申年新鐫,寓齋藏板,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書號VHc.1719。。由此不難看出,當時裴輝璧諸書《節(jié)要》的流行在提供給士子便利的同時,對當時的學術(shù)風氣乃至士子的水準都產(chǎn)生了不利的影響。科舉本是為了選拔人才,但《節(jié)要》的出現(xiàn)以及士子對《節(jié)要》的尊崇使人只專注于考試,反倒削弱了科舉選拔真正人才的功能。
此外,作者對于阮朝式微時期的科舉取士和科舉廢除的始末也敘述不多。筆者推測這或許是因為缺少資料之故。觀作者所引用之材料,多是《科榜錄》《實錄》之類,但關(guān)于阮朝末期成泰、維新和啟定三帝的《實錄》,卻并未見引。此三朝《實錄》匯成《大南實錄》第六紀附編和第七紀,但由于這兩紀并未收入日本慶應(yīng)義塾大學刊印本《大南實錄》中,故而為世人所少見。《大南實錄》第六紀附編和第七紀漢文本現(xiàn)藏于法國遠東學院圖書館②楊保筠:《關(guān)于〈大南實錄〉的一些補充介紹》,《印支研究》1984年第3期。,越南學者高自清(Cao Tu Thanh)等在2012年曾將第六紀附編翻譯為越文,由越南文化—文藝出版社出版。
(三)某些表述的細節(jié)需要充實或修正
這表現(xiàn)在5個方面:1.缺乏地圖。作者在行文中很注重文字和圖表的表述,卻沒有一幅地圖,即便在研究進士分布時也只是用表格來表現(xiàn),筆者認為,如能將這部分成果繪成地圖,則勢必給作者自身的表達以及讀者的領(lǐng)會都帶來很大的便利。2.對某些資料的使用還需謹慎。如第85頁以西山的碑文來說明后黎的情況,第90頁以明命時期的《名臣事略》內(nèi)容來論證后黎朝的教學內(nèi)容,后文之阮勉軒撰《天南四字經(jīng)》亦是如此。3.對于西方研究成果的參考需要加強。由于作者主要參考了中越兩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以致于對西方相關(guān)成果涉獵不多,如亞歷山大·伍德賽德于1971年出版的名著《越南與中國模式:19世紀前半葉阮朝與清朝政府的對比研究》③Alexander Woodside,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A Comparative Study of Nguyen and Ch’inh Civil Gover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以及2006年出版的《遺失的“現(xiàn)代”:中國、越南、朝鮮,以及世界歷史的冒險》④Alexander Woodside,Lost Modernities:China,Vietnam,Korea,and the Hazards of World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都專門辟出一部分篇幅來比較中越科舉制度,但作者并未引用。4.書中出現(xiàn)了一些引注錯誤。如第34頁“阮Q勝”當為“阮決勝(Nguyen Quyet thang)”。阮決勝系越南現(xiàn)代知名的文史編纂學者;第35頁“陳朝黎文休在《越鑒通考總論》中”之“黎文休”當為“黎崇”;第233頁“張寶嵐”應(yīng)為“張寶林(Truong Buu lam)”,張氏為南越著名歷史學家,后來赴美國夏威夷大學任教;第310頁注釋4之“Pham Boi Chau”當為“Phan Boi Chau”,即越南阮朝末期志士潘佩珠。又如對一些政區(qū)地名的使用需要剖判年代,并使用正確的名稱。如第104頁論述黎朝試場的設(shè)置時,就用了“外鎮(zhèn)”一詞,從作者的注釋可知,其依據(jù)的是潘清簡《欽定越史通鑒綱目》,但《綱目》一書編撰于阮朝,“外鎮(zhèn)”一詞出現(xiàn)于阮朝嘉隆時期(1802~1819年),《綱目》編撰于該詞出現(xiàn)之后,故而習用之,但該詞在后黎朝時期尚未出現(xiàn);第399頁“乂安鎮(zhèn)的蔡州”當為“葵州”;第413頁論述潘清簡鄉(xiāng)貫為“永清鎮(zhèn)定遠府”,實則定遠府在后黎朝時為“定遠州”,嘉隆七年(1808年)才升為府,而潘清簡生于1796年,定遠當時尚為州。
總之,《越南科舉制度研究》一書雖存在一些尚待探討和完善之處,但瑕不掩瑜,我們需要看到本書是學界第一部從長時段、整體視角,以豐富的史料為支撐,以越南歷史朝代為敘述脈絡(luò),從對中國科舉制度的移植和本土化的角度系統(tǒng)探討越南科舉制度的研究成果,該書的出版將目前學界對越南科舉制度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越南古代史學研究”(15CSS004)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責任編輯:李碧華)
Book Review of“Vietnam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an Zhoujing
※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