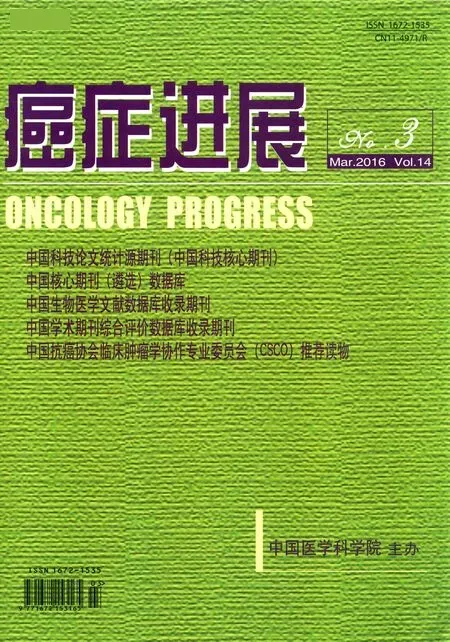中心型早期非小細胞肺癌立體定向放射治療研究進展
王濟東 王俊杰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腫瘤放療科,北京 102206
中心型早期非小細胞肺癌立體定向放射治療研究進展
王濟東王俊杰#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腫瘤放療科,北京102206
近年來,體部立體定向放射治療(SBRT)在早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中的作用和地位獲得了重大提升,現已成為因醫學原因不能手術的周圍型Ⅰ期NSCLC的標準治療方式。然而,SBRT在中心型早期肺癌中的應用一直受到質疑,經過大量臨床研究,對中心型肺癌的定義、安全性、劑量分割模式、正常組織的劑量限制以及禁忌證均有了新的認識,并對處方劑量、治療計劃不斷優化,對其誘導的自體免疫效應進行了探討。通過選擇合適的患者,嚴格掌握適應證,SBRT在中心型早期非小細胞肺癌中的應用也必將會有廣闊前景。
立體定向放射治療;早期非小細胞肺癌;中心型;周圍型;立體定向消融放射治療
體部立體定向放射治療(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也稱為立體定向消融放射治療(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SABR),或稱作立體定向放射外科(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SRS),最早起源于頭部治療,是與頭部SRS相對應的放射治療方式,是給予靶區聚焦式、消融性劑量治療,而周圍正常組織最小劑量的現代放射治療技術。近年來,SBRT在早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治療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包括我國在內許多國家的放療機構進行了大量臨床研究,取得了局部控制率超過90%,總生存率及疾病特異性生存率優于傳統放射治療,與肺葉切除術相似的臨床結果[1-3]。研究顯示[4],對于可手術的Ⅰ期NSCLC,SBRT不良反應小,3年總生存率高(SBRT 3年總生存率95%,手術79%),比手術切除具優勢,可能成為繼手術后另一種可選擇的治療方式。盡管SBRT已成為因醫學原因不能手術的周圍型Ⅰ期NSCLC的標準治療方式,然而,SBRT在治療中心型早期NSCLC時,由于有潛在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可能,因此其應用存在較大爭議[5-9]。本文就SBRT治療中心型早期NSCLC的最新進展作一綜述。
1 中心型肺癌的定義
不同研究機構對中心型肺癌的定義不同,在已發表的文獻中,主要對其有三種不同的定義:第一種是把腫瘤位于近端支氣管樹各個方向上2 cm以內范圍均被認為是中心型,包括隆突、左右主支氣管和二級分支支氣管樹[6]。第二種是把腫瘤位于縱隔的任何重要結構各個方向上2 cm以內統稱中心型,包括支氣管樹、食管、心臟、臂叢神經、大血管、脊髓、膈神經及喉返神經[10]。第三種是把腫瘤位于近端支氣管樹各個方向上2 cm內,以及緊鄰縱隔胸膜或心包胸膜的腫瘤,只要是臨床靶體積(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達到縱隔胸膜均被認為是中心型[11]。中心型肺癌定義的不同,導致SBRT的臨床結果及不良反應存在差異,其適應證也存在差異,隨著對SBRT治療肺癌的不斷深入,治療產生的不良反應不僅涉及肺,還包括食管、心臟和神經等,因此,中心型肺癌SBRT的研究大多采用第二種定義。
2 中心型肺癌SBRT劑量分割模式
對于高劑量放射治療,近端支氣管樹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禁區(no fly zone,NFZ),因為早期研究中對中心型肺癌行SBRT時發生嚴重不良反應。Timmerman等[6]報道采用60~66Gy 3次分割方式治療早期NSCLC,結果顯示中心型肺癌肺毒性反應發生率是周圍型肺癌的11倍。進一步總結4年研究結果表明[5],中心型肺癌的肺毒性反應平均發生率是27.3%,而周圍型肺癌的平均發生率是10.4%。這些研究結果顯示,60~66Gy 3次劑量分割模式并不適用于中心型肺癌SBRT。隨后許多機構對中心型肺癌SBRT進一步研究,結果發現如果降低分割劑量,增加分割次數,可以降低不良反應發生率。美國MD安德森腫瘤中心報道了27例中心型肺癌[10],采用40~50Gy 4次分割治療方式,結果全組患者均無致命性的不良反應,采用50Gy劑量組2年局部控制率為100%,而采用40Gy劑量組局部控制率只有57%。盡管低劑量降低了不良反應,但40Gy劑量組因局部控制率低而不再被采用。另一項研究報道了100例中心型肺癌SBRT的臨床結果[12],采用50Gy 4次分割的治療方式,2年局部控制率為96%,局部控制率及不良反應發生率均與周圍型肺癌結果相似。其他研究中心也報道了相似的結果,Haasbeek等[13]報道63例中心型肺癌采用60Gy 8次分割模式,結果3年局部控制率是93%,且無4~5級不良反應發生。William醫院比較了125例患者采用48~60Gy 4~5次分割模式,結果中心型肺癌與周圍型肺癌總生存率及嚴重不良反應發生率無統計學差異[11]。這些研究結果均表明,中心型肺癌不是不適用SBRT,而是要選擇合適的劑量分割模式。劑量過高,會導致嚴重不良反應,劑量過低則會降低局部控制率,因此對中心型肺癌而言,選擇合適的劑量分割模式至關重要。
基于目前的研究,中心型肺癌的劑量分割多采用45~50Gy 4次分割,50~60Gy 5次分割,60Gy 8次分割以及70Gy 10次分割模式。對于中心型肺癌采用的治療效果最佳劑量分割模式,目前尚無定論。臨床研究表明主要根據腫瘤的具體位置、腫瘤大小以及與重要結構的關系,既要遵循靶區生物有效劑量(biologic effective dose,BED)≥100Gy,又要考慮重要組織結構的劑量限制,以平衡二者的關系,在保證不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前提下,制定出最佳治療方案。
3 中心型肺癌SBRT如何選擇合適的BED
BED是由線性二次方程BED=nd[1+d/(α/β)]計算得到的,肺癌SBRT中,α/β為10,并遵循以提高單次劑量提高療效的“量-效”原則,臨床研究表明,若達到局部控制率>90%,不論是周圍型還是中心型肺癌,BED≥100Gy是必要條件。中心型肺癌SBRT模式受到質疑的主要原因是有潛在的、嚴重的甚至致命性的不良反應。從正常組織損傷方面考慮,降低單次劑量,增加治療次數,會降低正常組織損傷的發生概率,而當BED<100Gy時,如40Gy 4次分割,BED為80Gy,局部控制率也會相應下降;BED過高,如60Gy 3次分割,BED為180Gy,則會增加不良反應風險,甚至出現不可耐受的不良反應。從目前中心型肺癌的臨床研究得知,中心型肺癌SBRT的BED在100~132Gy較為合適,BED過高不良反應加重,BED過低則會影響療效。因此,對于如何選擇合適的BED仍是今后臨床研究中的熱點。
4 中心型肺癌SBRT正常組織劑量限制
由于劑量分割模式改變,SBRT治療早期NSCLC正常組織與常規放療腫瘤周圍正常組織的限制劑量不同,在制定正常組織劑量限制時,可參考近距離放療、術中放療以及采用LQ模型對正常組織的劑量進行換算、評估和指導,但SBRT的放療效應不能完全依賴于數學公式計算,目前主要根據臨床研究隨訪、總結經驗分析得到。
正常組織的劑量限制,取決于劑量分割模式的不同,中心型肺癌SBRT主要分割模式有50Gy 4次、70Gy 10次和50~60Gy 5次,MD安德森采用50Gy 4次分割模式治療100例中心型肺癌,對正常組織進行限制,包括支氣管樹、臂叢神經、大血管、食管、脊髓等,與其他分割方式相比,正常組織的劑量限制更嚴格,同時還增加了胸壁和心臟的劑量限制,結果發生放射性肺炎、胸壁疼痛等不良反應與周圍型肺癌SBRT的發生率并無差異,而且未出現4~5級嚴重不良反應。在制定放療計劃時,如果正常組織劑量限制不能滿足要求,即采用70Gy 10次分割模式,同樣可得到相似的局部控制率,不良反應也可以接受[14]。當腫瘤侵及肺門或侵犯到支氣管樹、縱隔重要結構時,即使BED降低到100Gy以下,也可能導致致命性的不良反應發生,因此,對于這類中心型肺癌患者,可能并不適用于SBRT。美國腫瘤放射治療協作組(RTOG0813)已開展劑量提升實驗,采用的是50~60Gy 5次劑量分割模式,并以此來確定危及器官的耐受劑量,這將會對中心型肺癌SBRT提供更多的經驗和指導,試驗結果令人拭目以待。
5 處方劑量和治療計劃的優化
腫瘤局部控制率依賴于PTV接受的照射劑量,臨床實踐表明當PTV接受的BED≥100Gy時,才能得到滿意的局部控制率。然而,即使處方劑量相同,PTV接受的照射劑量也有很大差別,如用60%的等劑量曲線作為處方劑量包繞PTV,與用100%的等劑量曲線包繞PTV,PTV所接受的平均劑量也會相差30%~50%。另外,不同的計劃系統,劑量計算也存在差異,如用筆形束和蒙特卡洛計算的劑量就相差15%以上[15]。因此,要確保治療效果,必須使PTV接受足夠的劑量覆蓋以及使用適當的計算方法。
中心型肺癌采用SBRT時,常常要平衡腫瘤的控制與正常組織損傷間的關系,因此在優化治療方案時,要求高劑量區集中在腫瘤靶體積(gross target volume,GTV)上,而使PTV外劑量陡降。采用三維適形放射治療(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3D-CRT),調強適形放射治療(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包括容積旋轉調強(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治療制定SBRT計劃時,應該采用6~12個共面或非共面射束,1~3個弧形調強(ARC)優化治療方案,PTV處方劑量用60%~90%的劑量曲線包繞,并盡量避免PTV內劑量的均勻分布,定位時應采用4維CT(four-dimensional computed tomography,4DCT)定位技術來確定內靶區或采用呼吸門控技術以縮小照射范圍。中心型肺癌SBRT完美的治療計劃,應該是能夠滿足正常組織限制劑量,并且PTV的劑量不需要躲避正常組織而降低,在保證PTV劑量的同時,降低正常組織的照射劑量,進一步降低晚期不良反應發生率,同時在治療過程中,要用在線CT或CBCT來調整靶體積的覆蓋和對正常組織的保護。
6 中心型早期肺癌SBRT相關臨床報道
周圍型早期NSCLC的SBRT劑量分割模式用于中心型肺癌可能并不適合,這在早期的臨床實踐中已有證實,許多研究者通過改變劑量分割模式,嚴格選擇患者,對中心型肺癌SBRT進一步探索研究,如采用48~50Gy 4~5次、60Gy 8次以及70Gy 10次的分割模式治療中心型肺癌均獲得了與周圍型肺癌療效相似的結果,并具有很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11-14]。
Park等[16]最近報道了采用SBRT治療251例NSCLC患者的臨床結果,其中111例為中心型,140例為周圍型肺癌,中位隨訪時間31.2個月,這組患者中,中心型肺癌腫瘤較大,平均直徑為2.5 cm,周圍型平均直徑為1.9 cm,兩組腫瘤大小比較P<0.001;BED中心型平均120.2Gy,周圍型平均143.5Gy,兩組劑量比較P<0.001。多因素分析顯示,其2年總生存率(中心型71.6%、周圍型71.0%)、2年局部控制率(中心型87.1%、周圍型88.6%)及≥3級不良反應(中心型4.5%、周圍型12.9%)與腫瘤的位置無關。因此得出結論,中心型肺癌采用比周圍型肺癌較低的BED,局部控制率、總生存率及不良反應與周圍型肺癌無明顯差異。
Mangona等[11]采用48~60Gy 4~5次的分割模式治療早期NSCLC,并選擇79例中心型及79例周圍型肺癌進行配對分析,中位隨訪時間為17個月,在2年累積2級以上不良反應發生率方面,中心型與周圍型肺癌比較無統計學差異,且肺功能下降發生率二者也無明顯差異。因此,選擇合適的劑量分割模式及BED對早期NSCLC行SBRT治療,中心型和周圍型肺癌有相似的療效和安全性。
以上研究結果表明,只要采取適當的劑量,早期NSCLC的SBRT,中心型與周圍型肺癌同樣可獲得滿意的局部控制率及總生存率,且嚴重不良反應發生率較低,可以接受。
7 SBRT誘導的自體免疫效應
肺癌SBRT治療后局部淋巴結復發率為5%~10%,遠處轉移率為10%~20%[17],中心型肺癌的局部淋巴結復發及遠處轉移的概率均高于周圍型。有報道認為[18],對于中心型肺癌采用SBRT,肺門淋巴結受照射劑量要>20Gy,對肺門淋巴結復發可能起到抑制作用,因此,至今未有研究支持對中心型肺癌進行肺門淋巴結預防照射。作為高劑量放射治療的一種方式,已經觀察到,肺癌經SBRT治療后,照射野外的腫瘤發生縮小,這種現象稱為放射的遠地伴隨效應(abscopal effect)[19]。腫瘤接受SBRT后,局部凝固壞死,釋放含有可能產生免疫性微粒的細胞碎片,其細胞碎片可以激發自身免疫應答,類似于原位疫苗產生自身免疫治療。這些遠地效應主要機制可能是SBRT誘導的免疫反應,進一步激發自身免疫功能清除殘留病灶,并能減少局部復發及遠處轉移的發生。通過對肺癌SBRT治療后免疫效應及聯合免疫治療的進一步研究,當部分中心型肺癌SBRT的BED<100Gy時,局部控制率達到95%以上也成為可能,這將會進一步降低中心型肺癌SBRT的不良反應發生率,并有可能擴大其適應證范圍。
8 小結
早期中心型NSCLC的SBRT治療是雙刃劍,消融放射劑量對腫瘤是致死性的,對正常組織也是致命性的,因此選擇合適的劑量分割模式,適當降低靶區BED,平衡靶區劑量與正常組織的劑量限制,最大限度地降低不良反應發生率尤為重要。遠處轉移是SBRT治療失敗的主要模式,隨著對自身免疫效應的逐步認識和篩選以及SBRT聯合免疫治療的不斷探索,這對某些中心型肺癌的局部復發和遠處轉移將起到一定作用。SBRT對中心型肺癌并非“禁飛區”,而是“飛行識別區”,關鍵是要準確掌握每一個重要組織結構的劑量限制,把握好適應證。
[1]Mokhles S,Verstegen N,Maat AP,et al.Comparison of clinical outcome of stage 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reated surgically or with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results from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J].Lung Cancer,2015,87(3):283-289.
[2]Zheng X,Schipper M,Kidwell K,et al.Survival outcome after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and surgery for stage 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a meta-analysis[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2014,90(3):603-611.
[3]Shirvani SM,Jiang J,Chang JY,et al.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five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the elderly[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2012,84(5):1060-1070.
[4]Chang JY,Senan S,Paul MA,et al.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 versus lobectomy for operable stage I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a pooled analysis of two randomised trials [J].Lancet Oncol,2015,16(6):630-637.
[5]Fakiris AJ,McGarry RC,Yiannoutsos CT,et al.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for early-stage non-small-cell lung carcinoma:four-year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phase II study[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2009,75(3):677-682.
[6]Timmerman R,McGarry R,Yiannoutsos C,et al.Excessive toxicity when treating central tumors in a phase II study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for medically inoperable early-stage lung cancer[J].J Clin Oncol,2006,24(30):4833-4839.
[7]Song SY,Choi W,Shin SS,et al.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for medically inoperable stage I lung cancer adjacent to central large bronchus[J].Lung Cancer,2009,66(1):89-93.
[8]Milano MT,Chen Y,Katz AW,et al.Central thoracic lesions treated with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J].Radiother Oncol,2009,91(3):301-306.
[9]Modh A,Rimner A,Williams E,et al.Local control and toxicity in a large cohort of central lung tumors treated with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2014,90(5):1168-1176.
[10]Chang JY,Balter PA,Dong L,et al.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in centrally and superiorly located stage I or isolated recurre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2008,72(1):967-971.
[11]Mangona VS,Aneese AM,Marina O,et al.Toxicity after central versus peripheral lung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A propensity score matched-pair analysis[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2015,91(1):124-132.
[12]Chang JY,Li QQ,Xu QY,et al.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ation therapy for centrally located early stage or isolated parenchymal recurrence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how to fly in a“no fly zone”[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2014,88(5):1120-1128.
[13]Haasbeek CJ,Lagerwaard FJ,Slotman BJ,et al.Outcomes of 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 for centrally located early-stage lung cancer[J].J Thorac Oncol,2011,6(12):2036-2043.
[14]Li Q,Swanick CW,Allen PK,et al.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SABR)using 70Gy in 10 fractions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exploration of clinical indications [J].Radiother Oncol,2014,112(2):256-261.
[15]Chang JY,Bezjak A,Mornex F.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 for centrally located early stag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what we have learned[J].J Thorac Oncol,2015,10(4):577-585.
[16]Park HS,Harder EM,Mancini BR,et al.Central versus peripheral tumor location:influence on survival,local control,and toxicity following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for primary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J].J Thorac Oncol,2015,10(5):832-837.
[17]Senthi S,Lagerwaard FJ,Haasbeek CJ,et al.Patterns of disease recurrence after 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 for early stag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a retrospective analysis[J].Lancet Oncol,2012,13(8):802-809.
[18]Lao L,Hope AJ,Maganti M,et al.Incidental prophylactic nodal irradiation and patterns of nodal relapse in inoperable early stage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SBRT:a casematched analysis[J].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2014,90(1):209-215.
[19]Zeng J,Harris TJ,Lim M,et al.Immune modulation and stereotactic radiation:improving local and abscopal responses[J].Biomed Res Int,2013,2013(15):1-8.
R734.2
A
10.11877/j.issn.1672-1535.2016.14.03.07
2015-07-13)
(corresponding author),郵箱:junjiewang_edu@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