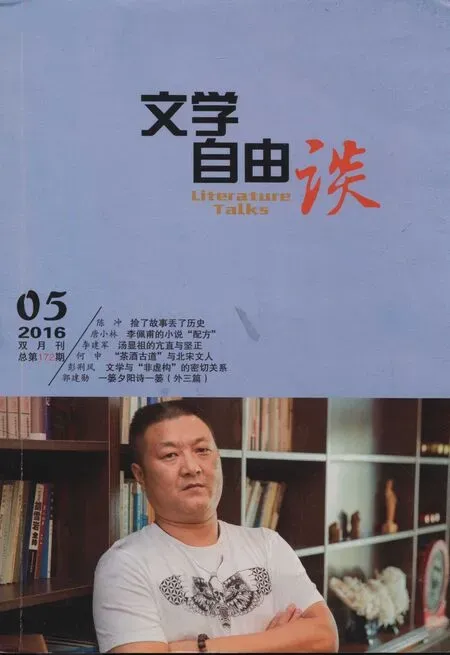撿了故事丟了歷史
□陳沖
撿了故事丟了歷史
□陳沖
我省文學院實行導師制,將我也定為導師之一,從此便被一個問題困擾。過去自己寫小說,怎樣才能往好里寫,自個兒慢慢琢磨就是了,現在卻要跟別人說怎樣把小說寫好,怎樣才能寫出好小說,這、這、這卻從何說起?直到前不久,這個問題似乎出現了一線轉機,似乎有了一個標準答案。在各種的文件、新聞、報道、座談、論壇乃至絕對符合學術標準的論文中,都頻繁而反復地出現了一種說法:講好中國故事。晚近則更有新發展,即如我的已故太太的老家,最近開了一個“峰會”——敢稱“峰會”,到會的自然都是各路的頂尖高手,大家不遠千里萬里地聚到一起,據報道“探討”的問題就包括“怎樣講好寧波故事”。如此看來,問題真是變得簡單了,再有人來問我怎樣寫好小說,答之曰講好中國故事、本省故事便是了。
問題在于:這樣真的就能交差嗎?
而新近出現的一些故事,則讓我更加心存疑慮:這樣只著眼于故事,會不會撿了故事卻丟了歷史?
故事之一,是前不久看到,著名的歷史小說作家二月河,在一次講座中說:“高薪養廉是個偽命題。”他舉北宋為例,說北宋官員的俸祿很優厚,但貪腐盛行。為此他講了個故事,說“包拯的年薪——折合人民幣650萬元”,然后問:“一個副省級官員,如果拿包公的工資,那稅收得有多少?老百姓能否承受?”于是得出結論:“高薪未必能養廉,低薪肯定不養廉”,“反腐倡廉的教育是學習歷史”。
一條很長的邏輯鏈,最后落在了“學習歷史”上,絕對突出了歷史的極端重要性。但是我的邏輯感覺告訴我,“故事”和“歷史”是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同一。如果在邏輯推導中用前者“頂替”了后者,那就很容易發生“撿了故事丟了歷史”之類的安全責任事故。如果那個“故事”再是虛構的,或假裝非虛構的,那就很可能釀成一次重大安全責任事故,撿了一個靠不住的故事,卻丟了一大片歷史。
包拯的年薪到底有多少?真能折合人民幣650萬元嗎?不知您知道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不知道沒關系,可以上網查。以前得查文獻,這類的活兒,沒有十天半月查不清;現在上網查,雖然不如查文獻嚴謹,不能算是做學問,但要把事情整明白,一個小時足夠了。不料這一查,又查出了另外一個小故事。原來早在一年前即2015年,就有人引用一篇二十年前的舊文,批駁了二月河的類似說法。然則二月河這回的講座,只是將已被批駁過的老調又重彈了一次。當然,著名作家一般都不怎么拿批評當回事兒,壓根兒不知道亦未可知。
還是回到故事的核兒——包拯的年薪。從網上提供的資料看,當年包拯的工資單并沒有保存下來,只能以他的級別去套當時的工資標準。流傳下來的這個工資標準又并不“標準”,只能算個大概。包爺的官,最大當到樞密副使,略相當于今之國防部副部長,即二月河所說的副省級。可是在那個工資標準里,沒有樞密副使的,只有樞密使的,而且不一致,有說月俸四百千錢的,有說三百千錢的。為了往高里說,且取其高者,再以“副”取其低,定包爺的月俸為三百千錢。雖然這里面已經有了若干個猜測和假設,不管你認不認,反正我認了。無論如何,這還是比較靠譜的。從邏輯上說,就拿它當作一個無需證明或不證自明的前提吧,往下就是換算了,即,它是怎樣經過一回回折算,折合成年薪人民幣650萬元的。
首先得把銅錢折算成銀子。按史書中的官方說法,是一千錢兌白銀一兩。這個好算,三百千錢,就等于白銀三百兩。對于一般讀者,即不懂經濟學,不了解古代經濟學,或者說認為中國古代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的讀者來說,這兒不存在任何歧義;但是如果我們動動腦筋,問題就來了。銅錢是一種貨幣,它在流通中體現的交換價值,是人為賦予的,與它的實物(銅)的價值兩碼事。而白銀卻是一種貴金屬。按史書的記載,中國發行貨幣實行銀本位制是從元朝開始的,那么在之前的宋朝,白銀就是一種純粹的,或者說與貨幣完全不掛鉤的貴金屬,它的價格是由自身的供需關系決定的。按史書記載,正是在包爺每月領取三百千錢俸錢的那段時間里,由于白銀的產量跟不上需求的增加,價格不斷上漲,漲到了兩千錢才能買到一兩白銀。如果依實按此折算,包爺的年薪立刻就只能折合人民幣325萬元了。
折算成白銀以后,再按其購買能力折算成現在的人民幣,需要一個中間物;從網上提供的換算資料來看,這個中間物被選定為“米”。我對此無異議。此物為那時的人和現在的人同樣不可或缺的生存必需品,自然那時和現在也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因而也有一定可比性的價格。可是盡管如此,這個折算還是從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在去掉一些不確定因素后,資料顯示宋時一兩銀子可購買米4至8石。問題是現在已經不以“石”為計量單位了,我們給出的數據只能是1斤米價為人民幣1.5元至2元。問題就出在如何將宋時的“石”折算為現在的“斤”,出在了存在兩種并行的說法——一說一石為96斤,一說為132斤。按前者算,一兩銀子折人民幣672至1344元;按后者算,折人民幣924至1848元。您圣明,最低值與最高值相差近三倍——這意味著包爺的年薪又有可能只折合人民幣不到150萬元,即還不如現在的某些央企高管了。
但無論如何,這個折算法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而且看上去也是比較靠譜的。可是按這同一個折算法折算出來的結果,竟然是在唐朝時一兩銀子折合人民幣高達2000至4000元,明朝時降為600至800元,而到了清朝只有150至220元。這跟我們看武俠小說所得到的印象相差太大了。看《射雕英雄傳》,郭靖向懷里一摸,就掏出二十兩銀子;看《三俠劍》,勝英向懷里一摸,掏出的銀子也是二十兩。誰也不會去想,這勝英的二十兩竟值不到那郭靖的二兩。可是遍查史書,又找不到不斷大量發現銀礦,致使白銀越來越不值錢的記載。
在中國的歷史里,各時期的消費品價格水平,各種流通貨幣間的折算,就是這樣一筆“大概其”的糊涂賬,而在各種“中國故事”里,這筆賬卻是相當清楚的,不然怎么會有“包拯的年薪——折合人民幣650萬元”這種“非虛構”?撿到這個靠不住的小故事之后,我們就丟掉了一大片歷史。首先,我們丟掉了中國古代長時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金融/經濟學的歷史。那是因為歷代統治者在制訂相關政策時,都是只考慮如何搜刮民財以充實國庫,從來不覺得還需要什么“學”。與此同時,我們也丟掉了這個漫長歷史中的一次短暫的例外,丟掉了中國歷史上一位最偉大(沒有之一)的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他叫阿合馬。他在七百五十多年前的元初,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發行紙幣的成功先例。與南宋發行的紙幣總是迅速大幅貶值不同,他發行的紙幣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幣值的基本穩定。能做到這一點,首先是因為他建立了銀本位制,即為紙幣的發行建立了足夠的白銀儲備。史書對此有明確記載。要到四百年后,西方人才明白發行紙幣必須有足夠的貴金屬儲備的道理,而阿合馬是怎樣提前四百年就明白了這個道理的,史書即付闕如。從后來的事實看,要保持紙幣的幣值穩定還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正確計算貨幣的總需求量和總發行量。阿合馬顯然會算,但他是怎樣算出來的,現在已無人知道。不過,二月河這個小故事最直接地丟掉的歷史,則是中國古代的歷代統治者從來不肯實行高薪養廉的歷史。時至今日,高薪養廉幾乎已是全世界公共政策制訂者的共識,唯獨咱們有些人持懷疑態度,說“未必”。什么叫“未必”?所有拿高薪的人中沒有一個貪污受賄的才叫“必”,出了幾個貪官就“未必”了?就是這種邏輯。而實際上,真正的問題并不是高薪能不能養廉,而是過去歷代統治者愿不愿意用高薪去養廉。他們不愿意。給官員們發高薪,那個錢是要從國庫里支出的,而在他們的心目中,那是他們自己的錢,多花了心疼,萬不得已時給有限的高官多發一點,大量的中下級官員絕不多發,不夠用時自己去想辦法,也就是去向民間搜刮。這個他們不心疼。不僅是這些官員的家用,即便是辦公的開銷,甚至辦事的人員,也是只給一部分。你看那些衙門里,不僅有吃官餉的在編制的“公務員”——稱為“屬吏”,往往還得有一幫由主官出錢聘用的 “編外人員”——稱為“幕僚”或“賓客”,這才能把該辦的事辦好。撿拾起這些歷史,你才能明白那些“自籌自支”的“事業單位”是怎么來的,才能明白為什么有的人總是置疑高薪養廉了。
時勢造英雄,一批講故事的能手正在應運而生,把故事講得越來越讓人癡迷。
但時勢同時也會造出取巧者。在越來越多的讓人癡迷的故事里,不見了歷史。
這也是一個中國故事,里面充盈著中國的特別國情。特別在哪里?在這種“敘事”里,故事的生命力在于“真實”,而歷史的生命力在于“真相”。這個嘛,看上去也還挺靠譜是不是?麻煩在于在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史里,“真實”也有它自己的“故事”。在近百年來的文學理論中,現實主義是無可置疑的主流,而至少在其中的后七十年里,作家們的現實主義書寫,卻幾乎總是得不到理論上的認可。這個相當離奇的故事情節,讓人不能不想到,在不同的人那里,存在著對現實主義真實性的完全不同的定義。這中間還涉及另一個猴皮筋概念:“生活”。此類離奇情節中往往會有一個高潮,就是向作家厲聲質問: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對于作家來說,這種問題基本上是毀滅性的,因為他們確實不知道生活到底是什么樣的。所以有段時間,很明確地提出來,創作要上去,作家先得下去。就是得深入生活。還不是一般的深入,而是要“三同”,和廣大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樣才能了解到現實。近讀《阿城文集》,閱至內中說到有一種“指定現實主義”,不覺啞然失笑,頗覺是一種生動、精準的描述。雖說是同吃同住同勞動,也并不是要把你看到、聽到即親身感受到的東西寫出來,而是要去發現那些“指定”的現實。最近在紀念柳青,我覺得很有必要。柳青的經典性就在于,他沒有去“三同”,而是干脆把家搬到農村去,并且特別擅長于把親身感受到的東西,揉合到指定的現實中去。等到那個指定的現實失去了指定的合法性以后,那些親身感受到的東西仍能保持一定的審美價值。另幾位有天賦的作家,例如李準、浩然,也有類似的情況,只可惜還沒人把這個編成故事講一講。現在時過境遷,那個“指定”的所指和能指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沒有變。不過這兒又有一個故事情節上的留白。人們幾乎都以為“深入生活”是毛澤東倡導的,其實“未必”。為了慎重,寫到這一段時,我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又仔仔細細重讀了一遍,所以可以負責任地跟您匯報,在這篇相當長的講話里,“深入生活”這個詞并沒有出現過。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能讀到的這個講話,是在多年以后,經過多次修改,包括毛主席本人親自修改后的定稿,應該可以判斷他沒有講過這個詞。不過,這個詞究竟是誰的原創,還是留到以后再說吧。現在這個詞雖然還在用,但在實踐上早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大概兩年前吧,上海一位女作家出版了一部新長篇小說,在接受采訪談到新作的寫作時說:“我一直都在生活里。”能說出這個話,是需要很大的理論勇氣的,但這個話卻沒有任何理論上的價值。它就是一個常識,常識到趨近于一句廢話。你可以很容易地將其“不屑一顧”:廢話!誰不是一直都在生活里?但問題又不像這個故事表面上看來的那么簡單。這位作家畢竟上了點年紀,眼睛還在盯著她那個“一直都在”里面的自己的“生活”。新一代作家多半都不這么傻了。他們洞察事物的本質,知道那個指定的現實在哪里,所以既不用深入他者的生活,也不必動用自己的生活,最多跟著一伙人出去采采風就行了,盡管回來以后講的也不是采風采來的故事。重要的是這些故事都講得很好,好就好在它們不是直奔那個指定的現實的所指,而是周旋于那些能指的附近。于是就有了一個又一個或者很有趣、或者很離奇的故事。這些故事里什么都可能有,唯一不可能有的只是歷史。它們或者看上去很真實,或者讓人很難確定它是否真實,可以確定的只是它不會把真相告訴你。
我承認上面這個故事講得有點亂——不,相當亂。即便是它本來就亂,并不是我把它講亂的,終歸也不好。所以下面有錯即改,講一個清楚的故事。
這是一個抗洪故事。
今年我國多省遭遇洪災,敝省也是其中之一。與南方各省相比較,因為成災原因不同,所以雖然歷時較短,但損失也相當慘重,尤其是人員傷亡方面。洪水退去,便有一個指定的現實浮出地面。有人去深入抗洪一線,不料卻發現并不存在這個“線”。敝省這次的洪水特別不講道理,它本身就是因短時間內降雨量超大引起的山洪暴發,所以忽喇喇一下子就來了,淹死、沖走一些人,毀壞了一些建筑、農田、財物,然后忽喇喇就走了,沒給當地軍民留下任何跟它抗一抗的機會。不過這只是現實之一種。沒過多久,該有的還是都有了,例如有張對開大報,就用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抗洪斗爭詩歌專輯,包括若干位詩人的若干首詩,全都激情四射地謳歌了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雖然不一定都有上佳的意象,但肯定都是好故事。
不過這個故事還有一個小小的支流。沒錯,它肯定是支流。講故事的是一個外省的記者。對不起,為什么是外地記者,以及這個外地記者為什么要到這兒來之類的問題,咱們就跳過去吧,否則又要把故事講亂了。總之他沒有深入到抗洪一線,而是直接就去找這次災難中那個漂浮在最最表層的人群——那些有親人被洪水沖走的家庭。然后,他的故事講的就是這些人在洪水退去以后都做了些什么。我是在微信上看到這個故事的,已經無法引述了,但我想我還是能夠憑記憶大略復述一下這個故事。這些人,即有親人被洪水沖走且尚無下落的人,有的還邀集了更多的親友,便開始沿著洪水退去的方向向下游行進,一路之上,一面向每一個遇到的人打聽有沒有看見過怎樣怎樣一個人,一面仔細地察看著沿途的每一個河灣,每一堆淤泥,每一片草叢。即使這些地方已經被前面的人無數次地仔細察看過,他們還是不會放過。中間,他們會聽說某處發現了一具遺體,他們總會立即抽人過去辨認。會不會撲空,大略就純粹是個概率分布的問題了,但還是出了一些戲劇性事件。有人辨認出那正是親人的遺體,卻被管理者告之這具遺體已經有人認領了。于是就有了爭議。但是沒有爭吵,因為很快就形成了共識:DNA說了算!就留下一兩個人等待DNA鑒定結果,而其余的人則繼續向下游搜尋。陸續有人退出了這支隊伍,那是因為他們或者確認了親人的下落,或者找到了親人的遺體,但直到最后,還是有一支規模可觀的隊伍到達了一座大型水庫。退去的山洪就泄入了這座水庫。這座水庫的設計庫容超過12億立方米,可以想象它的水面有多大。然而,即使到了這地步,他們還是不肯回歸指定的現實,化悲痛為力量,投入重建家園的戰斗,而是滯留在水庫附近,甚至干脆在當地縣城住下,有空就到水庫邊上轉悠,甚至雇條船到水庫里面轉悠。他們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他們說,老話說了,總得活要見人死要見尸不是?他們的信心也是不可動搖的——他們說,那人只要是到了這里,總得有一天漂上來不是?不怕您笑話,看到這里時我流淚了。以我現有的識見,我確實沒把握判斷這種故事的真實性。假如突然爆出一聲斷喝: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我確實不會感到特別意外。不過我還是確信,這種故事會成為歷史,因為它是真相。
我估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弄文學批評的人,恐怕仍會陷在某種困境里,在故事和歷史之間,在真實和真相之間,被拋過來扔過去。但迎難而上的人總會有的。比如最近我就看到一篇文章,題目叫《“70后”:去歷史化的歷史寫作》,作者叫曹霞。對于這位作者,除了可以從名諱上猜測可能是一位女性,我一無所知,甚至都沒能從網上搜到簡歷,倒是由此覺得她應該是一位新銳吧。文章讀下來,明顯感到了她的聰慧,但我還是要首先向她的理論勇氣致敬。按我的理解,一個批評家的理論勇氣,是最容易從其立論上體現出來的。您瞧瞧這文章的標題,開宗明義,就沖著“去歷史化的歷史寫作”而去,絕對是一種迎難而上的氣概。換了我,腦子就簡單多了:“去歷史化”之后,就沒有“歷史寫作”了。
這種評論文章是可以當作故事來看的,你可以從中很容易地找到某種歷時性的過程。這篇文章的議論對象是70后作家,所以它的第一個情節就是把70后作家,去和50后、60后作家做對比,并且在沒有做什么真正的對比的情況下,就“清晰地辨認出”了70后作家的“異質性”與“陌生性”,和這一代作家的歷史寫作中“正在呈現出新的維度與格局”。這正好適合于當作故事中的一個情節,而不是邏輯推導鏈條中的一個環節。這并不影響論證。既然論者所要論證的是她立論的可信性,也就是70后作家的“歷史寫作”是“去歷史化的”,那么他們和50后、60后的差別并不是最重要的,何況我們從其他地方還有可能得知,這兩個“后”絕非全都是歷史化的歷史寫作,甚至還有相當不少的偽歷史寫作。于是,下一個情節就是檢視70后作家的歷史寫作實踐了。這個情節又被分成了五個小情節,分別代表著這種歷史寫作的四個特點,即“短歷史”,“鏡像”里的歷史,“旁觀者”的歷史,“非親歷者”的歷史,然后再把這四種歷史寫作混裝為“一代人的歷史寫作”。在這些情節的展開過程中,曹霞充分展示了她不俗的理論表達能力。按我粗略的統計,這里一共提到了十六部長篇小說,基本上都是一句話概括一部長篇小說,其中一個更出彩的地方,是在用四句話概括了四部長篇小說之后,又用一句話概括了這四句話以及它們所概括的那四部長篇小說。這兒得說句公道話。對于作家來說,自己的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被人家一句話就說完了,其切身感受很可能不是被概括而是被宰割,但對于批評家來說,這還真是一種必備的基本功。如果要我說這兒是不是還有某些不足的地方,那么我覺得在把這十六句話放在一起之后,雖然確實可以證明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作品,確實是“去歷史化”的寫作,但是并沒有證明這種“去歷史化”的寫作仍然是歷史寫作,反倒是近似于證明了我那個很簡單的擔心——“去歷史化”之后,就成了沒有歷史的寫作了。其實曹霞挺冤的。讀她的文章,常可感到她識文的“眼光”準確而敏銳。這是一個合格批評家不可或缺的秉賦。比如她在談到某部作品時說:“(該作)講述了‘文革’中的武斗場景,卻化解了歷史的沉重與恐懼,而填塞進了熱鬧、嬉戲、歪打正著的友誼、溫暖細小的私情。”如果顛倒一下順序再略改幾個字,變成“(該作)講述的是‘文革’中的武斗場景,卻填塞進了種種熱鬧、嬉戲、歪打正著的友誼、溫暖細小的私情,從而化解了歷史的沉重與恐懼”,豈不是剛好用來描述“去歷史化”是怎樣把歷史丟掉的?我尤其贊賞文中的一句話,道是“這一代作家比‘50后’、‘60后’都更為清楚地認識到了自己所處的歷史真空”。看得、說得多準啊!當然,得把“認識到”改為“表現出”。表現出了不等于認識到了,渾然不覺者所在多有,甚至曹霞也是其中一位。同樣也是在這篇文章里,她還說了一句很糟糕的話,道是“中國近三十多年來(也是‘70后’的成長和成熟期)并無多少別開生面的政治運動和重大的戰爭動蕩,堪稱風雨滄桑的近現代中國以來難得的‘無事’時光”。這甚至讓我想起一個傳說中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回目叫“丁某怒斥張某某”。初聽之下頗為錯愕。以我的印象,張某某原是個不錯的新銳批評家,怎么就會被我一向景仰的丁教授怒斥呢?原來張某某確實說了一番糊涂話,道是不該總是跟年輕人說“文革”怎么怎么樣,“文革”那點事,誰不知道?就算不知道,上網查查就知道了。若按這個,也該斥。曹霞的這個三十多年的“‘無事’時光”,亦此類也。不過我又想,錯便錯了,其情可原,其因可憫。他們確實有很多事不知道,但那是因為一些本該把這些告訴他們的人,卻將其瞞過了。這等講時,倒是丁教授這輩人更應該反躬自省,為什么您老們教出來的學生會這樣?
是不是都熱衷于講故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