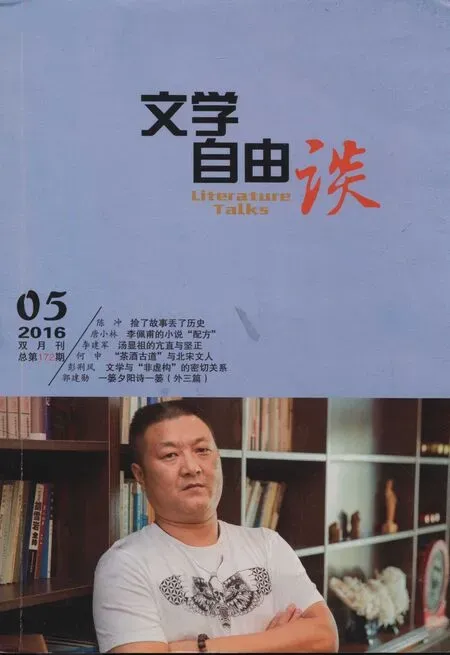一簍夕陽詩一簍(外三篇)
□郭建勛
一簍夕陽詩一簍(外三篇)
□郭建勛
今天到一個對對聯的網上逛了會兒,一個叫婉君的出了副上聯:“一簍夕陽詩一簍”。有好幾個人對,有“滿舟碧荷香滿舟”“滿天彩鴿祥滿天”“半窗冷月曲半窗”之類,均對得平平,沒有出句的好。對不好,我且揀了它做標題。
夕陽有點像過去當紅的窯姐兒,誰都要跟她來一腿,排不上隊的,心里也想著。翻開中國的古籍,幾乎每一頁都有“夕陽”,何止一簍兒?所以,再在這里寫夕陽,我都有點臉紅,紅得像空氣污染蠻嚴重時的夕陽,灰撲撲的紅。說起來更臉紅的是,我平生的第一首詩,也是寫夕陽的,至今仍記得“一輪紅日漸西沉”一句。幾年前又寫過一篇叫《他鄉落日》的散文,里面有幾句話,當時甚是得意:
我悚然驚醒到,我只是一個流浪的人,一個遠離故鄉在異地謀生的外鄉人。雖然這里有我的妻有我的兒,但這里沒有我的家,或許之前一度淡漠了這種異鄉之感,而現在,在這輪熔金般的落日里,我又已經確確實實、尖尖銳銳地感到這一點,我的家在那個千重山萬重水的資水邊的一個小小的山村里,那里才是我的家,才有我的根!
當然,我的得意只是敝帚自珍,不過是剝了崔顥的“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并無新意,更有拖沓之感。可見李白在黃鶴樓上擱了筆是對的:老崔算是把夕陽的那點意思寫絕了。所以,再讀諸如“竹憐新雨后,山愛夕陽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楓林滿江色,夕陽終古愁”“夕陽千古恨,分付短長亭”“夕陽簫鼓幾船歸”“孤村小店夕陽紅”等等,均覺味同嚼蠟。
聽說清朝有個叫鮑廷博的,嘗作《夕陽詩》二十首,人稱“鮑夕陽”。鮑的詩我沒讀過,也不想讀,估計也出不了老崔的意思。
姑從此處銷魂
曾國藩有挽聯癖,不僅給死了的人做,還給尚活著的人做。他所撰挽聯無數,但我以為寫得最好的,還是他送給一個相好的妓女的。妓女叫大姑,聯中嵌了她的名:
大抵浮生若夢;
姑從此處銷魂。
曾一生道學,唯此聯最現男人的真懷情,是周作人說的教書先生《論語》下壓著的那本《金瓶梅》。曾死了,別人送他的挽聯亦無數,但唯左宗棠的做得最好: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曾左二人素有隙,故傳對對聯互謔。曾出聯請左對:
季子敢言高?仕未在朝,隱未在野,與吾意見常相左。
左宗棠對:
藩臣多誤國,進不能攻,退不能守,問他經濟有何曾?
左挽曾的聯雖然不錯,但尚不是上品,仍有吹捧的味道。這大約也是做挽聯之大難,所謂蓋棺論定,其實是騙人的話,非得等棺爛了才能論定的。當然,也有例外,如楊度挽孫中山的:
英雄做事無他,只堅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
這是把孫中山當作人而不是神來看了。作為英雄,孫中山是一個失敗的英雄,而不是功冠絕代的成功的英雄。這是實話。
另有一聯可以與楊度挽孫中山的聯相媲美,是寫諸葛亮的: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此為清人趙藩所寫。趙系云南人,時任四川鹽茶使。此聯非夸獎而是諷諫,消解了諸葛的“正面形象”,有暗諷他好戰且不審勢之弊,也是一個失敗的英雄。
陽光不銹
曾讀到一個小故事,說是有個走天涯的文學青年,這天黃昏來到一個小縣城,抬頭看到招牌上四個字“陽光不銹”,覺得大有詩意。第二天再去看,原來是“陽光不銹鋼制品店”,不禁曬然。
這種小故事在《讀者》里常有,洋溢著偽善的溫情,看上去機巧,其實也不過是拾了禪宗打機鋒的牙慧。盡管如此,我卻還是蠻喜歡這個故事的,更確切地說,是喜歡“陽光不銹”這四個字。
“陽光不銹”和“陽光不銹鋼制品店”自有天壤之別,前者是詩的,后者是世俗柴米的。詩與世俗柴米差得并不遠,只隔了一張窗紙,捅一下就破了。
但捅破了就沒半點意思了。張岱《夜航船》中有個故事:一沙門與一秀才共渡。沙門因秀才乃讀書人,以為對方才高五斗,局促拘謹,盤坐一隅。后聽其大言欺人,方知是個繡花枕頭。恰值秀才高談闊論稍歇,問僧何如,沙門如釋重負,對曰:“小僧可以伸伸腿了!”
在我看來,這沙門的修行尚欠火候。佛門講忍耐為懷,他卻就這樣輕易地把腿伸了,急急地抖出 “陽光不銹鋼制品店”的招牌,其境界停留在那個走天涯的文學青年的層面。伸直了腿固然圖了個舒服,但“陽光不銹”的詩意他是欣賞不到了,更別說佛國的祥靄。
不過,話雖這樣說,其實我也并不比那位沙門高明。
有位老先生,懷揣舊學,游歷深圳,有點名氣,自己也以“學界泰斗”自居。一天,他拿出一本剛出的書送我,我瞟了一眼,覺得一首七律平仄對仗不對,就指出來了,弄得他一臉訕訕。至今想來,深以為憾。
退步原來是向前
看《魯豫有約》,是采訪李連杰的。在說自己心態的時候,李連杰記起了一首詩,即那首有名的“插田詩”,他忘了第三句。很湊巧的是,他忘掉的那句也正是我忘掉的。
不幾天去觀瀾跟好友釣魚,見面第一句話,他就問我這事,還說,他是專門等著問我這首詩的第三句是什么。原來他也看了那期的《魯豫有約》,恰恰也是把第三句忘了。我當然是回答不出來,錯過了一次“指導”別人的好機會。
第二天回來,我終于從網上查到了,原詩如下:
手把青秧插滿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凈方為道,
退步原來是向前。
第三句有好幾個版本,但我記得我當年背的就是上面抄的的這個版本,所以,其他的版本我也懶得抄了。
從這個事情上,我倒是想到了詩的一個問題。這首詩共四句,一、二句都是很具體地寫事兒,即所謂的形象思維;第四句雖然有點講理的味道,但味道不濃,也可以說是說事兒,至少可以介乎二者之間;唯第三句是純粹說理兒,而且是很臭的道理。這就是說,說理兒的句子讀者是很難記住的,唯有那些說事兒的句子一讀就記下來了。唐詩之所以膾炙人口,大抵是說事兒的,里面有細節,有畫面;宋詞更是,由于其篇幅更長,更有情節了,所以,我們能夠記住很多。但宋詩就大部分記不得了,為什么?就是說理,板著臉孔說理。
這就給了我們現在寫文章或寫詩的一個教訓:還是說事兒的好,而且,還要說得有趣,不要板起臉孔說教。
前段時間,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看了一篇文章,說王小波和王朔的,將二人從思想的高度上進行了評價。我認為這種評價有點扯淡,是思想性決定一切的病。說開來,我認為,二王最大的貢獻,就是把文字弄得有趣了,能夠逗人一笑,且一笑之余,能夠回味一點兒苦味。這與喝鐵觀音正好是相反的,鐵觀音是喝進嘴里的時候苦,吞了,就有回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