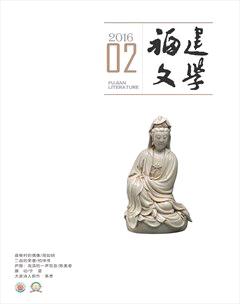健民短語(yǔ)
◎楊健民
?
健民短語(yǔ)
◎楊健民

楊健民,畢業(yè)于廈門(mén)大學(xué)中文系。研究員,中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享受國(guó)務(wù)院政府特殊津貼,首屆“福建省文化名家”稱號(hào)。著有《藝術(shù)感覺(jué)論》《中國(guó)古代夢(mèng)文化史》《論茅盾早期文學(xué)思想》《批評(píng)的批評(píng)》等。曾數(shù)次獲福建省社會(huì)科學(xué)優(yōu)秀成果獎(jiǎng)和省文學(xué)獎(jiǎng)。
斗茶
斗茶是男人的本事,女性一般不斗茶。見(jiàn)過(guò)幾次斗茶,基本上是男人。
斗茶的玩法就是對(duì)比,有對(duì)比才有區(qū)別,才能斗出個(gè)勝負(fù)。然而,斗茶是按照同一茶葉種類來(lái)斗的,巖茶不跟鐵觀音斗,紅茶不跟綠茶斗。見(jiàn)過(guò)幾次斗鐵觀音,清香型、濃香型和陳香型各自上陣。
某日下午,幾位好飲者想起來(lái)斗巖茶,有陳年鐵羅漢,乾隆老茶,五星和六星曦瓜版大紅袍,牛欄坑肉桂(簡(jiǎn)稱牛肉),還有老樅水仙等。巖茶種類多,比較豐富多彩,斗得也就有趣味,也算長(zhǎng)了一些見(jiàn)識(shí)。巖茶底蘊(yùn)深厚,飽滿沉著,有一種被稱為“巖韻”的意味在其中。巖茶一直是我近年來(lái)的最愛(ài),無(wú)論是它們中的哪一種,只要你抿上一口,咂出味來(lái),便完全沒(méi)有那種草本的微澀,只覺(jué)得巖韻里空間幽深,曲巷繁密,忽然就有了一種徜徉、探尋的余地。那個(gè)下午,數(shù)巡過(guò)后,一泡號(hào)稱乾隆老茶被撕開(kāi)了,一團(tuán)黑糊糊的茶塊被抖了出來(lái),放到鼻子底下聞一聞,沒(méi)有什么香氣。泡在茶盅里,有淺棕色漸漸漾出,隨后很快便蕩出了深黃色。湊上聞香杯一聞,整個(gè)像是普洱的味道,還有些藥香;喝上一小口,竟然是木頭的香味;等過(guò)了喉頭,便有一種巖韻慢慢釋出了。幾通過(guò)去,口感逐漸細(xì)膩,越喝越甜,然而不膩。老茶在腹中蠕動(dòng),胸間頓時(shí)通暢,舌下生津。這是什么老茶呀?一看茶盞里的茶渣,都已碳化碎裂,沒(méi)有了那種粗枝大葉的形狀。如此陳釅、透潤(rùn)的老茶,大家還是第一次品到的,于是欣喜莫名,驚呼這才是今天斗茶的“終極版”。收藏者說(shuō),其實(shí)它不過(guò)是1950年代的佛手。佛手不是鐵觀音嗎?怎么也拿來(lái)跟巖茶斗呢?待喝夠一大把了,眾人才醒悟,即便是幾十年前的什么茶,到這個(gè)時(shí)候骨子里的那種“老”的味道,釋放出來(lái)的一定就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藥香、二分草野霸氣。這就是老茶的“茶格”。
斗茶到如此境地,就不知如何來(lái)安頓自己的感覺(jué)了。過(guò)去的文人常以“好茶至淡”、“真茶無(wú)味”等句子來(lái)形容好茶,其實(shí)這是一種感覺(jué)的失落。不管怎么說(shuō),老茶是有“大味”的。有人說(shuō),老茶是老男人的茶。也許,只有男人、特別是老男人才真正知道老茶的韻味。老茶的深厚,沒(méi)有了綠茶的鮮活清芬,卻把香氣藏在里面,讓喝的人覺(jué)得年歲陡長(zhǎng)。在陳釅、透潤(rùn)的基調(diào)下,老茶變幻無(wú)窮,從藥香、木香、蟲(chóng)味進(jìn)入到普洱味,最后是甘甜,每一種重要的變換,都帶來(lái)新的的感覺(jué)和記憶,就像一個(gè)老男人一生的歷程。
靜氣
弟子從漳州寄來(lái)幾粒雕刻好的水仙,我把它養(yǎng)在水里。可能是干燥了幾天的緣故,一入水,它們竟然發(fā)出嗤嗤的聲響。我好奇地盯著水在冒出一圈一圈的細(xì)泡,覺(jué)得有些神秘。
這些水養(yǎng)的仙子,它們凌波的姿勢(shì)總不會(huì)是凝固的。水仙需要水,其實(shí)更需要的是靜氣。數(shù)年前,我辦公室里的一盆水仙,在開(kāi)放二十多天后突然倒伏了。倒伏的原因并不在其自身,而是一位好心的女同事發(fā)現(xiàn)水有些渾了,把它端到水龍頭下從頭到腳沖洗了一遍。結(jié)果搖搖欲墜的花朵經(jīng)不起折騰,全垂下高貴的頭顱。同事很內(nèi)疚,我也有點(diǎn)沮喪。賈平凹說(shuō)過(guò):女人不說(shuō)話就成了花,花一說(shuō)話就成了女人。水仙本無(wú)語(yǔ),只是靜靜地、默默地開(kāi)放著,直到慢慢變老。有些美是不能驚動(dòng)的,你一旦驚動(dòng)了它,它就倒了。水仙是淡雅而寧?kù)o的,無(wú)語(yǔ)的花是下自成蹊的靜美,但是它一開(kāi)口便成了女人,這時(shí)還會(huì)有靜美嗎?由此,我才感覺(jué)到賈平凹那句話的真正分量。
又是一年春來(lái)到,又將是一年一歲。變老是必然的,有些離開(kāi),是可以順其自然的,就像我們告別了過(guò)去的一年。所謂告別,不過(guò)是目光的一次出走,一切都可以靜止在生命走過(guò)來(lái)的甬道上。還記得那一杯喝得很慢很慢的玫瑰花茶嗎?坐在時(shí)光的風(fēng)中,往事被一滴滴稀釋,煩事也一片片凋零。這個(gè)時(shí)候你還會(huì)想到什么呢?俄羅斯象征主義詩(shī)人勃留索夫有句詩(shī):“他愛(ài)所有的大海,所有的碼頭,從無(wú)半點(diǎn)偏心。”我們也許不能做到巴赫無(wú)伴奏合唱曲那樣的純粹,但這句詩(shī)總是讓我感動(dòng)。李白當(dāng)年游峨眉山時(shí),曾在山上的萬(wàn)年寺毗盧殿聽(tīng)廣浚和尚彈琴,下山后他寫(xiě)了首《聽(tīng)蜀僧浚彈琴》,其中有句:“客心洗流水,余響如霜鐘。”說(shuō)的是人要有“洗流水”那樣的靜氣,有了靜氣就會(huì)有“如霜鐘”般的力量。
斯人往矣,境界猶在;靜氣若蘭,力量在心。人生中總需要有生命的溫度,就像水仙需要水,也需要一定的溫度。然而人也和水仙一樣,更需要一種平和與靜氣,才會(huì)自如地開(kāi)放,直到自如地結(jié)束。
思想的顆粒
多年前寫(xiě)過(guò)一篇《閱讀咖啡》,把咖啡讀成“思想的一種顆粒”。在我看來(lái),苦與澀是咖啡的本質(zhì)世界,然而咖啡真正的濃香又是從這苦澀中溢發(fā)出來(lái)的。我一直覺(jué)得,品味咖啡需要感覺(jué)和心境,需要有一種提純生活本質(zhì)的能力。
2011年冬天,我第二次去法國(guó),在巴黎呆了有十多天時(shí)間。巴黎有一萬(wàn)兩千多家咖啡館,每年能喝掉18萬(wàn)噸咖啡。巴黎人每天上班前都會(huì)先飲一杯咖啡,那樣就可以照亮他們一整天的時(shí)光。善于思辨并且崇尚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識(shí)的法國(guó)人,他們那些莊嚴(yán)的思想多數(shù)是在咖啡館里催生出來(lái)的。我讀過(guò)科塞的《理念人》,這本書(shū)描繪了18世紀(jì)那一群被咖啡所點(diǎn)染的新人類——“理念人”。他們“幾杯咖啡下肚,新鮮刺激、大膽妄為的言論便從嘴邊蹦到桌上,又從桌上躥到地上,隨即便興奮地跳起舞來(lái)”。18世紀(jì)的咖啡館就被這群“理念人”稱為一個(gè)思想表達(dá)的場(chǎng)所,它們以靜謐與沉思聞名。盧梭、孟德斯鳩一直是咖啡館的常客,伏爾泰在咖啡館里一次可以喝下40杯咖啡,蒙田的“我懷疑”,笛卡爾的“我知道”,帕斯卡爾的“我相信”等,就連近年來(lái)很火爆的阿倫特,都是在咖啡館里“研磨”出他們的思想顆粒。巴黎左岸咖啡館里的“花神”菜單上,有的還印上薩特的那句話:“自由之路經(jīng)由花神咖啡……”巴黎畢竟是巴黎,僅咖啡館就可以按照哲學(xué)、詩(shī)歌、戲劇、電影、音樂(lè)甚至天文來(lái)劃分主題,其中自然以哲學(xué)為盛。無(wú)怪乎徐志摩當(dāng)年會(huì)說(shuō):“如果巴黎少了咖啡館,恐怕會(huì)變得一無(wú)可愛(ài)。”
回到我所居住的這座城市,茶館、酒吧、咖啡館說(shuō)多也不多,我去過(guò)的就更少了。一段時(shí)間以來(lái),我在一家叫做“在咖啡”的咖啡館里虛擲了幾次光陰,那里有書(shū)讀,有人聊天,盯著眼前那杯被瓦解的深褐色的顆粒,覺(jué)得它似乎就溶化在我的感覺(jué)里,于是舌底開(kāi)始波俏,開(kāi)始瀾翻,目光炯炯,并且已經(jīng)被撩撥出一種想寫(xiě)點(diǎn)什么的沖動(dòng)了。“在咖啡”是一座精神的淵藪,是一個(gè)同樣帶有“煤煙”般苦澀香味的咖啡的名字,當(dāng)然,我更喜歡的還是那里時(shí)不時(shí)踅進(jìn)去一群詩(shī)人,他們紛紛把詩(shī)句抵押在那里,然后孵化。從秋天喝到春天,又從冬天喝到夏天,他們談海子,談?lì)櫝牵勈骀茫動(dòng)嘈闳A,談詩(shī)歌的時(shí)間的羽翼,以及詩(shī)的去向與歸途……這個(gè)春天,那個(gè)寫(xiě)過(guò)《春天,十個(gè)海子》的海子,一個(gè)都沒(méi)有復(fù)活,但是他身后的那些詩(shī)復(fù)活了,那些飽脹的詩(shī)的生命一句一句被攪活,被沉浮在“在咖啡”的咖啡里,就像海子筆下的《亞洲銅》那樣,藏匿著一個(gè)詩(shī)的燃燈人的痕跡。“在咖啡”,其實(shí)就是詩(shī)人的一個(gè)存在,一個(gè)詩(shī)意地棲居的場(chǎng)所。我還會(huì)來(lái)這里,在那種深褐色的浮沉中,尋找我的追問(wèn)和語(yǔ)言,尋找屬于我的“思想的顆粒”。當(dāng)然,我還會(huì)繼續(xù)尋找或追究咖啡最初的和最后的故事。
小巷的歷史和哲學(xué)
“撐著油紙傘,獨(dú)自彷徨在悠長(zhǎng)、悠長(zhǎng)又寂寥的雨巷……”誰(shuí)沒(méi)有低吟過(guò)戴望舒這首蕩氣回腸的《雨巷》?那位“丁香一樣地結(jié)著愁怨的姑娘”哪里去了?這種煎熬的旋律顯然不只是一個(gè)關(guān)于尋找的話題。我常常在小巷里一邊蝺蝺穿行,一邊在問(wèn)自己:你在尋找什么?其實(shí),我并不尋找什么,我只是徜徉,只是等待著城市人時(shí)常會(huì)目擊到的那一場(chǎng)遭遇。
2007年夏季的一天,我游走在布拉格著名的黃金小巷里,找到一座水藍(lán)色的房子。一百多年前,一個(gè)英俊而又憂郁的小伙子不堪忍受舊城區(qū)的嘈雜,搬進(jìn)了這座房子。他就是法蘭茲·卡夫卡。在這條童話般的小巷里,卡夫卡逃離了現(xiàn)實(shí),躲進(jìn)自己的世界,寫(xiě)出了著名的《城堡》。他孤獨(dú)、漂泊、恐懼、焦慮,這一切都寫(xiě)進(jìn)了他的字里行間。布拉格是個(gè)絕美而神秘的城市,有著眾多的小巷,在這里你隨時(shí)可以看到卡夫卡的腳印和昆德拉筆下的特蕾莎的背影。盡管卡夫卡說(shuō),布拉格就是“我的獄所,我的城堡”,盡管他的作品中充滿了丑陋和絕望,但是只要在這條黃金小巷里走過(guò),我都相信卡夫卡來(lái)到這里是為了尋找美麗、尋找希望的。布拉格的神秘在于它充滿童話般的燦爛,燦爛到人們很容易就忽略它的過(guò)去,以至于尼采發(fā)出如此的贊嘆:“當(dāng)我想以另一個(gè)字來(lái)表達(dá)音樂(lè)時(shí),我只找到了維也納;而當(dāng)我想以另一個(gè)字來(lái)表達(dá)神秘時(shí),我只想到了布拉格。它寂寞而又?jǐn)_人的美,正如彗星、火苗、蛇信,又如光蘊(yùn)般傳達(dá)了永恒的幻滅之美。”如此絕美的城市,讓我覺(jué)得它離卡夫卡小說(shuō)中所描繪的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境遇竟然是如此之遠(yuǎn)。
在黃金小巷里巡游的那個(gè)下午,我沒(méi)有迷失。我在讀這一條小巷的歷史和哲學(xué)。歷史是持久而又?jǐn)嗬m(xù)的,哲學(xué)是透明而又混沌的。那幾天布拉格遭遇到幾十年來(lái)最干熱的天氣,在四十余度的高溫下我揮著汗雨打量著這里的深街老巷。風(fēng)嘶啞了,像玻璃杯中的水,歸于沉靜。那么,什么是不沉靜呢?只有迷離,只有恍惚,只有那些難以承載的心理重量。正是在這個(gè)時(shí)候,我想起了福州的三坊七巷。其實(shí),福州原來(lái)就是淹沒(méi)在小巷之中的。小巷多少年來(lái)一直無(wú)聲地聆聽(tīng)著城市的呼吸,而現(xiàn)在一個(gè)喧囂的城市就要將它無(wú)聲地抹去。我似乎聽(tīng)到了小巷的如泣如訴,宛如天鵝的絕唱。然而,小巷依然達(dá)觀依然淡泊。誰(shuí)聽(tīng)過(guò)小巷一絲一縷的抱怨呢?不能想象小巷從這座城市撤走,喪失了小巷的纏綿和曲折,福州一定會(huì)失去許多的情韻。悠悠的小巷使得這座城市有了一種古老和滄桑,從而再現(xiàn)了這座城市的歷史。城市規(guī)模的不斷擴(kuò)大,相應(yīng)地切除了一些小巷。幸好,城內(nèi)的那些小巷還被保留著。如果不是這些熟悉的小巷為我留下相應(yīng)的記憶,我真要懷疑我腳下站著的,還是這座城市嗎?
詩(shī)歌的尖峰時(shí)刻
謝冕評(píng)論福建的四位女詩(shī)人冰心、林徽因、鄭敏和舒婷,末了引用了林徽因的詩(shī)句:“菩提樹(shù)下清蔭則是去年”,有其深意。我一直琢磨著這一句詩(shī),終于明白什么叫做“寂寞而偉大”,這注定是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歌史的一種面相。
余英時(shí)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胡適生逢其時(shí),“在胡適歸國(guó)前后,中國(guó)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我時(shí)常在中國(guó)文化究竟哪一段是屬于軸心時(shí)代這個(gè)問(wèn)題上犯困。這個(gè)問(wèn)題太大了,我的確說(shuō)不清楚。我想到的只能是這樣一個(gè)詞:“尖峰時(shí)刻”。這個(gè)詞現(xiàn)在多用來(lái)比喻上下班的車水馬龍,我或許可以用它來(lái)比喻現(xiàn)在的詩(shī)壇。詩(shī)的“尖峰時(shí)刻”來(lái)臨了么?當(dāng)代詩(shī)壇似乎就是一場(chǎng)變形記,詞語(yǔ)的尸骨和感性的妖魅正在不斷地撕裂詩(shī)歌的文本,甚至我們都來(lái)不及躲避它那閃電一般的炫目。
我讀詩(shī),也讀詩(shī)人,卻總是無(wú)法忍受詩(shī)人生命的脆弱。在海子離世了二十五年之后,一位原本比他還要年長(zhǎng)的詩(shī)人,懷著中年的荒寒與悲涼,在徹悟中飛躍向黑暗的一刻。他就是陳超。他在當(dāng)代詩(shī)歌的“尖峰時(shí)刻”遠(yuǎn)離了詩(shī),遠(yuǎn)離了詩(shī)歌的精神現(xiàn)象學(xué),從而成為了一個(gè)敏感而無(wú)解的話題。再一次捧讀陳超的《我看見(jiàn)轉(zhuǎn)世的桃花五種》,我突然意識(shí)到他的修辭是那樣精準(zhǔn)和完美,如同他的那些刀鋒般精準(zhǔn)的詩(shī)學(xué)評(píng)論。“桃花剛剛整理好衣冠,就面臨了死亡。/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淺淡。/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沙高一些,/它死過(guò)之后,就不會(huì)再死。/古老東方的隱喻。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只要讀一讀這幾句,大概就可以看出生命中那種血的悲愴,正綻放在時(shí)光與歷史的黑暗與恍惚之中。陳超以他的詩(shī)句,宿命般驗(yàn)證了不可躲避的悲劇意味,以及讖語(yǔ)一樣不可思議的先驗(yàn)性。
詩(shī)歌其實(shí)是很殘酷的語(yǔ)言游戲,它可以殘酷地讓情感的傷口在閃電中飛翔,然后縱身下落;它可以在風(fēng)和日麗的林間小溪狠狠剜下一刀,然后凍結(jié)隱喻;它還可以讓深秋退回陽(yáng)春,讓泥土躍上枝頭,完成生命的一次輪回。我始終敬畏詩(shī)歌,敬畏詩(shī)人,敬畏詩(shī)是如何聽(tīng)從死亡與黑暗、創(chuàng)痛與傷悼的魔一般的吸力。但無(wú)論如何,詩(shī)還是詩(shī),它不會(huì)失憶,不會(huì)以一塊簡(jiǎn)單的靈魂拼圖的七巧板形式鎖住詩(shī)人的想象力。菩提樹(shù)下的清蔭盡管已經(jīng)成為了去年,成為了昨天,卻依然是詩(shī)人精神歷險(xiǎn)的完成式。“尖峰時(shí)刻”——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詩(shī)歌的精神肖像,既有從前詩(shī)人的熱愛(ài),也有當(dāng)代詩(shī)人的歡愉。我們只要憑著一些詞語(yǔ),就可以將詩(shī)與生活的手握緊。
鄉(xiāng)愁
“鄉(xiāng)愁”一詞,頗具意味但是不容易觸碰,因?yàn)樗詈脑S多內(nèi)容。忍不住尋思下來(lái),發(fā)現(xiàn)詩(shī)人是最“鄉(xiāng)愁”的。鄭愁予的鄉(xiāng)愁:“我達(dá)達(dá)的馬蹄是美麗的錯(cuò)誤”;余光中那一枚“小小的郵票”,幾乎成了“鄉(xiāng)愁”的代名詞。而作為小說(shuō)家的阿城則在《威尼斯日記》里這樣寫(xiě)道:“所謂思鄉(xiāng),我觀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異鄉(xiāng)食物,不好消化,于是開(kāi)始鬧情緒。”阿城從亞利桑納州開(kāi)車回洛杉磯,路上帶了一袋四川榨菜,嚼過(guò)一根,家鄉(xiāng)的“味道就回來(lái)了”。把榨菜腌成了故鄉(xiāng),情感就變成一種榮耀。每一次出國(guó),都有朋友提示多帶些榨菜,身在異地,只要榨菜在,那種熟悉的家園的味道就在。所以說(shuō),故鄉(xiāng)不是別的什么,故鄉(xiāng)就是一種味道、記憶和感覺(jué)。
莫迪亞諾的小說(shuō)《夜巡》里有一句對(duì)于巴黎的描述,一直觸動(dòng)著我:“她是我的故鄉(xiāng)。我的地獄。我年邁而脂粉滿面的情婦。”思鄉(xiāng)的情結(jié)無(wú)論多么堅(jiān)韌,都是受雇于一個(gè)偉大的記憶。小時(shí)候生活在鄉(xiāng)下,一到夏日傍晚,坐在溪邊那一叢石崖上,給小伙伴們講“三俠五義”,講“水滸”,始于一個(gè)故事的謎,結(jié)束于另一個(gè)謎,總是有一群熱切的期待和守候。所有的未知和未明,不斷地被更廣闊的消逝和疑問(wèn)所籠罩。離開(kāi)故鄉(xiāng)近四十年了,我時(shí)時(shí)在揀回那些無(wú)法忘卻的記憶的碎片。那是屬于我的“達(dá)達(dá)的馬蹄”,是屬于我的“美麗的錯(cuò)誤”。
有時(shí)候想,面對(duì)故鄉(xiāng),我可能就是一只迷離的鹿,但在我的文字感覺(jué)里,我覺(jué)得又有一只鷹以及無(wú)盡的夜色在盤(pán)旋著。家鄉(xiāng)對(duì)我一直是一種延宕,一種閃爍,無(wú)論追憶還是探尋,我都感到人與自然、人與歷史正在發(fā)生一種巨大的斷裂。我曾經(jīng)為家鄉(xiāng)那條變黑的溪流寫(xiě)過(guò)一首悼念的詩(shī),那一叢石崖哪里去了?那些游動(dòng)的魚(yú)哪里去了?這還是我的“美麗的錯(cuò)誤”嗎?它最終成了我的憂傷和我的痛苦。人到中年,真的只是開(kāi)始“關(guān)懷自身”了嗎?我不斷地跟家鄉(xiāng)的土地和草木邂逅,追尋它們的漫漶和斑駁。其實(shí),就像莫迪亞諾在他的另一部小說(shuō)《暗店街》里所說(shuō)的,我們都是“海灘人”,“沙子把我們的腳印只能保留幾秒鐘”。
然而,我們所有的思鄉(xiāng)說(shuō)白了,就是追溯那些腳印。那么,“鄉(xiāng)愁”中的歷史會(huì)重演嗎?或者說(shuō),有多少“鄉(xiāng)愁”可以重來(lái)嗎?這就是我的一點(diǎn)可憐的想象。我想起馬克·吐溫說(shuō)過(guò)的一句話:“歷史不會(huì)重復(fù)自己,但會(huì)押著同樣的韻腳。”也許,這就夠了。
回望小柳村
小柳村拆了,又有一條街巷被切除了。說(shuō)不清在這里的多少個(gè)曾經(jīng):曾經(jīng)騎著自行車載著女兒去附近的幼兒園時(shí)路過(guò)這里,曾經(jīng)去省畫(huà)院找畫(huà)家謀哥聊天時(shí)蝺蝺獨(dú)行過(guò)這里,曾經(jīng)在夜晚散步時(shí)抄近路斜插過(guò)這里……曾經(jīng),曾經(jīng)其實(shí)就是路過(guò),無(wú)論在腳下還是在心里。
此時(shí),我突然就聞到昔日的某種氣息,令我不由得有點(diǎn)心悸地打量了它一下。這里的一家理發(fā)店終于搬走了,不知搬到何處。從八十年代初起,我數(shù)不清在這家理發(fā)店躑躅過(guò)多少時(shí)光。不能說(shuō)對(duì)這里沒(méi)有感情,街巷的歷史頃刻就要擦肩而過(guò),早晨的風(fēng)不會(huì)再讓人感受到它的更多的內(nèi)容。2000年時(shí)搬進(jìn)更靠近它的一座樓居住,從樓上一眼望去,無(wú)規(guī)則的錯(cuò)落而顯得雜亂的民房,從早到晚市聲攘攘,不時(shí)在深夜會(huì)傳來(lái)一聲摔杯子的脆響,或是一兩聲奇怪的尖叫,時(shí)而還有犬吠和母貓叫春的哀嚎。
滾滾紅塵,風(fēng)吹云散,我相信這一帶的深巷是有記憶的。這個(gè)記憶讓我在這座城市的這條街巷迂回了三十多年,它的每一處輪廓都深刻著一種屬于它們的鄉(xiāng)愁。的確,不需要太多的歷史事件的陳述,我都能觸摸到它的某些有意思的局部。比如,我妹妹曾經(jīng)在這里租住了幾個(gè)月時(shí)間,每一次我去探望她,都會(huì)感覺(jué)到留存在這里的一些時(shí)間的空隙和事件的懸疑。當(dāng)然,這并不是一個(gè)什么神秘地帶,而是讓人覺(jué)得可能存在著某些晦暗不明的東西,如同這個(gè)并不古老的街巷,在今天的最后一次負(fù)痛的掙扎。
我移居閩江邊也將近十年了,那里的深夜常常安靜得只能聽(tīng)見(jiàn)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于是有時(shí)就會(huì)回憶并懷念起小柳村的喧鬧。如今,這里的一切正在一步步地隱退,它幾乎連軀殼都不會(huì)留下。至于這里將會(huì)矗立起一種什么樣的期待,坦率地說(shuō),我并沒(méi)有太多的興趣。不是因?yàn)槲乙呀?jīng)移居別處,也不是因?yàn)檫€有別的什么原因,而是緣于對(duì)這座城中村的歷史乃至一條街巷的記憶和氣息的追溯和回望。甚至,我會(huì)無(wú)端地在腦海里閃現(xiàn)出這樣一幕:某日陽(yáng)光灼熱,一位高齡老婆婆佝僂著身子,坐在巷口的一張歪斜的石凳子上,呆望著匆匆來(lái)去的行人。這或許就是歷史的某些黑黝黝的鄉(xiāng)愁的節(jié)點(diǎn)抑或斷點(diǎn),密集地在我腦海里浮現(xiàn)。推土機(jī)正在亢奮地來(lái)回穿梭著,我看著它,看著這里的每一個(gè)暗角,想著我的這些小感慨其實(sh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還是決定動(dòng)手寫(xiě)下這則短語(yǔ),記錄下這個(gè)夏天的這些熾熱的動(dòng)靜。
責(zé)任編輯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