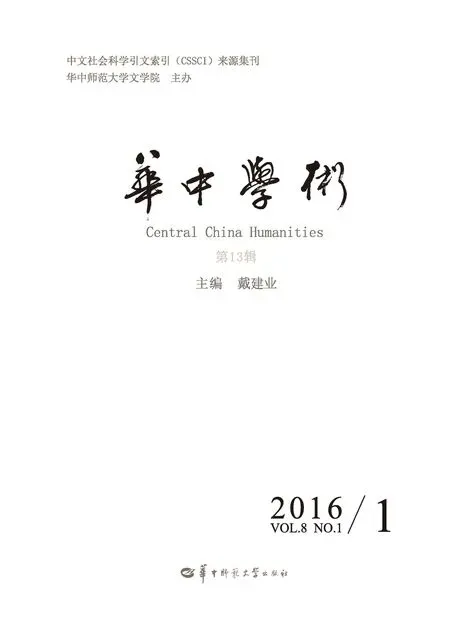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中的泛地主化書寫
王雨田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
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中的泛地主化書寫
王雨田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內容摘要:新中國十七年文學中,農民形象的多樣性在部分小說中呈現出泛地主化現象。因此,可以從相關小說中塑造反面地主形象的政策依據、作者被壓抑的主體性與農民的泛地主化描寫這幾個方面入手,論述其中地主與農民形象的書寫形態及其原因,揭示作家與時代主潮的復雜關系。論文通過這一時期小說中的相關形象研究,反思十七年土改小說研究。
關鍵詞:十七年文學;農村題材;地主形象;泛地主化
中國文學世界中廣義的地主形象古已有之,但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視角下的地主形象則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的革命小說中才開始進入人們的閱讀視野。自那時起的地主形象始終與當時的政治形勢緊密相關,因此,不同時期反映地主生活的小說也表征了多向度的政治生活側影。本文主要考察十七年農村題材小說中地主形象塑造的一些特點,而因為解放區文學與十七年文學存在諸多共通之處,故我們不妨從解放區文學作品中的地主形象談起。
一、解放區土地政策影響下的地主形象
1942年2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的第二條指出:“聯合地主抗日是我黨的戰略方針。但在實行這個戰略方針時,必須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針……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有許多地區并沒有認真實行發動群眾向地主的斗爭,黨員與群眾的熱情都未發動與組織起來,這是嚴重的右傾錯誤。”[1]
很快,身在解放區的康濯在1943年、1944年完成了兩個短篇小說《臘梅花》和《抽地》。這兩篇小說是目前能看到的較早以農民和地主的交鋒為描寫對象的解放區小說,它們的高潮部分都描寫了農民群眾反對地主“抽地”,這源于解放區一直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小說對交鋒雙方的場面描寫相當克制,但它們在當時并未引起評論界的注意。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的《減租和保衛生產是解放區的兩件大事》指出:“我黨當前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站在自衛立場上,粉碎國民黨的進攻,保衛解放區,爭取和平局面的出現……目前我黨方針,仍然是減租而不是沒收土地。”[2]
有研究指出,在1946年以前的解放區小說中,“‘地主’形象……與十惡不赦的壞面貌還相差很遠”[3]。例如,小說《談判》(束為,1943)中的地主馬寡婦面對農民的強勢逼問而輕聲細語。在束為1946年發表的兩篇小說《紅契》與《老婆嘴退租》中,還出現了兩個可笑的地主形象。前者中的笑面虎威脅農民:“你要不報告農會,我就答應把租子減一減,如果你報告農會,我就到你家大門口上吊。”[4]后者中的老婆嘴在減租大會上對眾人說:
“好,要減要退由你們!眾人是圣人,我一定照眾人的意思辦……”老婆嘴接著大聲問道,“明天退,眾人憑過我憑不過?”眾人一想到他逃跑兩次的經驗,就舉起胳膊吼道:憑不過![5]
這些描寫透露的信息主要有兩點:(1)老解放區在1945年以前的“減租減息”運動促使一部分地主以抽地、賣地的方式避免更多的開支;(2)此時的小說描寫更多還是嘲諷地主的蹩腳、土氣以及他們的小農氣息;而且,農民與地主的交鋒缺乏階級上的對立性。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其中鼓勵農民通過積極的方式從地主手里獲取土地[6]。“五四指示”的發布意味著“減租減息”已不再居于主導位置。對此,文學的反映則是突顯地主與惡霸的緊密聯系。如韋君宜的小說《三個朋友》(1946)中偽善的地主黃宗谷便是一個典型個案。此外,《血海深仇》(俞原,1946)中的地主婆、《烏龜店》(韓川,1947)中的朱元安、《一個空白村的變化》(那沙,1946)中的陳立賢、《孫賓與群力屯》(白朗,1947)中的姜恩、《棺》(白朗,1947)中的馬得鏢等人也與之相仿。
隨著解放戰爭的結束及1950年8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的發布,土改由解放區推向全國,如何處理地富階層成為土改運動的中心任務。很快,地富階層退出了現實生活的場景,他們在小說中繼續以開明形象出現就會顯得不合時宜。例如,趙樹理在解放區創作出了一系列涉及地主形象的小說,并慎重地對其中的個人倫理觀進行了處理,但他的創作也很快陷入了困境[7]。對于如何準確地表述農村的階級關系及其問題,作家們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準備。相對規范的作品要等到合作化運動以后才會出現。
二、作家個體倫理對政治倫理思想的偏離
反面地主形象的塑造總是有賴于當時的政策條文,但這并非是說我們就可以忽略作家的主體性創造和其隱含的寫作倫理。面對戰爭時期有限的創作條件,作家的個體倫理在解放區小說中已被隱晦地予以呈現。例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對地主和惡霸進行了區分,兩者并不是一定聯系在一起的“惡霸地主”[8]。而在趙樹理的兩部小說《李有才板話》和《李家莊的變遷》中,前者的地主閻恒元只是出現在眾人的講述中,他本人一直未出現在批斗會現場;后者的地主李如真則被憤怒的群眾肢解。
進入五六十年代,作家的個體倫理以更曲折的方式展現出來。例如,《創業史》部分地反映了鄉村在倫理重構以后,新的倫理主體在鄉村資源分配問題上的曖昧態度。土改時的積極分子、干部郭振山因為大家的擁護,不僅自己私下里買了幾畝地,還“笑納”了幾畝好地。他在土改還在進行中的1951年就給自己設立了追趕富裕中農郭世富的“五年計劃”[9]。土改時擔心自己被劃為地主的郭世富抱病向郭振山求情,最后獲悉自己的成分只是富裕中農,很快病愈。土改過后,富農姚士杰尋求機會與郭世富聯合起來沖擊互助組越來越大的影響。而且,郭振山與姚士杰的聯系一直是暢通的。如果互助組不能成功,那么這位土改時的積極分子將與上述二人形成一個新的小團體。鑒于互助組在虛構與現實中形成的鮮明對比,這給了在土改中成長起來的郭振山等人在現實中形成新的地富階層的可能,并且這在現實中得到了印證。例如,社會學專著《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中描述的村支書耿長鎖就是這種現象的原型。
在這一時期超出固定敘事模式的相關小說中,作者被壓抑的個體倫理反而得以彰顯。例如,孫犁完成于1950年1月的小說《秋千》中,從頭到尾一直就大絹的爺爺老燦是否為富農進行討論,但爭論的中心(富農候選人)一直缺場。這讓我們意識到作家或許想借助這樣的敘述空白來思考階級劃分中更為深刻的意義內涵。據檢舉人劉二壯的描述:“她爺爺叫老燦,當過順興隆缸瓦店的大掌柜,家里種到過五十畝地,喂過兩個大騾子,蓋了一所好宅子。”[10]根據剝削超過家庭總收入25%應該被認定為富農這一標準,劉二壯認為他是富農。但大絹對自己生活的講述是,自從日本人來了以后,他們家被洗劫一空。從她記事起,“兩手沒閑過……我哪見過大騾子大車呀?”[11]隨后,從其他人的對話中,我們進一步了解到,她爺爺從小家里很窮,長大后通過自己的勤儉與努力,開了一個小雜貨店。隨著生意越來越好,幾年以后“人們看著他有本事,就有的拿出股本,叫他領東,開了一座缸瓦瓷器店,這就是順興隆,用了幾個伙計,很是賺錢,三年一帳,三年一帳,他要了幾十畝地……”[12]負責這個村莊土改的李同志了解完上述情況后立即問道:“這時就雇了長工”?[13]李同志的態度恰當地詮釋了土改中如何劃分階級的要義,即按是否存在剝削為衡量的標準。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中對于劃分地主與富農分別是這樣規定的:“占有土地……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一般占有土地……但經常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之一或大部……”[14]但當大家討論大絹爺爺的階級成分時,他早已經成了破產富農。按上述《決定》指出的“破產地主仍然是地主的一部分……但地主破產后,依靠自己勞動為主要生活來源已滿一年者,應予改變成分。地主破產后,依靠自己勞動為生活來源之一部分,此部分達到其一年生活費用三分之一者,得照富農成分待遇”[15]來看,老燦不應被劃為富農。但群眾的意見在劃分階級中占據重要地位:“在某些情形下……而群眾不加反對者,仍不是富農,而是富裕中農。”[16]例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富裕中農顧涌就在群眾的積極建議下被劃為富農。當時富農已被納入“地富”群體,其農民群眾身份已被淡化。而地方政府為了避免改革中的右傾保守主義,也會對普通農民的翻身觀念進行強化。
1950年1月的《人民文學》發表了秦兆陽的小說《改造》,其中的王友德不同于此期相關小說中的其他地主。他既非惡霸,也不反黨,但小說作者被要求作檢討,因為小說的內容更像是戲謔一個小地主被改造成功的歷史,沒有寫出地主對農民殘酷的階級剝削,反而淡化了兩者之間的對立性。也就是說,作家在小說中表現出了某種溫和的土改理想。
《改造》和《秋千》這兩個短篇小說都發表于1950年土改即將全面展開的前夕。如果將二者進行對比,可見兩位作家都在構建一個理想的土改景象。《秋千》一直在討論如何劃分地富階級的標準問題。孫犁對大絹爺爺的過往持肯定和同情態度,這一形象或許潛隱地表現了作家的困惑:即憑借勤勞、聰明和能干來積攢財富的人是否應該被劃為地富分子。《改造》則在輕松戲謔的敘述中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和平土改”的可能性。有研究指出,中共中央在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初,出于種種考慮曾經嘗試過“和平土改”。其核心是通過和平贖買的方式向地主征收土地[17]。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秦兆陽的經歷。他在1938年來到陜甘寧邊區,“先后在陜北公學和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后到陜甘寧邊區保安處編印的《鋤奸畫報》工作”[18]。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我們尚不知道作家在此期間是否已經接觸到中共中央對土改的一系列相對溫和的文件,更不能確認他接觸到這些文件后,對土改的最初認識是否持單純樂觀的態度。如果上述推論成立,作家寫出戲謔性的《改造》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他并未接觸到相關文件,那就只能說作家對政治氛圍具有極其敏銳的感受力,并努力用藝術的形式去思考:土改中對地主的改造還能有別的方式嗎?很可能作者明白土改之激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小說中轉而表達了對“和平土改”的盼望。
對《改造》的批判指出了作家要學會如何用階級斗爭的方法來創作,即對地主的書寫必須突出其非人民的特性。這正如《艷陽天》中的村支書蕭長春在鄉長李世丹質疑沒有明確證據就隨便扣押地主馬小辮時回擊的:“憲法是保衛人民的,還是保衛地主的?”[19]
三、地主身份與心態的泛化
一系列歷史學研究成果都告訴我們,土改運動中一度存在將地主身份泛化的傾向;而在相關題材的小說藝術里,我們則看到人物身份和心理的雙重泛化。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相對于一般的農民,地主算農村中的富裕階層。對此,孫中山曾有“大貧”和“小貧”的看法。國民政府時期延續了這種看法,并認為“各縣現在不分佃農與地主,俱是貧窮”[20],他們不過是“大貧”與“小貧”之分。而“貧”的具體表現就在于土地的缺乏。1937年1月,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發布的《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認為,土地“分配顯然不均”,同時也強調“我國業主大多皆有地而甚少”,即使是“百畝之家,在華中華南比較上似已不小”[21]。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尚且如此,進入戰火紛飛的20世紀40年代以后,農村的生存條件可想而知。
對于農民的泛地主化,不妨根據現實中農民與地主的生活水準來觀照小說中二者在觀念上的互通之處。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晉西北為例:“白面在這里則更是極為奢侈的原料,只有在經濟優裕的人家或年節時才能看到……”[22]平時能吃上白面的已經是當地條件最好的地主了,這還是抗戰爆發前的生活水準。當戰爭爆發后,因為日軍的洗劫和“各種政權組織為動員所有社會資源進行抗戰而加之于地主階層逐年居高不下的各種捐稅負擔直接削弱了晉西北鄉村的地主經濟”[23]。以上因素造成的雙重甚至多重支出也會導致一般的地主倒退為中農甚至貧農。有研究以新中國剛成立時的四川省遂溪縣附西鄉的調查為例:
在農民眼里,貧富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一年吃多少頓大米上。但即使在地主家,一年四季最多也就80%的時間能吃上大米,貧農再窮一年也有大約四分之一的時間吃上大米。幾乎所有的調查都支持一點,即無論土地占有相差比例多大,都不足以證明地主在生活程度上一定會比一般農民高出多少。[24]
此看法建立在“中國占地主階層絕大多數的地主,多半都是些從小農中間逐漸成長的小地主”[25]這一結論的基礎上。有學者指出,在小農經濟的中國,“農村中并沒有固定的社會階層,各階層處于不停的分化與流動中……地主富農與中農貧農周期地永無休止地對流易位”[26]。可見,在某種程度上地主和農民實際上是相互泛化的,并且,此期小說中極少出現生活水準高的地主。例如,《紅旗譜》中描述的“惡霸地主”馮蘭池生活在民國時期,一直穿著穿了15年的破皮襖,吃糠菜,出門坐牛車。其子讀過大學的法科,當過軍法官,回家后建議父親開油坊,經商。但這些新觀念招來了馮蘭池的堅決反對,并以“你老輩爺爺都是勤儉持家……來錢的正道是 ‘地租’和 ‘利息’”[27]。這些描寫充分說明了馮蘭池的小農思想。這樣的地主究其本質也是農民。
《創業史》中最重要的人物梁生寶在解放前為了創立家業,“頭一年就租下呂老二的十八畝稻地,并且每畝又借下二斗大米來買肥料……”[28]盡管由于地主和政府的雙重剝削導致梁生寶創業失敗,但他在后來的土改運動中突然不再有單獨發家致富的想法,而是想要帶領身邊的貧農們一起共同富裕。如果梁生寶在佃戶時期意外發家,小說當然無法成立,但曾經同為貧農的郭世富兄弟三人倒是在土改前發家了。他們靠租種軍閥地主的48畝地創業成功了。盡管郭世富后來被劃為富裕中農,但我們無法得知分別租種惡霸地主與軍閥地主土地的同村村民梁生寶與郭士富為什么在創業的結果上差別巨大。將兩者進行對比可以得出一個帶疑問的結論:發家的偶然性因素太大。郭士富與梁生寶盡管生活在同一個村莊,但郭士富碰到了好雇主,并在其庇護下沒有被巧取豪奪,而梁生寶卻沒有這樣的好運。不論創業的結果如何,在試圖創業的初始階段,包括梁生寶在內的每個農民都渴望發家致富。這種期盼不僅僅是普通農民具備的,它也蔓延到不少農村干部自身。村民之間對于如何富裕存在不同的理解。如何將他們的沖突整合為一個整體,是所有相關作品都無法回避的問題。
如果說,相關小說的創作本意是將地主與農民表述為地主/農民這樣兩種截然對立的主體,但在實際的書寫中,二者之間呈現出農民向地主泛化的趨勢。這體現在農民的思想觀念向過往的地主趨同。也正因為有這種農民和地主心態的互相泛化,我們才會在《山鄉巨變》、《創業史》、《艷陽天》等經典小說中看到圍繞兩條路線的斗爭貫穿始終。如果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一部分各方面能力有所欠缺的農民會產生恐慌感。正如《艷陽天》中的模范飼養員馬老四對中農焦振茂說的:“憑你的家底,你的勞力,你的本領,要是我們跟你一塊兒走資本路,你能當地主,我們就得當你的長工;換個思想說,你不走社會主義路行,我們不走不行啊……”[29]這種恐慌感讓作家在書寫部分農民形象時不得不限制其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存在。盡管幾乎所有相關作家都指出這些人物(王菊生、郭世富、韓百安等人)吃苦耐勞,但他們這樣做都是為了自己而非集體。最終,對個人家庭生活的追求讓他們與過往象征私有制的地主形象部分重合。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0~52頁。
[2]《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116~1117頁。
[3]沈仲亮:《在小說修辭與意識形態之間——從峻青〈水落石出〉看解放區小說“地主”形象的嬗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1期,第178頁。
[4]束為:《老長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5頁。
[5]束為:《好人田木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45~246頁。
[7]據杜潤生回憶,趙樹理在1951年9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上明確表示:“農民不愿參加合作社,連互助組也不愿參加。”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頁。
[8]丁玲曾經談到《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富裕中農顧涌的原型,她的這段相關描述現已出現在一些相關研究的引用中,這里不再贅述。抱著這樣的認識去書寫土改,丁玲的個性得到了有限的展示。
[9]柳青:《創業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頁。
[10]孫犁:《孫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20頁。
[11]孫犁:《孫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21頁。
[12]孫犁:《孫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13]孫犁:《孫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14]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七)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91頁。
[15]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七)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2頁。
[16]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七)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7頁。
[17]楊奎松:《關于戰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嘗試與可能性問題》,《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
[18]北京語言學院《中國文學家辭典》編委會:《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 第一分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5頁。
[19]浩然:《艷陽天》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第1807頁。
[20]段本洛、單強:《近代江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4頁。
[21]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編:《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土地調查報告第一種》,1937年,第30頁。
[22]張瑋:《三四十年代晉西北農民家庭生活實態——兼論“地主階層”經濟與生活水平之變化》,《晉陽學刊》2005年第1期,第86頁。
[23]張瑋:《三四十年代晉西北農民家庭生活實態——兼論“地主階層”經濟與生活水平之變化》,《晉陽學刊》2005年第1期,第90頁。
[24]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問題》,《史林》2008年第6期,第17頁。
[25]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問題》,《史林》2008年第6期,第1頁。
[26]唐致卿:《近代山東農村社會經濟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頁。
[27]梁斌:《紅旗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71~72頁。
[28]柳青:《創業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13頁。
[29]浩然:《艷陽天》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第650頁。
【推薦人語】論文主要探討了十七年文學農村題材小說中的泛地主化現象。論者有較明確的文學史意識,首先從其“前史”——解放區文學中的農民形象與土改政策之關系——展開論述,進而把捉到在主流政治話語統攝之下作家個體倫理的潛滋暗長。全文以政治話語與作家主體性的互動關系為核心,較好地呈現了被當代文學史宏大敘事所遮蔽的歷史復雜性。該論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十七年土改小說研究中的“地主/農民”二元對立論析范式,頗具新意,特此推薦。(許祖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