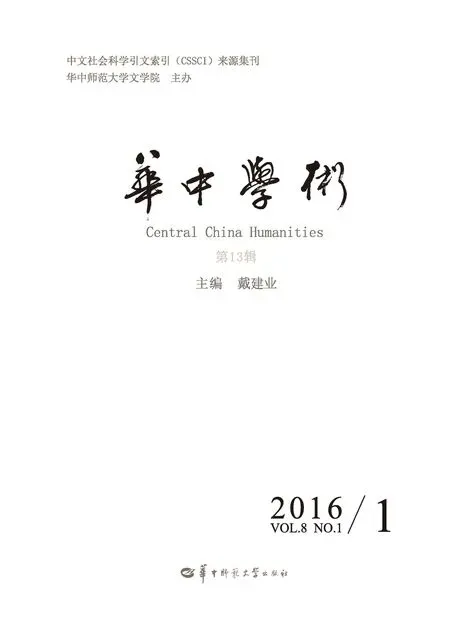世紀焦慮與歷史邏輯
——林語堂論中國文化的幾點啟示
陳國恩
(武漢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67)
?
中國現當代作家與作品研究
世紀焦慮與歷史邏輯
——林語堂論中國文化的幾點啟示
陳國恩
(武漢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67)
內容摘要:20世紀,林語堂對中國文化既進行了批判,也給予了肯定。林語堂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則經歷了一個從全面批判到有條件肯定的過程,而林語堂對中國文化的肯定,不是從中國傳統的角度來肯定中國文化的優點,而是從西方文化背景上向西方人展現中國文化的長處。盡管在批判與肯定中國文化中,林語堂的思想呈現出一定的復雜性,但對于我們今天進一步認識中國文化,仍然是有啟示性的。這也正是林語堂批判與肯定中國文化的觀點的現實價值之所在。
關鍵詞:林語堂;中國文化;西方視角;時間邏輯
在現代作家中,腳踏中西文明,向中國人說西方文化,向西方人說中國文化,兩頭討巧,成為世界文化名人,最成功的恐怕就數林語堂了。有人說林的國學根底比不上周氏兄弟,這或許是實情,但林語堂的長處是英語了得,不像周作人雖然深解從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文明,但他說中國話還帶著濃重的紹興方音,曾讓邀請他給北大學生演講的梁實秋直呼聽不懂,以為聽他的報告真不如看他的文章,那就更遑論要周作人用英語向英國人、美國人演講了。這意思是說,林語堂的優勢不在專門學問,而是中西文化兼通。這篇文章的主旨,也就與林語堂的這一優勢有關:因為他通中西文化,所以他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國文化的過去、當時和未來,他表面灑脫中的實質性焦慮,就具有別人所不具備的特別感受,提出的問題也就更值得我們深思。
一、從全面批判到有條件肯定
在“五四”時代,鑒于啟蒙的需要,中國現代作家絕大多數對傳統文化持批判的態度,有些還非常激烈。比較起來,留學英美的骨子里西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反而相對平和,個別的像聞一多,甚至稱他愛中國,固然因它是自己的祖國,更因為中國有它那種可敬愛的文化[1]。林語堂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比較接近魯迅和周作人,比如他寫了《祝土匪》,把自己與所謂的“學者”區別開來,宣告:“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代學者夭滅殤亡之時。到那時候,卻要請真理出來。”[2]在寫給錢玄同的信中,他說:“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他在此信中還引用周作人的話:“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 ‘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清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開民族昏憒的癰疽,閹割民族自大的瘋狂’”,由此強調“今日中國政象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欲對此下一對癥之針砭,則弟以為惟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3]然而,“精神之歐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為 ‘愛國’者所詆誣反對”。為此,他特地開出“精神復興”的六項條件:
(1)非中庸(即反對“永不生氣”也)。
(2)非樂天知命(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他咬我一口,我必還敬他一口)。
(3)不讓主義(此與上實同。中國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讓,只要不讓,只要能夠覺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討論方法而方法自來。法蘭西之革命未嘗有何方法,直感覺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鋤耙沖打而去而已,未嘗屯兵秣馬以為之也)。
(4)不悲觀。
(5)不怕洋習氣。求仙,學佛,靜坐,扶乩,拜菩薩,拜孔丘之國粹當然非吾所應有,然磕頭,打千,除眼鏡,送訃聞,亦當在屏棄之列。最好還是大家穿孫中山式之洋服。
(6)必談政治。所謂政治者,非王五趙六忽而喝白干忽而揪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發起此社時有一條規則,謂在社里什么都可來(剃頭,洗浴,喝啤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4]
很明顯,林語堂把矛頭指向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即實行所謂的非中庸、非樂天知命、不讓主義。他也否定傳統文化影響下的民間信仰,所謂“求仙,學佛,靜坐,扶乩,拜菩薩”之類。而他批判的武器顯然是西洋的,如“不怕洋習氣”、“必談政治”,都是西方的觀念。秉持這樣的態度,林語堂在20世紀20年代的前七八年,雖然在該不該打落水狗的問題上與魯迅發生過小小的分歧,但整體的態度卻與周氏兄弟十分接近。即使是關于弗厄潑賴之爭,他也很快畫了一幅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表示認同魯迅。特別是在女師大風潮及“三一八”慘案問題上,林語堂與周氏兄弟等是同一戰壕的戰友,他寫下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討狗檄文》、《閑話與謠言》等文章,抨擊軍閥政府的殘暴,揭露閑話派紳士的虛偽,其批判的鋒芒和力度絕不在魯迅之下。
但是,這樣一個林語堂,到了1932年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文化之精神》的文章,提出與他前此迥然有別的“新觀點”。他說:
我們要發覺中國民族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國哲學為最近人情之哲學,中國人民,固有他的偉大,也有他的弱點,絲毫沒有邈遠玄虛難懂之處。中國民族之特征,在于執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虛的理想。中國民族,頗似女性,腳踏實地,善謀自存,好講情理,而惡極端理論,凡事只憑天機本能,糊涂了事。凡此種種,與英國民性相同。西塞羅曾說,理論一貫者乃小人之美德。中英民族都是偉大的,理論一貫與否,與之無涉。所以理論一貫之民族早已滅亡,中國卻能糊涂過了四千年的歷史,英國民族果能保存其著名“糊涂渡過難關”(“Somehowmuddle through”)之本領,將來亦有四千年光耀歷史無疑。[5]
他原來批判中庸思想,現在說中庸思想正是中國哲學之近人情的表現:“腳踏實地,善謀自存,好講情理,而惡極端理論。”他接著又說:
凡事以近情近理為目的,故貴中和而惡偏倚,惡執一,惡狡猾,惡極端理論。羅素曾言:“中國人于美術上力求細膩,于生活上力求近情。”(“In art they aim at being exquisite,and in life at being reasonable.”見《論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在英文,所謂to be reasonable即等于“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對人說“你也得近情些”,即說“勿為己甚”。所以近情,即承認人之常情,每多弱點,推己及人,則凡事寬恕、容忍,而易趨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庸。堯訓舜“允執其中”,孟子曰“湯執中”,《禮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用白話解釋就是這邊聽聽,那邊聽聽,結果打個對折,如此則一切一貫的理論都談不到。譬如父親要送兒子入大學,不知牛津好,還是劍橋好,結果送他到伯明翰。所以兒子由倫敦出發,車開出來,不肯東轉劍橋,也不肯西轉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翰。那條伯明翰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雖然講學不如牛津與劍橋,卻可免傷牛津劍橋雙方的好感。明這條中庸主義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國歷年來政治及一切改革的歷史。[6]
這是在強調中庸之道有其積極的意義,中國的智慧也有其特別的價值。在談到法治時,林語堂又進一步說:
中國人主張中庸,所以惡趨極端,因為惡趨極端,所以不信一切機械式的法律制度。凡是制度,都是機械的、不徇私的、不講情的,一徇私講情,則不成其為制度。但是這種鐵面無私的制度與中國人的脾氣,最不相合。所以歷史上,法治在中國是失敗的。法治學說,中國古已有之,但是總得不到民眾的歡迎。商鞅變法,蓄怨寡恩,而卒車裂身殉。秦始皇用李斯學說,造出一種嚴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勢力的秦國,軍事政制,紀綱整飭,秦以富強,但是到了秦強而有天下,要把這法治制度行于中國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盤失敗。萬里長城,非始皇的法令筑不起來,但是長城雖筑起來,卻已種下他亡國的禍苗了。這些都是中國人惡法治、法治在中國失敗的明證,因為繩法不能徇情,徇情則無以立法。所以儒家倡尚賢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則情理并用,恩法兼施,有經有權,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討情”、“敷衍”,雖然遠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為這種人治,適宜于好放任自由個人主義的中國民族,而合于中國人文主義的理論,所以二千年來一直沿用下來,至于今日,這種通融、接洽、討情、敷衍,還是實行法治的最大障礙。[7]
這里,他稱中國人反對走極端,所以人治的情理并用、恩法兼施,“合于中國人文主義的理論”,二千年一直沿用下來。其實,這種人治制度最大的問題,是把國家安危、民眾福祉寄托在明君身上,而君王也是人,難以保障他的圣明,而且圣明也不可能具備普遍的適用性。林語堂卻說:“這種人文主義雖然使中國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卻產出一種比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之下,個性發展比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發展與武力侵略,比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這種文化是和平的,因為理性的發達與好勇斗狠是不相容的。”在他看來,這種人文主義就有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優點了。
二、西方視角帶來的新問題
關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優點如何呈現?林語堂的話告訴人們:是在西方文化的視野里!
林語堂不是從中國傳統的角度來肯定中國文化的優點,而是從西方文化背景上向西方人展現中國文化的長處。《中國文化之精神》原是他1932年春在牛津大學和平會的演講稿,后來他譯成中文發表時特意在前面加了一段說明:
(一)東方文明,余素抨擊最烈,至今仍主張非根本改革國民懦弱委頓之根性,優柔寡斷之風度,敷衍逶迤之哲學,而易以西方勵進奮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國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擊者一變而為宣傳者。宛然以我國之榮辱為個人之榮辱,處處愿為此東亞病夫作辯護,幾淪為通常外交隨員,事后思之,不覺一笑。(二)東方文明、東方藝術、東方哲學,本有極優異之點,故歐洲學者,竟有對中國文化引起浪漫的崇拜,而于中國美術尤甚。……(三)中國今日政治經濟工業學術,無一不落人后,而舉國正如醉如癡,連年戰亂,不恤民艱,強鄰外侮之際,且不能釋然私怨,豈非亡國之征?正因一般民眾與官僚,缺乏徹底改過革命之決心,黨國要人,或者正開口浮屠,閉口孔孟,思想不清之國粹家,又從而附和之,正如富家之紈绔子弟,不思所以發揮光大祖宗企業,徒日數家珍以夸人。吾于此時,復作頌揚東方文明之語,豈非對讀者下麻醉劑,為亡國者助聲勢乎?中國國民,固有優處,弱點亦多。若和平忍耐諸美德,本為東方精神所寄托,然今日環境不同,試問和平忍耐,足以救國乎,抑適足以為亡國之禍根乎?國人若不深省,中夜思過,換和平為抵抗,易忍耐為奮斗,而坐聽國粹家之催眠,終必昏聵不省,壽終正寢。愿讀者對中國文化之弱點著想,毋徒以東方文明之繼述者自負。[8]
這說明他在英國夸耀中國文化,不是簡單地出于愛國主義,而是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比如中庸、平和、韻雅,在中國本土成了懦弱委頓、優柔寡斷、敷衍逶迤,但在西方卻具有前面一節所述的各種優點。
這種一體兩面的文化觀念,在林語堂是貫徹到底的。比如他說:
我們可以舉出歷史的悠久綿長,文化的一統,美術的發達(尤其是詩詞、書畫、建筑、瓷器),種族上生機之強壯、耐勞、幽默、聰明,對女士之尊敬,熱烈的愛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親誼,及對人生目的比較確切的認識。在中立的方面,我們可以舉出守舊性、容忍性、和平主義及實際主義。此四者本來都是健康的特征,但是守舊易致落后,容忍則易于妥協,和平主義或者是起源于體魄上的懶于奮斗,實際主義則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熱誠。統觀上述,可見中國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屬于陰的、靜的、消極的,適宜一種和平堅忍的文化,而不適宜于進取外展的文化。此種民性,可以“老成溫厚”四字包括起來。[9]
照此看來,中國文化發揮何種作用,要看它針對什么人。“守舊性、容忍性、和平主義及實際主義”,在生活于靜的文化環境的中國人身上,會起壞的作用,而它們“本來都是健康的”,在“進取外展的文化”語境中,即在西方,對人就具有積極的意義。
林語堂提供了一種不同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發展觀。這之前,中國文化的改良基本是遵循中體西用的思路,也即中國文化遭遇了西方文明的挑戰后,一些文化人力求在維護中國文化正統地位的前提下通過吸收西方文明的元素,使中國文化適應變化了的現實,這客觀上也就形成了西學東漸之勢。但囿于“中體西用”的成見,在體用割裂的觀念指導下吸收西方文明,事實上只能取西方文明的一點皮毛,吸收的只是符合中國傳統文化標準的東西,說穿了也就是傳統文化自身的一個延續,而與傳統文化異質、為現實發展所需要的新思想卻難以進入本土,從而造成文化與現實嚴重不相適應的局面。這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林語堂的貢獻,當然是向人們展示,對歷史悠久、影響深遠的中國文化可以做不同的闡釋,其內在的豐富思想資源可以針對不同的要求闡釋為相互有聯系卻又功能不同的新體系。比如同樣的中庸思想,中國人拿來講人情,凡事取中,造成一團和氣、死氣沉沉的思想局面,但到了西方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這種近人情的思想卻可以發揮重塑生存哲學、緩和人際關系的積極作用。
林語堂以中西互參的方式,來評價中西文化,思考中國傳統文化的革新問題,與“五四”徹底反傳統的立場是有所不同的。換言之,他不是用一元論的視角,從中國的觀點看西方,又用中國的觀點看中國自身,而是從二元論的視角看待中西文化的關系:用西方的觀點看中國文化,重新發現中國文化的功能;又用中國的觀點來看西方文化,發現中國文化對西方有平衡和補充的意義。林語堂的這一態度,反映了時代的發展,說明“五四”激進主義的文化革命,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已經開辟了文化建設的新思路,減弱了反叛傳統的力度,從全面批判舊文化發展到對傳統文化有條件的肯定態度。當然,林語堂的這一變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本人的西學背景。他有充分的條件從西方的觀點來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義,并由此與20世紀30年代中期比較保守的本土文化派劃清了界線。30年代的本土文化派,是另一種形式的一元論,即用中國的觀點來擇取西方文明,與中體西用的老觀點相似,對異質的西方文明采取了排斥的態度。
但不得不指出,林語堂的中西互參的方法,在重新闡釋中西文化的同時,卻很容易陷入相對主義的困局。關鍵是它在處理中西文化關系、尋找中國文化革新方向時,缺少一種超越中西文化而可以對文化的歷史發展給出中立評價的客觀標準。用西方的觀點看待中國文化,會在西方視閾中扭曲中國文化;以中國的觀點看西方文化,也會把西方文化納入中國的思想體系,重回中體西用的老路。這兩種情況,都不利于以發展的觀點吸收西方文明的優點,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比如他說:
人文主義的發端,在于明理。所謂明理,非僅指理論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與理相調和。情理二字與理論不同,情理是容忍的、執中的、憑常識的、論實際的,與英文commonsense含義與作用極近。理論是求徹底的、趨極端的、憑專家學識的、尚理想的。講情理者,其歸結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雖解為“不易”,實則與common sense之common原義相同。中庸之道,實則庸人之道,學者專家所失,庸人每得之。執理論者必趨一端,而離實際,庸人則不然,憑直覺以斷事之是非。事理本是連續的、整個的,一經邏輯家之分析,乃成片斷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綜觀一切而下以評判,雖不中,已去實際不遠。[10]
他把中庸等同于“commonsense之common”,顯然脫離了中國文化的語境。他按西方的人文主義觀點賦予中庸新的意義,認為其直覺思維可以避免人們走極端,而又能把握事物的總體,“去實際不遠”。中庸的所謂近人情,與西方的人文主義本屬于不同的思想體系,相去甚遠。按林語堂的這樣解釋,肯定無法獲得中國堅持中庸觀點的文化人士的認同,也不可能對他們的思想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所以它的最終結果至多也是誤導西方學人,使他們按這一思路來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西文化關系上的這種相對主義觀點,在林語堂三十年代以及后來的文章中不時可見。比如他1929年12月在光華大學中國語文學會所作的報告《機器與精神》,有幾個足以代表他核心思想的小標題,其中有“論物質文明并非西洋所獨有”、“論有機器文明未必即無精神文明”、“論沒有機器文明不是便有精神文明之證”、“論機器就是精神之表現”等。這很有意思,一看便知是遵循逆向思維原則,在中西文化之間挪移意義,把某一概念置于新的語境中賦予其新的內涵。這種方法,可以讓人們對一些現象有新的發現,但發現新意的前提卻是他們要像林語堂那樣,此前已經有了新的立場,而不是這一新發現改變了人們的原有立場。這說明,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對于中國文化現代化沒有實質性影響,因為它的有效性是以中國社會西化為前提的[11]。如果中國社會已經西化,那就不存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問題;如果中國社會沒有西化,那么林語堂所設想的對西方人具有積極意義的中國新文化也就沒有合適的對象。它至多是向西方人展現中國文化優點的策略,而非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有效手段。
問題又回來了:如何使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歷史的過程中獲得現代的性質,在改造社會的同時改造自身,也在改造自身的同時推進社會的發展?這是一個世紀性的難題,曾造成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嚴重焦慮。林語堂不過是以表面的灑脫把這種無奈和焦慮,掩蓋起來罷了。
三、傳統現代化的時間邏輯
但是,林語堂的探索不是沒有意義的,它使我們今天可以轉變思考的角度,從時間邏輯上來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課題。
回到時間的邏輯,實質是正視中西互參的文化整合與革新思路的那種相對主義的不足,把文化傳統的革新與文化發展的立足點從中西互觀這樣懸空的概念降落到現實的土地,明確這是一個中國本土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而不是西方社會的問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不是西方視野中所想象的中國文化,而是與中國現實變革密切聯系的中國文化。不是西方用來點綴其文化豐富性,或者想象中國神秘性的工具,而是中國社會自身變革的一個重要條件。由于是與中國的現實變革緊密相連的,所以它的發展所呈現的時間邏輯,就是它自身聯系著中國現實的變化發展,以時間的連續性和發展的階段性相統一的一個過程。
林語堂的相對主義文化發展觀,優勢在于用外來的視角從中國傳統發現新意義,但這新的意義是與外來背景關聯的,而與本土的問題沒有直接聯系。這樣的思考,是一種旁觀者的態度,而不是實干家的姿態;是與“五四”反傳統相聯系的另一種批判性的口惠,而不是扎根在中國土地上的切實改革踐行。與此相反,一旦文化發展方略從游移的空中落到中國的大地,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有了明確的坐標,知道是中國自身的問題,而不是像林語堂所做的那樣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化,那么其發展就轉變為聯系著現實變革的時間問題,成為一個與現實矛盾和歷史糾葛聯系在一起的錯綜復雜的過程。
與現實聯系在一起,就意味著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是一個具體的歷史選擇。它與西方有關系——文化的交流當然仍很重要,但起決定作用的卻是中國社會的現實力量,而不再是西方的觀點,不再是從西文的視野來進行選擇。比如中庸,在封建末世面對西方列強的文化挑戰時,它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甚至成為中國民眾人格退化的思想根源。到了激進革命的時代,中庸很自然地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因為它凡事搞調和的傾向與革命精神格格不入,成了革命所要克服的思想障礙。但一旦再回到和平與建設的時代,社會要求協調發展,中庸里反對極端行為的思想資源就可能重新獲得正面的意義,發揮其積極的功能。比如它會引導人們追求合理的發展,處理好人與自然的沖突,協調好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在參與協調各種社會關系的過程中,它的防止極端和激進、保證社會有序運作的那種思想也就逐漸沉淀到新時代的思想體系中去。這時的中庸就已經不再是封建末世不講原則的中庸,而是有了現代性內涵的思想,大致接近西方的理性精神,從而成為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也應看到,這種現代性的反極端的理性精神在參與協調社會關系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已經吸收了別的思想資源,包括來自西方的以維護個人權利為目標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這些思想保證中庸不再有扼殺個人自身權利的內容,或者說剔除了封建末世的中庸中回避社會矛盾和中西沖突的那種模棱兩可的思想,突出了在協調發展中的有所為的方面,成了與古代中庸有質的差異的現代思想。當然,這一過程中西方思想的被吸收,又并非取決于西方思想本身,而是取決于西方思想適應中國現實發展邏輯的需要,因而西方思想不是簡單地挪移過來,而是在改造中國的中庸的同時,其自身也被改造,因而有了中國的特點。
由此可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外來思想的中國化,并非純粹是思想自身發展的問題,而是思想的現實的發展,是社會綜合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既然如此,那么它除了遵循思想發展的邏輯,更多地還是受著客觀條件的限制,要接受社會現實的選擇。現實是什么?現實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矛盾統一體,包含了不同的利益訴求。現實問題的解決,是不同利益群體力量平衡的一個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思想的參與及其影響,也就體現著不同群體的訴求及其平衡關系,絕不會是單純的思想設計那么簡單。一個人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甚至創建自己的思想體系,但它能不能成為具有影響的思想,能不能在社會發展中產生積極的作用,就不是單純地取決于個人的思想本身,而是看這個思想對社會實踐有沒有用。至于影響了歷史進程的思想,則肯定是代表了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合乎歷史發展方向的思想。
但困難就在于,“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是在歷史過程中通過沖突,甚至是非常尖銳的斗爭而實現的,歷史的方向也不是自明的,而是各種力量矛盾和沖突的一個結果。因而,要從傳統文化中發展出現代的思想,或者說對傳統進行現代化的改造,是不能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項相當長期的艱難而巨大的工程。其間必然充滿了許多不確定性,比如在一個時期被廣泛接受、認為是真理的思想,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實踐檢驗后,結果卻是一個災難(比如法西斯主義);相反,在一個時期里被批判的思想,到了后來卻發現它是真理,代表了人類的共同利益,這就是所謂的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如此逆轉,可能是因為這一思想本身隨著歷史的發展作了調整,其合理性后來被人們所認識;也可能是這一思想遇到了它得以發揮影響,甚至是巨大影響的歷史機遇,各種社會力量的折沖到那時恰好提供了使這一思想發揮作用,甚至是重大作用的條件。總而言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檢驗的具體環節和細節卻是非常復雜的。一種思想,一個傳統的革新,是不是合理有效,是不是成功,不是思想者和革新者自己說了算,甚至也不是他們同代人說了算,其真正的效果要由時間來裁決。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個時間問題,即歷史問題。而在這一過程中,無疑又充滿了復雜的斗爭和巨大的不確定性。
實踐檢驗的具體環節和細節,是一個專門的問題,有待于系統深入的研究,但這里可以鑒于它的復雜性簡單討論一下我們判斷思想的正確性時應該有的態度,而且這其實也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之時間邏輯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是實踐的觀點。林語堂式的中西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是就文化談文化,有助于促進跨界的文化對話,并在對話中相互溝通。這比中體西用的觀念堅持傳統主導的立場在思想上更為解放,但它仍不是解決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根本方法。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是一個歷史選擇的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發展問題,它涉及民族國家主體不同方面的訴求及其協調。在開放的環境中,保持交流關系的中西文化都參與其中,但都不可能單獨地主導,而是經由現實中不同力量的博弈和協調所進行的選擇來決定如何兼收并蓄,建構適應于現實發展的新的價值理念和文化體系。這樣的實踐觀點,就是尊重客觀規律、在實踐中發展并接受實踐檢驗的觀點,避免了任何個人的主觀武斷。
二是寬容的態度。既然是由實踐來檢驗,而且這不是在實驗室做科學實驗那樣的一次性復核,而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那么任何個人都無法在某個時間點確保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這就要求有一種謙虛和寬容的態度,認識到與自己不同的意見未必就是錯誤的。你可以堅持你在傳統文化轉型問題上的觀點,但你要準備好隨時修正自己的錯誤。你的“錯誤”可能最后又會被證明是正確的,就像在“五四”時期被批得體無完膚的中庸,一旦脫離了那個激進革命的背景而遇上了新的時代機遇,經過改造,它的避免極端、注重社會合理發展的理性觀點,又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傳統思想。其實,這種不偏執,隨時準備在證據面前修正錯誤的態度,本身就是中庸思想的一個現代翻版,這也正是林語堂在20世紀30年代從西方文化視野所設想,但因為其脫離中國的現實而沒有真正實現的理性精神。
三是進步的標準。在思想發展史上,即使把檢驗真理性的時間拉得足夠長,對于某種思想,或者對于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某種成果,依然是會有不同意見的。社會是分層的,不同的群體對于某一思想的認同一般受利益原則的支配:對自己有利的就接受,否則就反對,少不了分歧和沖突。因此,作為不同意見之間的溝通交流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個超越這些分歧和對抗的觀念的客觀標準,我認為這個客觀標準應該是進步的標準。個人或者社會集團,可以有自己的進步標準,相互之間甚至可能水火不容,但承認有一個進步標準,這是意見交鋒具有意義的前提。進步的具體內涵,可以爭論,但你得承認按照現實發展的觀點,有利于歷史進步的意見總是合理的,哪怕此種合理性可能要由超出個人視野的更為久遠的歷史來作結論。這樣的觀點,意義主要在于處理思想發展問題時,我們要有一顆謙虛的心和一種歷史的眼光,要避免獨斷。
注釋:
[1]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聞一多全集》第2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頁。
[2]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9頁。
[3]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1~12頁。
[4]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4頁。
[5]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4頁。
[6]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57~158頁。
[7]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58~159頁。
[8]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50頁。
[9]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53頁。
[10]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56~157頁。
[11]林語堂:《剪拂集大荒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第140~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