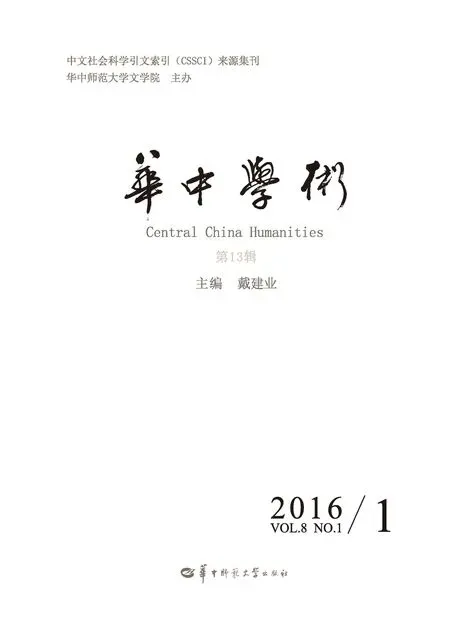微觀權力視野中的生存美學:對涂鴉藝術的文化考察
王慶衛 趙 戰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湖北武漢,430079;西安美術學院,陜西西安,710065)
?
微觀權力視野中的生存美學:對涂鴉藝術的文化考察
王慶衛 趙 戰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湖北武漢,430079;西安美術學院,陜西西安,710065)
內容摘要:涂鴉是街頭藝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它承襲了20世紀現代藝術運動中達達主義、表現主義、波普藝術等流派的主觀性和叛逆性精神,以扭曲、破碎和抽象化的形式表達對內在世界的體驗和對外部現實的疏離;從文化權力的角度來考察,涂鴉的反抗姿態體現著福柯意義上的生存美學和局部斗爭的理論意涵,是日常生活美學和大眾文化研究中值得關注的問題。本文從街頭藝術固有的“介入生活”和“局部反抗”的精神特質入手,分析主流審美意識對其拒絕、接納以及同化的邏輯線索;探討涂鴉藝術“自我關注”的生存美學態度及其與主流趣味的微觀權力關系,力圖展示大眾審美文化研究中的權力維度。
關鍵詞:生存美學;涂鴉;微觀權力;規訓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街頭藝術伴隨美國街頭的黑人hip-hop文化潮流而興起,今天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城市景觀。Rap(說唱)、涂鴉、街舞、行為藝術或者街頭音樂在很多城市里隨處可見。它們像城市的文身,有時顯示著本地的文化性格,有時又不得要領。過去它們很少成為主流文化所積極肯定的東西,而今天在旅游業、商業或廣告業領域中,人們越來越認識到街頭藝術的價值;但街頭藝術仍然是非主流的和邊緣的藝術形式。在不同時間、空間和體制下,人們對它的看法莫衷一是:它或者是一個社會多元性和包容性程度的標志、主流審美趣味的補充,或者是底層人群的粗俗和不規范的準藝術,有顛覆秩序、惡化趣味和敗壞風俗的危險。但作為大眾藝術類型和邊緣審美意識,除非將其消滅,否則已無法把它更遠地驅離公眾的視野。街頭藝術沒有可資炫耀的文化等級身份,也無益于增進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同;除了在少數場合,它似乎缺少一種值得被認真對待的氣質。因此,它很少被鼓勵,經常被無視;有時被當作無聊的胡鬧而聽之任之,有時被看成挑釁行為而遭到壓抑或禁止。
一、介入與反抗:涂鴉作為街頭藝術
在當代文化研究視野中,主流審美趣味是一種權力的延伸,是占據支配地位的社會群體意志在藝術中的體現,發揮著潛在的統治功能,把政治意識形態和理性統治法則內化為帶有愉悅感的主體內在要求。如伊格爾頓所言:“審美預示…… ‘內化的壓抑’,把社會統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體中,并因此作為一種最有效的政治領導權模式而發揮作用。”[1]從這個意義上說,審美趣味遠不是非功利的。它通過審美活動的中介,把肉體的觀念與國家、階級矛盾和生產方式等隱含的政治主題聯系起來,并根據審美趣味的差異劃分出文化等級。伊格爾頓進一步指出,美學一開始就是作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話語而興起的,“審美等于意識形態”[2]。而街頭藝術作為大眾審美趣味的體現,實際上也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一種不同于主流審美趣味的藝術形式,又是一種介入日常生活的活動,隱含著大眾的和個體的社會政治訴求。
街頭藝術在其廣義上,包括在公共場所為公眾表演的歌舞、體育以及商業的或民間的技藝展示,狹義上則專指20世紀70年代在歐美大城市興起的涂鴉、說唱、街舞、快閃和裝置藝術等。不同種類的街頭藝術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生活:街頭音樂和街頭舞蹈強調觀眾參與性和場地開放性,它們在觀念和形式上傾向于消除藝術與生活的界限;行為藝術有相對明確的主題,其藝術形式和演出手法雖然新穎,但我們仍可辨認其意義指向,它更像一種刻意降低了嚴肅性的政治活動或社會活動;而涂鴉的特點復雜得多。涂鴉不提出明確的藝術或社會主張,它通過獨特的形式特征,以展示某種生活態度或主觀感受為己任。它基本不去碰觸現行的生活和藝術規則(除了在公共空間非法作畫),而是在規則的斷裂或薄弱之處,塞入自己的看似無關大局的、更多涉及形式層面的東西;它也很少直接反對主流觀念和價值,只是以特立獨行的精神氣質與日常意識拉開距離。但畢竟,一種異質的東西顯現了,它與常情常理并存,意義含混模糊,從中看不到通行的審美趣味和思想意識,反而隱約顯現出對生活和藝術規范的破壞力;這不能不引起主流意識形態的警惕。
有必要區分街頭藝術與采取了藝術形式的大眾娛樂活動。與街頭藝術不同,后者從觀念到形式都合乎“正常的”審美趣味,換言之,是被“知識—權力”一體化的社會權力機制所規訓的作品,是對現存作品或通行的藝術形式的重復。它們只能喚起人們用慣常的情感方式去重溫、印證并強化這個審美趣味本身,從而鞏固對現實合理性的認同;如國內各地的廣場舞和自發的業余歌唱活動。主流審美趣味是對主體實施規訓的“知識—權力”機制的一部分,為建構合乎要求的社會主體而運作;主體在現代社會權力機制的規訓下,成為“被操縱、訓練、創造和發明的肉體,它是被馴服的肉體,它被一種精心計算的強制力所控制,它成為權力的對象和目標”[3]。官方所倡導和鼓勵的精英文化或大眾文化,即發揮著這種重復和強化主流觀念并規范社會成員的功能。多數街頭藝術則在觀念、藝術形式和技巧方面具有原創性;它們是對生活的重新解讀和發現,無視主流審美趣味的引導和教化,試圖在生活的意識形態帷幕上揭開另一種真相,展示被現實所激發的奇異心靈。它們在不被禁止的地方做著尚未被禁止的事情;在權力的極限、末端或邊緣之地,在規則難以企及的地方,街頭藝術創造自己的規則,拓展自己的疆域,直到社會權力機制和主流意識形態發現并補上自己的漏洞。
相對于主流意識形態對審美權力的操控,街頭藝術具有福柯所說的“局部反抗”的意味。在福柯看來,在這個被規范化的理性秩序所主宰的世界上,權力的支配無處不在,不僅控制了人的肉體,也入侵人的靈魂;權威的統治被深深植入人的心靈內部,建立在被統治者的“大腦柔軟的神經纖維上”[4],在身體和靈魂的每一個角落,人們無時不在接受社會權力機制的符號性修辭,并成為自己思想和言行的自覺監督者。在規訓力量的操縱擺布之下,人們的批判性、超越性和創造力被窒息而渾然不覺,正如康德所說:“他已經愛上了這種狀態,而且,事實上,就目前來說,他沒有能力利用他的理解,因為沒有人允許他做這樣的嘗試。”[5]但權力的薄弱和兩可之處,正是街頭藝術以其異質性向社會審美的元敘事挑戰之地。從街頭說唱、舞蹈、快閃、立體繪畫到涂鴉,其或明或暗的觀念和主張、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和技巧,指示出一個我們習焉不察的世界。它顯示了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一些被主流話題所遮蔽的然而可能是更為本然的方式;它們在為人們轉換生活觀念和藝術觀念而發出不斷的吁求。這是對主流審美趣味不動聲色的侵蝕和顛覆,對后者所隱含的關于理性與感性、個體與總體、情感方式與價值觀念的內在秩序形成潛在的挑戰。
而一旦街頭藝術被主流文化或商業活動所收編,它就被消解了異質性,變成了被容許的觀念、形式和情感模式,成為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和流行物,并在社會權力機制所劃分的文化等級中獲得一個位置。對異質性的包容是社會權力機制的一種謀劃:通過吸納種種“不同意”的觀念并賦予其合法性地位,來消解異質性事物的意義,并進一步增進社會成員對自身的認同。街頭藝術似乎無力也無須抗拒這種命運;相反,迫使社會習俗和審美趣味作出妥協并發生改變,使它所攜帶的觀念態度和形式技巧被接納,是街頭藝術隱含的目的之一。一旦反抗的合理性被承認,反抗就變得徒有其表,并轉而為反抗的對象服務;當代街頭藝術的發展歷程中隱含著深刻的悖論。
二、拒絕與同化:“不是”的藝術
涂鴉在街頭藝術中是獨具魅力的一種,指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出現在美國和歐洲城市公共空間中的涂繪作品,是大眾化的墻面圖畫創作;它的形式不拘一格,多是圖形雜以文字、標識和各種符號,題材廣及日常生活各個領域。在公共建筑物上面的胡涂亂畫古已有之,如在意大利龐貝古城遺跡中發現的涂鴉之作,但本文所涉涂鴉主要是指明確表達一種審美取向、具有與當代街頭藝術共同精神特征的有意識創作。
涂鴉在風格上承襲了20世紀現代藝術運動中從達達主義、表現主義到波普藝術諸流派的主觀性和叛逆性的精神氣質,以扭曲、破碎和抽象化的形式表達對內在世界的體驗和對外部現實的疏離。涂鴉起初是從城市黑幫的聯絡標記和下層社會青年宣泄苦悶的隨意涂抹脫胎而來。早期以表意功能為主,形式粗野狂放,帶有邊緣人群的反叛氣質;至80年代風格為之一變,出現了有意識的風格化的創作,手法流暢簡明,具有強烈的娛樂感和活潑的創造力,并引起商業和藝術領域的關注;其形式元素和風格特征開始被藝術設計越來越多地吸收借鑒。
從打破藝術現存規范的意義上,可以說一切現代街頭藝術都具有涂鴉的精神氣質。涂鴉的主題不可捉摸,怪異的造型、熱烈的色彩和夸張的線條顯示著反理性、反規則的情緒,往往是個體情感、沖動和本能的直接呈現。它的主題有時難以辨認,有時又用奇異的方式談論我們熟悉的話題,用獨特而敏銳的感受把生活世界陌生化。它對每一種試圖接近它的解釋說“不”,而又不斷地誘使觀看它的人們嘗試思考更多可能的解釋。沒有人能說清它們在表達什么,每一次闡釋的失敗只讓我們了解它們不是什么,它們不是我們一開始認為的東西,也不是我們能最終確認的東西,它是某種“不是”的藝術。
這種“不是”的態度意味著拒絕:拒絕熟悉的東西,拒絕給定的規范(無論藝術規范還是日常生活規范),拒絕認可通行的秩序和價值觀,拒絕藝術。它呈現出跟現實截然異樣的圖像和秩序,狂野怪誕、自由率真的形式風格與井然有序的社會生活格格不入;那是一些被獨特的心靈加工過的印象、感受和情緒,而這樣的心靈,必定是以我們尚未覺察的生活方式為土壤的,于是涂鴉對于我們具有了某種認識功能。但這種認識活動往往由于對象的難以把握而被引向我們自身:我們的日常意識、我們的認知和情感方式、我們感覺的疆界和局限。在這個拒絕的氛圍中我們能更深切地領會社會權力的規訓企圖。
涂鴉在風格、形式和觀念上受到波普藝術的強烈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后者的繼承和發展。它們的核心都是大眾文化;但波普藝術這一概念的形成,源于知識精英置身于大眾文化之外對大眾文化做出的梳理概括,是一種對象性的思考、旁觀者的中立判斷。波普藝術的代表人物從英國的保羅齊、蒂爾森、霍克尼到美國的勞申伯格、沃霍爾和戴恩,都是知名的藝術家,幾乎無一例外都受過專業藝術訓練,他們的文化主張和藝術實踐都有著清晰的理論自覺,是從對大眾文化的認識理解中走向對大眾文化元素的闡釋和運用;大眾文化對于他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知識性的對象,在情感上則是隔膜和疏遠的;涂鴉藝術家卻是城市大眾文化的直接產物,大眾文化又是他們不斷創造出來的作品,他們就是這種文化本身;涂鴉藝術具有波普藝術所不能模仿的精神氣質,即緣自社會底層生活的粗糲感和爆發力。
據說涂鴉起源于紐約的布朗克斯區(Bronx)。在20世紀60年代,這里是黑人和中美洲移民的聚居地。街區內到處可見劃分地盤的幫派符號,雜以各種猥褻圖案。該場景被當地報紙諷為“原始人聚居地”。后來幾個有繪畫天賦的幫派人士動手設計和美化這些標簽,于是墻上的圖案變得好看起來,這就吸引了一批非幫派畫家參與墻上作畫。隨著加入涂畫行動的人越來越多,“涂鴉”(Graffiti)藝術誕生了。這批最早從事涂鴉藝術創作的“作家”多數出身社會下層[6],有著共同的反戰爭、反種族歧視、反權力壓迫等社會主張,以此結成了所謂的反文化的藝術群體。他們活動在主流社會邊緣,多數人未接受過正規的藝術教育,因而其藝術形式的粗糙、姿態的叛逆和社會立場的邊緣性,使涂鴉作品具有了與生俱來的拒絕態度。在70年代涂鴉代表人物讓·米歇爾·巴斯奎特(Jean Michel Basquiat)的作品中,毛糙的線條構造出稚拙、原始的造型和畫面,在視覺上瞬間拉開與主流審美意識形態的距離,書寫的文字繪畫的內容均源自巴斯奎特自己非常個人的直觀印象,而少有主流知識、觀念的灌輸。至80年代,涂鴉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一些接受過正統藝術訓練的創作者紛紛加入涂鴉創作,涂鴉因而在繪畫方式上日益呈現出專業美術特質。最有代表性的是基思·哈林(Keith Haring),他曾就讀于紐約視覺藝術學院,被后人評價為20世紀藝術最具標志性的人物。“涂鴉,正如這種狂野自由的書寫形式被稱作的那樣——如此通俗而具叛逆性——對于幾代青年人而言它將代表著他們無意識地等待著的藝術革命。”[7]
涂鴉是崇尚主體、尊重個體自由的現代性精神在大眾群落中的自然延續,又鮮明地呈現出打破宏大敘事、顛覆規則、強調異質性的后現代特質,從而成為當代哲學、美學和藝術的日常生活轉向的一種藝術標識。對主流審美趣味而言,涂鴉是規訓不足的結果;而對涂鴉藝術家而言,涂鴉作品反而是對過度規訓進行反抗的產物。它是在社會權力機制的壓力之下產生出的拒絕態度,對輕視邊緣審美趣味的藝術觀念和文化等級意識嗤之以鼻,其形式的粗野性和侵犯性帶來強烈的視覺沖擊力;涂鴉憑借自身的魅力召喚各階層的藝術家加入其行列,以藝術實踐來顛覆社會固有的藝術偏見。在藝術領域,這種對主流審美趣味的拒絕成為大眾審美意識的活力之源。
涂鴉以其街頭藝術的品性保有著這種拒絕的態度。涂鴉者們是街頭神出鬼沒的麻煩制造者,公眾眼中的異類,警察追逐的對象。他們令市政當局頭疼,后者被迫每年撥出款項清理他們的作品。涂鴉藝術家們以惡作劇為榮,以逃竄為樂。直到基思·哈林(Keith Haring)、賽恩(Scien)、克羅爾(Klor)、史蒂芬·斯普洛(Stephen Sprouse)等天才作家獲得商家的青睞,在網絡空間和路易·威登之類產品上拓展其創造力時,涂鴉才逐漸成為藝術創意和設計靈感的寶庫,成為主流趣味樂意接納的東西。成功的涂鴉者無須在街頭東躲西藏了,有了商業這個同盟軍,涂鴉藝術進入了“后涂鴉”時代。這一轉變有幾個明顯特征:
首先,涂鴉展現的場所發生了改變,由地鐵、廣場和公共建筑轉向個人涂鴉網站;其次,它的破壞性受到遏制,對社會環境的影響轉變為對藝術規則的破壞;再次,涂鴉者的社會處境發生變化,不再被警方追逐,反而受到商家追捧。
然而,如果涂鴉藝術所做的僅限于此,它又何異于現代主義的先鋒派藝術呢?或許,因為涂鴉同樣反對唯美主義的藝術自律,可以被歸入廣義的先鋒派。但是,失去了現實參與性的后涂鴉主義已不能被歸入街頭藝術,它的反抗性和作為異質力量介入生活的特征被消磨殆盡。美學趣味的反抗轉變為一種求新的形式沖動。如何評價涂鴉藝術的這種轉變?是被收編之后喪失銳氣并成為商業文化的一部分,還是以部分妥協為代價獲得了更廣闊的表達空間?一個寬松溫和的環境削弱了涂鴉藝術反抗的動機。但反抗又能怎樣呢?反抗改變了社會的局部規則并獲得了認可,不正是涂鴉者的初衷嗎?
涂鴉藝術并非不能商業化或不能與主流文化合作,因為商業化和被主流文化納入是涂鴉藝術的歸宿和出路之一;應該說,不能消除涂鴉藝術的街頭土壤,不能完全用電子涂鴉網站或專用的涂鴉墻取代那種隨機和冒險的涂鴉創作。繼續這種涂鴉與清理的捉迷藏游戲,是社會為了保存涂鴉藝術的生命力所應付出的成本。我們承認后涂鴉藝術(被商業化的涂鴉)的價值,但一旦消滅了涂鴉的街頭屬性,涂鴉藝術乃至后涂鴉藝術都將失去力量的源泉。
三、審美權力與生存美學
街頭是一個非藝術場所。涂鴉以及所有街頭藝術經由這個場所而模糊了自己的藝術屬性,使我們對它們的分類缺少標準可循,必須求助于約定俗成的慣例。但實際上非藝術場所卻是藝術發生的本源之地,涂鴉具有最真實的原始藝術精神;而文明史以來的大多數藝術只不過是被規范化了的涂鴉。頗具反諷意味的是,20世紀90年代曾有人在紐約市內的美術館舉辦涂鴉畫展,欲拍賣作品,卻遭到評論家和公眾的嘲弄。因為人們早已取得了共識:那些涂畫在公共建筑墻壁、橋梁和地鐵上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涂鴉。
正如高更所說:孩子的東西,不僅無礙于藝術的嚴肅性,反而賦予藝術以魅力、快樂和淳樸。涂鴉藝術正是對原始和兒童時期的精神回歸,拋棄文明史和藝術史上的理性規則和理性化的感性,用富于原始生命力的精神力量來理解和表現世界或主體。它從一個試圖擺脫規訓的主觀心靈出發,通過非系統的、習慣性的個人繪畫方法,以及碎片化圖景的構造、取消透視的非常規手法、銳利或浮夸的造型,來造成對欣賞習慣的劇烈扭曲,引起人們對習以為常的現實世界的質疑,引起對知識經驗可靠性的反思。涂鴉展現世界或心靈的非理性的特征,突出個體經驗的在場,從而賦予世界一種新的秩序。這一運用強烈的虛構手法去懷疑世界的真相和秩序的企圖,正道出了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一書中對藝術的期望:“虛構的作品叫出了事實的名稱,事實的王國因此便土崩瓦解;因為虛構之物推翻了日常經驗并揭示了其殘缺不全和虛假之處。但藝術只有作為否定力量才能擁有這種魔力。只有當形象是拒絕和駁斥已確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時,它才能講述自己的語言。”[8]抽象源于主體對世界的不和諧所感到的不安,制造類似超級現實主義的幻象則由于對真實性的迷惑,不合常規的技法、炫技的扭曲線條、陌生的分寸感都在彰顯個體化的反主流的審美意識。在這個為“知識—權力”所宰制的社會中,這些不安、迷惑和不順從正不斷打破權力的連續性。
按照對權力的傳統理解,它是一種能力或者資源,是可以被擁有、爭奪和轉讓的財產。福柯則主張權力是一種處于流動循環過程中的關系,“它從未確定位置,它從不在某些人手中,從不像財產或者財富那樣被據為己有”[9]。這種權力關系在現代社會里無處不在,它并非自上而下的單向支配關系,而是構成一個循環相連、錯綜交織的網絡,福柯稱之為微觀權力。它不同于來自國家機構、法律制度等權力中心的宏觀權力,在實施上也有別于對肉體實施殘酷和恐怖統治的傳統方式,而是通過“居心叵測的憐憫、不可公開的殘酷伎倆、雞零狗碎的小花招、精心計算的方法以及技術與科學等等的形成。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制造出受規訓的個人”[10]。現代權力與知識合謀,通過設定標準、規訓和內化標準等一系列程序對個體的人實施操控,使人們把社會的外部要求轉化為內心自覺,以培養合格的社會人。通過無數細微的通道,權力抵達了個人的身體、姿態和日常行為,整個社會被造就成一個巨大的規訓和控制的場所。在福柯看來,對此采取總體性的斗爭來反抗權力規訓是無濟于事的,而應該通過局部斗爭來獲得微觀權力關系中的主動地位。
福柯提出以局部斗爭和生存美學作為掙脫現代權力的控制的武器。局部斗爭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而是在雙方共存的前提下對權力進行調整,通過對流動著的、無主體的微觀權力的獲取,使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位置發生改變。正如在涂鴉藝術興起的過程中,它與主流審美趣味持續地博弈,從被漠視、被禁止、被默許到被接納,使微觀權力關系中的雙方地位發生置換。涂鴉藝術家不再是主流趣味和大眾文化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在接受的過程中發揮著對文化權且利用的自主性,并且成為意義的主動生產者。涂鴉藝術中的意義的生產,改變了微觀權力關系中主體與對象的位置,在權力的末端或毛細狀態下,局部反抗使個體和邊緣人群的意志得以彰顯;當涂鴉被社會當作藝術接納時,一次反向的規訓發生了。
生存美學強調關懷自身,要求把認識自己放在生存的首位;注重自我控制、節制和協調,使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11]。然而,現代人的身體被權力所馴服,現代人的精神是各種學科知識的構成物,生活本身的目的被由權力所支撐的求真意志所取代。人雖然是特定時代的歷史實踐的產物,但這并不意味著人要由社會決定自己的一切,任憑其強制;相反,人應當極力擺脫他人的控制,同時放棄控制他人的欲望,回到自我決定、自我創造的生存藝術中。福柯論述道:“對于波德萊爾來說,現代人并不是那種去發現自己,發現自己的秘密和他的隱藏的真理的人;他是那種設法創造他自己的人,這個現代性并不在人的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強制人完成制作自己的任務。”[12]他提倡以創造風格化的生活為目的的生存美學,抗拒現代規訓權力,尋找自我解救的道路;這就需要反對現代道德的強制性和整齊劃一,反對迫使人接受和服從的普遍的道德形式,在美學指導下實現道德的多元化。具體而言,就是通過個人選擇,來實現一種不受普遍道德規范約束的美學生活,用自我塑造的主體來取代被社會權力規訓而成的主體。實現了這一生活方式的人,就是福柯心目中的古希臘人,“成為自己的君主,完全把握自身,完全獨立,完全屬于自己,它們經常表現為占有的快樂:享受自我,與自己享樂,在自己身上找到全部快樂”[13]。福柯對生存美學的構想及對權力的理解不乏片面粗疏之處和烏托邦色彩,但對于一種邊緣文化群體的思想意識或藝術主張而言,關注微觀權力,通過適當的抗爭獲取自己應有的話語權,擯棄權力和知識對主體的控制,而選擇自我塑造的風格化的美學存在,這一思路是頗有啟發的。在某種意義上,涂鴉藝術正是踐行著擺脫規訓和關懷自身、自我創造的原則。
涂鴉藝術自20世紀80年代傳入中國,今天已經融入了很多大城市的日常生活,成為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景觀,如北京的奧運文化墻、重慶市的涂鴉一條街、上海市莫干山路的涂鴉墻,以及廣州、武漢、西安等地建立的涂鴉藝術聯盟,等等。由于起步時間較晚,中國涂鴉藝術一開始還有相當濃厚的舶來色彩,其創作風格是對歐美涂鴉藝術精神的直接移植,屬于藝術專業人士的小眾文化。1990年代以來開始出現風格化的個人創作,注重對傳統文化因素和中國當代特色的呈現,但作品水平比歐美仍有相當差距。由于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文化知識結構的差異,中國受眾對于那種充滿狂野叛逆精神的繪畫風格有一定的心理隔膜,而習慣于接受富于人情味的作品。
從涂鴉藝術的發展特點來看,中國的涂鴉藝術一開始就被納入了社會管理部門的監督之下,專門開設的涂鴉墻和涂鴉網站,把涂鴉行為最大限度地置于規范的管理之中,試圖消除它對秩序和公共空間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但民間涂鴉藝術卻從未放棄冒險和叛逆,甚至不斷入侵到高等藝術院校和文化機構的藝術觀念和創作實踐層面。正視涂鴉藝術精神品格的內在要求和社會生活規范性之間的矛盾,仍是一個需要不斷在藝術觀念上進行探索的問題。其實,中國文化土壤中不乏涂鴉的傳統積淀。名山大川間的古代文人題刻,風景名勝處的游人留念字跡,新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大字報和政治漫畫,都是某種形式的涂鴉甚至涂鴉藝術。今天,中國的經濟建設的驕人成就與文化觀念的相對落伍,構成了一種“物質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狀態,過多的意識形態控制和無微不至的文化審查制度導致了普遍的創造力匱乏;在這樣的文化境遇中,涂鴉的藝術叛逆精神不失為一種可貴的品質。
結語
不管一件涂鴉藝術在觀念和技巧上多么溫和無害,或者它的主題看起來多么不著邊際,它都暗含著反對規訓、改變規則的意圖。異質性是社會規則的敵人,是多元真理對總體性的挑戰。涂鴉以陌生的面目出現在日常生活中,它拒絕被現有的標準所分類和固定,拒絕按照通行的路徑來思考——它們異于常態但又極少與各種規則相抵觸——這令規訓的權力無從判斷和著手,而最終以接納和認可的方式與之妥協。在藝術形式的掩蓋下,涂鴉對微觀權力的局部反抗,反復進行的僭越實驗,擠壓了知識—權力一體化的社會權力機制的容忍底線,迫使其作出改變和調整,也為邊緣審美趣味開啟了合法表達的空間。人們對涂鴉藝術的接納,不僅是接納了一種藝術形式,同時也是認同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對大眾審美趣味的話語權力的肯定。涂鴉藝術興起和發展,可以看作福柯的微觀權力和局部反抗理論的形象演示,它的意義超出了一種藝術類型本身,為日常生活美學在后現代狀況下的發展道路提供了借鑒,同時也在大眾審美文化的研究視野中展現了權力的維度。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研究”【11&ZD078】、國家留學基金委項目“中西建筑藝術的倫理功能研究”【20140677501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英]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王杰,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6~17頁。
[2][英]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王杰,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89頁。
[3]汪民安:《福柯的界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93頁。
[4][法]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13頁。
[5][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孫少偉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171頁。
[6]涂鴉藝術家看不起那些頭腦簡單的幫派涂鴉者,他們自稱是作家(writer)而不是畫家(painter),以區別于那些不懂藝術的胡涂亂畫者。
[7][法]Pyramyd編:《設計與藝術家》第二輯,陳晴,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6頁。
[8][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57頁。
[9][法]福柯:《必須保衛社會》,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頁。
[10][法]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353~354頁。
[11]高宣揚:《福柯的生存美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14頁。
[12][法]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等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第536頁。
[13][法]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等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第4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