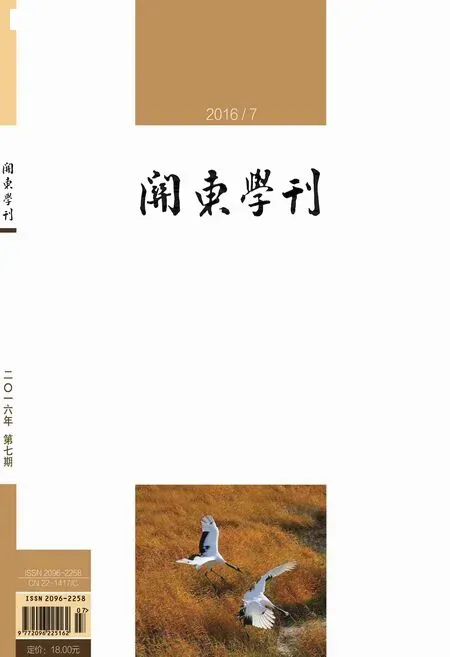敘述縫隙的探秘
——對閻真《活著之上》的另一番解讀
趙 耀
敘述縫隙的探秘
——對閻真《活著之上》的另一番解讀
趙 耀
在《活著之上》中,蒙天舒以聶致遠的他者身份出現并對其有著魔幻般的召喚能力,聶致遠始終處于追逐他者與堅守自我的矛盾沖突之中,轉型他者無果引發的自我逃逸是其精神危機的內在動因。在人物塑造方面,圓形人物與扁平人物的奇幻張力使作品在多維空間和純粹時間中自由展開,催生出新的美學價值。作品觸及到的當代知識分子“回歸”與“下滑”的雙重走向,切入了知識分子身份確立與自我救贖的永恒主題。
他者;召喚;張力;評價史
一、他者的召喚與自我的逃逸
在《活著之上》中,主人公聶致遠、蒙天舒以一種對應性的方式并置排列。二者不僅存在諸多可以進行比較性考察的因素,而且在對比中,一方的特質使另一方的特質更為鮮明凸顯,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更具張力。具體來說,聶致遠、蒙天舒二人求學時同為一班同學,畢業后同為高校教師,但是二者的人生際遇和精神圖景卻有著天壤之別。從表層上看,聶的慘淡經營與處處碰壁,蒙的左右逢源與如魚得水;聶的委曲求全與自暴自棄,蒙的游刃有余與鉆營投機;聶的自我弱化與彷徨迷失,蒙的果敢堅毅與青云直上;聶妻的哀怨不平與蒙妻的驕奢淫逸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一切極易造成讀者對聶同情憐憫而對蒙鄙夷厭惡,進而結合自身經歷批判體制的不健全、不合理以及由此引發的賢者無助、小人得志的惡性循環。然而,如果作品的主旨僅此而已,我們實難將其置于“展現知識分子心境的又一力作”行列。剝離同情弱者的因素之后,所暴露出的僅僅是窮酸書生不得志的情感宣泄,“官場現形記”的現代翻版,至多可以上升到傳統知識分子在現代轉型中不適應性有機呈現的高度。即便如此,這種臉譜化的設計與呆板的情感預設收獲的只能是作品審美價值的下滑與批判精神的下行。然而,我們不能否認或者不愿承認的是,創作過《滄浪之水》《曾在天涯》等佳作的閻真不會輕易自毀長城,《活著之上》一定存在著更為深層的意蘊等待挖掘。上述的分析僅僅是在表層上對作品價值的遮蔽與誤讀,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作品的深層結構進行一次全方位的細微考察,探究潛藏在作品內部的深層文化意蘊和哲理,最大限度地將《活著之上》的人文意蘊加以開掘與呈現。
如果我們將聶致遠認定為第一主人公,那么,蒙天舒則是以聶致遠的他者身份而出現的。所謂“他者”,是相對于“自我”而言的。人只有具備自我意識,能夠進行自我認同,將自我作為獨立存在的生命個體才會確認他者,而這種自我意識的覺醒也是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共同的思想啟蒙主題。正如魯迅先生所言:“蓋惟聲發自心,朕歸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6頁。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聶致遠將蒙天舒作為他者而視之是一種主體性的彰顯。然而,在《活著之上》中,聶、蒙二者之間都存在著一種不易被讀者察覺且怪異的關系。作為他者的蒙天舒對于聶致遠來說有一種鬼使神差般的魔力,召喚著聶使其渴望成為蒙,也即是他者對自我有著強烈的塑形作用,自我對現狀不滿,渴望成為他者。更具悲劇意味的是,這一過程并不是自我在他者的召喚下轉型成為他者而終結,而是自我向他者的逐夢過程中伴隨著強烈的心理危機和精神煉獄,承載著難以緩解的糾結與焦灼,最終的結局也不是破繭成蝶,涅槃重生,而是在生命的慣性作用下永遠無法成為他者,在自我的逃逸中咀嚼著靈魂迷失與理想的失落。
具體到作品中來,聶致遠雖然鄙視蒙天舒的鉆營投機、左右逢源,但是對蒙天舒的金錢與權勢卻有著本能的迷戀與渴望。他一方面以知識分子自居,以曹雪芹、陶淵明自勉,有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另一方面又抵擋不住世俗的誘惑,渴望獲得欲望的滿足;一方面鄙視蒙天舒,以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清流姿態不屑于蒙的世俗與墮落,另一方面又對蒙的權勢羨慕不已,潛意識里將其作為目標與榜樣。聶致遠是眾多矛盾的集合體,也正是源于此,他承載著蒙天舒所沒有的精神危機,一方面傳統知識分子的傲岸人格與精神追求的文化基因促使他堅守著獨善其身的理念,另一方面,人本能的世俗欲望又逼迫著他放棄超我,回歸本我。在這種雙重的強力擠壓之下,聶致遠經歷著難以擺脫的精神折磨,而且更具悲劇意味的是,在他者的強烈召喚作用下,聶致遠喪失了自我的本真,欲望的極度誘惑使其執著地要改變自己,而多年形成的本性又決定了他思想與行為的慣性,成為不可改變的。這樣一來,轉型他者注定是失敗的,而自我也在追逐他者的過程中變得面目全非,唯一剩下的就是自我逃逸的迷失狀態,這一狀態又絕非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而且因為他者的持續存在而永不停止,沒有終點的旅途注定是悲劇性的,同樣也是虛無的。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啟蒙是確立他者,實現自我,那么聶致遠則是追逐他者,放逐自我,或者說蒙天舒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完成態,聶致遠是彷徨迷失的現實進行態。更進一步說,聶致遠、蒙天舒實為一人,各自代表當代知識分子人格特征的一個側面。其實,如果我們將《滄浪之水》中的池大為與聶致遠、蒙天舒進行比較式閱讀,就會不難發現池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聶、蒙二人的有機結合,發跡前的池與聶的現實處境、精神狀態極為神似,發跡后的池與蒙的生存樣態也十分接近,甚至最后在父親墓前的懺悔也與《活著之上》結尾處聶致遠的內心獨白異曲同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他者召喚與自我逃逸貫穿著閻真創作的始終,是其作品的深層結構,同時也是揭開其創作密碼的絕密通道。
當然,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找到這個絕密通道,而是要以此為切入點,對閻真的生命書寫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秘。按照前面的分析,以聶致遠為代表的當代知識分子始終處于他者召喚的魔咒之中,不僅陷入長期的精神危機,而且迷失了自我,在這里,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真正具有召喚作用的是什么?毋庸置疑,蒙天舒僅僅是一個符號,他背后的能指才是發動召喚魔咒的罪魁禍首。那么,這個一切孽障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制約著知識分子健全人格的實現?剝離出外在的裝扮,暴露在我們面前的其實是那樣的赤裸:金錢、地位、名譽。歸根到底,引發聶致遠堅守理想發生動搖的根本動因就是名利的誘惑。共同的成長環境卻產生截然相反的現實境遇,同等勞動投入之下分配卻是天壤之別,真才實學的高低在社會認可上卻出現哭笑不得的翻轉。聶致遠在本能沖動之下追逐他者,這本無可厚非,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指責異常乏力。“將道德評判延期,這并非小說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小說是道德審判被延期的領地。”*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孟湄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頁。他者的召喚促發知識分子的分化,形成以聶致遠、蒙天舒為代表的兩大陣營。而無論是聶還是蒙,都與我們理想中的知識分子存在太大的落差,聶致遠的卑微無力、對現實的無奈使知識分子的光輝形象蒙塵,我們在哀其不幸的同時自然而然地怒其不爭。蒙天舒的投機鉆營式小市民特質離知識分子的偉岸人格漸行漸遠,相較于聶致遠,從情感上更為排斥。
理想中的知識分子不僅是知識的擁有者,更是思想的啟蒙者和傳播者,不僅僅是道德規范的制定者,更是踐行者與捍衛者。而以聶致遠、蒙天舒為代表的當代知識分子被“一切向錢看”的時代浪潮所裹挾,他們可以自主地將知識兌換成金錢,把知識作為謀生手段,這樣一來,知識分子本真的道德精神維度無限制的下滑,而現實功利維度卻瘋狂崛起。“金錢是我們時代的上帝,金錢一視同仁地支持截然相反的生活品質,同樣推動大相徑庭的思想方向和情感方向,就好像上帝的觀念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金錢這一語法形式表達其道德偏好。”*西美爾:《金錢、性別、現代社會風格》,顧仁明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第46頁。然而,真正的問題在于“在貨幣經濟生活中,人們通過金錢所能獲得的只能是功能上的等價物,事物自身的價值是無法被替代的。”*西美爾:《金錢、性別、現代社會風格》,顧仁明譯,第50頁。聶致遠、蒙天舒二人所扮演的正是這種喪失實質意義的空洞等價物,自身固有的價值被遮蔽,聶的痛苦也正源于此,這種自我的閹割既是當代知識分子悲劇命運的真實再現,也是其現實精神困境的真實寫照。聶、蒙二人的唯一區別僅僅在于蒙是主動的,聶是被動的。
按照薩義德的觀點,“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23頁。我們以此標準來考察聶、蒙二人,自然失望地發現毋寧談行動,二人根本上就長期處于失語狀態。具體來說,聶不具備話語權,即使在課堂上的言傳身教也遭到自我恪守的艱難與尷尬和學生的質疑與不屑;蒙作為領導干部具備話語權,但是蒙在使用話語權時從不采用知識分子的話語資源,他不會“在其活動中表現出對社會核心價值的強烈關切”,不會“希望提供道德標準和維護有意義的通用符號”*劉易斯·科賽:《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考察》,郭方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3頁。而是最大限度地為自我牟利,實現病態欲望的非理性滿足和自我是身份與價值的虛幻確認。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上述評論過多的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聶、蒙自身,而缺少必備外部社會環境的考量。其實,當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和產業化的魔掌伸向教育以來,高校教師也淪為社會這部大機器上的一個微小零件,機器的正常運轉要求教師讓渡自我價值而單方面服從模式化的需求,成為“單向度的人”,而到底如何實現馬爾庫塞所謂的“大拒絕”,又無需承載以聶致遠為代表的精神危機和以蒙為代表的靈魂出賣,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有時候,復雜問題的提出遠勝于簡單問題的解答,在這一點上,《活著之上》做到了。
二、“圓形”與“扁平”的奇幻張力
我們以愛德華·摩根·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提出的“圓形人物”與“扁平人物”理論考量《活著之上》的人物塑造,就會發展一個相當明顯的特征:作品中似乎只有聶致遠一個可以被歸入圓形人物的行列,其他人物皆趨于扁平。趙平平完全可以用“哭泣”與“抱怨”勾勒其生命輪廓,蒙天舒也可以用喪失責任感的世俗知識分子這一簡單概括。那么,問題則隨之而來,這樣的人物塑造是敗筆還是妙筆?如果確認為敗筆,我們能否簡單粗暴地單方面做出作者創作能力下滑的不負責任結論,還是這樣的下滑映射著作者克服寫作難度,實現自我超越的悲壯心路歷程。如果是妙筆,是作者的有意為之還是無意為之?二者之間各自潛藏著怎樣的文化內蘊與寫作沖動。下面,我們對上述問題進行逐一的猜測性解讀和對話性探索,意圖探究隱藏在圓形與扁平外表之下的奇幻張力。
首先,如果我們確定《活著之上》的人物塑造為敗筆這一大前提,那么,隨之而來的自然是負面的批評:作者被自我情感因素左右而喪失其對筆下人物的真實再現與理性駕馭,主觀預設的二元對立限制了讀者的有機參與和二度創作,過于明顯的主觀痕跡使聶致遠淪為缺乏深度的類型人物,受眾群體被局限于感同身受的高校知識分子。對人物的關注停留在世俗層面而非生命層面。蒙天舒、趙平平則存在嚴重的失真,與現實存在明顯隔膜,蒙的靈魂深度和趙的女性身份確立等重要命題未被有效開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連篇累牘的教科書式批評似乎正是張煒所極力糾正的:“我們現在的某些文學評論,所謂的研究工作,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理解或不想理解作家作品。往往是沒有進入純文學作品的能力卻又急于從學到的理論中求證作品,急于使用學到的新式武器,拿一個作品去解剖。這就糟了,實質上這些工作與作品本身沒有什么關系,因為沒有觸摸到作家作品的核心部分。這個過程只能是對作品的閹割,是幼稚化和簡單化。”*張煒:《純文學的當代境遇》,《魯東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而且,單純從讀者的期待和情感傾向上,也不愿意接受《活著之上》人物塑造為敗筆這一評判。
“文學批評應該對作品進行冷靜地反思和對話性的質疑,從而向社會提供負責任的判斷和有價值的‘批判性話語’”*李建軍:《是大象,還是甲蟲——莫言及當代中國作家作品析疑》,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5頁。我們按照這樣的思路對作品展開猜測性的互動,預先假設作者這樣的人物塑造方式是有意為之的。那么,首當其沖的問題是作者這樣做的意圖何在?從表層上來說,圓形人物與扁平人物的并置對比自然利于人物性格的凸顯,但是這樣做是以犧牲眾多人物形成的鮮活性來成就一個形象為代價的。換句話說,作品中所有人物形象的設置都是為聶致遠一個形象服務的,都是以喪失應有復雜深度性格特征來烘托一個中心人物的。這樣投入與產出比也許過于失諧,甚至得不償失。聰明的作者是不會這樣飲鴆止渴的。而且還應該指出的是,若對《活著之上》的人物塑造探究止步于此,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似乎都有一種意猶未盡之感,因此,作者有意為之的假設似乎缺乏必要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那么,經過抽絲剝繭式的分析,我們僅剩下唯一一種假設,即《活著之上》的人物塑造是作者無意為之的神來之筆,或者是作者潛意識的自然流露。無論是為何,都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正是在這種作者也未嘗覺察與觸碰的縫隙中,才能找到作品潛藏在水下的冰山。在這里,福柯的觀點為我們提供的理論資源:“今天的寫作已經將其自身從表現的維度脫離。(寫作)只指涉它自身,但不是把其限定在其自身的內在性的界定上,而是寫作在其展開的外部性中確立自身的身份。這意味著寫作是諸符號分布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根據意指符者的絕對本質,也很少依據所指的內容。寫作像一種游戲一樣展開自己,這種游戲超越自己的規則和違反自己的限度。在寫作中,要點不是展現或提升寫作的行為,也不是把一個主體固定在語言中,它是一個創造一種使寫作主體持續隱退的空間問題。”*M.Foucault,what Is An Auther?,see The Foucault’s Reader,ed.By Paul Rabinow,P.102,Pantheon Books,New York,1984.按照福柯的觀點,寫作是以作者的隱退為標志的,是“作者把自己減縮為不在場的無”*牛宏寶:《現代西方美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75頁。。《活著之上》的寫作似乎也是以這樣一種方式進行的,作者按照以往的寫作慣性向前自由滑行,不再考慮外部評價標準而是完全受命于內心的聲音,不再醉心于人物的精妙設置而是任由其自由排列組合。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種作者的淡出又是以一種非自覺的方式完成的,并不是作者在素材面前無能為力而被迫選擇的逃逸,其結果是使作品中的人物在未受任何雕琢的基礎上在圓形與扁平的二律背反中迸發出奇幻的張力,在作者的在場與隱退中取得微妙的平衡。如果空間與時間果真是康德的先驗哲學所認為的是人感知事物的先天形式,那么在《活著之上》中,隨著圓形人物與扁平人物之間的奇幻張力作用下,作品中的空間不再僅局限于高校這一狹窄的空間,而是被注入豐富經驗內容的多維空間;作品中的時間也不再只是高校教師生命年輪的單一線性增長,而是被抽離經驗內容的純粹時間。在多維空間中,人物可以不受現實空間羈絆而自由游走,在純粹時間中,人物可以不受現實時間制約而任意穿梭。這樣一來,傳統的關于圓形與扁平的定性評判標準失效,《活著之上》在新的維度上開拓出廣闊的美學意蘊。
三、知識分子評判史的評判
知識分子題材的創作在新文學發生伊始即占據重要位置。魯迅以其特有的深刻揭示出知識分子“夢醒了無路可走”的困境:覺醒的終點是滅亡,回歸必然走向淪落。知識分子在自我強化與自我弱化的二律背反中迷失焦灼,在傳統束縛與生存危機的雙重絞殺下墮落沉淪。因此,“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又在魯迅手中成熟,這在歷史上是一種并不多見的現象”*嚴家炎:《〈吶喊〉〈彷徨〉的歷史地位》,《世紀的定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64頁。。除魯迅之外,眾多其他作家也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書寫著知識分子特有的人生際遇與精神圖景,其中最有文學史價值的莫過于葉圣陶的《潘先生在難中》。作品生動刻畫了民國教員潘先生在軍閥混戰中的茍且偷生的猥瑣形象和首鼠兩端,成為知識分子“灰色化”的典型代表。這里當然不是在復述文學史,既無必要,也無意義。真正的問題在于,從《潘先生在難中》到《活著之上》,知識分子評判史發生了重大偏轉,這不僅意味著主流價值取向的變異,更記錄了社會思潮的整體流變。對這一流變歷程的深入透析才是本文的真正意圖所在。
毋庸置疑,讀者對潘先生這一形象的評判幾乎清一色是負面的。即使偶有相對客觀且具有深度啟發意義的觀點:“潘先生的行為并不是因為比別人卑劣,而是因為人們包括作者對其有著更高的人格要求。如果潘先生是一個農民,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是偉大的。因此說,社會是不公正的,因為它制定了不公平的道德層次。一個行為并不比潘先生高尚的工農民眾或者其他的什么人,也可以憑借歷史和社會對知識分子預設的不公正的標準,對其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作為社會中的普通個體,潘先生為什么一定要比別人活得更高尚?所以,首先應該懷疑和譴責的是既定的道德規范,而不是潘先生個人。如果說他應該受到所謂虛偽的指責的話,那么也正是這種超越于人的正常需要的道德規范制造了他的虛偽……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知識分子有一種高遠的倫理要求,而知識分子也把過于沉重的社會使命肩于自身,把社會使命看得過于沉重,并在理論上自認了這一角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歷史承傳使中國知識分子的每一種行動和思想都有了特別的要求,而為人師表的信條史足教師做人的傳統戒律。因此,一旦知識分子超出這一道德規范而表現出一種常人應有的欲望時便被人譴責。人的社會存在包含社會義務和社會責任兩個層次的要求,社會義務本質上是一種起碼的公民意識,是社會規范的一般要求。職業道德便屬于社會義務范疇;而社會責任則是一種更高的道德要求,是超越于自己的利益需求而表現出來的崇高。作為社會的精英,知識分子應該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慨當以慷的社會責任感,但是與天下同憂,和天下同樂也絕不是不崇高的狀態。但是在中國傳統的意識中,‘永遠高尚’或‘不許平庸’實際上己經成為全社會的評價尺度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傳統角色。”*張福貴:《錯位的批判:一篇缺少同情與關懷的冷漠之作——重讀葉圣陶的小說〈潘先生在難中〉》,《文藝爭鳴》2004年第5期。。也遭致各方的反駁*賀仲明:《弱者批判與知識分子的道德要求——也談對〈潘先生在難中〉的理解》,《文藝爭鳴》2004年第6期。,難成主流。而對大部分《活著之上》的讀者而言,對聶志遠的同情與理解遠遠超過潘先生,讀者從對知識分子“灰色人生”的鄙視轉為理解,受眾情感的翻轉映射著知識分子不再作為道德的楷模和精神導師被頂禮膜拜,不再被視為“尋求提供道德標準和維護有意義的一般象征的人和理性、正義、真理這樣的抽象觀念的專門看護人”*張汝倫:《思考與批判》,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第551-552頁。,而是作為大眾中的一員,同樣面臨柴米油鹽的瑣事煩擾,也不再被強制要求具備高尚品質與犧牲精神,一旦堅守不定即遭致全面討伐。所有這一切共同指向的是知識分子角色向大眾的回歸和先鋒精神的下滑。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雖然將“回歸”與“下滑”并置,但是二者卻有著截然相反的意義指向。“回歸”象征著某種程度上的進步。知識分子向大眾的回歸意味著中國傳統“學而優則仕”的觀念破產,知識分子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啟蒙者姿態俯視大眾,以悲天憫人的超脫情懷觀照大眾的悲苦。知識分子回歸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也有著凡人的喜怒哀樂,面臨生存危機的擠壓也會卑微折腰,也會為了欲望的病態滿足而出賣靈魂。這一定意義上有效規避了啟蒙所帶來的負面因子:“他們的啟蒙并不是真正立足于喚醒對象的自覺,以求達到對象的獨立自主,而是以一個領袖和導師的身份出現,居高臨下地把自己的主觀思想灌輸到對象中去,而灌輸本身就帶有強制性。這種啟蒙是干預式的,而非啟發式的。這種干預式的啟蒙顯然帶有專制特征。但是這種啟蒙的專制是隱藏在堂吉訶德式的熱情無私的教誨背后的。不但啟蒙者自身不自覺,而且被啟蒙者也難以自察。問題在于,是被啟蒙者同意這么做的,是被對象所歡迎的所渴望的。這是崇高的理想和道德追求目標下的手段的專制,人們往往為了目標的崇高,而自覺或半自覺地接受這種專制”*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8頁。。他們(知識分子)不再是冰冷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的鮮活生命,他們不是一種群體性的稱謂,而是對一種新的社會階層的概括;他們喪失了導師的光環,但卻收獲了凡人的真實情感;他們不再以站在神壇上布道的圣人身份出現在社會視野,而是以普通大眾的平民姿態映入公眾的眼簾。溝通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扭帶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說教而是作為人的真情實感的普遍流露。
相對于“回歸”的進步指向,“下滑”則不可避免地導向難以操控的退步。從對潘先生的批評指責到對聶志遠的理解同情,映射著受眾對知識分子主體性彌散與精英意識弱化從痛心疾首到悲觀失望的異化過程。因為抱有希望,所以才會怒其不爭。一旦希望破滅,自然僅剩下原始情感的同情。對于潘先生,從作者到讀者似乎依舊保留其能教育救國的點滴希望;而對于聶志遠,僅僅是對倒霉蛋與失意者的樸素同情與本能憐憫。可怕的并不是聶致遠內部承受的靈魂陣痛和外部遭遇的體制擠壓,最可怕的是希望的破滅與激情的冷卻。精神一旦失落,剩下的只能是物質的超常態欲求,對更新的感官刺激的追逐,靈魂的游蕩與價值的虛無。因此,《活著之上》的價值似乎并未止步于對知識分子悲劇命運的單純揭示與呈現,而是對當代知識分子評判的考察中展現更為悲涼的文化沙漠與精神荒原,進而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與重視,探尋知識分子的救贖之路。
吉林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學理依據探究”(2016120)。
趙耀(1989—),男,吉林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長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