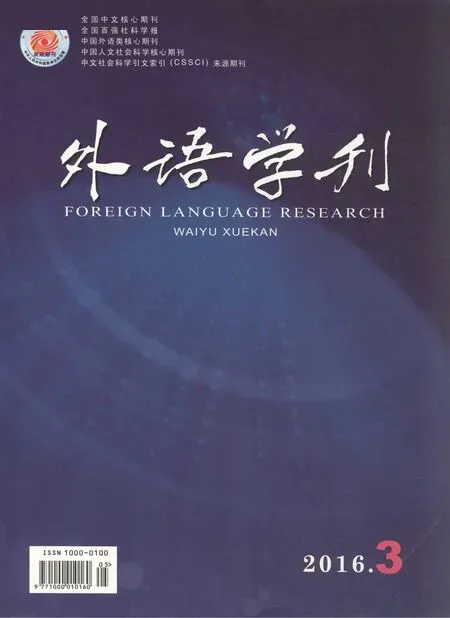哀悼與憂郁癥*
——論《理智與情感》中的心理與權力
武 靜 范一亭
(北京科技大學,北京 100083)
哀悼與憂郁癥*
——論《理智與情感》中的心理與權力
武 靜 范一亭
(北京科技大學,北京 100083)
《理智與情感》是簡·奧斯丁發表的第一部作品。小說中性格迥異的姐妹倆在“失去所愛”時,理性的姐姐埃莉諾表現出一種“哀悼”,而善感的妹妹瑪麗安則進入一種“憂郁癥”狀態。弗洛伊德的《哀悼與憂郁癥》區分正常的“哀悼”和病理性“憂郁癥”,而實質上無論是“哀悼”還是“憂郁癥”,其背后隱含的是個體與權力在心理層面的博弈。本文梳理“憂郁癥”這一心理名詞在文化理論史上從弗洛伊德到巴特勒的衍變,強調精神層面主體的分裂是主體服從的基礎,而“憂郁癥”造成主體反對自身的轉向,是權力迫使主體“服從”的必經之路。研究表明,埃莉諾的“哀悼”事實上是其在權力與個體之間成功斡旋的結果,屈從中不乏女性主義的能動性;而瑪麗安的“憂郁癥”則展現權力在心理層面的管制和外部規訓的共同作用下迫使女性個體走向服從,而姐妹二人不同的心理癥狀無疑揭示奧斯丁小說的心理、性別與權力結構的關聯。
《理智與情感》;哀悼;憂郁癥;權力;心理;性別
1 引言
簡·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6)作為經典作家的地位毋庸置疑。19世紀著名的莎士比亞批評家辛普森(Richard Simpson)將奧斯丁與莎士比亞相比肩(Wiltshire 2003:59),到了20世紀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將奧斯丁視為歐美文學史上的心理大師亨利·詹姆斯和普魯斯特的先驅(Southam 1987:281)。本文借助弗洛伊德《哀悼與憂郁癥》(1917)一文以及當代文化理論家朱迪絲·巴特勒帶有福柯色彩的“憂郁癥”概念,來考察奧斯丁的這部代表作。研究表明,小說中性格迥異的姐妹倆在愛情中雖然都有過“失去所愛”的經歷,但姐姐埃莉諾“思想敏銳,頭腦冷靜”,妹妹瑪麗安則“沒有節制,過于感情用事”,因此理智的埃莉諾在失去所愛時表現出克制的“哀悼”(mourning),而瑪麗安則一病不起,進入一種“憂郁癥”(melancholia)狀態,最終埃莉諾得償所愛,而瑪麗安則退而求其次,“懷著崇高的敬意和真摯的友情”嫁給了本不喜歡的布蘭登上校(奧斯丁 2013:9,276)。此等過程迥異卻結局類似的心理衍變能更好地幫助我們深層次認識奧斯丁小說中的權力與性別的關系。
2 從心理到權力:弗洛伊德、福柯與巴特勒
在早期對奧斯丁的評論中,學者通常二元對立地看待作家對“理智”與“情感”關系的處理:認為埃莉諾代表理性,而瑪麗安則代表感性或者非理性,整部作品是對理性的褒獎和對感性以及非理性的批評,是現實主義對當時“淹沒在一派偽浪漫主義的感傷淚水之中”的英國小說的有力回應。奧斯丁研究專家巴特勒(Marilyn Butler)認為:在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奧斯丁的作品表現張揚情感的激進派(雅各賓派)和重視理性、責任以及自我克制的保守派(反雅各賓派)之間的思想論戰,《理智與情感》便是這一論戰的鮮明代表,反映奧斯丁的保守傾向(黃梅 2012:235-236)。表面上看,這是奧斯丁支持理性的保守派的表現,然而,探尋理性和非理性背后深層次的權力關系可以幫助我們發現,這其中蘊含著權力與個體之間的博弈。正如福柯所說,“權力的效果能深入每個人最精微和潛藏的部分”(Foucault 2007:216),只是由于“社會規范在心理層面的作用為規訓權力提供更為隱秘的作用方式”,于是“這種規范在精神心理上的運作為管制的權力提供一種比外在的強力更陰險的路線,它的成功使它在社會范圍內心照不宣的實施成為可能”(Butler 1997:21)。所以“感情強烈,然而會克制自己”的埃莉諾通過斡旋個體意愿與外部權力,使權力規訓在心理層面以無害的“哀悼”形式出現;而“感情用事”、“沒有節制”和“不謹慎”的瑪麗安則患上“憂郁癥”,使權力規訓以一種新的心理形式出現,使她“天生注定要發現她的看法是錯誤的”(奧斯丁 2013:9,276)。與其說是“天生注定”,不如說是權力博弈、協商與規訓的必然結果。所以埃莉諾的理性只不過是主體與外部權力斡旋的結果,而瑪麗安的非理性則是對規范的反叛,但反叛必將受到權力的懲罰和規訓,表現為主體在權力心理層面的管制和權力外部規訓的共同作用下走向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服從(subjection),整個小說著重表現的正是這種權力與個體在心理層面的博弈。
美國文化理論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將福柯的權力理論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做了完美的嫁接,她指出:人們“習慣于把權力想象為一種來自外部的壓迫主體的東西”,但是根據福柯的觀點,服從意味著被權力屈從(su-bordinated)的過程,同時也是主體形成的過程,即在屈服(submission)中,權力同時形成主體(Butler 1997:2)。然而,無論是阿爾都塞的“詢喚”(interpellation)還是福柯的“話語生產”(discursive productivity)都沒有解釋主體是如何形成的,那么這就形成一個悖論:“一種關于主體指稱的矛盾性”, 福柯對這一表述的矛盾之處并沒有作詳細的闡述。而關于主體如何在屈從中形成的問題,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尼采的《論道德譜系》中早有涉及,二者都將主體在屈從中的形成描述為外部權力以一種“轉向”(turning)的姿態進入精神層面,并“構成主體自我認同的精神形式”(psychic form),這是權力進入精神領域的開端(同上:2-4)。對此,巴特勒從后現代主義詩學立場對權力與心理之間的緊密關聯進行細致的梳理。
根據巴特勒的分析,當權力不再被簡單地看成一種“外力”而起作用時,權力在精神心理層面的運行便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德里達認為,福柯關于權力的理論實際上早已存在于弗洛伊德的理論中(Derrida 1998:93)。格里斯(Wendy Grace)則認為,福柯從1970年開始將心理分析看成“權力在全景式監獄社會運行的又一種工具”(Grace 2013:228),而心理學實質上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機器(ideological apparatus)來運行和起作用的”(Sloan 2007:viii)。弗洛伊德的理論于是就和邊沁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理論有諸多相似之處(Tonner 2007:1),也進一步印證“心理學本身是現代權力運行不可或缺的媒介”(Hook 2007:2)。巴特勒由此指出,要厘清權力在心理層面的運行所采取的形式,首先必須“把權力理論和精神分析理論結合在一起進行思考”(Butler 1997:2-3)。盡管福柯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很少提及,但對“服從”的解釋又必須在心理層面進行探索,因為“主體(subject)的分裂……是處于服從(subjection)狀態的主體的基礎”(同上:1)。那么“服從”便意味著分裂的主體相對于自身的“轉向”,在被權力屈從(subordination)的過程中,使權力成為“主體的自我認同的精神形式”,進而替代主體成為新的服從的精神主體(同上:4)。如果說弗洛伊德對《哀悼與憂郁癥》中主體的“分裂”和“轉向”的論述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揭示這一新主體的產生,那么福柯化的巴特勒的權力理論無疑結合了二者的精華。
3 哀悼與憂郁癥:權力作用下主體的產生
福柯認為,“應該在其物質層面設法把握作為一種主體構成的服從(subjection)”(Faucault 1980:78),然而無論是在福柯還是阿爾都塞的學說中,“主體都是以對權力的屈服為開端”,都沒有解釋主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但是,“服從”不僅包含主體被權力屈從的過程,還包含主體形成(forming)的過程,所以要探尋“權力在主體屈從和產生的雙重作用(valence)”,必須要厘清權力在心理層面運行所采取的形式(psychic form)(Butler 1997:2)。而弗洛伊德關于《哀悼和憂郁癥》的理論恰好為權力在心理層面所采取的形式和運行方式提供理論基礎:即在憂郁癥中“主體的分裂和其反對自身的轉向”,構成“服從”的必要條件(同上:168)。通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我們發現,姐妹倆在面對“失去所愛”時,埃莉諾呈現出一種哀悼的狀態,而瑪麗安則進入“憂郁癥”的狀態。不同的是,埃莉諾在哀悼之后恢復了自由的“自我”(ego),而瑪麗安則在憂郁癥中使“自我的一部分讓它自己反對其他部分”,造成主體的“分裂”和“轉向”,自我自身成為一個心理對象(psychic object)被生產出來,而這一過程預示一個新的主體的形成(同上:168)。
弗洛伊德指出,哀悼和憂郁癥有共同的誘因,即“因為失去所愛之人而產生的一種反應,或者是對失去某種抽象物所產生的一種反應,這種抽象物所占據的位置可以是一個人的國家、自由或者理想等等”(Freud 1986:203)。但哀悼和憂郁癥最重要的區別卻在于,哀悼是一種“痛苦的情緒”,“當哀悼工作完成之后,自我再次變得自由無拘”(同上:209);而憂郁癥則造成自我的分裂,“自我的一部分讓它自己反對其他部分,批判性地評判其他部分,把其他部分當作它自己的對象”(同上:207)。在這種“自我反對自身的轉向中,自我自身成為一個心理對象(psychic object)被生產出來”,成為權力進入心理層面的開端(psychic inception)(Butler 1997:168)。
在小說中,被瑪麗安認為是缺乏感情的埃莉諾在失去愛人時經受巨大的痛苦,“轉瞬間,她幾乎為感情所壓倒——情緒一落千丈,兩條腿幾乎站都站不住了……她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抑郁之感”,在她平靜的語氣后面“隱藏著她從未感到過的激動和憂傷”以及“屈辱、震驚和惶恐”,“為即將把她和她心愛的人永遠隔離開來的種種障礙而暗自悲傷”(奧斯丁 2013:103,104,106),弗洛伊德將這種哀悼的情緒稱為“痛苦的”情緒,它表達的是“對哀悼排他性的虔誠”;他進一步指出:“雖然哀悼涉及到主體與正常的生活態度嚴重分離,但它絕不會讓我們將其當作一種病態的情況,并且認為它需要求助于醫學治療。克服哀悼只需一段時間的緩解即可”(Freud 1986:204)。所以埃莉諾并沒有一蹶不振,在分析個中緣由后,她認為“愛德華的魯莽行動給她帶來了一時的痛苦……她遲早是會恢復平靜的”(奧斯丁 2013:193)。對于埃莉諾來說,“現實已經表明所愛對象已經不存在了,這進而要求所有的力比多(libido)都應該從對這個對象的依戀中回撤,這一要求遭到了可以理解的反對”(Freud 1986:204),因為埃莉諾仍然“希望從露西的神色里發現點破綻”來證實“露西所說的絕大部分都是假話”,從而逃避現實;而當真相被證實,“除了她自己的主觀愿望外,無論如何也得不出相反的結論”時(奧斯丁 2013:102,105),她便進入“哀悼的狀態”,即沉浸在一種“痛苦的情緒”中,但是自我終究會接受這樣的現實,“當哀悼工作完成之后,自我再次變得自由無拘”。所以埃莉諾表現出的是一種理性的克制,并告訴自己“他愛德華就是露西的丈夫了”(同上:213)。接受這一現實,在哀悼過后,力比多從這個依戀的對象撤回,她認為“盡管人們可以說一個人的幸福安全依賴某一個人,但是這并不意味應該如此——那是不恰當,不可能的”(同上:193)。于是,她便積極地投入生活,甚至當愛德華由于和露西私定終身而被剝奪了繼承權后,她還積極努力地為愛德華謀了個牧師的生計。
而瑪麗安的情況卻完全不同,面對同樣的遭遇,她進入了一種“憂郁癥”的狀態。弗洛伊德提出,盡管哀悼和憂郁癥有相同的表象,如“非常痛苦的沮喪,對外在世界不感興趣,喪失愛的能力,抑制一切活動”等,但“自我評價方面的失調”卻是憂郁癥獨有的特征(Freud 1986:211)。這種“自我評價方面的失調”把正常的哀悼和病理性憂郁癥區分開來,使自我分裂,造成“主體反對自我的轉向”,通過將對象回撤進自我,并建構出與喪失對象本身的認同(identification),從而通過一種“自我折磨”的方式“表示了與一個對象相聯系的虐待狂傾向和憤恨傾向的滿足……通過自我懲罰這條迂回路徑,來向最初的對象復仇”(同上:211)。但是,由于自我已經與這個喪失的對象相認同,憂郁癥便呈現出分裂出來的自我對其他部分自我的一種譴責和懲罰。所以,在憂郁癥中“自我評價降低,以至于通過自我批評、自我譴責來加以表達,這種情況發展到極致時甚至會虛妄地期待受到懲罰”(同上:212)。瑪麗安在遭到威洛比的拋棄后,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她完全變了樣——變得病弱不堪——被折磨垮了”,“意志變得如此脆弱,仍然認為現在克制自己是不可能的,因此落得越發沮喪”,人們認為她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戀愛”,并且在一場風寒后一病不起,“差一點送了命”(奧斯丁 2013:154,198,253)。瑪麗安自己卻認為,她的不幸遭遇“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并“一直設法為威洛比開脫罪責”,把本應該對威洛比的譴責轉化為一種“滔滔不絕的自我責備”,認為自己“殘忍自私”,“要痛恨自己一輩子”(同上:156,194,253)。即使在重病中,她也渴望“有機會向上帝、向大家贖罪”,而到頭來“居然沒有一命嗚呼”,于是“滔滔不絕地自我責備”(同上:253)。在憂郁癥中,面對一個失去的外在客體或理想時,拒絕“從對這個對象的依戀中回撤”,而使這個客體或理想回撤進自我,進而取代自我,“以那個被放棄的對象來建構自我的認同”,“以這種方式,對象喪失(object-loss)變成了自我喪失(ego-loss),而自我與所愛之人的沖突變成了橫亙在自我的批判性活動和由于認同作用而改變的自我之間的裂縫”,這造成主體的分裂,為主體的產生創造條件(Freud 1986:206)。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姐妹倆有相同的經歷,但其結果卻不一樣。對于埃莉諾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我會“尊重(失去所愛之人的)現實”,力比多會“從對這個對象的依戀中回撤”,從而在哀悼之后使“自我再次變得自由無拘”(同上:209)。而瑪麗安則在憂郁癥中“力比多并未流向另一個對象,它回撤進了自我”,進而取代自我(同上:209)。于是如巴特勒所說,在“自我反對自身的轉向中,自我自身成為一個心理對象(psychic object)被生產出來,而這正是權力進入精神心理層面的開端(psychic inception)”(Butler 1997:168)。
4 屈從與服從:個體與父權制權力的博弈與斡旋
福柯曾指出,“古典時代的人發現人體是權力的對象和目標……這種人體是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它服從,配合,變得靈巧、強壯”(Foucault 2007:154)。在任何社會中“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控制”,但是在古典時代末期,這種權力的運行更加精確有效(Foucault 2007:154)。這種精確的“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楊衛東 2002:54),因為在奧斯丁生活和寫作的時代,整個社會正經歷現代化進程,資本主義發展進入第一個輝煌階段,農業慢慢發展成為一種資本主義產業(Irvine 2005:7)。在這個正在生成的斂財逐利的社會中,個人角色和人際關系被資本主義利益關系所左右,形成一整套為資本主義發展所服務的婚姻、法律和社會規范,為現代化進程中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福柯指出,“規范(norm)的力量似乎貫穿在紀律(disciplines)之中,自18世紀以來,它與其他力量——法律、圣經、傳統結合起來……成為古典時代末期重要的權力手段之一”(Foucault 2007:207)。在這個過程中,女性漸漸被隔離開來(Irvine 2005:7),依從對資本主義發展有利的各種制度和規范來選擇自己的人生。亨利·達什伍德去世后由他的兒子繼承了家產,資本主義“長子繼承權”(primogeniture)保證資本的聚集,而女性則被排除在外,所以盡管兩姐妹的祖祖輩輩都定居在諾蘭莊園,但亨利死后,“全盤家業都被凍結了”,只能世襲給“偶爾來過幾趟的兒子和四歲的孫子”,埃莉諾姐妹和母親“反而落得寄人籬下”,不得不另尋去處(奧斯丁 2013:7-10)。對這樣的制度她們只能遵從,這是權力從外部物質層面起作用的結果,即個體在外部權力的作用下身體的屈從。在這個屈從的過程中,“規訓(discipline)就制造出馴服的、訓練有素的肉體,即‘馴順的’肉體”(docile body)(Foucault 2007:156)。但是“服從”卻包含兩個必要條件:一是“被屈從”(subordinated)的過程,即“馴順的肉體”的形成,二是主體的分裂和轉向導致權力以一種精神形式成為新的主體,即馴順的精神主體。而就權力如何從物質領域進入精神領域,并造就馴服的精神主體,巴特勒借助弗洛伊德“自我”與“超我”(super-ego)的理論給出完美的闡釋。
弗洛伊德認為,“自我與理想(超我)之間的沖突……最終反映出什么是現實,什么是心理、外在世界和內在世界之間的對立”(Freud 1960:32),其理論中的“超我”人格實際上相當于福柯理論中的規訓的權力(Tonner 2007:1)。主體化過程(服從)主要通過身體發生,“權力不僅僅對身體起作用,而且也在身體內部起作用,權力不僅產生出一個主體的邊界,也滲透到那個主體的內部……對身體來說,似乎有一個內在層面(inside)在權力入侵之前就存在了”。巴特勒認為,這個“內在層面”是個體的心理范疇,而心理層面形成了抵制權力管制的陣地(Butler 1997:79,84,86)。然而,在古典時代這種權力的規訓和控制已經演化得愈發精確有效,“人體不再是被當做不可分割的整體來對待,而是‘零敲碎打’的分別處理,對其施加微妙的強制”,所以不僅身體的各部分受到權力的強制,就連最隱秘的心理層面也無法逃脫權力的管制(Foucault 2007:155)。
權力對身體的強制產生主體的屈從,因為“社會范疇同時意味著屈從和存在,服從利用存在的欲望,在服從的范圍內,主體存在的代價就是屈從”(Butler 1997:18)。阿爾都塞和福柯都認為,在“服從”的過程中,有一種基本的屈從(同上:5)。這就是為什么埃莉諾姐妹必須遵從外部權力,以制度和規范的形式對其生活進行規范。這種“屈從”表現為主體對外部權威力量的一種接受, 但是在“屈從”中暗示一種主體的能動性(agency),主體這種能動性總是且只反對權力(同上:15)。這種能動性存在于埃莉諾“自由無拘的自我”之中,當她在確認愛德華訂婚的消息時,盡管帶著“揪心的悲愴”,卻“沒有失去自制”(奧斯丁 2013:101)。后來在向瑪麗安袒露心聲時,她表示對于愛德華與露西訂婚這種斂財逐利的婚姻現象她只能屈從,盡管她“一直很痛苦”,但是由于她“要向親友負責,不讓他們擔心”,所以她理性地克制著她的痛苦情緒,不讓人們發現異樣,而這些都“不是自然發生的”,都是她“一直拼命克制的結果”(同上:192,194)。埃莉諾的這種“克制”實際上是主體能動性斡旋外部權力的表現,對于外部權力的規訓(資本主義婚姻制度),她并沒有一味地反抗,也沒有被徹底壓垮,而是在屈從中保存主體斡旋權力的能動性,保證主體的存在,并且同時微妙地彰顯女性主義的能動性。
而對于瑪麗安而言,對規訓權力的一味抗拒使這種能動性在憂郁癥中,即變得“貧乏和空虛的自我”中喪失,進而被權力的精神形式所取代,成為馴順的精神主體。威洛比為了追逐金錢利益和格雷小姐訂婚而拋棄了瑪麗安,作為和埃莉諾一樣的資本主義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她并沒有調停(mediate)自身與規訓權力的沖突并選擇屈從,而是拒絕接受現實,她“一陣陣地失聲痛哭,感到悲痛欲絕”,“她白日不思茶飯,夜晚睡不踏實……感到頭痛胃虛,整個神經脆弱不堪”,并告訴埃莉諾“你永遠也看不到我變成另外一幅樣子。我的痛苦無論怎樣也無法解除”(同上:137,138)。她對權力一味抗拒的結果便是權力對身體更加嚴厲的規訓,于是瑪麗安一病不起,“病情越來越嚴重”(同上:224),最后進入“憂郁癥”的狀態,肉體被規訓權力徹底壓垮,精神層面也隨之陷落,她開始“滔滔不絕地自責”,使“自我的一部分反對其他部分”,造成主體的“分裂”和“轉向”,權力以一種自我“轉向”后的精神形式替代主體,使主體徹底喪失反抗權力的能動性(Freud 1986:209)。
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埃莉諾的“哀悼”還是瑪麗安的“憂郁癥”,實質上都是對權力規訓所作出的反應,同時也是權力在規訓過程中對個體二元分化和標記的結果。弗洛伊德從心理分析理論出發,將憂郁癥定性為一種精神疾病。福柯則將憂郁癥定義為瘋癲的一種,認為“瘋癲只有相對于非理性才能被解釋,非理性是它的支柱,或者說非理性規定瘋癲可能的范圍”(Foucault 1988:75)。憂郁或憂郁癥作為一種異常的狀態,早已被廣泛關注,古希臘醫學家希波克拉底的“體液學說”以及蓋倫(Galen)的“氣質學說”都將憂郁癥歸結于“黑膽汁”(black bile)過多導致人體體液的不平衡。18世紀,塞繆爾·約翰遜在他編寫的《英語大辭典》(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1755)中,將憂郁定義為“一種由于黑膽汁過多而導致的疾病,一種執著于某物導致的瘋癲”(Bowring 2008:14)。所以“理性/瘋癲關系構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個獨特向度”,理性時代“造成理性與非理性相互疏離的斷裂,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強行使非理性不再成為瘋癲、犯罪或疾病”(Foucault 1988:2)。而權力對個人的控制按照雙重模式運行,首先將對象二元劃分并打上“瘋癲/心智健全、有害/無害、正常/反常”等標記,然后對反常的個體進行分配和規訓(Foucault 2007:223)。
弗洛伊德的“哀悼與憂郁癥”實際上將埃莉諾和瑪麗安劃分進了不同的群體范疇,瑪麗安成為被打上標記的“反常的個體”,使其進一步成為“權力規訓的對象和目標”(同上:154);而奧斯丁對疾病在社會文化層面意義的關注,使瑪麗安的這場疾病在文學象征層面具有福柯式規訓和懲罰的意味(Wiltshire 2005:304)。在瑪麗安病重命懸一線之際,奧斯丁安排善于斡旋的埃莉諾同資本主義婚姻和父權的代表威洛比進行交流,之后瑪麗安象征性地復活并從憂郁癥中康復。這場帶有亞里士多德式凈化色彩(Aristotelian Catharsis)的懺悔和暢談似乎象征昏迷中的瑪麗安的本我、自我、超我間的對話和斡旋,代表自我的埃莉諾作為重病昏迷中瑪麗安的代理,與代表資本主義婚姻和父權的威洛比進行對話,威洛比懺悔自己“并非一直都是個壞蛋”,但為了“重振家業,避免陷入相對的貧窮”,他不得不在妻子的威逼下,“奴隸般地抄寫了”絕情信給瑪麗安,并哀求埃莉諾“可憐可憐他當時的處境”(奧斯丁 2013:234,235,240)。而最后埃莉諾“確實改變了對他的看法,她還說原諒他,同情他,祝他幸運”(同上:243)。這無疑代表本我與超我的一次調停,個體與權力的一種斡旋(讀者應該注意到經歷“哀悼”之情后的埃莉諾在此處的能動作用)。所以在這場會面后,瑪麗安奇跡般地康復,并按照大家的意愿選擇嫁給布蘭登上校,成為一名“擔負起新的義務……的村莊的女保護人”(同上:276),至此她同埃莉諾一起成為奧斯丁筆下典型的啟蒙女性主義的代表。
在這場個體與權力的博弈中,埃莉諾在權衡自身欲望與外部權力時,理性地斡旋與外部權力的關系,雖然屈從于外部權力,卻仍舊保存反抗和調停權力的能動性,她在被權力擊垮的重病中的瑪麗安昏迷之際,以調停者的身份與權力進行斡旋協商,最終幫助妹妹達成心理與精神上的雙重和解。而瑪麗安最終成為權力從外部和心理層面雙重管制下“服從”的個體,這無疑代表福柯意義上的被規訓的個體。
5 結束語
蒲葦(Mary Poovey)認為,與奧斯丁的其他作品相比,《理智與情感》是一部更為“陰暗”的小說,主要表現個人意愿與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Poovey 2009:32)。而這場沖突正是個體與權力的博弈,很明顯個體的意愿屈從了社會規范代表的規訓權力,其最終結果是權力完成了對個體的規訓與管制。這種個體在物質層面對權力的屈從保證主體的存在;而個體的激烈反抗必然招致權力更加嚴厲的規訓與管制。奧斯丁對疾病在社會文化層面意義上的關注(Wiltshire 2005:304),使瑪麗安的疾病成為違反規范的“懲罰”(Mullan 2005:384)。在這場個體與權力的博弈中,埃莉諾在“哀悼”中保持理性的斡旋,使性別的主體在屈從的條件下得以存在,在馴順的肉體中保存了“自由無拘的自我”和主體的能動性。而瑪麗安則在反抗資本主義和父權的過程中,招致了權力更加嚴厲的規訓與管制,使自我變得“貧乏而空虛”,喪失了應有的能動性,導致權力的精神形式對自我的取代,最終走向主體的服從。
黃 梅. 新中國六十年奧斯丁小說研究之考察與分析[J]. 浙江大學學報, 2012(1).
簡·奧斯汀. 理智與情感[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3.
楊衛東. 規訓與懲罰——《土生子》中監獄式社會的權力運行機制[J].外國文學, 2002(4).
Bowring, J.AFieldGuidetoMelancholy[M].Harpenden: Old Castle Books, 2008.
Butler, J.ThePsychicLifeofPower:TheoriesinSubjection[M]. Chicag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errida, J.To Do Justice to Freud: The History of Madness in an Age of Psychoanalysis[A]. In: Davidson, A. (Ed.),FoucaultandHisInterlocutors[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A]. In:Gordon, C.(Ed.),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andOtherWri-tings, 1972-1977[C].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Foucault, M.MadnessandCivilization:AHistoryofInsanityintheAgeofReason[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
Foucault, M.DisciplineandPunish:TheBirthofthePrison[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7.
Freud, S.TheEgoandtheId[M]. London/New York: Norton, 1960.
Freud, S.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A]. In: Smith, A.(Ed.),TheStandardEditionoftheCompletePsycholo-gicalWorksofSigmundFreud,VolumeXIV(1914-1916):OntheHistoryofthePsycho-AnalyticMovement,PapersonMetapsychologyandOtherWorks[C]. London:Hogarth, 1986.
Grace, W. Foucault and the Freudians[A]. In: Falzonetc, C.(Ed.),ACompaniontoFoucault[C].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Hook, D.Foucault,PsychologyandtheAnalyticsofPower[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Irvine, R. P.JaneAusten:ASourceBook[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5.
Mullan, J. Psychology[A].In: Todd, J.(Ed.),JaneAusteninContext[C].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oovey, M.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Consolations of Form: The Case of Jane Austen[A].In: Bloom, H. (Ed.),Bloom’sModernCriticalViews:JaneAusten,NewEdition[C].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09.
Sloan, T. Preface[A]. In: Hook, D.(Ed.),Foucault,PsychologyandtheAnalyticsofPower[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Southam, B.C.JaneAusten:TheCriticalHeritage,Volume2, 1870-1940[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7.
Tonner, P. Freud, Bentham: Panopticism and the Super-Ego[J].CulturalLogic:AnElectronicJournalofMarxistTheory&Practice, 2007(10).
Wiltshire, J.RecreatingJaneAusten[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Wiltshire, J. Medicine, Illness and Disease[A]. In:Todd, J.(Ed.),JaneAusteninContext[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MourningandMelancholia:OnPsychologyandPowerinSenseandSensibility
Wu Jing Fan Yi-t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Elinor and Marianne, the two sisters in Jane Austen’s first novelSenseandSensibility, when facing “the loss of a beloved person”, respond quite differently. Elinor exhibits a process of Freudian mourning whereas Marianne enters into a state of melan-cholia.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the psychic process of mourning or melancholia demonstrat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dividual subject and the Foucauldian disciplinary power at the psychic level. By drawing upon the cultural theoretical history of melancholia from Freud to Judith Butler, the paper analyzes how melancholia leads to the subject’s turning back upon itself as the indispensible stage of subjection. While Elinor’s mourning is the result of her mediating with the disciplinary patriarchal power, thus manifesting both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her feminist agency. Marianne’s story of melancholia as the outcome of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subject by the psychic form of patriarchal power results from her fierce rebellion against it. Eventually, Marianne yields to the double discipline of power at the physical and psychic level by symbolically falling into great sickness, hence gets into the state of subjection. By so doing, Austen presents an interfacing of power, gender and psychology.
SenseandSensibility; Mourning; Melancholia; power;psychology; gender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19世紀英國文學文化思想史研究”(12YJCZH041)的階段性成果。
I106
A
1000-0100(2016)03-0152-6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31
定稿日期:2016-03-10
【責任編輯王松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