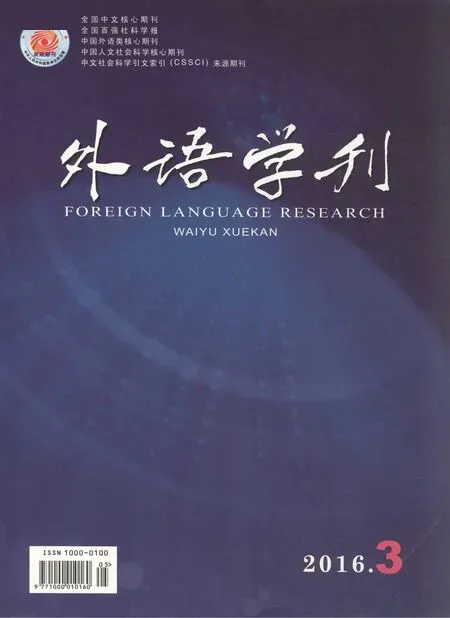識解理論視角下的《黃帝內經》醫學術語翻譯
孫鳳蘭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 100089)
識解理論視角下的《黃帝內經》醫學術語翻譯
孫鳳蘭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 100089)
中醫術語在語義內涵、文化意象、認知背景等方面特點突出,這些特點造成一定的翻譯難度,也形成不同的譯文。分析翻譯語言背后譯者的認知機制,有助于解釋同一文本產生不同譯文的深層原因。基于此,本文依據認知語言學中的“識解”理論來分析《皇帝內經》經典英譯本在術語翻譯方面的差異。本研究側重從4個方面討論中醫術語翻譯的差異: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以及詳略度,并對產生這些“識解”方式差異的深度原因做出解釋。本文認為,譯者的轄域和背景盡可能接近原文世界,視角與原文實現最佳關聯,突顯上最大可能接近原文的認知參照點,詳略度上體現認知努力和認知增量,這些都有助于最大程度準確翻譯原文本義。
識解理論;醫學術語;翻譯;《黃帝內經》
1 引言
《黃帝內經》是中國古典醫學的理論思想基礎,是現存最早的完整的中醫典籍。“斯書之問世, 奠定了華夏醫藥千古一脈之煒煒大系。”(李照國 2009:3)《黃帝內經》分《素問》和《靈樞》兩部分,早在漢唐之際就流傳于國外,并產生極大影響。20世紀初部分章節被譯成英文,到80年代后,各式完整的譯本開始出現在西方醫學界。但由于《黃帝內經》涉獵廣泛,包含文史百家,文體和修辭晦澀難懂,加之語言隔閡,所以對其翻譯很困難,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黃帝內經》乃至中醫的傳播發展。本文選取倪毛信(Ni 1995)和羅希文(Luo 2009)的《黃帝內經》英譯本為對象,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從認知語言學的識解理論視角解讀《黃帝內經》的醫學術語翻譯,并藉此討論醫學術語的翻譯原則和方法。
2 《黃帝內經》的英譯意義
中醫和西醫是人類醫學發展史上最為璀璨的兩顆明珠。無論中醫還是西醫,其目的是治病救人或延年益壽,但是二者在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中西醫之爭愈發激烈。其中,占主流地位的西醫對中醫的誤解很深,中醫是偽科學的報道屢見不鮮。在這樣的背景下,中醫典籍的英譯作為中西方醫學交流的橋梁,作用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黃帝內經》是中國古典醫學的四大經典著作之一,堪稱中醫理論的開山之作。“《黃帝內經》是我國的醫學之祖、醫典之宗, 其思想發乎于遠古, 體系形成于先秦, 編撰成書于兩漢, 其語言之精美、理論之精深、思想之精湛、論述之精練, 堪與三墳五典相媲美。”(李照國 2009:3)從學術理論基礎來看,《黃帝內經》全面總結從三皇五帝到秦漢兩朝以來的醫學經驗,將中醫從實踐領域發展到理論高度,它創立的“整體觀”、“經絡學”、“病理學”等中醫基礎觀點對中醫的發展起到決定作用,是中醫發展的理論基礎。從診治原則來看,“《黃帝內經》里所講述的是養生保健治療的原則”(孫海燕 2014:13)。這同時也奠定中醫理論是以“原則”為基礎,這一點和西醫以“現實”為基礎的理論有很大差異。“中醫是醫學和文化的結合體,她既是一種醫學,又是一種文化,她的產生與發展融入在歷史、社會、文化之中,并深深地扎根在我們中華民族的各個領域。悠悠千年,如此濃厚的底蘊是短短幾百年歷史的西醫所無法相比的。”(孫海燕 2014:14)
因為中醫和西醫各自成長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不同,在思想、文化和原則上就有著根本的區別,所以在治療方法、藥物使用以及對疾病的認識方面都不盡相同。西醫依靠現代科學技術占據現代醫學的制高點,長期擁有醫學界的話語權,他們對于中醫理論和方法缺乏必要的了解,對中醫長期存在誤解和偏見。因此,中醫典籍的譯者有責任和義務承擔起中西醫溝通橋梁的任務。準確翻譯中醫典籍不但能促進中醫的傳播發展,而且能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醫、感受中醫、相信中醫,有利于中醫造福全人類。《黃帝內經》作為中醫的“醫之始祖”必然要作為醫書典籍英譯的排頭兵。
《黃帝內經》中醫學術語都與人體以及人對世界的身心體驗有關,這與認知語言學所提倡的人與世界的“互動體驗”有緊密的聯系。這些醫學術語經過不同譯者的翻譯體現出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這說明,盡管不同譯者對世界的基本體驗相同,但是在翻譯語言的認知加工過程中存在差異。形成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識解方式的不同。在進行譯文文本分析之前,筆者將對識解的理論范疇及其構成因素加以分析和描述。
眾多版本的《黃帝內經》英譯本中中醫基本術語的翻譯各有不同,而認知識解理論可以詮釋造成這些不同的原因。
3 識解的理論范疇及其構成因素
“識解”(construal)既用來指稱人們對外界事件感知體驗過程中所形成的抽象表征,也用于描述人們為達到表達及其構成因素的目的從而選擇不同的方法觀察語境并解釋內容的一種認知能力。它是說話人心理形成和建構一個表達式語義內容的方式(文旭 2007:36)。蘭蓋克則認為“識解”是說話人(或聽話人)與其所概念化和描繪的情景之間的關系(Langacker 1987:487-488)。一個特殊的情景可用不同的方式“識解”,并且編碼情景的方式構成不同的概念化(文旭 2007:36)。“識解”的概念最早由語言學家Moore與Carling提出,心理學領域也對其進行相關概念的平行研究。后來,隨著認知語言學的發展,認知語言學家對“識解”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并加以應用。
從內涵來看,“識解”在蘭蓋克的定義里主要是用來表達認知語法中認知視角的內涵,也就是指說話者或語法主語作為觀察者或參加者的作用,這種作用通常在被表達的事件或者情境中顯現出來(Langacker 1998:4)。還有研究者從“優勢理論”的視角研究“識解”,從而更好地突顯與選擇性心理現實相關的內容(Winters 2009:5)。基于此,研究者進一步描述“優勢性識解”的內涵,突出“識解”過程中選擇性視角的具體應用 (Anishchanka 2009:1-14)。不論從語言還是從心理角度來定義,“識解”都是描述語言生產和感知如何建基于人的認知、人的認知又是如何在“識解”過程中起作用的這一過程。
從范疇發展看,“識解”的研究經歷結構主義語言學階段、認知“識解”階段、動態“識解”階段。其中,“識解”的核心定義從普遍的認知基礎與能力發展到認知能力可用于主體體驗范疇,進一步發展到不同的識解行為代表對不同體驗的基本認知能力。基于此,認知識解理論可以深入描述知覺過程與認知參與的約束,對于解釋具有內在連貫性的語言認知與語用行為,例如翻譯研究,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從構成因素來看,文化語言學家帕爾默(Palmer 1996)將“識解”的構成因素分為圖形-背景、詳略度、視角和轄域。蘭蓋克將“識解”的構成因素分為詳略度、轄域、背景、視角和突顯。詳略度(specificity)是指對實體描述的詳細程度和精細級別(吳小芳 2011:58)。也就是說,詳略度就是作者對一個具體事物描寫的細致程度,描寫越詳細,詳略度越高,識解的空間越小,反之亦然。“轄域(scope)是指被激活的概念內容配置,至少包括基體(base)和側顯(profile)”(王寅 2006:25)。轄域和認知域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都是表達者在發出一個表達式的時候,接受者在已有的認知領域中激發的與之相匹配的區域。背景(background)就是“理解一個表達式的意義和結構需要另外一個或數個表達式的意義或者結構來作為基礎”(王寅 2006:28)。尤其是漢語,表達一層意義的同時需要很多概念作為背景出現,來限制語意的表達范圍。視角(perspective)指“人們對事體描述的角度,涉及到觀察者與事體之間的相對關系”(王寅 2006:28)。視角又分視點(vantage point)、客觀或主觀描述(objective or subjective construal)、心智掃描方向(direction of mental scanning)。人們對事物的觀察角度不同會直接影響到對事物的理解和語言的表達。不同的認知參考點所產生的認知途徑就不同,認知結果也就相應的不同,意義和概念也受此影響。“突顯(salience)的認知基礎是我們有確定注意力方向和焦點的認知能力”(吳小芳 2001:58)。突顯的目的在于在構建場景的巨大信息量里表現出相對重要的內容,因為完全敘述場景內容不切實際,只能通過突顯表現主要意義。
Croft和Cruse則將“識解”的構成因素分析分為突顯、比較、視角和整合。這些構成因素的劃分雖然在具體細節上有所不同,但在核心構成因素上都突出描述事物的認知參照點、注意力方向和焦點的確定等內容。在這3種分類中,帕爾默的因素分析更傾向于文化語言學的視角;Croft和Cruse更為突出動態“識解”,特別具有概念整合的意義(Croft, Cruse 2004);蘭蓋克的認知“識解”構成因素分析最為全面地描述整個認知識解過程。基于此,本文分析文本時基于蘭蓋克的認知“識解”5個構成因素加以描述。考慮到蘭蓋克所提出的轄域和背景兩個因素在內容上比較接近,筆者將其合并成一個因素,即本文將從4個方面分析“識解”過程: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詳略度。
在認知域所構成的意義網絡系統、概念結構和經驗空間中,“識解”是理解言語意義的理性行為,可以解釋言語實踐過程中語言內部的差異。如果我們回到翻譯本身來看識解理論就更有解釋力。因為翻譯是將一種意義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轉換的過程,所以翻譯會產生不同版本是因為意義轉換過程受到主觀“識解”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譯者注意力和視角等不同“識解”因素體現在翻譯語言上形成不同的譯文版本。
本文基于《黃帝內經》術語翻譯的不同版本,解析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性“識解”對于翻譯語言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針對不同“識解”因素形成的不同版本提出翻譯認知“識解”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的核心只有一個:確切傳達原文本的本義。在此基礎上,譯者的翻譯認知“識解”不論其具體方式有何差異,都有參照標準,以最大程度上接近原文世界和原作者意圖為基點(或稱認知參照點),最大程度上實現與原文的最佳關聯,方能準確、達意。
4 《黃帝內經》醫學術語英譯分析
《黃帝內經》的中醫術語在語義內涵、文化意象、認知背景等方面特點突出,這些特點給翻譯造成一定難度,也形成不同的譯文。在本節,筆者將從認知“識解”理論下的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以及詳略度4個基本要素對《黃帝內經》關鍵術語的英文譯文進行分析和論述。
4.1 轄域和背景:最大限度接近原文
轄域和背景從廣義上可以理解為翻譯活動的語境范圍,從狹義上可以理解為譯者翻譯過程中激活認知“識解”活動的概念域范疇。落實到中醫術語范疇,就是指在理解原文的術語表達范疇的時候,同時需要一個或者多個范疇被激活,以此提供與這個術語范疇相關的背景或者是經驗來幫助譯文讀者理解原文術語的概念和意義。轄域和背景的不同在《黃帝內經》的英譯本中有很多體現。
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心”作為一個重要的術語應用非常廣泛。中醫里五臟六腑的概念和西方臟器的概念其實有很大差別。對于“心”的理解和翻譯在中西醫里就必然要涉及不同的概念域。“中醫里的這些名詞(心、肝、脾、肺、腎)不僅是一個解剖概念、而更多的是一個功能概念。”(許麗芹 王娟 2008:118) 中醫里“心”的概念在表示心臟的同時也可以有“神志、心智”的功能。而西醫里“心”等同于心臟,是人體的一個臟器。既然轄域不同,那么在理解和翻譯時就要根據要激發的不同概念域來確定用詞。
例如,在《上古天真論篇第一》中“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羅希文將“心安”譯為easy mind,而倪毛信譯為untainted conscience. 二人給出的翻譯激發的概念轄域都在精神領域,而不是臟器心臟的概念。也就是說二人對于“心”這個詞的理解都是中醫意義上的“神志、心智”。根據原文,我們可以體驗到作者在這里描述的是一種精神狀態而不是心臟的平穩。再如,《金匱真言論篇第四》中“南風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脅”這句話中“心”的翻譯。羅和倪的翻譯都是“heart”.這句話中“心”所激發的概念域和前一例中的就不同,這里的“心”所指的就是人體器官“心臟”。“病在心”并非不可理解為“精神萎靡不振”,但是根據原文作者前后所提供的背景和經驗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確定此例中“心”的意思是“心臟”。
通觀全篇,在《黃帝內經·素問》英譯本中,對于“心”的翻譯整體上來說是成功的,二位譯者都有深厚的漢語功底,在理解表達式激發的概念轄域上非常精確,所以在翻譯中語言的處理也十分到位。翻譯的轄域和背景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譯者的認知努力和認知加工趨向準確,譯文既忠實原文又能精確表達原文本義,這是成功的翻譯識解行為。
4.2 視角:努力實現原文和譯文最佳關聯
確定概念表達式的描述范圍和背景后,就要思考從哪個方面去觀察這個概念表達式,也就是視角的選擇問題。視角的選擇實際上就是認知參照點的選擇,人們選擇一個特定的認知參照點,以這個參照點為參照去認知其他事物。這樣,人們的認知途徑就會不同,所產生的語言表達形式必然也不同,對同一個事物的認知結果也就不同。視角在翻譯文本上的體現就是觀察者和事物之間的關系,再具體一點來說,翻譯文本中主語的人稱選擇能夠體現視角傾向。
《黃帝內經》的視角選擇很特別,絕大部分篇幅都是黃帝與岐伯之間的對話,通過黃帝問問題、岐伯解答問題的方式記錄和表達所要傳遞的醫學信息。這樣,幾乎所有的英文譯本都采用一問一答的第三人稱形式進行敘述,文章中整體視角被牢牢地固定住。譯文既忠實于原文,又能展現文本信息的客觀性,與醫學專著的性質相符。
視角的分歧出現在岐伯的回答之中。因為是在這種一問一答的模式下闡述醫學思想,其中回答的部分一定要闡述詳盡,而漢語省略主語的特點使原文巧妙地避開選擇視角的問題。但是翻譯中就會涉及到闡述過程中視角的再選擇問題,也就是說岐伯用什么樣的視角來敘述。多數的譯本也在盡力回避這個問題,大多內容用“it”作形式主語,或者直接用不定式作主語,亦或動名詞作主語。這樣的翻譯看似忠實于原文,但是實際上并沒有準確再現原文,在譯文中大量的不明主語容易造成視角的混亂,從而產生歧義和誤解。
在必須翻譯出主語的句子中,主語的再選擇主要分為兩種作法,羅譯本選擇第三人稱“doctor”作主語,視角也設為第三人稱。例如《脈要精微論篇第十七》中“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翻譯為“In diagnosing the pulse that represents the pathological condition, doctor should feel the pulse in the morning before the patient has taken his breakfast when the Yang Vital Essence is not moving and the Yang Vital Energy is not evanescent.”而倪譯本選擇“we”作主語,視角在第一人稱上。《脈要精微論篇第十七》中“長則氣治,短則氣病”譯為“If we see a long pulse, it indicates that the qi is flowing smoothly. If we see a short pulse,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pathology at the qi level.”我們可以看出,選擇“we”作主語將岐伯涵蓋在內,將岐伯也作為動作的參與者而不單單是觀察者,這樣的翻譯進一步拉進與讀者的距離,表現出一種岐伯體驗的感覺。而選擇“doctor”則更加客觀,與原著醫書的特點相符。總的來說,兩種視角各有千秋。由于岐伯是有名望的醫生,且是皇帝的太醫,皇帝非常信任他,所以翻譯中采用“we”的視角可以把原文所描述的主觀觀察和客觀觀察融合在一起,更加接近原文的認知參照點,同時實現原文和譯文的最佳關聯。這個最佳關聯是譯者對原文內容認知識解的結果,從原文的明示或者暗示中進行推理,再根據上下文語境加以驗證,最終確定與原文最為有效的關聯。
4.3 突顯:最大程度接近原文認知參照點
確定描述事物的轄域和視角之后,就要考慮從事物的哪個方面著重描寫突出事物的特點。突顯的形成原因在于轄域和視角形成后,確定下來的場景和認知參照點不同導致的描寫著力點不同,所謂的著力點也就是所突顯的部分。
例如,《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中“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倪毛信譯為“The law of yin and yang is the natural order of the universe,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ings, mother of all changes, the root of life and death.” 羅希文譯為“Yin and Yang are the Tao between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the dominating force of all creatures, the origin of all changes, the root of germination and killing, the housing of spirit and consciousness.”相比較倪譯本將“萬物”譯為“all things”,將“父母”譯作“mother”,最后的“神明之府也”直接省略未譯,譯文顯示出對原文的尊重,平實而準確。而羅希文將此3項分別譯為“all creatures”,“the origin”以及“the housing of the spirit and conscious”. 羅譯本突顯出《黃帝內經》醫書的特點,同時又不失文學性,“all creatures”對應“萬物”,突出中醫理論中的生命力和動態性。而“the origin”譯出原文中要表達的本源的意義,而又更具客觀性。而“housing”一詞又正好將“府”字的隱喻性恰到好處地體現在譯文中。由此可見,不同的譯者有不同的突顯,體現在翻譯的語言上也就產生差異。
總體來看,前者的譯文“識解”突顯主體所在的當下場景,后者的譯文“識解”突顯已儲存在大腦中的文化知識部分。從上下文語境來看,后者的譯文更接近原文的認知參照點。羅譯文體現出更強的比較事體之間異同和進行類推的能力,更突顯以一個事物作為參照點來認知另一個事物的能力,原文和譯文之間相應事體之間的關系描述更為充分,在表達原文本義方面也就更詳細、更確切。
4.4 詳略度:體現認知努力和認知增量
詳略度通常和突顯的關系很密切,為突顯事物的某些方面,在認識事物的時候可以就事物的一些部分進行仔細描寫,而對于其他部分則可以一筆帶過,甚至是直接省略。翻譯中的詳略度選擇是譯者對原文側重點的“識解”結果。詳略度的選擇不僅僅存在于詞語層面,而且在語篇層面也同樣存在。
從整體語篇翻譯來看,羅譯《黃帝內經》對中醫理論和中醫術語的介紹很詳細,而且在譯文中夾雜著很多批注,用批注的形式解釋譯文中晦澀難懂的部分。實際上,這也是一種詳略度的選擇,譯者通過增加譯文內容的方式詳盡描述中醫理論的運行方式,這也是一種認知“識解”過程中認知增量的具體體現。
從詞語層面上來看,《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中有一句:“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對于這句話,羅譯為“to run counter to this, Kidney Vital Energy will be damaged, bringing with it diseases in cold nature in summer, as the germination and growth of spring has been damaged.”而倪譯為“Furthermore, violating the natural order of spring will cause cold disease, illness inflicted by atmospheric cold, during summer.”不難看出,羅譯更加詳細,其中“肝”譯為“Kidney Vital Energy”,一方面是對原文的修補,另一方面解釋出傷的是腎氣,而非“腎”本身,細致而準確。而倪譯簡單直接,省略“奉長者少”的翻譯,而對“肝”也采用省略的處理方法,整體翻譯簡單點明因果而止。
翻譯過程中譯者詳略的選擇可能與譯者自身儲備的文化知識背景有關,也可能與譯者所選擇的認知努力程度有關。翻譯中醫術語這樣文化內涵豐富的概念,譯者依據自身豐富的文化知識背景和積極克服語境約束做出認知努力,在詳略度方面體現認知增量,是準確表達原文術語本義的一個很好途徑。
5 結束語
基于體驗哲學的認知語言學是當今語言學界的主流,而識解理論是認知語言學重要的組成部分。翻譯作為一種語言的認知活動能體現譯者不同的認知識解方式,所以認知識解理論可以描述和解釋譯者的主觀性差異,也可以解釋不同譯文產生的原因。本文在認知識解的理論視角下,運用轄域和背景、視角、突顯和詳略度等識解因素,討論《黃帝內經》醫學術語在翻譯過程中受到主觀性影響的具體體現。
通過對《黃帝內經》術語英譯4個識解因素的譯文分析我們發現:在翻譯過程中,準確傳達原文本義是第一要旨。盡管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有不同的識解方式,相同的識解因素之下也有細微差異,但翻譯認知識解過程中有些原則還是應該加以考慮:最佳關聯原則、解釋相似性原則和認知增量原則,這些都有助于最大程度準確翻譯原文本義。
李照國. 《黃帝內經》英譯得失談[J]. 中國科技翻譯, 2009(4).
孫海燕. 陳意教授中西醫六異解析[J]. 浙江中西醫大學學報, 2014(38).
王 寅. 認知語法概論[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6.
王 寅. 認知語言學的“體驗性概念化”對翻譯中主客觀性的解釋力——一項基于古詩《楓橋夜泊》40 篇英語譯文的研究[J].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8(3).
文 旭. 語義、認知與識解[J]. 外語學刊, 2007(6).
吳小芳. 識解理論綜述:回顧與展望[J]. 長春理工大學學報, 2011(8).
謝 華. 黃帝內經[M]. 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 2000.
許麗芹 王 娟. 中醫術語英譯研究再論[J]. 翻譯研究, 2008(6).
Anishchanka, A. Vantage Construal in the Attributive Use of Basic Color Terms: the AcN and N of Nc Constructions[J].LanguageSciences, 2010(32).
Croft, W., Cruse, A. D.Cognitive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Langacker, R. W. Conceptualization, Symbolization, and Grammar[A]. In: Michael, T.(Ed.),TheNewPsychologyofLanguage:CognitiveandFunctionalApproachestoLanguageStructure[C].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Langacker, R.W.Foun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Theoretical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Langacker, R.W.FoundationsofCognitiveGrammar:DescriptiveApplica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Luo, X.-W.IntroductroyStudyofHuangdiNeijing[M]. 北京: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2009.
Ni, M.-S.TheYellowEmperor’sClassicofMedicine:ANewTranslationoftheNeijingSuwenwithCommentary[M]. Boston: Shambhala, 1995.
Palmer, G.B.TowardaTheoryofCulturalLinguistic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Winters, M. E. On Construals and Vantages[J].LanguageSciences, 2009(13).
TranslationofMedicalTermsofHuangdiNeijingundertheConstrualTheory
Sun Feng-l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Chinese medical terms manifest themselves in semantic connotations, cultural images and cognitive backgrounds, which, though difficult to translate, produces different translations. The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he translators can help to explain the reasons why the same source text produces different transl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difference of Chinese medical terms inHuangdiNeijingunder construal theory from the four aspects: scope and background, perspective, salience and specificity along with the reasons of these four aspec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translat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source text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the scope and background of the translator should be close to the source text; the salience should be close to the reference points of the source text; cognitive effort and cognitive increment should be reflected on the specificity.
construal theory; medical terms; translation;HuangdiNeijing
H059
A
1000-0100(2016)03-0107-5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21
定稿日期:2016-02-09
【責任編輯陳慶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