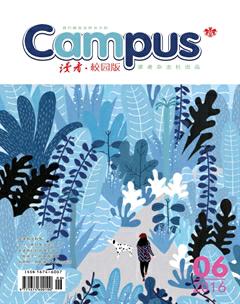媽媽的愛有時真的很恐怖
2016-03-07 19:01:15譯鄧笛
讀者·校園版 2016年6期
關鍵詞:動作
譯鄧笛

我10多歲的時候,媽媽經常向我發脾氣。
我動作慢了,她大發脾氣,說我磨磨蹭蹭、拖拖拉拉。
我動作快了,她大發脾氣,說我毛毛躁躁、瘋瘋癲癲。
我搞一點惡作劇,她大發脾氣,說我搞歪門邪道、沒有正形。
我不茍言笑,她大發脾氣,說我呆板木訥、沒有禮貌。
我跟她頂嘴,她大發脾氣,說我不懂規矩、忘恩負義。
我對她言聽計從,她大發脾氣,說我唯唯諾諾、沒有主見。
有一天,她說她是愛我的,但我把這種愛冠名為“恐怖”。
后來,我也有了一個女兒,在她10多歲的時候,我也經常向她發脾氣。
她動作慢了,我大發脾氣,說她磨磨蹭蹭、拖拖拉拉。
她動作快了,我大發脾氣,說她毛毛躁躁、瘋瘋癲癲。
她搞一點惡作劇,我大發脾氣,說她搞歪門邪道、沒有正形。
她不茍言笑,我大發脾氣,說她呆板木訥、沒有禮貌。
她跟我頂嘴,我大發脾氣,說她不懂規矩、忘恩負義。
她對我言聽計從,我大發脾氣,說她唯唯諾諾、沒有主見。
有一天,她說我真的很恐怖,但我把這種恐怖冠名為“愛”。
現在回首,我只能說,媽媽的愛無論以何種面貌出現,仍舊是愛,雖然有些面貌——真的很恐怖。
猜你喜歡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22年16期)2022-05-07 11:28:30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21年8期)2021-07-07 11:00:47
動漫界·幼教365(大班)(2021年4期)2021-05-23 21:33:16
小學生作文(低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7 00:58:35
少年博覽·小學低年級(2017年4期)2017-06-09 16:22:28
作文周刊·小學一年級版(2016年28期)2017-06-03 00:28:49
作文評點報·低幼版(2017年7期)2017-03-11 20:49:41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0:56:37
電影故事(2015年30期)2015-02-27 09:03:12
七彩語文·低年級(2014年10期)2015-01-14 14:4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