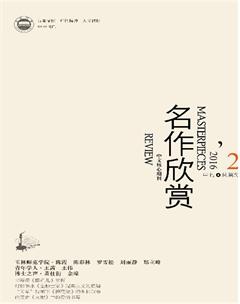須一瓜的救贖之道
朱思超
摘 要:須一瓜的《火車火車娶老婆沒有》呈現了整個社會在價值虛無的主導下,面臨生存困境的個體,如何進行自我拯救以及拯救他人的圖景。一邊是“戀物癖”式的自我慰藉,一邊是通過苦中取樂和犧牲自己給他人以生的機會的救贖。前一種體現了現代人在精神或物質面臨困境時的自我麻痹,后一種為須一瓜救贖主題的一個基本模式,但也有其缺陷。
關鍵詞:價值虛無 人性異化 戀物癖 救贖
須一瓜的小說《火車火車娶老婆沒有》,發表于《人民文學》2009年第11期。小說講述的是身為刑警的“我”在目睹了師傅們開槍互射的慘烈場面后,調到交警隊,開始了與非法載客的摩托的哥童年貴的斗智斗勇,交警隊的生活并沒有讓“我”的內心煎熬絲毫減少,人性扭曲的一面同樣在這里上演。人性普遍扭曲的世界中,童年貴一家卻展現出快樂、溫暖的一面。在一次專項整治行動中,“我”在橋上遭遇了童年貴,走投無路的童年貴,開著破車向“我”沖來,這無疑是自尋死路。此時“我”的腦海中浮現出風鈴的“噔叮咚”和問候火車的聲音,于是決定將生的機會留給童年貴,最終自己選擇墜下高架橋。
一
尼采曾說:“我談論的是兩個世紀以后的歷史。我描繪的是將要到來、而且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到來的現象:虛無主義的降臨。”{1}尼采的這段話寫于1888年春,不到兩個世紀,尼采的預言就實現了。當代中國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席卷之下,舊有的倫理道德價值似乎瞬間被一掃而空,缺少固有道德倫理束縛的人們如打開了潘多拉之盒,紛紛將目光轉向對名利的追求,并逐步喪失了其理性。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不無擔憂地指出:“理性主義過程的終結就是虛無主義。是人的自我意識在意圖毀壞過去、控制未來。在其極致,就是現代性。盡管虛無主義是建立在形而上的基礎上,但它彌漫了整個社會,而其終結必然是毀掉自身。”{2}丹尼爾·貝爾的話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須一瓜所構建的這個故事正是發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她看到了我們社會的癥結所在。“須一瓜的每一個作品都是在講述人性荒蕪的故事”,而導致人性荒蕪的原因是“舍生取義、存理滅欲等一個完整而封閉的價值體系”遭受到了“偏重于個人的‘利‘情”價值觀的挑戰。{3}雖然在小說中須一瓜只是圍繞“法律”展開其關于人性的敘事,但是“法律”作為一種價值取向無疑有其代表性,它的一個小小的橫截面展示的是更多價值倫理的崩潰。
首先,須一瓜將執法者的公正性、權威性置于被質疑的位置。小說中的“我”以及專項整治中隊的吳稚和陳軍,在花市門口堵截童年貴的時候,感受到的是來自群眾的敵意。童年貴拉的女乘客在被攔截之后,就破口大罵他們為“土匪”“敗壞政府形象的人”。“圍觀者都公開站在那女人一邊,有人大罵公共交通不延伸服務,又不許摩托載客,就是不管百姓死活”,這里群眾與執法者處于一種緊張、沖突的狀態,以至于“我”不由地發出無奈的感嘆:“現在就是這樣,人群中,只要有沖突,警察肯定就是眾矢之的,什么三教九流,都萬眾一心瞬間結成統一戰線。”
其次,“法”只是執法者與群眾為己所用的工具。小說中的群眾和執法者都在拿法律說事,群眾試圖以法律作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武器,而執法者則以此作為自己執法的依據,但二者都并不真正嚴格遵守法律。童年貴黑車上的女乘客很善于用法律保護自己:“哪條法律規定我不能坐黑哥的車?噢,我不能坐我老鄉的車?你們拿出法律來!”而執法者吳稚、陳軍等也并非把法律當回事,他們不過將法律當作維護自己個人尊嚴的工具,不容他人挑戰其權威。吳稚在踢一個老拉客時說:“混賬!你守不守法跟我無關,但是,既然我在管這條法律,你就要守!你就要給我面子!”“我”對童年貴的排斥感正是來自于這種感覺,他的“笑”被視為“在法律面前,是非常輕浮的笑”。須一瓜帶著一種很復雜的情緒描繪警民沖突,“法律”這面多棱鏡折射出的遠遠不止我們所看到的這一面,而是更為復雜的社會現實,親情、友情、愛情所包含的價值倫理在這現實面前呈現出又一番病態。
二
舊的價值體系崩潰后,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人們普遍感到壓抑、困惑,尋找不到更好的自我拯救的方式,在這個大潮的沖擊下,他們心甘情愿地隨波逐流。既然活著就要尋找活下去的理由,他們的方案是尋找可以寄托個人精神苦悶的物件,以使這種異化的心理暫時得以緩解。殊不知這種慰藉方式卻如癌細胞一樣在人體蔓延,再也無法擺脫。所以,小說中的人物普遍表現出一種“戀物癖”式的自我慰藉,它的宣告失敗是必然的。
小康長期處理交通事故現場,以至于心理發生了變態,他進行自我調適的藥方是搜集血腥的交通事故現場照片以及循環播放電腦里的一首曲子。師母既無正經工作,也不管女兒,貪玩嗜賭。前女友彭蕾唯利是圖,她所選擇寄托的物無疑就是金錢。刑警師傅生活、工作皆不如意,只得向自己所養的鷯哥傾訴苦悶,以至于鷯哥學會了說臟話,他是把鷯哥當成了自己的寄托。然而這些“戀物癖”式的自我慰藉注定是失敗的,也許它能暫時緩解現代都市人的孤寂與迷茫,但不能幫助身陷囹圄的人們從根本上擺脫精神貧瘠的魔咒。
小說中童年貴一家所呈現的自我慰藉方式其實也是“戀物癖”式的,然而他們卻呈現了一種不一樣的精神狀態,與前者的陰迷、死寂不同,他們在物質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樂觀、積極,憧憬著生活的美好。童年貴一家住在火車鐵軌旁,每次火車開過,他們都會問一句:“火車火車娶老婆了沒有?”火車就會應聲而起,“嗚,嗚——”而這時“樓下,立刻爆起好幾個人跺腳大笑聲”。在接受《燕趙都市報》記者的采訪,被問及小說“有些悲觀主義,通篇壓抑與陰霾,您在現實中是否也是有悲觀傾向”時,須一瓜回答說:“小說里面有火車的問候啊,它在我身上安裝了和飛蛾一樣的趨光裝置。”{4}
異化的社會帶來人的異化,人的異化又促使人們進行自我解救。小說家往往會將個人情感投射到自己的小說中,在小說人物進行自我突圍的同時,作者投射其中的情感也在幫著小說人物出謀劃策。所以,這篇小說的救贖就涉及小說人物的救贖之道和作者的救贖之道,或者說小說人物的救贖之道就是作者的救贖之道。
三
須一瓜診斷出病情,又觸摸到病情蔓延所帶來的炎癥,最后不得不開出處方。“救贖”主題成了須一瓜小說的一個基本元素,我們不知道須一瓜為何如此迷戀“救贖”這個話題,但是不難發現她并不滿足于一個人物只有陰面或者只有陽面,而往往呈現出小說人物人性的復雜面。而所謂的“救贖”,往往呈現的就是陰暗人物的“光輝面”。須一瓜小說的救贖主題有一個基本的模式:個體身負罪感,艱難活在世上,生死關頭主動放棄生命,使他人得救以求心靈的安穩。雷蒙·威廉斯指出,最簡單的犧牲形式就是“一個人被奪去生命,從而使整個群體能夠生存或生活得更加充實”{5}。
小說中的“我”被調到交警部門,目睹了一系列丑惡現象后,看到童年貴一家的積極樂觀,在生死關頭將生的機會給了童年貴。我們可以在須一瓜的其他小說中尋得印證,《太陽黑子》中,辛小豐、揚自道、陳比覺三人因為強奸殺人案逃亡多年,卻收養了一個患有先天心臟病的棄嬰,愛護有加,在事情敗露之際,他們沒有選擇繼續逃亡,而是坦然接受到來的結果。《雨把煙打濕了》中的蔡水清,大雨天老鄉請他吃飯,路上和的士司機起了爭執,用刀捅死了司機。蔡水清出生農村,相貌丑陋,性格溫和老實,作為倒插門的女婿長期在家庭倫理關系中得不到尊重,他厭惡自己,看到和自己相貌頗為相似的司機便起了殺心,小說中說“就像殺了我自己”。其他人努力為他開脫罪名時,他卻甘愿伏法。《蛇宮》中,“那個人”婚姻破滅,窮困潦倒后走上了殺人搶劫的道路,在與曉菌和印秋的交往中,逐漸吐露自己的心聲,被毒蛇咬后,他放棄注射血清。須一瓜對這種救贖模式的情有獨鐘,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一個本來就沮喪絕望的人,把最后一點溫暖留給了無助的人”{6}。
童年貴一家的苦中取樂和“我”的棄絕構成了須一瓜小說人物自我救贖以及拯救他人的兩種值得肯定的救贖方式,然而,這個救贖能不能成功是有待商榷的。看似溫暖、感人的救贖背后隱藏著一個大的時代背景,即這篇小說所塑造的現實社會。在強大的社會現實所制造的“牢籠”面前,個體沒有更好的辦法突圍,而須一瓜的救贖之路只是一種內在面向的選擇,無法真正使圍困其中的個體獲得拯救。“我”和童年貴兩車對撞,“我”的死雖說給了童年貴生的機會,但他們一家在物質極其困窘的情況下,生活將如何繼續?這時童年貴一家所表現出的快樂不正如師母所言是“窮開心”,最多不過是讓“嗜血”的小康在血腥的現場中暫時得到寬慰。
須一瓜作為一個法制記者,以其手術刀般鋒利的眼光診斷出了我們當代社會生活的病情,并以一個女性慣有的溫暖為我們開出了處方,雖然效果不那么明顯,至少能讓我們在絕望與孤寂中看到一絲曙光,正如童獻綱所言:“當今的小說創作,能將目光略過一己的生活瑣碎與泛濫的情色征逐而對準社會真實已然不易,而能在司空見慣的現實中打量出另外一種真實并且建造起一個我們必須重新認真審視的世界就更是難能可貴。須一瓜做到了,這就是她的意義與價值。”{7}
①②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嚴蓓雯譯,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第3頁。
③⑦ 童獻綱:《直面人性的荒蕪——須一瓜小說簡論》,《小說評論》2005年第4期。
④⑤ 須一瓜:《作家都需要附體的能力》,《燕趙都市報》2013年7月28日。
⑥ [英]雷蒙·威廉斯:《現代悲劇》,丁爾蘇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