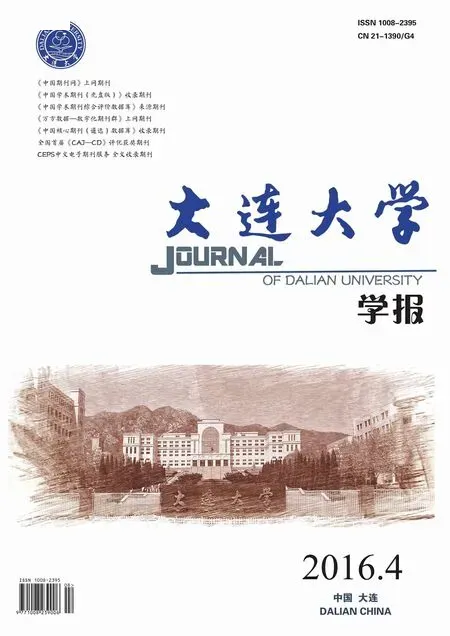“類像”時代中女性寫作的意義和價值
高小弘
(大連理工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遼寧 大連 116023)
“類像”時代中女性寫作的意義和價值
高小弘
(大連理工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遼寧大連116023)
在“類像”時代,當(dāng)代女性的處境與傳統(tǒng)女性相比有了更為復(fù)雜的變化,被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消費意識充分美化和篡改過的“理想女性”,遠(yuǎn)離了女性的真實體驗。許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坦率和沉痛揭示了女性在真實生活中所體驗到的身體壓抑,并以迂回性的策略,重新構(gòu)筑女性真實的日常生活場景,不僅充分肯定女性經(jīng)驗的特殊性,而且再三重申女性經(jīng)驗的不可取代的價值。
“類像”時代;女性寫作;身體壓抑;日常生活;女性經(jīng)驗
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是個市場經(jīng)濟(jì)占主導(dǎo)因素的商業(yè)社會,消費主義主潮將大量的后現(xiàn)代因素播撒在社會文化各領(lǐng)域中。隨著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的相互解構(gòu),整個世界在消解深度的同時日趨平面化。而靠機械復(fù)制、廣告宣傳、媒體傳播、消費幻象等支撐起來的“類像”,構(gòu)成了九十年代最富有后現(xiàn)代文化性質(zhì)并且最有影響力的時代表征。所謂“類像”是法國當(dāng)代著名思想家讓·鮑德里亞分析后現(xiàn)代社會文化現(xiàn)象時應(yīng)用的一個關(guān)鍵性術(shù)語。它是指在大眾傳播媒介急劇膨脹的消費主義社會中大量復(fù)制、極度真實而又沒有客觀本源、沒有任何所指的圖像、形象或符號。其特點是模擬再現(xiàn)物或仿本,并且在精確復(fù)制、逼真模擬的過程中,有意遺忘原本或源頭以及其所攜帶的價值與意義。
在一個“類像”時代中,視覺形象成為壓倒一切的統(tǒng)治性力量。在大量流行的數(shù)碼復(fù)制的語境中,當(dāng)代女性的處境與傳統(tǒng)女性相比有了更為復(fù)雜的變化。如果說在傳統(tǒng)的父權(quán)社會中,女性就一直被各種節(jié)婦烈女的模范形象引導(dǎo)、規(guī)訓(xùn),使之忘卻女性真實的自我形象。而在當(dāng)代轉(zhuǎn)型社會,女性每天都要面對各種被壓縮、復(fù)制的“理想”女性形象,這些被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消費意識充分美化和篡改過的“摹本”,遠(yuǎn)離女性真實體驗,以一種富有視覺沖擊力的形式被反復(fù)生產(chǎn)、流通。置身于“類像”時代的真實女性,往往會在無意識中將自我物化、對象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闡釋女性真實生命體驗、解構(gòu)了男權(quán)文化對于女性生命神秘化、虛無化的文化想象,顯露了女性主體性曲折成長的女性寫作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
女性寫作中的身體敘事對于打破女性類像的審美奇觀,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在類像時代中,影像、模型和符號有力地塑造并改寫著人類經(jīng)驗結(jié)構(gòu),同時會以一種潛在力量模糊甚至腐蝕著“摹本”與真實形象之間的差別。被消費廣告、影視劇中一再展示的女性“理想化”的身體,在充分被商業(yè)炒作、包裝之后,成為滿足男性欲望眼光的“類像”。對于這種過度美化的形體,勞拉·莫爾維在《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中有精彩論述:“在一個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為主動的/男性的和被動的/女性的。起決定作用的男性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風(fēng)格化的女性的形體上。女性在她們那傳統(tǒng)裸露的角色中被人看和展示,她們的外貌被編碼成強烈的視覺和色情感染力,從而能夠把她們說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內(nèi)涵。”[1]因此,置身于承載著男性欲望眼光和銘刻著男權(quán)意識的各種女性“類像”泛濫的汪洋中,女性的“真我”卻成為眾多女性“類像”遮蔽下一個無從追尋的原本。而商業(yè)時代語境中隱藏的男權(quán)文化秩序,迫使現(xiàn)實生活中很多女性堅信:她們所面對的各種女性“類像”就是女性“真我”,就是她們成長所遵從的現(xiàn)實范本與終極理想。與此同時,這些女性“類像”所創(chuàng)造的審美奇觀,構(gòu)建了一種足以混淆個體視聽的超級“真實”,并以強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改造著女性的生命感覺與情感體驗。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時代語境下,女性寫作顯現(xiàn)了其不可或缺的精神意義和人文價值。許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的身體敘事,以前所未有的坦率和沉痛揭示了女性在真實生活中所體驗到的身體壓抑。正是男權(quán)社會對于女性身體的貶抑、規(guī)范和利用,使女性身體的自然屬性和本體欲求被偽善的男權(quán)道德無情遮蔽,而女性對自身身體的感性認(rèn)知和感官體驗也被反身體、反感性的傳統(tǒng)身體倫理觀念徹底驅(qū)逐。從這個意義上講,女性寫作中所展示的女性身體那種由被壓抑、被遮蔽、被歪曲到自我發(fā)現(xiàn)、自我反抗、自我張揚就具有了不可忽視的意義。同時女性寫作中的身體敘事,也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力度掀開了遮蔽在身體之上的偽善的道德面紗,自覺袒露女性自身獨特的身體及心理體驗,并在此基礎(chǔ)上直陳女性個性化的情感欲望,就有利于揭露完美女性類像的虛偽性本質(zhì),同時為女性重新認(rèn)識自己身體的意義和價值打開了一扇可能性的大門。但不得不看到的是,女性寫作中身體敘事在張揚女性身體體驗時又暗含著諸多無奈:顯露的女性身體很容易被商業(yè)炒作、包裝,成為滿足男性欲望眼光的特殊消費品,而一些女性作家在身體書寫時由于過度倚重生理感受,使作品損耗了本應(yīng)具有的人文價值,而具有了更多“形而下”的意味,甚至導(dǎo)致了純粹的“身體寫作”甚至是“下半身寫作”情形的出現(xiàn)。因此,如何既能張顯女性獨特的性別身體體驗,卻又不淪于絕對的性別本質(zhì)主義,這是當(dāng)代女性寫作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
女性寫作在打破形形色色的女性神話類像方面,在當(dāng)代文化層面有著不可或缺的獨特成就。長久以來,作為類像存在的女性神話,在各種男權(quán)神話建構(gòu)時起著獨特的作用,在耀目的“婦德”的光環(huán)下,它以被動性、依附性、附屬性等女性氣質(zhì),成就了男權(quán)意識形態(tài)敘事體系中永恒不變的客體形象。在一定意義上,女性類像是男權(quán)神話秩序中的一個有待被意義填充的空洞,是幫助男權(quán)意識掩蓋、置換與抹煞女性真相的真正“幫兇”。由男權(quán)主流意識形態(tài)構(gòu)建的女性神話,表面上“神圣化”了女性,將女性托舉到了真善美的道德與審美的高度。但在歷代男性文人用美麗花草的比興隱喻構(gòu)筑女性神話時,我們卻發(fā)現(xiàn)了女性神話背后的真相:女性被男性視作審美對象與性對象的同時也被徹底客體化與物化了。在這樣的女性神話中,女性扮演著“花瓶”甚至“金絲鳥”的角色,以一種絕對缺乏行動力的靜態(tài)美,被男性的眼光,閉鎖在唯美幻象的鏡中。這些活躍在女性神話中的女性類像,從它們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無法更改被男性眼光窺視、打量、檢查的宿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與女性真實的生命現(xiàn)狀無關(guān),只是扮演著男性凝視中的“景觀”甚至“奇觀”。正如克萊爾·莊斯頓在《作為反電影的女性電影》中闡明:“女性形象始終在電影里充當(dāng)神話學(xué)意義上的符號。她在影片敘境中的符號價值(表象為其能指,類型意義為其所指),將在男權(quán)神話、或曰建立在性偏見之上的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層面上第二次被“榨干”或“抽空”(敘境中的符號/類型為其能指,神話素/意識形態(tài)意義為其所指),以填充、負(fù)荷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意義于其中。”[2]置身于充滿女性類像的女性神話的包圍中,真實女性非常容易被誘導(dǎo)將自我的成就感、價值觀建立于是否被男權(quán)社會“觀賞”與認(rèn)可中,而在這種期待被觀看與被評價中,女性已經(jīng)成為一個需要依賴他人的眼光而存在的、一個雖有主動行動能力但完全客體化的空洞的能指。在滿足男性主體欲望的同時,女性也漸漸篡改了自我生命的真實。
面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不斷制造的林林總總的女性神話,女性寫作沒有直接地對其進(jìn)行全方位的批判,而是采用了迂回性的策略,通過在寫作中構(gòu)筑女性真實的日常生活場景,還原女性真實的生活體驗,來無聲地解構(gòu)那些給女性感受自己、命名自己過程中帶來迷障的女性神話。事實上,對于女性而言,日常生活也是有一個有著重要意識形態(tài)意義的場域。長期以來,由于父權(quán)制社會基于性別氣質(zhì)和性別角色的社會分工,女性被長久地固定在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圍之內(nèi),父權(quán)制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和控制,也是通過日常生活來發(fā)生作用的,即日常生活實踐到處滲透著以男性中心觀念為核心的父系價值。因此,在現(xiàn)代文學(xué)女性寫作的經(jīng)典敘境中,女主人公走向成熟的第一步就是走出家庭的日常生活,沖向社會,在社會這一廣闊天地里與男性一樣實現(xiàn)著自我的價值,承擔(dān)與享受著作為一個個體的“人”所本該擁有的一切。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女性成長的點滴體驗都來自于日常生活,是與自己對于日常生活的玩味與反思分不開的,甚至女性的成長節(jié)奏都應(yīng)和著日常生活的律動。因此,在充分汲取五四以來傳統(tǒng)女性寫作的滋養(yǎng)以及充分借鑒西方女性寫作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女性寫作,都不再把日常生活看做制造女性神話、隔離女性真實的“鏡城”,相反都不同程度聚焦于女性在與日常生活和解中所獲得的主體性成長。這種在反抗女性神話中走向日常生活的女性寫作本身,就是一種豐腴而不單薄的成熟,是一種始終堅守著理性的女性主體意識卻又飽含感性生活汁液的內(nèi)在成熟。也許對于今后的女性寫作而言,如何在女性日常生活的敘事中,既能擺脫父權(quán)制意識形態(tài)對女性家庭角色的強力塑造,又能在豐富駁雜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種女性主體選擇的能動性,是當(dāng)下女性寫作破解女性神話的難點與重點。
三
當(dāng)代女性寫作在揭示女性生命真相,展示女性主體性生成方面,相較其他藝術(shù)形式而言,具有先天的優(yōu)勢。事實上,女性寫作的一個前提就是要擺脫男性視域中傳統(tǒng)女性的形象,然而在類像的時代這一前提的實現(xiàn)卻面臨重重困難。首先,“類像”時代中女性難以掙脫“被看”的處境。在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的中國,市場經(jīng)濟(jì)占主導(dǎo)地位,機械復(fù)制、廣告宣傳、媒體傳播夸張性地改寫著真實的女性形象。由于這些被深深烙上時代商品化印記的女性類像,其最初摹本就是男性欲望眼光投射的產(chǎn)物,其實質(zhì)因遠(yuǎn)離女性真實形貌。更為嚴(yán)重的是,商業(yè)時代語境中隱藏的男權(quán)文化秩序構(gòu)建了一種足以混淆個體視聽的超級“真實”,并以強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介入女性的生命與生活,它迫使現(xiàn)實中的女性堅信:她們所面對的各種女性“類像”就是女性“真我”,就是她們成長所遵從的現(xiàn)實范本與終極理想。因此,如何擺脫這些虛幻“類像”的纏繞,尋找真實的女性體驗就成為擺在女性寫作面前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另外,類像時代更容易將女性設(shè)定為一種可供觀賞的“奇觀”。從孩提時代起,女性就學(xué)會不時地觀察自己,她將自己一分為二,既是觀察者又是被觀察者。她必須觀察自己和自己的行為,因為她給男性甚至男權(quán)社會留下的基本印象,將會成為外界對她評判的關(guān)鍵,而這也似乎決定了她在社會中所受的待遇。因此女性很容易以外界的評判來取代了她原有的生命感覺,她把在不斷觀察自我與質(zhì)詢自我的過程中,把自我變成一個極特殊的視覺對象——景觀。尤其在類像時代,各式消費觀念所塑造的女性類像被現(xiàn)代傳媒批量生產(chǎn)、快速流通,這就使得已經(jīng)把自我當(dāng)成“奇觀”的女性,更容易接受消費性的女性類像成為映照自我的鏡子。在這種內(nèi)外夾擊之下,女性不僅喪失了內(nèi)心的判斷力,也喪失了女性的生命真實。
當(dāng)代的女性寫作并沒有回避這種困難。面對各式浸淫著男權(quán)意識形態(tài)的女性類像的包圍,女性寫作在各種女性敘事中不僅充分肯定女性經(jīng)驗的特殊性,而且再三重申女性經(jīng)驗的不可取代的價值。長久以來,在主流文學(xué)的景觀中,是以男性的經(jīng)驗為基礎(chǔ)的,情節(jié)故事與情境安排基本符合男權(quán)制結(jié)構(gòu)的社會機制與刻板的性別差異,因此,女性在文學(xué)中的位置就像她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一樣,不僅無足輕重的,甚至是隱匿無形的、邊緣歪曲的,甚至完全缺席的。在這種寫作語境中,這種包孕著女性肉身痛楚與精神創(chuàng)傷的生命體驗,成為女性寫作中女性故事的真正本源與情節(jié)的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就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在女性作家筆下,類像化的女性由于遠(yuǎn)離了真實的女性經(jīng)驗,遭到女性寫作的放逐,或者至多作為一個陪襯、反襯的類型化角色出現(xiàn)在故事場景中。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說,當(dāng)女性作家一旦把女性體驗放在自己創(chuàng)作的核心位置上,她就常常需要以“帶入式”的方式進(jìn)行“以血代墨”的書寫。也許,只有這樣才能堅持女性“他者”的視角和立場,才能不加掩飾地披露女性在家庭與社會領(lǐng)域的真實位置,也才能發(fā)現(xiàn)女性長久以來被男權(quán)社會忽略、刪改和壓制的東西,因而才能有力地揭示出女性表面多樣化生活的背后那被重重壓抑的同一機制。當(dāng)代女性寫作,繞離女性類像堆疊而成的迷幻“鏡城”,堅持讓女性以自己特有的聲帶講出屬于自己的內(nèi)心深處的生命故事。這種講述低沉有力,與社會的習(xí)見甚至習(xí)俗背道而馳,以文學(xué)象征的方式有力地挑戰(zhàn)了社會上具有性別歧視意味的所謂“正統(tǒng)見解”,啟示人們重新審視社會上習(xí)以為常的性別氣質(zhì)、性別角色,以及在這種貌似客觀“真理性”的性別習(xí)見背后所蘊含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dāng)代女性寫作對于女性生命真相的披露,讓長久以來匿名而邊緣的女性經(jīng)驗獲得了自我聲張的機會,讓女性經(jīng)驗世界中幽深而密閉的景觀第一次獲得合法性的命名。毫無疑問,這就是類像化時代中當(dāng)代女性寫作的真正價值所在。
在一個類像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新現(xiàn)實”的年代,當(dāng)代女性寫作在還原女性真實、高揚女性生命主體方面,具有深遠(yuǎn)而重要的意義。但無須回避的是,不僅由于幾千年父權(quán)制意識形態(tài)的熏染,使得女性的主體性成長困難重重,而且更由于數(shù)碼復(fù)制生產(chǎn)的女性類像不斷召喚、誘惑女性刪改自我生命體驗,當(dāng)代女性寫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與問題。然而,我們也應(yīng)當(dāng)看到,女性寫作也并非孤軍奮戰(zhàn),由于男權(quán)社會對于女性還是男性來說都是一條通向存在之深淵的奴役之路,因此兩性攜手,重建兩性和諧是二十一世紀(jì)社會轉(zhuǎn)型語境中女性群體成長的遠(yuǎn)景目標(biāo),也是實現(xiàn)以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yán)為核心的人類健康成長的必經(jīng)之路。
[1]勞拉·莫爾維.視覺快感與敘事性電影[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6:299.
[2]克萊爾·莊斯頓.作為反電影的女性電影[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562.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Female Writing in the Era of“Isomorphism”
GAO Xiao-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3,China)
In the era of”isomorphism”,contemporary women’s situation has got more complex chang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women.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consumption consciousness have fully beautified and tampered with the”ideal woman”,who is away from the real experience.Many female writers with unprecedented frankness and grief deeply reveal the physical distress of the women in their real life.They adopt the circuitous strategy to build women’s real daily life scenes,which not only fully affirm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female experience,but also reiterates its irreplaceable value.
Isomorphism;Female writing;Body depression;Daily life;Women experience
I06
A
1008-2395(2016)04-0060-04
2016-06-11
基金課題:遼寧省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L11DZW014);大連理工大學(xu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wù)費項目(項目編號:DUT14RW205)。
高小弘(1976-),女,大連理工大學(xué)人文社科學(xué)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女性文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