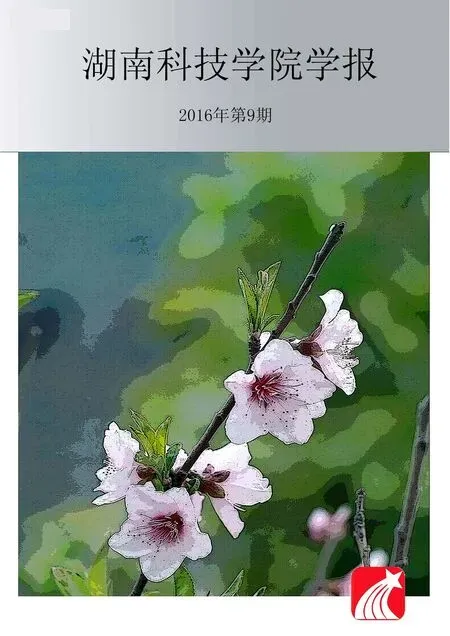我國行政法回歸“行政”的探究
黃 銳
?
我國行政法回歸“行政”的探究
黃銳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我國現行行政法主要是建立控權論基礎上,強調對行政權的控制,保障公民的權利。但現行行政法的發展已缺乏更多的后繼動力,開始落后于現實需要。我們應該讓行政法回歸“行政”,實現行政法的轉變。
行政法;控權論;行政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方面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政治方面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由于市場經濟天然地要求控制和規范政府權力,加之我國社會大眾恐懼于文革中國家權力的濫用,改革開放后行政法“趁勢而起”,以《行政訴訟法》為起點,我國相繼建立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復議、行政賠償等重要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治突飛猛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峰。[1]
目前,我國行政法基礎理論的主流觀點為“控權論”。在上述理論的主導下,我國行政法基本上是圍繞行政訴訟制度和行政程序制度進行展開的。行政法的法律目的被認為是通過對行政權行使者的控制,保障相對人的個人權利,使個人自由和權利免受行政權的侵害。在法律價值上,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相混同,幾無本質區別。在行政訴訟法頒布至今近30年的時間里,現行行政法強調行政權的有限性,要求行政權的運行正當,強調對行政機關的監督,順應了時代需求,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行政法總體上來看是一部移植于國外的法律,行政主體、行政行為、行政程序等核心概念均源于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誠然,在法治缺乏內部土壤和動力的我國,大膽吸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推動了行政法的發展。但也同樣因為行政法是移植法,從一開始一定程度上就存在了先天不足和水土不服的問題——研究者對國外的概念和具體制度的理解上或多或少的存在偏差,再加上我國過于強調對行政權的外部控制的發展路徑,我們不難發現,這種以監督行政權為核心的行政法反哺行政活動的能力越來越低,出現了發展上的困境:行政體制改革中行政法學者集體失語、行政程序法遲遲不能出臺、行政組織法的發展孱弱等等,甚至是處于行政法中心地位的行政訴訟制度也處于相當的困頓之中。薛綱凌教授認為:“(行政法)控權模式發展艱難,在規范政府行為、解決利益沖突方面表現得無力,也不能有效解決城鄉發展的失衡,地區、行業之間的差異,社會貧富不均”[2];何海波教授也指出:“行政訴訟法實施二十多年法院‘慘淡經營’,卻仍然走不出‘艱難困厄’的局面……行政訴訟解決行政糾紛、保護公民權利和監督依法行政的功能已經嚴重受挫。”[3]行政法的發展亟待轉變。
一行政法發展困境的原因
(一)現行行政法不符合世界公共行政發展趨勢
我國現行行政法理論認為西方行政存在一個“夜警國家”—“行政國家”—“有限政府”的發展階段,鑒于目前處于“有限政府”階段,從而推導出行政法要對行政權進行有效制約和控制。事實上,這是對有限政府的誤解:有限政府或者說限權政府在西方是憲法原則或者說是一項法治觀念,并非一種真實存在的行政發展階段。“行政國家”或者說“福利國家”之后,也就是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各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重新占據了理論主導地位,認為市場力量應該最大化,政府干預應該最小化,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政府掀起了新公共管理改革即是這一理論的行政實踐。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西方各國政府又開始用刺激計劃介入經濟,進行積極調查,建立管制體系,避免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可見,西方社會政府的角色時盛時衰,行政干預時強時弱,行政針對出現的社會問題的不同而隨時進行調整,并非一味的對政府權力進行限制。如果我們對西方行政的真實情況不引起足夠重視,會導致我們的行政法“一葉障目不見森林”,只關注一頭而忽視了另一頭——將有限政府作為一種憲法層面的價值理念和將其作為真實存在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二)現行行政法與我國行政機關的宗旨不匹配
根據憲法第27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因此我國行政機關的宗旨和其他國家機關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并非一句簡單的政治口號,它意味著我國的行政機關在行政領域,主要是主動的去尋找人民的需求,并采取措施滿足人民需求。由于“人民需求”這一概念在形式上多樣,內容上趨于無限,客觀上就要求行政機關更加重視經濟、民生、社會建設等方面的工作,具體來講,即行政活動的重心更多的集中在經濟增長、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文化教育、體育衛生、弱勢群體的幫扶等領域。因此,現行行政法強調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與我國憲法規定的行政機關的“主動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的”宗旨存在一定矛盾。
(三)現行行政法無法適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需求
現行行政法強調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優點在于強調對公民權力的保護,利用行政權以外的國家權力對行政權進行控制,防止其被濫用。但它的缺點也非常的明顯,基本上忽略了行政權和行政機關本身,行政權如何授予,如何調整,行政機關的組織如何建構等問題基本上不涉及,實際上游走于行政的邊緣,忽略行政體制方面的建設。現行行政法帶來的一個重要的惡果即是行政組織法律制度的構建方面無所作為,直接導致了我國目前如火如荼的政治經濟改革中,行政法難覓蹤影,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綜合執法體制改革、群團改革、工商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等鮮有行政法學者的分析評論。
二 行政的疆域及行政法的回歸
行政法是對研究“行政”的法,只有讓行政法回歸“行政”,才能真正意義上促進行政的發展。對現行行政法的評判及反思,首先繞不開的是對“行政”這一“起點”概念的探尋。
(一)行政的“疆域”
行政,是行政法上的核心范疇,是行政法的研究對象,也是行政法學研究的起點。行政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釋義為“行使國家權力的(活動);機關、企業、團體等內部的管理工作。”我國行政法教材一般認為,行政主要指國家行政機關執行國家法律、管理國家內政外交事務的職能。行政法主要研究的是公行政,主要是國家行政、形式行政。[4]
西方國家與我國行政相對應的英語詞匯為:administra-tion,主要含義有5種,分別為“管理、經營、支配”、“法律的實施”、“政府”、“行政管理職能”、“遺產管理”。[5]在《布萊克法律詞典》中,administration的含義也有四類。兩相對比,我國行政法學研究的行政主要是從行政機關的行政職能來解釋行政,而西方行政概念有多個層面,我國行政法行政的疆域要小于西方國家的定義。
(二)行政法應該回歸“行政”
那么,怎樣才能讓行政法與行政的真實疆域所匹配呢?可以從行政的要素為切入點予以解決。行政,不僅是行政法的研究對象,它同樣是政治學、憲法學、行政學、公共管理學等多個學科共同研究的對象,我們需要超越行政法本身,轉向其他學科,以博采眾長、取長補短的態度借鑒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美國公共行政學者詹姆斯·W·費斯勒在研究公共行政時,從“政府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組織與政府結構的作用”、“政府組織中的人”、“政府決策”、“民主制中的行政”五個方面進行了探討,并認為“公共組織與私人之間的最基本差別在于法治(rule of law),公共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執行法律,它們的結構、職員、預算和目的—都是法律權威的產品”[6]。從公共行政學的角度,行政的要素有職能、結構、人員、政策、監督五個。將之與我國行政法的研究相對比,現行行政法在職能、結構、人員的研究方面處于弱勢,優勢是監督領域,而政策方面幾乎不涉及。因此,現行行政法要進一步發展,必須重新回歸“行政”。
三 法實現回歸行政需要堅持的原則
(一)行政法立法思想的轉變
目前,行政法領域的法律《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國家賠償法》強調對行政行為的事后監督,《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強調對行政行為事中的規范和監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與行政訴訟法相銜接。轉變后的行政法強調行政組織行使權力的來源和行政組織本身的結構,需要我們加強對《憲法》、《立法法》、《組織法》、《授權法》、《公務員法》等法律的研究、制定和完善。
(二)行政法律關系的轉變
雖然我國行政法學將行政法律關系分為了對內行政法律關系和對外行政法律關系,主流觀點也承認內部行政關系也受到行政法的調整。但是,內部行政法律關系在我國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一直處于外部行政關系的從屬地位。當然,按照目前的行政法律關系理論,并不承認授權主體和行政組織之間屬于行政法律關系(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院的委托),但至少,我們可以開始研究并梳理行政組織與授權主體之間,以及行政組織內部之間的關系。
(三)行政主體范式的轉變
行政主體概念是一個法學概念。目前我國行政主體制度,主要是為了解決行政訴訟被告的資格問題,與德國等國的行政法學討論行政主體在探究誰可以行使行政權不同。在我國,行政主體理論直到今天也仍是純理論性的探討,沒有出現在法律規范中,也沒有相應的制度支撐。行政組織是授權主體授予職權的對象,不討論該權力的擁有者能否以自己名義獨立行使行政權力,并承擔責任的問題。只要符合行政組織的一般條件,能夠被授予職權,即為行政組織。因此,我們可以考慮將行政主體范式轉變為行政組織。
(四)監督體系的轉變
我國目前行政法強調司法權對行政行為的監督,監督時間處于行政行為的末端。而“回歸行政的行政法”是對行政過程進行全方位的監督。從從權力機關到行政機關,再從司法機關到行政機關,是全流程監督。同時,需要我們更加注重行政組織的結構合法性問題,從行政系統內部進行監督,通過與行政行為法、行政程序法等其他行政法的相互配合,促使行政機關決策符合法律、公共利益,達成行政目標。
總之,政法的發展已缺乏更多的后繼動力,開始落后于現實需要,特別是在中國社會治理結構進行調整,治理能迫切需要大幅提升的社會大背景下,行政法的發展缺乏對社會需求的積極回應,不能為快速轉型的社會提供制度支撐。因此,行政法的發展應該重新回歸“行政”,將行政法的范圍擴大至行政要素涉及的所有領域。
[1]陳新民.中國行政法學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6.
[2]薛剛凌.行政法發展模式之檢討與重構[A].中國行政法之回顧與展望——“中國行政法二十年”博鰲論壇暨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05年年會論文集[C].2005.
[3]何海波.困頓的行政訴訟[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2,(2):96.
[4]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6.
[5]元照英美法詞典[Z].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34.
[6][美]詹姆斯·W·費斯勒,唐納德·F·凱特爾.公共行政學新論——行政過程的政治[M].陳振明,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2.
(責任編校:周欣)
D922.1
A
1673-2219(2016)09-0111-03
2016-03-15
重慶市社科一般項目“重大環境行政決策風險防控的法律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14YBFX111)。
黃銳(1982-),男,四川萬源人,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憲法與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