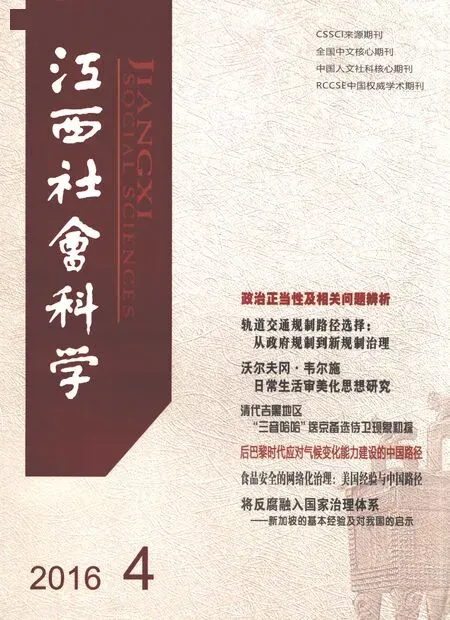后巴黎時代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的中國路徑
2016-03-06 21:48:35曾文革
江西社會科學
2016年4期
■曾文革 馮 帥
后巴黎時代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的中國路徑
■曾文革 馮 帥
《巴黎協定》的達成昭示著后巴黎時代的到來。從《巴黎協定》的內容可知,其是各方利益博弈后相互妥協的產物,帶有濃重的發達國家利益訴求色彩,因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體系下的CBDR原則也受到較大程度的弱化,導致中國在能力建設上面臨形式、角色和立法的諸多挑戰。盡管中國已加強能力建設政策和立法制定,并大力實施能源節約制度和碳排放權交易制度,但其在立法規劃、立法科學基礎和立法內容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有鑒于此,中國應在能力建設的立法理念、立法方向、立法基礎、制度完善和《巴黎協定》的落實等方面不斷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力度、完善INDC內容、加強組織機構能力建設、推進碳排放權交易立法并強化國際氣候立法的國內實施。
《巴黎協定》;后巴黎時代;應對氣候變化
曾文革,重慶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馮 帥,重慶大學法學院博士生。(重慶 400044)
能力建設(capacity-building)①是減弱氣候變化對發展中國家不利影響的重要保障,是發展中國家不斷提高履約能力的首要條件,也是發展中國家提升國際氣候談判地位的必然選擇。因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hange,以下簡稱《公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和“巴厘路線圖”(Bali Roadmap)等均對其進行了規定。②這些文件將中國納入發展中國家陣營,認為其應當接受發達國家的援助。然而,由于這些大會成果或過于原則化,或時限僅至……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發明與創新(2022年30期)2022-10-03 08:40:56
動漫星空(興趣百科)(2020年12期)2020-12-12 05:31:40
中國外匯(2019年18期)2019-11-25 01:41:56
電子制作(2018年14期)2018-08-21 01:38:28
人大建設(2018年6期)2018-08-16 07:23:10
文理導航·科普童話(2017年5期)2018-02-10 19:42:14
人大建設(2017年10期)2018-01-23 03:10:17
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 10:29:03
無人機(2017年10期)2017-07-06 03:04:36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3年1期)2013-03-01 04: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