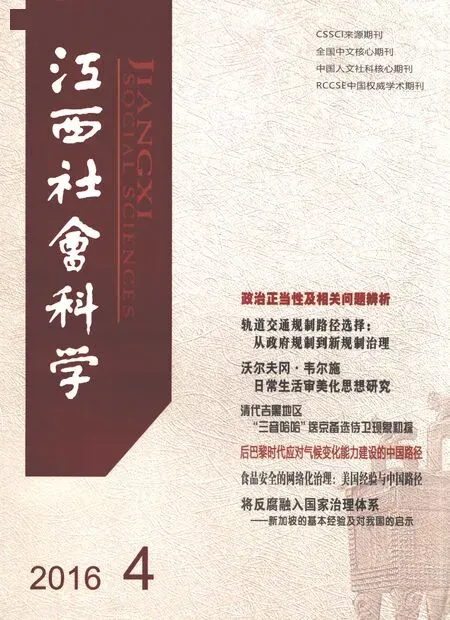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當代英國黑人文化的變遷
2016-03-06 21:48:35張建萍
江西社會科學
2016年4期
■張建萍
全球化背景下當代英國黑人文化的變遷
■張建萍
英國黑人經歷了從二戰前的被迫隱身到當代逐步現身的過程,而在這歷史長河中,當代英國黑人的總體變遷最為多元與復雜,尤其是在浩浩蕩蕩的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和英國國內政策的調整,英國黑人不再是封閉、獨立的個體,而是與英國白人的命運相互交織,互相影響。在短短的60年間,英國白人和黑人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又主要體現在“黑人性”、“英國性”和“英國黑人性”三個概念的變遷上,基于三個概念的相關關聯性,受全球化思潮普及的影響,它們均呈現出“混雜共生”的特點。隨著黑人文化被英國主流社會所承認,黑人文化研究必將成為學界一個極具研究潛力的領域。
黑人性;英國性;黑人英國性;全球化背景;變遷
張建萍,中國民航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天津 300300)
黑人在英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皮特·弗萊耶(Peter Fryer)的《持久力:英國黑人的歷史》中,他寫道“非洲黑人在大不列顛群島上有英國人前就已經來到這里”。[1](P1)他指的是公元3世紀古羅馬帝國北非士兵奉命駐扎在大不列顛島的事件。之后大批的黑人曾生活在英國,到了近代其人數更是達到高潮,一戰時曾有一萬多名加勒比黑人在英國軍隊服役。盡管如此,英國主流社會為保持其白人種族的 “純潔性”,對黑人鮮有提及。此種局面直至20世紀中期才有所改觀。二戰后英國急需大批勞動力進行國內重建,因此英政府頒布了新的《移民法》,以吸引英屬殖民地人們前往英國。……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2022年3期)2022-05-23 13:46:54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瘋狂英語·初中天地(2021年6期)2021-08-06 09:03:24
遼金歷史與考古(2021年0期)2021-07-29 01:06:54
科技傳播(2019年22期)2020-01-14 03:06:54
民用飛機設計與研究(2019年4期)2019-05-21 07:21:24
中國外匯(2019年21期)2019-05-21 03:04:06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少年漫畫(藝術創想)(2018年12期)2018-04-04 05:2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