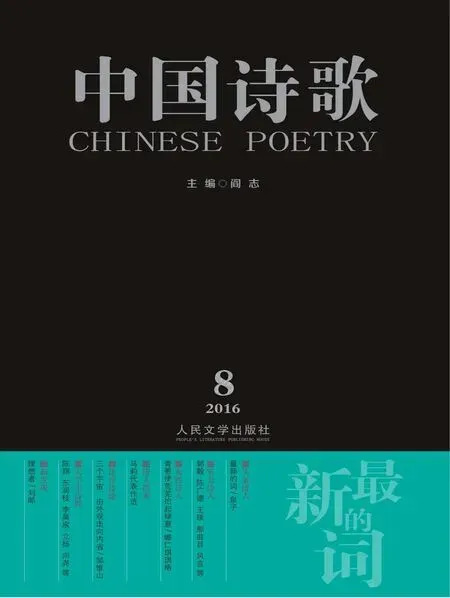在外國詩歌、民歌與中國傳統詩詞之間
——柯仲平新詩導讀
□鄒建軍 葉雨其
在外國詩歌、民歌與中國傳統詩詞之間
——柯仲平新詩導讀
□鄒建軍 葉雨其
柯仲平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詩人,他開始創作新詩的時候,還很少有人集中時間與精力來進行新詩創作,也許我們可以說他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新詩人之一,并且是后期創造社的重要成員,創作了大量的、優秀的愛情與自然詩篇,具有積極的、革命的浪漫主義精神,在藝術上也有很高的起點。他在早期創作了那么豐富的優秀詩作,是我們在閱讀相關文獻與作品之前,所沒有料到的。在我們從前的印象中,柯仲平只是一位從延安成長起來的詩人,其所有的詩歌作品是在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們都是實際革命工作的產物,現在看來不是這樣的情況。他的確是延安新詩歌的代表詩人,那個時期的許多詩作政治性過強,并且都是唱贊美詩的,因此在從前的我們看來,這樣的作品是不可讀的,也不會有任何詩藝價值和詩史地位可言。可見,我們的研究如果不從詩歌作品的實際出發,而只是看現有的文學史和文學作品選集,會發生多么大的誤會,甚至可能會埋沒一位本來相當杰出的詩人。這是我們在導讀柯仲平新詩作品的時候,首先要向讀者交代清楚的一點。
我們不想全面地回顧柯仲平一生的創作道路,而只是想指出其整個的詩歌創作歷史明顯地分成了三個階段:“五四”早期的新詩創作;到延安以后的新詩創作;建國以后的新詩創作。現在我們發現,在這三者之間具有很大的不同,表明其詩歌創作受到了他所在的政治與時代因素的重大影響,并且其詩藝水平總是在不斷地下降,以至于在后來幾乎退回到了少年時代之前。我們也不想專門去討論其詩歌作品的題材與內容,因為他從事詩歌創作的歷史比較長,作品也比較多,題材多種多樣,形式也是豐富多彩的。在他的作品中,不僅有抒情短詩,也有敘事長詩與抒情長詩,還有街頭詩與墻頭詩、口號詩與民歌體,所以要用一種理論或術語,難于對其整個詩歌創作進行概括。這就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一個詩人的詩學觀念,在其一生的詩歌創作中,仍然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早期的柯仲平接受來自于西方的浪漫主義詩學觀念,對于英國與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特別熟悉,并且在創造社這么一個文學團體內,也受到了來自于團體成員相互之間的影響。在那個時期,他的詩歌創作沒有限制,全是個性的自由表達與氣質的自然流露,所以留下了諸多美妙的自然與愛情詩篇。可是,后來到了革命根據地延安,受到當時的政治思想與時代思潮的影響,每一個人具有明確的創作任務,要求用民歌的形式進行創作,要讓工農讀得懂、看得清,于是創作出了許多革命題材、政治思想與民歌形式的作品,現在看來這樣的作品沒有自己的個性與風格,更沒有自己的思想與見識,出現了詩藝的倒退與思想的空無。因此,在這樣一篇短文中只能是概說其詩歌創作在思想與藝術上所形成的幾個特點,也順便討論一個外國詩歌、民歌和中國傳統詩詞的結合問題,以就教于大方之家與理論工作者。這樣的導讀以求讓我們的后來者,能夠對其詩歌作品有更準確的理解,以幫助大家更好地閱讀其詩歌作品,理解一位詩人在那個時代的不易,以及詩藝求索的不易。
其一,其早期詩歌的傳奇性與神秘性。如果我們只是接觸其延安時期及其以后的作品,那么就會認為柯仲平只是一位“革命詩人”,或者一位“戰爭詩人”,其實他早期詩歌完全不是這樣,而是自我色彩深濃、傳奇性與神秘性兼有,許多作品抒發的都是極其鮮明的個人主義情感與精神,并且似乎與愛情相關,甚至有的時候,也不是那么好懂與好讀,甚至他還憑借著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而被稱為“狂飆詩人”(沈用大:《中國新詩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345頁)。這就與其后期詩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到延安從事革命工作以后的作品都是很好讀的,雖然有的時候方言土語過多,只要加以少量的注解一讀就懂,詩思不深、詩意不濃,當然是很好理解的。后來我們所謂的“大眾化”、“民族化”與“通俗化”的詩歌作品,它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讓我們先看一首他在1922年創作的抒情詩《贈歌》:“我贈你以春蘭,/你贈我以秋菊;/我贈你以芳香的,/你贈我以美麗的;/芳香的,美麗的,/吾們是呵/春蘭!/秋菊!”這里主要抒寫“我”與“你”之間的交往與情感,從總體上來說兩人之間具有相當的感情,當然也存在不理解甚至是矛盾的時候,詩人為此而感到苦惱。最后,詩人只有向自然界求得理解,做一個“星月客”。詩中的“我”大概就是詩人自己,而“你”是誰?也許誰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你”當是一位女性,正是詩中“春蘭”與“秋菊”意象的由來了。這就給詩帶來了一種神秘性,不知他們之間的關系,沒有始也沒有終,然后就在“逍遙太空!/太空逍遙!”這樣的詩句中,結束了情感的抒寫。在《此千起萬伏的銀河——二十五節跑雪曲》這首抒情長詩中,詩人展示了他在古舊的北京城跑步時的全部感受,因為其末尾有這樣的說明:“1923年冬月尾一個雪霧茫茫的早晨,我在北京西城跑雪歸來寫。”我們來看其中的一節:“原來這兒還是荒原,/原來這兒還是坎坷之場。/正好趕她一群蝴蝶兒,/可我一跤跌在白茫茫的荒原上。//落得君引頸而啾啾,/君,一只勇敢的飛禽;/落得君掀絳紗而微笑,/君——我云中的行星。”詩人創造了“荒原”與“行星”的意象,一個代表地上,一個代表天上,在我們的面前呈現出了一個神秘的自然世界。隨后還出現了“醒獅”、“荒墓”、“兩個紅日”、“銀灰色的世界”等意象,似乎詩人是在天空里奔跑時所見,完全不是在地上跑步時所見,可見,這首詩里的許多意象都是想象的產物。“去罷!可笑你累累的荒墓!/可笑你一根根的白骨!/你生前或甚受人愛敬,/你死呵,一根根的白骨!//——咦!咒到死者嗎?/喂!我周圍可站著無數張牙的鬼!?/——呸!你們算什么!/敢來罷!你們張牙的鬼!”這里出現的“荒墓”、“白骨”、“張牙的鬼”等意象,不僅具有神秘性,簡直具有怪誕性與神性之色彩。在抒情長詩《走到地獄地獄下》中,寫到抒情主人公在天上行走的所見所聞,許多時候詩人就在云端立馬,于是出現了“雪花馬”、“烏駒馬”、“灰色馬”等意象,甚至還出現了“快買呀!/快買呀!/人頭賤過冬瓜價!”這樣的詩句,令人毛骨悚然。“我騎的不是桃花馬,而是雪花馬,/那馬兒生就是奔放云濤,慣走天涯;/好容易呵!一次云端立馬,/射不死幾個仇敵冤家,/我馬空立我箭不就白發嗎?/——然而我馬真空立我箭更是瞎發了,/那叫哭連天的都不是仇敵冤家,/那叫哭連天的都不是仇敵冤家。”雖然是詩人的一種想象,卻令人驚奇,讓人揪心,因為抒情主人公要殺仇敵,可是不僅沒有達到目標,反而射中了自己的馬,發生這樣的事情,只有讓自己淚如雨下。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詩人早期詩歌中的傳奇性與神秘性相當突出,也是其詩往往能夠引人入勝的地方,和他后來通俗易懂、思想淺顯、語言俗白的詩作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與外形。這樣的詩作是如何產生的?也許出于青春期的熱情,也許出于少年時代的個性,也許出于那個時代的浪漫文學思潮,也許出于那樣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要求。自我及自我的詩情與想象,在詩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具有很高的地位。而詩人后來的詩作為什么產生了那么大的變化,一變而為一個典型的“革命詩人”?主要是因為其生存環境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過程中,思想情感也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自我轉變而為人民與革命,所有的思想與語言都與從前不同了,甚至說發生了“跳崖式的斷裂”。

其二,其早期詩作具有深廣的宇宙意識,而后期的詩作完全沒有這樣的意識,其主要內容反而全是發生在地上的身邊瑣事。詩人早期的許多詩都表現青春少年的情感,往往與宇宙天空相關,天上地下聯為一體,體現了詩人豐富的想象力,與開闊大氣的情懷。在寫于1922年的《贈歌》這首優美的愛情詩中,我們先來看第三節:“我贈你以白芙蓉,/你還我以蔓荊草;/我親熱地來和你握手,/你冷眼地轉了頭!/蔓荊草,轉了頭,/吾們還能夠/再送芙蓉,/重來握手!?”語氣的變化不可謂不大,種種疑問都被詩人提出,表現了“你我”之間的情感發生逆轉及其美學意義。如果說第一節主要意象是“春蘭”與“秋菊”,第二節的主要意象是“秋衣草”和“活麻葉”,第三節中的主要意象是“白芙蓉”和“蔓荊草”,所有的這些意象都還是人間的平常之物,那么到了第四節之后的“白云”與“青天”,“星月”與“太空”,就表明詩人的關注點從地上轉移到天上去了。詩人的想象可以橫掃南北東西,也可以上天而入地,一時在地上一時在天上,天馬行空可以獨往獨來,沒有了任何的限制,這樣的想象與詩情簡直可與屈原相比了。在《此千起萬伏的銀河——二十五節跑雪曲》中,詩人在地面跑著跑著,一不小心就進入了天空。“昨晨前晨,/東天降生了兩顆赤星;/一個撥云霧而奮進,/一個赤精精閃放光明。”也許并沒有什么兩顆太陽,只是詩人的一種感覺與想象而已。也許,其
他創造社詩人們的作品也與之相仿,他們喜歡在自然世界中發現詩情,他們也喜歡與自然世界進行對話,他們表現的對象主要不是日常生活,而是更遠的地方、更遠的事情,所以其詩作中才出現了許多遠離人間的意象。在其詩劇《風火山》中,也有與此相近的傾向。本來是一部革命的史詩,卻與天地自然聯系起來,詩人的感悟力與想象力,在此得到了高度的擴展。在那個時代的詩人中,宇宙意識是本有的存在,就如宗白華、郭沫若、田漢的詩,基本上也是如此。創造社詩人主要的思想來自于西方的浪漫派,他們詩學思想的主導方面就是自然、想象與情感,“回到自然”是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如何才可以回到自然呢?當然就是靠想象和情感兩種方式,把自我的情感投入自然,以詩人的想象把握自然,而自然的最高層次與最高綜合,也就是宇宙空間了。可惜他后來更多的詩作過于關注現實與革命了,把自己當成了一個政治的動物,一個時代的產物,越來越實、越來越近,與自然卻越來越遠,想象力越來越小、情感力越來越弱,當然詩質也就越來越差,再多的作品也不如早期詩歌的創造性與感染力了。

從其詩歌作品的實際出發,值得討論的似乎還有革命的主題、民歌的意義、詩藝的進退以及民歌、外國詩歌與中國傳統詩詞的結合與統一問題。第一,革命的主題之問題。柯仲平的革命詩作“大多寫新生活、新人物、新思想,及革命斗爭之強,情緒熱烈、昂揚”(朱光燦:《中國現代詩歌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85頁)。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革命題材,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里,詩人作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表現革命情懷與革命思想是一種必然,當然是無可厚非的。然而,是不是要像有的人那樣平面地記錄革命的生活與斗爭,是不是要像有的詩人那樣只是表現革命領袖的思想與言行,而沒有自我的發現、個人的見識?是不是只要記錄了現實的生活和革命的斗爭,詩歌作品就一定具有了思想與藝術價值?這是一個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得出結論的一般問題。“玩是玩,不貪玩,/哨子一響,鑼鼓家什背包立刻一齊背起來。/歇足了勁,我們還要使勁往前趕,/趕去幫助保衛我們人民的桃花園。/喊出一聲‘同志們!/邊境上的戰士、老百姓/已經盼了我們好幾天!’/大小同志、男女老少趕起路來格外快又格外歡!”(《“打肩”》,1940年,關中)這首詩無疑描寫了革命的場景,表現了戰士們與群眾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保衛革命成果的意志與熱情,然而從詩的角度而言沒有什么獨創性的東西,過于直接與直白,讀起來沒有什么特別的味道。因此,我們認為題材本身并無價值可言,也就是說寫古代生活和當代生活,只要寫得好都具有同樣的價值。古人不可能寫當代的生活,今人當然可以寫古代的生活,有的人也許認為寫古代生活沒有價值,而寫當代生活就是新的,就會具有重大的思想與藝術價值,這樣的認識是存在問題的。寫什么都是沒有關系的,而在于如何去寫,只要寫得好就是有價值的,而只要寫得不好就不會有什么價值。柯仲平在延安時期所寫的一些東西,就像一位新聞記者所寫的一樣具有紀實性,如繪畫中的速寫,如數學中的速記,沒有任何的深度與廣度,這樣的作品雖然寫到了革命甚至革命領袖,也不會具有什么價值,因為它們與思想、藝術、詩歌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關系。這是那個時代許多詩人作品里的重要毛病,包括李季、田間、阮章竟、蕭三、陳輝等。如果說《邊區自衛軍》這樣的作品還有生活的實感,那么有的作品則完全是標語與口號,與詩思和詩藝本身沒有什么關系。所以,問題不在于表現了革命的題材,而是看你如何去進行表現。題材本身沒有任何詩學意義與詩藝價值,新的題材并不能給你的詩本身帶來什么意義。這樣說并不是反對革命題材入詩,而是就事論事而已。艾青、郭小川與賀敬之早期的作品就不一樣,雖然也是表現了革命或者說與革命相關的題材,然而他們是以詩人的方式、以詩藝的方式、以個人化的方式來表現的,其思想與藝術價值就因為詩與自我而存在了。第二,民歌與“詩人之詩”之間的關系問題。在延安時期,在那個時代的主導思想影響之下,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詩人作家要轉變自己的政治立場,甚至要求詩人作家要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以為這樣可以寫出優秀的作品。于是產生了對于民歌的重視,收集、整理與學習民歌也就成為了一種思潮甚至是運動,柯仲平是其中的重要成員之一。柯仲平十分強調采用民族化的形式來進行詩歌創作,他雖然認為應該向優秀的外國詩歌學習,但他同時也認為,這種學習應該是一種“批判的學習”(柯仲平:《柯仲平詩文集》第4卷,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頁),而學習的目的,也是為了“繼承我們幾千年來的民族詩歌的優良傳統,向前發揚,提高創造,使我們發展著的社會主義內容,能夠有最恰當完美的民族形式來表現”((柯仲平:《柯仲平詩文集》第4卷,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頁)。當時詩人所能接觸到的民歌,主要是山西、陜西、甘肅和河北一帶的民歌,并且也只是一部分而已。收集民歌與整理民歌本是一件好事,學習民歌也可以讓詩人吸收一些思想與藝術的養料,從而有利于自己的創作。然而,全民收集與整理民歌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沒有那么多民歌可以收集,民歌也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并且還是底層文化的一部分。向民歌學習,并不是要求你創作出來的東西就是民歌,如果創作出來的東西就是民歌,那你不就是一位民間詩人了嗎?“快釀你加料的白干酒與紅葡萄!/快釀你加料的白干酒與紅葡萄!/耐不住了!耐不住了!/我們兒女的戰火都在熊熊燒!/我們兒女的戰火都在熊熊燒!/耐不住了!耐不住了!/快釀你加料的白干酒與紅葡萄!/快釀你加料的白干酒與紅葡萄!”(《我要喝加料的白干酒與紅葡萄》)這是詩人寫于1925年的一首詩作,說明那個時期詩人已經有了民歌的意識,雖然是現代漢語口語,而反復的采用和頂真的技法,讓我們感覺到了民歌的魅力。然而還不是標準意義上的民歌。在那樣一個特別的歷史時期,柯仲平只是其中的一位,就他那個時期的詩歌作品而言,除了長詩《邊區自衛軍》和《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以外,許多作品本身就是民歌,與收集到的當地民歌沒有什么區別,甚至還不如從民間收集起來的民歌之土味與野味。寫于1946年10月張家口的《英雄且退張家口——街頭詩之一》:“我把城墻當鐵鏈,/我把城池當罐罐;/英雄且退張家口,/王八入甕鏈子拴。//你占城來我占鄉,/把你包圍在中央;/東風定與孔明便,/撤退里頭有錦囊。”這首所謂的“街頭詩”其實就是當時的口號或標語,看起來像打油詩或順口溜,沒有什么詩意的創造與詩的形式。把自己的創作還原為民歌本身,當然是存在問題的。我們認為民歌與“詩人之詩”還是有差別的,正確的道路是從民歌中學習一些藝術手法,然而創作出來的作品還得是個人化的東西,還得是符合現代標準的“詩人之詩”。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之所以引人入勝,就在于它是在民歌信天游基礎上的創作,具有獨立的藝術構思與藝術形式,
味道很濃,人物形象鮮明,而其他許多作品完全不是這樣,所以并沒有取得成功。第三,詩藝的進退問題。一個詩人總會有創作的歷史,是不是后來的作品一定會超過原來的作品,后期的作品一定會超過前期的作品?完全不是這樣的。何其芳是一位杰出的現代詩人,他早期的詩集《預言》詩思與詩質都具有探索性,而后期的作品則遠不如這本詩集,延安時期的一些作品尚可,處于轉變的過程中。柯仲平的詩歌同樣有這樣的過程,即早期作品具有鮮明的個性與風格,個人化的東西是大量的存在,與革命、政治、現實并沒有什么關系,當然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然而是一種情感上、意象上與形式上的產物。寫于1934年開封的一首詩《酒不消愁還喝酒》中有這樣的詩句:“整日你愁,為甚值得這般愁?/黃河決口,開封不也變沙丘?/只愛五月花,臘梅把你恨煞,/西風要罵,難得美玉無疵瑕?”也就是說在比較早的時候,柯仲平的詩風就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這種轉變一個是題材上的,一個是情感上的;一個是形式上的,一個是風格上的,與早期詩作已經完全不同了。這不是一種好的轉變,而是一種退化甚至是“嚴重的退化”。也就是說,他早期的詩作是詩質與詩藝俱佳的,而到了延安時期就完全脫離了原來的軌道,而進入了所謂的革命與政治之中,所寫的東西往往離詩美與詩藝本身越來越遠,并且沒有一點個性與氣質。“柯仲平對于詩的認識,都偏向于聽覺上的、時間上的”(沈用大:《中國新詩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頁),他個人的癖好是朗誦,而帶有表演性質的朗誦,也最能令其詩歌產生效果,這一特征在其早期詩歌中內化為詩句的激昂與氣魄,而到了晚期,則反而使其詩歌淪為了政治的傳聲筒與留聲機。這是一種詩藝的倒退,也是詩思的倒退,就此而言,柯仲平當然是一個悲劇,一個嚴重的悲劇。而他自己并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反而認為是一種進步,并且是一種時代性的進步。我們相信,這樣的悲劇不只是發生在柯仲平一個人的身上。第四,外國詩歌、民歌與中國傳統詩詞的結合與統一的問題。在一個人的創作上,是不是可以把外國詩歌、民歌與中國傳統詩詞的思想與藝術特點相結合,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在實踐上卻存在嚴重的問題。柯仲平早期主要受到西方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又在那樣一個思想解放與個性解放的時代里,所以創作出來的許多作品具有相當的創造性,就是在今天看來也是具有相當水平的唯美詩篇。到了革命根據地之后,如果再寫這樣的作品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加上那個時代所提倡的民族化與大眾化的詩歌思潮,后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要求所有的文藝工作者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轉變到工農立場上來,同時也要求以民歌的形式來寫詩,在這種情況下,柯仲平就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詩歌形式,采用當時的口語來寫革命生活,采取陜北民歌的形式,所以創作出來的許多作品沒有思想、沒有個性、沒有形式上的特點,包括這里所選的三首詩,現在看來都沒有可讀性。他從小熟讀唐詩三百首,而這種講究節律、可以吟誦的古詩,對于其詩似乎也沒有發揮本該有的作用,雖然他的許多作品講究外在的形式,可是在沒有內在思想內容的情況下,也就不再有什么良好的藝術效果。所以,我們對于五十年代與六七十年代提出的所謂的“三結合”的創作方法,以及同時流行的在民歌加古典詩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的詩見,是持保留意見的。實踐證明,對于一位詩人而言,要不就以外國詩歌為主,要不就以民歌為主,要不就以中國古典詩詞為主,才可以發展起自己的特點,形成自己的優勢。在理論上探討了那么多年,發表的論文成千上萬,可是違背藝術規律的理論,對于創作不會發揮任何好的作用,相反會造成災難甚至是嚴重的災難。柯仲平一生的詩藝實踐,就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