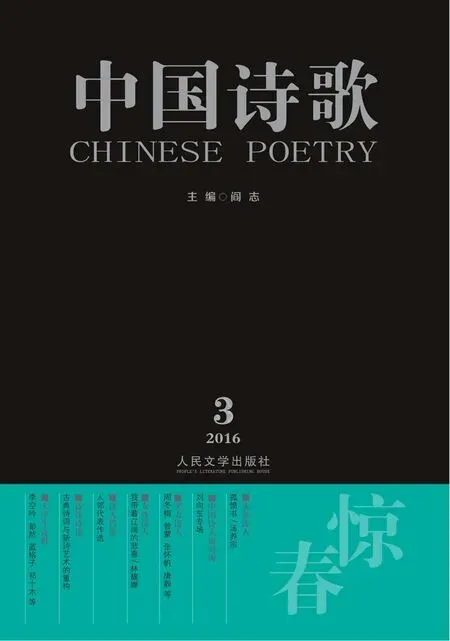中國詩人面對面
——劉向東專場
□主講人:劉向東
主持人:田 禾
中國詩人面對面
——劉向東專場
□主講人:劉向東
主持人:田 禾
時間:2015年8月16日 地點:卓爾書店
田禾:大家下午好!今天由我主持劉向東老師的講座。
劉向東,河北人,1982年任石家莊鋼鐵廠宣傳部副部長,1991年調入河北省作協,歷任副秘書長、《文論報》主編、創聯部主任,《大眾閱讀報》社社長、總編輯,現為專業作家。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詩九首》和《母親的燈》分獲第八、九屆河北省政府文藝振興獎,組詩《記憶的權利》1996年獲中國作協抗戰征文獎。1994年當選首屆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順便說一句,劉向東老師是詩歌世家,寫詩的人對他的父親——劉章都不會陌生,劉章老師是現在《詩刊》老一輩詩人中為數不多的健在的詩人,是德高望重的文壇泰斗。劉向東老師去年以河北省文化廳的名義用他父親的名字設立了“劉章詩歌獎”,我要感謝他們父子,剛好我是首屆“劉章詩歌獎”獲得者之一。我以前從來沒有跟他們聯系過,當他們告訴我的時候我很驚訝。他們父子對中國詩壇是有貢獻的。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劉向東老師給大家講課!
劉向東:非常感謝大家,正是打瞌睡的時間,還來聽我說話。本來交代給我的是一個講座,后來臨時改為和我們夏令營的學員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我沒想到的是還有那么多成熟的詩人、批評家,還有我們當地那么多的詩歌愛好者在場。能在這樣一個時間和大家面對面,客套的話我就不多說了。我想我今天要和大家說的重心是,對待詩歌,應該要采取一個什么樣的態度?可能基本上是常識,但是又和教科書上說的不一樣。其實,這和我們對待世界萬物的態度是一樣的,干什么有什么規律。對詩的態度最首要的一點就是把詩當詩。無論是讀詩還是寫詩,當你把詩拿過來的時候,我們首先要意識到我們讀的是詩,而不是別的,寫詩也一樣,我們很多人的誤區可能就在這里。詩,終歸是一個魂牽夢繞的東西。有人要問我,能把詩歌解釋清楚嗎?我不直接回答,因為在我這兒,我從來不會提出“什么是詩”這樣的問題,我只去感受它。也就是說在我的閱讀和寫作中,我感受到了它,我就會很有把握地說這就是詩,這是詩歌的一個基本原理。但是反過來說,我們能不能對它進行解釋呢?是可以的,這就牽扯到了閱讀,我們閱讀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我們閱讀的質量,甚至也決定了我們寫作的質量。那么,在我們的閱讀當中,我想指出,關于詩的最好的詞條不是來自于我們的詞典,而是來自于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7卷第239頁詞條,由于時間關系,我就不細說它了。“詩,是運用語言的特殊方式”,這個等于白說,但是不這么說又不行,接下來又說:“假設,詩起源于對豐收的祈禱,起源于最古老的語言”,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我們的前生前世基本上每個人都是詩人,詩人也沒有特別的地方,接下來,它就舉了很多詩人對于詩歌的解釋,比如說“詩是舞蹈”,“詩是散文表達過程中不能表達的部分”,這些解釋都很精準。我覺得看十本詩學專著,不如認真讀懂這一個詞條。
在我們的古典文學中,最讓我感動的是《紅樓夢》的第四十八回,黛玉與香凝談詩,香凝作為一個丫鬟都能夠對詩有那么好的感悟,可見古人都是詩人了。有一些詩的小故事,對大家的啟發或許更大一些。比如,西南聯大有個教授,叫劉恩典,他是研究莊子的專家,他被西南聯大開除之后,他就到云南大學去講課,他經常在云南大學的校園里,面朝西南聯大,來與西南聯大抗衡,當有學生問他什么是詩,他說了五個字,“觀世音菩薩”。“觀世”是一個詩人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入世的態度,“音”關涉到詩的發聲學,古詩是講究音律的,新詩是講究內在韻律的,“菩薩”是指任何一個詩人都應該具有菩薩心腸。我記住了這五個字,對我的啟發非常大。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那我如何概括詩呢?相對于事物來說,它是超越事物一般狀態的感覺,相對于生活,一定是生活的意外,不是生活本身,一定不是直接介入生活,而是直覺的介入。那么,在現代詩學當中,解釋可能會更深奧一些,“詩,是個體生命和語言的瞬間展開”。古老的詩學觀念我也不反對,但是一定要把它正過來,比如說“詩言志”,這句話來自“詩者,志之所之也”,“志”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志向,或許我們把它理解為“三國志”的“志”更好。“志之所之也”所強調的是訴說的過程和方法,“志”是作為動詞來使用的。也就是說,“詩言志”強調的是寫作的過程與方法,而與你要表達志向等沒有多大關系,這是首先要明確的一點。
古人對詩的認識是趨同的。比如,嚴羽的《滄浪詩話·詩辨》里說,詩是“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非常精辟,沒有一個意向是實的,近乎影子,但是它一定有一個實的參照物。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說一說閱讀與寫作。閱讀是非常要緊的。有些人是天才,具有非常好的詩性直覺,在我身邊就有這種老頭,快八十歲了,燒鍋爐的老頭,沒怎么念過書,他見我們經常寫詩,有一次他望望天,看看地,然后對我說:“云清疑有影,地大動無聲。”還有的老太太退休之后,經常來聽我們的講座,到公園里轉一轉,回家也寫詩歌,然后拿給我看,“最是蝶兒真大膽,人前親吻小黃花”。他們都寫得非常好,這樣的人是非常有詩性直覺的,這是天才。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來認真地積累、閱讀、研究、體會詩歌,這是非常有效的。古人也說過“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我覺得一個有雄心、有才能的人應該廣泛閱讀不同類型的經典,打開視野,增強感受力,不是為了仿寫,而是為了知道應該超越什么。欣賞一首詩,還有一個關鍵點,那就是不要揣度詩人想什么,說什么,而是要把它和你自己聯系起來,理解一首詩的前提是理解你自己,而不是去理解別人。我們現在還很欣賞杜甫、李白,那我們讀到的是真的李白和杜甫嗎?是原生態的嗎?已經不是了。但是真到了自己寫的時候,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開放狀態,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只寫你命里面有的東西就夠了,凝神靜聽,默想諦聽。真正進入創作狀態的時候要把自己稍稍地封閉起來,靜思默想,如果要那么多的信息干擾你,那詩是寫不好的。我想順便說一下,從精神分析學上來說,詩人大體上是自戀者。可是我們的讀者恰恰反對的就是詩人自戀,這個問題出在哪里呢?我想是詩人有個角色轉換沒有處理好,如果詩人把自戀轉換為對詩的迷戀、沉浸,這個問題就成功地解決了,如果詩人拿出了好的文本,讀者就不會反感詩人。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古典詩詞跟新詩的關系以及新詩所面臨的最突出的問題。每次在我談詩的時候,我基本上不分古體詩詞、現代詩或者新詩,我沒有這樣的觀點,我認為它們是一脈相承的,本質是一樣的。有些新的詩人會退去寫詩詞,與其說是表明了詩詞較新詩優越,實際上不如說是新詩比詩詞更難寫。古體詩和新詩在表達上有所不同,作為詩歌本質卻是相通的,那就是新詩是可以返祖的。比如舒婷的《雙桅船》,“霧,打濕了我的雙翼,可風,卻不容我再遲疑。”轉換為五言詩,即“霧濕雙桅翼,風吹一葉舟”,七言為“霧雖濕翼雙桅重,風正吹舟一葉輕”,這樣很容易就把新詩翻譯成古體詩。再如冰心的《春水》,“黃昏了,湖泊欲睡了,走不盡的長廊啊”,稍一排列組合,便可以變換為五言詩“湖水倦黃昏,長廊行不盡”,七言為“湖泊欲睡黃昏至,不盡長廊緩緩行”。我承認古詩翻譯成新詩比較困難,弄不好就成了白開水,原因是古詩的基本語義單位是句子,而新詩的基本語義單位是詞語,把詞語組成句子相對容易,但是把句子拆開重新組織比較難;還有就是很多翻譯家犯了一個錯誤,采用了一對一的方法,就是一句古詩翻譯成一句新詩,完全對著翻譯的,應該把古體詩詞打碎,重新提煉,照樣可以變成新詩,這就是古體詩詞和新詩血脈相承的地方。這一點,國外的很多大詩人比我們做得好,他們不知道用現代漢語一對一地去翻譯,他們只是把詩意提煉出來。另外,我想說凡是新詩寫得出色的詩人,舊體詩的功力都非常好,無一例外。像于堅,他枕頭邊上放的是《唐詩三百首》,他天天讀,幾十年不倦;像西川,他是從寫古體詩詞起家的,他對古體詩詞門兒清。還有像我的老師陳超先生,他研究的是古典文學,搞的是先鋒詩論,所以他的新詩是非常古典的,他有時候用反傳統的方法,有時候甚至又用傳統的方法。那么反過來,在當代古體詩詞寫得好的人,一直在認真地默默關注新詩,甚至有些小說家也在關注新詩,例如劉醒龍,他是很好的小說家,讀詩比讀小說多,他的文章里面常常會有這樣的句子,有時候我們都不禁稱其為一首詩的時候,他覺得它們對小說的生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比如說他有的小說中會寫到“一碗油鹽飯”,完全是憑借著詩性直覺,“前天我回家,鍋里有一碗油鹽飯,昨天我回家,鍋里沒有油鹽飯,今天我回家,炒一碗油鹽飯放在媽媽的墳前”。如果它不是借助了詩的形式,那它是沒有力量的,它是不是一首好的現代詩,有待商榷,但是它卻有詩的要素在里面。
下面,我要講的是當下新詩突出的幾個問題。
第一,我們對新詩缺乏敬畏,一再降低寫詩的難度。尤其是網絡寫作,我們以為這是最容易的,但是表面上最容易的東西是最難的,有些人以為它自由,其實它是最不自由的。它不僅關涉到詩章,而且關涉到詩句;它不僅關涉到詩句,而且關涉到詞語;它不僅關涉到詞語,而且關涉到詞素;它不僅關涉到詞素,而且關涉到詞根。一個對語言沒有深入了解和把握的人,新詩是無法寫好的。并且標點和空白都在發揮作用,這些都是表意的部分。
第二,是結構。我們覺得新詩是自由的,想怎么寫就怎么寫,但是現代詩的結構形式變動不拘,非常多樣,每一首意味豐盈、技巧高妙的詩都需要臨時發明出自己的結構方式,一個具象化的此刻都不同于另一個,因此每一個都必須意識到規則必須從內部重新開始。現在有很多人覺得寫詩很簡單,所以就瞧不起詩人,其實現在有好多好詩人寫的詩非常深刻,它的生存、生命乃至語言、結構能力都非常了得,這需要我們認真去體會它。同時,非常要命的是意義誤區。顯而易見的是,一些概念意義大于詩性意義的詩作正是當下大量平庸詩的特征。那有的人會想:“現代詩是不是可以拒絕追求意義呢?”不是,現代詩追求的不是本質主義一元化的意義,而是非常復雜的意義領域,拒絕的是集體話語而非個人的感受力和個人化的感知力,也就是說詩的意義不是公眾語言所能表達的,一首詩需要在自身呈現一種意義參照,它是臨時的、偶然的情境下的意義模式,或者是同諸多意義聯系在一起的意義關聯域,那么,詩給我們的絕對不是直接的意義,而是1+1>2的意義可能,它是懸置但不落實,它是許諾而不兌現。而我們常犯的毛病就是一上來就要把意義端出來,并且在道德上一貫正確,這是很多詩人的失誤。在詩歌中一直存在著模擬要素與現實要素,存在著神奇與美麗的部分,真理與意義的部分,一個好的詩人所標的都是這二者之間的對話。我們寫詩主要是聆聽,讀詩實際上也是聆聽,即便是那些最成功地表達了本真日常經驗的詩歌,有80%的可目擊性,其余的在我們的目光和語義中不能透露,但可以更深層打動我們的幽暗的部分。我們有誰看到了詩呢?我們看到的只是符號,詩在語言文字的背后或者說在語言的縫隙之中。盲目追求意義的手段,非常值得警惕的就是強行注入或給予,而不是去揭示。所謂強行注入或給予就是詩人在處理材料時以單一的視點和明確的態度直接地拿給讀者,顯擺他的倫理判斷,價值立場,情感趨向,這種詩歌表面上看來清晰透徹,但是實際上往往成為枯燥的道德說教。如果詩歌變為簡單的道德說教,詩人就會在不期然中以一貫正確標榜所謂的正義、純潔、終極關懷,讓這些都站在自己一邊,這樣就取消了詩的多樣性和與讀者的平等對話。

那么,盲目追求意義最突出的標志是妄圖在詩的結尾拔高。我們很多詩把最后一段去掉,大體上正好合適,我們最后一節往往是拔高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的。我們一定要記住一條:詩沒有結尾,只有結句。當詩結句的時候,不是把門窗關上,而是把一個空間打開,讓聲音繼續鳴響。
第三,就是形象匱乏。現在詩歌有兩種,一是把事說完全,甚至都說不完全;二是完全地自白。詩,肯定是離不開形象的,“隱喻”或者“象征”無非就是用具體的形象來表達抽象的觀念,在詩中,形象屬于從屬的地位,目的是為了表達“觀念”,這完全是一種誤解。真正的關鍵在于外界事項能不能與人的內心發生神秘感應。從技術上說,“意象”不是簡單的“意”加“象”,而是“意”和“象”的反復相乘。“象征”也不是一般的修辭技巧,而是內外現實的相互融合。詩中的“形象”絕不是從屬的工具,它自身擁有自己的價值。拿“樹”這樣一個形象來說,像牛漢先生有《半棵樹》,曾卓先生有《懸崖邊的樹》,舒婷有《致橡樹》等等,但是田原先生翻譯的古川俊太郎的《樹》別出心裁,他說:
看得見憧憬天空的樹梢/卻看不見隱藏在土地里的根/步步逼近地生長/根仿佛要緊緊揪住/浮動在真空里的天體/那貪婪的指爪看不見 //一生只是為了停留在一個地方/根繼續在尋找著什么呢?/在繁枝小鳥的歌唱間/在葉片的隨風搖曳間/在大地灰暗的深處/它們彼此地糾纏在一起
他從樹梢一下子就寫到了根,但是他仍然是樹立了一個樹的形象,并且達到了根本。
第四,有些詩人寫詩,靠回車敲打、強行斷句制造節奏。一讀這樣的詩,我就憋氣、胸悶,有話不好好說,偏偏這樣的詩又非常多。反過來說,那些值得被詩歌書寫的東西,都有自己內在的節奏,我們詩人要尋找它,呈現它,包括我們自身生命的節奏。好的現代詩,基本上節奏是事物自身的,內在的;不好的詩,節奏都是作者強行嵌入的。這一點不值得我們深入地說,但是值得我們考慮。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現代詩人里面做得最好的有兩位。一是艾青。艾青的詩歌語言近似白開水,在走鋼絲,可以說句句不是詩,而首首是詩。每一句拿出來都不是詩,組織在一起的時候非常有效,它是詩;句句都能懂,但是組織在一起的時候不一定懂。當然懂不懂不是判斷詩的標準,要看你的感受。二是女詩人娜夜。她從來不強行回行,句子可長可短,有時候句子短到1個字,長到30個字,給你的感受是她是彈著鋼琴來完成她的詩作的。
不再細說了,現代詩雖然普遍追求非韻化,其實它應該特別重視個人的生命節奏,成功的詩不僅是心靈的運動,也應該是聲音的運動,高妙的聲音能在語義字詞接受之后,繼續鳴響,召喚出語義不能說出的東西,猶如我們寫字,比如說書法。你說書法美,難道是幾個漢字本身嗎?不是,而是你的運筆的生命的律動。
接下來,我想說一說很多現代詩包括中外的是我欣賞的,我所做的詩歌筆記里面,我選擇了大概七百多首,我為它們做了二百多萬字的讀書筆記。我想說的是我欣賞什么,它給我什么樣的啟示?我個人不反對暗示、隱喻之類的東西,但是我更欣賞回避間接性,準確、本真地提煉細節,有些詩簡直不需要以言辭的贅述的方式介入,也不需要調動更多的直覺,它不留余地,直接撞在你的心上。比如說曾卓先生《懸崖邊的樹》,由于時間有限,我就不詳細地讀這首詩歌了,大家下去之后一定要找來讀一讀,這是大師級的詩人的作品。我特別喜歡簡潔但并不簡單的詩,率真、出人意料的簡樸和本真的純凈。詩歌的簡潔與繁復,含混與清晰,本身并不等于詩歌的價值,詩的價值在于繁復要有內在的精致、精明,清晰空靈要有透明的核心和光明的神秘,輕靈要寫得像鳥兒一樣輕,那是“飛翔”,而不是像羽毛一樣輕,那是“飄”。要真切得叫人恍惚,熟悉得叫人陌生。詩歌的簡潔與否,并不是簡單地說詩歌的長與短,不是一個體積概念,而是一個包容的概念。一首飽滿的長詩也可能是簡潔的,一首簡潔的短詩也可能是豐富的。有一些似乎有悖于常識的詩,不重形象,近乎于抽象,沒有修飾,也沒有象征、比喻和暗示,幾乎就是口語和白話,是直接的呼喚,卻比一千個比喻加在一起還要動人,更有力量,這樣的詩對于詩歌大師級的詩人,一生也可能就只有一次。比如說田間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
去一個字都不行。我們很多人懷疑田間,否定他的詩人地位,那是一個用生命寫詩的人,有這樣一首詩就夠了。反過來說,就像雪萊的詩中說:“讓我死去!昏倒!我虛弱無力!”這就是詩,這是生命的本真狀態。再如阿赫瑪托娃說:“會見為了分別,戀愛為了不再戀愛,我真想哈哈大笑,放聲大哭,不想活了!”這樣的詩,一生當中只有一次。她還有一首詩《失戀》說:“我把左手的手套戴在了右手上,我邁下了許多臺階,仿佛才邁下了一個。”我想說的是,這樣的詩直接來自于胸襟,同樣會于心,甚至是不需要解讀的,也是難以解讀的。詩,有可解,有不可解,有不需解,我們要把它們分出來。成功的詩歌給我的一個啟示是一個過程,是用具體超越具體,詩歌要有具體感,但它不是生活化的具體,而是用具體超越具體。詩歌源于個體生命的經驗,經驗具有一定的敘述成分,它是具體的,但是僅僅意識到具體,沒有真切的經驗不行,再好的經驗細節也不能自動等同于詩歌,一旦進入寫作,我們的心智和感官應該馬上醒來,跟上去,審視這經驗,將之置于想象力的智慧和自足的話語形式之下,用具體超越具體,它的圖式基本上是具體——抽象——新的具體,這就是一首詩的過程。那么,我們試著舉三個小例子。我認為這個世界上最高級的詩是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牧場》這樣的詩:
我去清理牧場的水泉/我只是把落葉撩干凈/(可能要等泉水澄清)/不用太久的——你跟我來 //我還要到母牛身邊/把小牛犢抱來/它太小,母牛舐一下都要跌倒/不用太久的——你跟我來
這樣一首詩看似簡單,它完全經得住分析,我可以為它寫一萬字。這里面有實:我、母牛、水泉、落葉,有虛:你,其實這個“你”是不存在的,但是你感覺“你”就在你身邊,也許就是等著讀者去參與。這首詩歌充滿了愛,一個老漢的心靈還是那樣的柔嫩,沒有被時間磨成老繭,特別好。
還有法國詩人普列維爾的《公園里》:
一千年一萬年/也難以/訴說盡/這瞬間的永恒/你吻了我/我吻了你/在冬日朦朧的清晨/清晨在蒙蘇利公園/公園在巴黎/巴黎是地球上的一座城/地球是天上的一顆星
太簡單了,你感覺是太簡單了,但是一生能寫出這樣一首詩來就是大師。我再舉一個我身邊的例子,很多人都喜歡我的一個詩人朋友大解,我們每天在一起,經常下河去撿石頭,他有一首詩就是我們一起撿石頭撿回來的,叫《衣服》:
三個胖女人在河邊洗衣服/其中兩個把腳浸在水里 另一個站起來/抖開衣服晾在石頭上//水是清水 河是小河/洗衣服的是些年輕人//幾十年前在這里洗衣服的人/已經老了 那時的水/如今不知流到了何處//離河邊不遠 幾個孩子向她們跑去/唉 這些孩子/幾年前還呆在肚子里/把母親穿在身上 又厚又溫暖/穿著一件會走路的衣服
就這么簡單。這樣一些詩從具體到抽象再到新的具體,它的現場發生了轉移,從生活現場抵達了詩歌現場,它抽象的過程是一個命名的過程,一旦命名成功,抽象的過程終結,達到了新的具體。有些詩是從生活中來的,有些是從心靈中來的。如果是從心靈中來的,該怎么辦?我們可以從現實生活中找一點對應物,我們也同樣可以通過具體到抽象再到新的具體,反過來也一樣。
最后,我再說一個小小的問題,關于詩歌的寓言方式。詩的寓言方式,這對我們非常重要。我們讀詩歌的時候,經常會發現它以一種寓言方式出現,這與我們這個時代有關。我們用了30年時間,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到半機械化社會再到機械化社會、工業化社會、模擬的數字化社會再到數字化社會,我們跨越了不同形態,因為我們身臨其境,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它的部分,但是要認識全部還很困難。再加上體制內寫作,強調主旋律,我們受的限制很多。但是很多人可以用寓言的方式,在超越這個時代,給了我們很多空間。也有很多人用了另外一種方式,即口語寫作,不要以為“口語”就是說話,而是口語的秘密變體,它時刻都在警惕口語,它的語言大于口語,幾乎無法用日常的口語來還原。
好了,我就說這么多,謝謝大家!
田禾:劉向東老師作了很認真的準備,我看到劉老師拿了好多稿子!再一次謝謝劉老師!接下來,大家可以向劉老師提問,大家可以舉手示意!
提問者1:劉向東老師,您好,我是“新發現”學員馬曉康,我們之前在山東已經見過了,當時您給我列了一個50本書的書單,很不好意思,這些書我還沒有讀完。我讀過一些書包括《滄浪詩話》、《造字六法》等。中國的造字六法主要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但是我覺得古代的詩歌還是以造字六法為主,而古詩主要有兩種形式,借景抒情和睹物思人,就算到今天有各種詩歌形式,但是我覺得都沒有逃脫這兩種。我之前也參加過《星星》夏令營,我感覺現在很多人寫詩受西方詩影響很大,我在國外留學7年,我就感覺現在很多人亂用語法。今天有一點疑惑想請教您,就是西方詩對中國新詩的影響,還有就是中國詩歌的氣象問題,我們究竟該注重詩歌語言的精雕細琢還是原始的粗糲感覺?
劉向東:曉康的書沒有白讀,寫詩長進非常大,接連幾個重要刊物的夏令營他都參加了。我英語一定不如你好,我的回答是,詩歌翻譯以后,就一定不是外國詩了,無法用漢字寫外國詩歌。鄭炳先生說,我們中國的新詩基本上就是對外國的翻譯詩的模仿,無論我多么尊重這個老先生,但是這個觀點是有問題的。用漢語言、漢字詞素,中國的歷史、地理等,我們寫不出外國詩歌。古典詩歌轉為新詩是世界的一個普遍現象,英語世界也不過是從布萊克開始到惠特曼到狄金森,他們比我們早不了幾年。我們的先賢們非常有智慧,為什么要變?詩在變,是因為生活變了,語言變了。全世界的詩歌都是從古典詩到特定的時間點轉變為新詩。
新詩其實不必要去雕琢。我們說古詩要煉字、煉句,是要煉,為什么呢?是因為它本身就只有七個字為一句,我們現在不用了。古詩其實借助了一個外殼,其實它是散文的形式,比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這不是散文么,不過是說了一件事情,它只不過是借用了詩歌的形式,而我們新詩沒有形式可以借助了,我們借助的仍然是散文的語言,但是它要求你直接抵達詩的本質,它的難度就在這里。不需要你去雕琢,有時候煉字反而會把整首詩顛覆,你不如用散文化的語言。正如有些人說艾青的語言散文化,艾青笑著說,他不是散文化,是散文美。

提問者2(蘆葦岸):劉向東老師,您好!我就借著您剛才的話來說,我很贊同您剛才說的英語世界也不過是從布萊克開始到惠特曼到狄金森,他們比我們早不了幾年這個觀點。有些人說咱們國家的新詩向外開放的時候受益于美國新的詩歌較多,但是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很多當時美國的大詩人對中國傳統詩歌的借鑒也很明顯,比如說龐德對劉徹等的尊崇,他的尊崇并不是說對絕句、律詩的寫法,而是對意境和意象。我有個問題想問您,您現在掌管《詩選刊》,您能不能從刊物角度來談談詩歌的美學走向,或者說對當下詩歌的優劣做一下分析?
劉向東:蘆葦岸是理論家,他對詩歌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我接手《詩選刊》時間不太長。有時候我們會懷著巨大的期望值。我那里有全國各地能變成漢字的詩歌刊物,有龐大的資料室,我有好幾個責任編輯天天在看這些東西,給我建立檔案室,讀每一首詩歌都是帶著極大的期望的,但是常常失望而歸。在我這里,我主張詩歌一定要多元,詩歌和文學沒有所謂發展不發展的問題,只有變化,那是因為生活,因為語境,我期待每一首好詩。我惟一的想法就是你們稍微少寫一點,寫得精一點。有些知道我郵箱的人經常給我發一本書的稿子,我真的看不過來,累得我這個老漢腰都直不起來。你能不能只給我10首或者20首?我不拒絕任何一首好詩,但是我不保證《詩選刊》發出來的都是好詩,因素太多,但是我期待我的刊物里面80%是有效的。謝謝大家!
田禾:時間已經到了,但是我們還是給一個機會,給最后一位讀者。
提問者3:劉老師好,剛剛劉老師說到弗羅斯特的《牧場》,我很喜歡弗羅斯特的詩歌,但是弗羅斯特的詩歌跟詩壇現代派的主流是不一樣的,感覺現在的詩歌更加講究技巧和形式。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對不對,請劉老師批評指正。
劉向東:我很認同你的觀點。弗羅斯特是美國當代第一大詩人。我們都知道惠特曼更多,是因為他更符合美國人的價值取向,美國人在推廣他,而我們以前是一個封建社會,我們尋求自由,惠特曼是自由大愛的詩人,所以我們喜愛他。但是他在美國沒有弗羅斯特那么重要,狄金森也一樣,我們喜歡她,不過是她太封閉了,每天連莊園都不出,卻給我們留下那么多的好詩,有一種很大的宗教感和神秘感。在美國,每一個選本都是用弗羅斯特作為開篇的,家喻戶曉。我們讀詩,我們認同誰,不一定說要跟著誰跑,可是反過來我要說的是,寫出惠特曼這樣的詩歌相對容易,無非是連同黑奴、妓女、逃兵一樣愛嗎?無非是要抒發帶電的肉體和靈魂嗎?而寫到弗羅斯特這樣的境界實在太難,我此生可望而不可即的。謝謝!
田禾:對不起啊,由于時間關系,活動安排比較緊湊,我們劉老師的講座就要告一段落了。我們劉向東老師的演講是非常精彩的,這是他多年寫詩、編詩、讀詩的經驗之談,也是他自己對詩歌獨特、敏銳的思考。他跟我們談論了好幾個問題,我就不一一細說了,主要包括:什么是詩?我們要讀什么樣的詩歌,怎么樣來讀詩歌?古體詩和新詩的關系,他特別強調新詩寫得好的詩人一定是古典詩功力非常深厚的人,他一直勸大家要多讀一點古典詩詞,不斷豐富自己。他也談到了當代新詩突出的幾個問題,語言問題、詩歌的結構問題、詩歌的寓言方式,包括他回答了大家提出的有關詩歌的問題。可以說,劉老師今天的講課深刻、透徹、精辟,富有深度和高度。如果大家還有問題,大家可以和劉老師私下作進一步的交流。
最后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對劉老師表示感謝!
(李亞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