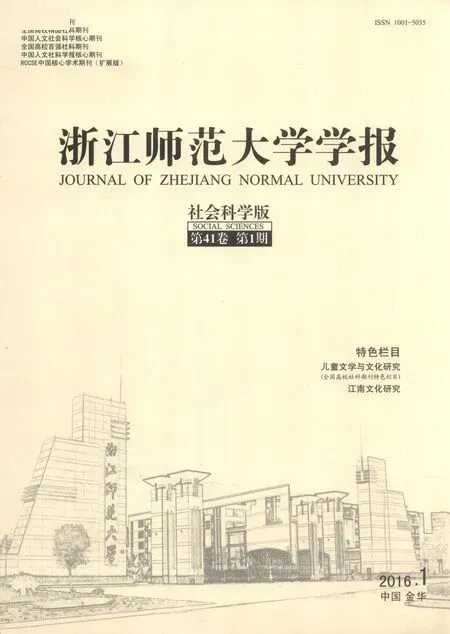論《艱難時世》《功利主義》《論邊沁》中共同的情感結構*
閔曉萌
(北京郵電大學人文學院,北京100876)
?
論《艱難時世》《功利主義》《論邊沁》中共同的情感結構*
閔曉萌
(北京郵電大學人文學院,北京100876)
摘要:狄更斯和穆勒分別在《艱難時世》《功利主義》和《論邊沁》三部著作中對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做出回應。兩人看似立場殊異,實則殊途同歸。他們倡導個體權利、反對機械化的情感計算方式、堅持精神至上的價值判斷,試圖從對象、方法論和價值觀三個層面對功利主義學說進行全面彌合,表現出了共同的情感結構。這種情感結構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彼時文化界對邊沁學說的接受和反撥,為深入探析功利主義哲學影響下的文化模式和意識結構提供了管中窺豹的一個片段。
關鍵詞:狄更斯;穆勒;功利主義;情感結構
查爾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名著《艱難時世》( Hard Times,1854)雖與穆勒(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哲學倫理學論著《論邊沁》( On Bentham,1838)、《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1863)有著共同的話題,都對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作出回應,卻鮮有學者將上述名作并置,進行比較研究和相關性分析。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從兩人的生平經歷來看,狄更斯雖與維多利亞社會批判家們關系密切,不僅曾借鑒和效仿卡萊爾( Thomas Carlyle)的觀點,[1]也頗得阿諾德( Matthew Arnold)、羅斯金( John Ruskin)嘉許;但他與穆勒卻并無交集。有歷史記載稱,穆勒在閱讀完狄更斯的《荒涼山莊》( Bleak House,1853)后,曾憤憤然說道:“狄更斯那家伙!”[2]顯得兩人還頗有些嫌隙。其二,從兩人作品中折射出的觀點來看,狄更斯在《艱難時世》中對功利主義不遺余力地進行了猛烈抨擊。而穆勒一方面受其父詹姆斯·穆勒( James Mill)的教誨,篤信功利主義的“快樂動因”學說,捍衛功利主義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受到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等人的影響,對功利主義的冷酷和缺乏同情心加以駁斥。兩人不僅寫作文體和風格大相徑庭,基本立場和態度也迥然相異。然而,如果借用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文化唯物主義”理論中的重要范疇——“情感結構”( structures of feeling)對上述作品加以考察,就不難發現,兩人南轅北轍的闡述中隱藏著深刻的一致性,表現出共同的情感結構。本文擬在這一范疇的關照下研讀上述作品,打破文學與哲學的學科邊界,發掘差異性背后隱藏的一致性。這不僅有助于我們重構作品生成的文化語境,還原和發掘作品的思想真貌;也使得我們得以管窺19世紀中葉前后,文化界圍繞邊沁功利主義思潮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意識結構。
“情感結構”的概念最早見于《電影序言》( Preface to Film,1954)一書,后經由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 The Long Revolution,1961)、《馬克思主義與文學》( 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中做了進一步闡發。在上述著作中,威廉斯將情感結構界定為處在特定時期中的一代人對所處世界的一種回應。有別于“世界觀”“意識形態”等體系完整、官方認可、制度確認的價值觀念,“情感結構”表現為人們真實體驗和親身感知的一種文化模式。[3]它既可能與社會主導價值體系趨同,也可能與其相悖;既具有“結構”的相對穩定性,又具有“情感”的細膩和難以捕捉性;[4]既表現出與前代人情感結構的連續性,又表現出特定時期內人們感知生活方式的獨特性;是一種處在不斷變化過程中的有機文化模式。[5]從這個意義上說,狄穆兩人的著述正是對19世紀中葉前后、邊沁學說影響和作用下情感結構的一種書寫。它從功利主義學說的缺陷中衍生而來,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彼時文化界對邊沁學說的接受和反撥。
功利主義學說是邊沁( Jeremy Bentham)于1789年提出的一套哲學思想,最早應用于立法和道德領域,認為追求快樂和回避痛苦是人類行為的內在驅動力,因此政府與社會應倡導個人合理利益的最大化,以實現共同體利益最大化。為將這一原則細化為一套可操作的倫理規范,邊沁提出了一系列指標,主張通過先量化計算個體的快樂值和痛苦值,再運用數學公式加減求和,測算共同體的快樂傾向和痛苦傾向,以評估一項決策或一種行為對社會產生的整體影響。[6]雖然這一學說的問世極大地促進了政治、司法、道德領域的社會生活向更為民主和人道的方向發展,其積極作用不可小覷;但其局限性同樣不容諱言。從對象來看,功利主義雖然試圖兼顧個人與集體,但在對共同體利益進行評估時,個人只作為集體中無差別的砝碼和單元存在。“最大多數人利益最大化”原則使得與集體利益相左的個人處在被犧牲的危險邊緣,可能導致伯克( Edmund Burke)等保守派思想家所憂慮的“多數人專政”的局面出現。[7]8從方法論來看,苦樂這樣復雜的情感該如何分類、量化和計算,同樣是個不小的技術難題。穆勒就曾在《論邊沁》一文中批評邊沁缺乏必要的人生歷練,對人性不夠了解;這種個人缺陷直接導致功利主義哲學“忽視了人類具有的大約一半的內心情感的存在”。[8]33從價值導向層面來說,功利主義偏重物質層面的快樂,對精神之樂則強調不足;“能使社會制定賴以保護其物質利益的規則”,但卻“無助于社會的精神利益”。[8]34在一個卡萊爾眼中被金錢關系主導和異化的社會里,這樣的學說確有助長物質主義和拜金主義之虞。
穆勒和狄更斯對邊沁學說的缺陷有著清醒的認識,并積極予以回應。穆勒以慎思的哲學精神,以拓寬內涵、澄清誤解、糾正偏頗的方式修正學說的種種不足。而狄更斯則憑借小說家的生花妙筆,在特定敘事結構、人物塑造、情節設置中傾注了作者的價值判斷。二人關注個體合理權利、反對機械化的情感計算方式、堅持精神至上的價值判斷,試圖從對象、方法論和價值觀三個層面對功利主義學說進行全面彌合。下文將逐層分析這一共同的情感結構,以期在哲學、文學、文化三位一體的參照系統中領悟作品精髓,拓寬和加深對作品的認識。
一、重現多數人專政下的個體聲音
功利主義將學說捍衛的對象界定為“最大多數人”,從而賦予了大多數人將其意志凌駕于少數人意志之上的特權。[7]61面對岌岌可危的少數派權利,穆勒和狄更斯力圖凸顯多數人專政體制下的個體聲音,以化解功利主義帶來的邏輯困境。早在1838年問世的《論邊沁》一文中,穆勒就曾探討過多數人專政體制的局限性。他承認功利主義學說竭力保障多數人權利,甚至窮盡一切手段和資源,試圖用大眾輿論鉗制政府官員的言行。然而,學說在對個體權利的保護上強調不夠、論證力度不足。社會仍然需要建立一種平衡機制,為少數人保留一定的話語權,“以此來矯正片面的觀點,保護思想自由和人的個性”。否則,個人正當權利極有可能會“處于極度危險的境地”。[8]47-48這種觀點在時隔25年后面世的《功利主義》一文中發展為對功利主義學說的一種拓展和修正,強調功利主義并不要求人們只專注于“世界或社會整體這樣寬泛的一般對象”;在不損害他人合法權利的前提下,“最有道德的人也只需考慮有關的個人”。[9]18-19這一再詮釋雖然在沃洛克( Mary Warnock)看來“已經偏離了嚴格意義上的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10]但其用意與25年前并無二致,都是為多數人專政體制下的少數派個體代言發聲。
多數人專政下的少數人困境不僅是穆勒在《論邊沁》和《功利主義》中著重討論的議題,也是狄更斯在《艱難時世》第九章關注的焦點。小說家在寫作小說時雖不像哲學家那樣直抒胸臆,但特定的情節安排、人物塑造、詞匯選擇和句法修辭常常成為傳遞隱含作者觀點的表意方式。在上述章節中,馴馬師之女西絲接受了功利主義教育者麥卻孔掐孩先生的思維訓練,并向露意莎轉述了這次經歷。依照熱奈特( Gérard Genette)在《敘事話語》( Narrative Discourse,1983)中的提法,該片段包含多重敘事層次,其中隱含作者寫作小說這一事件屬于故事外層( extradiegetic),西絲與露易莎之間的交談為故事內事件( diegetic or intradiegetic),西絲轉述的課堂教學內容為元故事( metadiegetic)。[11]狄更斯反對多數人專政、維護個體權利的基本態度,即鑲嵌在這種獨特的敘事結構中。
在元故事層面,麥卻孔掐孩與西絲在看待幾個命題的態度上發生了分歧: 1.假設課堂是個擁有5 000萬英鎊的國家,可否稱之為繁榮? 2.如果課堂是一個有100萬居民的大都市,在一年之中,只有25個居民餓死在街上。這個比例怎樣? 3.如果10萬人在海上作長途航行,有500人淹死或被火燒死,這個百分比是多少?按照功利主義原則,這三個例子均是符合“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原則的實例。然而在西絲看來,第一個例子中的國家富裕并不能等同于國家繁榮,因為財富的去向及個人所占份額并不明了;第二個例子中有100萬居民存活也不是幸福的表征,因為畢竟有25個人失去了他們最寶貴的生命;在第三個例子中,雖然有10萬人得以安然度過海難,但對于親友在海難中喪生的人來說,每一個生命的離去都讓人難以承受。[12]66-67西絲的看法沒有得到麥卻孔掐孩的認同。然而,這些判斷建立在對公平的追求、對個人生命的尊重、對他人傷痛的同情之上,符合公平、人道、博愛等普世價值觀。麥卻孔掐孩將其否定的同時,也就在元故事層面構建了功利主義價值觀與公正、人道、博愛等普世價值觀的對立。隱含作者通過將多數人專政可能引發的道德困境實例化,使原本枯燥概念化的倫理問題真實可感,也促使讀者采用更為情感化的視角審視多數人專政下的少數人困境。
而到了故事內事件層面,西絲在長期無法取得“進步”的壓抑情緒作用下,向露易莎傾吐了自己的苦悶,轉述了這次經歷。由于西絲個性溫良、見識不廣,服從麥卻孔掐孩在元故事層的教導;因此在這一敘事層次中完全否認了自己之前的判斷,認為自己犯下了“天大錯誤”。而露易莎從小深受功利主義教育浸淫,早已將功利主義哲學內化,所以也不假思索地附和了西絲的自我否定,“這就是你的一樁大錯”。[12]66-67結合上文相關情節來看,兩人的價值判斷實際上呈現了功利主義教育與西絲原本秉持的公正、人道、博愛原則在故事層面的對立。
由此可見,狄更斯層層構建了多數人權利——個體合理權利以及功利主義教育——西絲原本正確的信念這兩組矛盾的雙重對立,融維護個體權利、反對多數人專政、質疑功利主義教育的價值判斷于多層次敘事結構中。這與穆勒對同一命題的論述相比,雖形式不同,但立場無異。正是得益于兩人歷時多年、不拘體裁、富于層次的反復論證和呼吁,“維護個體權利”這一主題才得以在19世紀中葉以更加豐富、更加多元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面前,敦促人們在各個階段、從不同渠道對功利主義的多數人原則進行反思。
二、質疑情感的數字化考量方式
功利主義學說以確立明晰有序的立法原則為出發點,因而必須改變以往立法含糊不清、模棱兩可和草率立論的局面。為實現這一目標,邊沁采用了一套量化的計算方式。他不僅對快樂和痛苦做了32種分類,在陳述計算方法時也追求數學般的嚴密精確。這些做法“使法學從莫名其妙之物變成為科學”[13](麥考利語)。穆勒在《論邊沁》一文中重申了麥考利(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結論,對邊沁在法學領域的建樹予以充分肯定,[8]11-12但他同時也指出:邊沁本人人生經歷太過單純,對人性的復雜性缺乏足夠了解,對苦樂的分類又完全建立在主觀經驗之上,這些局限性不僅使得他的計算方式只在非常狹窄的范圍內具有適用性,而且對于人性中復雜深邃和難以估算的部分,他的學說更是較少涉及。這無疑大大降低了功利主義計算體系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他對人類情感知之甚少,對情感形成的影響知之更少,思想自身以及外在事物對思想更加細微的運作被他遺忘。”[8]26
事實上,人性的深度和廣度使得苦樂這樣的情感生成機制極為復雜,不可捉摸、難以測算,唯有以情感的方式才能理解情感。也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穆勒將想象力與同情心并置,并將這兩種特質視作彌補功利主義缺陷的不二法門。早在1838年寫作的《論邊沁》一文中,穆勒就毫不諱言地宣稱,邊沁對人性中許多最自然、最強烈的感情沒有同情心,這是他作為哲學家的一大缺陷。[8]2425年后,穆勒在《功利主義》一書中又再次強調,許多功利主義者“培養了自己的道德感情,卻沒有培養自己的同情心和審美鑒賞力”,因此“在看待行為的道德性時考慮過分單一”。[9]20而要獲得“共情”的能力,必要的想象力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想象力是一個人可以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和境遇的能力”,它“幫助人們通過自發的努力來將不在場的事物感受為好像在場,并且讓人們將想象的事物感受為好像是現實中的事物”。[8]24在穆勒看來,想象力激發同情心,而唯有同情心才能使人們設身處地、心靈相通,從而體悟他人情感,而非僵化測算、漠然無視他人內心的情感訴求。
穆勒筆下不通人情的邊沁成為《艱難時世》中葛擂硬的人物原型;他對功利主義計算體系危害性的預估,在小說中經由一樁荒唐的婚事得到了證實;而他所看重的同情心、想象力等特質,被狄更斯賦予了一位扭轉不利情勢、改善人物關系的理想化人物——西絲。葛擂硬與邊沁同為功利主義教育家,他看重事實,對情感和想象力有著難以言喻的鄙夷,慣于用數學方法測算復雜難解的情感問題。即便是女兒露意莎和好友龐得貝的婚事,他也要通過代數計算予以定奪。一番測算下來,他發現,在所有婚姻中,有相當比例的夫妻雙方年齡相差懸殊,且3/4以上為男方年長。這一結論一方面經英格蘭和威爾士搜集來的婚姻數據驗證無誤,另一方面由旅行家在印度、中國、韃靼等地,以最好的估算方法予以證明;因而可以被認作是大多數婚姻的存在狀態,符合“最大多數人最大利益原則”。依照這一推論,龐得貝和露意莎雖然年齡相差30歲,兩人結合仍完全合理,婚后幸福理應可以預期。[12]110-111葛擂硬的計算過程雖然精準,但他卻忽略了婚姻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忽略了女兒自身的意愿。而這種情感上的體諒只有通過共情心理才能獲得。葛擂硬正和缺少必要人生經歷的邊沁一樣,不具備這種能力,因而看不到這樁毫無感情基礎的婚姻帶給露意莎的傷害。對此狄更斯不無諷刺地評論到:“要是他看到這一點,他一定會一躍跳過那些人為的障礙,這些障礙全是他多年來在他自己與那些微妙的人性本質之間樹立起來的。那些本質直到世界的末日,也不是極巧妙代數學所能捉摸的,而到那時候,就是代數學也要與世界同歸于盡了。這些障礙是太多了,也太高了,他跳不過去。”[12]112
狄更斯的措辭與穆勒對邊沁個性的剖析十分契合,兩人都意在批評邊沁、葛擂硬一派的功利主義教育家對人性的不了解,以及以代數公式處理情感問題的不恰當。而這段婚姻的后續發展軌跡則充分詮釋了上述處理問題模式的可能性后果。露意莎與龐得貝婚前毫無感情基礎,婚后兩人生活并不和睦融洽。露意莎長年壓抑的情感找不到出口,幾乎淪為花花公子詹姆斯·赫德豪士的玩物,險些和他私奔。雖然露意莎迷途知返,折返至娘家與父親一起生活,但她與龐得貝的關系也因此完全破裂,兩人終身分居,婚姻實際上已經消亡。一樁以精準數據為依據的婚姻,最終以婚姻破裂作結;狄更斯通過這樣的情節設置,在將穆勒的觀點實例化的同時,也傳達了對功利主義體系的辛辣嘲諷。
而西絲的出現既成為葛擂硬一家扭轉不利情勢、改善相互關系的契機,也從側面印證了穆勒的觀點——為緩和功利主義的僵化教條,同情心和想象力至關重要。史里克( Paul Schlicke)指出,西絲長年生活的史里銳馬戲團是全書想象力( fancy)和手足之情( fellow-feeling)等人本價值的寄存地,[14]與代表著功利主義的葛擂硬學校以及象征著大工業生產的焦炭鎮形成相抗衡的態勢。西絲本人很明顯繼承了馬戲團象征的這兩種特質,她溫柔感性、善解人意,在緩解葛擂硬家庭危機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露意莎剛剛宣布訂婚,西絲就敏感地察覺到露意莎的痛苦,預見到這樁婚姻前景堪憂。[12]80而當露意莎婚姻破裂、身心俱疲地回歸家庭時,首先也是向西絲發出求救的呼聲:“原諒我,可憐我,幫助我!現在我極其需要人幫助,你要憐憫我,讓我把頭放在你那友愛的心坎兒上吧!”[12]252
這時的西絲則如同圣徒一般,“發出一種美麗的光輝照亮對方心中的黑暗”,[12]251用同情和愛心撫慰露意莎的傷痛。在她的幫助照顧下,露意莎過上了雖不甜蜜卻還安寧的日子;葛擂硬也從女兒的婚姻失敗中汲取教訓,開始認識到情感教育的重要性,家中僵硬冷漠的氣氛有所和緩。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葛擂硬家族的小女兒珍雖然仍然接受功利主義教育,但由于自幼與西絲感情甚篤,受其影響頗深,長大后成為了一個“容光煥發”的孩子。狄更斯借露意莎之口,稱兩派力量的中和使得珍“年輕的心弦已被撥出和諧的音符”,[12]248-249顯然是在暗示用同情心和想象力中和功利主義僵化教條的可能性。
這不禁又讓我們聯想到,穆勒在1840年面世的《論柯勒律治》( On Coleridge)一文中,將邊沁哲學和柯勒律治的學說視作對立的兩個學派,認為這兩個人的哲學互為補充,缺一不可。柯勒律治對情感和想象力的強調人所共知。從這一主張中,不難發現穆勒和狄更斯殊途同歸,都試圖從浪漫主義傳統中尋求到醫治功利主義機械理性的良方。這種努力也許如威廉斯所說,是一種“機械的整合方式”。[7]54但是,兩人如何分別以哲學論述和文學創作的方式闡發這種立場,各自獨立又共同建構了英國文化傳統,仍然是一個值得后世讀者反復回味的命題。
三、堅持精神至上的價值判斷
將追求快樂、回避痛苦奉為圭臬的哲學倫理學說常常難以擺脫耽于感官享受、沉溺物質誘惑的指責;亞里斯提卜( Aristippos)的享樂主義學說、伊壁鳩魯( Epicurus)的快樂倫理學說和愛爾維修(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的唯物主義倫理思想皆是如此。功利主義學說問世不久,同樣因為以“快樂”為基準的論調而被德、法、英等國的抨擊者們將之與伊氏的快樂倫理學說相提并論。反對派認為兩派學說都因追求感官享受而將人類與牲畜等同起來,落入了物質主義的樊籬。[9]8不可否認,邊沁確將追求“快樂”視為人類一切行為的動機;但若不加辨析地認為功利主義只強調物質層面的快樂,則是對學說的一種誤讀。在《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一書中,邊沁既列舉了虔誠之樂、仁慈之樂、想像之樂等精神層面的快樂,也列舉了感官之樂、財富之樂等依托物質、訴諸感官的快樂。[6]42可以說,學說創立的本意非但沒有排斥精神之樂,反而將物質之樂和精神之樂并置,視二者為缺一不可的重要組成元素。
穆勒一方面承認精神之樂在功利主義哲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不吝指出,相較物質之樂而言,精神之樂并沒有得到強調和重視。功利主義忽略了約半數人類精神上可能產生的情感,即使是碩果僅存的那些,它們的存在也并沒有引導出什么實質性的結論。[8]33但即便如此,如果認為功利主義意在鼓動人們追求感官享受,仍然是對學說宗旨的一種誤解。在《功利主義》一書的第二章中,穆勒首先駁斥了反對派的觀點。他指出,以邊沁為首的功利主義者們雖然信奉快樂動因學說,但并沒有將人和牲畜等同起來。反對派們如果認定學說中的快樂等同于感官之樂,恰恰說明他們自己否認人類擁有高于感官的精神愉悅,認為人類之樂與動物之樂是無差別的。在隨后的論述中,穆勒又對感官之樂和精神之樂的高下做了辨析。在他看來,只有對物質之樂和精神之樂皆有體驗的人,才能體會到兩者之間的差別。而但凡經歷過靈與肉兩重愉悅的人,都會更為偏好更高級官能的快樂,即精神之樂。如果從這一經驗引申開來,那么精神之樂較物質之樂不僅程度上更為強烈,而且境界更為高遠,理應更為功利主義信奉者們所推崇。
穆勒借助個體經驗,以說明精神之樂和物質之樂的高下優劣之分,這與狄更斯借助小說情節設置,凸顯物質主義導致的精神荒蕪和婚姻不幸,具有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我們不妨看看《艱難時世》中,功利主義者葛擂硬和資本家龐得貝的一次正面交鋒。露意莎婚姻的不順遂促使葛擂硬認真反省了自己的教育模式,從而調整了對待女兒的態度。為化解女兒的婚姻危機、緩和她和丈夫的關系,葛擂硬試圖勸說龐得貝更為體貼地對待露意莎的情感訴求。正是在這次交談中,功利主義者篤信的“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原則”和商業資本家執持的“物質至上”原則發生了激烈的沖撞。葛擂硬承認自己對女兒性格的不了解,意在從精神層面做出補救。為此他與龐得貝交涉道:“我想露意莎的性格有許多部分是——是被我們粗心地忽略了,因此——因此她性格中的這些部分也就從壞的方面去發展而使她走入歧途。我——我要向你建議的是——要是你肯幫我設法,任憑她自由地發展她的好天性,溫柔體貼地鼓勵她讓她去發展——這樣做對我們都有好處。”[12]267
然而,龐得貝的答復中卻充斥著將婚姻物質化的粗鄙觀念:“只要一個人告訴我什么富于想象力的本能,不管是誰,我就知道他用意何在。他的意思是想用金調羹吃甲魚湯和鹿肉,想坐六匹馬的馬車。這就是你女兒想的東西。”[12]268
在這場婚姻精神性和物質性的交鋒中,葛擂硬的立場和態度較之前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他雖然仍以功利主義的“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原則為立足點,以“對我們都有好處”為行事的目標;但當他認識到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只能招致不幸時,也適時地調整了自己的立場,改變了先前執持的觀點——“人從生到死的生活每一步都應是一種隔著柜臺的現錢買賣關系”,[12]315并開始關注女兒的情感需求。他的改變印證了穆勒的申辯之辭,證實了功利主義學說與精神之樂的兼容性。然而,龐得貝慣于以商業視角考量問題,以物質利益衡量得失。在他眼中,所謂的情感需要只不過是攫取物質利益的托詞,婚姻的實質不過是“用金調羹吃甲魚湯和鹿肉”,夫妻琴瑟相調比不上“坐六匹馬的馬車”的舒服愜意。正是這種立場的殊異決定了翁婿兩人的決裂,而他們的決裂也正代表著功利主義者與物質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從這樁婚姻的走向上來看,龐得貝固守物質主義立場,使得他與露意莎的婚姻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最終因為難以為繼而破碎,這種結局無疑是對所有相關方傷害最大的一種情節設置;在極其重視家庭完整性的維多利亞社會里,這一情節更是起到了警醒世人的作用,傳遞了小說家批駁“物質至上”,追求情感和諧、人性關懷的基本態度。在這一情節設計上,狄更斯走向了穆勒:兩人都在為功利主義原則與物質主義原則劃清界線的同時,強調精神價值的重要性。而葛擂硬的轉變也正契合了穆勒的判斷:功利主義者最終要在精神之樂中才能真正尋求到“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
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 Culture and Society,1958)一書中,將穆勒的立場界定為“拓展了的、人性化的功利主義”[7]71;而將狄更斯的態度概括為,小說家在秉持善良、同情心、包容等人本價值的基礎之上,對以葛擂硬為代表的功利主義者加以抨擊。[7]101-102然而上述分析卻為我們揭示了兩人看似殊異立場下的內在一致性。阿爾圖賽( Louis Althusser)認為,科學讓我們獲得關于對象狀況的概念知識,使我們認識到意識形態;藝術讓我們獲得關于對象狀況的經驗知識,“看到”和“感覺到”意識形態。[15]穆勒和狄更斯在《論邊沁》《功利主義》和《艱難時世》中,分別以哲學論證和藝術再現的形式建構了共同的情感結構,對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予以回應、反撥和修正。穆勒以一名功利主義信徒的身份,試圖拓寬功利主義學說的內涵,彌合其缺陷;而狄更斯通過敘事結構、人物刻畫、情節安排等藝術手法,巧妙地傳達了一個具有反哲學傾向的文學家對功利主義哲學的反思。二者一為哲學思辨,明晰而嚴謹;一為文學建構,具體且感性。在形式上各有特色,在根本立場和根本目的上卻殊途同歸。從跨越文學和哲學兩界的共同情感結構中,我們不難讀解到功利主義思潮下,維多利亞知識分子輾轉尋求出路的困頓、艱辛、睿智和洞見,以及這些思想的火花如何匯聚到一處,轉變為同一個強勁而有力的聲音。
參考文獻:
[1]FORD G H.Dickens and His Readers[M].New Jersey: Princeton UP,1955: 88-92.
[2]BOWEN J.Dickens and the Force of Writing[M]/ /BOWEN J,PATTEN R I.Palgrave Advances in Charles Dickens Studies.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6: 259.
[3]WILLIAMS R.Marxism and Literature[M].New York: Oxford UP,1977: 132.
[4]WILLIAMS R.The Long Revolution[M].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1961: 64.
[5]閻嘉.情感結構[J].國外理論動態,2006( 3) : 60-61.
[6]邊沁.論道德與立法的原則[M].程立顯,宇文利,譯.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2009: 25-26.
[7]WILLIAMS R.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M].New York: Doubleday&Company,1960.
[8]穆勒.論邊沁與柯勒律治[M].白利兵,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穆勒.功利主義[M].徐大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WARNOCK M.Introduction by Mary Warnock[M]/ / WARNOCK M.Utilitarianism and On Liberty.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 9-10.
[11]GENETTE G.Narrative Discourse[M].LEWIN J E,trans.Ithaca: Cornell UP,1983: 228.
[12]狄更斯.艱難時世[M].全增嘏,胡文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13]哈特.導言[M]/ /邊沁.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時殷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6.
[14]SCHLICKE P.Hard Times[M]/ /SCHLICKE P.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New York: Oxford UP,1999: 269.
[15]馬海良.文化政治美學——伊格爾頓批評理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41.
(責任編輯周芷汀)
The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Hard Times,Utilitarianism and On Bentham
MIN Xiaomeng
( School of Humanities,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Beijing 100876,China)
Abstract:In Hard Times,Utilitarianism and On Bentham,Charles Dickens and John Stuart Mill responded separately to Utilitarianism put forward by Jeremy Bentham.Their seemingly opposing arguments actually share some common ground.Both of them attempted to modify utilitarian doctrines by advocating individual rights,objecting to the mechanical method of calculation and emphasizing spiritual happiness as against sensual pleasures.Their arguments manifest the same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their response to Utilitar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bjects,methodology and judgment of value.To some extent these structures of feeling reflect how Utilitarianism was received and responded in the literary circle,hence provide a sample study on cultural pattern and ideological formation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Key words:Dickens; Mill; Utilitarianism; structures of feeling
作者簡介:閔曉萌( 1983-),女,湖北孝感人,北京郵電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
*收稿日期:2015-01-04
中圖分類號:I109. 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35( 2016) 01-002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