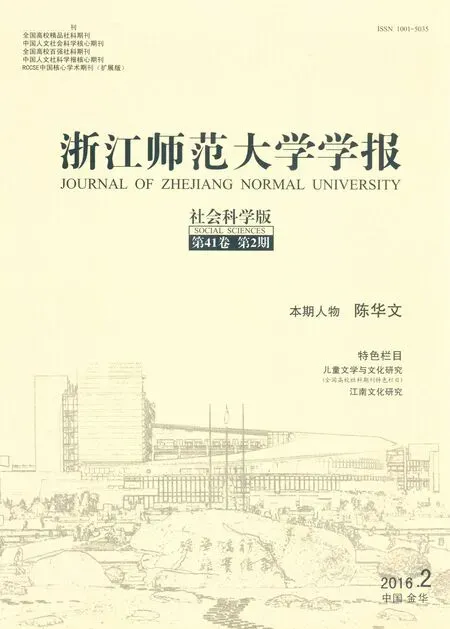破、立、持:《莊子》生死觀的“三段論”
王 錕, 邵林凡
(浙江師范大學 法政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
破、立、持:《莊子》生死觀的“三段論”
王錕,邵林凡
(浙江師范大學 法政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摘要:與以往研究不同,文章把《莊子》一書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分析,認為《莊子》書中的生死觀內涵著“破、立、持”三段論:“破”的階段以“物化”對世俗的生死觀進行摧毀,“立”的階段以不滅之“我”的肯定來建立積極的生存觀,而“持”的階段以“人故無情”的闡明使 “我”在“物化”的過程中保持對生死不作是非、好惡的念頭。“破、立、持”三段論既區別又融貫,構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死觀。
關鍵詞:《莊子》;生死觀;物化;我;無情
如何看待生死,一直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共同話題。對生死的哲思是《莊子》一書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該書最深邃、最迷人的地方。對《莊子》生死觀的討論,學界觀點不一。本文與學界的不同之處有兩方面:就內容而言,學界探討多集中在“物化”[1]61(即本文所謂“破”的方面)的研究,而對后兩個方面,即不滅的“我”[1]381(即本文所謂“立”的方面)和“人故無情”[1]121(即本文所謂“持”的方面)鮮有涉及。就文本而言,本文并不嚴格區分為內、外、雜篇,而是將《莊子》一書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融匯詮解。當然,我們并不否認《莊子》的生死觀存在著較為獨立的幾個方面,只是力求在邏輯上對其進行貫通,考察其是否存在較為融貫的系統。
一、“物化”——破的階段
“物化”是《莊子》生死觀的主要組成部分。涂光社先生說:“‘物化’的要義是,宇宙萬物在永恒的運動變化中,萬物以至各種生命個體雖然各具形質,但都是互相轉化的某個階段的一個暫時的存在形態。” “對于人來說,‘化’常指由生而死化為他物的變異過程。”[2]事實上,“物化”概念在《莊子》中至少有三層含義:首先是化為他物的意思,即上文涂光社所指的“物化”;其次是萬物化育的意思,同于《老子》37章里的“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3]中的“物化”;最后是隨波逐流而被外物干擾的意思,如《天地》篇中所說,“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1]226“物化”的這三層含義主旨是“化為他物”,這也是上述涂光社所說的。筆者采納他對“物化”的定義來討論《莊子》的生死觀。必須指出,除了“物化”概念,《莊子》生死觀中還有與之類似的其他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氣變”[1]334和“萬化”,[1]381因此有必要澄清“物化”與“氣變”“萬化”的關系。“物化”強調的是“化”的結果,即由一物化為他物。“氣變”強調的是“化”的承載者,即氣,所謂“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1]334也就是說,生死是氣的聚集與消散而已,氣是這一變化過程的承載者。而“萬化”強調的是“物化”過程的恒久無息的特征,所以用了“萬”字來強調這一特征。本文將根據具體語境或使用“物化”,或使用“氣變”,或使用“萬化”來闡述相關內容,但后兩個概念可以歸納于“物化”這一概念之下,所以“物化”概念在《莊子》中是最主要的。
在《莊子》中,“物化”(一物化為他物)的方向具有各種可能性。比如《大宗師》里說:“反覆始終,不知端倪。”[1]148“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1]144也就是說,“物化”的過程具有不確定性,不能保證下一次“化”所造就的就是人而非他物。“物化”的這種可能性消除了人與他物之間的價值的不平等,在“物化”中,一切之“化”都有可能,人并不具備優越性。所以《大宗師》說:“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1]145
總而言之,莊子認為生死是一個轉化的過程,雖然死后不一定再一次轉變為人,但死后有生,生后有死,生死相扣若環,生是向死的狀態,死是向生的狀態。因此生中有死的潛在,死中有生的潛在,基于這樣的認識,莊子認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1]35“方”體現了人生的短暫,也體現了生死其實并無本質的區別。人的一生在“物化”之中,不過是一環,所以莊子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1]397但是莊子并不是泯滅生與死的區別,他只是將生與死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考察,放在“物化”中去考察。在這種背景中,生和死的那種不平等的價值被拉平了,人與他物的不平等的價值被拉平了。
值得注意的是,學界關于“物化”的論述通常是將其劃分為幾個方面并分別加以探討的,即“物化”大致歸類為:必然的生死觀、氣變的生死觀、道一的生死觀、超越的生死觀。這種探討并沒有進一步去說明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筆者認為,這幾個方面實際上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是一個整體的幾個側面,而非莊子不同時期的不同思想或逐層遞進的思想。因為,氣變的過程本身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它是自然界不可逆的過程,氣變觀只是強調了這一過程的活動主體是氣。而這一過程的結論則是生死無貴賤之別,不必執著,即以道視之,萬物齊一。換言之,根據氣變的客觀必然過程所得出的主觀結論是道一的生死觀,而道一的生死觀本身又是對生死的超越。所以,《莊子》生死觀的這四個方面實際上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如果說前二者偏重于對自然的客觀方面的描述,那么后二者則是根據描述所得出的主觀方面的結論。這四個方面合而為一,則是本文所謂的《莊子》生死觀中“物化”的方面。
綜上,《莊子》生死觀的根據是“氣變”,客觀結果是“物化”;據此而得出的主觀結論是齊生死,齊萬物與人;最終目的是要實現超越生死、看破生死,不再執著于生死。
除了上面已經提過的“物化”“氣變”之外,《莊子》的生死觀中還存在其他內容。從邏輯上講,取消了生與死的價值的不等價,取消了人與他物或萬物之間的不等價,剩下的等價就能夠使我們看破生死嗎?價值的逝去難道不會造就一片虛無嗎?從文本來看,《莊子》中的生死觀也確實不止于此。除了把生與死、人與萬物之間的價值等價之外,《莊子》某種程度上在這種拉平的范圍內又重新建立起去面對“物化”的勇氣,使人樂于去“化”去“變”。而這種勇于、樂于去“變”去“化”的東西正是變中之不變、化中之不化。這個不變不化,就是——“我”。
二、不滅的“我”——立的階段
不滅的“我”是《莊子》生死觀中對“物化”的進一步深入,《莊子》對這方面的論述并不直接、明顯且涉及不多。雖然不多,但在以下的文字中,我們仍能強烈地體驗到《莊子》為這個充滿了變數與不確定性的“物化”所注入的永恒的主體:
《田子方》:“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1]378又說:“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1]381
《德充符》:“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1]104
《大宗師》:“假于異物,托于同體。”[1]148
《刻意》:“圣人……其神純粹,其魂不罷。”[1]292-293
《知北游》:“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1]407
…………
從“不忘者”“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守其宗”“托于同體”“其魂不罷”“一不化”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莊子》強調在變化不息的“物化”之中存在一定的不變或永恒。但是這個永恒到底是什么?其具體的規定卻似乎很難由現存的這些文獻中得出。依據《莊子注疏》中郭象與成玄英對這幾句的解釋,我們似乎可以認為,這個永恒的東西,即是一個主體——“我”,即使在《莊子》那句“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中也鮮明地體現了這一觀點。郭象注“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時說:“不亡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1]378可見這個不變的東西正是——“吾”。
那么這個“我”是如何能夠看破生死的呢?筆者認為,雖然在“物化”之中,形體發生了變化,甚至是根本的改變,但是無論變作什么,都有一個主體,即“我”。縱然這個“我”與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之間不能保持任何記憶上的連續性。正如郭象所言:“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1]381也就是說,每一個生物它都是具有自我肯定性的,如《大宗師》中說:“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于淵。”[1]152換言之,無論“物化”為什么生物,都可以自得其樂,每一生物都有其自我持存的本性。所以,萬物都具有一個“我”,即使它的形態和記憶都發生了徹底的洗牌。這個“我”不是一個小我,即個體的我;也不是一個大我,即集體的我。“我”既指每一個個體,指“萬化”當中的每一個個體,也指每一個體中所體現著的個我,即每個個我對自己個體或類的肯定。所以“我”是小我中的大我,大我中的小我,集二者為一體。或者換種方式也可以說,《莊子》的“我”重在形式上,即每一“我”所具有的自我持存的規定性上,而非某一具體的內容的“我”之上。
在這一觀點上,《莊子》的觀點與世俗的生死觀有所相同又有所不同,相同之處在于世俗的戀生是因為“我”,《莊子》認為生死并沒有使我們失去什么,也是因為每一物化都有一個“我”。換言之,他們認為人生的可貴之處都在于“我”。然而不同之處在于,世俗的戀生只在乎此生此世的“我”,是一個“小我”,而《莊子》的“我”既是個體的“小我”,又是每一物化后的“我”,是一個“大我”。這一“大我”正是對物化恒轉不定之虛無感的克服。
《莊子》不滅的“我”的觀點在《齊物論》的莊周夢蝶中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莊周在夢中有一個蝶“我”,卻感受不到莊周“我”;當他醒來時,感受到一個莊周“我”,卻感受不到一個蝶“我”,雖然記得自己在夢中為蝶“我”,但無法再重復那種置身于蝶中的“我”了。但是,無論是蝶是莊周,都有一個“我”,莊子似乎由此悟出“我”既不依賴于蝶也不依賴于莊周,同時“我”既在于蝶又在于莊周。在這一點上,生與死是一致的。①生死轉化都將有一個“我”,俗世之人樂生惡死,只知道此生之“我”,而不知來生亦有“我”,萬化皆有“我”,雖非一“我”,然“我”不息也。在這個“我”中,筆者以為《莊子》似乎看出了每一個“我”都具有自我肯定性,既然此生的你肯定今生,你又何必擔心物化之后的你不會肯定那時的一生呢?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說:“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于淵。”[1]152正是這種化為一物則肯定“我”之所在之物的特點,在《莊子》看來是看破生死必然性及形體之不相續性的突破點。
對于這種具有不連續性的“我”,而又永遠不會消失的“我”,《莊子》用了兩個比方來說明這個道理。第一個即《養生主》中的“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1]70“指”和“薪”是“火”得以燃燒的載體,但火可以脫離載體而存在,在其他不同的載體上重新燃起,雖然重新燃起的不是原來的“火”。這與生死轉化的情況是一致的,形體雖異,但萬化皆有“我”,而“我”無窮,亦猶火之“不知其盡也”。第二個即《寓言》中“罔兩問于影”[1]500的故事。在這一部分想要說明影不待于火、日,猶蛇可以脫離蛻而存在,蜩可以脫離甲而存在。這個意思正如世俗之人以為有“我”必有此生此身,而不知“我”不待于此生此身。
通過這個在物化之中具有永恒性的“我”的自我肯定,使《莊子》在拉平了生與死的價值的區別、我與他物之間價值的區別之后,又不至于陷入虛無主義,陷入此生此世因這種萬化而變得毫無意義、毫無價值,墜入自我否定與消極悲觀的情緒中去。可是現在還面臨一個問題,如果看破生死必須通過以上兩個步驟,即對拉平生死價值區別的認識,對不變的“我”的認識,那么請問:是否能認識的才算看破生死,而不能認識的便不能看破生死?既然物化中的每一個“我”都不具有記憶上的連續性,那么如何確保下一次的“化”后之“我”也能夠認識并看破生死或者起碼有要去看破生死的想法呢?關于這一問題,筆者在《莊子》中找到了其生死觀的另一重要命題——“人故無情”。
三、“人故無情”——持的階段
《莊子》生死觀中的“人故無情”是對“物化”和不滅的“我”看破生死后所得到的主觀境界的保持。如果說“物化”重在對世俗生死觀的“破”,那么不滅的“我”則是重在建“立”莊子自己積極的生死觀,而“人故無情”則是對“破”與“立”所得到成果的保持,我們可以稱之為“持”的階段。
莊子與惠子有一段著名的“人故無情”的對話。在《德充符》中,莊子主張“人故無情”,而“道”和“天”只授“與”人以“貌”和“形”,并沒有使人“以好惡內傷其身”。[1]121-122在《田子方》中,老聃給孔子講了一些“死生終始將為晝夜”和“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1]381的道理后,孔子感慨說,老聃這么厲害的人物都需要“假至言以修心”,[1]381那么“古之君子,孰能脫焉”。[1]381孔子這里的問題,可以放入我們剛才的問題來理解,即如何使學到的《莊子》思想在下一次轉化中也能得到保持?老聃的回答是:“不然,夫水之于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1]381成玄英解釋道:“汋,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由修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夫何修為?自然而已矣!”[1]381也就是說,水的本性是清澈的,只要保持住,其實并不需要外加修煉就能做到。正是基于這種“本性”清凈的思想,莊子才會認為“人故無情”。
也就是說,人本性是好的,當然,這種好指的是:沒有多余的是非、好惡之心,這些好惡、是非之心正是莊子所謂的“情”。如果不受到污染,根本不用去看破生死,甚至連要看破生死的意向也不具備。正是這種“人故無情”的觀點,《養生主》中秦失才會批判那些哭老聃的人,倒不是如有些學者所解釋的,這些人的哭是假的、“虛偽”的,而是因為他們違背了“人故無情”的本性。這與“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而不哭,而民不非也”[1]285-286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莊子》看來,真正能看破生死的人連想看破生死的念頭也沒有。《賡桑楚》中說:“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是三者雖異,公族也。”[1]424-425從這段文字中,我們看出,“未始有物”的最高境界是看不出生與死的區分,將之合二為一。所以生死在某種意義上或最高境界上而言是不可說的。這種“不可說”的原因并不是說要靠直覺去悟而非用理智去理解,而是因為一說(這個“說”也包括“想”)則有“分”,分則不再是“一”,但又不能不說,所以《莊子》認為可以說到“三”。至于為什么只能說到“三”,這涉及《莊子》的是非觀,茲不贅述。這里我們只需要知道,在《莊子》看來,本性純潔的人并無必要去看破生死,因為純潔的本性對生死并沒有作是非、好惡式的區分。但是面對已經沉淪的世俗,《莊子》又不得不說,所以它只好說到“三”,但這一“三”畢竟還是與“一”具有本質的聯系的,所謂“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1]45亦如以上引文所言:“是三者雖異,公族也。”[1]425
總而言之,《莊子》認為,人本來就沒有是非、好惡之情,每一次“物化”之后的“我”如果不受后天的污染,那么他便不需要獲得那些看破生死的認識,所以也不會去區分生死的價值。只有對于已經區分生死的不同的價值的社會,只有靠對生死“真相”的理解和認識才能做到看破生死,對上古那些純樸之世或人來說則不需要;而每一次“化”的“我”從開始或生命的起點來說,都是“混沌”的,不需要去看破生死的,所以我們需要保持住這份純潔。
四、總結
根據文章的論述,我們可知:首先,莊子將生與死、我與萬物在世俗那里不平等的價值放到“物化”中去拉平,使它們等價。甚至可以說,這種等價使今生今世變得渺小化。其次,緊跟著渺小化的則是在不確定的、存在各種可能性的“物化”中注入一個確定的永恒的“我”,而這個“我”使今生今世變得具有可忍受性,甚至帶有可歡可樂的性質。最后,為了保證前兩方面,即對生死的渺小化與萬化有“我”的可貴性認識,《莊子》認為“人故無情”,認為純真人并不需要多加反思,便能以自然的心態順應“物化”。也就是說,前兩個方面的內容是對那些看不破生死的人或社會說教用的,這種說教并不需要在下一次“化”中得到延續才能使“萬化”中的每一個“我”都能看破生死。
綜上所述,保證《莊子》看破生死的其實有三樣法寶:即生死、物我價值的平等化,這是“破”的階段;萬化有我而使萬生萬死變得可以忍受,即萬化有我的可貴性,這是“立”的階段;以及最后“人故無情”對前二者的保證,即人的本性并不需要通過后天的認識來看破生死,這是“持”的階段。此三者所構成的是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有機整體。如果只有“物化”,而沒有不滅的“我”,則人生終將陷入無法自救的必然性的虛無中去,而“人故無情”則使生死實現忘的境界,不需要通過后天學習來獲得。所以,《莊子》生死觀最終可以歸結為“破、立、持”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注釋:
①莊周夢蝶這段文字中剛好有“物化”二字,而這一術語在《莊子》中是與生死相關的。
參考文獻:
[1]郭象,成玄英.莊子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涂光杜.莊子范疇心解[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77.
[3]陳鼓應.老子注譯及評介[M].北京:中華書局,1984:209.
(責任編輯吳月芽)
Breaking, Establishing and Sustaining:“Syllogism” ofZhuangzi’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WANG Kun,SHAO Linfan
(CollegeofLawandPoliticalScience,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bstract: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studies Zhuangzi as an organic whole, and argues that there is the connotation of “breaking, establishing and sustaining” syllogism in Zhuangzi’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At the “breaking” s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destroys the secular view of life and death. At the “establishing” stage, the imperishable “I” is used to create a positive view of survival. At the “sustaining” stage, the elaborations of “people having no feeling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keep people away from holding such ideas like being right and wrong, likes and dislikes about life and death. The three stages are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coherent, constituting a uniqu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Key words:Zhuangzi; view of life and death; transformation of things; I; no feelings
中圖分類號:B2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35(2016)02-0033-0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論現代新儒家對懷特海哲學的紹述和融合”(12YJC720035)
作者簡介:王錕(1973-),男,甘肅天水人,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教授,史學博士;邵林凡(1987-),男,浙江溫州人,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