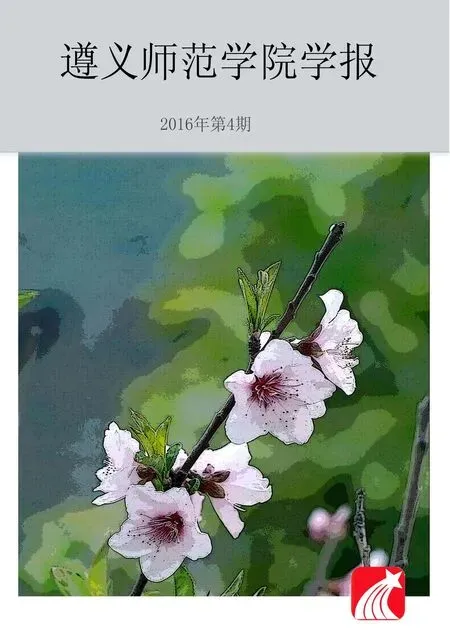也談土司文化的內涵
彭福榮,李 娟
(長江師范學院烏江流域社會經濟文化研究中心,重慶涪陵408100)
也談土司文化的內涵
彭福榮,李 娟
(長江師范學院烏江流域社會經濟文化研究中心,重慶涪陵408100)
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推行過程中,由國家政治精英、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及世代民眾共同創造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總和。制度層面包括土司制度及支撐土司政治的歷朝羈縻制度、宗法制度和民族傳統制度、民間習慣法等;政治層面包括土司政權的治所、衙署、運行機制和土司及族裔的生活起居、飲食服飾、社會交往及審美活動等;教化層面包括土司文治教化的活動、場所、器物、人物、事件及成果,民間文化層面包括民情風俗、生活經驗、生產知識、審美情趣和社會理想等并表現在生產勞動、生活習俗、歲時節慶、方言土語、故事傳說、歌舞戲劇、婚葬嫁娶、人生禮儀、社會交往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土司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區域性、民族性、等級性、政治性、倫理性、等級性及性別性特征,值得深入研究。
土司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教育文化;民族民間文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余嘉華先生研究云南“木氏土司的詩文成就”,首提應重視“土司文化的研究與評價”。[1]隨后因土司制度與土司問題等研究的深入,“土司文化”漸成熱詞,但對其存在不盡相同的認識。筆者以“土司文化”為“主題”,在中國知網檢索出150余條相關記錄,主要是關于土司制度與土司政治、土司時期文治教化與土司文化遺產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少量會議與論壇的綜述也提及土司文化。截至2016年上半年,“土司文化”至少被李世愉、羅維慶和田敏等近十位專家學者撰文研討。筆者不揣妄陋,試圖論述土司文化的內涵,以磚引玉,請予指正。
一、土司制度文化
學界經二十年研討,基本達成“‘土司文化’根源
于土司制度,但土司文化是從土司這個概念引伸出來的”共識。從發生角度看,元朝吸取秦漢至唐宋羈縻統治的經驗教訓,將“齊政修教,因俗而治”的成功治策推及西南等少數民族地區,并上升為“大一統”歷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體制下,整合少數民族和治理民族地區的國家制度之一,系數百年土司政治的根本,為土司文化積淀傳承開啟了道路。“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的產物”,是土司制度概念的延伸和拓展,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2]
學界長期用力揭示中國土司制度的內涵、源流與價值和西南等地土司政治的興起、廢止和影響等問題,全國視角研究中國土司制度源流變化的代表成果主要有佘貽澤《中國土司制度》、龔蔭《中國土司制度》與《中國土司制度史》和吳永章《中國土司制度淵源與發展史》等,斷代研究土司制度的代表成果主要有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論考》、成臻銘《清代土司研究:一種政治文化的歷史人類學觀察》等,區域研究土司制度的代表成果主要有吳永章《明代貴州土司制度》與《清代廣西土司制度》、藍武《從設土到改流:元明時期廣西土司制度研究》等,李良品《明清時期西南地區土兵制度與軍事戰爭研究》探討土司時期軍事制度。余嘉華先生開啟了文化視角的土司研究,成臻銘指出“土司文化:民族史研究不能忽略的領域”,李世愉先生認為“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推行過程中出現和存續的一種歷史現象”,是土司制度實施的產物,[3]二者屬于遞進因果關系,即沒有土司制度也就沒有土司文化。
筆者曾把“石砫土司制度與社會控制”作為石砫土司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認為土司制度包含于土司文化。因為制度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并要求人們遵守的法令、禮俗等,主要包括國家行政管理體制、人才培養選拔制度、法律法規制度和民間禮儀俗規等,具體形式有習慣、道德、法律法規、戒律、規章、條例及其他正式與非正式約束及實施機制,具有調節人際社會關系的作用和價值,是與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并提的重要概念,被應用到社會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等學科領域。制度與文化相互統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不存在沒有文化價值的制度和沒有制度形式的文化。成臻銘從政治文化角度整體觀察“清代土司”,其成果《清代土司研究:一種政治文化的歷史人類學觀察》包含清代土司制度,也把清代土司制度當作清代土司文化的內涵。劉興國把土司制度納入土司文化來觀察,其文《明代達州南昌灘土司文化》關涉明代達州南昌灘土司的歷史沿革、土司制度興廢、南昌灘位置和南昌灘土司即石鼓鎮守等。[4]事實上,土司制度是中華民族制度文明的重要部分,是元明清等朝根據西南、中南和西北等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狀貌,吸取歷朝國家整合與社會治理的經驗教訓,在“大一統”歷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體制下,制定和實施的地方政治制度,是旨在推進國家權力滲延、強化王朝統治的治理策略和民族政策,成為國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構成,在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及中國國家“多元同創”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深遠影響。
西南等地民族眾多,歷史時期形成的民族傳統制度乃至民間習慣法和元明清時期的中原文化匯融借采,共同維系王朝的國家統治和地方的土司政治。宗法制度和民族傳統政治制度如彝族“九扯九縱”及家支制度等具有和國家土司制度與地方土司政治融通支撐的價值,也是元明清等朝維系地方土司政權和各民族土司政治的重要制度,也是土司制度文化的重要內涵。忻城莫氏土司文化源于元明清等朝的土司制度,忻城土司文化是多種制度文化的結晶。[5]因此,土司制度文化作為土司文化的重要構成,既包括元明清等朝創設實踐的土司制度及以前歷朝的土官羈縻制度和作為意識形態的宗法制度,也包括土司時期西南等地民族傳統制度和民間習慣法,創造主體是歷朝國家政治精英、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及世代民眾,是土司文化得以創新發展的制度基礎和支持。
二、土司政治文化
土司制度從根本上說,是元明清等朝整合西南等少數民族和國家強化民族地區統治的制度。受自然人文環境、民族構成及交通狀況差別等影響,各族土司在履行職位承襲、軍事征調、朝貢納賦及崇儒興學等義務中表現出的土司政治差別明顯。專家學者研究國家關涉土司的重大歷史問題、西南等地土司治理及土司關系等,土司政權的治所、衙署及運行機制和土司及其族裔的生活起居、飲食服飾、社會交往及審美活動等被視為土司政治文化。它具有民族性、等級性、貴族性及家族性特征,體現王朝國家時期中華民族整合、邊疆事務治理的制度文明和政治智慧,包含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認同,是深化中國國家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認同和民族區域自
治制度的重要資源。[6]
土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和王朝國家的土司制度與民族地區的土司政治緊密相關,包括建筑、雕塑、繪畫、寺觀、神像、飲食、音樂、藝術等復雜方面,土司及其族裔和各族土民共同參與文化創造。“土司學的研究對象是土司文化,土司學就是研究土司文化形態及其轉化規律的專門學”,土司文化在政治層面包括“土司政治意識形態、土司政治行為、土司政治制度和土司政治體系”等方面,[7]成臻銘《清代土司研究:一種政治文化的歷史人類學觀察》等成果從政治文化角度觀察認識“清代土司”問題,是研究清代土司文化的重要成果。土司城搬遷折射土司的命運變化和土司區的盈縮變動,各族土司在建筑選址和城市規劃方面具有迷戀風水、以內馭外的政治文化傾向,倫理型建筑體系一定程度體現土司的政治制度文化、政治行為文化與政治心態文化,是土司文化的核心構成之一。[8]貴州遵義的播州土司海龍屯遺址、湖北咸豐的唐崖土司城遺址及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等在2015年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表明國內外都高度認可三處遺址所顯示的土司政治文化。現貴州岑鞏的木召古城被目為“元至明早期田氏思州司城”,由沿江安撫司等土司規劃并組織土民筑成,是“元明思州田氏土司的政治中心”,在明清時期是政治、軍屯、農耕與商業的結合體,政治、軍事和經濟氣息濃厚。[9]
因此,土司政權構成與運行體制及土司族裔生活居飲與社會交往等是土司政治文化的重要內涵。廣西莫氏土司自明萬歷莫鎮威開始,繼承民族傳統建筑習慣,吸收中原漢族建筑的精華,設計、構建和擴建其衙署、祠堂、府第、官塘、陵園、三界廟、關帝廟等土司政治建筑群落與土司生活居飲、社會交往所需的土司庭院館閣等,是廣西莫氏土司政治文化乃至壯族土司文化的鮮活例證,創造主體是國家制度層面的政治精英和各民族的上層分子及世代土民。
三、土司教育文化
元明清三朝將土司制度作為對西南等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國家整合的手段和策略,十分重視學校教育和中原文化傳播在“以文化民”和文化一體中的作用,獎勸少數民族地區的科舉教育,推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及中華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10]受這一政策的影響,西南等地各族土司為鞏固和擴大自身統治而致力于文化建設,包括崇儒興學、變風革俗、交游唱和,極大影響了土司文化的內涵和品位。學界二十年來逐漸關注各族土司的文化建設,揭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與地方民族文化的二元互動,發掘土司制度及地方土司政治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認同各族土司文治教化的活動、場所、器物及成果等的文化屬性,西南等各民族土司文學及土司時期學宮、書院等教育及相關人物、事件、器物等凝結深厚的人文底蘊,屬于土司文化的重要范疇和基本內涵。
(一)土司文治教化
土司文化是中原文化、民族文化交流互動的成果,由王朝國家與各族土司共同促成。[11]受王朝意識形態影響和為融入國家主流文化,西南等地各族土司堅持民族宗教信仰,接受中原文化影響,倡導儒家道德倫常,推動釋道等宗教的傳播,其崇儒興學和倡修寺廟宮觀及交結僧侶道徒等被目為土司宗教文化,體現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特征和形成過程,是今土司文化遺產的內涵構成。
西南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政治長達數百年,國家和土司的文化建設給歷史形成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施加影響,土司文化得以形成、積淀和傳承,并有時代、民族和地域的烙印。酉陽土司“發動科舉教育”,“變革民情風俗”,“交結文人墨客”,其結果是“培養封建人才”,“提高文化素質”,“促進文化交流”,學宮司學、寺院宮觀等得以興建,土司文學得以興起,民情風俗得到變革,對各族土民的影響深遠。[12]播州土司推行“以漢文化和儒家學說為主的文化教育”,其崇儒興學的場所如播州宣慰司學,人物如楊粲,成就如民風變革等,都屬于土司文化的范疇,[11]遺址遺物、詩文佚事傳說及道德倫理觀念等是土司文化的內涵,被稱為土司教育文化。土司教育文化涵蓋土司的教化機構、興學理念、研習內容、教育條規及文史作品等方面。[6]湖廣土司及其族裔學習推廣“漢文化”,興辦學校,結交漢區知識分子,“發展本民族文化并引入新內容”,“把漢族先進文化引入自己文化體系內”。[13]因此,土司文化淵源于土司制度,和土司文治教化活動相關,表現在制度設計、意識形態和生活習俗等方面,影響到部分而非全部的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
西南等少數民族堅守原始宗教信仰,接受中原文化英雄,在土司政治背景下推動佛教、道教乃至伊斯蘭教的傳播,被視為“土司宗教文化”,其創造主體
包括各族土司及其族裔和歷代土民。土司宗教文化包含和土司制度、土司政治有關的道教、佛教、伊斯蘭教與少數民族原始宗教,多元多態的場所、科儀、神族、信徒及宗教民俗活動的影響。[6]武陵山區的土家族土司為強化統治,神化并提升其祖先神為土民共同信奉的神靈,大搞土王崇拜;同時修建宗廟政教場所,如祠堂、寺廟、宮觀;參與宗教活動,刊刻宗教科儀經籍。總之土司宗教文化積淀深厚。
(二)土司文學創作
西南等地各族土司及其族裔獨專文教權利,逐漸具備運用漢族語言文字進行創作的能力,出現代不乏人的文學世家現象,被視為“土司文學”,是土司文化的重要方面。土司文學和土司制度推行、國家權力滲延、中原文化傳播、崇儒興學推進及西南等地的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變遷緊密相關。與之相關的事件、人物、成就及規律、經驗等都是土司文化重要的內涵。
從學術史角度看,西南等地各族土司及其族裔的詩文作品一開始就作為土司文化的經典內涵被加以研究。除云南納西族木公、木高和木青等詩文成就外,西南等“各地土司有大批詩文集及學術著作傳世”,“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植根于豐厚的民族文化。如云南巍山左氏數代詩文傳世,華寧祿氏工尚書法文藝,又結交名流,姚安高氏興學修志塑像,《妙香國詩草》及《雞足山志》等著作“代表了當時當地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直接豐富了該民族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土司文學在土司文化、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與土司文化共同呈現民族文化“多樣性”與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一體性”的辯證統一。筆者曾專門討論“石砫土司的文治教化”與“石砫土司文學”,認為“土司文學是歷史上各族土司及其家族成員創作的文學,具有作者家族性、題材封閉性、體裁失衡性、技巧成熟性等特征”,是民族地區在元明清時期文化建設的成果,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與中原文化傳播與學校教育共同作用的產物。[14]鄂西南容美土司文學“是土家族文化與中原漢文化交匯融合的文學碩果”,系“容美田氏土司文人”學習中原文化、提高漢文學修養、交流文藝創作理念技藝,運用漢族語言文字創作的結果,是歷史時期民族地區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和鄉俗民風的藝術再現,文化價值豐贍,對民族文化融合的語境、途徑、方式及其成效有啟示作用和學術意義。[15]因此,容美土司文學是明清時期土家族文化與漢文化互動的碩果,“漢文化與土司文化”的雙向互動在鼎革亂世尤其突出。[16]
西南等地各族土司及其族裔飽含宗族深情纂述家族源流功業、領地風土人文及經史研讀體會,作品因內容表達的情感性、語言運用的技巧性及體裁形式的傳統性等,分屬土司文學“文史類”和“純文學類”等類別。土司文學的“純文學類”體裁主要包括詩歌、散文及詞等,創作呈現增多趨勢,以詩歌最為成熟最具影響;“文史類”特殊形式主要指家族譜牒、地方史志和公文檄書等,撰著也日趨豐富。[17]P166土司族裔及土民精英纂修的家譜、方志等是土司文化的重要構成,如容美土司《田氏族譜》、施南土司《覃氏族譜》、永順土司《彭氏族譜》等,具有補正史籍的意義。土司及其族裔的史學撰著更具文化意義,如《永順宣慰司志》、《卯洞安撫司志》、《石砫宣慰司志》等,研讀經史的成果還有永順土司彭明道《逃世逸史》、容美土司田舜年《二十一史報要》和《二十一史補遺》等。思州土司文化還有相關土司的史籍、方志、族譜、史傳謠諺、民間傳聞和地域名稱。[18]
由此而論,土司文學為土司文化的核心內涵之一,深受土司政治的影響,在中原文化傳播與崇儒興學、科舉取士等國家策略的推動下,土司及其族裔運用漢族語言文字創作而成,并在交流切磋中得到提高。
四、土司民族民間文化
在土司制度下,為維系地方統治,進行朝貢納賦,各族土司致力于經濟開發,借助漢族地區先進的技術、物種和工具,推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形成獨特的社會形態、生產關系、交往方式和生活習俗。受土司制度規約和土司政治的影響,西南等地各族土民的生產勞動與社會生活及由此形成的民情風俗、生活經驗、生產知識及審美情趣和社會理想,也是土司文化的重要內涵,被稱為“土司民族民間文化”。土司民族民間文化還包括方言、民間故事、神話傳說、戲劇舞蹈及節日、婚葬嫁娶等多樣形式,內涵豐富,是我國邊疆地區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重要部分,[6]直接或間接地反映民族地區在土司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面貌。
西南等地大多生態脆弱和貧瘠難耕,各民族世代傳承的地方性生態知識,在土司時期蘊含著豐富的生態美學思想,是國家推行土司制度和延續土司政治的重要原因。[19]如廣西壯族土司文化與民間文
化相關者主要包括歌圩文化、社廟文化、審美文化、建筑文化、山水文化等。[20]土民的生產生活、游藝競技、歲時節慶、社交禮儀等打上了土司政治的烙印,時代性、民族性和區域性差異明顯。[5]西南等地各民族受土司政治的影響,服飾飲食、宗教信仰、人生禮儀、歲時節慶及方言、民間故事、神話傳說、戲劇舞蹈及節日、婚葬嫁娶等體現出民族性、地方性、時代性、等級性、禮儀性、場合性、季節性等特點,是今天邊疆地區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6]播州“土司文化是指生活在土司所統治區域內的少數民族在進入封建社會后,在土司制度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文化,是邊疆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民族民間文化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服飾、飲食、樂器、歌舞、宗教、器物、交際禮品、工藝產品、生活用具、生產工具等有形文化事象及流傳在大眾中的神話傳說、史傳謠諺、故事寓言、音樂舞蹈、節慶活動、民間習俗、人生禮儀、宗教祭典、習慣法規等無形文化事象,系“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歷史文化、藝術觀賞和科學考察等價值,[21]是黔北文化的組成部分。[22]藍利萍認為:土司文化的民族民間文化部分理應包括土司時期各族土民的生產生活用具等物質實體文化及國家土司制度與地方土司政治影響下的土民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審美情趣等精神虛體文化。[23]云南土司文化是云南境內各民族因國家土司制度與地方土司政治影響,形成和發展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總和,其民族民間文化部分表現在民居建筑、服飾、飲食、器樂、歌舞、宗教器物、交際禮品、工藝產品、生活用具、生產工具等有形文化及包括土司的神話傳說、史傳謠諺、故事寓言、音樂舞蹈、節慶活動、民間習俗、人生禮儀、宗教祭典、習慣法等無形文化。[24]永順老司城、遵義海龍屯、咸豐唐崖土司城等反映了土司時期人們的社會交往、生產生活、房舍建筑、音樂歌舞、歲時節慶、人生禮儀,承載著土司時期的社會結構、人際關系、審美情趣、價值觀念,“傳說故事、音樂戲劇、巫儺儀式、生產生活器具、牌坊石刻等展示著土司時期西南族群的社會文化面貌”。[25]東人達先生較早注意到土司文化的遺產價值,指出土司文化包括土司時期的民族民間建筑,戲曲如土戲與儺戲,歌舞如擺手舞與山歌,飲食,節慶如族年與趕年,墓葬如巖棺葬等方面。[26]
盡管部分專家學者站在民族民間文化世代累積的學理邏輯上,進行假想性學術判斷,但和國家土司制度與地方土司政治不相關涉的民族民間文化事象不應納入土司文化的范疇。筆者翻檢關于石砫土司和秦良玉的明清史料,甚少見到直接記載石砫土司政治與土家族儺戲、擺手舞、土戲、山歌、飲食、節慶、巖棺葬等關系的信息,這與言之鑿鑿的學術論斷或許存在研討和商榷的空間。[26]由于地域廣闊而環境封閉、人口有限而交通不便等原因,元明清等朝乃至西南等地各族土司難以形成橫到邊縱到底的統治框架,文化事象的歷時積淀與階段創新同時并存,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或并不完全與元明清等朝土司制度和西南地區土司政治相始終相關涉相重疊。因此,不加區分地將西南等地民族民間文化和國家實施土司制度與地方存續土司政治影響下的民族民間文化籠統混同等同,非惟有損科學研究的嚴謹,且并不一定符合事實。對此,羅維慶先生指出:土司文化依附于歷史時期的土司制度,“是民族文化的階段性反映”。[27]
五、結語
土司文化是最近二十年學術討論的重要話題,涉及西南等各民族及上層分子的國家認同、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是未來土司制度研究的學術前沿問題”,[28]“土司時期的文化建構、文化策略、文化生成、文化融合、習俗文化、地名文化以及土司文化保護與利用等”“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29]
爬梳代表性成果和吸收專家學者的智慧,土司文化概念可表述如下:土司文化依附元明清等朝創設實踐的土司制度和西南等地建立推行的土司政治,是由國家政治精英、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及世代民眾共同創造的物質與精神財富總和,制度層面包括土司制度及支撐土司統治的歷朝羈縻制度、宗法制度和民族傳統制度、民間習慣法,政治層面包括土司政權的治所、衙署及運行機制和土司及其族裔的生活起居、飲食服飾、社會交往及審美活動等,教化層面包括土司文治教化的活動、場所、器物、人物、事件及成果和土司及其族裔與各族土民推崇信奉的宗教信仰與神族科儀、修建的宗祠寺廟宮觀等政教場所、參與的宗教活動與刊刻的宗教經籍,民間文化層面包括民情風俗、生活經驗、生產知識、審美情趣和社會理想等并表現在生產勞動、生活習俗、歲時節慶、方言土語、故事傳說、歌舞戲劇、婚葬嫁娶、人生禮儀、社會交往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鮮明的時代
性、區域性、民族性、政治性、倫理性、等級性甚至性別性特征。“土司文化中的女性角色對土司文化性別建構以及在民族文化旅游開發中具有積極意義”,甚至轉化為傳統記憶符號。[30]
土司文化內涵豐富,形式多樣,價值突出,是當下經濟開發、社會發展、文化創新、遺產保護和學術研究應給予重視的對象和領域,其中包含的中華民族制度文明、中國國家整合和民族事務治理經驗、文化資源產業化價值和文化遺產保護等對促進中華民族團結繁榮與制度自信,強化中華文化、中國國家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認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創新學科理論等都具重要意義,值得深入研究。
[1]余嘉華.雪山文脈傳千古:兼談土司文化評價的幾個問題[J].民族藝術研究,1996,(2):38-45.
[2]李良玉.土司與土司文化研究芻議[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9,(3):132-134.
[3]李世愉.試論“土司文化”的定義與內涵[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16,(2):16-20.
[4]劉興國.明代達州南昌灘土司文化[J].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5,(4):34-38.
[5]莫軍苗.忻城土司文化的歷史源流與理性思考[J].綏化學院學報,2010,(3):71-73.
[6]萬紅.鄉土教育視閾下的土司文化及其價值[J].民族教育研究,2014,(6):102-106.
[7]成臻銘.論土司與土司學——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價值[J].青海民族研究,2010,(1):86-95.
[8]成臻銘.“以內馭外”:論清代土司城市建筑布局的政治文化傾向——以土家族區域為例證[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9,(6):8-14.
[9]葉成勇.關于貴州岑鞏縣木召古城的再認識——兼論思州田氏土司治所之變遷[J].地方文化研究,2014,(3):10-19.
[10]彭福榮.國家認同視野下的土司文教制度:烏江流域例證[J].廣西民族研究,2014,(4):138-142.
[11]陳季君.播州土司文化教育考述[J].教育文化論壇,2011,(6):103-107.
[12]劉小寒.酉陽土司文化建設述論[J].黑龍江史志,2009,(14): 19-20.
[13]段超,李振.略論湖廣土司的文化政策[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1990,(4):9-16.
[14]彭福榮.試論土司文學的特征[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9):228-234.
[15]胡紹華.論容美土司文學與民族文化融合[J].民族文學研究,2012,(1):137-146.
[16]柏俊才,趙星.明清之際容美土司文學及其文化互動[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6,(3):15-21.
[17]彭福榮.烏江流域土司時期文學探賾[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18]張旭.思州土司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以江口縣省溪、提溪司為例[J].銅仁學院學報,2014,(6):47-53.
[19]藍利萍.論土司文化中的生態美學思想——以廣西土司文化為例[J].廣西社會科學,2013,(11):174-178.
[20]王暉.壯族土司文化及其旅游開發價值概述——廣西民族文化與旅游開發研究之一[J].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2005,(1):75-78.
[21]況紅玲.開發利用遵義土司文化[J].四川旅游學院學報,2006,(4):51-54.
[22]禹玉環.遵義播州土司文化旅游資源開發探討[J].滄桑,2013,(2):155-157.
[23]藍利萍.論當代土司文化研究的文化生態環境[J].河池學院學報,2015,(1):23-27.
[24]自語.走近云南的土司文化[J].今日民族,2015,(7):6-12.
[25]葛政委.土司文化遺產的價值凝練與表達[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4,(5):8-12.
[26]東人達.三峽石柱土司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1):44-48.
[27]羅維慶.土司文化的邊際界定[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16,(2):21-24.
[28]李躍平.“第四屆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述要[J].民族學刊,2014,(6):88-89.
[29]李良品.第三屆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暨秦良玉國際學術研討會述略[J].中國史研究動態,2014,(2):71-72.
[30]謝秋慧.論土司文化中的女性角色研究[J].文學評論,2014,(10):291-293.
(責任編輯:魏登云)
A Re-study of the Connotations of Tusi Culture
PENG Fu-rong,LI Juan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y and Culture along Wujiang River Basin,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Fuling 408100,China)
Tusi culture,the totality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is created by national political elites,upper-class elements in minority groups and other grassroots people.System culture refers to Tusi system and other systems such as Jimi system,patriarchal system and folk habits which supported Tusi politics;political culture is the government’s residence,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the living habit,food,clothing,social activity and esthetic activities of Tusi people;educating culture includes the educating activity,place, container,person,event and result;and folk culture is the folk custom,life experience,production knowledge,esthetic interest and social ideal as well as their performance in labour,custom,celebration,and the like.Tusi culture has many features like salient,regionality, nationality,,politics,etc,which deserves to be looked at.
Tusi culture;system culture;political culture;educating culture;national folk culture
K03
A
1009-3583(2016)-0019-06
2016-05-12
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烏江流域歷代土司的國家認同研究”(10XMZ013)成果之一;長江師范學院“中國土司制度與土司文化研究創新團隊”建設計劃資助項目(2014XJTD04)
彭福榮,男,重慶涪陵人,長江師范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烏江流域社會經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長江師范學院文學院兼職教師,主要從事古代文學和西南土司文化研究。李 娟,女,重慶巫山人,長江師范學院文學院教師,主要從事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