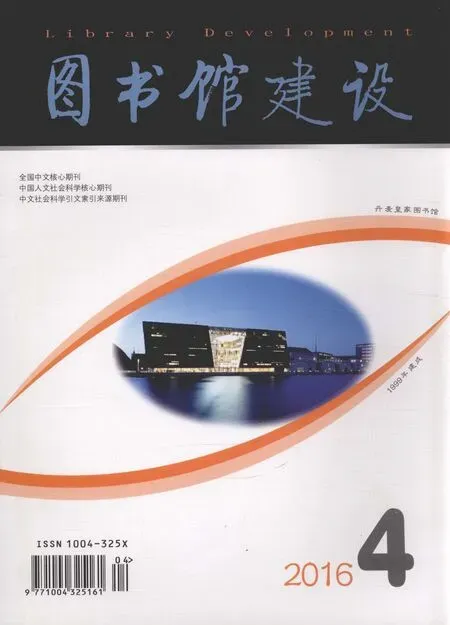歷史語境下圖書館權利意涵、實質的再思考*
魏建琳(西安文理學院圖書館 陜西 西安 710065)
?
歷史語境下圖書館權利意涵、實質的再思考*
魏建琳(西安文理學院圖書館 陜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圖書館權利是讀者自由平等地利用圖書館的權利”,這個界定存在認識盲點,需要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展開進一步的辨析與解讀。“圖書館權利”應溯源于ALA《圖書館權利法案》,《圖書館權利法案》是ALA在一個具體的時代背景下發表的宣示行業立場的聲明,聲明所宣示的“圖書館權利”的意涵實質是“思想言論自由”,它是西方傳統的基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權利文化”在圖書館活動中的具體表現。
[關鍵詞]圖書館權利 美國 《圖書館權利法案》 歷史語境
1 引 言
“進入21世紀后,我國圖書館界迅速掀起‘權利話語熱’,凸顯‘走向權利時代’的趨向”[1]。毋庸置疑,21世紀我國圖書館權利的研究是“中國圖書館學發生重大轉變的標志性研究之一”[2],不僅在理論層面“豐富了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完善了對圖書館社會功能和價值的理論解釋”[3],而且在實踐層面“指導了中國圖書館的公益回歸和服務轉型實踐,唱出了公共文化服務以保障公眾基本文化權益為目標的先聲。今天,當我們用歷史眼光審視新世紀以來我國圖書館事業乃至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發展進程時,當我們梳理和總結理論創新對事業發展的促進時,可以看到圖書館權利思想、理念研究和傳播的時代貢獻”[3]。
但是,由于“新世紀之前,圖書館權利研究在我國尚屬空白”[3],使得研究缺乏基礎,缺乏深厚的積淀,所以盡管十數年間的研究火花四射且異彩紛呈,但仍難以避免地留下了大量的認識盲點,甚至盲區。存在盲點和盲區,不僅造成認知的迷惘與困惑,而且會直接導致新世紀的圖書館文化服務實踐產生矛盾與誤區。因而,對權利話題的繼續探究,不僅是理論建設的必然要求,更是當前實踐活動的迫切需要。
圖書館權利究竟是什么?截至目前,業界似乎已達成共識,圖書館權利是讀者自由平等地利用圖書館的權利。可是如果深究,這個權威且得到普遍認同的界定,仍有許多讓人困惑迷茫之處。依據法學、政治學等領域的研究結論,如果存在一項權利,就必然有權利主體(權利人)、權利客體、義務人、道德法律依據、救濟渠道等一些權利要件[4]。然而,到目前為止,對于圖書館權利要件的界定仍然模糊。截至目前,業內的探究似乎大多立足于哲學意義的宏觀概括和法學意義的文本分析兩個層面,而結合具體語境對權利要件具體所指的分析卻似乎并不多見。故筆者在此繼續拾遺補缺,擬在歷史的語境下對圖書館權利的意涵、實質進行再思考。冀望拋磚引玉,得到業內專家同行的指教。
2 圖書館權利意涵、實質的困惑
21世紀以來,圖書館權利的研究風風火火、異彩紛呈。但是,“圖書館權利”究竟是什么?其意涵、實質究竟為何?卻仍讓筆者一頭霧水、不明就里。首先,目前業界理解的圖書館權利,大多將主體限定于讀者,卻將義務人虛置。這樣就無法理解讀者是向誰主張的權利。其次,對于權利的道德法律依據,當前業界的研究,或尋根于憲法、政府文件,或溯源于ALA、IFLA,但是,恕筆者直言,對此困惑難解之處頗多。最后,關于權利客體,即權利人對義務人的“作為或不作為的為道德、法律或習俗所認定為正當的利益、主張、資格、力量或自由”[4],雖然有“文化權利”“信息權利”“受教育權”之說,但是似乎大多都是高度的概括,鮮有更進一步的具體論述,因而很難領會理解意涵實質,更難以做進一步的辨別分析。以上是筆者對“圖書館權利”困惑的大致概括。
產生困惑之原因,除筆者資質愚魯,悟性欠佳外,似還有一客觀原因,就是當前的研究仍有缺憾,缺憾之處就是引言中已提到的“當前的探究大多立足于哲學意義的宏觀概括和法學意義的文本分析兩個層面,對于圖書館權利要件的界定仍然模糊”。正所謂“天道遠人道邇”,“宏觀概括”與“文本分析”如果沒有具體語境的聯想感悟,極易發生解讀障礙,甚至誤讀濫用,導致研究與實踐中的困惑與迷惘。
筆者以為,解決心中的困惑與迷惘,不應僅停留于名家觀點的重復引申,也不應停留在口號式宣傳的情感表達,更不應對圖書館權利不求甚解地誤讀濫用造成“權利的泛化與烏龍”[5],而應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置身于具體的歷史時空,以科學的態度對圖書館權利的意涵實質展開進一步的辨析與解讀。
3 西方歷史語境下圖書館權利意涵實質的再解讀
3.1西方歷史語境下圖書館權利研究之梳理
回顧新世紀的圖書館權利研究,似可以說濫觴于李國新對日本“圖書館自由”的研究,隨后,在中國圖書館學會、學術期刊、業界巨擘的大力推動下,在業界專家同行的踴躍參與中,迅速興起、高漲,形成一股研究思潮[6]。在這股思潮中涌現出的較有代表的研究,如李國新的“圖書館自由”研究、范并思的“作為制度安排的公共圖書館”研究、程煥文的“圖書館權利與職業道德”研究、蔣永福的“知識自由與文化權利”研究等,基本都涉及到了IFLA、ALA、JLA的內容,可以說都是不同程度的西方語境下的探究。目前,業內基本已形成共識——“圖書館權利”舶來于西方,是“舶來品”。
按照業界的結論,“如同‘權利’(Rights)一詞源自西方的概念一樣,‘圖書館權利’一詞也是源自對ALA《圖書館權利法案》英文‘Library Bill of Rights’的翻譯”[7]。“既然‘圖書館權利’一詞源自英文‘Library Bill of Rights’的翻譯,那么,要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圖書館權利的意義,就必須回歸到ALA《圖書館權利法案》(Library Bill of Rights)的文本上來分析”[8]。故此,程煥文、張靖、肖鵬、潘燕桃、何燕華、袁慶東、王靜芬等專家學者圍繞《圖書館權利法案》的內容、實質、緣起、歷史演變做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圖書館權利是指民眾利用圖書館的自由、平等權利”[8]等研究結論。
但是,上述研究不知是由于專家學者們認為無需過多陳述而無意的忽視,還是由于受限于史料匱乏而被刻意回避,似乎都淡化了對關聯時代背景的敘述。由于東西方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諸多差異,僅從文本分析與制定修訂過程的簡述,使人很難理解其具體所指,更無法辨析解讀其意涵實質。故筆者以為,當前的“圖書館權利”研究需要在已有文本分析與制定、修訂過程研究的基礎上,擴大視野,在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做進一步的辨析解讀。
3.2美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簡要回顧與分析
在此,筆者無意對美國歷史事件簡單羅列,更無意對美國歷史的研究過多深究,僅想圍繞“與解讀《圖書館權利法案》有關的命題”,對美國的文化傳統、政治制度、社會狀態做一簡單梳理,為下一步具體解讀奠定基礎。
美國是18世紀由英裔殖民者在北美洲建立的新興國家,其文化傳統可溯源于古希臘。濫觴于古希臘的西方文化,盡管其價值多元,但是各種理念的核心和基礎似乎都可以追溯于“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不是被國人經常誤讀的自私自利和損人利己,而是一種本體論認識,探究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的關系。“個人主義”是相對于“整體主義”觀念而言的,認為“獨立的個人是社會的本原和基礎,個人是社會的終極價值,所有的人都是獨立、自由和平等的,社會需要厘清群己界限(即社會存在公域和私域,私域是屬于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范疇,其他人和社會,特別是國家權力不得干預)……”[9]77-94。“個人主義”強調個體至上, 推崇追求個人幸福的生活方式,主張個性充分發展、個人充分自由,這對滿懷創業激情、胸懷淘金夢想的北美殖民者來說極易得到認同,所以,成為北美自18世紀延續至今的社會主流價值取向。
正是由于“個人主義”理念的影響,使得英裔殖民者對“自由”“平等”“人權”有股發自內心的熱愛,進而產生了對“母國”(英國)掠奪的不滿,最終掀起了獨立革命,建立了民主憲政共和國。這個民主憲政共和國具有憲政的高起點與實施困境的雙重特征。一方面,由于沒有封建傳統的歷史包袱,北美殖民者可以在高起點構建其國家制度。《獨立宣言》開宗明義,“造物主創造了平等的個人,并賦予了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10]108顯然,他們是以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思想巨擘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為立國理論基礎來構建其政治制度。審視美國的政治制度,無論是民主憲政、三權分立,還是多黨制、代議制,無不體現了“個體至上”“權利至上”的原則,貫穿了“社會契約”及“以個體權利制約公共權力,以公共權力保障個體權利”的民主理念。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美國是聯邦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分享主權的國家,即二元主權聯邦制,憲政制度常常無法適用于州和地方政府,常常因作用有限而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并引發各種各樣的分歧與糾紛。
在社會層面,美國是一種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架構,相對于政府的被限制,社會體現出多元與自由的特色,具體表現為多元自由的社會組織、多元自由的生活方式、多元自由的宗教及多元自由的意識形態[9]142。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意識形態的多元,西方文化有酷愛自由的文化傳統,自由的一層含意是個人私域不受干預,另一層含意是內在精神世界的自由。精神世界的自由肇始于基督教,基督教主張宗教自由,提倡精神世界服從上帝,不受世俗權力的干預。文藝復興后,人文主義將宗教自由發展為思想言論自由。178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權利法案》(又稱《憲法修正案》),在第一條就作為其首要人權,明確了思想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原則。19世紀,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撰寫《論自由》一書,對“思想言論自由”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從此,“思想言論自由”就成為美國一個重要的價值觀,被社會各界所廣泛認同。
3.3具體歷史語境下的ALA《圖書館權利法案》再解讀
上節筆者對美國的歷史做了簡要的概括性回溯分析,這一節結合具體語境對《圖書館權利法案》進行再解讀。
截至目前,業內專家學者從“基尼解雇事件”到“愛荷華州得梅因公共圖書館權利法案”再到“ALA舊金山年會《圖書館權利法案》的正式推出和隨后的修訂歷程”,以及“IFC(智識自由委員會)的設立及其作用發揮”,已做出了相關研究與論述。但由于對相關宏觀背景的介紹過于簡略,筆者讀來仍有語焉不詳、晦澀難懂之感,故想做一點進一步的猜測。
在此筆者不想再次復述從《得梅因公共圖書館權利法案》到ALA《圖書館權利法案》的演變過程,亦不想再三重復《圖書館權利法案》的具體條文,因為對此業內專家學者已做出了較為詳盡的論述與分析[8,11-13]。另外,筆者也無意追究蒙大拿州立大學圖書館館長基尼(Philip O.Keeney)是不愿剔除什么內容的爭議性圖書,因什么樣的理由而被校方解雇,校方又是屈從于來自何方的壓力,出于怎樣的考慮,等等,權利案例的一些不為人知的史實,因為筆者對此并不了解。坦率地說,筆者僅有的一點認識皆來自專家同行的相關介紹與論述。之所以在此不顧淺陋,過多置喙,是想拾遺補缺,與同行交流一下個人的感受。
通過對業內專家同行已發表成果的拜讀,再加上結合具體史實的聯想,筆者以為:圍繞《圖書館權利法案》的所有一切,從緣起、推出及其修訂演變,都貫穿著一個深層次歷史邏輯——“思想言論自由”及其具體落實的沖突。
如上節歸納,美國以“個人主義”為主流價值觀,構建了保障個人的各項制度,社會自由多元,這就使社會充滿活力,“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內,美國完成了從農業國家到工業國家的轉型,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特殊的國情,也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為放任自由的國家”[10]135。但是正所謂“物極必反”,在“自由放任”推動美國走向繁榮的同時,也使各種矛盾逐步累積。20世紀初,經濟大危機襲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引發美國長達4年的經濟大蕭條,“它把美國資本主義制度推到崩潰的邊緣,對美國社會各方面影響至深”[14]。為應對經濟危機,羅斯福政府采用凱恩斯主義實行“新政”,大力加強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節。但因“新政”與傳統的“放任自由”道路迥異,許多人并不認可,“新政”的支持與反對者觀點各異,尖銳對立,各個領域矛盾沖突不斷。這就是《圖書館權利法案》發布前的時代大背景。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思想言論自由”的神圣地位發生了動搖。
如上節所述,“思想言論自由”是美國人歷來十分珍視的文化傳統,建國不久就以《憲法第一修正案》作為首要人權予以確認。但是,隨著一片慘淡的經濟大蕭條,以及風起云涌的共產主義運動,“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理念開始回潮。“在自由放任觀念開始回潮和恐懼俄國革命的大背景下,聯邦和州政府制定了《反間諜法》《反煽動叛亂法》和一些新聞限制法”[10]165,“對言論的限制以及圖書審查制度的控制相當嚴格”[13]。當然,筆者以為,王靜芬女士所言的“相當嚴格”只是相對而言,是相對于美國社會已長期形成習慣的“自由放任”“政府不得干涉”的歷史傳統而言。“美國政府受制于《憲法第一修正案》和關于言論自由的條例而沒有禁書的權力,沒有專門的政府機構負責圖書審查”[15],因而,其嚴格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面對習慣性的文化傳統,也是一定會遭到強烈抵制的。20世紀30年代,“保守的聯邦最高法院以保護自由和權利為理由,先后宣布國會和一些州政府制定的一些立法違憲”[10]166,一葉知秋,由此可以想見,對于一些將“思想言論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美國人而言,反應一定會更為激烈。可以猜測,基尼(Philip O.Keeney)館長、斯波爾丁(Forrest Spaulding)館長、ALA服務原則和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所有《圖書館權利法案》的支持者,都是將“思想言論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美國人,制定《圖書館權利法案》就是這些“美國人”的激烈反應之一。
如果美國社會各界(從政府到公民社會)都是一以貫之地將“思想言論自由”奉為圭臬,那么ALA就無需畫蛇添足地發表這個政策性聲明。而如果美國社會奉行“整體主義(非個人主義)”價值觀,強調個人服從集體,強調思想言論統一,那么,作為一個非政府民間協會組織似也無力發出一種與主流相對抗的法案(Bill)。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一切都合乎邏輯、順理成章地發生了。在經濟蕭條的恐慌中,在推行“新政”的沖突中,在“二元主權聯邦”的制度架構下,各種聲音雜沓發出,宣示著不同甚至對立的立場。ALA作為代表圖書館行業的社會組織,一向將“所有圖書館都是信息和思想的論壇”[8]奉為核心理念,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在這種矛盾糾結的氛圍中,責無旁貸,必然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行業的立場。“基尼解雇”等事件,與其說是導致《圖書館權利法案》推出的原因,不如說是ALA拿來借題發揮的“引子”。
在對美國歷史的簡要回顧與分析后,再回過頭來梳理《圖書館權利法案》及蘊含其中的“圖書館權利”的意涵實質,筆者頓覺豁然許多。恰如程煥文先生所言,“而事實上《圖書館權利法案》不過是美國圖書館協會闡述圖書館利用者的智識自由權利與平等權利和美國圖書館協會期望圖書館支持這些權利的政策性聲明”[8],而“利用者的智識自由權利與平等權利”就是“思想言論自由”的權利。
4 世界現當代歷史語境下圖書館權利意涵、實質發展演變的再解讀
綜上所述,《圖書館權利法案》是ALA在具體的時代背景下發出的宣示立場的“聲音”,所宣示的立場是美國傳統的基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言論自由”。因而,美國歷史語境下的“圖書館權利”的實質就是個人的思想言論自由,它是第一代人權——自由權在圖書館活動中的具體體現。這也剛好印證了文獻16中筆者對于“圖書館權利”的概念理解。在文獻16中,筆者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對權利概念的產生、發展演變及多元分歧的現狀進行了梳理,認為,“圖書館權利”不是圖書館界創造出的一種新權利,而是普遍的權利文化在圖書館活動中的具體體現。
20世紀30年代,占主流的普遍的權利文化是基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消極權利”文化,強調權利的防御權能與公權主體的消極義務。權利的防御權能是指“權利主體應享有的一種要求其他人承擔不得侵害其權利的不作為義務的能力……防御權能主要是從自由權所導出,是社會主體的權利所普遍具有的……防御權能是針對權利主體以外的所有社會主體的,包括個人、社會組織和各類國家機關。但是防御權能的最基本指向,只能是指向國家公權力”[10]250-255。也就是說,“圖書館權利”(普遍的權利文化在圖書館活動中的具體體現)的權利主體范圍囊括所有社會主體,可以是任何社會主體之一;權利義務人是權利主體以外的其他社會主體,包括個人、社會組織和各類國家機關,但是“最基本指向是國家公權力”。關于權利的道德法律依據,前文已述,“思想言論自由”在美國有悠久的傳統,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建國不久就以《憲法第一修正案》作為首要人權予以確認,特別需要補充強調的是,1925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吉特羅訴紐約州案裁定,《憲法第一修正案》不僅適用于聯邦中央政府,而且普遍適用于州及各級地方政府,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二元主權聯邦制的體制障礙,使得在美國主張“思想言論自由”權利的依據有力而且充分[10]13-18。而權利客體,文中已提及多次,就是在圖書館活動范圍中涉及的基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言論自由”。
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權利本位”的文化氛圍中,“思想言論自由”有悠久的傳統,得到普遍的認同,其意涵實質是明確的。在圖書館活動中,很自然從公民日常生活的思想言論自由權利具體化為讀者的圖書館權利。“圖書館權利在西方圖書館界已經是不需要討論的一個概念。美國圖書館協會的權利宣言得到了圖書館界的一致公認,沒什么好討論的了”[7]。但是,程煥文先生所說的“一致公認”應該僅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圖書館界。
二戰之后,美國地位空前提高,在各行各業似乎都引導了國際的主流。1947年5月,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9 000美元的資助使得IFLA成為戰后首批恢復活動的非政府的國際組織之一[17]12。隨后IFLA迅速發展,由一個“西歐圖書館界的論壇”發展為“代表圖書館和信息服務機構及其用戶利益的領導性國際組織”[17]7-32。在這期間,美國圖書館界及相關組織做出了巨大貢獻。2000年8月,IFLA通過了新的章程,明確宣示了4條基本價值,內容與ALA《圖書館權利法案》高度相似[17]39,這就自然使人聯想到美國圖書館界在IFLA基本價值擬定中的影響與作用。由于目前缺乏更多材料的證實或證偽,這個聯想只是筆者個人的一個猜測。假設猜測成立,那么,IFLA的基本價值就是ALA《圖書館權利法案》所宣示的“圖書館權利”,其意涵實質就是在圖書館活動范圍中涉及的基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言論自由”。
IFLA號召“在實現章程中陳述的宗旨時,將在基本價值的基礎上作出努力”[17]39,這就意謂著IFLA的基本價值應成為全世界圖書館行業的基本理念。但是,由于世界各地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基本價值在東方文化語境發生了解讀障礙與水土不服。在美國,在西方歷史文化語境下,諸如“自由”“平等”等一些原本清晰的價值概括,在移植東方文化語境的過程中,逐漸演變為一些含義模糊的宣傳口號。而“圖書館權利”,也不再是“一致公認”,而是“歧義叢生”,這就由“沒什么好討論的了”變成了需要繼續深入探討的話題。
5 結 語
文中,筆者嘗試在歷史的語境下對圖書館權利的意涵實質進行解讀。通過解讀,恰好印證了辯證唯物主義對“權利”的經典闡釋,“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文化發展”[18]。“有什么樣的社會經濟結構,人們就有什么樣的權利。權利是歷史的、具體的”[19]。ALA 宣示的“圖書館權利”有明晰的意涵實質,有孕育其發展的歷史文化土壤,有其具體針對的現實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ALA的理念,甚至IFLA的理念,可以為中國的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與實踐活動提供參考借鑒,但不應超驗地闡釋,將其直接照搬,奉為教條,更不應直接用其指導中國圖書館的實踐活動。中國當代的圖書館權利研究不能脫離中國當代具體的歷史語境,必須“本土化”。
參考文獻 :
[1]現代圖書館理念的基石“:權利時代的圖書館” 巔峰論談[J].圖書館建設, 2015(1):4-19.
[2]范并思.權利、讀者權利和圖書館權利[J].圖書館, 2013(2):1-4.
[3]李國新.21世紀初年的“圖書館權利”研究與傳播[J].中國圖書館學報, 2015(6):4-11.
[4]夏 勇.權利哲學的基本問題[J].法學研究, 2004(3):3-26.
[5]陳林林.反思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權利泛化[J].法學研究, 2014(1): 10-13.
[6]王 政, 劉 鑫, 張 鐵, 等.圖書館權利大事記[J].圖書館建設, 2015(1):20-25.
[7]程煥文.圖書館權利的來由[J].圖書館論壇, 2009(6):30-36.
[8]程煥文.圖書館權利的界定[J].中國圖書館學報, 2010(2):38-45.
[9]叢日云.西方文明講演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10]菅從進.權利制約權力論[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8.
[11]張 婧, 肖 鵬.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的制定與修訂過程[J].圖書情報工作, 2015(4):12-19.
[12]袁慶東.美國《圖書館權利宣言》發展史論略[J].圖書館, 2009 (1):70-72.
[13]王靜芬.美國《圖書館權利法案》的歷史演變及其特點[J].圖書館論壇, 2014(5):121-126.
[14]劉緒貽, 李存訓.美國通史(第五卷) :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代1929-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
[15]盧章平, 劉蔣聯, 李明娟.新世紀以來美國禁書排行榜透析[J].大學圖書館學報, 2015(4):109-115.
[16]魏建琳.權利理論視閾下圖書館權利概念的辨析與解讀[J].圖書館, 2015(8):27-31,48.
[17]丘東江.國際圖聯(IFLA)與中國圖書館事業:上[M].北京:華藝出版社, 2002.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2.
[19]辛世俊.公民權利意識研究[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 2006:62.
Further Reflection on Library Rights' Implications and Essence under Historical Context
[Abstract]The definition that library rights is the rights of readers utilize library freely and equally has blind spots, so it needs further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under historical context.Library right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ALA's Library Bill of Rights, that is ALA's declared industry's statement in a specific era background , which declared the library right's essence is th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speech, it is a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western traditional right culture based on individualism and liberalism in the library activity.
[Key words]Library right; America; Library Bill of Rights; Historical context
[中圖分類號]G250.1
[文獻標識碼]A
*本文系西安市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建設中公共圖書館文化服務體系發展研究”的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5WL16。
[作者簡介]
魏建琳 男,1967年生,現工作于西安文理學院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收稿日期:2015-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