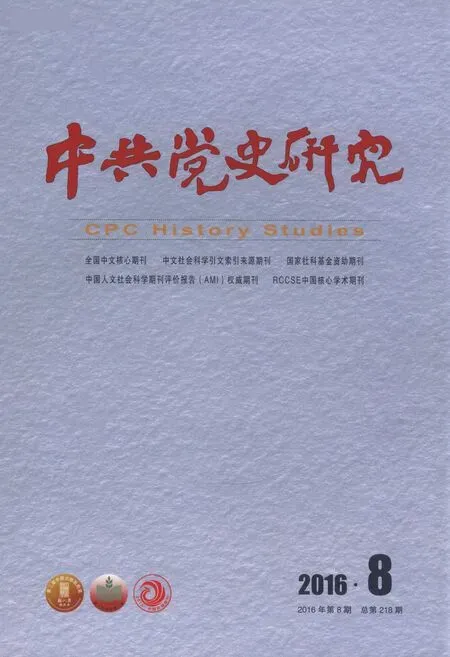試論撥亂反正時期權威理論的重塑與演進
吳 志 軍
試論撥亂反正時期權威理論的重塑與演進
吳 志 軍
作為撥亂反正時期時代變遷與思想重建的議題回響,權威理論的重塑歷經多重演化,從最初一年多時間里對于重樹權威的極端強調,到1978年后對“絕對權威”論的深入批判和解構與新的政治權威理論之重塑的同步嬗變,充分展現了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自身的起承轉合及其歷史的復雜性和多元性。關于權威問題的理論重構是撥亂反正時期的一種亞類型政治思潮,但因其與當代中國的高度相關性,須將之納入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書寫。
撥亂反正時期;權威理論;嬗變;亞類型政治思潮;政治思想史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隨著撥亂反正進程的逐步展開和思想解放潮流的漸次深入,思想理論界開始就以往一大批被極左勢力歪曲的思想理論展開矯枉除弊和匡謬正俗的基礎性工作,權威理論尤其是政治權威理論的重塑是其間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既得益于撥亂反正時期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重建的宏大語境,又受到中共集中批判“文化大革命”時期和撥亂反正時期出現的各種無政府(主義)現象的直接刺激*吳志軍:《撥亂反正時期中共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5期。。由于權威理論的重建與撥亂反正時期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革舊徙新以及未來中國政治文明形態的長遠演變等根本問題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因此權威理論的重塑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而透過對這一問題的思想史考察,可為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評量撥亂反正時期的歷史地位以及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內在結構與未來書寫提供一種獨特的文化維度和學術棱鏡。
一、“文化大革命”批判背景下對重樹權威的極端強調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出于對十年運動期間政治動蕩和社會混亂以及具有復發性的無政府狀態所帶來的切身之痛,整個國家和社會都存在著一種迅速重樹權威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強烈訴求。在全國迅速興起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中,“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受到全面批判。在此情勢下,發表于1873年的恩格斯《論權威》一文,重新成為批判無政府主義、論證權威合理性的經典思想資源。很多重要報刊都相繼刊布《論權威》全文或節錄重要段落,并指出恩格斯在這篇重要歷史文獻中,精辟地論證了革命權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徹底批駁了無政府主義否認一切權威、主張絕對自由的思想,再次闡明并捍衛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觀點。這在全社會引起了廣泛回應和積極反響,很多批判者由此展開對權威理論的重新探討與全力構建。
批判者首先集中回顧了恩格斯發表《論權威》的主要歷史背景和基本目的,即在第一國際內對巴枯寧政治集團及其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批判,指出“反對權威”是巴枯寧無政府主義學說的核心,也是巴枯寧集團的行動綱領——巴枯寧認為權威是絕對的禍害,將權威看作是屈辱和奴役的根源,把權威原則看作是“一種罪惡昭彰的對人性的否定”、“奴隸制、精神墮落、道德墮落的源泉”,宣布“一切權威都是虛假的、專橫的、獨斷的、致人死命的”;凡與權威有關的東西,如國家、專政、革命、領袖等,不管其階級屬性若何,均屬一概打倒和消滅之列,而代之以個人絕對自治的無政府狀態;巴枯寧的理想社會不存在任何權威,“反映了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發展過程中遭到破產的手工業者的絕對平等觀念”*張文煥:《“四人幫”和巴枯寧匪幫》,《人民日報》1977年4月14日。。批判者同時普遍認為:林彪、“四人幫”等政治勢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用國家政權力量推行無政府主義,其主要特點也是“反對權威、反對專家、反對規章制度和國家法制”*孫文廣:《關于理論問題給中央信》(1977年11月9日)。,“正是今天破壞黨的紀律,破壞無產階級權威的罪魁禍首”*省氣象局理論組:《維護無產階級權威 聽從華主席指揮》,《陜西氣象》1977年第2期。;他們對黨的領導、軍事紀律和規章制度等社會各領域不同形式權威的蔑視、否定與歪曲,正是導致中國一度陷入無政府主義亂局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外無政府主義在“反對權威”這一點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統一性,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如出一轍”*何文亭:《“四人幫”同巴枯寧如出一轍》,《解放軍報》1977年3月30日。。
鑒于此,為加強對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批判,批判者以恩格斯關于“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之論斷為依據,著手重新論證“權威”所蘊涵的基本性質和根本理念。他們大都認為,要全面正確地理解“權威”,無法離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別人接受的帶強制性的意志,另一方面是對這種意志的服從和遵行。強制和服從的關系在不同情況下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有時表現為對政治權力的服從,有時表現為按計劃或命令辦事,有時表現為對規章制度的遵守等。盡管在服從和遵守的時候,可能是自覺的或者是被強制而不夠自覺的,但這種強制和服從的關系同權威自身一樣,都是必然存在的,“如果強制的意志可以不服從,權威也就不成其為權威了”*許可成:《〈論權威〉——批判無政府主義的經典文獻》,《天津師院學報》1977年第2期。;盡管強制與服從的關系往往“使服從的一方感到難堪”,但“我們還是必須維護這種關系,不能隨意廢除它”*韓威:《無產階級必須捍衛自己的革命權威——學習〈論權威〉》,《安徽大學學報》1977年第1期。。批判者強調指出,“服從革命的權威,遵守鐵的革命紀律,無疑是保證革命事業獲得勝利的絕對必需的條件”*長自輪工人理論小組:《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文匯報》1977年3月31日。,人類世界從來就沒有絕對自由的社會,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組織社會生產,也必須有紀律和服從,更何況有階級存在的社會”,無政府主義思想“既是空想的,又是反動的,完全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冰巖:《從蒲魯東主義看“四人幫”攻擊革命紀律的反動性》,《解放軍報》1977年3月18日。。
基于這種認識,有論者重新解釋了重樹無產階級革命權威強制性的可能性。他們承襲以往的階級斗爭思維,將“權威”劃分為“無產階級”和“反動階級”或“革命”和“反革命”等相對應的兩類屬性,指出凡權威就具有強制性,必須服從,但無產階級革命權威只對敵對階級、敵對集團和敵對分子實行專制,而在人民內部,服從則是建立在自覺基礎上的。堅持權威和服從權威,都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無法對自己實行專制。無產階級革命權威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必然得到其擁護,因而能夠經過說服教育而達到服從的目的,“一定的權威”和“一定的服從”完全可以實現統一。只有“四人幫”等“反黨反革命分子”才會感到無產階級權威是致命的威脅,而“敵人的反對,從反面教育我們,權威是個不可缺少的東西”。*韓威:《無產階級必須捍衛自己的革命權威——學習〈論權威〉》,《安徽大學學報》1977年第1期。他們繼而指出,權威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具有很強的歷史性和條件性,即使階級社會中的政治權威隨階級消滅而消失,社會管理權威又必代之而起,權威絕不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物,它在社會主義社會直至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里仍然存在,“比如,隨著航空事業的發展,權威范圍也就將擴及天空;新近宇宙航行事業的發展,權威范圍也將擴及外層空間”*黃志賢:《現代化大生產與權威——讀恩格斯〈論權威〉札記》,《福建師大學報》1977年第1—2期。,因此“必須唯物地、辯證地看待權威問題,反對形而上學觀點”*陳忠雄:《批判無政府主義的銳利武器——恩格斯的〈論權威〉試析》,《開封師院學報》1977年第5期。。可見,這些思想認識不僅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反對權威的本質,而且著重強調了權威在社會生活中的存在樣態和永續性。
在此基礎上,批判者充分運用恩格斯《論權威》的基本思想,針對“四人幫”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惡行,著力論證權威在從生產斗爭到階級斗爭、從經濟領域到政治領域中的不可或缺性及其存在之永恒性。在經濟領域,重點以恩格斯關于“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這一經典論斷,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越來越復雜化,現代經濟關系“有一種使各個分散的活動愈來愈為人們的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這就需要建立權威性的規章制度,以統一協調人們的意志和行動,而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一旦制訂出來,對每個勞動者都必須具有強制性的約束力,“這樣才能使之成為革命權威,否則只能是一紙空文”*評論員文章:《生產指揮要有權威》,《人民日報》1977年11月9日。,權威根源于現代化大生產,不會因社會經濟形式的更迭而消失,“一萬年以后只要有大工業,就必定還有規章制度”*《一萬年以后還要有規章制度——斥“要總結一個沒有規章制度而搞好生產的典型”》,《文匯報》1977年12月21日。。在軍事領域,則引用恩格斯的經典論斷“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最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強調現代戰爭的突出特點是合成軍協同作戰,需要高度的集中和統一,“在這種情況下,權威就具有更重大的意義”*海軍湛江部隊理論組:《從艦船談權威》,《人民日報》1977年7月8日。,“進行現代戰爭,使用現代武器裝備,不是要取消或者削弱權威和紀律,而是要更進一步地加強它”*鄭宣:《遵守紀律在現代戰爭中尤其重要》,《解放軍報》1977年5月16日。。可見,批判者著重從權威所能發揮的社會功能及其管理和組織方式等方面,突出了權威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重要協調機制的基本價值,畢竟“協調需要權威和明確定義的規則”*〔英〕戴維·畢瑟姆著,韓志明、張毅譯:《官僚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9頁。。
尤為重要的是,批判者普遍指出,林彪、“四人幫”等政治勢力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味鼓吹“踢開黨委鬧革命”“矛頭向上就是大方向正確”等謬論,以及對黨的一元化領導、黨內民主和組織紀律的粗暴踐踏,不僅是誘發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的根本原因,而且嚴重危害黨的政治權威。因此,重樹中共領導核心的權威地位無疑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這成為撥亂反正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共識。他們引用恩格斯對巴黎公社失敗原因的分析,指出缺乏集中和權威,“沒有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路線正確、團結一致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領導,這是巴黎公社失敗的最根本的原因”*群力:《學習恩格斯的〈論權威〉》,《廣西師院學報》1977年第2期。;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必須有革命的權威,鞏固政權更需要革命的權威,無產階級要使自己成為強大的階級,步調一致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須依靠具有革命權威的黨的領導,必須要有各級黨的領導的革命權威,特別是要有黨中央領導的革命權威”,“我國解放二十多年來的革命和建設實踐,證明了恩格斯的科學論斷是完全正確的”*中共旬邑縣委員會:《煽動無政府主義,就是為反動派效勞——學習恩格斯的〈論權威〉》,《西北大學學報》1977年第1期。。批判者由這一理論邏輯自然地引申出“黨中央的革命權威又必須由無產階級的英明領袖來主持和擔負”這樣的傳統認識,甚至有論者認為,重新溫習《論權威》的根本目的就是以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權威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努力培養自己熱愛黨的領袖、擁護黨的領袖、保衛黨的領袖的高度自覺性”*群力:《學習恩格斯的〈論權威〉》,《廣西師院學報》1977年第2期。。從更為長遠的歷史視野來看,由于政治權威在中國的權威結構和體系中長期占據主導性地位,重樹堅定的政治權威不僅促成了權威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而且必然使其再次具備人格化的特征與力量,從而在政治管理和道德高度等多方面形成更具吸引力與凝聚力的態勢。
事實上,為規避毛澤東去世后出現權力真空,對華國鋒作為繼毛澤東之后最大的合法政治權威的宣傳,便成為“文化大革命”結束伊始權威理論構建的立足點和落腳點。主要的政治宣傳媒體和批判者從毛澤東與華國鋒的政治繼承關系、華國鋒本人的政治道德和個人品行以及華國鋒豐富的斗爭和從政經驗等方面,系統地論證了華國鋒作為政治領袖的合法性來源。批判者由此指出,以華國鋒為代表的革命領袖的權威是在斗爭實踐中形成的,代表著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扎根于群眾之中,不是自封的,“事實充分說明,革命權威——華主席、黨中央的權威,對于革命人民如同布帛菽粟一樣,是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我們要維護和服從華主席、黨中央的革命權威,宣傳華主席,保衛黨的領袖,決不能有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糊涂觀念”*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理論組:《自覺維護華主席、黨中央的革命權威——學習恩格斯〈論權威〉的一點體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7年第1期。。這樣的政治理論宣傳使華國鋒迅速成為當時中共政治權威的集中代表,是撥亂反正初期重建權威理論的必然邏輯結果。
綜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最初一年多的時間里,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催生出強烈批判和深入反思“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以及大力宣揚與重樹秩序、制度和紀律觀念的社會氛圍,重建并鞏固各種形式的權威成為普遍而強烈的社會共識。批判者以對恩格斯《論權威》的重新詮解為核心,逐步構建出一整套貌似合理化的關于重樹無產階級權威的理論邏輯和話語體系。這一理論對于權威的極力強調取向,既是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權威失落而招致的政治與社會混亂局勢的反撥,更直接受到當時整個社會急于和“四人幫”等政治勢力劃清界限之心態的全面影響,“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四人幫’瘋狂反對我們的革命權威,我們就要堅決捍衛革命權威”*韓威:《無產階級必須捍衛自己的革命權威——學習〈論權威〉》,《安徽大學學報》1977年第1期。,這實際上是中國政治社會長期受極左思潮影響所形成的“非黑即白”的二元絕然對立思維的直接反映。而對華國鋒作為最高政治權威的宣傳與型塑,更是當時在“兩個凡是”理論宰制下所滋生出來的新的個人崇拜思潮的反映,為新的現代迷信提供了特殊的理論論證。在此期間,雖然也有個別研究者注意到并論述了恩格斯關于權威與自治之辯證關系的內容,指出:“權威與自治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沒有自治,也就無所謂權威。所以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群力:《學習恩格斯的〈論權威〉》,《廣西師院學報》1977年第2期。但這些思想認識籠罩在對“革命權威”的極力強調和新的個人崇拜的滋長等政治環境中,沒有得到更為充分的理論論證,也未得到整個政治社會的關注和認可。
因此,這一時期新構建和詮釋的權威理論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在前提預設、邏輯自洽和話語體系等方面仍然帶有濃厚的政治大批判色彩,很多內容缺乏充分的事實經驗和嚴謹的邏輯規范的支持,是當時思想理論界因循“左”的指導思想所必然產生的一種理論形態,其思維結構和政治取向實際上與“左”的思潮分享著幾乎同一的知識與文化譜系,是“左”的意識形態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一種表現或征候,極大地背離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很多中國人努力擺脫極左思潮鉗制以及渴望社會主義民主的歷史潮流,注定要受到思想理論界的重新拷問。
二、對“絕對權威”論的批判與權威理論的根本轉向
進入1978年后,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任務的階段性轉變以及撥亂反正進程的漸次深入,思想理論界對于“權威”的理解重心以及相應的理論構建也隨之發生位移。這一轉變首先開始于伴隨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而開啟的對真理(觀)問題的重新認識與理解。思想理論界從對“真理”基本概念的界定出發,普遍否認了所謂“真理具有階級性”的“左”的觀點,確立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準則,重新探討了真理的客觀性、具體性、普遍性(普適性)、過程性(發展性)等基本屬性,尤其對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之辯證關系的重新討論,更打破了長期籠罩在真理問題上的極左迷霧。
真理(觀)問題的重新討論再次為思想文化界更加深入地審視權威問題提供了獨特的歷史契機,因為權威與真理往往具有嚴密的共生關系,任何形式的權威——尤其是具有廣泛控制力和影響力的政治權威——都必然以對“真理”的普遍性甚至壟斷性占有為基本特征。有學者就此首先從科學文化史上的“理論權威”角度指出,一種理論一旦發生較大影響并取得支配性或統治性地位,固然會被普遍地視為權威,但有的權威擁有真理,有的權威則沒有真理,“權威不一定都是真理,真理卻最終具有權威性。對沒有真理的錯誤的理論權威固然不能相信,就是對于擁有真理的正確的理論權威也要取分析態度”,盲目迷信理論權威只會導致科學文化的停滯不前,“科學文化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突破權威,發現和發展真理的歷史”。但林彪、“四人幫”等政治勢力故意顛倒是非,在真理問題上制造種種謬論,“把這一個十分明白的問題弄得十分混亂”,“我們不得不對這個問題重新進行一番考察”。*石仲泉:《權威與真理》,《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
從這一基本認識出發,思想理論界關于權威問題的探討重心從對樹立革命權威的極力強調,迅即轉移至對“絕對真理”論和“絕對權威”論等極左思潮的深入批判,權威理論的重建方向由此發生根本轉變。有研究者認為,“絕對真理”論是“絕對權威”論的理論基礎,二者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一對孿生兄弟”,應將二者視為一種共同體加以徹底批判,林彪、“四人幫”所鼓吹的“絕對真理”論的集中表現是所謂“頂峰”論,即宣揚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廣泛推行諸如“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記條條、背警句”“遇到問題找語錄”等謬論,將毛澤東思想甚至毛澤東的某些思想和話語片斷奉為不可移易的“絕對真理”、不能質疑的“絕對權威”,直至形成“以權威的是非為是非,以權威人士的言論、思想、理論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權威標準”論,“把權威絕對到了不能再絕對的地步”*石仲泉:《權威與真理》,《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這“是對人類思想史的大反動”*張成興:《評林彪、“四人幫”的實用主義真理觀》,《廣西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批判者充分運用經過學界重新討論的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之辯證關系原理,指出“絕對真理”論的根本錯誤就在于用真理的絕對性抹殺了真理的相對性,極端夸大了真理的絕對性,但絕對真理只存在于相對真理之中,所有的理論(真理)都是在實踐基礎上的無限發展的歷史過程,“認識只能達到新高度,不能達到頂峰”*沈陽部隊后勤部理論組:《批林彪的“頂峰”論》,《人民日報》1978年5月8日。,世界上從來沒有單獨存在的“絕對真理”,因而也從來不會存在“絕對權威”。通過回顧中外歷史上各種“絕對權威”的衰亡史,批判者一致認為,“絕對權威”論從根本上違背了理論(真理)的權威根源于實踐的權威、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并非權威理論而是社會實踐這一基本原理,只有被實踐證明了的理論才獲得真理權和權威性,維護任何一種堪稱真理的思想與理論體系的權威,“唯一的辦法,是讓它在實踐檢驗中不斷吐故納新,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而不是人為地、主觀地把它的權威‘絕對’化”,“絕對權威”論實際上是極左勢力推行封建法西斯“全面專政”、扼殺一切科學文化的反動理論武器,它“本是封建時代蒙昧主義的表現,是專制主義的產物,是沒有真理、害怕真理的一種曲折的反映。哪里有‘絕對權威’的統治,哪里就壓抑、排斥人民的智慧,妨礙真理的發現,阻滯社會的發展”*金汶:《理論的權威從何而來?——駁林彪、“四人幫”的“絕對權威”論》,《解放軍報》1978年10月9日。。在這一論證過程中,毛澤東于1967年底就“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提法而做的批語*這一批語的主要內容有:“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于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從斗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55頁。,被批判者不斷征引,成為迅速擊穿極左勢力創造的一系列政治理論神話的直接論據。當然,注意到“絕對權威”論背后的封建專制主義本質,更凸顯“絕對權威”論的極端反動性,使這一理論批判具有鮮明的啟蒙主義色彩。
對“絕對權威”論的批判迅速帶來一個問題,即如何重新認識和評價革命領袖及其思想理論——在當時的語境下,當然具體是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自身權威的合理性,因為很明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長期以來被極左勢力塑造為“絕對權威”的化身。欲徹底地批判“絕對權威”論,就必須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從“絕對權威”論的神話中解放出來。一批研究者著重從“為什么要有領袖”“領袖是怎樣產生的”“領袖產生以后起什么作用”等方面重構無產階級革命權威理論。他們首先肯定任何社會都需要權威,無產階級不是反權威主義者,但是將領袖的權威絕對化和神秘化還是將領袖的權威當作真理的旗幟,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領袖權威觀。研究者再次從認識論的角度分析指出,革命真理同任何真理一樣都是具體的、歷史的,因此革命導師的科學理論植根于具體的時空之中,受到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這“決定了革命權威不能不具有一定的相對性”,任何權威“都是指一個時代或一定領域的權威”;革命真理的不斷發展,也決定了革命權威的相對性,從馬克思主義到毛澤東思想就是革命真理不斷發展的過程,“不講發展,否認發展,是和這個體現革命辯證法的革命理論本身不相容的”,“充分說明體現革命真理的革命權威只能是相對的”。總之,“絕對權威”論“根本否定了領袖權威的客觀性,根本否定了領袖權威的相對性”。*石仲泉:《權威與真理》,《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苗高生:《試論領袖的權威》,《蘭州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經過一年多的理論批判,從哲學角度全面認識權威的絕對性和相對性在1979年開始清晰起來。研究者概括指出,無產階級權威同任何權威一樣,都具有絕對性和相對性這兩重屬性,主要體現在:人類在本質上可以認識一切客觀事物及其規律,但具體人只能部分地認識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只擁有局部真理權和局部改造世界的主動權;任何個人或集團的權威只適用于一定范圍,超出此范圍便不再是權威;任何個人或集團的權威總隨著實踐而不斷發展變化,是具體的而非絕對的;權威本身不具有完全而絕對的純粹性,任何權威自身包含著非權威因素;無產階級權威必須以廣泛的無產階級民主為基礎,沒有這種民主,也就沒有反映無產階級意志的領袖權威。因此,必須反對一切形式的“絕對權威”論,“對待無產階級的權威,不論大小,都要采取兩分法,既要看到其絕對性一面,更應看到其相對性一面”。*洪松濤:《論權威及其兩重性》,《學習與探索》1979年第1期。可見,此時思想理論界對這一基本理論的重述,側重強調的是權威的“相對性”,這成為重新理解和建構權威理論的重要共識。
這種新的權威理論又隨著政治社會主題的變化而得到持續加強。在1980年,從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提出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必須批判封建特權思想等問題,到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堅持“少宣傳個人”的指示》,及至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肅清封建主義影響”,以及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召開,激發起思想文化界的新一輪思想解放潮流。很多學者以極高的政治與理論熱情,發表了大量批判封建主義遺毒的著述。他們強烈抨擊個人崇拜、官僚主義、等級制度和特權觀念等不正常現象,呼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在社會中產生了廣泛呼應。在此期間,關于“領袖與人民”之關系的探討和論述成為一大理論重心。一些思想理論工作者正確地指出,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一系列弊端的產生和延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確對待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方文、李振霞:《徹底清除個人崇拜的影響》,《紅旗》1980年第24期。。他們從“人民應當忠于領袖,還是領袖應當忠于人民”“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領袖是天生的,還是在實踐中成長的”“領袖是單數還是復數”“領袖能不能批評”等方面,清理了長期籠罩在這些問題上的極左認識,并著重結合當時正在討論的“終身制”“接班人”等問題,深刻批判了在這些問題上所遺留的封建主義觀念,實現了“領袖與人民”關系理論的重構與更新,成為進一步瓦解“絕對權威”論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在整個撥亂反正時期,權威理論的重塑和演化都無法離開對“領袖與人民”關系問題的理解,其間產生了很多至今看來依然頗具震撼力的思想*如在1979年,就有學者從反對現代迷信的角度指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熱愛領袖應以尊重群眾作為前提,林彪、“四人幫”對革命領袖的神化“使人民對領袖的熱愛變成對人民自己的否定”,“對領袖的神化,就是對群眾的奴化……領袖的神圣狀況,它的反面就是群眾的奴隸狀況”,因此,只有“取消神學權威,才能樹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權威”。參見《思想要解放 理論要徹底》,《紅旗》1979年第3期。。
在此基礎上,有學者清醒地意識到,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產生個人崇拜現象和現代迷信運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將權威和迷信混為一談直至將權威迷信化,尤其當“我們在理論上又往往只注意權威的必要性,不注意權威的科學性”之際,更引致極左思潮的泛濫,因此必須更為明確地區劃權威與迷信的聯系和殊異,增強權威的科學性或科學化,“科學的權威不斷戰勝迷信的過程,迷信的徹底消滅,就是權威的普遍科學化”。研究者指出,權威和迷信這兩個概念都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支配與服從關系,對社會都具有控制和威懾作用,并且廣泛地存在于各種領域,但二者的區別也是明顯的:權威產生的根源是社會聯合活動的客觀必然性,其存在條件是人類社會的永續性,而迷信與生產力低下和人類的愚昧無知性直接相聯,它是在人類的抽象思維能力有了一定發展但又嚴重不足的階段上將自然力人格化的產物,并不必然與人類社會共生;隨著社會進步,科學的發展日益擴大著權威的應用半徑,權威也愈加需要以科學為基礎,任何反科學的權威無法得到持久維持,而迷信活動尤其是現代迷信思潮則極力貶低理性、摧殘智慧、推行蒙昧主義,根本排斥科學精神,是科學的大敵;正常的權威是在歷史實踐中自然形成的,擔任權威角色的杰出人物不能離開他所要服務的聯合活動以及他所要體現其意志的人民,反對夸大個人作用,而迷信活動要保證對別人的強制支配關系,就必然神化現實的個人,推行個人崇拜,以左右歷史進程。因此,權威和迷信是根本不同的,盡管人類實現正確地區分權威和迷信經歷了長期的歷史過程,但“社會主義最終要消滅迷信,權威一定要普遍科學化這個根本性的趨勢是任何力量也改變不了的”。*蒙晨:《權威與迷信》,《貴陽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這一基本理論問題進一步明晰了權威的邊界所在,表明學術界在權威問題上愈益明顯的理性化傾向。
在此前后,學術界還非常注重發掘更多批判“絕對權威”論的歷史與思想資源,涌現出很多具有較高水準的學術成果,使關于權威的新理論形態進一步趨于精細和完善。有學者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大量事例,充分論述了馬克思對待個人和權威的科學態度,指出馬克思“終生對狂熱的崇拜持有反感”,主張“在權威面前不是跪著而是站著”,欣賞“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的態度,不斷隨著實踐和思考的進展而修正、補充與完善自己的理論;他堅決反對別人對他自己的迷信,一貫厭棄別人為他歌功頌德,并為此一度拒絕發表他的傳記,反對將其名字和著作寫進黨綱,更反對將他的理論絕對化,認為“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黃子云:《學習馬克思對待個人及權威的科學態度》,《華南師院學報》1980年第4期。。還有學者概述了被馬克思稱為“近代唯物主義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批判中世紀經院哲學家將亞里士多德視為不容置疑的權威的相關思想,突出了他呼吁人們由崇拜權威、迷信經典變為面向自然、尊重科學、注意實驗和發明以及追求真理的強烈愿望,彰顯了培根的一系列經典格言如“人們之所以在科學上不能進步,乃是由于……崇拜哲學中所謂偉大人物的權威”、“真理是時間的女兒,不是權威的女兒”以及“知識就是力量”的批判力量*朱葵菊:《培根對迷信和權威崇拜的批判》,《社會科學輯刊》1980年第4期。。應當指出,馬克思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而培根是最為國人所熟知的西方唯物主義(經驗主義)哲學家之一,他們對塑造中國人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科學知識理念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重新發掘他們反對和批判權威崇拜的事實,對深受個人崇拜思潮之苦的廣大國民來說,無疑是一種有力的批判性武器。
在這些深入的學術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突破是學界開始注重探求和理解“權威”生成的原初思想理論及其內在結構。《哲學譯叢》于1981年節譯美國著名哲學家馬爾庫塞的一篇論文,析理出黑格爾國家哲學對權威問題的基本描述,即黑格爾辯證法思想揚棄康德哲學思想關于市民社會的自足性,市民社會自我建設成國家的思想被拒絕,認定“幾乎已被看作是問題百出的市民社會”不能再為社會權威體系提供基礎,而國家作為獨立的整體性站在社會對立面,“從社會的否定性中解脫了出來,并成了所有社會權威的絕對承擔者。權威制度的普遍合理化被放棄了;絕對理性的哲學把完全反理性的權威放進了國家的基礎”,社會和國家由此分離,“這對權威問題的發展是一個決定性步驟”,因此黑格爾不再從個人的(物質的)利益和需要(它們是要消滅權威的)之角度探索國家起源,“而是把國家的‘自在自為’的客觀性抬得高于所有原初的條件”,國家成為社會政治制度權威的唯一承擔者。馬爾庫塞進而認為,可以將黑格爾關于國家和社會哲學的基礎及其理論展演視為“一部權威意識發展簡史”,尤其黑格爾關于統治與奴役關系的分析表明“統治的權威,從根本上講,是依附于奴隸對這一權威的相信和維護”。*〔美〕H.馬爾庫塞著,任立譯:《論黑格爾關于權威和家庭的思想》,《哲學譯叢》1981年第2期。譯者注明該文出自馬爾庫塞《社會批判理論的思想》一書,筆者暫未查到該書原版及相應的中文譯本,但參考馬爾庫塞的主要著作目錄以及中國學術界對于該書的參引情況,初步判斷該書可能是西方知識文化界出版的一部馬爾庫塞論文集。盡管該文的準確來源不明,但馬爾庫塞的很多著作如《理性和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興起》(程志民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均收納和反映了該文的主要內容與基礎意向。顯然,這些思想分析彰顯了權威(國家)生成的哲學邏輯、政治結構及其本質屬性,是當時中國學術界未曾抵達的思考境地。作為西方世界的著名左翼學者,馬爾庫塞的基本思想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有著較強的親和性,因而得到國內學界的積極引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為對其思想體系的接受與認可*雖然國內學界對馬爾庫塞這一思想的消化和接受情況及其所產生的學術影響之程度如何,還需要更為精細的學術史考量,但其基本的思想取向無疑與當時學術界關于權威問題的新認識和新思考頗有若合符節之處。。這也間接地為國內學界在權威問題上的理論探討提供了卓富特色的思想與理論資源,并使其浸染上一定的國際文化性。
這種國際性還通過引介國外學者關于權威在非政治領域中的作用的評論而得到鮮明、特別的體現,如有美國學者分析人類的創造性活動與政府的行政性權威之間的關系,認為在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真正的創造性活動“還是最好由那些能夠知道并根據情況來判斷的人去決定”,這些領域中的公認權威以及有創造能力的專家學者“能更好地決定這方面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美〕R.T.德·喬治著,裘輝譯:《創造性與權威》,《國外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還有學者全文譯介了19世紀俄羅斯文學批評家杜勃羅留波夫論述權威與教育的一篇哲學論文,該文認為絕對服從會對兒童的自然邏輯和意志發展產生致命危害性,使他們缺乏獨立判斷與見解,對于發展兒童的道德和良心意識更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因為“一個人如果習慣了不通過思考去行動,如果他的行動不是出于自己深信其正當、善良……那他就會善惡不分,做了違反道德的事而毫不感到良心上的不安”,最終成為“最卑劣的感情與傾向的犧牲品”*〔俄〕杜勃羅留波夫著,任鐘印譯:《論權威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研究與實驗》1982年第2期。。可見,這些觀點以非常鮮明的批判意識契合了其時在權威問題上的反思精神與重建進程。
正是在這種具有高度思想解放特性的政治與文化之多重情境的促動下,各種關于權威的新式說法和概念開始漸次替代“絕對權威”論,成為推使整個國家和社會走向現代理性的重要思想性元素,如主張在學術研究、文藝創作和教育工作等領域全面恢復和樹立“實事求是的權威”、“實踐的權威”和“科學的權威”,迅速成為思想文化界沖破極左思潮束縛、全面推進撥亂反正的基礎性動力;“四個現代化的實踐是衡量一切的權威”“社會主義法律應有極大的權威”等認識的廣泛散播,更極大地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結構和重心的調整與實踐。
綜上觀之,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歷史契機,對“絕對權威”論這種極左思潮的深入批判與沉靜反思,著重彰顯了權威的相對性特征,以此為中心構建出相對理性化和富有邏輯性的權威理論框架,在全社會尤其是思想理論界奠定了科學而理性地認識和理解權威的基本準則,有效扭轉了很長時期以來國人對于權威的“左”傾化觀念,“絕對權威”論失去了神壇般的地位和影響,重建權威的現代理性觀點開始涌現:“羨慕期求權威嗎?那就摒棄人為的‘權威者’姿態,從平凡處做起,從一點一滴積累起。”*汪遠平:《試談教師的權威》,《人民教育》1981年第9期。對“絕對權威”論的批判還帶動了一批思想理論問題的重新探討,權威問題與真理(觀)問題、實踐標準問題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構成一組互相交織、彼此鑲嵌、互為“他者”、因緣為用的“課題共同體”,很多基礎性問題的框架重構對包括哲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等在內的很多學科(尤其是與此相關聯的中共黨史和國際共運史)都產生了積極影響,非常有利于這些學科在研究理念、方法和內容等方面的改善與重塑,展現了撥亂反正時期乃至整個80年代中國學術研究的強大生命力。總之,對“絕對權威”論的批判及其所取得的闊泛的理論成果,既是撥亂反正時期政治和社會變遷的積極回應,也是學術研究領域之理論自覺和思想重建水平提升的邏輯結果。
三、主流意識形態重建與權威理論的另一路向
每一種政治思想的重塑都不會是單向度的,因其受到政治格局、社會局勢、文化生態和意識形態重組甚至一些突發事件等更多復雜因素的影響與牽制,權威理論亦如此。伴隨著思想文化界深入批判“絕對權威”論并逐步取得重要的理論突破,權威理論的重建也在多種歷史因素的推動下向著另一路向轉換,并呈現具有特殊理論邏輯的思想形態。
權威理論形態重塑進程中的這一路向,明顯受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泛起的一股溢出傳統意識形態范疇的社會思潮的刺激。面對這種社會思潮,中共黨內對其性質、范圍和政治定位存在多種認識和概括,但大都認為其具有鮮明的無政府主義特征或傾向,并將其視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延續。而就黨內情況來看,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的各級組織和政府機關中的派性思想與活動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消除,組織渙散和紀律松弛等現象異常嚴重,尤其在界定和處理新泛起的社會思潮的過程中,黨內一度出現意見分歧,使中共中央認定社會思潮與黨內的這種無政府狀況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從而加劇了黨內的政治危機感,甚至有論者斷言無政府主義的“陰魂在祖國上空仍然時隱時現”,“把一切權威和服從統統看成是應該詛咒和應該摧毀的東西”,“它會腐蝕人們的思想,渙散人們的斗志,損傷社會機體”,批判和克服無政府主義思潮絕不是“小題大做”“庸人自擾”*顧肇基:《談談無政府主義》,《解放軍報》1979年11月23日。。
從較長的歷史時段來看,社會和黨內出現的這些政治傾向,既是“文化大革命”所引致的政治失序格局的慣性賡續,也是新一輪思想解放潮流的興起和以往嚴苛的政治控制機制漸趨放松及其帶來的社會自主空間擴大的結果,又與執政黨在調整政治領導結構之際一度出現的部分權力真空等情況有關。鄧小平迅速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于1979年初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四個堅持”(即“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指出,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開展經濟建設和克服官僚主義等,都要靠發揚民主,“但是,沒有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這些。講黨的領導,強調要有統一領導,要有權威”,沒有黨的統一領導將“一事無成”,“列寧非常強調集中統一,強調紀律”。在他看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將主要精力投入撥亂反正、清理極左思潮、推動經濟建設等緊迫任務,未能及時提出、闡釋并宣傳新的權威指導思想,因此提出“四個堅持”“可能比較有力量,針對性較強。空泛的語言多了,針對性就不突出,也缺乏說服力,缺乏動員的力量”,思想理論界應該借此契機形成“一個主導思想”,引導人們團結一致向前看,多宣傳黨的守紀律、艱苦奮斗等好的傳統。*《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99—500頁。此后,鄧小平開始不斷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在新的主流意識形態建設中的權威性,并且高度凸顯黨的領導在四項基本原則中的第一優先性:“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保證黨的領導。我們之所以能經得起風浪,黨的領導是最根本的一條保證。黨的領導,是四項基本原則中帶根本性的一條。”*《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41—142頁。
在這種政治情勢下,堅決地確立四項基本原則的權威性很快得到中共高層領導群體的認可與支持,很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對重樹黨的領導權威展開了進一步闡述。1979年6月,華國鋒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在政治上“實行必要的高度集中”,堅決維護人民政府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執行人民意志的領導者和管理者的權威”。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在學習葉劍英國慶講話時強調,在黨的威信已經受到“文化大革命”嚴重損害的情況下,必須堅決抵制和批判當前在少數人中間出現的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要在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中進行增強黨性和黨的觀念的教育,“自覺地服從黨的領導,維護黨的權威,特別是要維護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戰斗司令部——黨中央的權威,同一切削弱、擺脫黨的領導的傾向作堅決的斗爭”。胡喬木則從社會主義建基于所有公民的利益基本一致的理論前提出發,認為整個國家和社會擁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道德,因此必須擁有“共同的領導”,并“承認這種共同領導的權威和力量”,“天安門事件不是為了破壞我們的共同領導,是為了重新建立這種共同領導”,“如果有人打著天安門事件的旗號,要求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要來瓦解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權威……他們不是在宣傳天安門事件,而是在污蔑它”*《胡喬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8、79頁。。可見,這些具有高度指導性的思想論述已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尤其是黨的領導視為一種必須遵從的政治圭臬和不可逾越的規則邊界。盡管當時更多的高層政治話語在具體表述中并未將四項基本原則直接等同于新的政治權威,但其間內蘊著的權威性特質已經相當明顯。
思想理論界也針對這股社會思潮,從多方面論述重樹政治權威的根本價值和現實意義。一些批判者基于傳統的政治認識,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與中共的政治領導之間的因果聯系,認為在“文化大革命”后集中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推進國家重建任務等迫切情勢下,“在某些方面,更要強調講集中,講紀律,講統一意志……不顧大局,鬧個人主義是不對的。無理不能取鬧,有理也不能取鬧”*《要重視紀律教育》,《解放軍報》1979年12月5日。。有論者則從解釋社會主義民主內涵的層面指出,“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人們討論民主比討論權威要多得多,“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林彪、“四人幫”等政治勢力是從踐踏民主和褻瀆權威兩個方面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傳統的,因此“我們既要講民主,又要講權威,講服從”,“發揚民主固然不可少,服從權威更是不可缺”,“這權威,就全國來說,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就各地、各單位來說,就是各級黨委、各級人民政府的領導;就軍隊來說,還有中央軍委、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首長的領導”*征平:《民主與權威》,《解放軍報》1980年2月8日。。還有論者主張要劃清反對個人崇拜和維護革命權威的是非界限,認為革命權威是人民的權力和利益的集中體現,服從革命權威和維護黨的領袖人物的威信,“本質上是行使人民的權力,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反對因為批判個人崇拜而完全否定領袖人物威信的傾向,批判個人崇拜“恰恰是為了科學地正確地肯定領袖人物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威,領袖集團的權威,領袖人物的威信”*施君喬、李鵬飛:《反對個人崇拜 維護革命權威》,《文匯報》1981年8月29日。。可見,思想理論界對于重樹權威的理論思考,既帶有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化底色,又具有撥亂反正時期的鮮明時代特征。
與此同時,為解決黨內長期存在的各種無政府現象,從1979年開始,中共中央以擬訂《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草案)》為契機,強化宣傳民主集中制對于重塑中央權威地位和黨內政治關系的根本作用,通過高度強調“集中是民主的指導和歸宿”和“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突出民主集中制框架下集中對于民主的規制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片面強調民主,否定集中,必然導致分散主義、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狀態,削弱或破壞黨的領導”*《黨的基本知識》,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頁。,并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四大服從”為核心內容的“高度集中”思想:“所謂高度的集中,主要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決不允許在行動上搞自由主義,搞無政府主義”*鄭仲兵主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403頁。,“在這里,服從就是集中,沒有服從也就沒有什么集中”*何匡:《也談民主集中制》,《讀書》1980年第5期。。鑒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黨的現狀,這一思想在黨內得到相當普遍性的認可與支持,并推動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和中共十二大在最高政治層面確認了“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的重要制度規則。在此期間,思想理論界大量援引列寧關于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建立高度的集中制和鐵的紀律以及強調思想統一的理論,認為列寧的這些理論學說“無可置疑地具有普遍的意義”*郭用憲等:《列寧論黨的集中制和紀律》,《光明日報》1980年6月5日。,為“高度集中”思想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傳統理論支持。這一思想的提出集中彰顯了黨內對于由“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政治權威失落情勢的焦慮感和重建政治權威的緊迫感,它以非常鮮明的立場和堅決的態度,試圖收縮和壓制黨內的無組織化現象,從而基本確立了一種特殊的權威理論原則,關于民主集中制理論闡釋的側重點顯然在這一維度上發生了側移,展現了一種政治權威在重新樹立之際所具有的強大統攝力量,極大地強化了四項基本原則尤其是黨的領導之權威性的深度論證,是撥亂反正時期重塑政治權威的一種典型性和征候性的表達概念。準此而論,“高度集中”思想不僅促進和刺激了黨內權威理論的重新生成,而且其本身便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權威理論。
經過密集的政治宣傳和理論解釋,新的政治權威原則迅速得到非常廣泛的認可與接受,四項基本原則很快產生了具有實質性的政治規制作用,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很多層面都對突破這一權威性原則的思想或行動產生了較為敏感的感受和體認,如對《苦戀》展開的激烈的政治批判即體現了這種態勢,并折射出中國思想文化界在批判“絕對權威”論之際所同時發生的政治心態的微妙變動。重塑政治權威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種具有悠久傳統的道德化理想所構成的,體現了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政治文化中長期流行的某些價值準則。
但受益于對“文化大革命”以及更長時間的極左思潮歷史的反思和批判,部分思想理論工作者也在若干方面就如何理解這種權威理論的重心尤其是黨的領導展開了具有時代訴求的探索和思考。他們大都認為,從黨的領導的內容和途徑來看,重點是加強政治領導而非以黨代政,黨所承擔的領導責任從來就不應當是直接管理,“僅僅是而且必須是在所有這些方面實行列寧所說的‘總的領導’”,即通過路線、方針和政策指引國家的發展方向,那種由黨包辦一切、把黨的領導變成對國家生活的直接管理,從而使人民管理國家、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根本權利不能正常實現的現象,“是同黨的性質和它作為國家生活領導者的地位不相稱的,因而是必須改變的”,“這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熊復:《試論黨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紅旗》1981年第9期。;從黨的領導體制來看,必須堅持集體領導,個人決定一切的領導方法從根本上違背共產黨的世界觀和組織原則,我們固然需要維護領袖人物的權威,“但這種宣傳和維護必須同宣傳和維護黨的權威和領袖集團的權威一致起來”*施君喬、李鵬飛:《反對個人崇拜 維護革命權威》,《文匯報》1981年8月29日。;從黨的領導的手段或方法來看,決不能采用強制的方法,而只能通過說服教育,使被領導者自愿接受和服膺黨的權威,“這是牽涉到黨和群眾的關系這樣一個生命攸關的大問題”,對人民群眾實行強迫命令的本質是“有權就有一切”的心態,極其嚴重地破壞黨和群眾的正常關系。這些思想建樹具有很冷靜的辨析思維,在一定程度上賦予新的政治權威理論以明顯的理性化色彩和原則性理念,事實上劃定了權威行使的又一重現實邊界*在一些情況下,一些論者將四項基本原則尤其是黨的領導比喻為規訓“某些混亂的、錯誤的思想”并加以“引導糾正”的“韁繩”,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這種重樹權威的思想理論的某種邊界性表達。參見敢峰:《韁繩的哲理》,《人民日報》1981年6月9日。。
權威理論重塑進程中的這種理性化傾向,也體現在部分思想者對民主與集中之關系的重新厘定,因為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或民主集中制原則是重構權威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主流意識形態體系的關鍵要素,正如論者指出的那樣:“民主同集中,或者說民主同權威和服從,從來都是聯系在一起的。”*征平:《民主與權威》,《解放軍報》1980年2月8日。正因如此,一些研究者更傾向于從民主的基本內涵和本質屬性之角度,重新詮釋重樹權威的理論重心。他們指出,民主的原意是多數人的統治,而在民主集中制這個整體中,服從也就是集中,“民主與集中的實質或核心都是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它們之間并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們通常說正確地理解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其實就是指正確地把握好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原則”*馬鳴:《共產黨“尤其要集中”嗎?》,《文匯報》1980年9月16日。,因此真正的民主就是服從多數人的意志,“多數人的意志對于民主來說就是一種權威,承認并且服從這個權威是民主的基本原則;否定了這個基本原則,就是否定了民主本身”,民主又是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國家制度或形態,“而國家本身就是一種權威”,所以,“民主不能排斥權威,而是以一定的權威為前提的”*龔希光:《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理論政法部編:《四項基本原則通俗講座》,廣播出版社,1981年,第129頁。。基于這種認識,有論者更明確提出要樹立“民主的權威”,所謂“民主的權威”首先是指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不容侵犯,是指主人(人民群眾)和公仆(官員干部)的關系不容顛倒,官員干部的權力來自于廣大人民,干部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民主的權威就是由此而來的”;“民主的權威”體現在黨內生活中的準則就是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和全黨服從中央所對應的理論基礎正是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誰也不能違反,這就是民主的權威”。顯然,這些頗具創造性的思考使民主與權威(集中)這兩大元素之間形成了一種張力關系,成為新的政治權威理論結構中的重要一極。
可見,雖然撥亂反正的最終邏輯結果之一便是重建并強固新的政治權威,此時重樹政治權威的理論論述以及實際的政治運作也與“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整個國家和社會極力強調權威的思想潛流之間存在內在的邏輯關聯,但很明顯的事實是,這一重樹權威的理論底色已與極左思潮宰制下的“絕對權威”論有著本質不同,它首先要受到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即漸次興起的具有普遍民意基礎的社會主義民主思想及相應的理論建構的制約,任何權威的形成和擴張都至少在形式上必須尊重民主意愿與程序,不僅要以民主為基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且要以民主理念的堅守和伸張鞏固權威自身。很多學者意識到切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及其相應的體制建設,對于預防新的“絕對權威”論以及與此相關的極左思潮以改頭換面的形式而重新泛起的根本性意義,從而形成了一種有效的理論制約力量。顯然,這是撥亂反正時期民主進程的推進以及自《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至中共十二大前后生成的“高度民主”思想的反映,生動地詮釋了撥亂反正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生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此外,重樹權威還受到其他一些政治、社會和文化語境的制約。在初步啟動的法制建設進程中,“要使社會主義法制具有極大的權威”、貫徹有法必依和違法必究的法律原則等已成為非常普遍的觀念,這種觀念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利于對政治權威本身的施行和擴張構成一種制約機制。在呼吁和重樹權威之際,學術界還清晰地意識到必須警惕和克服官僚主義,他們經常引用列寧關于“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之論斷,說明官僚主義的滋長與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泛起及其所帶來的權威失落之間的因果關系,“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證明,凡是官僚主義滋長的時候,無政府主義就抬頭;哪些地方官僚主義嚴重,無政府主義就泛濫成災”*馮干文:《論無產階級國家經濟職能的發展》,《廣西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反對否定一切權威的無政府主義,另方面要反對無限擴大權威作用的官僚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徐鴻武、李敬德:《恩格斯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斗爭》,《江淮論壇》1980年第6期。。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政治境況,這一思想見地至少在理論上為杜絕政治權威與官僚主義體制的畸形結合提供了一道屏障,顯然有利于權威結構的理性化。與此相聯系,震驚全國的“渤海事件”公布后,很多人都對這件生產事故所暴露出的“官僚主義瞎指揮”和民主管理缺失現象提出批評,認為重建社會化大生產所不可缺少的權威和培養敢于指揮、敢于管理的各級領導人是必要的,但“問題在于講權威必須把權與責統一起來”,“有權就必須有責”,由此提出權威承擔者必須要有責任意識,徹底改變管理體制中的權責不明狀態,“這是當前體制改革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齊昶:《權威與責任》,《經濟管理》1980年第9期。。這實際上提出了任何權威所必須具備并踐行的責任倫理向度。顯而易見,新的時代境遇和理性言說為重樹權威所設定的各種前提預設與條件限制,將從很多重要方向防范在新的歷史時期再次產生類似“文化大革命”時期“絕對權威”論的權力話語,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權威理論的現代性,展現了撥亂反正時期思想理論研究的包容性和開放性。
承上所論,在不斷變動的政治局勢和中共高層的推動以及思想理論界的持續努力下,重樹政治權威的思想討論匯聚為一種較為完備的理論形態,并在撥亂反正時期的最后一段時間里成為中國政治社會重塑更大范疇內的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一部分。在新的權威理論的基本結構中,權威或集中與民主是一對基本的認知范疇,它既批判“絕對權威”論對于人類社會的基本民主權利的踐踏,又確認執政黨的權威對于維系政治社會有機發展的內在要求,“濫用民主,就是毀滅民主本身;濫用權威,也就是毀滅權威本身”*龔希光:《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四項基本原則通俗講座》,第131頁。這樣的思想觀念得到非常廣泛的接受和認可,從而使新的政治權威與治理對象之間形成了較具張力的微妙關聯。因此,這是相較于“絕對權威”論的一種弱權威理論,既是撥亂反正時期整體權威理論的重要構成,也是權威理論發展的最終邏輯結果。這一理論導向為此后中國改革進程指導思想的設計和更新提供了某些思想養分,它所蘊涵的現代性規則和傳統性質素的共存結構,與80年代中后期泛起的“新權威主義”理論之間存在著一種不可輕忽的精神聯系,更影響了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政治治理原則和結構的演變軌跡。
四、余論:權威理論的時代特質與亞類型政治思潮的發現
縱觀撥亂反正時期權威理論的重塑進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即歷經多重演化: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最初一年多的時間里,中國政治社會極端強調重建權威的根本價值和決定性作用,急切召喚新的“革命權威”形式和體制;以1978年為重要分界點,權威理論向存在密切關系但又具有明顯不同特性的兩種理路分頭嬗變,即伴隨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而對“絕對權威”論的強烈批判和對權威之地位與作用等問題的理性探討,以及因應新社會思潮所帶來的復雜局勢而再次高度重視權威在政治社會中的統馭作用和對盡快樹立并鞏固嚴整的政治權威理論與體制等問題的復雜討論。其中,對“絕對權威”論的深入批判和解構與新的政治權威理論的重塑和調適具有很明顯的同步性,二者之間還形成了比較強烈的張力關系以及特殊形態的邏輯自洽和共生結構,并且同時得到廣泛的理論解釋和政治接受;這一特殊關系和結構既存在于撥亂反正時期的整體歷史躍遷之中,又同時存在于很多思想者個體的思維結構與論證話語之間,表明“思想史或意識史的演進——即便是在短時間內,分裂出意義軌跡的不同岔道”*郭若平:《塑造與被塑造——“五四”闡釋與革命意識形態建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95頁。。而權威理論的不同演進理路固然有其性質和特征的本質分野,但它們之間顯然也潛蘊著一脈相承的精神維度,即高度重視權威在國家和社會結構中必須發揮基礎性的地位和作用,這體現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傳統乃至更為久遠的歷史時期里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結構中某些固有元素所擁有的巨大而復雜的影響力。
可見,權威理論重塑的歷史內容非常豐富、多變,其演進過程不是單向度的,也不是簡單的線性遞進過程,各種類型的批判者和思想者都對權威理論作出了各有側重點的公共言說,構筑出在權威問題上的眾聲喧嘩的思想圖景,形成了撥亂反正時期特有的一股思潮。顯然,這一思潮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得益于對“四人幫”及至“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批判以及在此基礎上啟動的撥亂反正進程,如何認識、糾正和反思“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及其對民主集中制的破壞是基本的參照點,表明權威理論的重構既推動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廣泛性批判,其本身又是這種政治與文化批判的邏輯性結果。新塑型的權威理論在基本的原則性上具有較強的自洽性,盡管在相關政治制度的設計與遵行方面還有待培育,但包括權威理論在內的一系列相關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的初步重建及其所形成的廣泛共識,極大地提高了國民對于權威的思想認識水平。此后,無論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何等復雜的變動,“絕對權威”和個人崇拜的荒謬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
因此,權威理論的重塑與演進主要是撥亂反正時期政治和社會變動的思想產物,鮮明地呈現出撥亂反正時期之革舊徙新的強烈訴求和時代特征,顯現了這一時期中國思想理論創造的政治化和社會性特征,而其所形成的不同發展路徑更充分展現了這一時期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自身的起承轉合及其歷史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以及經過幾十年“左”的思潮浸染的中國在重建政治結構和社會秩序之歷史進程中的時代特質,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整個80年代乃至此后很長時間里的中國政治政策和發展方向選擇的重要因素與變量。權威理論重塑所展現的這種時代特性既源于對以往歷史某些關鍵元素的因襲,又源于對開創未來的擘畫與希冀,就此而言,“當代政治思潮在20世紀80年代的出現與展開,是以對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反思以及對權威體系的徹底改造作為其總體特征的”*高瑞泉、楊揚等:《轉折時期的精神轉折——“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思潮及其走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頁。。
但隨著時光推移,權威理論在80年代初期的歷史變遷逐步湮沒于快速行進的國家和社會變動以及更為繁復而蕪雜的歷史信息中,長期不為研究者重新發現,成為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但權威理論對于當代中國依然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自90年代以降,中國的體制轉型進程一度遇到了諸如社會共識度不高等很多困難。產生這種局勢的因素很復雜,但與未能及時清理當代中國思想史中的許多重大理論課題,并將其及時納入當代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傳統有著密切關聯,換言之,就是缺乏對于相關歷史課題的學理性研究以及相關歷史思想資源的積極殷鑒。很明顯,歷史不僅僅屬于歷史自身,它與當下和未來之間都存在著非常密切的(因果)聯系。缺乏對歷史的理解、解釋和尊重,我們便無法在推動中國改革之路上獲得積極而有效的進展。
而權威理論的思想史研究在學術界的缺位,當然也與政治思潮自身的文化屬性和內在結構有關。任何一種產生重大社會影響并在一段時期或特定層面發揮主導性作用的政治思潮,固然受到諸多現實因素的影響,但完全憑恃政治外力和社會需要的推動是難以完成的,即使勉強完成,也會不可避免地存在難以彌合的思想與邏輯障礙。因此,政治思潮之公共影響的發揮還必須仰賴思想理論自身的知識自足性和邏輯嚴密性,需要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議題的共時性響應和支持。任何一種具有主導性的政治思潮生成與發展的結構和機制往往不會是單向度或一維化的,它往往具有非常復雜的知識結構和邏輯體系的多面相構建。在這些主導性思潮的表層之下,往往潛流著一系列與之相關的亞類型思潮。這些亞類型思潮雖然直接受到主導性思潮的激發并存在密切的隸屬關系,但亞類型思潮也以專業的審視角度和強大的論證力量,深入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內在結構與肌理,不僅對主導性思潮發揮著無可替代的支持性作用,而且可以滲透至與主導性思潮相關的一些重要思想論域甚至邊緣地帶,轉而激發起更多的問題意識、思想論爭和公共參與,從而放大主導性思潮的影響力和穿透力。可見,亞類型政治思潮極大地豐富了主導性政治思潮的基本脈絡和發展紋理。離開這些亞類型思潮,主導性思潮的邏輯力量和思想價值將受到歷史與史學的雙重拷問,其論題的真偽性以及被賦予的意義蘊涵無疑將受到影響。
權威理論的重塑與演進便是這樣一種亞類型政治思潮。這一思潮并未直接呈顯于中國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之框架的表層,也不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它潛藏于各種重要的顯性化政治思潮的表象和結構之下,并伴隨著這些大的思潮的變動而發生方向轉換和重點側移。它附屬于與之相關的更為宏觀的政治思潮,對這些大的思潮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印證、補充和強化的作用。在此意義或層面上,“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政治社會對于權威的極力強調、自1978年開始的對于“絕對權威”論的深入批判和重建政治權威的理論建構,應該分別是“兩個凡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和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核心價值的主流意識形態重建等主導性思潮之下的亞類型政治思潮。這就是權威理論討論這樣的思想文化形態無法有效進入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學書寫的重要原因。
長期以來,學界對于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多地關注宏觀的政治轉型和社會發展對思想文化的直接制約與影響,因而偏好于對主導性政治思潮的史學建構和書寫,這固然有利于從宏觀層面理解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輪廓和學術內蘊,但這種研究理念和寫作結構顯然將思想史理解為政治社會史的一種附屬物和產出物,低估了思想(史)自身的某種獨立性和自足性及其拓展性。因為很明顯,亞類型政治思潮生成后,反過來會對主導性思潮乃至更廣泛的政治和社會現實產生多樣化的復雜影響,這種反作用力量與當時的政治社會和主導性思潮之間可能呈現正向建設性關系,也可能呈現負向解構性關系,從而生產出更多具備闡釋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場域。如果無視這些亞類型思潮的作用和地位,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書寫肯定是不完整甚至不科學的。
通過考察權威理論在撥亂反正時期的重塑與演進,我們完全可以領略一種特殊的亞類型政治思潮在歷史轉型期對所謂“黃金往昔”的延纏糾結以及在新的政治和社會壓力下向符合人類普遍道德的進步方向逐步轉換的文化圖景。而展現一種政治理論在相對短暫的特定歷史時期內的急劇轉變,既可為深入理解和感悟撥亂反正時期的時代特質與精神風貌提供一種獨特的歷史維度,更可為增強探察歷史深處的學術能力并由此彰顯歷史研究之魅力提供持續綿延的思想與文化資源。這不僅反映著一種文化理論的更新,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思想進步,更凸顯了研治此類貌似細微卻反映社會變遷的歷史學問題的重要性和吸引力,因為“人類事務變化多端的更新與延續結合而成的萬花筒,正是這門學問的迷人之處”*〔英〕邁克爾·斯坦福著,劉世安譯:《歷史研究導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第7頁。。就此意義言之,關注權威理論在當代中國史上的特殊形態這樣的歷史與理論問題,更能進一步昭顯歷史研究以追求真理為根本訴求的文化特質,盡管獲致并捍衛真理存在很多難以克服的困難與障礙。
而思想理論界顯然應當為此承擔更多的責任和使命。在權威理論的重塑進程中,思想理論界以極大的政治參與和理論熱情參與其間,尤其在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絕對權威”論的批判和對新時期政治權威理論的理性思考等方面,知識分子更擔當了最主要的文化角色。他們對現代迷信的批判和個人崇拜的警惕,洋溢著整個80年代立場鮮明的啟蒙主義理想。歷史學界應該繼續關注和挖掘當代中國史上的很多類似議題,重新發現、理解和建構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內容、結構與譜系,使那些曾經具備普遍性價值的文化成果,真正成為推動國家民主政治進步和人類自由幸福的常識,“人類為杜絕過程的悲劇所采取的努力中,鉤沉廓清常識則是必需的”*艾云:《尋找失蹤者》,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90頁。。從此處瞻望未來,如何在尊重和還原真實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觀照具有長遠性和前瞻性的國家與社會之公共利益,通過關注和研治思想文化史以彌合知識與社會、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裂痕,進一步推動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以及改革開放史的深入研究和重新書寫,從而為中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制度的完善提供更豐富多元的思想與歷史資源,依然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拷問歷史研究者的政治智慧和學術良知的基本課題。這便是我們重新注重權威理論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義與價值所在。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 北京 100080)
(責任編輯 趙 鵬)
The Remodeling and Evolution of Theories of Author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Bring Order out of Chaos
Wu Zhijun
The remodeling of theories of authority had multiply evolved as an echo of issues that arose because of changing times and id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bring order out of chaos.It began with an extreme emphasis on reshaping authority after Mao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extending to the synchronous transmutation of the profound criticism, deconstruction of the “undisputed author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new political theories of authority after 1978.These fully demonstrated the self-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and history’s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Th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authority, a sub-political trend that emerged during this period, was highly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China.Therefore, it definitely should be brought into research and academic writing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092=74;K275
A
1003-3815(2016)-08-00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