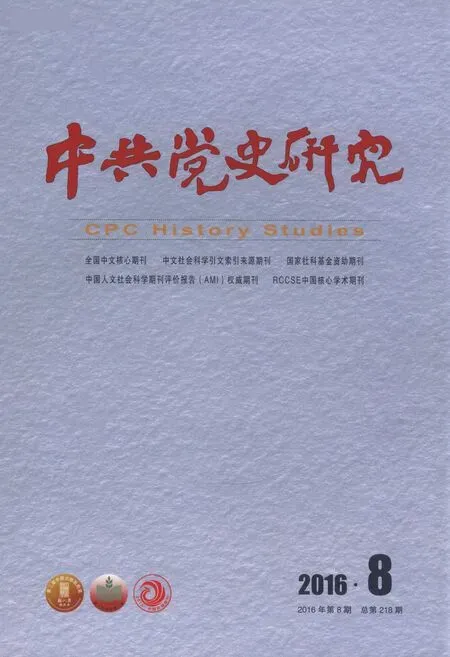民主革命時期國共宣傳工作比較研究
盧 毅
·專題研究·
民主革命時期國共宣傳工作比較研究
盧 毅
民主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宣傳工作的成效大相徑庭。從宏觀上分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其一,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后宣傳日趨保守,而作為革命黨的中共始終保持著極為凌厲的宣傳攻勢;其二,中共宣傳戰線人才濟濟,國民黨的宣傳人才則乏善可陳;其三,中共非常重視宣傳的統一,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紛爭卻使其宣傳日益渙散;其四,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始終未能深入農村,而共產黨則成功動員了廣大民眾;其五,中共十分重視言行一致,國民黨的作為卻往往與其宣傳背道而馳。
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國民黨;宣傳效果
民主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均十分重視宣傳工作。中共自誕生之日起就一再強調:“宣傳鼓動工作異常重要,各級黨部要特別注意的做傳單,壁報,時事畫,小報,小冊子,標語,報告事實消息的小紙片……不斷的刺激鼓動群眾的熱情。”*《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74頁。1932年,紅軍總政治部出版的《政治工作》甚至在發刊詞中說:“宣傳鼓動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中的最重要部分”,“宣傳工作是革命運動的酵母”*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2冊,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第86頁。。而國民黨亦不遑多讓,其軍方曾言:“戰爭之勝利,必賴于宣傳,而進剿赤匪,尤不能不利用宣傳”*《緊張剿匪宣傳工作案》,《軍政旬刊》第1期,1933年10月20日。。蔣介石在談到“剿共”時也說:“宣傳重于軍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4冊,“國史館”(臺北),2011年,第379頁。。其中所透顯出對宣傳的重視,比諸中共毫不遜色。
然而,二者的宣傳成效卻大相徑庭。國民黨執政之初,一般群眾對其宣傳還保持一定的熱情,“視主義為圭臬,視標語如信符……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朱宛鄰編:《福建黨務概況》,福建省特派員辦事處,1935年,第22頁,轉引自嚴海建:《淺析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意識形態層面的劣勢》,《民國檔案》2006年第2期。。相反地,毛澤東率領紅軍向湘贛邊界轉移時則深深感到:“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后,才慢慢地起來。”*《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頁。但這種情況很快發生逆轉。1933年,《國聞周報》即發表文章說:“現在一般民眾,除其黨員外,對國民黨實已重足側目。其厭棄之心理,為不可諱言之事實。”*劉震東:《中國出路問題》,《國聞周報》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1939年,蔣介石也公開承認:“到了現在本黨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無聲,一般民眾不僅對黨無信仰,而且表示蔑視。”*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6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27頁。而陳果夫亦向蔣介石提出:“本黨宣傳工作之不善,由來久矣!以積久之頹風,自難挽回于頃刻。”*李云漢主編:《陳果夫先生文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3年,第26頁。與此同時,中共的宣傳卻獲得巨大成功,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1944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期間,蔣介石便不無怨艾地對其說,他對共產黨的宣傳是“五體投地的佩服”*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下卷,重慶出版社,1992年,第271頁。。1946年,他甚至手令宣傳部部長彭學沛,要求國民黨新聞機構深入研究中共宣傳戰術,“于每星期檢討一次,詳加分析,務求徹底了解然后再研究對策”*《蔣介石指示彭學沛對共黨軍事政治教育社會之宣傳戰術及運用方法切實研究》(1946年5月22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161.42/4450.01-05,轉引自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后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第199頁。。
那么,國共兩黨的宣傳工作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大的反差?鑒于以往學界對此討論不多*近些年專門研究此問題的論文僅有一篇,即胡大牛的《1949年以前國共思想理論及其宣傳比較研究論綱》(《探索》2006年第6期)。該文從兩黨理論體系、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和宣傳條件三個層面,分析了中共壓倒國民黨的優勢所在。然或限于篇幅,所論較為簡單。,本文擬從宏觀層面做幾點分析。
一、攻守之勢異也
大革命時期,由于國共合作和大批共產黨員的協助,國民黨的宣傳還算充滿朝氣,呈現出一派蓬勃生機。特別因為彼時它是革命黨,在輿論宣傳上屬于進攻的一方,可以輕裝上陣,毫無顧忌地高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幟,以此喚醒民眾。而一旦打下半壁江山后,它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這在對待外國列強的態度上體現得尤其明顯。國民黨為了繼續北伐,不得不收斂鋒芒,對帝國主義采取了讓步的政策。陳公博當時便坦言:“在目前我個人最感覺痛苦的,如果要國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國主義不可,但同時要國民革命成功,非妥協帝國主義不可……自從革命軍到達長江以后,我們已避不了這種矛盾了。”*陳公博:《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貢獻》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15日。對封建地主,同樣也是如此。而這種政策的急劇調整,自然會給有關宣傳帶來很大的困擾。
同時,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換也使國民黨的宣傳日趨保守、暮氣漸顯,甚至連蔣介石都批評道:“我們的宣傳不能主動,理論亦缺少戰斗性。”*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9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184頁。實際上,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身處執政地位,有時難免投鼠忌器、畏首畏尾有關。曾任《民國日報》主編的陶百川回憶:“《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向由邵力子先生主編,邵去廣州參加革命軍后,改歸陳德征先生接辦。后陳過忙,不能兼任,乃交我主編。因為它有那么輝煌的歷史,我以后生小子擔當重任,不能不特別用心,但它的聲光顯然不及邵陳時代了。那固然是由于我資淺能鮮,但未始不是由于中國國民黨己從在野黨成為在朝黨,《民國日報》既是黨報,言論自由受著限制,魅力自然減少了。”*陶百川:《困勉強狷八十年》,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1984年,第164頁。《中央日報》更是如此。1940年5月,孫科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對于宣傳工作,頗多評責,尤于《中央日報》深致不滿”,時任中宣部部長的王世杰則解釋道:“實則近來中央對于黨報言論,諸多限制,主持報事者,初無自動發言之余地。”后來他又指出:“《中央日報》為本黨中央言論機關。執筆者懼受各方干涉與指摘,不易發揮自己見解;群以為苦。”*林美莉編校:《王世杰日記》上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2012年,第267、467頁。應該說,此確為肺腑之言,深諳個中苦衷。
不難想見,這種顧忌重重和諸多限制必然削弱國民黨宣傳的吸引力。早在1929年,天津《大公報》就說:“報紙專為政府作宣傳機關之結果,全國言論界單調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讀報之興味,最后足使報紙失其信用。”*《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表示》,《大公報》(天津)1929年12月29日。1933年,它又發現:“上海大報時受干涉,動多顧忌,故群眾對報紙浸失信仰,而全國終不能造成一種眾流共信之輿論中心。”*《如此檢查新聞》,《大公報》(天津)1933年5月29日。其中對國民黨宣傳缺乏吸引力的原因分析,可謂鞭辟入里。在抗戰后擔任中央日報社社長的馬星野也曾反思官辦報紙的作風:“在抗戰期中,一般人都感覺到官辦報紙不如商辦報紙辦得好,官辦報紙從政府得到經費補助和平價物資,照理比商辦報紙容易經營,可惜多半都流于官僚化,衙門化,缺乏獨立和創造的精神,以致不能與商辦報紙競爭。抗戰勝利了,新聞事業勢將有更蓬勃的發展,官辦報紙的這種作風,必須徹底改變,否則一定要在競爭中被淘汰。”*馬星野:《官辦報紙的作風必須改變》,《中央周刊》第7卷第34、35期合刊,1945年9月7日。從后來的情況看,庶幾一語成讖。
與此相反,中共作為革命黨,其宣傳仍是高歌猛進、沛然莫御,具有犀利尖銳、旗幟鮮明的戰斗風格,且能以美好愿景相號召。當時就有人說:共產黨自與國民黨分裂后,“從此嶄然露頭角,以急進之思想號召青年,以在野政黨之地位攻擊在朝之國民黨,其吸引力之大,破壞力之強,大足自豪”,同時“宣傳國民黨之革命為右,標榜該黨本身所領導之革命為左,使人人心目中有無產階級革命將來總有一日來臨之印象”*周炳林:《我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批評》,《獨立評論》第62號,1933年8月6日。。國民黨還曾總結中共宣傳的手法和原則:“把一切解放區的‘事’盡量描寫的一百二十分的‘明朗’,相反的卻對我們盡量的污蔑攻擊”*《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文化”,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1頁。。而在中共這種猛烈抨擊下,國民黨屢屢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檢討說:“奸黨每乘我上述之宣傳弱點發動攻勢,其結果彼攻我守,彼陳訴我辯護,彼為主動我為被動,永遠落后,永無反擊可能”*《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文化”(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01頁。。對此,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唐縱亦感同身受:“本黨在朝,對于政府之缺點,不能不加掩飾,攻擊的話容易講,亦容易聽,頌譽的話不易講,亦不易聽。”*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第355頁。
面對中共凌厲的宣傳攻勢,國民黨只好采取龜縮回避的消極政策,王世杰提出:“關于宣傳,我不主張與中共多打筆墨官司,否則中共問題日日在國人及國際人士眼目中喧嚷,事實上只是為中共宣傳。”*林美莉編校:《王世杰日記》上冊,第680頁。這無異于一種鴕鳥政策,恰恰給中共宣傳留出了更多空間。曾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的吳國楨后來便說:“在那些年代里,毫無疑問,共產黨宣傳是最活躍和普遍存在的。但很奇怪的是,國民黨卻始終保持沉默和遲鈍。當共產黨從各方將指控對準國民黨時,國民黨卻裝得若無其事,甚至不屑答辯……所以,國民黨在丟失中國大陸之前,就早已在宣傳上打了敗仗。”*吳國楨著,吳修垣譯:《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4頁。這番話道出了國民黨宣傳失敗的一個重要教訓,即消極回避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除了消極回避,國民黨還試圖用粉飾太平來抵消中共的宣傳攻勢,即報喜不報憂,甚至不惜編造謊言。國民黨中央社當時炮制了許多“捷報”,結果使其新聞信用暴跌。時人即言:“從國民黨中央社所發的戰訊中,不難理解,它所宣傳的勝利,正是它的失敗;越大吹‘戰果輝煌’,越是敗得精光”*傅斯甫:《〈貴州商報〉回憶錄》,《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內部資料,1986年,第81頁。,“到后來,凡是口呼‘保衛’的地方,不久這地方一定失掉;凡是大言‘毫無問題’的地方,不久一定要出問題”*劉光炎:《怎樣對民眾宣傳》,《臺灣黨務》第12期,1951年7月1日。。一時間,中央社說謊成為社會公眾的普遍共識,軍統局曾得到這樣的情報:“查蜀都中學近來紛紛傳謂,中央通訊社所報導之消息不確,甚至成為一般之口頭禪。如某生詢以某事確否?彼則答曰:中央社。”*重慶市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白色恐怖下的新華日報——國民黨當局控制新華日報的檔案材料匯編》,重慶出版社,1987年,第625—626頁。
與這種喜好粉飾的心理相匹配,國民黨宣傳部門還對輿論批評十分敏感和忌諱。著名戲劇家吳祖光回憶,他在1946年“對國民黨的當政者內心空虛粉飾太平就深有體會”,“具體表現就是劇本中經常會有正面和反面的斗爭,而審查官都一貫把反面的視為是批評當政者,而把正面事物認為是歌頌共產黨;就從來不會把當前的政府視為光明的象征”。“那時的國民黨已經完全喪失了信心,自然就永遠把自己擺在挨罵的地位上,再也不能想到會有人夸獎他、贊美他。”*吳祖光:《游戲人間》,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8—9頁。而這一切,顯然都與國民黨處于守勢有關。
二、宣傳人才的充沛和匱乏
對國共兩黨宣傳的差異,唐縱曾總結道:“異黨在野,辦文化宣傳的人,都是最優秀的人才。本黨在朝,優秀的人都做了官。”*《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55頁。這一觀察是頗為新奇和敏銳的。誠如其所言,中共自創建伊始就集中了一大批致力于宣傳的優秀人才,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博古、張聞天、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均是宣傳的行家里手,在理論上建樹頗豐,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同時,為了鼓勵更多的人才從事宣傳工作,中共還比較妥善地處理了以下兩種關系。
一是宣傳工作與軍事工作的關系。大革命失敗后,中共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但對宣傳工作仍給予了一如既往的重視。1928年10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便表示:“過去邊界各縣的黨,太沒有注意宣傳工作,妄以為只要幾個槍就可以打出一個天下,不知道共產黨是要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內部資料,1979年,第454頁。到了戰火紛飛的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對宣傳工作與軍事工作的關系又有了進一步的清晰定位。1940年9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指出:“要把一個印廠的建設看得比建設一萬幾萬軍隊還重要”,“要把運輸文化食糧看得比運輸被服彈藥還重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87頁。。1942年5月,毛澤東更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公開提出:要想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僅僅有“手里拿槍的軍隊”是不夠的,還要有“文化的軍隊”*《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頁。。這無疑是將宣傳與軍事相提并論,提到了同樣重要的高度。
二是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的關系。眾所周知,宣傳與組織是黨務工作的兩項重要內容,但在實際工作中,組織工作往往更為人們所重視,從而難免會影響到宣傳工作者的積極性。為了糾正這種偏向,中共中央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矯枉過正。1924年5月,擴大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文件強調:“不能認機械式的組織與宣傳鼓動是同等重要的。”“宣傳更重要于組織。”同時規定“地方委員會由三人組織之:委員長兼宣傳部,秘書兼組織部”,亦將宣傳的重要性置于組織工作之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32、245頁。
1929年6月,中共中央通過的《宣傳工作決議案》還特別針對那種忽視宣傳工作、認為“組織重于宣傳”以及主張“先組織訓練而后宣傳”等錯誤觀念指出:有些同志以為只有組織與斗爭工作才是實際工作,宣傳只是“說白話”“做文章”,是一般“文把子”“老先生”的事情。于是,他們指定那些完全不能做實際工作、只能寫幾句文章的人擔任宣傳工作,而且只有組織與斗爭工作不甚緊張之時,才注意到宣傳工作。這使得宣傳工作完全脫離了實際。“黨必須以最大的力量糾正這種錯誤觀念。黨的正確的宣傳工作,便是最實際的工作,而且有推動黨的一切其他實際工作的偉大作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第250—251頁。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于充實和健全各級宣傳部門的組織及工作的決定》中重申:黨內還存在“重組織輕宣傳”的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把宣傳工作看得可有可無,從而有些地方未設宣傳部或者形同虛設。此外還表現在分配干部上,把意識不好或不可靠的分子塞在宣傳部門里。這種傾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黨內某些同志沒有了解宣傳部門是黨在政治上、理論上和思想上領導戰斗的機關,它同組織部門的工作有同樣的重要性。對于這種傾向,必須加以徹底糾正。*《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506—507頁。
1941年6月,中宣部又發布《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對宣傳鼓動工作與組織工作的關系做了詳細闡述:宣傳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是黨的工作中兩個有機的部門,也是其他一切部門工作中兩個有機的部分,它們對于整個黨的工作正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是同樣重要的。對于過去在黨的某些機關與黨員中存在著的忽視宣傳鼓動工作的觀點,必須加以糾正。這份《提綱》還提出:“宣傳鼓動工作的發展,有賴于宣傳鼓動組織機構的健全。在各級黨的組織內建立強有力的宣傳鼓動部門,集中宣傳鼓動的人材,統一宣傳鼓動工作的領導,這是非常必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36—137、138頁。這顯然是要求組織部門為宣傳工作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以上一系列材料表明,盡管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的宣傳工作有時難免會受到其他方面的沖擊,但中共中央始終對此保持警醒,并采取了許多糾偏措施。而這無疑是其宣傳戰線人才濟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方面,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蓬勃興起與抗戰時期延安文藝界的繁榮適足為例證。相比之下,國民黨則除了戴季陶、陶希圣、葉青等屈指可數者之外,宣傳人才乏善可陳。1943年1月,蔣介石手諭中央黨部常務委員陳果夫和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對于文化運動與宣傳工作,今后應多研究發展,但須務求實在,不可徒重外表。應如何加強工作與收羅人才,希即擬具辦法呈報為要。”*《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2冊,“國史館”(臺北),2011年,第383頁。其求賢若渴之心情溢于言表。
但后來的情況仍不容樂觀。1943年9月,蔣介石為了抵制中共宣傳,下令有關部門編撰反共材料,但“其內容幾乎全為共匪宣傳其能力強大而作”,最后不得不親自修訂。他因此一再感嘆:“吾黨現時之宣傳不惟無一能手,而且拙劣已極”;“吾黨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親自動筆幾無法公布,奈何”*《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4冊,第480、472頁。。1944年3月,他又連續在日記中寫道:“對共匪罪行之宣傳文字,中央秘書處不僅英譯詞不達意,即中文亦幾乎大半為共黨所張目,閱之痛心不已”;“本黨干部幾乏人可使之操觚,不勝痛心”*《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6冊,“國史館”(臺北),2011年,第395、399頁。。1945年7月,蔣介石更因《中央日報》編輯、社論的水準“幼稚拙劣,雖中學生猶不如也”,要求將編輯與評論者盡速調換*張瑞德:《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國民黨宣傳人才之匱乏由此可見一斑。
毫無疑問,國民黨這種宣傳人才的匱乏勢必導致其理論宣傳的疲弱。黃紹竑曾回憶:“那時候的黨務,自以宣傳與組織兩項工作為首要。宣傳工作,在表面上固以三民主義為依據,但是在當時真正了解三民主義的,是沒有幾個人。”*《黃紹竑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169頁。王世杰同樣指出:“本黨老同志對于孫中山先生主義,大多只是一知半解,此為最難補救之缺憾。”*林美莉編校:《王世杰日記》上冊,第266頁。復興社賀衷寒亦承認:雖然馬克思主義尚無完全的譯本,但是共產黨人都能講出一套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相反,國民黨人對其尊奉的三民主義,“能夠人人從頭至尾講一遍的恐無幾人”。他認為,這是宣傳成績不如共產黨的一個原因。*梁麗萍:《國民黨主流意識形態的構建與失敗(1928—1949)》,《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4年第3期。曾任銓敘部政務次長的王子壯也說:“北伐迄今已達十余載,而黨義著作之貧乏,不特未能表現于社會科學各方面,甚且解釋主義之著作亦寥寥可數。”*《王子壯日記》第5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2001年,第102頁。
不惟理論宣傳,文藝宣傳亦是如此。早在1934年,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便坦承:“本黨欲增厚黨的文藝運動的力量,則對于國內一般素無色彩之作家,自應予以相當之聯絡,使之漸漸與本黨接近而成為本黨文藝戰線之友軍。惟過去本黨對于此輩作家,完全缺少聯絡,致使大多數皆為左翼聯盟所吸收,此確為失策之事。”*《文藝宣傳會議錄》,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編印,1934年,轉引自唐紀如:《國民黨1934年〈文藝宣傳會議錄〉評述》,《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1943年4月21日,蔣介石觀看話劇《蛻變》后在日記中感慨:“可知本黨之無能,而一般文藝界之思想,仍為共黨所操縱與受其惡化之影響之深也。”25日,他觀看電影《日本間諜》后又說:“可憐張治中、張道藩(分任政治部主任、宣傳部部長——引者注)等毫無政治與宣傳常識,致使吾黨所辦之宣傳機構,幾全為共黨利用而不知也,可恥盍極。”鑒于這種狀況,他于27日緊急召開黨務小組會議,嚴厲批評“宣傳部與政治部之宣傳藝術,毫無本黨革命意義與主義色彩,反被共黨作宣傳,尤以《日本間諜》之影片為甚”*《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3冊,“國史館”(臺北),2011年,第271、284、289—290頁。。
對蔣介石這次發火,王子壯表示:“事實上文藝界黨的力量始終未嘗打入,抗戰以前之左翼作家在上海一帶,甚囂塵上,抗戰以后,一部分表示灰色,而內幕仍為共黨張目。”*《王子壯日記》第8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北),2001年,第168頁。稍后,唐縱亦說:“本黨平日無計劃來培養這一類人才,則不能辭其責也。”*《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55頁。陳果夫也特意為此向蔣介石建言:“本黨素未注意獎勵人才,即以選拔文藝人才而論……迄今仍未進行,以致電影宣傳及一切文藝作品,均仍操于左傾份子之手。若本黨再不以鼓勵方法,培養延攬之,恐新生之才,均將為共黨所用。”*李云漢主編:《陳果夫先生文集》,第27頁。言詞中充滿了文藝人才匱乏的危機感。
按理說,國民黨作為執政黨,掌握大量行政資源,應該比長期處于危險艱苦環境下的中共更容易吸引人才,但真實情況并非如此,這就不得不歸因于國民黨黨員的信仰缺失了。早在1927年,胡漢民即說:“我常常想,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五六歲的乳臭小兒,中國國民黨卻正當壯年,經驗豐富有作為之年;論份子,中國國民黨多他百倍;論勢力,中國國民黨也大他百倍。為什么倒被這個小鬼搗亂得亂紛紛呢?”“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對于主義沒有徹底的了解,故沒有堅決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種力量來抵抗引誘和威迫……這樣的黨如何能不坍臺?”*胡漢民:《清黨之意義》,《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7月1日。
正是由于缺乏真實的信仰,國民黨雖有少量宣傳人才,卻不耐困苦,無法將其主義加以廣泛傳播。1938年,蔣介石非常生氣地說:“假使我們真已盡到了黨員的責任,在這十年很長的時間以內,很可以把我們的主義宣傳到窮鄉僻壤,深入人心,也早就應該把我們的主義和總理遺教,全部實施,當然不會有別的主義存在,也不會再有別的黨派活動的余地了。唯其我們自身不能盡到責任,以致黨沒有力量,黨的基礎不能深植于民眾中間”*《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1—402頁。。1944年,他又嚴厲批評道:“中央宣傳部缺乏積極奮斗之精神”;“宣傳部實不知責任之所在,其對共黨宣傳更缺乏斗爭精神。人以積極攻我,而我之內部反散漫薄弱如此,可嘆也”*《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6冊,第385、504頁。。敗退到臺灣后,蔣介石更總結指出:“黨的失敗主因,是在三民主義信仰的動搖。”*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5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131頁。
除缺失信仰外,國民黨宣傳人才之匱乏,或許還與宣傳工作在其黨內的地位不高有關。盡管國民黨一再強調宣傳的重要性,但往往口惠而實不至,在經費保障和激勵機制上均存在嚴重問題。如王世杰在1938年就抱怨說:“中央通訊社為近年來中央宣傳部之唯一成績……惟經費迄今甚小,發展維艱。”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吸引到優秀人才?至于宣傳與組織的關系,國民黨處理得也極為偏頗。1945年,王世杰曾直接向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申訴:“此次六全大會之選舉,組織部處長、秘書,無一不被選出或指定為代表;中央宣傳部之秘書、處長,無一被選或被指定之人。”*林美莉編校:《王世杰日記》上冊,第150、695頁。如此強烈的反差,又怎么能對宣傳人才產生激勵?
三、宣傳系統的統一與分裂
為了確保宣傳工作的黨性原則得以貫徹,中共對宣傳的統一是非常重視的,并做出了一系列紀律規定。《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便明確規定:“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不論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應受黨員的領導。”“任何出版物,無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6—7頁。1922年,中共二大在決定加入共產國際時附上了《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其中聲明:“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報紙與出版物,須完全服從黨的中央委員會,無論他是合法的或違法的,決不許出版機關任意自主,以致引出違反本黨的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68頁。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制定的《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又提出:“全黨的宣傳鼓動工作必須統一在中央總的宣傳政策領導之下”,只有如此,“才能在現代的宣傳戰中,戰勝我們的敵人”,否則是“非常危險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139頁。。這一系列規定,為中共宣傳的統一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
中共的這種宣傳統一,給其對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年,國民黨“圍剿”部隊就發現:“全部紅軍有整個的宣傳計劃,各部隊紅軍皆能取一致之步調,同一之意思,劃一之口號標語以為宣傳。”*李一之:《剿共隨軍日記》,第二軍政治訓練處,1932年,第102頁。后來,吳國楨也指出:“所有共產黨的報紙,無論是在俄國、英國、法國、美國或中國印行,都完全相同。它們似乎都屬于同一個人,同一個業主,像是出自同一個編委會的報紙系列。”*吳國楨著,吳修垣譯:《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斗》,第212頁。此話雖不盡客觀,卻也點明了共產黨宣傳口徑極其統一的特征。
相比之下,國民黨的宣傳卻是極不統一的。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內對意識形態的解釋和宣傳開始分裂,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等政治派別圍繞黨統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各自有一套意識形態理論。同是一個三民主義,在不同派系那里卻分別有一套體系。最早是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主要代表了國民黨右派的觀點;緊接著是左派甘乃光的《孫文主義之理論與實際》和《孫文主義大綱》;其后,又有再造派胡漢民的《三民主義連環性》、改組派周佛海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和蔣介石的《國父遺教概要》等陸續出版。各派別根據自身的需要,使三民主義時而孔學化,時而法西斯化,時而民主化,時而專制化。經過這種紛爭,三民主義變成了隨意的口號堆積,無法作為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而加以利用。*嚴海建:《淺析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意識形態層面的劣勢》,《民國檔案》2006年第2期。
1928年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統一革命理論案》指出:“自總理逝世迄至現在,黨的革命理論由同志憑各個對主義的認識,及革命實際變動的觀察,致革命理論,紛歧萬端……數年來,黨內糾紛百出,實源于黨員對于革命理論未能統一。現在本黨宣傳刊物如雨后春筍,其思想立場,微有出入者有之;絕對異趨者有之……黨員之間,都有以意氣而分派別的傾向,甚至有劍拔弩張,形成敵對團體的危險。”*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535頁。1929年3月,蔣介石也在國民黨三大上說:“不幸許多同志,把總理所爭創的三民主義置之腦后,他們不根據三民主義去發揮本黨的革命理論,而離開三民主義,自己任意發揮個人主觀的見解,致使黨內理論紛歧,思想復雜。”他同時還痛心疾首地強調:“本黨的病根,實在是思想不統一。”*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379、380頁。甚至到1952年,他還指出:“我們三民主義的理論,除開總理遺教給予我們最高的準則以外,黨中同志雖有許多詮釋、許多發揮的著作,但是始終都未能把黨的理論基礎,正確而統一地建立起來。因此,眾說紛紜,議論不一。不但沒有把主義的真義發揚光大,相反地還給主義帶來了許多困惑和曲解。這樣,黨中同志對自己已經爭吵不清,那如何還能使人民來信奉主義、接受主義呢?”*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160頁。平心而論,這一反省尚屬深刻。
可以說,在國民黨統治大陸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嚴重的派系斗爭和各種權力糾葛。而維系各派系的主要是實際利益關系,所以往往隨意曲解意識形態,甚至相互攻訐,這種內耗使國民黨的宣傳日益渙散。例如,創辦黨報的目的本來是為黨宣傳,但國民黨內的長期紛爭卻混淆了這一宣傳方向,“各個派系都需要有為自己宣傳和競選的工具,出版報刊便成為派系一項重要工作。搞派系活動的人,在參加競選中把報刊作為攻擊對方的工具,同時也作為吹捧上級和拉攏人的工具,各種報刊也就應運而生,各為其主”*石生:《貴陽報刊拾遺補缺》,《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第198—199頁。。而且,這種內部傾軋還給中共提供了分化、奪取的機會。1946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就囑咐《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處主任羅石生:“要利用國民黨地方勢力和中央嫡系勢力間的矛盾開展工作。”*《新華日報成都營業分處史稿》,成都出版社,1991年,第18頁。而國民黨重慶市商會機關報《商務日報》也很快被中共分化奪取,該報的中共地下黨員回憶:“這家報紙和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有深刻的矛盾”,“各派特務分子互相敵視,誰也沒有能夠在商務日報建立起反動組織,就連一個三青團的區分部也沒有建立起來。敵人不是有組織的活動,而是各個人在那里爭名奪利,這樣的敵人容易各個擊破”*曾在商務日報工作的部分同志:《周恩來、董必武同志領導我們奪取商務日報》,《新聞研究資料》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37頁。。
四、鄉村宣傳能力的差異
國民黨在城市的宣傳已屬不濟,到了廣袤的鄉村,更無法與中共抗衡。1928年,國民黨在“剿匪”報告中坦承:“我們可以消滅共產黨勢力,無法消滅共產黨的宣傳。”*江西省檔案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頁。有鑒于此,蔣介石提出:“剿匪的實施,宣傳要占六分力量,軍事只能占四分力量。”*《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0冊,“國史館”(臺北),2004年,第50頁。1931年6月召開的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也訓令各級黨部:“不斷的為剿匪宣傳,尤須組織健全的巡回鄉村宣傳隊。”“省黨部應隨時派員分赴各縣,縣黨部應隨時派員分赴各區,視察所屬黨部黨員之剿匪宣傳等工作”。“在暑假期內,各級黨部應設法聯絡回籍教員、學生,組織臨時講演會、展覽會、表演會等,或特約優秀忠實之份子,組織臨時宣傳隊等,以增厚剿匪宣傳之力量。”*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第1007頁。對在鄉村開展宣傳,部署得可謂相當細致。
但蔣介石很快大失所望。1933年11月,他在一次演講中悲哀地說:“現在江西各縣的黨務,我看就太幼稚太不行了,不僅是不能做什么實際工作,協助剿匪,就是連貼標語的工作也都不會!”*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1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608頁。直至1944年9月,蔣介石仍手諭侍從室主任陳布雷:“今后如何闡揚本黨之政治理論使之深入民間及貫徹本黨之政治策略使之充分實施,希研擬具體辦法報核為要。”*《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8冊,“國史館”(臺北),2011年,第280—281頁。由此可見,國民黨宣傳依然未能深入民間。1945年,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在國民黨六大上也檢討道:黨在宣傳上最主要的缺點是“浮”和“拙”,“城市的宣傳,多于鄉村的宣傳”,結果“弄得上級盡管‘宣’,下級卻很少‘傳’,一到中層,不免擱止”*《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政治”(一),第799頁。。
反觀共產黨方面,則處處得心應手。紅四軍成立后,立即在根據地廣泛開展宣傳,“每到一處少則頓住半天,多則頓住五天,先之以廣大的宣傳(政治部統屬的文字宣傳隊和口頭宣傳隊,均以連為單位,每連二隊,每隊三人,路上行軍及每到一處,宣傳就立刻普及)……這時候的紅軍不是一個單純打仗的東西,它的主要作用是發動群眾,打仗僅是一種手段”*《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57頁。。從后來的情況看,紅軍的宣傳一直十分努力。1932年,國民黨“圍剿”部隊發現:“共匪所至,字跡不拘大小優劣,必在墻壁遍涂標語,或標貼文字宣傳,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至其對俘虜對民眾等亦能盡量宣傳。”*李一之:《剿共隨軍日記》,第102頁。一位與紅軍有過接觸的外國傳教士也回憶:“他們所到之處,大寫標語,紅的、白的、藍的,一個個方塊字格外醒目……這些標語都是由宣傳班寫成的,這些人走到哪兒總是帶著一桶漆,凡是能寫字的地方,顯眼的地方,他們都寫大標語,有時還散發油印的傳單。”*金紫光、靳思彤主編:《外國人筆下的中國紅軍》,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8頁。
除了貼標語、發傳單,中共還采取了多種多樣的宣傳方式。據粗略統計,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共使用過的宣傳方式方法多達60多種,除了常見的印傳單、小冊子,張貼標語、布告,召開報告會、演講會、讀書會,創辦各種類型的墻報、油印小報、鉛印大報,組織各種形式的宣傳隊(宣講隊、演劇隊、秧歌隊、歌詠隊、巡回展覽隊、孩子劇團等),還通過放幻燈、印鼓動畫、寫街頭詩、貼壁上新聞、演活報劇、寄年貼、寫慰問信、贈紀念品,甚至放孔明燈等形式進行宣傳。對于不同的宣傳對象,或火線喊話,或上門談心,或登臺辯論,或即興演說,或慷慨激昂地鼓動,或對宣傳觀點進行嚴密的邏輯論證,或將宣傳內容寓于各種生動活潑的文化娛樂活動中,搞得有聲有色,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林之達主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頁。
更關鍵的是,中共的鄉村宣傳還非常講求實效。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宣傳部工作議決案》指出:中央宣傳部日常部務工作之一,就是“每月須調查一次:我們實行了幾次全國的‘宣傳動員’,各界各派對于我們這種宣傳的態度如何,對于各地地方的‘宣傳動員’亦是如此”。《議決案》還要求地方黨委“每月報告思想輿論的調查”,“每月總〔綜〕合報告中央各種刊物在當地的影響”。*《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90、192、193頁。可見中共在進行宣傳時,是十分重視宣傳效果及反饋的。
當然,中共的鄉村宣傳也曾走過一段彎路。1932年,國民黨列舉了中共宣傳的一些缺點:“一、文字宣傳,詞義艱深,民眾無由領會:除標語外,其余各種傳單告民眾書等,無不千篇一律,長篇大論有如前代八股,宣傳效力,直等于零。二、不分時間空間一律施用不能適合環境:如在民族主義高潮中而高呼‘武裝擁護蘇聯’,適足引起愛國民眾之反感;在農村而高呼‘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工人增加工資’,不啻無的放矢。”*李一之:《剿共隨軍日記》,第103頁。不過,中共很快就發現并糾正了這些偏差。劉少奇在《論口號的轉變》一文中指出:“口號太多了,太長了,叫得不順口,意思不明顯,不切合群眾的要求和心理,叫得太久而至于厭煩,引不起注意,都不適合作為群眾行動的口號。”*《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頁。于是,在后來的宣傳中,中共的口號大多簡單直接、通俗易懂、沖擊力強,而且有的放矢,注重切合農民的實際。陳毅曾舉例說明:“比如紅軍標語打倒土豪劣紳這樣寫的時候很少,因為太空洞而不具體,我們必需先調查當地某幾個人是群眾最恨的,調查以后則寫標語時就要成為打倒土豪劣紳某某等,這個口號無論如何不浮泛引起群眾深的認識。”*《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762頁。
正是通過這種行之有效的宣傳,廣大群眾被動員起來,政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無論窮鄉僻壤,都普及了黨的政治主張的標語,群眾到處找共產黨,擁護共產黨的標語,群眾自動的張貼”,“蘇府范圍內的農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國際歌,少先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紅軍歌,及各種革命歌曲,尤其是階級意識的強,無論三歲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及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幾乎成了每個群眾的口頭禪,最顯著的是許多不識字的工農分子,都能作很長的演說,國民黨與共產黨,刮民政府與蘇維埃政府,紅軍與白軍,每個人都能分別能解釋”*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1、355頁。。《申報》記者陳賡雅在蘇區考察時也驚奇地發現:“若問他們過去的情形,他們都能簡單明了地告訴你,你聽了令你滿意。‘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國際路線’一類名詞,語間提及,慣用如數家珍”。還有幾個國統區記者同樣說:“匪化”過的地方,“一般民眾的談吐,多半帶些赤色的意味:他們竟都知道什么叫做‘敵軍’,什么叫做‘土劣’,什么叫做‘列寧主義’,赤匪的《國際歌》是人人會唱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6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397—398、396頁。“共匪運動民眾,教育民眾,真是說得上。他們十天一大會,五天一小會,宣傳演講的結果,把素無知識、一字不曉的民眾,對他們的實事和情理都弄得清楚。一個街童,一個村婦,你問起關于共匪的事體來,都可以給你說得一篇,道得一段”*宋益清:《從四川匪區回來》,《獨立評論》第120號,1934年9月30日。。面對這種狀況,他們不得不贊嘆:“赤匪不但有武力,可以作破壞的工作,同時還有政治力量,可以作建設性的工作。赤匪最有效的政治工作便是宣傳;他的宣傳,是含有充分的麻醉性的”,“使一般民眾看了或聽了,最容易受麻醉,的確,赤匪麻醉的宣傳真太可怕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6卷,第397頁。。此語雖不無誣蔑,但亦透露出對中共鄉村宣傳能力的羨慕。
五、事實比宣傳更重要
事實勝于雄辯,事實對民心的導向勝過一切宣傳。中共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1926年,代理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的毛澤東參與起草了《關于宣傳決議案》,其中提出:“抽象宣傳,不能造成一個群眾的黨。唯有從事實上表示某黨對民眾的工作,才能造成一個群眾的黨……要使民眾相信本黨確能為他們在實際上謀利益。”*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第141—142頁。1945年,他再次指出:“革命行動的實際影響比理論宣傳文章傳播得快得多”*《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9頁。。其實,這不僅是毛澤東個人的認識,同時也是中共中央的共識。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便強調:“共產黨要在中國革命中取得領導權,單靠黨的宣傳鼓動是不夠的,必須使他的一切黨員在實際行動中,在每日的斗爭中,表現出他們是群眾的領導者。”*《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17頁。從后來的情況看,中共在此方面做得可謂相當出色,這就使其在與國民黨的宣傳戰中占了上風。1940年,朱德曾十分自豪地表示:“今天的頑固分子,天天在那里歪曲現實,對我們大肆攻擊,但全國廣大的人民群眾并不為他們所欺騙;相反的,共產黨人的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正因為我們所講的道理是最能反映客觀現實的,是最真實的最正確的。”*《朱德年譜(新編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971頁。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也說:“共產黨是靠踏踏實實爭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談的政治哲學獲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是靠喚起人民內心的希望、信任和愛戴,不是靠空談大道理而贏得人民對他們事業的支持。”*〔美〕杰克·貝爾登著,邱應覺等譯:《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87頁。英國《曼哲斯特導報》(《衛報》)同樣贊揚道:“共產黨在爭取此次戰爭之勝利中,起有顯著的作用,因該黨之宣傳方法新穎靈活而有力,并在進行全國之共同事業時,彼等均能獲得甚大之效果。”*《民主精神》,《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與此相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卻往往與其宣傳背道而馳。1926年,汪精衛在國民黨二大閉幕會上說:“我們革命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宣傳與事實不能一致……不把事實來改變,是不能宣傳的,但是想把事實改變,卻又必先努力于宣傳。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是我們覺得非常痛苦的事。”*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第168—169頁。這明顯是感到國民黨的宣傳與事實之間存在沖突甚至格格不入。1932年,蔣介石在漢口對黨政人員演講《如何使民眾對黨和政府發生信仰》時也批評道:因為黨部和政府沒有真正干出有益于民眾的事情,在百姓的眼里,黨部的委員和政府的官員,統統是一些“吃飯拿錢的做官階級”和“老爺”,這自然無法贏得民眾的信仰。如此下去,就只有等著人家來革命了。他因此再三告誡:“我們更要實事求是,不要坐而言,要起而行,并且行而一定要有成效!”*梁麗萍:《國民黨主流意識形態的構建與失敗(1928—1949)》,《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4年第3期。
但正所謂“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國民黨一直沒有做出好的樣子來。盡管各種會議上說得天花亂墜,但往往未徹底落實。早在1933年,就有人批評說:“國民政府之成立,雖為時不久,然亦已有六七年之歷史,對其所標榜之政策,似為一悲慘之失敗。”因此,“當北伐方興之時,人民擁護國民黨熱烈程度,為從來所僅見。現在忽一變而為厭棄之態度,當非無因而至。向日之擁護國民黨,非擁護國民黨之黨,系擁護其為解放民眾,打倒萬惡之軍閥而來。現在之厭棄國民黨,亦非厭棄國民黨之黨,乃厭棄其失其黨之效用,為民族解放之梗”。*劉震東:《中國出路問題》,《國聞周報》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1947年,又有人在《中央日報》發文針砭:國民黨歷次會議90%的議案無異于廢紙*金平歐:《國民黨的改造》,《中央日報》1947年9月16日。。1949年,國民黨內還有人反思說:“本黨歷屆全國代表大會全體執行委員會宣言及其他各種會議之宣言與決議,無不冠冕堂皇,讀之令人起敬佩慰無既,而事實上則多徒托空言,未能實行,致社會上對本黨之批評,謂系‘說盡天下之好話,做盡天下之壞事’、‘掛羊頭賣狗肉’,標榜實行三民主義而實際上一切措施大都違反三民主義。”*《粵漢區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對黨務改造之意見》(1949年9月27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6.41/34,轉引自馮琳:《1950年代初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2010年,第246頁。可見,國民黨流于空談的宣傳已經讓其黨員都無法容忍,遑論社會公信力了。
國民黨糟糕的執政作為還給其諸多宣傳部門帶來了麻煩。如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在1947年的一份報告中坦言:“兩年以來國際輿論對我政府時肆抨擊,美國輿論界除少數報紙雜志以外,無論左傾右傾,或東部西部,幾異口同聲誣我政府為不民主,貪污與無能……凡此現象之產生,共匪宣傳固為其主要原因,而我積極具體宣傳材料之貧乏,亦不能辭其咎,糾正之道,端賴加緊積極性之宣傳,以事實為言論之比照,庶可逐漸更改國內外對我政府之觀感。”他們還表示:“推進對外宣傳須與政治配合。欲求宣傳發揮效果,必須宣揚事實,不能徒托虛詞以事粉飾,因此,如宣傳不能與政治配合,難期發生最大成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文化”,第15、42頁。其間明顯流露出對國民黨內政的不滿。而學生運動方面,1947年五二〇運動爆發后,三青團重慶市支團部在報告中稱:“學潮之發生,雖有共匪之策動,然經濟危機嚴重,政治腐敗,一般中立學生,對政府由不擁護而走入對立狀態,實為主要原因。此點我全體黨團同志及政府官員,均應痛切反省,而謀根本解決之道。”*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五二〇運動資料》第2輯,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0頁。言詞中同樣不無抱怨。
面對國民黨宣傳部門這種處處被動的情況,連一向擅長宣傳演說的復興社骨干劉健群也不禁哀嘆:“宣傳不是不重要,但空洞而不切實解決問題的宣傳,不可以久且大。有好幾個訓練機構,曾經慕名來請我去講宣傳術,我說至誠可以感天,宣傳實在無術,我以為注重面對現實解決問題比重視宣傳更為切要。”*劉健群:《銀河憶往》,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78年,第89頁。而梁實秋更是毫不客氣地指出:“事實擺在面前,已經兵臨城下,一切宣傳伎倆都歸于無效。”*梁實秋:《沈陽觀感》,《世紀評論》第3卷第9期,1948年3月。由是觀之,國民黨的失敗確實不是僅靠宣傳就可以挽回的。其最終垮臺,毋寧說是根子已爛,大勢已去,故縱有巧舌如簧,亦絕無回天之力。
1948年3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向國務卿馬歇爾匯報:“我們往往發現,事實是國民政府的宣傳很少被大部分公眾輿論相信,而由中共散布的宣傳通常毫不置疑地便被接受”*〔美〕肯尼斯·雷、約翰·布魯爾編,尤存、牛軍譯:《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1946—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4頁。。國共兩黨宣傳交鋒的結果由此可見一斑。說到底,宣傳戰線的交鋒乃是階級利益沖突在思想領域的表現,決定其勝負的因素不是技術性的宣傳策略或手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平衡和社會公正。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盡管掌握強大的輿論宣傳工具,但因其不能平衡各方利益,未能保證廣大民眾的基本生存需求,必然要失信于民,無法避免墜入“塔西佗陷阱”的命運。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若不行,“技”再巧也無濟于事。1952年,已敗退到臺灣的蔣介石終于認識到:“大家最應注意的,就是理論決不可以離開事實,離開時代的,理論惟有能順應事實,合乎時代的需要,才不致落空,也才能為民眾所接受。”*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卷,第161頁。此言雖精當,只是未免來得太晚了些。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091)
(責任編輯 趙 鵬)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Propaganda Work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Lu Y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propaganda work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macroscopic analysis, there were mainly several reasons. Firstly, the propaganda of the Kuomintang became more and more conservative, after they took ov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s a revolutionary party, the CPC always maintained a very aggressive publicity campaign. Secondly, there were great and many talents in the CPC propaganda front, but the Kuomintang propaganda talents were rare. Thirdlyly, the CPC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nity of the propaganda, but the factions within the Kuomintang made their publicity increasingly loose. Fourthly, the Kuomintang propaganda work never went down to rural areas, while the CPC successfully mobilized the masses. Fifthly, the CPC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matching word to deed, while the Kuomintang’s deeds often drew further apart from their propaganda.
D231;D261.5
A
1003-3815(2016)-08-0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