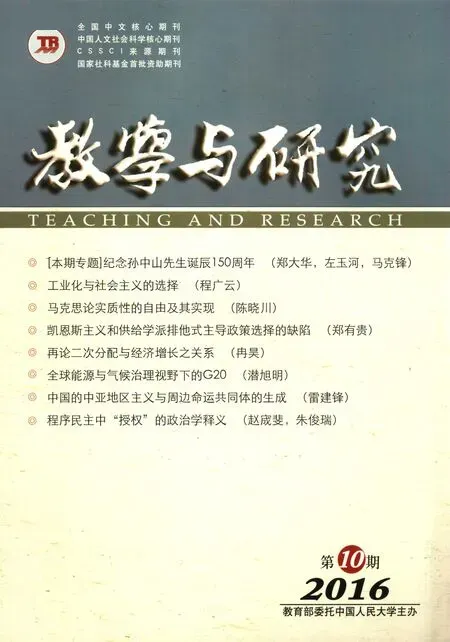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話語權分析
——兼論當代中國外交話語權的發展
孫 曉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話語權分析
——兼論當代中國外交話語權的發展
孫 曉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話語;話語權;中國外交
近年來,隨著一系列關于國際格局、全球治理等外交話語的提出,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問題備受關注。本文試圖提出從話語到話語權形成的分析框架,并以此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話語權的產生進行分析,探討話語權產生背后的話語因素。以此為基礎,本文對當前中國外交話語權問題進行反思,提出要在找準自身定位的基礎上,注重外交話語發展的包容性可溝通性,把握時代進步性,同時增強話語的實踐性,推動中國外交話語體系的完善與發展,進而擴大中國的外交話語權。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雙邊、多邊等外交場合頻頻發出中國聲音,從“堅持正確義利觀”,到“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再到“命運共同體”等,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提出新倡議,注入了中國元素,彰顯出中國作為大國的責任意識以及對全球治理的參與意識,體現出中國對地區及國際社會和平與發展的責任和擔當。當前中國外交話語的創新使我們更加關注中國外交話語權的發展:如何將我們的外交話語在國際社會進行進一步的傳播并增強其話語的影響力,使其成為各國所接受的外交話語并最終實現話語權,這是中國提升自身影響力、推動外交話語傳播的重要問題。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以中國為主體,同印度、緬甸在20世紀50年代共同提出的外交話語,歷經不同國際格局的發展,在處理國際事務、發展各國關系等方面擁有較大的話語權,成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重要準則,對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自主性、獨立性起到積極作用,推動了國際社會的和平發展。本文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話語權的發展進行分析,以此為基礎探討中國外交話語傳播、話語權獲取等現實問題,對當前中國外交話語存在的問題進行思考,無疑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一、話語權形成機制研究——從話語到話語權
話語一詞被廣泛應用于語言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一般而言,話語可以理解為“使用中的語言”,[1](P38)在對語言有理論自覺之前,一般認為人的思想和權力決定了話語,但是哲學研究發現語言在很多時候決定了人的思想和權力。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一開始有了語言,有了語言就有了神,語言又成為了神。世界上有多種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2](P149)每一種能夠自成體系的語言都建構了一個完整的意義世界,它能夠引導和規訓這個語言共同體內人的言行舉止。
話語借助于特定的語言結構實現表達,而語言結構依靠話語不斷再生。因此,話語的表達需要依靠特定的意義結構才能有效,而成功的話語表述將擴展和鞏固特定的秩序和結構。因此,話語總是與權力聯系在一起。將話語權作為獨立概念提出的是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福柯強調話語對觀念的建構作用,探討話語、知識與權力的關系,以權力視角審視話語背后的意義,認為話語的制造受一定數量程序的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3](P3)他提出“話語即權力”的論斷。哈貝馬斯(Habermas)并不局限于對話語的邏輯分析,而是突出強調話語的實踐性意義,他把話語視為實現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促進人的合理交往的前提條件。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受福柯及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提出“東方觀”的觀點,[4]反對帝國主義、強勢話語霸權,推動平等、包容的理念發展。
國際關系領域對話語的關注較晚,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所發展,主要集中于建構主義領域。克拉托奇威爾(Friedrich Kratochwil)指出話語分析能夠幫助我們在不同的約束性因素之間進行區分,通過話語分析,我們可以觀察到各種約束性力量的來源。[5](P686)真正將話語行為理論引入國際關系領域的是尼古拉斯·奧努弗(Nicholas Greenwood Onuf)。奧努弗以微觀層次為起點,認為個人通過一定的規則使用語言,話語演繹出規則,規則造就社會秩序。[6]伊曼紐爾·阿德勒(Emanuel Adler)在他的建構主義共同體理論中指出,語言是規范擴散以及機制化的中間媒介,是制度化實踐得以延續的條件,是社會事實建構的機制。[7](P13)話語在國際關系領域起著獨特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來講,國際關系是一種依賴話語的社會及文化建構。它不僅僅是人們之間交往的工具,而且是具有創造力的因素;不僅可以描述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還可以建構事實建構思想,甚至是建構人的身份。[8](P12)
目前對話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理思辨上,對話語權的形成機制缺乏具體研究。從話語到話語權的產生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進程。對社會進程進行分析可以辨別出話語權形成的具體機制,對實力處于上升狀態的中國建立自己的話語權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話語能夠得以傳播,并最終產生話語權,需要經歷不同階段,這種生成方式與國際規范內化的相關理論有一定的相似性。本文以瑪莎·費力莫的國際規范“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探究話語權形成的進程和機制。
在瑪莎·費力莫的國際規范“生命周期”理論中,規范的發展主要包括規范的起源、擴散和內化三個階段。[9](P887-917)費力莫的規范生成理論是從體系角度進行探討,而要從話語本體角度探討話語權的生成,也大體經歷這三個階段,即話語的形成與提出——話語傳播——話語的國際規范化。
具體而言,首先,國家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以總體性國家戰略為基礎,在已有的對自身、他國以及整個國際體系認知基礎上,形成對某一國際事務或者整個國際體系具有建設性、發展性的國際理念;話語的提出方式一般是通過領導人講話、與他國的共同聲明或者其他為實現外交話語政策目標而采取的手段等方式體現出來,在這一階段,著重關注話語提出的過程性研究;其次,在話語提出后,便是對話語的傳播,在此時期內,通過國際會議等雙邊、多邊活動,外交話語最終獲得話語權的基礎是該國自身對話語的踐行,并逐漸推廣到其他國家,通過他國乃至整個國際體系的學習、遵守與實踐,推動話語權的實現;最后,外交理念方面話語權實現的最終標志便是話語演變為國際規范,成為國家間行為、互動的基本準則。掌握話語權的國家可以影響其他國家的觀念和行為,影響國際議程的設定。
話語能夠產生權力主要有三種原因:第一,與使用話語的主體地位相關。地位取決于主體的實力大小以及在特定秩序中所處的位置。在穩定的國內社會中,人所處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決定了自身說話的分量。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國家實力的增長不一定能夠帶來話語權的增長。以既有的話語體系為參照,一個國家話語權的增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補充性的和替代性的。一個國家尋求話語權會帶來什么樣的國際結果取決于它提供的是替代性還是補充性的話語體系。補充性話語是對既有的話語體系進行適度的調整和修正,從根本上講補充性話語體系是在鞏固既有的話語秩序。替代性的話語體系是對現有的話語進行局部甚至是全局性的重塑,因此它是沖擊和動搖現有的話語秩序。
隨著實力的增長,如果國家在既有話語體系內尋求增長話語權,或者至多是提供一些補充性的話語,那么它的阻力不會太大,甚至會被話語權力的掌握者樹立為典型。如果一個國家沖擊了既有話語結構的根基,想要樹立替代性話語,那么它將面臨激烈的話語競爭。替代性話語實際上是為人們提供了另一種認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它會沖擊現有的身份界定和思維方式,所以會遭到既有話語主導者的壓制。所以,在建構替代性話語時一定要注意話語本身的特性。
第二,話語能夠產生權力還因為話語本身的特性。話語能夠產生權力是因為話語最終成為國際規范、國際準則以及全球范圍內的國際理念,進而影響了人的思想和行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就是話語主張得到足夠數量的國家的支持。因此,話語自身的特性至關重要,國家話語要成為世界性話語,成為國際規范,要求話語首先要與當前的國際關系、國際法基本準則相一致,體現包容性。話語可以是針對具體問題提出來的,但是話語的表達需要具備普遍性,這樣能夠被更多國家接受;同時又體現出時代性與進步性特色,能夠引導國家、國際體系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第三,話語更為重要的是要具有實踐性,通過對話語的實踐推動話語合法性的提升,最終實現話語權。在話語轉變為話語權的進程中,正是實踐使得話語和權力實現了統一。“言傳身教”就說明了話語和實踐之間的緊密聯系。話語體系和語言結構都需要在表達和實踐(表達本身就是一種實踐)中不斷再生,而在實踐中人們會反思話語和語言。個體和集體都具備反思能力,如果在實踐中話語沒有可行性或者話語的倡導者自身就不遵循話語,那么話語就難以推廣開來。如果情況相反,那么話語就能吸引到眾多到追隨者,上升為國際規范。
值得注意的是,話語權的生成與國際規范內化的過程有其相似性,但比較突出的一個不同點便是規范的內化過程在某一階段國家所表現出的往往是被動性行為,國家為推動自身國際利益的實現而加入國際組織,在加入初期往往存在著國內機制不跟進等現象。而從話語到話語權的生成,整個過程中國家的行為是主動性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國家遵守話語是因為話語自身的“吸引力”,以這種“吸引力”為基礎話語生成規范,產生“影響力”,進而推動話語權的實現。因此,需要探討外交話語能否發展出話語權,并要著重關注話語自身的“吸引力”。本文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例,對其在國際社會話語權的獲得,在60余年時間中話語權持續發展進行過程性研究,同時,以話語自身因素進行分析,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話語權產生的話語“影響力”因素進行分析,以此為基礎對當前中國話語權發展進行反思。
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話語權的形成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實現了國家疆域的基本統一,逐步完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內部整合,經濟逐漸恢復并得到發展,國家實力迅速增強。在當時兩極對立的話語體系中,中國要想在“一邊倒”之外打開局面,必須能夠提出替代性話語,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之外構筑其他身份并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認同與合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話語權的形成主要經歷了話語的形成與提出、話語在國際社會的傳播并最終形成話語權這三個階段,下面對這三個階段進行分別闡述。
(一)話語的形成與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倒向社會主義蘇聯一邊,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外交關系。如何與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國家尤其是周邊其他新獨立國家發展外交關系,成為新中國領導集體面臨的重要任務。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外交話語也是在此背景之下醞釀并形成。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在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中國執政黨的背景下,毛澤東指出中國希望能夠以平等的原則發展同國際社會一切國家的外交關系。6月15日,在新政協會議籌備會上,毛澤東講話指出,任何外國政府,只要愿意斷絕與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中國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原則的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10](P91)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只有團結國內國際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才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發展同他國的外交關系。[10](P94)同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指出“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展通商貿易關系。”[11](P13)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本思想開始醞釀,并逐漸運用于中國發展同其他國家關系中。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第一次完整提出是1953年周恩來在與來訪印度代表團就涉及紛爭的西藏問題談判時,周恩來在與印度代表團的談話中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原則”。[12](P63)隨后,五項原則寫入中印雙方共同簽署的《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與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推動中印相關雙邊事務發展,五項原則首次以字面形式被寫入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性文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提出是在亞非國際會議,會議最終通過《亞非會議最后公報》,提出了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這十項原則的內容是: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尊重一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地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不使用集體防御的安排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任何國家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不以侵略行為或侵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按照《聯合國憲章》,通過如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決等和平方法以及有關方面自己選擇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來解決一切國際爭端;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擴展,大大提升了五項原則的國際影響力。
(二)話語的傳播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1954年提出并倡導之后,得到國際輿論的積極評價,反響強烈,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在亞非國家之間迅速傳播。在20世紀50年代,已有將近20個國家表示接受五項原則;60年代,又有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等多個國家同中國以公報或雙邊協定的形式,承認五項原則;在70年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更好的傳播,受到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背景下,1971年11月,中國代表團參加第26屆聯合國代表大會,喬冠華在發言中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該成為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準則。
五項原則還受到了來自眾多國家的遵守與實踐。1954年10月,在越南和印度發表的兩國聯合聲明中,表示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系。1955年,尼赫魯和吳努簽署印緬聯合公報,指出五項原則是和平最好的保障,通過他國的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進一步認可,增強了影響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更多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積極深入發展同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交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受到了更多的來自世界范圍的關注及認可,在致力于維護國際關系穩定的同時,也體現出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美好愿望,認為維持各國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是每個國家所應當為之努力的,強調堅持國家間的平等交往,對于維護國際秩序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國際規范化
國家對于國際準則的實踐推動了準則的合法化,也推動了準則的國際規范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于推動國際社會的良性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61年,聯大第六委員會提出“審議各國和平觀念共處的國際法原則”,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反對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國際法原則的確立被暫時擱置,但經過不懈努力,終于在1970年聯合國大會《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中獲得通過,在1974年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通過的《建立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國經濟權利義務憲章》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提及。以此為基礎,大量雙邊條約及條約性文件中,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行為準則被提及,真正成為指導國與國關系的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于建設和平共處、和平發展、和諧共生的地區和國際秩序[13]以及豐富中國特色外交理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國際體系中,來自于各國的關于國際體系發展、全球治理相關理念層出不窮,有些話語在從提出時便不被國際社會認同,有些外交話語雖然在提出時影響力頗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被歷史所拋棄,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歷經六十余載,仍然具有深遠的影響力以及較大的話語權,值得我們反思。
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話語內涵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話語權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話語本身的特性。相較于其他外交話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話語具有同當代國際關系準則、國際法體系的包容性特征,具有時代進步性,同時又有很強的實踐性,這些因素都推動了話語權的形成。
(一)話語的包容性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包容性體現在其與當代世界國際關系、國際法基本準則的相容性,作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法原則,集中體現了主權、正義、民主、法治的價值觀。[14]二戰后,民族解放運動興起,世界各國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以更為平等的地位獲得發展機會,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各國主權獨立、和平發展,其話語具有包容性,體現出各國權利義務責任相統一的精神。
同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話語的包容性還體現在其話語的普適性。它提出了適用于大多數國家的交往模式,不分東西方、社會制度、發展水平。這種包容性賦予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強大的生命力。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自己的原則,這種原則超越了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異,對于世界不同文明間相互借鑒、共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話語的時代進步性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有其時代進步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話語客體主要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新獨立國家,在此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獨立運動空前高漲,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蓬勃興起,第三世界國家成為蘇美兩極對立的國際體系之外存在著不依附于任何一方的第三種力量,影響著國際局勢的走向。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于推動這一時期亞非拉國家的合作發展、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等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時代表了國際社會的發展方向,體現出時代進步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摒棄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壯大了反帝反殖民力量,加速了殖民體系崩潰瓦解,為和平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及國際爭端開辟了嶄新道路,[14]代表了當時的進步力量。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發生深刻變化,世界不再是兩極對峙的模式,國際體系告別強權政治的模式,非傳統安全問題開始顯現,國家間和平共處、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積極發展雙邊、多邊經濟貿易文化等合作要求凸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未由于冷戰結束后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而過時,而是煥發出新的更強的生命力,在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話語的實踐性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話語的實踐性體現在它作為中國外交實踐的戰略話語,指導雙邊多邊關系發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出現在中國與160多個國家的建交公報中,對于發展中國同他國關系、推動世界和平與穩定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建構性地應用于具體外交領域,如在對外援助方面,1964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訪問亞非十四國期間宣布了“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其核心理念包括: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提供援助,不把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提供外援時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也不要求任何特權;對外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它們走上自力更生、獨立發展的道路。,對外援助的核心原則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得到了非洲等欠發達地區人民的支持。同時,在對國家外交理念的推動方面,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影響深遠:以主權為主體,中國近年來在推進自身核心利益發展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主權歸屬等方面問題均起到了積極性的示范作用;中國積極發展新型國際關系,互聯互通惠及他國,命運共同體等觀念均是對五項原則中國家相處模式的探索,是五項原則在當今的具體應用。
四、對當代中國外交話語權發展的啟示
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話語權發展為出發點,我們來關注當前中國的話語權狀況。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國際事務參與實現了由“一般參與者”到“重點建設者”到“負責任大國”的角色轉換,[15]外交話語也經歷了從“失語”到“話語稀缺”到“謀求話語權”的變化。[16]而相對來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外交話語權卻相對較小,主要有兩方面原因:首先,在“韜光養晦”的國家戰略背景下,中國“不當頭、不出頭、不結盟”,[17]將注意力放在國內經濟建設上,提出的外交話語相對較少,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但同時也使中國的外交話語權發展受到影響。其次,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也相繼推出了一系列外交話語及具體某一國際事務的外交話語,卻并沒有實現相應的話語權,甚至召來西方國家的負面評價,面臨一定的話語困境及話語權困境。中國作為具有豐富文化傳統的大國,要為世界的發展貢獻自己的智慧,因此中國的話語權建設在某種程度上對既有的國際話語體系是替代性的。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隨著實力的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了這一悖論。
中國開始思考近年來的外交話語困境,并尋求出路。2010 年 5月,胡錦濤在參加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 65 周年活動期間指出中俄應當“加強二十國集團機制化問題上的協調和配合,提高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18]這是中國在當代尋求外交話語權的重要信號。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中國相繼提出“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外交話語,為全球治理提出中國方案。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外交戰略尋求“有所作為”,在已有的外交話語基礎上,形成積極進取之勢,外交話語權開始有實質性發展。習近平提出的外交理念體現了當代中國對于國際體系和平與發展的思考,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及普適性。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扎根,認為中國夢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19]進而生發創新一系列對于國際關系發展以及全球治理的外交理念,孕育中國與不同地區、文明、制度國家合作共贏發展的絢爛之花。習近平外交話語在體現包容性的同時還具有創新性,這種創新性體現在發展同世界各國關系過程中:在處理大國關系時,習近平指出要建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打破權力轉移過程中大國對抗沖突的歷史魔咒;同時積極發展新型國際關系,在處理與各國關系時,應當“把握方向,共建命運共同體;夯實基礎,推動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互諒互讓,堅持對話協商和平解決爭議”,[20]摒棄對抗、沖突,通過交流、溝通、對話的方式推進國際社會的和平發展,在溝通合作中提升自身的外交話語權。外交話語權的實現還依賴于對話語的實踐。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的提出及建立是中國對自身外交話語的實踐,在具體實踐中,重視給相關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追求“百花齊放的大利”,而不是“一枝獨秀的小利”,[21]與世界各國共享發展成果,以此為基礎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感召力、影響力,進而實現外交話語權。
同時,要真正實現外交話語權,在推動話語創新、話語實踐的同時,還應當創新話語傳播方式,進一步提高中國在全球事務中設置議程能力以及規范傳播能力,需要注意話語傳播的策略,要善于將話語與事件、娛樂等結合起來,比如優秀的電影作品和歌曲都是傳播話語的重要載體;要注意話語的表達方式,減少照本宣科式的說教,采取靈活多變的形式,以此提高全球治理的水平,推動外交話語權的實現。
結 語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歷經六十余載,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及話語影響力,這給我們當代中國外交話語權的發展提供了借鑒。要提升當代中國外交話語權,推動自身話語的國際規范化,中國需要在對自身國際身份定位基礎上進行話語發展,作為負責任大國、新興國家,在外交話語提出時應該有全球意識、包容意識,以國際關系準則、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為基礎,注重不同制度、文明的和諧發展;推動外交話語發展的時代進步性,推出符合時代發展潮流、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話語,積極推動外交話語的可溝通性及可操作性,生產國際社會聽得到、聽得懂的“中國話”,要有源自中國、打動世界的國際關系話語體系。[22]同時,外交話語權的實現要在實踐創新中完成。我們應該在全球經濟、政治、安全等各方面治理中把握機遇,以話語為基礎,通過話語實踐、話語創新提升話語權。當前,中國在建立金磚銀行、亞投行等金融機制方面頻有創新之舉,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經濟制度中的話語權,這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創新性實踐;在推動“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注重話語權的提升,推動建立與周邊國家的“命運共同體”,在此基礎上,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進而實現外交話語權。
[1] 劉永濤.話語政治——符號權力和美國對外政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2]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M].北京:三聯書店,2008.
[3] 米歇爾·福柯.話語的秩序[A].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4] 愛德華·薩義德.東方學[M].上海:三聯書店,1999.
[5] Friedrich Kratochwil. Force of Prescription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4, 1984.
[6] Nicholas Greenwood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7] Emanuel Adler. 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M].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5.
[8] 秦亞青.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9] Martha Finnemore,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1998.
[10] 毛澤東外交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1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A].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C].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12] 周恩來外交文選[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13] 蘇長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中國國際法理論體系的思索[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6).
[14] 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28/c_1111364206_2.htm.
[15] 王逸舟.中國外交十特色——兼論對外交研究的啟示[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5).
[16] 吳瑛.中國話語權生產機制研究——對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與西方媒體的解讀[D].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17] 徐進.世界政治中的感召力及中國的選擇[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3).
[18] 胡錦濤建議中俄加強協調配合提高國際話語權[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0hufange/2010-05/10/content_9827769_2.htm.
[19] 習近平在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共同會見記者時的講話(2013年6月7日)[N].人民日報,2013-06-09.
[20] 凝聚共識,促進對話——共創亞洲和平與繁榮的美好未來[EB/OL].習近平在亞信第五次外長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2016-04-2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8/c_1118761158.htm.
[21] 習近平在埃及媒體發表署名文章:“讓中阿友誼如尼羅河水奔涌向前”[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20/c1024-28068370.html.
[22] 裘援平.中國和平發展與公共外交[J].國際問題研究,2010,(6).
[責任編輯 劉蔚然]
An Analysis on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Also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ontemporary China’s Diplomacy
Sun Xi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discourse; discourse power; China’s diplomac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 series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on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and global governance, China’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an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the discourse to the formation of discourse power, and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power and sugguests that China should find its own positioning, focus on the inclusiveness and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of discourse,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and expand its diplomatic discourse power.
孫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