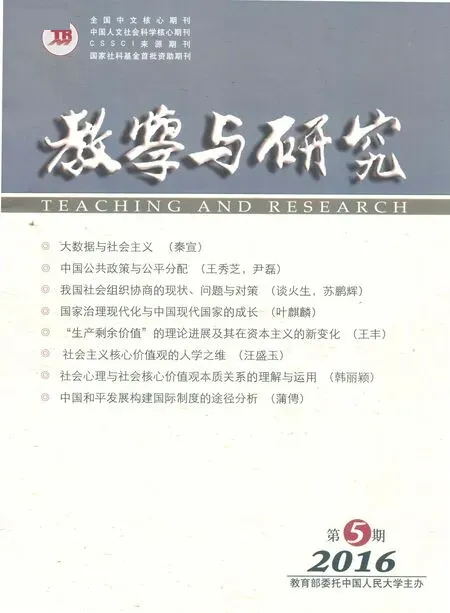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與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成長*
葉麒麟
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與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成長*
葉麒麟
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國家成長
以社會資源正義分配、國內(nèi)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證為核心要義、任務(wù)的國家治理,是現(xiàn)代國家的基本屬性,而國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是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內(nèi)在邏輯,它是考察現(xiàn)代國家成長較為科學(xué)、合理的維度。在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維度下,中國的現(xiàn)代國家經(jīng)歷了獨(dú)特的成長軌跡,即由傳統(tǒng)國家治理危機(jī)所促成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建國階段,到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運(yùn)動式治理所帶來的國家一體化階段,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化治理所帶來的執(zhí)政興國階段。
以民族國家作為組織形態(tài)的現(xiàn)代國家的出現(xiàn),是社會現(xiàn)代化的結(jié)果,其成長或曰建構(gòu)(State-building)體現(xiàn)著一個社會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政治方面,它是一個全球性的現(xiàn)象。在20世紀(jì)70、80年代以來西方學(xué)術(shù)界掀起的回歸國家研究熱潮下,現(xiàn)代國家成長成為了一個研究熱點(diǎn)。當(dāng)然,西方學(xué)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洲的現(xiàn)代國家成長上。例如,美國學(xué)者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西歐的現(xiàn)代國家是通過戰(zhàn)爭的方式從而產(chǎn)生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的集中控制,進(jìn)而逐漸成長起來的。[1]又如,英國學(xué)者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rèn)為,國家行政力量的強(qiáng)大所帶來的內(nèi)部綏靖、軍事進(jìn)步所帶來的國家對暴力更加強(qiáng)有力的壟斷,致使國家對社會形成反思性的監(jiān)控,這是促成民族國家形成的根本因素。[2]再如,美國學(xué)者西里爾·布萊克(Cyril E.Black)指出,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內(nèi)容可以概括為政治權(quán)力的集中化(表現(xiàn)為決策的強(qiáng)化)、法律規(guī)范的普及(同時導(dǎo)致官僚機(jī)制的發(fā)展)和公民在公共事務(wù)中作用的擴(kuò)大。[3]不難看出,現(xiàn)有西方學(xué)者關(guān)于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擴(kuò)張與控制的層面上。
相對于西方學(xué)術(shù)界而言,國內(nèi)關(guān)于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研究熱潮則是進(jìn)入21世紀(jì)才興起的。也正是進(jìn)入21世紀(jì),才興起了中國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專門研究熱潮。但是,綜觀現(xiàn)有文獻(xiàn),與西方學(xué)術(shù)界一樣,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現(xiàn)有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擴(kuò)張與控制的層面上。例如,學(xué)者徐勇從以權(quán)力集中為特征的民族—國家和以權(quán)力合理配置為特征的民主—國家這兩個角度考察了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成長歷程。[4]又如,學(xué)者樊紅敏嘗試從權(quán)力的集中、滲透與重新分配等角度來探討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理想型。[5]再如,學(xué)者儲健國從國家機(jī)構(gòu)的設(shè)置與調(diào)整角度來剖析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成長。[6]
不可否認(rèn),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的擴(kuò)張與控制,是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重要內(nèi)容、任務(wù)和特征,但它不是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全部內(nèi)容、任務(wù)和特征。因?yàn)樵趪覚?quán)力對社會擴(kuò)張與控制的背后,還隱藏著一個合法性問題,換言之,我們?yōu)楹我非蟋F(xiàn)代國家?本文認(rèn)為,認(rèn)可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的擴(kuò)張與控制,以及追求現(xiàn)代國家,關(guān)鍵的原因在于現(xiàn)代國家能夠解決傳統(tǒng)國家的治理危機(jī),能夠帶來更好的治理績效,包括社會資源的正義分配(即盡可能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權(quán)益和訴求)、內(nèi)部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證。就此而言,相對于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的現(xiàn)代性擴(kuò)張,以社會資源正義分配、內(nèi)部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證為核心要義、任務(wù)的國家治理的現(xiàn)代化,更能準(zhǔn)確反映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內(nèi)在邏輯,更是剖析中國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科學(xué)、合理維度。但是,現(xiàn)有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擴(kuò)張與控制的層面,深陷在“統(tǒng)治”的理念桎梏之中。鑒于此,本文試圖從國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維度來剖析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成長歷程。
一、傳統(tǒng)國家治理危機(jī)與革命建國
新中國成立以前,特殊的自然和社會經(jīng)濟(jì)等條件造就了“君主——官僚——民間精英”的獨(dú)特的帝國治理體系和治理邏輯。在這一傳統(tǒng)國家治理體系中,權(quán)力的核心在于君主,君主擁有絕對的權(quán)力,但它則是通過體系化的官僚隊(duì)伍進(jìn)行國家治理的。由于官僚隊(duì)伍主要居住在地域性城市中,因而傳統(tǒng)國家權(quán)力并未直接深入到廣闊的鄉(xiāng)土社會中,即“皇權(quán)不下鄉(xiāng)”。而廣闊的鄉(xiāng)土社會則是由族長、鄉(xiāng)紳、商紳和地方名流等民間精英進(jìn)行治理,從而使得鄉(xiāng)土社會超然于國家。同時,“學(xué)而優(yōu)則仕”理念的科舉制對社會進(jìn)行教化,選拔和吸收民間精英進(jìn)入官僚體系,從而又實(shí)現(xiàn)了官僚國家對鄉(xiāng)土社會的整合,最終造就了君主專制集權(quán)的帝國治理邏輯。但是,該帝國治理邏輯的根本要害就在于君主的專制集權(quán)上。在相當(dāng)大程度上,王朝的興衰命運(yùn)系于君主個人上,取決于其品質(zhì)。而這一根本要害又帶來了帝國治理體系如下三個具體弊病:(1)王朝重“內(nèi)控”輕“御外”。中國傳統(tǒng)國家治理的重心在于如何統(tǒng)治社會成員,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征收稅賦。相對內(nèi)部秩序而言,外部安全則較為忽視。(2)君主與官僚體系的溝通銜接往往存在問題。除了各種形式的朝會等正式渠道外,君主與官僚體系更多地通過君主的侍從、親信和家人(尤其是外戚)等非正式渠道進(jìn)行接觸和溝通。而這些非正式溝通渠道往往會導(dǎo)致君主和官僚體系的沖突和矛盾,從而造就了宦官、外戚和女主專權(quán)這三大王朝禍患。(3)社會缺乏活力。在君主專制集權(quán)的帝國治理邏輯下,國家凌駕于社會之上,官僚體系壟斷了所有公共權(quán)力,對社會采取“重農(nóng)抑商”經(jīng)濟(jì)政策,并借此對社會進(jìn)行“分而治之”的統(tǒng)治,社會大眾依附和受制于家族以及官僚體系,社會活力十分欠缺。
正因?yàn)樯鲜霰撞。袊鴤鹘y(tǒng)國家無法提供長久的社會資源正義分配、內(nèi)部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證,常常出現(xiàn)外族入侵、君權(quán)爭斗以及農(nóng)民起義等治理危機(jī),從而出現(xiàn)不斷改朝換代的歷史境遇。尤其在明朝宰相制度被取消之后,君主專制集權(quán)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強(qiáng)化,帝國治理邏輯的弊病更加暴露出來,致使鴉片戰(zhàn)爭后的清朝政權(quán)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治理危機(jī)。這具體體現(xiàn)在:(1)社會資源分配相當(dāng)不正義。奢靡貪污、賣官鬻爵之風(fēng)盛行,官僚、貴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zé)o地的農(nóng)民越來越多,大量農(nóng)民因無法忍受橫征暴斂而棄田逃亡,失去生計(jì),四處流浪,整個社會貧富相當(dāng)懸殊。(2)內(nèi)部秩序紊亂。階級矛盾激化,各地起義不斷。其中,1851年爆發(fā)的太平天國運(yùn)動,更是沉重打擊了清朝的統(tǒng)治。(3)外部安全蕩然無存。在中華文明無法同化的西方文明的沖擊下,清政府被迫割地、賠款和開放通商,國家主權(quán)和領(lǐng)土逐漸喪失,致使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中。正是傳統(tǒng)國家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治理危機(jī),以國家和民族為認(rèn)同對象的民族主義才開始形成,中國的國家轉(zhuǎn)型和現(xiàn)代國家成長之路才被迫開啟。
在如何推動國家轉(zhuǎn)型、解決傳統(tǒng)國家治理危機(jī)的問題上,出現(xiàn)了改良和革命兩種思路和做法。但實(shí)踐證明,“戊戌變法”和“預(yù)備立憲”等改良式的現(xiàn)代國家建構(gòu)在中國行不通,尤其是清政府在實(shí)行“預(yù)備立憲”時將科舉制廢除,更是中斷了國家與鄉(xiāng)土社會的流動與溝通,瓦解了國家對鄉(xiāng)土社會的整合,造就了“一盤散沙”的社會狀態(tài),加重了國家的治理危機(jī)。而這更加決定了中國要走“革命建國”的道路。為此,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領(lǐng)導(dǎo)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結(jié)束了帝國形態(tài),并建立起了中華民國。然而,中華民國徒有現(xiàn)代國家的形式,地方軍閥割據(jù),社會資源正義分配、內(nèi)部秩序以及外部安全都無法實(shí)現(xiàn),國家仍然處于治理危機(jī)之中。正因?yàn)槿绱耍瑢O中山意識到了組織對于革命建國的重要性,主張通過“列寧式的政黨”來解決國家治理危機(jī),推動現(xiàn)代國家的成長。隨后,孫中山的“以黨建國”主張被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所繼承。其中,國民黨在蔣介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lǐng)袖”的指示下,試圖以強(qiáng)大的軍事力量和專制政權(quán)來解決國家治理危機(jī)。然而,這一努力給社會帶來的是無窮戰(zhàn)爭和沉重賦役,不僅未能解決國家外部安全問題,更加劇了社會資源分配的不正義以及內(nèi)部秩序的動蕩,從而遭受全社會的強(qiáng)烈反彈,由此也直接掀起了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中國革命。相對國民黨而言,共產(chǎn)黨的紀(jì)律更嚴(yán)格,組織更嚴(yán)密,革命方法更為徹底。共產(chǎn)黨堅(jiān)持以階級斗爭為指導(dǎo)思想,并由此引出群眾觀念,走群眾路線,將組織深入至地方基層社會,動員廣大群眾參與到革命中來。正是在共產(chǎn)黨的廣泛動員和堅(jiān)強(qiáng)領(lǐng)導(dǎo)之下,中國革命終于取得勝利,并于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使得中國獲得了國家主權(quán)獨(dú)立,在全社會范圍內(nèi)確立了有效的中央權(quán)威,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換言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建國”實(shí)踐在解決傳統(tǒng)國家的社會資源分配不正義、秩序紊亂以及外部安全蕩然無存等治理危機(jī),推動傳統(tǒng)國家轉(zhuǎn)型的任務(wù)上,已經(jīng)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
二、運(yùn)動式治理與國家一體化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共產(chǎn)黨通過革命真正結(jié)束了帝國這一傳統(tǒng)國家形態(tài),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現(xiàn)代國家已經(jīng)完全成長起來了。這是因?yàn)樾律恼?quán)還不穩(wěn)固,國家治理還面臨著因長年戰(zhàn)火導(dǎo)致的社會經(jīng)濟(jì)資源匱乏,國民黨特務(wù)、土匪和惡霸地主等國內(nèi)反動殘余勢力擾亂國內(nèi)秩序,美國等國外敵對勢力威脅外部安全等嚴(yán)重危機(jī)。面對這些嚴(yán)重的國家治理危機(jī),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chǎn)黨,繼續(xù)采取了革命時期的群眾運(yùn)動方式,先后發(fā)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yùn)動。具體而言,為了消除反動勢力的擾亂,鞏固國家政權(quán),開展了“剿匪”、鎮(zhèn)壓反革命以及內(nèi)部肅反等運(yùn)動;為了改造社會,開展了“土改”、農(nóng)業(y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運(yùn)動;為了發(fā)展生產(chǎn)力,開展了“大躍進(jìn)”、“增產(chǎn)節(jié)約”以及“農(nóng)業(yè)學(xué)大寨”等運(yùn)動;為了改造思想,開展了“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以及“破四舊”等運(yùn)動。據(jù)國內(nèi)學(xué)者胡鞍鋼的初步統(tǒng)計(jì),從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開展各類政治運(yùn)動多達(dá)67次,年均2.5次。[7](P620)據(jù)此,美國學(xué)者詹姆斯·R ·湯森(James R.Townsend)和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指出,“反復(fù)出現(xiàn)的群眾運(yùn)動是中共政治自1933年以來的一個特征,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府運(yùn)作的一種主要方式。”[8](P153)換言之,運(yùn)動式治理成為了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中國共產(chǎn)黨所領(lǐng)導(dǎo)的主要國家治理方式。
從本質(zhì)上說,運(yùn)動式治理是一種人治治理。具體而言,運(yùn)動式治理是一種自上而下動員型的群眾運(yùn)動,是一種貫徹魅力型領(lǐng)袖意志的強(qiáng)力治理。這種治理方式極力反對官僚主義,極為崇尚領(lǐng)袖的智慧權(quán)威和群眾的運(yùn)動力量,因而具有如下顯著的弊端:群眾運(yùn)動高度依賴于社會成員飽滿的革命意志和激情,國家治理的績效高度取決于領(lǐng)袖個人的運(yùn)動治國理念和目標(biāo)指示;一味要求社會成員個體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犧牲,忽視個體必需的自由和權(quán)利;反對官僚主義,容易摧毀掉必需的國家科層制;崇尚群眾運(yùn)動式“大民主”,容易阻滯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直至損害到民主自身;群眾運(yùn)動過度,容易擾亂穩(wěn)定秩序,削弱共產(chǎn)黨的威信,等等。運(yùn)動式治理的上述弊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1957年“反右”斗爭擴(kuò)大化之后,充分暴露出來。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運(yùn)動式治理上述弊端的最充分體現(xiàn)。它造成了政治上的長期動亂,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大批干部和群眾遭到殘酷迫害,國民經(jīng)濟(jì)遭受嚴(yán)重破壞,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簡言之,國家治理秩序遭受嚴(yán)重破壞,現(xiàn)代國家成長遭受嚴(yán)重阻滯。
既然運(yùn)動式治理暴露出上述嚴(yán)重的弊端,那么是否意味著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運(yùn)動式治理對于國家治理和現(xiàn)代國家成長毫無積極意義呢?對此,正如美國學(xué)者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所言,“無論共產(chǎn)黨在其前30年的統(tǒng)治中有過什么樣的政策失誤,由于認(rèn)識到要適當(dāng)?shù)乇3指骷壍胤街g的平衡,它始終十分重視如何控制社會、積累資源、發(fā)展經(jīng)濟(jì)和國家一體化等問題。中國共產(chǎn)黨同樣面臨著1949年以前阻礙中國進(jìn)行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各種問題,盡管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并在許多領(lǐng)域受挫,但它還是基本解決了這些問題。”[9]應(yīng)該說,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運(yùn)動式治理的客觀結(jié)果就是,實(shí)現(xiàn)了國家權(quán)力對整個社會的高度動員和深度控制,對于恢復(fù)和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jì)、鞏固執(zhí)政黨地位和純潔革命隊(duì)伍起到了積極有效的作用,從而造就了國家一體化的現(xiàn)代國家成長態(tài)勢。
三、制度化治理與執(zhí)政興國
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運(yùn)動式治理,雖然實(shí)現(xiàn)了國家權(quán)力對整個社會的高度動員和深度控制,造就了國家一體化的現(xiàn)代國家成長態(tài)勢,但其所帶來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場嚴(yán)重的國家治理危機(jī),引起了全社會對運(yùn)動式國家治理的反思和批判。也正是在這種反思和批判的潮流下,自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伊始,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推動的國家治理方式由運(yùn)動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轉(zhuǎn)變,自覺承擔(dān)起執(zhí)政興國的使命,現(xiàn)代國家成長也才由此逐步恢復(fù)到常規(guī)化的理性軌道上來。
當(dāng)然,這里必須提及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二代領(lǐng)導(dǎo)核心鄧小平,在制度化的國家治理方面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xiàn)。他總結(jié)了運(yùn)動式治理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高度重視和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要加強(qiáng)法制建設(shè),努力完善各項(xiàng)具體制度。他在1980年《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指出,“我們過去發(fā)生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lǐng)導(dǎo)人的思想、作風(fēng)有關(guān),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10](P333)“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10](P333)正是在鄧小平的倡導(dǎo)下,自20世紀(jì)80年代初伊始,中國逐步恢復(fù)和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民族區(qū)域自治和基層群眾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認(rèn)識不斷深化的基礎(chǔ)上,也逐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jīng)濟(jì)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jīng)濟(jì)制度。作為對各項(xiàng)制度的權(quán)威確認(rèn)的憲法也得到修改,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也得以制定,中共十五大更是將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yán)、違法必究”為基本要求的“依法治國”確定為基本治國方略。在某種意義上,該治國方略的提出,標(biāo)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由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身份認(rèn)知轉(zhuǎn)型,標(biāo)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自覺以全面的制度化國家治理來完成執(zhí)政興國使命。
應(yīng)該說,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建設(shè)和制度化治理,充實(shí)了政治、經(jīng)濟(jì)和社會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制度,提升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能力,促進(jìn)了人民民主的成長,保障了公民社會的成長,奠定了法理制度權(quán)威的基礎(chǔ),促成了重大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成就,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維護(hù)了國家的基本安全秩序。簡言之,較之于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運(yùn)動式治理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化治理在社會資源正義分配、國內(nèi)秩序以及外部安全等國家治理層面具有不俗的表現(xiàn),為中國共產(chǎn)黨完成執(zhí)政興國使命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然而,由于制度設(shè)計(jì)和制度運(yùn)作等層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致使制度化治理還不完美。具體而言,在制度設(shè)計(jì)層面,由于認(rèn)識和客觀環(huán)境等原因,一些制度機(jī)制的設(shè)計(jì)還不到位。例如,中國各層級政府的權(quán)力清單制度還未到位,法制建設(shè)滯后,黨紀(jì)約束、反腐以及協(xié)商民主等方面的制度設(shè)計(jì)也尚未到位。在制度運(yùn)作層面,一些制度運(yùn)作過程中出現(xiàn)了偏差和沖突現(xiàn)象,未能取得預(yù)期的效果。例如,黨的領(lǐng)導(dǎo)、人民當(dāng)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jī)統(tǒng)一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架構(gòu),在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中還不完善,作為人民當(dāng)家作主重要途徑的人民代表大會未發(fā)揮應(yīng)有作用等問題。總之,正是制度設(shè)計(jì)和制度運(yùn)作存在某些問題,致使社會分配不公、群體性事件頻發(fā)、社會秩序不夠穩(wěn)定等國家治理問題。
制度化國家治理所存在的上述問題,恰恰給運(yùn)動式治理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和空間。正因?yàn)槿绱耍覀儾懦3?吹健皰唿S打黑專項(xiàng)斗爭”、“消防安全專項(xiàng)治理”等“集中整治”、“專項(xiàng)治理”、“零點(diǎn)行動”這類的行政性運(yùn)動治理,還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所推動的“三講教育”、“先進(jìn)性教育”、“群眾路線教育實(shí)踐”以及“三嚴(yán)三實(shí)”教育等政治學(xué)習(xí)性運(yùn)動治理。當(dāng)然,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在上述行政性運(yùn)動治理和政治學(xué)習(xí)性運(yùn)動治理的實(shí)踐過程中,相應(yīng)治理領(lǐng)域的制度也得以處于不斷改革和完善的進(jìn)程之中。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的運(yùn)動式治理不僅僅是為了彌補(bǔ)當(dāng)前制度化國家治理的漏洞,而且還促成了相應(yīng)治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最顯著的體現(xiàn)就在于,為了應(yīng)對治理的制度化不足,規(guī)避運(yùn)動式治理的弊端,中國共產(chǎn)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和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biāo)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到了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國共產(chǎn)黨更是首次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對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做出了總體部署。總之,盡管改革開放進(jìn)程中存在著如美國學(xué)者湯森和沃馬克所指出的由運(yùn)動式治理來推進(jìn)制度化治理進(jìn)程這一“制度化運(yùn)動的悖論”,[8]但制度化治理已是目前中國國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執(zhí)政興國已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自覺認(rèn)識和行動,已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現(xiàn)代國家成長態(tài)勢。
四、結(jié) 語
綜上所述,以社會資源正義分配、國內(nèi)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證為核心要義、任務(wù)的國家治理,是現(xiàn)代國家的基本屬性,而國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是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內(nèi)在邏輯,它是考察現(xiàn)代國家成長較為科學(xué)、合理的維度。正基于此,如前文所述,中國現(xiàn)代國家經(jīng)歷了獨(dú)特的成長軌跡,即由傳統(tǒng)國家治理危機(jī)所促成的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建國階段,到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運(yùn)動式治理所帶來的國家一體化階段,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化治理所帶來的執(zhí)政興國階段。應(yīng)該說,制度化治理是中國目前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主要任務(wù),也是現(xiàn)代國家的理想治理模式所在。
另外,必須提及的是,本文所選擇的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維度,對于目前現(xiàn)代國家成長研究至少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意義:
第一,現(xiàn)代國家成長研究不能簡單停留在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的擴(kuò)張與控制層面上,還應(yīng)深入剖析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擴(kuò)張與控制的合法性問題。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擴(kuò)張與控制的合法性在于,國家權(quán)力對社會基本訴求的實(shí)現(xiàn)和滿足,而這涉及的是國家治理范疇,包括社會資源的正義分配、國內(nèi)秩序的保障以及外部安全的保證等。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研究,應(yīng)重點(diǎn)關(guān)注國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問題,這樣才能更深刻地認(rèn)識現(xiàn)代國家的基本屬性以及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內(nèi)在邏輯。正因?yàn)閲抑卫碇诂F(xiàn)代國家成長的重要性,作為為數(shù)不多的探討國家治理能力與國家構(gòu)建關(guān)系的學(xué)者,日裔美籍政治學(xué)者弗蘭西斯·福山的相關(guān)研究近年來受到廣泛關(guān)注。[11]
第二,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可以淡化現(xiàn)代國家成長研究的西歐色調(diào)。正如有國內(nèi)學(xué)者指出,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在論及現(xiàn)代國家成長時,主要引用和分析的是西歐經(jīng)驗(yàn)。[12]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西歐民族國家的成長經(jīng)驗(yàn)為依據(jù),探討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動力問題,探討國家權(quán)力與社會之間的組織結(jié)構(gòu)架設(shè)等問題,從而忽視了非西歐國家的特殊情境。而從以社會資源正義分配、國內(nèi)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證為核心要義、任務(wù)的國家治理維度,來探討現(xiàn)代國家成長問題,就可以淡化現(xiàn)代國家成長研究的西歐色調(diào),可以增加現(xiàn)代國家的多元成長模式。
第三,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為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比較研究提供更為科學(xué)、合理的分析維度。目前關(guān)于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比較研究,往往簡單地從國家組織結(jié)構(gòu)、制度形式等維度進(jìn)行比較。這樣的比較研究容易陷入制度結(jié)構(gòu)形式的簡單論爭之中,得不出有價值和規(guī)律性的認(rèn)識。而從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維度,對各國制度結(jié)構(gòu)形式運(yùn)作效果進(jìn)行比較研究,將為各國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比較和評價提供一種更為科學(xué)、合理的維度,而這將有助于深化和充實(shí)現(xiàn)代國家成長的比較研究。
[1] Charles Tilly.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2] [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M].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
[3] [美]西里爾·布萊克.現(xiàn)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 徐勇.“回歸國家”與現(xiàn)代國家的建構(gòu)[J].東南學(xué)術(shù),2006,(4).
[5] 樊紅敏.論現(xiàn)代國家的理想型——以權(quán)力運(yùn)作為視角[J].東南學(xué)術(shù),2006,(4).
[6] 儲建國.大部制改革與現(xiàn)代國家構(gòu)建[J].學(xué)習(xí)與探索,2008,(7).
[7] 胡鞍鋼.中國政治經(jīng)濟(jì)史論(1949—1976)[M].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8.
[8] [美]詹姆斯·R·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M].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9] 轉(zhuǎn)引自郭為桂.群眾路線與現(xiàn)代中國的國家建構(gòu)——紀(jì)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九十周年[J].東南學(xué)術(shù),2011,(4).
[10] 鄧小平文選[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美]弗朗西斯·福山.國家構(gòu)建——21世紀(jì)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7;政治秩序的起源[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yè)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5.
[12] 劉義強(qiáng),管宇浩.國家建構(gòu):為什么建構(gòu)、建構(gòu)什么與如何建構(gòu)——簡論國內(nèi)研究之不足[J].學(xué)習(xí)與探索,2015,(6).
[責(zé)任編輯 劉蔚然]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Building of China’s Modern State
Ye Qil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building of modern state
The state governance, which takes the justic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e guarantee of domestic order and the external security as the core, is the basic attribute of the modern st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building of modern state. In the dimens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the modern state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unique building path, which is from the traditional state governance crisi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revolu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30 years of state integr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n to the new stage of building th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 本文系華僑大學(xué)科研基金資助項(xiàng)目、華僑大學(xué)高層次人才科研啟動費(fèi)項(xiàng)目“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與中國現(xiàn)代國家成長研究”(項(xiàng)目號:14SKBS204)的階段性成果。
葉麒麟,華僑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副教授(福建 泉州36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