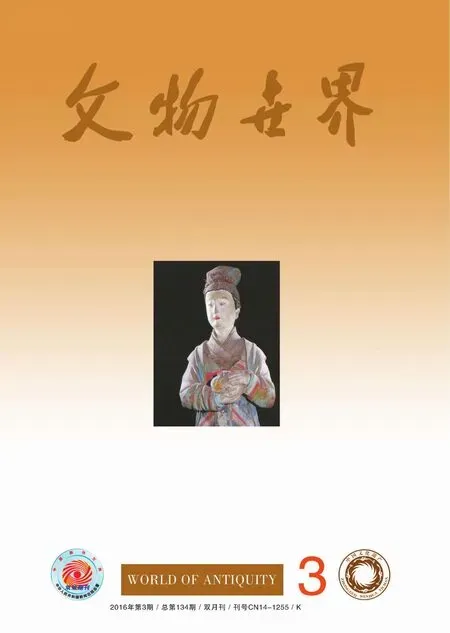傅山與屈大均交游考論
□宋濤
傅山與屈大均交游考論
□宋濤
傅山與屈大均,為清初南北兩大遺民,在山西、廣東兩地遺民群體和士大夫階層中均為旗幟性人物,而兩人在當時也有交往,本文擬就傅、屈兩人的交游進行考證,并對這兩位煊赫青史的文化巨人在志節、思想等方面做出比較和論述,以冀對明遺民的行藏異同進行探考。
傅山屈大均遺民交游
一
公元1644年,明朝滅亡,隨即入關的清軍迅速掃蕩各地農民軍及殘明武裝,神州大地又一次陷入兵燹之中。明清遞嬗,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朝代更迭,而更兼有文化陸沉帶給中原士夫的恐慌,正如陳寅恪先生在為王國維所撰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所說:“凡一種文化,值其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故而凡遇此衣冠更迭之際,家國命運與士夫氣節就猶如水之于石,必有“水落石出”之效果。從宏觀的角度觀之,當然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忠烈”還是“遺民”,抑或是“貳臣”,造成其出處迥異的深層原因多維而復雜,不可一概而論,但遺民畢竟是中華傳統文化得以獲得尊嚴的群體,理應得到后人的尊敬。
清初遺民見諸史籍者,據謝正光所編《明遺民錄匯輯》所統計即有2000余人,而其中根據分省和文化區域不同,各地又各有其公認的領袖人物。在山西,傅山無疑是遺民領袖,而在廣東,屈大均則在殉明的陳邦彥、陳子壯、張家玉等“三忠”之后,扛起了遺民士大夫抱志守節的文化大旗,這一北一南兩大遺民的交往,往往為后世研究者所樂道,而其中的細節正是本文試圖梳理和厘清的。
二
傅山生于1607年,時在明萬歷三十五年,明亡時38歲,故其在《甲申守歲》一詩中有“三十八歲盡可死,棲棲不死復何言……怕聞誰與聞雞舞,戀著崇禎十七年”[1]之語。屈大均生于1630年,為明崇禎三年,明亡時僅15歲。然而與北方不同的是,隨著京師陷落,崇禎殉國,南方各省紛紛成立政權,是為歷史上的“南明”,由于內訌及腐敗,南明各小朝廷也相繼覆亡,殘明勢力逐漸向東南沿海和云貴一帶退縮,在這一時期,南方各省仍沿用明朝年號,奉明為正朔,實際上并未納入清朝的控制,所以直到廣東的隆武政權滅亡、李成棟反正和廣州城再次被清軍攻陷,時已在順治七年,即1650年,而這一年屈大均已經21歲,已是幾度投身抗清武裝斗爭并蜚聲嶺南文壇的著名遺民了。傅山和屈大均兩人年齡相差23歲,在行輩上應為兩代,但由于南北淪喪的時段不同而都可稱之為第一代遺民。其中傅山由于在崇禎時期即以援救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而名震士林,所以在大江南北尤為受人尊崇,在北方遺民的心目中,儼然僅次于隱居河南的孫奇逢之下而成為領軍人物之一。
明亡后,傅山輾轉飄零,后定居于太原東郊松莊,此后,松莊漸成南北遺民、著名學者拜謁傅山、追懷故國的一處勝地,顧炎武、閻爾梅、申涵光、李因篤、朱彝尊、閻若璩等都曾前來拜訪并留下了諸多詩句篇章,屈大均也是其中之一。
康熙五年(1666年),志在恢復的屈大均為聯絡南北遺民而遍游秦晉,六月,他經由陜西入晉,從代州一路南下太原,在太原期間,屈大均憑吊古跡,慷慨悲歌,也就在此年年末,屈大均赴松莊拜訪傅山,并以兩詩志念其事:
唐氏遺民在,憂思正未央。故人期飲食,良士戒衣裳。苓采今無地,桐封舊有鄉。叔虞祠下柏,與爾共風霜。
下馬晉王宮,山河感慨中。無成空老大,不死即英雄。汾水堪灌城,并門騎易通。思深當歲暮,且詠有唐風。
——過太原傅丈青渚宅賦贈[2]
第一首詩開首“唐氏遺民在”,乃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的典故,暗指明朝為正朔,也由于山西是古代唐國故地,所以一語而兼多義,用意頗深。頸聯“苓采今無地”乃取《詩經》中的《采苓》:“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之義,以首陽山比喻遺民志節,但是“苓采今無地”,就連首陽山也已易色,還好“桐封舊有鄉”,可供遺老如傅青主者暫避身形。按“桐封”是取義周成王“剪桐封地”故事,將位于晉南的唐國封賞給其弟叔虞的典故,在此,屈大均顯然根據一些典籍誤考將太原當做了唐國的始封地,加之此前他剛剛游歷晉祠,更使他加深了這一判斷,而將詩句中的“桐封之鄉”當做了傅山隱居的太原。晉祠有周柏,相傳樹齡已有三千多年,為周代遺植,所以屈大均以周柏比喻傅山,與前面“苓采”句中暗含的“首陽山”典故相呼應,最后發出了“與爾共風霜”的期許。
第二首詩描寫屈大均游觀晉王宮殿,引發其無限慨嘆,感喟明朝宗室晉王,實則就是在追懷故明王朝,而下面的一句“無成空老大,不死即英雄”則堪稱寫照遺民可歌可嘆精神的名句。遺民之所以為遺民,正是由于他們選擇了一條既沒有殉國盡忠的死難之路,也拒絕了出仕新朝的青云之梯,他們以一種固守忠孝氣節,為文化衛道的更為艱辛、危險的生活方式艱難求存——甚至茍活,身處道德評價逼仄的傳統社會,“不死”也許是他們心中的永久自責,前引傅山《甲申守歲》一詩中“三十八歲盡可死,棲棲不死復何言”的詩句,何其悲涼,這一點,也是曾經幾度抗清又幾番失敗,目睹同志師友死難的屈大均的隱痛,然而,頑強地活下去也是抗爭的一種形式,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形式較之死難,更為壯絕和艱難,經歷了亡國之痛、恢復無望的傅山和屈大均都深深地明白這一點,所以“不死即英雄”必曾引起兩人的共鳴,也是數以千計的明遺民的共同心聲。
“汾水堪灌城,并門騎易通”一句,用春秋時智瑤聯合韓、魏攻趙,欲用汾水灌晉陽城而反為三家聯手攻滅的故事,比喻太原經歷鼎革之際的戰亂。最后一句“思深當歲暮,且詠有唐風”,可知屈大均拜訪傅山應在當年年末“歲暮”,而當時兩人應該皆有歌詠唱酬之作,按今存傅山的《霜紅龕集》中,未存傅山為屈大均所作篇什,而這決不能證明傅山沒有與屈氏相唱和,由于傅山傳世詩文結集較晚,所以他的詩文屢經后人或出于保護或出于恐懼的刪削,而直到民國時,山西學者郭象升還能見到一些今已不存的傅山詆誚清政府的詩文,可見由于屈大均的詩文集在乾隆時被打入“禁毀”之列,這勢必影響曾與他唱和的詩歌在后來諸家文集的編纂過程中被大量刪削,刪削尤為嚴重的傅山詩文“十不存一”,也就影響了后人考證其當日的交游情況。但屈大均此詩中“且詠有唐風”,應指傅山之吟詠頗有古風,傅山曾經與屈大均唱酬的史實也就不難想見了。
三
關于傅山與屈大均的結識,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兩人對彼此的崇敬,但是也一定關聯到兩人共同的朋友圈,這個主要由遺民和學者組成的文化群落在順治至康熙初期逐漸形成了一個影響力跨越南北的網絡,尊崇遺民是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風氣好尚的特色。
可能介紹傅山與屈大均結識的,首先是關中名士李因篤。李因篤(1631-1692),字子德,又字天生、孔德,號中南山人,陜西富平人,其父李映林為關學名儒馮從吾的私淑弟子。他于崇禎十六年(1643年)因李自成農民軍攻占西安而棄諸生身份。后一力為學,詩名大震,遂為關中遺民翹楚,他與盩厔李颙、眉縣李柏并稱為“關中三李”。康熙十八年(1679年)被迫應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僅月余即以母老為由上疏陳情,獲準歸養。
與傅山、屈大均一樣,李因篤也曾四方奔走,意圖反清,但最終也以失敗而告終。從現有資料來看,早在康熙二年(1663年),傅山就已與李因篤結識[3],康熙三年(1664年)李因篤到太原拜訪傅山,并作詩奉贈,而傅山也回贈以《為李天生作十首》[4],次年傅山至關中,曾訪問李因篤,此后兩人來往一直密切。
屈大均與李因篤于康熙五年五月二日結識于西安并訂交[5],二人一見傾心,遂于六月一同由秦入晉,其間李因篤還曾為屈大均做媒,介紹代州守將趙彝鼎姐姐的養女許配屈氏為妻,所以屈大均對李因篤可謂感念至深。隨后二人沿途結交遺民豪士,題詠酬唱,一路南下太原。康熙五年屈大均造訪傅山,應是與李因篤同行,或是緣于李因篤直接介紹相識,也在情理之中。
傅、屈二人另一個共同的重要友朋是顧炎武。顧炎武(1613-1682)本名繼坤,改名絳,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傭,昆山人。明季諸生,青年時發憤為經世致用之學,明亡后曾參加昆山抗清義軍,敗后漫游南北,發憤著書,為有清一代樸學之開山。傅山與顧炎武相識于康熙二年,是年顧炎武自霍州至太原,初訪傅山,隨即北上代州與李因篤相遇訂交,至陜西,又返太原再會傅山,與傅山作詩互贈,顧作《贈傅處士山》,詩中“相逢江上客,有淚濕青衫”[6]句頗有亡國之痛和相見恨晚之感,傅山作《顧子寧人贈詩,隨復報之如韻》,謂“秘讀朝陵記,臣躬汗浹衫”[7],對顧炎武的忠貞之志表示欽敬。這次之后,傅、顧之間屢有唱和,友情彌篤。
屈大均與顧炎武即相識于康熙五年,是年顧炎武北上代州,與南下太原的屈大均和李因篤相遇,顧炎武作有《屈山人大均自關中至》、《出雁門關屈、趙二生相送至此有賦》諸詩以紀其事[8]。屈大均在此之后結識傅山,其中不乏途中所遇顧炎武的推許,遺民之間的廣通聲氣,逐漸使之結成了一個廣泛的交際網絡。
也是這次并門之游,屈大均見到了老友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魚師,浙江秀水人。朱彝尊在清初詩名甚隆,與王士禛齊名,時稱“北王南朱”,朱氏曾在明亡后參加抗清斗爭,失敗后游走四方,依幕公卿。朱彝尊與屈大均結識很早,早在順治十四年(1657年),屈大均就與南游至粵的朱彝尊相交并詩文和答[9],后屈大均北上途經秀水,也曾與朱彝尊、徐嘉炎等名士流連唱和。
康熙五年(1666年),朱彝尊在太原布政使王顯祚幕府,時顧炎武住在太原東郊松莊傅山家中,朱彝尊曾往拜訪,顧炎武作《朱處士彝尊過余于太原東郊,贈之》[10],而這次拜會顯然也讓朱彝尊得以結識傅山。雖然朱彝尊未必像李因篤、顧炎武那樣與傅山、屈大均兩人均極熟識,日后他也易轍投效清政府,但此時朱彝尊也屬于由顧炎武、傅山等人構筑而成的這一遺民群落。
除李因篤、顧炎武、朱彝尊三人之外,在康熙五年前后,傅山和屈大均在太原還均曾與戴本孝、毛會建等遺民人士唱和,可知這一時期居住、游幕和途經太原的眾多遺民的密集交往,曾推動了一個遺民聯絡的高潮,傅山、顧炎武無疑是這一高潮的核心人物,而屈大均也是這一高潮形成的重要組成。
四
傅山與屈大均,雖則南北相隔千里之遙,但觀察二人生平行藏,卻頗有相合之處,這些相似或相近的人生軌跡,不僅不是巧合,反而是后人觀察、研究遺民生活和心路歷程不可繞過的問題。
首先,傅山與屈大均均曾投身火熱的抗清斗爭,對于明朝,可謂盡其“忠”字。傅山曾于順治六年(1649年)襄贊大同總兵姜瓖反正,后雖然失敗卻仍不灰心,順治四年至十年間(1647-1653),傅山與南明宋謙秘密聯絡,后因宋謙被捕而牽連下獄,在獄中,傅山抗詞不屈,絕食欲死,后雖在朋友、弟子的營救下得以開釋,但卻“深自咤恨,以為不如速死之為愈”(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此后傅山仍不改初衷,終生不與清政府合作,據考證,他還與山東榆園義軍、山西交山義軍等抗清力量聯絡,可謂矢志不渝。
屈大均于順治四年(1647年)就參加了其師陳邦彥的抗清武裝,后清軍攻克廣州,陳邦彥兵敗身死,屈大均冒險將老師尸骸收埋。順治五年(1648年),清將李成棟反正,南明永歷帝由廣西桂林遷回廣東肇慶,屈大均聞訊趕赴肇慶行在并被授予官職,然而之后形勢惡化,廣州又被攻下,屈大均出家為僧,逃避迫害。順治十七年(1660年),屈大均北上紹興,與抗清人士魏耕一起參與到鄭成功、張煌言的反攻計劃中,可惜鄭氏失敗,退回廈門,屈大均的復明夢想又一次落空,其后屈大均甚至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參加吳三桂、孫延陵的軍隊,結果又一次以失敗告終。雖然反清斗爭愈來愈不可為,但屈大均在一次次的失敗之余,仍然繼續北上,聯絡各地反清力量和遺民人士,意圖恢復。
無獨有偶,經歷了牢獄之災的傅山在順治十六年(1659年)聽聞鄭成功進兵江南的消息后,急忙從山西出發,浮淮渡江,趕奔南京鄭氏軍營,可惜鄭氏兵敗先退,傅山在失望之余甚至萌發浮海東去之意,后雖不果行,但又一次證明了傅山的心中仍不滅復明的火焰。
其次,在傅山與屈大均的身上,又都反映出一個“孝”字。傅山一生事母至孝,甲申國變,傅山奉母輾轉以避兵燹,后雖出家入道,卻仍奉侍老母周
到如常,在生不如死的內心煎熬下,他幾次想要殉國或者出亡,但都因為考慮到母親而馬上作罷,其中包括前述傅山投奔鄭成功而不得,面對大海寫下《東海倒座崖》,若非老母在堂,則極有可能浮海東奔而去。
每當鼎革之際,對于忠孝的選擇就勢必對遺民知識分子的靈魂產生痛苦的焦灼,僅以明清之際為例,“易堂九子”之一的曾燦,明亡后也落發為僧,但在遨游閩、浙、兩廣后還是歸家以躬耕養母;著名遺民周容,明亡后亦削發為僧,后以老母在,又還俗供養,與傅山一樣,周容后也被薦博學鴻詞,但亦誓死不應召而罷。屈大均于順治七年(1650年)為避迫害而出家為僧,12年后為盡孝道而還俗,其后屈大均恪守孝道,供養老母,娶妻生子,直到其母去世之后,他才最終絕意塵世,重新遁入空門,一心禮佛。
在傅山與屈大均的內心深處,占主導地位的始終是儒家思想,無論是傅山的出家為道,還是屈大均的遁入佛門,其中都不乏對現實世界中易服薙發的反抗和蔑視,正如賈景德先生為傅山所撰聯語,真可稱道盡此等遺民衷曲:“文章氣節爭千古,忠孝神仙本一途。”
[1]傅山《傅山全書》卷十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2]屈大均《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年。
[3]李因篤《得傅征君信》,《受祺堂詩集》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1997年。
[4][7]傅山《傅山全書》卷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5]屈大均《宗周游記》,《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6][8][10]顧炎武《顧亭林詩箋釋》卷四,中華書局,1998年。
[9]朱彝尊《東官客舍屈五過譚羅浮之勝,時因道阻不得游,悵然有懷,作詩三首》,《曝書亭集》卷三;屈大均《過朱十夜話》,《曝書亭集》卷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
(作者工作單位:山西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