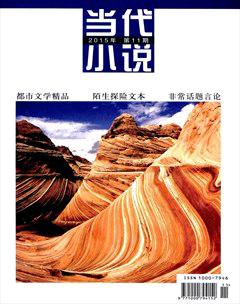花局
阮家國
這個春天好像與我無關,我已經(jīng)退休了,但說退休又不對,準確說,我是退居二線,就是不再擔任實職,不再當一個不起眼兒的副局長。縣里有個不成文的規(guī)矩,副科只能做到五十歲。本來,我想跟妻子一路外出打工,多少掙點錢,補貼一下家用,但我們單位的局長又找我做工作,要我為單位寫部門志。當然,如果我能答應下來,局里還是要另外再給我發(fā)一點辛苦費的。我跟妻子商量,妻子說,既然給你多發(fā)錢,那你就給局長一個面子。
早春時節(jié),妻子就外出了。妻子的單位是個事業(yè)單位,內(nèi)部規(guī)定可以請長假,但工資基本不算少。妻子也不是要出去打工掙錢,是要減肥。妻子身高一米六八,年輕時體重一百二十斤,生下孩子后奶水不足,不得不發(fā)奶,但一吃發(fā)奶的東西,就把身子發(fā)胖了,體重一下子長到一百五十斤。等她過了四十歲,體重就又長了十多斤。這兩年,她一直在堅持靠運動減肥,但作用不大。去年她就說,今年要想辦法減肥。有一天睡覺,我們親熱過后,她說,明年我一定要出去打工,下苦力減肥,不然就連搞這事都搞不起來了。她下了很大決心,要找回苗條,找回青春。
妻子一走,我的生活就難過起來。我不會做飯,吃飯就成了我每天最頭疼的事,因此,能在外面吃,我就盡量在外面吃。
清明前,我進山回老家踏青祭祖,給祖墳掛青,懸掛寄托哀思的清明吊。給自家祖墳掛了青,我又去妻子娘家的祖墳掛青。其實,岳父母已去世好多年了,也就是說,妻子娘家那邊也沒妻子的親人了。
岳父留下來的老房子,二舅子住過,后來二舅子也不住了,搬到了城里。岳父的老房子現(xiàn)在仍有人住,是岳父的一個本家兄弟寄居。我一個人來給妻子的父母跟爺爺奶奶掛青,好像就有點孤單。去岳父的老房子里找了一把砍刀,先順著小路上山,又走進路邊的樹扒(樹林),給妻子的爺爺奶奶掛青。這兩座墳在樹扒中間,緊挨著,墳堆上也都成了小樹扒,擠滿了茅草、竹子跟荊刺,亂蓬蓬的,看著叫人心寒。不把墳上收拾利索,掛青就是不敬不孝。我開始拿砍刀砍除妻子爺爺墳上長的東西。等把這座墳上的東西砍利索,我就出汗了。我脫掉外衣,又砍妻子奶奶墳上的東西。墳上的東西都砍干凈了,這兒就好看多了。我找了兩根我剛砍下來的青竹條子,用來掛青,給兩座墳的墳頭都掛上了清明吊。本來,我還想為妻子的爺爺奶奶燒點紙,但我又怕失火,沒敢燒。
離開這里,我又去給岳父掛青。沒想到我會遇到一個叫我姐夫的姨妹子,在去岳父墳上的半路上。叫我姐夫的人親熱地叫我姐夫,我差點就忘了答應,因為我有點吃驚,不敢相信對面走來的一個好像還年輕的女人還是我的一個姨妹子。姨妹子穿著樸素的青色衣裳,但歲月好像并沒帶走她苗條的腰身,看上去,她就像路邊剛發(fā)出來的一蔸嫩嫩的小草。還有兩個字,我不想說出來,那就是好看。我在想,她到底是我的哪個姨妹子。妻子娘家是個大家族,這么一來,我就好像有好多既認不完全又記不清楚的姨妹子,也不曉得這個姨妹子是我的叔伯姨妹子,還是叔伯的叔伯姨妹子,但我又不便問她。因此,我寫這個蹩腳故事,還只能把她稱做姨妹子。
話說回來,從我一看見姨妹子起,就覺得她對我好熱情,好像就是我的親姨妹子。我注意到,她好像一直在笑著,她臉上還有兩個小酒窩兒,酒窩兒好像也在笑著。特別是她的眼神,好像就是晴天夜空里的星星,叫人一看心里總會產(chǎn)生一點想象。看上去,她好像是個嘻嘻哈哈嬉皮笑臉的熱鬧人。真沒想到,我還有這樣一個姨妹子。姨妹子說,姐夫,你年年回來給老的掛青盡孝,可不容易。我說,有時候我也沒回來。姨妹子說,姐夫,你莫摳字眼兒,就是偶爾一兩年沒來,還不是年年來?姨妹子笑了起來,我也笑了。我問姨妹子到哪兒去,姨妹子說,春上還沒吃到筍子(竹筍),想去扳點筍子嘗新。我說,筍子應該是才發(fā)出來,正好吃,你快去扳。姨妹子說,扳筍子還不簡單?眨個眼就能扳一大捆,我先陪你去掛青,不是你一個人還怪孤單。孤單?姨妹子說我孤單,我孤單不?我也不曉得自己孤單不孤單,她這么說,我也不好說不叫她去。我們就一路去掛青。
岳父的墳在地邊上,這兒倒是不怕失火,能燒紙。姨妹子也從家里拿了火紙跟清明吊來,我說,這些都有,你就不用拿了。她說,各是各的心意,到伯父伯母他們墳前來,不燒點紙,心里會過不去。她這話說得倒也有理。她先陪著我給岳父岳母燒紙,又給墳頭掛上清明吊。
給岳父岳母墳上掛了青,我的事就做完了,可姨妹子又要我跟她一路去扳筍子。想到她陪我掛青,禮尚往來,我就陪她去扳筍子。到了要扳筍子的地點,她說我,你沒扳過筍子吧。我說,好像還是小時候扳過。她說,我就曉得你沒扳過,樹扒里難得拱,你就莫去扳了。扳筍子,我還是想扳,但我又怕別人看見我跟姨妹子往樹扒里鉆,會說閑話,就沒進樹扒。
姨妹子進路里邊的樹扒去扳筍子,我就在路外邊的樹扒里找筍子。長竹子的地點才長筍子,找啊找,可我也沒找到好多筍子。我又鉆進一處竹子更多的樹扒,才看見不少筍子。聽見姨妹子在上邊叫我,我也沒答應。不知咋的,我想跟她開個玩笑,叫她一時不曉得我在哪兒。她又在喊,姐夫姐夫,你在哪兒。我仍然不吭氣,這時,我又聽見她猛地驚叫起來說,哎喲,蛇,好大一條蛇。聽見她說蛇,我就渾身一掣,打了一個大激靈。再看我身邊,樹扒里每一根竹子的竹蔸邊上,還有好多枯枝敗葉里邊,好像就都有蛇要出來。有一條大蛇好像就看見了我,正吐著長長的蛇信子。我自小就怕蛇,怕得要命,就再也不扳筍子了,就連已扳的筍子也不要了,連滾帶爬地朝樹扒外跑,要快速甩開大蛇對我的威脅。
我還沒上路,姨妹子就格格格地笑了起來。等我上路,她說,姐夫,看把你駭?shù)模愫眯θ耍λ牢伊耍λ牢伊恕N冶г顾f,你還笑?她這才不笑了,說,你放心,蛇還躲在洞里呢,到熱天才會出來。我說,一聽見蛇我就怕,哪兒還顧得想會不會有蛇?她不說蛇了,問我,你扳的筍子呢?我說,還在下邊。她抿著嘴笑,又進路下樹扒里去拿筍子。過好一下,她才上來,又多扳了一些筍子。見我坐在路邊上,右腳沒穿鞋,她說,哎喲哎喲,看我看我,這玩笑可開大了,害你把右腳皮鞋都蹬壞了。她擱下筍子,拿我右腳皮鞋看。我的右腳皮鞋,右邊的鞋幫子豁了,肯定是剛才搶時間上來時,哪一腳沒踩好,一腳就把皮鞋右邊的鞋幫子蹬豁了。她說,姐夫,對不起,我明兒給你買一雙皮鞋。我說,哪個要你買?這鞋幫子找修鞋匠還能補起來。她說,那算不行,補過的皮鞋不把你穿丑了?現(xiàn)在你沒鞋子穿了,咋搞?要不你在這兒等著,我回去給你拿一雙鞋來。我說,沒事兒,就是不穿鞋也能走。
見姨妹子把扳的筍子都撿到挎籮里,要走了,我站起來,右腳把鞋趿著,想將就著走。她叫我等一下,說,這挎籮背帶上恰好綁著一條布條子,好像就是給你準備的,來,把鞋綁到腳上,就能走了。我用布條把皮鞋綁到腳上,果然就能走了。
到她家里,她給我找了一雙布鞋,叫我換上。布鞋是新鞋,倒也還合腳,我說,這布鞋好像就是給我做的,布鞋養(yǎng)腳,還是穿布鞋舒服。她說,你在城里就沒穿過布鞋?我說,上班不穿,回家才穿。她說,這雙你先穿著,我明兒再給你做一雙。我隨話問話說,這鞋是你做的?她說,咋的,你還不信?閑的時候,我也做布鞋賣。我這才注意到,我腳上穿的是一雙膠地子、燈心絨鞋面的布鞋,跟從店里買的布鞋差不多。我說,沒想到你還有做鞋的手藝。她說,啥手藝不手藝,還不是想摸幾個錢?我再次看我腳上穿的布鞋,沒想到我這次回來掛青,倒把皮鞋踩壞了,又穿上了一雙姨妹子做的布鞋。
她洗手給我泡茶,開始剝筍子。見她忙著,我也去幫忙。她說,你們城里,筍子早就嘗新了吧?我說,筍子是有人在賣,不過我倒還沒嘗新。她說,那好,中午我們就炒筍子嘗新。杯子里泡的茶不燙嘴了,我喝兩口茶說,還是春天好,又能吃椿芽兒(香椿),又能吃筍子,新茶馬上又要出來了。她說,茶場馬上開園,又要忙著摘茶葉了。我說,給茶場摘茶葉,多少錢一斤?她說,頭一茬兒單芽茶,一百元一斤。我說,那要是摘自家的茶葉,賣給茶場呢?她說,那又不一樣了,一斤多三十元。我問,你家有茶葉沒?她說,有一點,不多,不像茶場那邊的人,家家都有不少茶葉。我說,茶場的新茶不好買吧?她說,茶場開園頭幾天,等著買新茶的人多,不曉得有好多。我說,明兒去看看新茶能買到不。她說,茶場一開園,我先摘自家的茶葉,拿去請茶場先做出來給你。我說,這兩天茶場能開園不?她說,說不定明兒天就開園了。
姨妹子家門前院壩邊上有一棵桃樹,桃花掛滿枝頭,紅艷似火。我正在觀賞桃花,姨妹子喊我吃飯。
姨妹子三兒兩下就把午飯做好了,炒了個筍子臘肉,還有個椿芽兒炒雞蛋,看起來好像也并沒把我當客待,其實像這樣遇飯吃飯最好。要是她把飯菜做得太豐盛了,我心里還會有負擔,但吃飯只有我們兩個人吃。后來我才曉得,她男的外出打工去了,她家在城里買了房子,要裝房子。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給我打電話,說茶場今兒開園,叫我先到她家。我一看時間,才五點過一點,還真有點后悔昨兒天不該給她手機號。我說,太早了。她說,一日之計在于晨,不起早,摘茶葉還能掙到錢?一日之計在于晨,理是這個理,但我仍不想起早。她說,你趕緊起床,我騎摩托來接你。看來我就是再不想起早也不行了,還只能起床。
來到她家,時間還不到六點。見她把摩托朝屋里推,我說,不到茶場了?她說,先摘自家的茶葉,再到茶場,請技術員把茶葉做出來。我說,你今兒就想把新茶喝到嘴?她說,是呀,春上不喝新茶,又缺味兒又差勁兒。我說,你說話也好有味兒。她哈哈笑著說,有沒有味兒我不曉得,我只曉得今日有酒今日醉,人要及時行樂。我說,所以你今兒就要把新茶喝到嘴。她說,就是呀,不瞎說了,我們趕緊搶時間摘茶葉。現(xiàn)在,我好像又發(fā)覺,她又像個心直口快、有口無心的人。
她家門外有自來水水龍頭,鎖上門,她去洗手,還叫我也洗手。她說,摘茶葉,手要干凈。我說,我可沒摘過茶葉。她說,摘茶葉還不簡單?一看就會。我說,摘茶葉好像就不是男的做的事。她說,你怪說,等我們到了茶場,你看有沒有男的摘茶葉。
她家的茶園離家有兩里路,有三四分地。我們來到茶園,天才亮。茶葉才發(fā)出來,只發(fā)出一個嫩芽芽兒來,摘單芽茶,正是摘的時候。清明前后,茶場要做一芽一芽的芽茶,摘茶葉要摘單芽。她邊摘茶葉邊說,摘單芽茶,要摘得勻凈,選稍大一點的芽茶摘,不能拿手指甲掐芽茶葉根兒,拿兩個手指逮住,輕輕一拈一拽,一個芽茶就摘下來了。我摘了幾下,她笑著說,摘茶葉就是這樣摘的,看來你倒還怪在行,我說一看就會嘛。這是我頭一回進茶園摘茶葉,也是頭一回看她摘茶葉。手腳快的人,不拿一只手摘茶葉,拿一雙手摘。姨妹子就是一雙手摘茶葉,兩個手刷刷刷地摘。
由于摘茶葉摘得早,我們只用了半早上就把她家的茶葉摘完了。我們又騎車趕往茶場。
一到茶場,我就看見,茶場滿山遍坡的茶園,處處都站著摘茶葉的人,果然也有男的在摘茶葉。茶場場房的茶葉加工車間正在忙著加工今年摘得最早的茶葉,有好多人在這兒等著拿新茶。我就遇見了好幾個從縣城來等著買新茶的老熟人,見我騎車帶個女的來,有人還不懷好意地看我。
等姨妹子把才摘的茶葉交到技術員手上,我們又到茶場的茶園摘茶葉。路上,我問她,茶場能幫你做茶葉?她說,你想得倒美,人家自己加工茶葉都忙不過來。她前后看看,見沒人過來,才說,有個技術員是我一個老表,我給他衣裳荷包里塞了包煙,他才勉強答應下來。我說,看來喝點新茶還不容易。她說,當然,你說哪個不想先嘗新呢?
為搶摘茶葉,茶場給摘茶葉的人管午飯。午飯前我們只摘了個把小時茶葉,我手笨,摘的茶葉少得可憐,好像還沒蓋住籃子底,不好意思過秤,我把我摘的茶葉倒到了她的茶葉上面。她說,你摘的也不少,下午你攢勁兒摘,看能摘好多。
下午是我頭一回摘茶葉掙錢,我摘了足足五個小時茶葉,掙了五十元錢。她說我,行啊你,掙了不少。我說,我掙的錢還不夠你的一半。她說,也不少了,你沒想想?你一只手就摘了這多。我說,這倒是的,但我只能一只手摘。她說,明兒天再摘,爭取掙一張大票子。我說,你摘,我不想摘了。她說,摘茶葉多好,又不出力氣又能掙錢,你就把這當做下鄉(xiāng)體驗生活。把摘茶葉當做體驗生活,我沒想到她還會這樣說。我說,我又不是大作家,還要體驗生活?她說,那大作家又是啥人?聽說你就是個大筆桿子,大筆桿子難道就不是作家?我說,莫言你聽說過沒?他就是大作家。她說,電視上看過,好像前不久還得過世界大獎,拿了好幾百萬獎金。我說,我只是個能將就著寫個材料的人,跟他比,他在天上,我在地上。她說,也不能那樣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她請茶場幫忙做的茶葉還拿不到手,也就是說,今兒天還喝不到新茶,但我們一到她家,她就從身上拿出一點新茶來。新茶用一個小塑料袋裝著,只有一點點,大概只能泡幾杯茶。我說,哪兒來的新茶,是不是你老表悄悄給你的。她笑笑說,新茶總算能喝到嘴了,還真是的,是他悄悄給我的,熟人總能多吃四兩豆腐嘛。
她拿兩個玻璃杯泡新茶,叫我喝茶,她去做晚飯吃。剛泡的芽茶漂面,過好一氣,芽茶才會在淡青色的茶水中下沉到杯底。這時,茶葉不燙嘴了,正好喝。這是我今年喝頭一杯新茶,我先把茶杯拿到鼻子前聞聞香氣。新茶的清香味兒好誘人,我抿了一點,再抿一點,慢慢品嘗新茶的清香。
我叫她來喝茶。她喝下一口,說,香,好香,只有清明前喝新茶才香。我說,過了清明喝新茶就不香了?她說,也不是不香,但節(jié)令不能錯過,等過了清明,你再喝新茶,就又是一個味兒了,少了一種清明前才有的鮮味兒。
吃過晚飯,她帶我去卡五星。昨兒天她就留我卡五星,但昨兒晚上我回老家有事,沒玩成。
卡五星是現(xiàn)在這邊正流行的一種麻將牌的新玩法,據(jù)說是從諸葛亮生活過的襄陽那邊傳過來的。卡五星三個人比輸贏,只打條餅萬三種牌中的條餅兩種牌,外加紅中、白板、發(fā)財三種字牌,不準吃牌,只準碰牌杠牌,牌路活,大和多,可規(guī)矩也多。手中有四六條、四六餅,停牌五條、五餅,贏牌就叫卡五星。最小的和叫“屁和”,屁和不能逮炮,只能自摸,曬牌(亮牌)自摸才能翻一番。卡五星贏錢,一般是屁和的四番,跟清一色、小七對贏錢一樣多。像“杠上杠”、“杠上開花”、“手抓一”、“海底撈”,贏錢都翻一番。最大的和叫“滿的”,贏錢是屁和的八番。像清一色卡五星、清一色中有四張同樣的牌、有兩對同樣對子的“龍七對”,還有有三句字牌的“大三元”,都是滿的。
現(xiàn)在是個吃喝玩樂的時代,縣城里除了人多房多,就是麻將機多。可以這樣說,卡五星讓麻將館兒跟麻將機都翻了好幾番。城里大街小巷處處都是麻將館兒,麻將館兒還蔓延到了鄉(xiāng)下。在岳父家老屋后邊的貢維平家,就有一臺麻將機,今兒晚我們就去那兒卡五星。
在貢維平家卡五星,打一場牌收臺費十元。我跟貢維平也是老熟人,跟他說幾句客氣話后,我們就去卡五星。我們還沒在麻將機邊坐下,我見姨妹子就遞給貢維平二十元。貢維平對我說,我哪兒能收你臺費?我說,人親財不親。姨妹子說,就是,老表是老表,蘿卜還是三分錢一斤。貢維平咧著嘴笑,還是把錢接了。貢維平打開麻將機開關,說,哪個跟你是老表?姨妹子說,黃泥巴打灶,各喊各叫,我今兒就把你喊老表,咋了?貢維平說她,你是個熱鬧人,咋說咋好聽,老表就老表吧。貢維平叫我先做莊家,我推辭一下,只好按色子拿牌。要說起來,貢維平把我岳母喊姑太婆,在輩分上他比我還矮兩輩。
卡五星,五條五餅最燙手,晚打不如早打。頭一把牌,我手中有三個五餅、三個八餅,天生停和,停四七條,抓頭一張牌,我抓到一個八餅,開杠,杠到一張四條,屁和自摸,但我卻嫌和小,把五條打了出去,過一圈,上家貢維平碰三條,打出一張五餅,我又開杠,竟又杠到一張五條。我們玩的是屁和自摸輸家一人給五元的麻將,這把牌,我杠開卡五星,贏了個滿和,滿和封頂四十元,加上一個暗杠、一個點杠,貢維平給我六十元,姨妹子給我五十元。這把牌我只用了分把鐘就贏了一百一十元,而我今兒天摘大半天茶葉,才掙了五十元,難怪好多人都眼熱卡五星。要說魅力,能贏錢才是卡五星的魅力。
玩物喪志,說起卡五星,我怕上癮,平常也不大玩,可牌逢生手,這晚我火兒沖,牌運好得出奇,手上要啥牌,就能抓到啥牌,或碰到啥牌,隔三岔五總要摸個滿和。有好幾把牌,我還得感謝姨妹子,是她給了我碰牌的機會。
牌打到后來,她說不打了,沒錢給了,再說明兒天還要起早摘茶葉。她掉了三百多元,貢維平也掉了百把元,我上場就沒掏本兒,贏了將近五百元。她掉得最多,我說把她掉的錢退給她,她說,看你,姐夫,說到哪兒去了?錢是身外之物,掙不完也花不完。看來,她倒還真是個豁達人。
這晚我就在貢維平家睡覺。第二天一早,我跟姨妹子又去茶場摘茶葉。這天,我在茶場買了一斤不帶包裝的新茶,她把請茶場做的新茶也拿回來了。晚上,我們又在貢維平家卡五星。這晚,她又輸了兩百多元,把她今兒天摘茶葉掙的錢掉了個精光。
睡覺起來,我看見天在下雨。下雨自然就摘不成茶葉了,難怪姨妹子沒過來。下雨也好,我正好回去。昨兒天局長親自給我打電話,要我回去幫忙搞個材料。
我洗漱用的東西隨身帶著,本來,我可以不到姨妹子家,可我的腳不知不覺就走到了她家。
我說要走,她說,莫走,下雨正好陪你卡五星。我說,十賭九輸,我看這卡五星玩不得,你最好也莫玩了。她說,愿賭服輸,卡五星哪兒有不輸錢的?我說,你還是早點進城裝房子。她說,等茶葉一摘完,我就進城。見我真要走,她把請茶場做的新茶拿出來給我,我說,你留著喝,新茶我買了。她說,你買的是你買的,這是我的一點心意,不嫌棄就拿著。她這樣說,我就只好拿著。
我要去鄉(xiāng)上搭車,可雨下得大了一點,我又沒帶傘。她給我找了一把傘,叫我等她一下。我打開傘,走過她家院壩,走到桃樹邊看桃花,我發(fā)覺兩天沒看,這棵桃樹上的桃花開得更艷了。桃花太好看了,我有點戀戀不舍的,好像舍不得離開這棵桃樹。
她說到鄉(xiāng)上有事,就便兒送送我。我說,看來這雨是慢上勁兒,得下一天,那你就便兒給你女兒送把傘。她說,就是,今兒天星期五,女兒要回來。我說,你女兒在上幾年級,學習不錯吧?她說,在上三年級,好像還行,我還想把她轉(zhuǎn)到城里去上學呢。我說,這當然應該。她說,可又怕進不了縣實驗小學,我還想請你幫個忙,看能不能把我女兒的戶口轉(zhuǎn)到你家。我說,到縣實小上學,是不是一定要看戶口?她說,是這樣,縣城十字街、北大街、東門街的戶口才報得上名。呃,姐夫,給我女兒轉(zhuǎn)戶口這事,你要給我姐說吧?我說,這事肯定要跟她商量,我把她電話給你,你直接跟她說吧。她說,我才不跟她說呢,我就找你。我說,這事你等我想想再說。
我沒想到,姨妹子要我?guī)瓦@個忙,也不知道這個忙我能不能給她幫到。回家后,我一直在猶豫著,這事跟不跟妻子說,又該咋跟她說。妻子每隔幾天就會發(fā)短信,說她打工的辛苦,說她有多累,當然,也說她的減肥,說她體重下降了八公斤。每次跟她發(fā)短信,我都想說說姨妹子女兒轉(zhuǎn)戶口的事,可話到嘴邊,我又咽回去了。我還真怕妻子不僅不答應,還會犯疑,懷疑我的動機,為啥要給一個原來我都不認識的姨妹子幫忙,給她的女兒轉(zhuǎn)戶口。
谷雨過后,有一天下午,姨妹子打來電話,叫我到公園東頭兒的小廣場去。這時我在家里剛把單位一個材料修改完,一看時間,我在電腦前已坐了兩個多小時,正想出去走走,活動活動身子骨。
縣城有一條小河,河北是老城,河南是新城,公園就在新城河邊。我家住在東門街,從這兒到公園不遠,過河就到了。公園建成有好幾年了,據(jù)說曾規(guī)劃在公園南邊建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三館”,可后來原計劃建“三館”的土地卻變成了一棟棟電梯樓。一大片電梯樓把公園南邊的視野都堵死了,看起來,公園又好像成了電梯樓的院壩。
河上有座大躍進時建成的躍進橋,過了躍進橋,往西邊走幾步就是公園東頭兒小廣場。小廣場的北邊下面是河,邊上有欄桿,姨妹子正站在欄桿邊上,手扶著欄桿。我過橋時就看見她了,她也看見了我。一看見她,就見她在笑。我好像有好久都沒看見她笑了,看見她臉上的兩個酒窩兒,我心里竟咯噔了一下。
她帶我去看她買的房子。她買的房子就在公園小廣場南邊路外,是一樓,不大不小,有一百一十多個平方。我說,這個點好,離學校、菜市、縣醫(yī)院都不遠,辦事就是方便。她說,最好能趕在秋季開學住房子,兩三個月裝得完不?可我現(xiàn)在就連裝修工都沒請到。我說,算你運氣好,我這兒就有裝修公司老板的電話,我馬上給你找裝修工。
我一打電話,裝修公司的人馬上就來看房子,說明天就派人來裝修。裝修公司的人一走,我發(fā)覺姨妹子的臉上簡直就笑成了一朵花,她又叫我到她住的地方去。
我沒想到她還租了住處,她租了兩小間房子,隔她買的房子不遠,也是一樓。一進屋,我就看見屋里擱著不少筍子、椿芽兒。我說,你帶了這么多好吃的來。她說,我還給你帶了一些,走時你帶回去。我說,我不要,又不會做飯。她說,你不會做飯,姐姐也不會做嗎?我說,忘了給你說,她出門去了。她說,那也好辦,在她回來前,你就在我這兒吃飯。她洗手給我泡了茶,又開始擇菜做飯。看來,晚飯只有在這兒吃了。
她這次進城,給我?guī)Я艘浑p她親手做的布鞋。我喜歡穿她做的布鞋,把布鞋拿了回去。晚上,洗腳后,我就把新鞋穿上了。穿上前,說不清是為啥,我還把一只鞋子拿到嘴前,叭叭地親了兩口。
頭兩天,裝修工在她的毛坯房里給墻打排電線的槽子,做敲敲打打的事,我們就去采買先要用的裝修材料。她沒裝修過房子,也不曉得咋買材料好。材料只有看了才有比較,才能選擇,我就帶她先看材料,找賣裝修材料的商店一家家地看。我們差不多看了整整一天,可她還是拿不定主意,該買哪種檔次的材料好。我說,裝房子不能太愛好了,你就是花百兒八十萬元裝修,十年后看起來跟人家只花十萬元裝的房子也沒好大差別,倒不如圖簡單。她說,你說的我懂,就是不能花大價錢裝房子,可也不能買太差的材料,那就買中不溜兒的中檔貨。我說,還有,我覺得最好不鋪地板,一鋪地板,一來客,人家就要換腳,穿鞋套,多麻煩?她說,倒也是,鋪不鋪地板,等我問問你挑擔(連襟)再說。
在她那兒一連吃了幾天飯,我就不好意思再吃下去了。這天下午,她又留我吃飯,我說,晚上有人約我吃飯。她看看我說,你哄人,看你一下,我就曉得你在說假話。我說,我總不能白吃白喝,咋好意思在你這兒長期吃飯?干脆這樣,以后我來吃飯,每頓給你二十元生活費。她說,看你,又說到哪兒去了?你一直在給我?guī)兔φ泻粞b房子,按說,我又要管你飯,又要給你開工錢。這話聽起來順耳,聽她這樣一說,我就覺得她真會說話。我心里又不能不說,她這話說得不是沒道理。
妻子走后,我就像個沒家的人,但自從姨妹子進城后,到她那兒去,我能吃現(xiàn)成兒的飯,我就又像個有家的人了。既然她這兒好像是我的家,我就得顧家。第二天,我就買了幾根萵筍跟兩斤嫩豌豆米過去,她卻說我不會買菜。她說,菜倒是好菜,可就是太老了。我說,這菜看起來多嫩,明明不老。她說,你看,是你看走眼了,你哪兒有眼睛勁兒?你根本就不會買菜,以后就別再買菜了。
有一天上午,她見我沒過去,又打電話叫我去吃午飯。我說,今兒天中午真的有事,要參加人家婚宴。她倒沒說啥,這時,我正準備拿刀削兩個洋芋,煮油鹽面條吃。
我在電腦上又處理一段文字后,起身準備做飯。我才開始削洋芋,就聽見門響。自從妻子走后,我家房門還沒被人敲過。我在想,敲門聲是不是來自我家房門,我是不是聽走耳了。再聽,是有人敲我家的門,門又不輕不重地被敲了一下。
我萬萬沒想到敲門的人會是姨妹子,她卻又不進屋,說,我就曉得你又在說假話。我只好又過去吃飯,看來,我只有在她那兒把便宜飯吃下去了。
天不覺就熱了起來,有一天,我又下鄉(xiāng)。這次在鄉(xiāng)下多待了一天,一共待了三天。昨兒天她還給我打過電話,但今兒天她就不打電話了。我打她的電話,她又不接,我就覺得有點怪。回城已是晚上了,我想先到她那兒去看看。
她的租住處屋里沒開燈,我又去看她正在裝修的房子。這兒有燈,裝修工正在忙著,卻不見她。我問她呢,裝修工說,她還是早上來過,后來就不來了。
我覺得不對勁兒,她有可能就在屋里。我又到她的住處,看見門上并沒掛鎖,可門卻推不動。她肯定在屋里,我在門外打她電話,聽見她的手機在屋里響著,可就是沒人接聽。打電話沒用,我又開始敲門,重重地敲門,大大的敲門聲把房東都引來了。房東說,今兒一大天都沒看見她了,是不對勁兒,該不會是出事兒了吧?經(jīng)房東允許,我把房門撞開了。
她在床上,臉上滾燙,人事不知。房東幫我把她攙扶到我背上,說,你趕緊送她上醫(yī)院,屋里你放心,我照看著就是。
我背著她一路小跑,直奔縣醫(yī)院急診科,先辦住院手續(xù),安排床位,給她打上吊瓶兒。
快到半夜了,她才醒過來。她一醒就笑,有氣無力地說,這是哪兒?我說,你還行,還笑得出來。她說,我也不曉得是咋搞的,下午覺得渾身沒勁兒,就睡覺,哪兒曉得一覺就睡成這樣了。我扶她坐起來,拿濕毛巾給她擦嘴。她嘴干得厲害,都干起殼了。我給她拿了一個喝水的杯子,杯里已倒了小半杯開水涼著,我又倒一點開水進去,讓她喝溫開水。她肯定渴得厲害,看,一杯開水她一氣就喝完了。我說,我去給你買點東西吃。她說,不想吃,也不餓。我說,我還是回去給你煮點稀米湯喝。她說,稀米湯也不想喝,真的,有你在這兒陪我,我簡直一點都不餓。我不曉得她咋要說這話,這話說得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可等吊瓶兒打完,她又叫我回去睡覺。這間病房沒有空床,想到明兒天早上還要過來幫她看病,我只好回家休息。
好在第二天,經(jīng)檢查診斷,她只是得了重感冒。
她出院的第二天,我們沒吃晚飯,她約我出去吃燒烤。我說,咋想起來要吃燒烤?她說,想吃,還就想瀟灑一回。
我們到河堤燒烤一條街吃烤魚,找了一個有空調(diào)的小單間。天熱,我們在喝冰凍啤酒,這是我頭一次見她喝酒。她好像能喝酒,已喝了好幾瓶兒啤酒。我發(fā)覺,她喝酒上臉,她的臉紅了起來,看起來艷若桃花,我好像就又看到了老家她家門前那棵桃樹上的桃花。我說,你是不是很能喝酒?她說,才不是呢,我只能喝一點點。我說,是不是臉上有酒窩兒的人,特能喝酒?她說,我不是說了,沒酒量嗎?呃,你跟哪些有酒窩兒的人喝過酒?我說,也就跟你喝過。她說,誰信?不行,誰叫你這樣說?要罰你,從現(xiàn)在開始,你喝兩杯,我喝一杯。我說,這咋行?我又沒多大酒量。她說,好久沒喝酒了,今兒酒一定要喝好,你就給我個面子吧,二比一,我才有勁兒往下喝啊。我這人心腸軟,只好犧牲自己,讓自己吃虧。我們又喝了不少啤酒,才走。
她好像喝多了,走路有點東倒西歪的。我們順著河堤走,要走過南大橋南橋頭,往公園走。在橋頭,我們還站了一下,看河上的夜景。這兩年,城里在河上修建了攔水蓄水的橡皮壩,流過縣城的小河好像變成了波濤滾滾的大河,又在河兩邊的河堤上搞夜景建設。每到夜晚,南大橋上下一河兩岸,總會布滿裝點夜色的彩燈。現(xiàn)在,在我們眼里,河上五花八門五光十色的彩燈好迷人,看起來簡直就像天上的銀河。看眼前的天上的銀河,我們都有點激動,她說好美好美,我也跟著說好美好美。
走到公園,她說,我差點就忘了問你,那天我是咋到醫(yī)院去的?我說忘了,她抓著我的胳膊,搖著說,我要你說。我說,當然是坐車去的。她說,不對,好像不是的,你說出來呀。我只好說,是背她到醫(yī)院的。她說,那你現(xiàn)在也背背我,我喝多了,走不動了。說著,她就趴到了我身后,看來,不背她好像又拗不脫,我只好背她。她在我背上說,長大后還從來沒人背過我,叫人背著真好。說著,她身子往上一縱,兩腿就把我的身子夾得更緊了。這時,她哪兒曉得我身上有多難過,說心里話,我都有點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當然曉得,自己要是控制不住,后面就會做出啥事來。
好不容易,我才把她背到屋,可她又不愿意下來開門,還賴在我背上。她給我鑰匙開門,在我耳邊悄悄地說,把我背到床上。我又背她進屋,到床邊,把她放到床上,但我又放不利索。她人溜到了床上,但她的兩條胳膊卻還在纏著我,又在拽我。我放在褲兜里的手機,好像又貼著我的大腿,振動了一下,這叫我打了一個激靈。我說,啤酒喝多了。她這才丟手。我不說要去解手,又哪兒走得脫身?
實際上,剛才在公園,我們就都上過廁所。一出門,我就趕緊溜了。我當然明白,再不走,自己就肯定走不了了。
過了橋,我的心才放下來。一看手機,妻子給我發(fā)了好幾條短信,還給我打過電話。這時,我就是給她打電話,也根本解釋不清,我也懶得跟她解釋了。她今年走后,一直懷疑我,怕我出軌,怕我有外遇。我多次向她保證,她好像還不信。實際上,在我心里,她根本就沒離開過我,一直還潛伏在我身邊。一想到她這多年來對我跟我們家的付出,我就不能對不起她。再說,我還向她保證過,就更不能對不起她。起碼,我要像個男人,說話算話。
奇怪的是,這之后,姨妹子就不再聯(lián)系我了。
回想起來,我們吃燒烤喝啤酒那天晚上的事,我可能沒處理好,弄得我們雙方都無比尷尬難堪。看來,只有讓時間來慢慢淡化我們的記憶。
不知不覺,熱天又往前走了一截,學校就放暑假了。
實際上,我心里還一直在等她的電話,但我就是等不到她的電話。有一天,我去她那兒看,房東說,她退房了。
她的房子當然也早就裝好了。在她裝好了的房子前,我給她打電話。她的手機提醒我說,你的電話已轉(zhuǎn)入來電提示。我給她打電話,不是想見她,是要給她說個事,就是她女兒轉(zhuǎn)學的事。盡管自從在老家她跟我說過一次后就一直沒再說過,可我還是沒忘記這事。我想不給孩子轉(zhuǎn)戶口,看能不能把這事辦成。也是事有湊巧,我大學畢業(yè)頭幾年曾在縣教育局工作過,原來的一個老同事后來一直在縣實小工作,是財務主管。財務主管是內(nèi)當家,我就找他幫忙。我跟他說,不管你想啥辦法,你都要保證幫我把這事辦成。學校放暑假前,他給我打電話,叫我一開學就帶孩子來報名。這兩天,我就急著要給她說這事,可現(xiàn)在又打不通她的電話。難道她是跟我說著玩的,又不想給女兒轉(zhuǎn)學了?我打算既不等她的電話,又不再給她打電話了,只當自己沒事找事,做了一次蠢事。
妻子在江蘇張家港一家工廠做工,說要到年底才會回來。
有一天凌晨,我從敲門聲中醒來。天還沒亮,我走到門邊,卻又不敢開門。這時,放在床頭的手機又響了,我又進臥室去接電話。是妻子打來的電話,我問她在哪兒,才曉得她隔著門板給我打電話。妻子突然回來,我差點都認不出她了。她黑了瘦了,但看起來倒好像更年輕了。我說,你回來也不打個電話?她說,就不打電話。
這天,妻子說起她一個叔伯妹妹請我?guī)退呐畠恨D(zhuǎn)學的事。我說,我搞不清你有好多妹妹,你說的是你哪一個妹妹?她說,就是清明前你進山掛青時,請你幫她女兒轉(zhuǎn)學的那個妹妹。我說,這我倒是想起來了,是有這事,但這事又不大好辦,還沒辦好。她說,不會吧,你是不是在哄我?我說,你曉得,我素來不哄人的。她說,那你趕快去辦,看不給她女兒轉(zhuǎn)戶口行不行。我說,你咋曉得這事?她說,我那個妹妹,她男的在我做工的那個廠管事,最近她下去玩,跟我說的。我說,呃,你那個妹妹,我的姨妹子,她到底叫啥名字?妻子卻說,我也不曉得她的名字,咋的,你到現(xiàn)在也還不曉得?頓時我就一愣,我不曉得妻子是不是說,我跟姨妹子交往時間不短,應該知道她的名字。看來,妻子還是知道一些我跟姨妹子交往的事。那么,妻子是不是早就有心,才讓姨妹子在她去張家港后照顧我的生活?這又是不是就是妻子為了考驗我才給我做的一個局呢?還有,我那個姨妹子,其實她早就曉得她姐姐外出,起初,她只是想試探試探我,但后來她是不是就春心萌動,也想嘗試一下呢?
其實,我到現(xiàn)在都還不曉得姨妹子的名字。后來,我也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就有這樣一個姨妹子,她山里老家門前有一棵一到春天就開滿桃花的桃樹?我們是不是真在一起扳過筍子,摘過茶葉,打過麻將,還喝過酒呢?那晚喝酒后,我是不是就趁著酒興,還背過她呢?而這一切又好像根本就不存在,我越想越糊涂,好像正從一個開滿桃花的桃色夢中醒來。
責任編輯: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