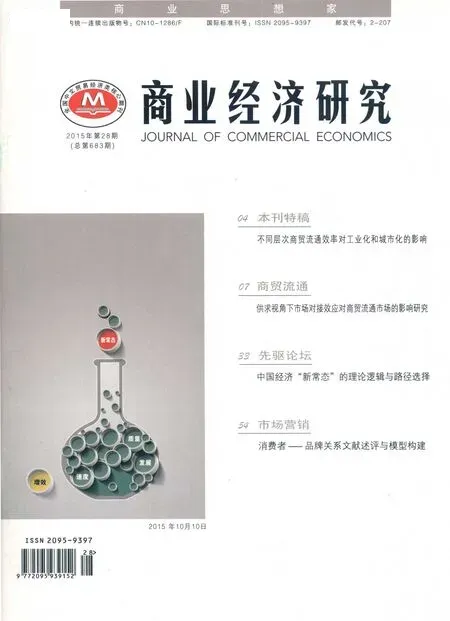區域金融中心發展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 宋儒君 博士后 張座銘(、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北京 00083、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武漢 430074)
紐約金融中心發展經驗
(一)金融集聚優勢
一方面,紐約在美國具有較強的金融聚集優勢。縱向而言,1997年紐約金融業在全美金融業產值中的占比接近20%,隨后這一數字雖有下滑,但2003年后,紐約金融業在全美金融業中的地位又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與提升。橫向而言,美國現有50個州,而近10年來,紐約州金融業產值在全美金融業產值中的平均占比卻已達15.29%,與其它州相比,紐約金融產業的優勢不言而喻,雖然美國一共有50個州,但金融較發達的六個州的金融業總產值已接近全美金融業總產值的50%。其中,金融最發達的紐約州的金融業總產值更是高達16%。
另一方面,美國的國際資本集聚優勢突出。美國的國際資本流動率較高,資本流入量逐年攀升。以證券市場上非美國股的成交情況為例,1980年至2006年期間,紐交所非美國股票的成交額與成交比重大幅上漲,其中,非美國股票的成交額占比一度于2000年達到了10.8%。
(二)金融創新能力
自紐約金融中心建成以來,紐約金融業的從業人數及其人均收入大幅增長,截至2011年,紐約金融業從業人員人均收入達到了紐約人均收入的2.11倍。事實上,自2000年開始,紐約金融業人均收入一直維持在紐約整體人均收入的2倍以上,這一數字在2006年甚至高達2.63,金融業在紐約的行業領先地位一目了然。在紐約現有人均工資水平較高且增勢明顯的背景下,大量人力資本會流入其中,充足的人力資本為人才隊伍的建設奠定了基礎,而金融業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支撐。金融產品的設計、銷售等環節對創新的要求較高,創新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金融競爭力,人才的支撐則為創新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三)監管制度完善
起初,美國政府制訂了一系列資本管制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限制資本外流,具體包括對外信貸限制、利息平衡稅等,這些政策在保護國內現有資本的同時也阻礙了國際資本的流入,歐洲美元市場應運而生,在此期間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受到了嚴重制約。基于此,美國政府隨后陸續取消了原有的部分管制制度,例如,1974年原有的資本管制政策得以廢除,1982年對存款利率進行管制的Q條例被正式廢止等。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金融市場的自由化程度進一步加深,2006年初美國政府組建了以華爾街高管為主體的資本市場監管委員會以改善上市業務流失現狀;2009年起在美外國公司可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制作財務報表,美國會計制度不斷國際化。
倫敦金融中心發展經驗
(一)金融集聚優勢
倫敦金融中心擁有的外國金融機構的數量占其所有金融機構總量的70%以上,這與1986年以及20世紀90年代末倫敦金融市場的兩次“大爆炸”密不可分。1986年的金融大爆炸加速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開放的競爭環境得以形成,政府對內管制也有所放松,隨后,以監管方式改革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次大爆炸的出現,分離了英格蘭銀行的監管職能,逐步將所有金融監管職能集中到英國金融服務局。經歷過兩次改革后的英國具備了良好的開放競爭環境與高效的監管體系,因此歐洲大陸乃至全球的金融機構都傾向于在英國設立分支,而倫敦作為英國最大的金融中心,金融服務業的增加值一度高達全國的近40%,伴隨著倫敦金融服務業的不斷發展壯大,其增加值對英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斷攀升,并于2004年達到18.89%。
(二)創新人才集聚
英國絕大多數的金融人才都聚集在了倫敦,2004年,英國金融業從業人員的數量大約達到了108萬人,而其中近30%的從業人員都集中在倫敦,這一數字自1999年開始便呈現出了明顯的上漲趨勢,盡管在蕭條期有所下滑,但整體受經濟蕭條的影響并不大。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署的相關數據顯示,2004年倫敦人均創造的增加值,即人均GVA為2.63萬英鎊,而倫敦金融業的這一指標達到了約11萬美元,為倫敦人均GVA的四余倍,倫敦金融業的人均GVA同樣遠遠多于英國的人均GVA。發展至今,英國的金融業基本形成了以倫敦為金融中心的產業集群,近一半的英國金融企業集聚在了倫敦,倫敦金融中心的優勢不言而喻。
(三)監管制度高效
英國對金融業的管制與美國、日本等國家相比都更為寬松,其對國內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限制并不多,對國外分支機構的管制也較少,國際化程度極高,僅在1974到1984的10年間,倫敦所擁有的外國銀行數量就上漲了60%。隨后的兩次“大爆炸”更是進一步寬松了英國政府與金融服務業的管制。另外,政府為了保護倫敦金融市場的獨立性,于2006年底通過了“投資交易所和清算公司議案”,該議案賦予了金融服務局控制交易規則變動的職能,保障交易規則不在不合理的范圍內進行變動。

圖1 1980-2006年英國復合稅率變化趨勢
現有研究用復合稅率,即財政收入與GDP的比率來衡量金融管制的強弱變化。英國的復合稅率水平相對穩定(見圖1),一直維持在26.5%上下,這一方面反映出了英國經濟制度的變化程度較小,另一方面也凸顯出了長期以來英國經濟制度的完善性。
新加坡金融中心發展經驗
(一)政府主體推動力量
不同于全球其它國際金融中心,新加坡金融中心從建成開始政府就發揮了極大的輔助作用。不可否認的是,在政府的積極干預下,新加坡的整體經濟確實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其對內嚴格管制對外放松的監管模式也獨具創意,然而時至今日,政府是否應該繼續在金融中心的發展過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這一點還有待探討。但是,在新加坡金融中心成立后的十余年里,政府的一系列改革對加速金融中心發展而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無可厚非的。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東亞太地區經濟增長迅速,新加坡在這10年間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近1.5倍,國際投資需求旺盛。面對如此好的發展機遇,新加坡政府于1968年廢除了離岸外幣存款利息稅,此舉吸引了大批有意從事離岸借貸業務的跨國銀行在新設了分支機構,這也是新加坡政府為建立新加坡金融中心邁出的第一步。1970年后,新加坡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構建內外分離的金融體制,在不斷加強國內市場建設的同時,不斷深化外部市場的金融自由化程度。
(二)銀行業的雄厚實力
現有研究普遍采用資產收益率(ROA)來衡量銀行業的經營效率,資本收益率(ROE)來衡量銀行業的經營績效。新加坡一直具有穩健的法律環境,加上其本就具備的優越地理環境,新加坡銀行業市場極具優勢。但從新加坡銀行業的資產收益率與資本收益率來看,近年來其資產收益率指標的波動更為穩定,而資本收益率卻在10%到20%的區間內有一定幅度的波動,由此可以反映出新加坡政治經濟環境的穩定性。相比較而言,同樣作為亞太地區主要金融中心的中國香港金融中心,其銀行業的資產收益率和資本收益率普遍低于新加坡,1990至2004年,香港銀行業的平均資產收益率大約為1.06%,而同一時期新加坡銀行業的平均資產收益率達到了1.29%。
結論與啟示
(一)不斷創新金融監管模式
紐約金融中心是全球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其最大的競爭優勢莫過于金融創新能力。現有研究普遍認為創新能力的提高需要依托專業人才的支撐,以及相對寬松的金融監管模式的配套,在此僅就監管模式進行探討。
對比我國與美國、英國等金融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條例發現,我國金融條例重在強調金融機構允許采取的各種行為,未指明允許的都是禁止的,相反的,國外的金融條例重在強調金融機構禁止在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行為,未指明禁止的都是允許的。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后者更利于激發金融市場的活力,前者限制了金融機構的行為,抑制了金融機構的創新動力。政府管制在紐約、東京以及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相對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的過多干預極大的影響了紐約金融中心的正常發展,導致紐約金融市場流失了大量的業務,而東京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經濟泡沫的產生,擴大了東京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金融中心的差距,新加坡政府目前對其金融市場的管制并未對其造成十分明顯的影響,但其對內嚴格管制、對外放松管制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二)加快宏觀經濟發展速度
宏觀經濟的高速增長是金融中心成立并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成立之初,該地區經濟正處于高速增長期,而紐約金融中心贏得全球霸主地位之時其經濟也處于戰后的高速增長期。經濟增長直接決定了金融中心的未來,從個人的角度而言,經濟的高速發展可以提高其收入水平,刺激其投資理財的需求;從企業的角度而言,經濟的高速發展可以擴大企業的發展空間,通過為企業提供相應資金等需求擴大企業規模進而進一步促動經濟增長;從國家的角度而言,經濟的高速發展有利于穩定一國的國際地位,為國家營造安全穩定的經濟環境,提高大型跨國企業的入駐率,帶動本國企業的發展。
(三)注重控制政府干預力度
政府在有些金融中心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發展進程中,政府的推動與引導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放眼紐約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政府的干預卻更多起到的是抑制其正常發展的作用。不同于金融監管部門,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金融中心的發展離不開一個相對寬松、法制健全的大環境,而這需要依托政府政策才能實現,但是政府的干預力度必須適中。
在金融中心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提供金融中心發展所需的輔助政策、營造寬松的經濟環境以及防范金融風險。英國政府一直采取較為寬松的經濟政策,紐約政府在意識到寬松經濟環境的重要性后也逐步放寬了對金融的管制,歷史經驗證明了政府制定相應政策適當放松經濟管制的重要意義。另外,政府作為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在監督金融業發展的同時,還應當監督金融監管部門并對其職能進行調整以保障監管效率,提高金融市場的安全系數。縱觀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發展歷程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盡管政府的干預力度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政府勢必需要對金融中心的發展予以充分關注。
(四)加大人才引進培養力度
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的發展都需要充足的專業人才,對金融產品、交易方式、管理模式等的創新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以滿足客戶多樣的需求,擴大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的規模。具體而言,政府需要在加大對現有人才的培養力度的同時,提供多種優惠政策吸引國際人才的進入。一方面,政府需要設立人才專項培養基金,有針對性的對現有金融人才進行培訓,為高級人才提供出國深造的機會,為中高級人才解決生活所需,防止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政府需明確金融市場的人才需求規模,有針對性的引進國際專業人才,努力培養精通金融、保險、債券等的復合型人才,建立靈活的人才流動機制。
1.陳崴.倫敦—世界金融之都[J].金融經濟,2004(10)
2.劉仁伍.區域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證研究[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
3.劉桂榮,徐靜.國際金融中心的實證研究及其對上海的借鑒[J].上海商業,2006(Z1)
4.陸紅軍.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評估研究[J].財經研究,2007(3)
5.王傳輝.國際金融中心產生的模式比較研究及對我國的啟示[J].世界經濟研究,2000(6)
6.游碧蓉.透視國際金融中心的百年變遷[J].亞太縱橫,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