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zhèn)舊人(三題)
俞贊江
小鎮(zhèn)舊人(三題)
俞贊江
竹器爛眼
農歷五九,照例是小鎮(zhèn)的集市。天還沒亮透,十里八村的農民們便挑籮夾擔涌到老街,忙不迭地搶攤占位。而光德橋下的河埠頭,早已橫七豎八拴滿了各類船只,一捆捆、一壇壇貨物源源不斷被卸下來。漸漸地,在攢動的人頭和此起彼伏的叫嚷聲、吆喝聲中,小鎮(zhèn)上演了一幅氣勢恢宏的清明上河圖。
舊江口集市南起老街南口,北至光德橋,爛眼和他的竹器攤是整個集市一道耀眼奪目的風景。
記憶中的爛眼,宛若兒童畫里紅著眼圈的滑稽人物,大約三十多歲,高個偏瘦,姓啥名啥無人知曉,他的雙眼因何而爛、爛了多久、爛的程度均無從考證。那年月全鎮(zhèn)老少都這么喊他,四鄰八鄉(xiāng)的農民也這樣叫他。幸好爛眼爛的是眼眶,未爛及眼球,不影響視力。
爛眼獨家經營竹器,品種琳瑯滿目,竹籃、竹帚、竹簍、竹匾、竹篩、簸箕、谷籮、食罩、蒸籠……應有盡有。常客們有經驗,說挑竹器時應盡量低頭,避免與爛眼的目光對視,不然你的眼睛立馬也會火辣辣,然后忍不住用手揉,揉著揉著說不定自個兒也變成了爛眼。爛眼的攤位固定在光德橋南頭往庵弄街拐口,此位置乃爛眼深謀遠慮的結果,首先它是橋頭堡,占領著集市的制高點,幾乎有著萬眾矚目的效果;其次,背面是東西向的塘墩(攔洪堤壩)大道,能進能退,有利于逃跑。為什么要逃跑呢?全因為爛眼這行當,用當下話說,叫攤販,但不流動。可爛眼的根子就出在這個“販”字,販即販賣,指買進賣出,那年代叫投機倒把,這是資本主義的尾巴,社會主義是絕對不允許的,必須毫不留情割掉。誰來割?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簡稱“打辦”,即今天工商所的前身。
“打辦”地處老街南口,門面朝西,約三間屋面寬,臨街隔著一排木格子玻璃門,里面的舊地板踩著總會發(fā)出“吱嘎吱嘎”難聽的聲音。每逢有“投機倒把分子”被抓,玻璃門外總趴滿大人與孩子,膽戰(zhàn)心驚又無比好奇地偷窺里面的人被訓斥、被毆打的情景,而不幸的爛眼是“打辦”的常客。“打辦”的一把手叫老應,這位操蘇北口音的老干部,儼然小鎮(zhèn)里制裁投機倒把的最高法官,與爛眼是一對水火不相容的冤家。老應管爛眼,是履行本職工作;爛眼要生存,就挖空心思搞“投機倒把”。天長日久,人們就把他們的關系喻作“老鷹抓小雞”,老應成了老鷹,一只犀利兇猛的老鷹。
老鷹初識爛眼很偶然。那天農歷廿五集,老鷹佩戴著“打辦”的紅袖章,開始常規(guī)巡查。老街南頭到北頭,全長僅兩百米,但這會兒,趕集的人流擠得老街水泄不通,老鷹走在逼仄的街頭,又要逐攤掃描,速度慢得像蝸牛。沒等老鷹查完半截老街,“老鷹來了”的消息已像擊鼓傳花,老早傳遍各個攤位。待老鷹查到庵弄街拐口時,突然發(fā)現(xiàn)一個雙眼潰爛的陌生攤主正扯著嗓子起勁叫喊,面前擺著五花八門的竹器,數(shù)數(shù)足有一百多件,并且一人搶了三個攤位。像是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老鷹雙眸發(fā)光,異常興奮。

“這哪里來的?”老鷹咄咄逼人。
“自家編的。”爛眼不慌不忙。
“誰編的?”老鷹窮追不舍。
“阿拉老婆與我。”爛眼略顯緊張。
“胡說八道!”老鷹怒不可遏。
“我說謊,你挖掉我眼睛!”爛眼信誓旦旦。
“我不要挖你的爛眼,要這些……全部沒收!”老鷹一錘定音。
爛眼不知所措,木然呆立了一會兒,突然蹲下來嚎啕大哭。哭了許久,直到隔壁打鐵店“叮叮當當”的聲音把爛眼的哭聲完全淹沒。由于初來乍到,不諳市面行情,還對相鄰攤主的勸告置若罔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爛眼為自己的莽撞付出了沉重代價,悔之已晚。
爛眼第二次來集市,臉上平添了幾道傷痕,據(jù)說是那次回去被潑婦老婆抓的,老婆把對老鷹的滿腔憤懣一股腦撒在爛眼身上。爛眼底子忠厚,向來怕老婆,每次賣完竹器的錢,如數(shù)上交,一分不漏。那次在“打辦”,老鷹要求爛眼在保證書上立誓:往后每次來集市最多賣十件,超出就算投機倒把,全部沒收。因為老鷹十二分斷定爛眼的竹器是從別處販來的,而爛眼死不認賬,一口咬定是自家編的。由于證據(jù)不足,老鷹只能從數(shù)量上壓制爛眼的投機倒把行徑。吃一塹長一智,爛眼這次變聰明了,大清早就把運來的竹器全部藏到后面的公共廁所里,然后取十件,賣十件,攤面上始終保持十件。老鷹巡查到此,瞅瞅爛眼和他的十件竹器,頗感滿意,放心而去。
爛眼偷藏竹器東窗事發(fā),是在瞞天過海歷經數(shù)個集市之后。有人搞惡作劇,把爛眼藏在男廁所的竹器扔到了隔壁女廁所,爛眼賣完了手頭的竹器,見此情景,火冒三丈,罵罵咧咧闖進女廁所,不想驚嚇了拉屎的女人。女人大喊抓流氓。“打辦”老鷹聞訊趕來,真相大白,氣得老鷹當場就把剩余的竹器全部踩扁,末了,還把爛眼捆成粽子押到“打辦”,暴打了一頓。
懾于老鷹的強大威力,爛眼開始誠惶誠恐,每次來集市如驚弓之鳥,東躲西藏。公共廁所已毫無安全可言,老鷹每次到爛眼攤前,必先直奔廁所。道高一丈,魔高一尺,爛眼這個“不倒翁”,不久又發(fā)明了對付老鷹的好辦法。
夏秋兩季,剡江堤壩兩側長滿茂盛的蘆葦,爛眼把竹器藏匿在一望無際的蘆葦叢里;冬春兩季,沒了蘆葦,爛眼就把竹器寄藏在庵弄街幾戶老太太家里,照舊上演著取十件、賣十件的老把戲。那年代,同情爛眼的人多,幾乎沒人會做奸細,爛眼得到了群眾的暗中保護,如魚得水。目睹爛眼如此安分守己,老鷹起初半信半疑,還故意殺了幾次回馬槍,但均一無所獲。老鷹信以為真,從此徹底死心,最后甚至把爛眼列入免檢對象。
1977年以后,集市上的人們漸漸發(fā)現(xiàn),老鷹已對類似的“投機倒把”行為開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形勢在悄悄地發(fā)生著變化。1978年秋天,爛眼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叫工商所的全新機構完全取代了“打辦”,這一年,老鷹也光榮退休,爛眼預感到屬于他的春天要來了。
小剃頭董山
小鎮(zhèn)剃頭店原先在老街南口,與威風凜凜的“打辦”對頭對腦。店內又舊又臟,人多時,地板吱吱嘎嘎的叫喚聲聒噪得厲害;天花板上積滿陳灰與蛛網,冷不防掉下一團,剃干凈的頭發(fā)常得返工重洗——這環(huán)境頂天立地都糟糕。為此,公社在南街南側新蓋了一長溜樓房,郵電所、稅務所、剃頭店啥的都搬過來了。新剃頭店寬敞亮堂,人氣興旺,剃頭師傅也驟然增加到十位,董山就在這個新舊交替時刻被招入剃頭店。
這年董山才二十歲,來自大山深處一個叫董村的地方。里山人說話聲調曲里拐彎,像裊裊炊煙,加上董山個頭一米六不到,讓人過目不忘。沒多久,這位剃頭店新來的“里山童工”便成了鎮(zhèn)上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由于剃頭店在小鎮(zhèn)屬于獨家,而且又是集體單位,董山無疑捧上了令人艷羨的鐵飯碗,相當于一步跨入了工人階級行列,那年頭,工人的地位可要比農民強百倍。
剃頭學徒期規(guī)定為三年,這三年里,在論資排輩的師傅們面前,董山是名副其實的矮人三分,干重活臟活是他的分內事,比如每天提前開店門、買煤球、生煤灶、扒煤灰、掃頭發(fā)、挑河水等等。但董山的主業(yè)還是剃頭——“雖是毫發(fā)手藝,卻是頂上功夫”,剃不好頭,雜活干再多,也是不討師傅們好,不稱顧客們心。也許生長在山旮旯里,沒見過多大世面,董山總顯得木乎乎,笨兮兮,師傅們一年調教下來,董山剃頭技術的進步微乎其微。
董山盡管個子矮,卻長著寬肩厚背,挑起水來健步如飛,可能里山人打小挑慣了柴擔,也被柴擔壓扁了骨骼。在剃頭店,缺電不怕,就怕缺水,缺了水,顧客不能洗頭,剃頭店就得癱瘓。那時沒自來水,全靠人力一擔擔從河里挑來。
鎮(zhèn)西有條小河,通過碶閘流向剡江。剡江有潮汐,小河水一日兩次漲落,董山總在退潮前去小河挑水。剃頭店的兩口大缸安放在后門露天平臺上,平臺離地面兩米半,董山每天“嘿喲嘿喲”從兩百米外的小河挑來水,還要邁上十多級臺階,方能倒進缸里。挑滿這兩大缸水需要18擔以上,每天18擔,每月就540擔,每年至少6500擔,這可是個天文數(shù)字,彰顯了董山驚人的蠻力與毅力。董山歷經兩年挑水,矮個子進一步定型,身材也愈發(fā)像水桶般粗壯。
挑水雖無技術含量,但也需動腦子,就像學剃頭,腦子不轉動,技術就差勁。董山挑水總是清濁不分,挑來的多半是渾水,往往沒過幾天,缸底就積滿厚厚的泥漿,一到傍晚,黃泥漿水就從洗頭盆的水龍頭汩汩流出,剃頭店的毛巾越來越黃,顧客們的頭越洗越臟。這時,師傅們必定大呼小叫,隨即劈頭蓋臉罵起董山來。罵多了,董山也習以為常,里山人一根筋到底、認死理的毛病就犯了——權當沒聽見,挑水時繼續(xù)我行我素。
每位剃頭師傅的技術與風格都不同,顧客們挑誰剃頭,就如蘿卜青菜各有所好。鑒于董山的剃頭技術遲遲沒有長進,挑他剃頭的顧客寥寥無幾,除非顧客們瞎了眼。很多時候,師傅們忙得要命,董山卻落得清閑。當然越清閑,董山的技術越不會進步。
那年,小鎮(zhèn)突發(fā)“紅眼病”,街上一下子冒出大批戴墨鏡的“紅眼人士”,人們談紅色變,卻又對此束手無策。由于廣泛接觸各色人等,剃頭自然成為高危職業(yè),沒多久,店里有六位師傅不幸感染了“紅眼病”,陸續(xù)戴上了墨鏡。剩下的四位,包括董山,瞬間成為香餑餑,顧客們爭先恐后找他們剃頭求安全。非常時期的董山主要負責給小孩子剃頭,由于小孩們對剃頭技術要求低,也不用講究美觀啥的,董山意外獲得了施展身手的良機。
那時剃頭基本用手軋?zhí)甑叮幌瘳F(xiàn)在用的電推刀既省時又省力——這就考量剃頭師傅的手上功夫是否細膩。董山的剃發(fā)水平很糟糕,沒有從短到長的自然過渡,剃得著的地方,剃得光光的;剃不著的地方,該多長還多長——“鍋蓋頭”發(fā)型就此形成。“鍋蓋頭”本是剃頭初學者經歷的最原始階段,論年限,董山早該度過了這個階段,可事實上董山愣是邁不過這道坎,他缺乏剃頭天賦,捧這飯碗實在是陰差陽錯。
那些天,小鎮(zhèn)里滿街跑著剃“鍋蓋頭”的孩子,這如出一轍的版本,地球人都知道是董山的“杰作”。目睹街頭這一道道怪異的風景,董山反而感到神清氣爽。
是做個碌碌無為的剃頭匠,還是做個出類拔萃的美發(fā)師,師傅們不止一次開導董山。空余時,他們還張羅著為董山做媒,可惜都因董山個子矮小、手藝蹩腳,被姑娘們婉言謝絕。后來師傅們灰心了,董山也泄氣了。幾年時光悄悄流過去,董山漸漸淪為大齡青年。
每天的日子就像董山挑的18擔水,機械重復,平淡乏味。每當水桶沉得晃晃悠悠時,董山總會異想天開,俺每天這么辛苦地挑,說不定哪天就感動了龍王,龍王派兩位水神每天給俺灌滿兩大缸……沒過幾天,董山真的做了件感天動地的大事,讓他一下子變成了平民英雄,剃頭店里的人都始料未及。
那天早上,北風呼嘯,氣溫降到零下,小河也破天荒結了冰。董山搓著雙手,照例來到河埠頭挑水,兩桶水剛舀滿,正待上肩,突然,不遠處一位砸冰的老漢“嘩啦”一聲掉進河里,老漢不會游泳,在水里拼命撲騰。在這千鈞一發(fā)之際,“旱鴨子”董山用腳踢翻桶水,抱起兩空木桶,毫不猶豫地跳下去,一邊拉住下沉的老漢,一邊將其中一只木桶塞給他,死拉硬拽,終于把老漢弄上了岸,兩人都凍得幾乎昏厥過去。
幾天后,一個陽光煦暖的日子,老漢的子女們敲鑼打鼓給董山送來了大紅感謝信。感謝信就張貼在剃頭店大門外墻上,前來圍觀的人里三層外三層,小鎮(zhèn)里爭相傳頌著董山的美名。從此,店里所有的師傅對董山刮目相看,董山再也不用挑水了,有人接過了董山的擔子。鎮(zhèn)上的人們開始熱衷于找“英雄”董山剃頭,這讓董山的剃頭技術突飛猛進。至于董山的個人問題是否水到渠成,這是后話,暫且不提。
陸軍連長
陸軍連長姓陸名軍,少年時是我形影不離的伙伴之一。陸軍上有哥姐一大串,排行最末端,父母哥姐對他寵愛有加。興許是愛之過急,大補過頭,物極必反,陸軍長得又矮又瘦,民間俗稱“僵個貓”。但濃縮的往往是精華,陸軍的生相活絡靈巧,滿腦瓜都是鬼點子。
其時班上風靡陸戰(zhàn)棋,陸軍對此情有獨鐘,每天找人對弈,樂此不疲。有同學封他為小“工兵”,他極不服氣,認為這是有意貶低他,公開宣稱自己適宜做連長,說大凡連長都腰挎威武駁殼槍,率兵打仗沖鋒在前,電影《南征北戰(zhàn)》里的張連長、《渡江偵察記》里的李連長統(tǒng)統(tǒng)是他崇拜的偶像。自此,“陸軍連長”這個名號當仁不讓地在小鎮(zhèn)叫響。
戰(zhàn)爭片看多了,各種打仗的驚險偷襲場景便爛熟于心。可惜陸軍連長生不逢時,和平年代再也沒有戰(zhàn)爭機會,他這輩子注定要英雄無用武之地了。但陸連長不會如此善罷甘休,他開始搜尋現(xiàn)實生活中驚心動魄的“戰(zhàn)爭”事件。
有一次,經過偵察,他發(fā)現(xiàn)孤老頭“老酒壺”的莊園里長滿了橘子,可是莊園里戒備森嚴,四周雖沒圍墻,卻栽著高大厚實的荊棘,別說人鉆不進,野貓見了也肯定退避三舍。莊園西端是一棟古舊的樓房,白天的“老酒壺”要么瞇縫著雙眼,紋絲不動坐在屋檐下;要么手握酒壺,細酌慢品,居高臨下看護著莊園里的一草一木。這陣勢,一般人很難找到下手的機會。陸軍連長的老鼠眼滴溜溜轉了三天,辦法就來了。那天黃昏,連長從家里偷偷背來把大鐵剪,讓我遠遠望風,自己匍匐前進,慢慢靠近刺蔓,像排雷一般,小心翼翼剪開一個大窟窿。我倆一前一后爬進神秘的莊園,只見里面種滿了花花色色的菜蔬豆莢,四邊的橘樹上掛滿了金燦燦的橘子,橘香撲鼻。屋檐下竟不見“老酒壺”的身影,大概正是“老酒壺”進屋做飯時刻。我們分頭散開,手腳麻利地摘了一大堆金橘,裝進兩只書包,然后又從窟窿原路返回。不過陸連長并沒有馬上撤離,而是折轉身,對那窟窿作了精心修補,直到看不出異樣。事后我得知,選擇這個時候行動,是他事先踩點和縝密分析的結果,我不由得深深折服于陸連長的膽魄與睿智。
小鎮(zhèn)東隅有一條蜿蜒曲折的小河,河邊點綴著碎片般的蘆葦叢,河東屬新塔村,河西屬江口村。這條小小界河在那些年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沿岸遍布戰(zhàn)壕和陷阱。兩村孩子隔三岔五在此展開“游擊戰(zhàn)”,河面上常常是泥巴彈漫天飛舞,河兩岸喊殺聲震天價響,雙方覬覦的目標不外乎各自田野上的農作物,一方要捍衛(wèi),一方要破壞。這里是陸軍連長大顯身手的舞臺,由于率領小伙伴們屢立戰(zhàn)功,大家集體表決,一致同意授予他為“戰(zhàn)斗英雄”稱號。
盛夏午后,被烈日炙烤著的農作物毫無生氣,知了在河邊的柳樹上不知疲倦地嚷著嗓子,兩岸一片靜寂。對面“敵方”的田野上是一望無際的番茄地,數(shù)不清的殷紅果實在萬綠叢中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強烈的視覺沖擊與強大的饑餓感,讓我們垂涎欲滴。我們曾無數(shù)次想象在“敵方”番茄地里酣暢淋漓地偷摘番茄,就像溜進神秘的伊甸園偷摘五顏六色的禁果一般,那是多么激動人心的場景!這個酷熱的午后,這個連鬼都不敢出來的時辰,無論如何該“偷襲”了——我與陸軍連長決定游過小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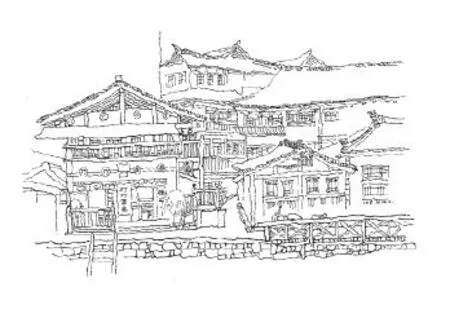
我們四下里偵察了五分鐘,確信沒人,就刷刷脫掉汗衫褲衩,又把汗衫卷起叼在嘴里,赤條條下河,眨眼游過五六米寬的小河,像野狗一樣爬上河東岸,一頭撲進番茄地。綠色的藤蔓上綴滿了誘人的紅番茄,兩顆小心臟像闖進了兩只小鹿,“突突突”地亂蹦亂撞。我們喘著粗氣,貪婪地挑選著最大最紅的番茄。各自摘了十多顆后,我們把汗衫的領袖口用細草繩扎住,充當布袋,裝入番茄。然后一個猛子扎進河里,一手劃水一手托舉著番茄,吃力地游到岸邊。剛跌跌撞撞上岸,還來不及穿上褲衩,分享成功的喜悅。突然間,河東岸罵罵咧咧跑來一老太婆,仿佛引爆了顆定時炸彈,剎那間天崩地裂。
“快跑啊!”我驚慌失措,邊催促陸連長,邊扔掉番茄,光著屁股,狼狽地奔逃起來。等我氣喘吁吁跑了一段路回頭看,卻見陸軍連長壓根兒沒跑,仍然站在原地,并向對岸的老太婆一個勁地討好:“阿婆,我真的沒偷過,是他在偷,你看——他逃了。”邊說邊把我娘的工作單位和姓名一股腦兒泄露給了老太婆。
一個在逃;一個沒逃,并勇于檢舉揭發(fā)——老太婆馬上信以為真,隨即和顏悅色,大夸陸軍是乖孩子。然后繞過河來,撿起地上的番茄,屁顛屁顛趕去我娘單位告御狀。我自知闖了大禍,磨蹭著不敢回家,那一刻,我對紅番茄的美好印象早已土崩瓦解。天黑后,才鼓起勇氣怯生生溜進家門。我受到了娘的嚴厲呵斥,有沒有受皮肉之苦,卻已記不清了。
事到如今,我都搞不懂陸軍連長為何要出賣我,因為當時他完全有時間選擇逃走,而且我們與老太婆素不相識,更何況她在河對岸顛著小腳,插翅也飛不過來。我不禁懷疑陸軍骨子里天生就藏著一種叛徒基因,一旦遇上合適時機立刻原形畢露。
自此,我與陸軍的友情一刀兩斷。我甚至惡狠狠地想,要是在戰(zhàn)爭年代,我非一槍崩了這個“叛徒”不可。若干年后,我舉家遷徙城里,他音訊全無。后來,我聽鎮(zhèn)上同學說,十八歲那年,他得重病不幸夭折,我聞訊,扼腕嘆息:這世上少了一位連長。

